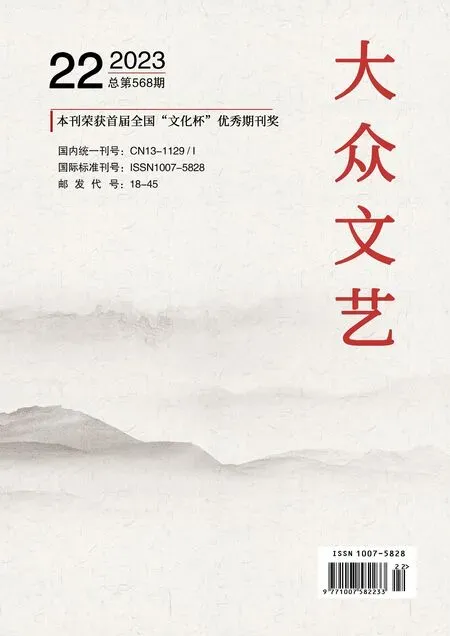爱情视角下《紫钗记》与《被盗走的幸福》戏剧人物矛盾人格情理冲突比较*
2023-02-16彭程
彭 程
(东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紫钗记》与《被盗走的幸福》描写的都是爱情故事,其男女主人公在爱情驱使下人格呈现出矛盾现象。《紫钗记》是汤显祖的第一部作品,描写霍小玉与李益感人的爱情故事,霍小玉是汤翁创造的“情痴”典型。剧中小玉灞桥送别李益并再邀盟誓;为探听丈夫在边关的消息,慷慨解囊资助韦崔二人;为访求李益消息,忍痛割爱变卖首饰燕钗。以上无不体现出霍小玉对李益爱情的真挚、专一,但剧中很多细节透露出小玉依旧恪守着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教条规则,映衬出其矛盾人格下形成了对丈夫的“情”与程朱理学之“理”的情理冲突。《被盗走的幸福》是乌克兰著名戏剧家伊凡·弗兰科的佳作,剧中安娜深爱着米哈伊洛·古尔曼(以下简称为古尔曼),但在丈夫米科拉面前,为了顺应封建婚姻制度的规范,生活中她不得不完成作为妻子的义务,这也突显出其矛盾人格,安娜对古尔曼的这种爱情的“情”和当时封建婚姻制度的“理”产生了情理冲突。此外,《紫钗记》男主人公李益在爱妻霍小玉面前,原本懦弱的人物性格,却刚强起来,敢于反抗封建强权;《被盗走的幸福》男主人公米科拉,在妻子安娜面前,能容忍情敌古尔曼的无理侵扰等,都与爱情下的矛盾人格心理有关。
一、两剧主人公的矛盾人格与爱情
首先,让我们对“人格”和“矛盾人格”的概念给予界定。“人格”(Personality)这一词源于拉丁文“Persona”其意指面具、脸谱是“个体在遗传素质的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和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1]”对其还可解释为:“人格”意指“个体公开的自我,或者说是一个人在公众与社会中的形象。[2]”“矛盾人格”可理解为:每个人要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就会装扮自己,戴上脸谱或面具去生活,将真实的自我的某些部分隐藏起来。这样个体就有两种状态:在“面具”下的内在状态和作为“面具”的外在状态,二者之间的差异就构成人格的双重性和矛盾性,即人格的内在状态与外在状态的不一致,以及这两种状态中的各自矛盾的内容的交叉对立。关于人格动力弗洛伊德认为本能或驱力(drives)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本能具有生物性、原始性和无方向性,而平时所说的动机(motive)是有方向的。弗洛伊德曾对冲突作过研究。精神分析学家们强调的动力潜意识与动机、冲突等重要特性相联系。希弗立(H.Shevrin)指出,潜意识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
《紫钗记》与《被盗走的幸福》中的男女主人公,他们的人格都受其爱情的影响,做出了爱情与封建礼教相矛盾的人格举动,从而诠释出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倾向。《紫钗记》的历史背景是:程朱理学对宋明文化影响深远,理学将“天理”当做是世间万物的道德标准,世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男尊女卑都当应当遵循天理。对于男女地位,理学规定“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倡随之礼,此常理也。[3]”在这种封建礼教的桎梏下也就不难解释在剧中开头对小玉的描述给人的印象便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闺少女形象,剧中“尽日深帘人不到[4]15”(第三出《插钗新赏》)足以使读者可以想象出小玉的肖像:娇滴滴、羞答答、纤纤玉手,终日恪守理学家法。但是霍小玉对待爱情的态度却是纯洁的、真诚的,对爱情发自内心的守护,忠诚,专一。她渴望自由的爱情,这也正是汤显祖文艺思想中明显具有的个性自由、思想解放、反叛封建礼教的叛逆倾向。汤翁所言情与理的关系中的理也是指宋明程朱理学之理和礼教之理。汤显祖指出理、势、情三者的对立关系,认为或“理至而势违”,或“势合而情反”,或“情在而理亡”,三者不可能并存,也不可能调和。汤显祖尤其将情与理的对立推向极端,他在与达观和尚的信中指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5]129。依照人的本性、崇尚自然之情也正是汤显祖贯穿于整部剧的核心,由此可见,霍小玉向往的自由爱情及汤翁倡导的“至情”与封建礼教之理是矛盾的、背道而驰的,形成了情理冲突。同理,《被盗走的幸福》中安娜所处的时代是在乌克兰父权主义下,女性也是无任何权利的。妇女解放问题对伊凡·弗兰科作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剧中安娜深爱着古尔曼,只是在其兄弟的诓骗下被迫嫁给了不爱的米科拉,但安娜对爱情的追求,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体现了乌克兰妇女性格的民族特点及在她内心蕴藏的对社会压迫的反抗精神。因此,安娜对古尔曼的“情”与当时社会封建婚姻制度的“理”是矛盾的,形成了情理冲突。
二、两剧女主人公矛盾人格表现的“情”与“理”的冲突
“存天理,灭人欲”是程朱理学伦理观的最典型命题,它所指的“天理”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制定的“道德”规则;而“人欲”则是不利于其统治的人性欲望。在这一理论的主张下,又有了针对女子的“夫为妻纲”的谬论和男尊女卑思想,更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近情意的谬言,理学中纲常教条尤其对妇女的约束尤为苛刻,程朱理学提出女人要讲“三从四德”,“三从”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不止如此,还有妇人要遵守的“七出”(七去)等。可见针对女性小到日常生活大到贞节嫁娶,程朱理学都做了严格的规范要求,传统和保守成为当时女性的标签。受理学影响,汤翁笔下的霍小玉,在言行上还是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深闺少女被动恪守戒律的形象。剧中鲍四娘持钗来向霍小玉及其母亲提亲,当初步了解了李益的情况后,小玉却转而说“此事须问老妇人[4]46”(第八出《佳期议允》),小玉的答复一方面透露出对李益的好感,同时又带有女孩子的害羞,也符合当时一个深闺少女的身份和处境,即在言行上要遵循礼教的约束,婚姻大事还是要遵从父母之命。但霍小玉与李益的爱情是自由意志的表达,从他们相识《坠钗灯影》到相爱《花朝合卺》不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自我做主的恋情与婚姻。因此,尽管霍小玉的言行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但当遭遇封建势力剥夺她与李益的爱情时,小玉人格中爱情至上的潜意识被激发出来,表现出矛盾人格的情理冲突。小玉深爱着李益但同时又要顾及礼教的禁忌,因此小玉的矛盾人格表现出情理冲突,即小玉对李益的“情”与封建礼教的“理”之间的矛盾冲突。
小玉在爱情下的矛盾人格的情理冲突,除了体现在对封建势力的抗争外,也有对其妥协的一面,从古代的娶妻制度说起,明朝的男性根据自身权利和地位,是可以有三妻四妾的,《折柳阳关》中小玉送别李益在极度伤感之中也隐含了对未来命运的顾虑,她担心李益“他丝鞭陌上多奇女”[4]159,担心日久在外的李益变心,自己很可能从此被抛弃,因此小玉提出愿以八年的夫妻为约:“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秒选高门,以求秦晋,亦未为晚”[4]159,她愿意以人人都有权得到的一生的生命享受为代价,换取八年的幸福。同时默许了封建礼教下李益可以纳妾的制度,反映出当时女性地位是多么卑微,同时也反映出小玉的矛盾人格,对李益的“情”与当时礼教“理”间的矛盾,形成了情理冲突。
同样在《被盗走的幸福》中安娜也拥有矛盾人格,她所处的年代,是封建父权制年代,在其父亲去世后,她的两个哥哥为了侵占安娜应得的遗产,先是和村长合谋把古尔曼送到战场,并谎称古尔曼已战死,把安娜和恋人古尔曼拆散(因为古尔曼性格强硬,是他们剥夺安娜财产的障碍),后又把安娜强行嫁给老实木讷的米科拉,从此导致安娜在丈夫与情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和矛盾人格。如:剧中米科拉被村长控告偷卖劈柴而被殴打受伤后回到家中,安娜(扑向他,解开他的坎肩的扣子)“你等一等!汗衫上也有血!米科拉,你出了什么事?”[6]578安娜按照妻子的本分,出于对丈夫伤情的担心,表现出的是焦急、惶恐:“天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跟别人打架啦?也许在哪儿摔了跤?[6]578”尽管安娜迫于兄弟的压力不情愿的嫁给了米科拉,但是在她内心是爱着古尔曼的,迫于婚姻制度的束缚,安娜一方面要表现出对丈夫的关心,另一方面又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爱着情人古尔曼,所以安娜矛盾的人格也形成了情理冲突,是妻子对丈夫责任和义务的天伦之理与她对古尔曼真实爱情的矛盾冲突。
《紫钗记》中霍小玉与李益的恋情和婚姻是他们人格本能的体现,小玉对李益的爱情是真诚的、毋庸置疑的,但受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对妇女的限制,小玉又不得不考虑到礼教的规范要求,因此在她矛盾人格下表现出对李益的“情”与封建礼教的“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被盗走的幸福》中,安娜潜意识里是真爱着古尔曼的,但是丈夫米科拉受伤回家,出于妻子的矛盾人格应遵循的纲常伦理,她表现出对丈夫伤情的焦虑和担忧,这也形成了情理冲突,是她对古尔曼的“情”与纲常伦理之“理”间的冲突。因此两剧女主人公都存有矛盾人格且表现为“情”与“理”的冲突。
三、两剧男主人公矛盾人格表现的“情”与“理”的冲突
《紫钗记》中的李益也存在这种矛盾人格的影子,他身为书生,是怕官的,即便成为新科状元后,也有畏惧权势的心理,在剧中他惧怕卢太尉,因卢“霸掌朝纲”,卢太尉因新科状元李益没有到府上参谒,心生不满,借着玉门关节度使刘济讨参的时机,把李益遣到边关,并下令“写敕书付他星夜前往。官儿催发、不许他向家门傍。[4]137”但李益这时却对其命令置若罔闻“久领朝命,容下官数日启程[4]142”,使客将消息送到时,李益已在家,完全可以催其动身,却轻易地容他“数日启程”,李益在面对使客的催促表现得比较从容,前后是矛盾的。李益对霍小玉同样也是情真意切,剧中面对小玉的惊问,则回答:“(低云)朝命催俺去玉门关,参谋刘节镇军事,不久便回”[4]142。一方面担心使客听到,揭出实情,另一方面是不想让小玉受惊和伤心而有意说谎。体现出李益对小玉的“情”之深切。在爱情的驱使下,一向软弱的李益面对卢太尉的强权势力变得刚强起来。如果说卢太尉代表的是封建权贵势力的“理”的话,那么李益矛盾人格对小玉表现出的“情”与卢权势的“理”形成了情理冲突。
在《被盗走的幸福》中男主人公米科拉作为安娜的丈夫有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责任和义务,他爱着妻子安娜,他明知安娜和古尔曼之前是相好,按照常理情敌古尔曼的出现,米科拉的情绪应当是激动的,理应对古尔曼表现的极为排斥才对,但他的言行却显得十分恭敬、客气,不禁让人怀疑其丈夫的身份,剧中他邀请古尔曼一同共进晚餐:“……米哈伊洛啊,米哈伊洛!我看你还是和过去一样的淘气!(摇头)嗯,坐吧,咱们一块吃晚饭。[6]583”古尔曼认为米科拉身上的伤不是由于木柴砸伤的,而质疑米科拉受伤另有隐情,但面对古尔曼言语上多次挑衅,米科拉的情绪并没有失控,反倒晚上让古尔曼留宿在自己家里,他对妻子安娜这样说:“我马上就回来!我想这么办,抱捆草来,在这儿,地板上给米哈伊洛铺个铺。你准备褥单和枕头,请他盖皮袄。[6]586”从以上米科拉的反常表现可以推断与他的爱情有关,他爱安娜,为了不失去她,他什么都可以忍受,包括她的情人,因而表现出违反常理的矛盾人格。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他是惧怕古尔曼的,一方面,他与古尔曼无论是身材和力量上都相差甚远,古尔曼魁梧健壮,而他是矮小的,在体型上明显处于劣势,如果发生肢体冲突,必定不是古尔曼的对手;另一方面,米科拉担心村长殴打他的事被古尔曼问出,从而牵出他偷卖劈柴的事,所以面对古尔曼的质问,他躲躲闪闪,言语闪烁其词。后来,古尔曼诬陷米科拉与库平诺酒店凶杀案有关联,逮捕米科拉并将他投到了监狱,最后因证据不足将米科拉释放回家。这时的米科拉,从古尔曼对他的陷害到他被捕后安娜与古尔曼公开恋情,他对安娜已产生了绝望,当米科拉再次在家里遇到古尔曼时言语上就表现得极为不敬:“你能不再到我家里来吗?[6]626”以致最后发展为极端抗争性的举动,“我就是要给你开玩笑!(放开马枪,抓起斧子,朝村警的胸部砍去。村警倒下)[6]642”由之前的畏惧到后来的不敬,再到最后将古尔曼杀死,米科拉矛盾人格所表现得一反常态的举动形成了情理冲突。
李益有畏官心理,同时他又对小玉情深意切,但面对卢太尉的强权时李益的矛盾人格又表现得异常反抗,李益对小玉的“情”与卢太尉强权的“理”间形成了情理冲突;米科拉爱着安娜并惧怕古尔曼,米科拉矛盾人格促使他最后击杀了古尔曼,他对安娜的“情”与常理的“理”产生了情理冲突。
四、结语
两剧中,霍小玉对李益和安娜对古尔曼的真情都可以肯定,但受程朱理学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女主人公们矛盾人格都表现为爱情与封建礼教之间的情理冲突;男主人公李益畏惧强权卢太尉,但李益矛盾人格下对小玉情深意切与强权之“理”产生了情理冲突,同样米科拉惧怕古尔曼,由于被盗走的爱情,矛盾人格促使他竟对古尔曼表现出反抗甚至最后杀死对方,形成了情理冲突。以上是两部剧的相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