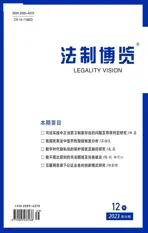物业纠纷中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再完善研究
2023-02-13于敏
于 敏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一、物业纠纷的特点
(一)物业纠纷案件数量急剧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起,全国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呈现直线飞跃式增长,至2018 年达到增长顶峰。贵州省在2013 年到2021 年一共审理了37000 余件物业纠纷的案件,从2013 年受理的28 件到2021 年的9335 件,急剧增长的案件数量给司法机关带来巨大的压力。贵州省G 市B 法院仅2019 年一个季度就受理了物业案件600余件,而当年B 法院正式在编的工作人员只有85人。根据贵州某中院的统计,在2010 年物业合同纠纷案仅4 起,2013 年案件数量增长至800 余件,同比2012 年增长了5 倍。北京市H 区法院在2006 年受理的物业纠纷案件为1752 件,同年H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物业纠纷为353 件,[1]可见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实务中的作用还有深入探讨的需要。
(二)物业纠纷具有群体性且成因复杂
物业管理中的纠纷多涉及公共利益,业主会联合其他业主形成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从单个的冲突演变成业主联合起来对抗物业公司,向政府和司法机关施压的极端情形。物业纠纷中涉及的不单是个人利益,还有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个案的处理不慎可能引发群体性的事件。
根据物业纠纷产生时间段的不同,物业纠纷可以分为前期物业纠纷与后期物业纠纷。前期物业纠纷主要是指由开发商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导致的,在业主入住后遗留问题才显现出来。后期物业纠纷则是物业公司在管理物业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后期物业纠纷又可细分为物业管理与维护引发的纠纷;物业管理费用与服务标准引起的纠纷;物业公司进行紧急避险引起的纠纷,例如救灾、救人等;因侵权引起的物业纠纷。
二、物业纠纷中采用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合理性
(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程序简易灵活
在物业纠纷中,普遍采用调解的非诉解决方式。相比于诉讼所需的时间以及费用,非诉讼方式一是节省了起诉立案开庭的程序,不需经过严格的证据审查,双方质证辩论的过程直击争议的核心,争议解决的结果不采用固定形式,口头或书面都可以;二是减少专业法律职业人员的参与,非诉讼解决方式不需机械地适用法律条文的规定,留有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中进行灵活变通的空间。
(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平和性与非对抗性,能更好地维护人际关系
在私法中,法律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维护公平,同时需要促进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有效化解,尽量挽回当事人的损失。解决物业纠纷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判定对错,还应当试图修复业主与物业服务行业的关系,促进当事人之间互相谅解,降低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纠纷解决方式才是司法所追求的,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就具有这样的特点。相较于诉讼中追求的程序正义,当事人的利益需求在非诉讼追求个案的“实质正义”更易实现。非诉讼方式给双方当事人提供沟通平台,不断协商、包容、妥协,最终取得双方利益的平衡,这一过程是情理与法理相交融的体现,也达到了缓和或者修复紧张的社区关系,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运用中的成效
在Alpha 案例库中检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2022 年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仅有18670 件,相较于2021 年 的37341 件、2020 年 的89935 件、2019 年的600445 件大量减少。其中一审撤诉率69.73%,二审撤诉率66.46%,再审撤诉率72.77%。撤回上诉的主要原因都是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中物业服务行业经营者与业主在审理期间达成调解或者和解,主动撤回上诉。据此分析案件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人民法院加大了诉前调解的工作力度,大量的案件在正式立案前就已经通过调解解决;二是各地建设的多元化解纠纷机制已经发挥作用,许多案件被分流到诸如人民调解、仲裁等机制中解决,大大减少了诉讼案件的数量。
三、现行物业纠纷中非诉讼解决机制面临的困境
(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仍较为单一
迄今为止,我国的特殊类型纠纷的调解制度、程序和组织缺少法律规范。目前物业纠纷的非诉讼机制多是在既有制度和传统资源基础上加以改造而形成的。并且我国目前的物业纠纷的非诉讼解决还是由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来主导,并且采用协商和仲裁方式的比率过低。但社会已产生物业管理纠纷专门化处理的需求,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各种物业纠纷调解、仲裁组织,这些民间性的非诉讼解决方式,由于未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公信度不足以及缺少经费等因素,发展停滞不前。
在物业纠纷的调解中,人民调解占据主要地位。现代化社会里村落和宗族的聚居形式被新型社区取代,社区住户人口流动频繁使得基层人民调解所依赖的地域性和属地性大大削弱,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导致基层人民调解难度加大。但行政调解整体萎缩,行业调解的自主发展空间日益变窄。[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的规定,仅有人民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定的具体规范,尚缺少其他类型的调解协议能否通过司法确认的规范。相比于人民调解协议缺乏司法保障,对调解协议效力的限制性规定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其他调解方式的发展。
(二)行业调解机制发展缓慢
物业纠纷解决中行业调解的优势和作用并未充分发挥。2007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开展司法改革项目以推进特殊领域纠纷“案多人少”问题的化解,根据2019 年北京物业管理协会和2016 年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的调研数据,多地积极响应司法改革政策,地方行政部门与司法机关联合建立了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由地方房管部门与司法局下发指导意见,各级社区、街道和物业协会参与实施,是一种将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与行业调解相联动的综合化纠纷调解机制,但至今大多数地区并未达到这一综合化纠纷调解机制的预期效果。报告中75% 的物业协会所进行的行业调解协议并未能得到法院的司法确认。物业协会参与物业纠纷调解工作,但实际上仍与主管部门联系紧密,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既有资源,行业调解适用率低。聘请专业的调解员或法律人员的成本过高,各地物业协会的质量良莠不齐,因此行业调解多依赖于政府部门和法院的力量,无法开展高质量的调解工作。根据报告80%的受访人员仅认可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效力,只有极少数物业协会与当地法院建立了诉调对接关系。[3]此外,经费保障不稳定制约了物业纠纷行业调解工作的有序发展,导致物业纠纷行业调解人员的积极性下降以及调解质量不高,物业纠纷化解的长效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三)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的对接问题
第一,在物业纠纷领域,我国法律缺少相应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前置程序。随着法治社会的建设以及法治思想的普及,当事人首选诉讼手段维护权益,早期物业纠纷案件直接进入诉讼程序,导致物业纠纷案件数量众多。2021 年旨在缓解审判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各地法院积极开展“诉前治理”工作,但目前诉前治理缺少社会面的深入了解,被误解为法院的内部工作,行政部门未能与法院开展有效的联合治理。一方面诉前治理工作搭建的平台缺少高质量高水平的调解人员,导致调解成功率不高;另一方面调解平台缺乏管理和相应工作规范,没有投入实际运作,在经费保障方面投入力度弱,调解费收取标准不一。
第二,非诉调解协议效力的问题。学理上认为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都可以到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其法律效力。但我国《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都仅对于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及程序做出了明确规定。[4]而未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本质上属于当事人之间的和解,缺乏法律约束力。
四、对物业纠纷中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未来展望
(一)推动物业纠纷中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发展
非诉讼纠纷解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理想状态下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将纠纷由简到难,由多到少进行过滤分拣,先通过协商调解再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最后到司法的三层防线分流,对纠纷进行疏导分拣最后化解。[5]
因此在物业纠纷领域将立体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型建立起来,一是必须建立相应的告知程序和优先选择程序。行政部门、调解组织、律师或者法院等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可以选择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帮助当事人选择最合适的方式化解纠纷。优先引导当事人选择成本低、对抗性低的非诉讼解决方式,将诉讼作为最后选择;二是需要完善协商制度在物业纠纷中的规范。确定当事人协商应当遵循的原则,能够适用协商解决的纠纷范围,以及当事人在协商中所享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尽量达到双方的权责统一。确立协商第三方介入的程序与形式,明确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协议的效力。加大协商制度的宣传教育,通过社会舆论,社区普法等方式引导民众,同时加强物业相关知识培训,普及法律知识;三是需要打造物业纠纷仲裁调解结合的非诉讼争议解决机制。河北沧州、江苏常州等地组建了物业纠纷仲裁机构。此类仲裁机构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打造“仲裁+调解”的非诉讼争议解决机制,受理调解不成转入仲裁程序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鼓励纠纷当事人在自行协商或调解不成后选择仲裁方式解决问题,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仲裁机构,此种解决机制程序简单结案快,并且仲裁机构的仲裁决定具有法律强制性,有法律保障。
(二)建立健全物业纠纷行业调解机制
第一,推动全国物业纠纷行业调解机制的建立,构建行业调解的平台,并积极接纳行业调解,将其纳入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型的第一道防线中。加强物业协会和基层政府以及人民调解组织的联系,合作开展工作。目前各地的物业相关部门和就如何丰富物业纠纷行业调解方法和提高行业调解的效果上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例如温州市成立了全国首个调解物业纠纷的民间团体;第二,规范物业纠纷行业调解运行,加强保障机制,提高物业纠纷行业调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调解组织在资金充足,人员稳定的环境下开展工作。政府适当为行业调解组织提供扶持,例如哈尔滨市建立了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专家库;第三,建立行业调解监督机制,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缺一不可,严格监督资金使用和调解费用收取。做到信息公开透明,提升行业调解组织的公信力。
(三)完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的对接
物业纠纷解决中调解与诉讼的对接是整个衔接程序中的重点与难点。一是诉调对接平台的搭建,这个平台是法院与调解组织进行合作的有效渠道,目前法院开展的诉前治理工作也可以依托该平台,或直接以其为基础。将繁简分流的速裁机制与该平台链接;二是明确能适用调解前置程序的案件类型,例如婚姻纠纷、劳务纠纷和宅基地纠纷等已有专门文件,而物业纠纷可以适用调解前置程序的规范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尚未达到法律层面;三是完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厦门以及黑龙江已经在司法确认的适用范围和管辖法院上进行大胆的尝试。要推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使用度,扩大司法确认的范围,行业调解在物业纠纷化解中可以并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但物业纠纷行业调解协议迫切需要法律效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