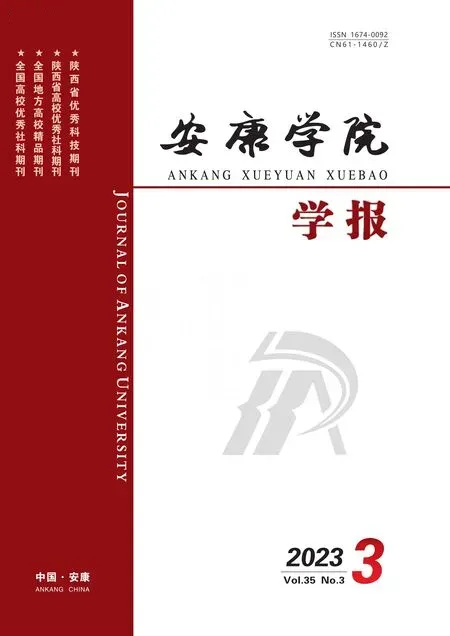《主角》与《秦腔》叙事艺术比较研究
2023-02-08梁萌
梁 萌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陈彦的《主角》以细腻温婉的笔触,为读者讲述了陕西偏远乡村九岩沟里的放羊女易招娣历经磨难最终成为一代秦腔皇后忆秦娥的传奇故事,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让人感叹。贾平凹的《秦腔》描写了清风街夏家、白家及其他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真实生动地再现了社会大转型之下的农村全貌,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故土和传统文化的一片深情。两部小说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两位作者对民间秦腔艺术元素的成功运用,使小说体现出浓郁的乡土文化意蕴。本文从叙述视角、叙事空间、叙事道具三个方面对两部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更准确地把握两部小说的审美特色和创作主旨。
一、叙述视角:全知型与多角度
小说是叙事文学中最重要的体裁。小说的叙述视角就是根据作家主观意图所确定的反映生活的角度。作家确定了写什么后,紧接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写,从哪件事、哪个人、哪个地方写起。这种选择不仅是技巧问题、艺术形式问题,它与作品的内容和作家为表现这一内容所采取的整体构思密切联系在一起。
叙述视角指讲述故事的视角和立足点。按照不同时空的叙述关系,可划分成时间叙述角度和空间叙述角度。时间叙述角度研究叙述与事件的叙述关系,事件与叙述间隔的时间关系。空间叙述角度主要研究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前者是故事内的叙述角度,后者是故事外的叙述角度。也有学者把叙述视角分为全知、限制和纯客观叙述三种。随着小说艺术的发展,视角的转换、交叉和多元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这是小说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叙述视角与叙述者有密切关系,叙述者可以是作家本人,也可以由作家创造出来。在《主角》与《秦腔》这两部小说中,叙述视角和叙述者是不同的。陈彦在《主角》中设置的叙述者是全知型的,主体形象鲜活而丰满,而贾平凹的《秦腔》则采用第三人称视角叙述,作者让疯子张引生充当叙述者,叙述者的疯言疯语和作者的散文化叙事使小说呈现出碎片化、溃散化的特点。
统摄《主角》的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小说的主人公可理解为忆秦娥,也可理解为具有“大匠”生命气质的秦腔艺人,或者可以认为是象征着“传统”的秦腔艺术。小说引人关注的恰恰是那个貌似隐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带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叙述者。《主角》的主人公不仅与叙述者有着高度同一性,还时时化身为忆秦娥、秦八娃、存字派四位老人,甚至画家石怀玉,化成一个个真实可感的肉身,讲述着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借忆秦娥习艺和演艺进行讲述,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现实、国家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故事也就是我们民族的故事,主人公顽强奋斗的精神也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小说最后,一个明确意识到自身价值的主体宣告生成,她既是忆秦娥,也是成百上千个不知名的秦腔艺人,他们勇敢地担负起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使命。《主角》中这个全知型叙述者是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者,他讲秦腔、艺人和传统文化,把传统从流逝的时间和历史中解救出来,将之作为一种自然事实进行细致描述。“不仅如此,他更深入传统内部,探究民众文化心理结构,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规律。”[1]
贾平凹的《秦腔》厚重宏大,为当代乡土中国叙事建构了一个非常杰出的文本。这部小说突破了传统以基本情节支撑作品的创作模式,采取的是一种生活漫流式的细节连缀。作者抽取了一般文本故事的元素,如悬念元素、情节元素,把对农村“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的痛切感受娓娓道来,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细流蔓延,汇流成海,浑然天成,直达本质的真实。作品塑造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夏天义,代表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没落,一个是夏天智,代表了乡土文化的衰败,一个就是叙述人张引生。
《秦腔》的叙述者是“疯子”张引生。引生具有“疯子”的身份,时常在清风街四处游荡,从引生的果园到三踅的砖厂,从村委会的所在地大清寺到赵宏声的药店大清堂,从丁霸槽的万宝楼酒店到夏天义淤地的七里沟,清风街的大事、小事、好事、孬事全都在引生的那双“疯眼”下赤裸裸地显现,他目光所及就是叙述所及,没有逻辑。引生受到特殊刺激就会“嘴脸乌青,口吐白沫”,进而会因癫痫发作而出现间歇性失忆,所以,他所感知的世界是无序、零散、错乱的,他眼里的世界,正是以这样一种非连贯的生活碎片连缀而成。此外,引生具有能与万物感应的“通灵”功能,他能与飞鸟走兽、草木虫鱼对话交流。这种叙事设计打破了一般的全知型叙事模式,整个故事的讲述呈现出溃散化、碎片化的特点,彰显了当下乡村纷杂而不乏活力的现实。可以说,引生的加入使《秦腔》的叙事时空趋于模糊,读者只是跟随作者的思绪神游漫步。
有人认为这个叙述者不过是中外文学史上常见的疯癫或痴狂叙述者的再现,但实际情况恐怕更为复杂。其一,中外文学史上的癫狂叙述者可称之为圣愚,他是愚蠢的,又是圣明的,在他的癫狂、愚蠢之后有某种真理支撑着他,如《尘埃落定》就是这样。而《秦腔》不一样,叙述者无所不知又无所知。其二,这个叙述者把作者全知的无所不在的视角和人物的有限视角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超越了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局限。《秦腔》中两种视角的转换非常巧妙。“疯子”张引生既是贾平凹自己,又是作者的另一部分,借用萨特的经典表述:“我以不是我所是和是我所不是的方式存在”[2],在是与不是之间,贾平凹实现了个人的叙事意图。《秦腔》的叙事节奏十分缓慢,有大量的减缓与停顿。减缓与停顿,均指小说中文本时间慢于故事时间,作品中充满了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致描写,有许多绵密的细节,基本故事时间是“每天”“一天傍晚”“那个晚上”,时间虽短,描写的内容却十分丰富。
《主角》以全知型叙述者讲述了秦腔皇后忆秦娥近五十年的起伏人生,也讲述了秦腔艺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秦腔》采用流水式的语调将鸡零狗碎的日子缓慢道出。叙述者身份的不断变化、场景的移动及多种矛盾的串联,将纷杂的人物和事件粘连成一个整体,在整体的背后呈现出一个残破的乡土世界。
二、叙事空间:秦腔舞台与乡土世界
小说的叙事空间是人物的活动场所,是故事的发生地。学者方英认为:“文学叙事中的空间是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想象的、艺术化的空间,以文字为媒介,由作者、读者和文本共同建构。作为一个想象的、艺术化的空间,叙事空间绝不等同于现实空间,这种不同不仅在于其虚构性,更在于其特殊的媒介决定了这是一个断裂的、模糊的、不直观、不透明、不连续、非匀质的空间。”[3]
《主角》和《秦腔》都以民间秦腔艺术为线索展开叙事,且都继承和发扬了当代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但二位作家的叙事策略不同,各自建构的叙事空间存在明显差异。
陈彦的《主角》将人们带到一个具体的、华丽的秦腔舞台世界。陈彦1963年出生于陕西商洛,从小热爱读书写作,古典文学底蕴深厚,16 岁便崭露头角,随即被县剧团录用,以后一直在剧团和文化单位工作,所以他的关注点与陕派前辈作家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相比自然是有所转变的。陈彦在《主角》中没有像陕派前辈作家一般把视野投放在乡土农村,或者是“城乡交叉地带”,而是神秘美丽的舞台世界,是形形色色的秦腔演职人员,是红红绿绿的现代城市。易招娣本是秦岭山村的放羊女,后被鼓师舅舅胡三元带去县剧团学习秦腔。由于胡三元个性刚烈强悍,自恃鼓艺超群,团里离不了他,就不注意尊重领导,搞好群众关系,结果别人就找茬整他。在那个政治运动不断的时代,任何人稍不注意就会被抓住把柄,胡三元这种人显然很容易被抓住辫子,而他倒霉后自然连累到外甥女。易招娣被贬进厨房烧火,掌勺的大师傅廖耀辉道德败坏,乘机侮辱她。虽然被宋光祖所救,坏人未能得逞,但给她后来的生活与事业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易招娣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里,仍然坚持练功,看门的秦腔老艺人苟存忠发现她的潜质,偷偷指导她,使她的表演技艺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紧接着易招娣迎来了人生的转机,下乡演出临时扮演《打焦赞》中的丫鬟杨排风一角而一炮走红,因此重新回到演员队伍,并历尽磨折终成一代秦腔皇后忆秦娥。作者创作时将关注点投射在秦腔艺术舞台的台前幕后。在小说中作者除了塑造出忆秦娥这么一个动人心魄的主角形象,还刻画出其他生动的人物形象,如争当主角的胡彩香和米兰,想唱主角却不肯吃苦下功夫的楚嘉禾,鼓艺精湛却个性刚烈、不谙人情世故的胡三元,厨房争权的廖耀辉和宋光祖等,作者对这些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及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
贾平凹出生在商州棣花街,十九岁离开故土去了西安。贾平凹从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步入文坛后,对故乡一直情有独钟。早期作品《兵娃》《姊妹本纪》《早晨的歌》,以及稍后的“商州系列”等都表达了对故乡风土的一片深情。在长篇小说《秦腔》里,作者以故乡棣花镇为原型创设出一个叫清风街的村庄,写了村子里夏家和白家以及众多村民的生活变迁,生动真实地再现了社会大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原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土地和精壮劳动力不断流失,农村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清风街上人们的勾心斗角也给农民带来了心灵的撕裂。《秦腔》以清风街上的大户夏家四兄弟天仁(早已去世)、天义、天礼、天智及其家人子孙二十多人加上张引生、赵宏声等人及来运、赛虎两只狗,共计出场角色五十多个。夏天义尽管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他还是舍不得他早年当村干部时没有治理好的七里沟。在有生之年,带上哑巴和引生早出晚归地抬石运土,砌坝堵水淤地。夏天智虽然没有下这样牛大的苦,但他却对二哥表示支持。当儿子夏风要把他们老两口接到省城享清闲的时候,他毅然拒绝了,每天还是在马勺背上画制他的秦腔脸谱,播放他的秦腔戏曲。小说最后,夏天智因胃癌发作死去。白雪是夏天智儿子夏风的媳妇,她漂亮端庄,性情和顺,却偏偏命运不济,作为县剧团台柱子的她,正当施展艺术才华的时候,剧团经营却不景气,只得走村串巷为人唱红白喜事助兴。更让人同情的是,她生下了残疾女儿,由于不堪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最终和丈夫夏风离婚。夏天智和白雪都喜爱秦腔,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夏天智的离世和白雪的悲剧命运意味着传统文土文明走向了穷途末路。引生的自我阉割也表达出作者对乡土文明在商品经济冲击下走向解体的无奈和绝望。
《秦腔》的叙事时间是一年左右,作者写得非常日常化,非常琐碎细密。我们检验一个作家是不是具备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主要是看他能否在最日常的地方、最生活化的地方写出真情或写出当代生活中非常根本性的东西,这一点《秦腔》做到了。
《主角》和《秦腔》对传统的观照、建构或阐释,都是通过现实主义的书写得以实现的,但由于观照视域和建构路径——秦腔舞台与乡土世界的差异,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美。《主角》以秦腔舞台、现代都市为叙述空间,而贾平凹则把叙述空间定位在乡土农村,两位作家都以“民间”为透镜观照中国历史、现实和传统。在现代性话语中,“民间”所指涉或关联的民众葆有最可贵的、恒常的自由自在精神、反抗意志、生命本然状态和最高道德价值。这决定了两部小说都是以返归传统的形式而走向现代。虽然民间视域中的传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冲击,但它作为生命的宣泄也是生命的确认,是不绝如缕、生生不息的存在。“民间性”具有不被传统和现代二元架构所拘囿的敞开性,具有随语境迁移而转换其含义的多种可能,无论在何种历史情境下,它既可能有对历史的对抗,亦可能有对历史的穿越或超脱。民间视域代表着时代主流话语压抑下的传统,它是可以转化为现代性话语要素的,是一种天然的现代话语资源。
三、叙事道具:秦腔艺术的不同呈现
陈彦和贾平凹都将民间秦腔艺术融入叙事之中。借助秦腔塑造人物,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使小说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是,通过对文本的比较分析可知,两位作家对秦腔这种叙述道具的运用却各不相同。
《主角》中,作者对秦腔的剧目、戏文、演出进行了细致的叙写,尤其是对秦腔演出的描写可谓浓墨重彩。小说对忆秦娥练功的描述,从“水袖”“吹火”“卧鱼”到“断崖飞狐”,从拜师、传艺、习艺到排练、演出、戏台布置、锣鼓、演员和舞台造型、戏剧观众等都作了生动具体的描写。比如,忆秦娥跟师父苟存忠学的第一出戏《打焦赞》,作者就对戏曲曲目以及排练过程用了大量笔墨。在易秦娥正式上场时,作者是这样描写的:“易秦娥就手持‘烧火棍’,一边出场,一边嗖地一下,将棍抛出老远。然后她一个‘高吊毛’,再起一个‘飞脚’,几乎是在空中,背身将‘烧火棍’稳稳接住了。再然后,又是‘大跳’加‘卧鱼’;再起一个‘五龙绞柱’加‘三跌叉’;紧接着‘大绷子’‘刀翻身’‘棍缠头’亮相”[4]178。经过作者的精细描写,忆秦娥所演绎的烧火丫头杨排风的形象跃然纸上。除了对忆秦娥的舞台表现作正面描写,还对观众的观剧反应作了描写。比如,忆秦娥在调入省秦剧团后出演的《游西湖》获得了如潮好评。“尤其是忆秦娥的《鬼怨》《杀生》两场戏,几乎是一句唱一个好;一口火焰,一次掌声。直拍到群鬼一齐出动,把残害忠良、杀死无辜、横行霸道的奸相贾似道,生生吹死在团团烈火中。谢幕的时候,忆秦娥出来三次深深鞠躬,观众仍然不走。”[4]393演员在舞台上演绎出公道、正义、仁厚、诚信等价值伦理,观众在观赏的过程中接受这些道德规范,增强了向上向善的社会力量。
在《秦腔》中,作者并未对秦腔艺术的表演作精细的呈现,更多的是将秦腔乐谱穿插其中,同时运用秦腔音乐和锣鼓节奏来表现人物心理,渲染气氛。清风街里夏天智是秦腔爱好者,他用收音机播放秦腔曲目,有时跟着哼唱起来,同时,他还痴迷于制作秦腔脸谱,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儿子夏风的帮助下出版。白雪是夏天智的儿媳妇,也是县剧团的主角,但小说中对其舞台表演的描写并不多,只有在她演唱的《藏舟》时做了些许描述:“她在台上演《藏舟》,唱道‘耳听得樵楼上三更四点,小舟内难坏了胡氏凤莲,哭了声老爹爹儿难得见,要相逢除非是南柯梦间’”[5]。最后一次写白雪演唱是在她公公夏天智的灵堂前,也只是呈现出一段《藏舟》的曲谱。《秦腔》中秦腔随处可见,贯穿小说始末,写到了许多经典剧目如《拾玉镯》《铡美案》《游龟山》《斩单童》《金沙滩》《走雪》《送女》《金碗钗》《木南寺》《背娃进府》《滚楼》《周仁回府》《巧相逢》《钻烟洞》《纺线曲》《十三铰子》等,每当情节发展到一定程度,一曲秦腔便唱起来了,小说中共计出现秦腔曲谱二十多处。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并未对这些秦腔剧目进行细致描写,往往一笔带过。
考察作家生活经历可知,陈彦有着近三十年的剧团工作经验,对秦腔曲目可谓耳熟能详,因而在书写这一题材时有更好的表现。
四、结语
陈彦和贾平凹均将民间秦腔艺术元素融入小说创作中,且都以现实主义手法进行书写,但由于叙述技法不同,两部小说呈现出不同的美学特质。通过对两部小说的叙述视角、叙事空间和叙事道具的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两部作品在叙事艺术方面的差异。应该认识到,两位作家对叙述视角、叙事空间的不同选择,以及对作为叙事道具的秦腔的不同运用,是各自表达思想主题的需要。《主角》旨在表现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及秦腔艺术传承发展的困境,而《秦腔》则侧重表现对传统乡土文化衰落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