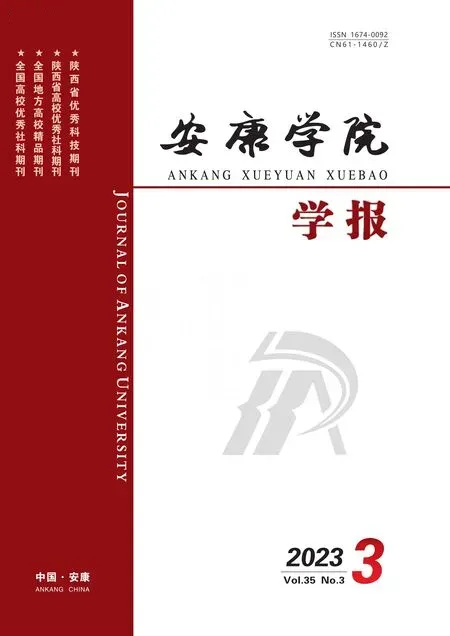海德格尔的语言之途
——从“形式指示”走向“道说”
2023-02-08陈亚玲伏飞雄
陈亚玲,伏飞雄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转向,他前后时期的思想与方法存在差异,但不可割裂思考。对他而言,运思与语言密不可分,对语言的思考是他整体思想的一条重要引线。但在学界现有的讨论中,较少将他前期形式指示(formale Anzeige)①formale Anzeige 多被翻译为“形式显示”,也译为“形式指引”。字面上二译皆可,但“显示”侧重于“形式”自发的显现,“指引”更强调“形式”的符号引导作用。海德格尔后期强调“道说”即指示(Zeigen),认为符号(Zeichen)就是指示者(Zeigenden),正是从指示(Zeigen)方面来经验的。两义皆存在于海德格尔的思想旨趣中,“形式”在“显示”中得到“指引”,“显示”本身也就是一种“指引”,采用“指示”综合协调两义,或是更恰切的译法。另外,本文的德语翻译主要参照孙周兴先生的译文,部分译文有改动。的现象学方法与其后期的语言思想联系起来作整体考察,即使少部分学者有所关注,仍缺乏具体的梳理与分析。
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言:“只有从在海德格尔I那里思出的东西出发,才能最切近地通达在海德格尔Ⅱ那里有待思的东西。但海德格尔I又只有包含在海德格尔Ⅱ中,才成为可能的。”[1]XXII海德格尔不断尝试突破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与语言,试图从“第一开端”转向、回溯、开启思的“另一开端”(ander Anfang)。他前期以形式指示的方法从“此在”追问“存在”,后期在“道说”中让“大道成道”。但他始终追寻的就是“道”——在“道”中,万物显现,成其自身,“存在”和“大道”是他寻“道”途中遭遇的不同路标名。
本文从海德格尔早期的形式指示的现象学方法出发,梳理他两个时期思想中或隐或显的语言路径,指出其连续性与差异性,以期阐明他如何在语言上不断克服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开启思的“另一开端”。最后立足于海德格尔整体的语言思想,揭示他思与言不可避免的局限,提示寻“道”的其他可能路径。
一、形式指示的现象学
在弗莱堡大学执教时,海德格尔形成了形式指示的现象学。形式指示是他为应对那托普批评提出的现象学方法,相关阐述主要集中在其全集的56/57、60、61卷中。下文梳理海德格尔对该批评的回应,以期阐明他早期现象学方法与语言的重要联系。
(一)那托普批评:反思性描述的现象学方法
在1919年战时补救学期的讲座中,海德格尔就已开始思考并尝试回应那托普尖锐的批评。那托普批评胡塞尔:“描述性反思或反思性描述的方法”(Methode der reflektiven Deskription oder beschreibenden Reflexion),并以此直接否定现象学的合法性。他认为,胡塞尔的“反思”必然会对体验者施加一种如同“解剖或化学分解式”的分析性作用。“描述”也是用“概念”来进行的,“它(描述)是用普遍性(Allgemeinheiten)对某物的改写,是‘概括’;它已经以某种概念构成为前提,因而是‘抽象’和理论,也就是‘中介’(Vermittlung)。”[2]101海德格尔认为那托普从根本上质疑了现象学的合法性,“如果人们想把体验搞成一门学科的对象,那就不可能逃避理论化。也就是说:不存在对体验的直接领会(unmittelbares Erfassen)”[2]101。换言之,因为胡塞尔的“反思”和“描述”的现象学方法会对体验之流造成破坏和扭曲,所以他的现象学根本无法把握活生生的体验之流,不可能“回到事物本身”。海德格尔赞同那托普对胡塞尔的批评,随后他一直尝试解决该问题,最终创立了超越胡塞尔和那托普的独特哲学方法——形式指示,“一种可以不丧失体验之流并具有非概念化表达能力的思想方法”[3]。
(二)实际生活经验
形式指示的现象学方法正面回应了那托普两点尖锐的批评。首先,有别于胡塞尔“对体验的反思”,海德格尔找到了一种“对体验的体验”(ein Erleben des Erlebens),一个“原初的体验领域”,这恰是那托普因为其“系统的、泛逻辑的基本定向”的阻碍,而“无法自由地通达的体验领域”[2108。即他在1920 至1921年冬季学期的《宗教现象学引论》中提到的实际生活经验(faktische Lebenserfahrung)。实际生活经验的实质在于“经验者本身与被经验者不是如同物体那样被撕裂……它既具有一种主动的意义又具有一种被动的意义”[4]9。也就是说,在这种体验中,体验、体验者、被体验者不是割裂的,不分主、被动,也不分主、客体,一切只是在体验之流中相互关联,随之流动。这种相互关联的“意蕴”(Bedeutsamkeit)是经验原初给予的,不存在理论化,“经由意蕴的方式(它规定着经验的内容本身),我经验着我所有的实际生活处境。而当我询问:我是如何在实际生活经验里进行经验的?此点就会清楚起来:——没有理论”[4]13。
海德格尔1919年在分析“周围世界体验”(Umwelterlebnis)的结构时,就已说明人们如何在实际生活经验中非反思、非理论地“经验”。“走进教室,看到讲台。让我们完全放弃用语言来表述体验。‘我’看到了什么呢?……我是几乎一下子就看见了这个讲台;我不只是孤立地看到它,我看到这个桌子,它对我来说放到太高了。我看到上面放着一本书,直接对我造成妨碍(是一本书,而绝不是一些堆叠起来的散页,上面撒上了黑色的污点),我在一种定向、光线中,在一个背景中看到这个讲台。”[2]71他看到了“周围世界性的东西”,同时这些东西还被把握为有这样那样的“意蕴”直接向“我”给出,比如“讲台、书、黑板、听课笔记簿、自来水笔、校舍管理员、学生联谊会会员、有轨电车、汽车”。他不是胡塞尔式的“反思性描述”,先看到桌子的颜色、材料、体积,再到文化层次的讲台。他是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个讲台和他周围的世界,同时具体地领会了这些东西的原初意蕴,所以他说“意蕴乃是原初的东西,是直接(unmittelbar)给予我的”[2]73。这种实际生活经验正是对体验的体验、在体验中的体验,它是同时刻的、直接的,不是事后的反思,也不会理论化体验之流。
(三)形式指示
海德格尔以实际生活经验回应了那托普对“反思”的批评。接着,他以形式指示的现象学方法来解决有关“描述”的语言疑难。
海德格尔认为形式指示不同于一般化(generalisierend)的语言描述,它不会切断体验之流。“方法难题以一种关于体验的可能描述问题的形态向我们表现出来。最原初的、但已经足够危险的异议紧盯着语言。一切描述都是一种言语表达(In-Worte-Fassen)——‘言语表达’是一般化这种异议的基础是下面这种意见:一切语言本身都已经是客体化的。”[2]111他发现了那托普预设的前提——因为所有语言都已是一般化、客体化的,而一切关于现象的讨论都必须使用语言进行“描述”,那么使用语言的“描述”必然失去直接性。但海德格尔认为,形式指示的语言是一种例外,它是非一般化、非客体化的。“解释学的直觉”(hermeneutische Intuition),即后来的形式指示,并不是一般化的言语表达,就像上文提到的周围世界体验,“我”一眼看到“讲台”,这种语言直接流动在实际生活经验之中,“它们与体验同行,生活于生命本身中,在同行之际,它们同时也来到,于自身中承载着来源。它们既先行把握又回行把握,也就是说,它们表达出生命的引发动因的意向或者意向化的动因引发”[2]117。
更进一步,海德格尔认为形式指示的语言不仅不会切断实际生活经验,而且必须通过形式指示才能“突显”。实际生活经验总有一种“趋向固定的下沉趋势”,是“有立场的、下沉的、有关涉的-浑然无别的、自足的意蕴之烦忧”[4]16。这个“下沉趋势”正是被一般化语言所固定的倾向,它的“下沉趋势中总是再形塑出一种客体关联(Objektszusammenhang),此关联总是一再趋于凝固。只要意蕴在客体关联里起着作用,由此人们就可达到一种周围世界的逻辑。所有的科学都力求超出这样的逻辑而构造出一种更为严格的关于客体的秩序,这就是一种物事逻辑(Sachlogik),一种实事关联(Sachzusammenhang),一种根植于实事本身(Sachen selbst)的逻辑”[4]17。但形式指示的语言可以避免实际生活经验的“下沉趋势”。形式指示是一种“防范”,一种“先行的保证”,能够“防止这种预先论断、这种事先的成见”,阻止实际生活经验“滑向客体化之物”,使“现象从生活经验中重新突显”[4]65。实际生活经验可以为形式指示不加歪曲地指引、显示,并且也必须通过形式指示来“防范”自身“下沉的客体化趋势”。那托普的第二点批评——对“描述性”语言表述的疑难也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
梳理海德格尔早期的思想路径可以发现,海德格尔在早期就对语言问题非常关注,语言在他的思想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实际生活经验与语言直接相关的,这种经验已经包含了“原初的意蕴”,“含义要素、语言表达,无需直接地成为理论的,或者甚至直接意指客体的,相反是原始地体验着的,是前世界性质的或者世界性质的……词语含义的普遍性首先表示某种原初的东西,即:被体验的体验的世界性质(Welthaftigkeit des erlebten Erlebens)”[2]117。实际生活经验离不开语言的参与,它必须以形式指示的语言防范其下沉趋势。海德格尔要以这种语言否定一般化的语言,还原实际生活经验的“原初意蕴”,回到活生生的体验之流。形式指示的思想由语言问题生发而来,并最终需要返回语言寻求解决。
二、前期的语言路径:旧语言——形式指示——存在
海德格尔确立了形式指示的现象学方法,接着便以形式指示的语言开启自己的思路。下文聚焦海德格尔前期思想中的一些具体实例,特别《存在与时间》中的形式指示,进一步阐明该方法的运思特点和具体的语言形式,总结他前期的语言思想。
(一)形式指示的基本环节:还原、建构、解构
1927 年夏季学期,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开设的“现象学之基本问题”课程中,进一步阐明形式指示展开的三个基本环节:还原、建构、解构(Reduktion、Konstruktion、Destruktion)。现象学还原是指,“把现象学的目光从对存在者的把握引回(Rückführung)对存在者之存在的领会”[5]29。也就是通过还原,将实际生活经验从下沉、固定的某种关联引返回原初意蕴的多种且充满可能性的意义关联。引返也需要现象学的建构,它是“以肯定的方式把自身带向存在本身”,是“对预先所给的存在者进行指向其存在及其存在之结构的筹划”[5]30。现象学的解构是为“充分保证存在论诸概念的纯正性”,对“被传承的、必然首先应用的概念”进行的“批判性拆除”[5]31。还原、建构、解构三者密不可分,都是形式指示的基本环节。这三个环节“在内容上共属一体,并且必须在它们的共属性中被解释。”形式指示就是以“否定性解构”的方式“建构”,在“肯定性的建构”中“还原”存在①不同于有论者将形式指示理解为现象学解构的一个环节和因素,应是形式指示包含了这三个基本环节。。
(二)形式指示的运思特点:指示、开端
从海德格尔对哲学的一个新定义,可阐明形式指示的运思特点。
哲学的原则性形式指示的定义(prinzipielle formal anzeigende Definition der Philosophie):哲学是原则性指向作为存在的(有存在意义的)存在者的认识行为,也就是说,为了处于或者实现这种行为,则决定性地共同取决于当时行为各自拥有的存在(存在的意义)。[6]60
这个不同于“第一开端”的哲学定义指示了什么?首先,“原则性的定义”是指哲学根本不是“实事”;而是“原则性地拥有”(prinzipielles Haben)实事。其次,“形式指示的定义”是指“它是‘形式的’指示,指示‘道路’,在‘开端’之中。它先行给出的是一种内容上不确定的、实行上确定的联系(Bindung)”[6]20。也就是说,这个定义首先颠覆了以往形而上学传统中对“哲学”说明性、事实性的清晰定义,还原“哲学”,再建构出一段关于“哲学”的形式指示的言语表达。对“哲学”的定义不是对实事的规定,而是要“指示方向,标划道路”[6]34,使每一个读到该定义的人能够指向具体的领会处境(Verstehenssituation),指向每个此在对“哲学”的在世体验。
(三)《存在与时间》中的形式指示
通过现象学方法的三个基本环节,海德格尔构造了一系列形式指示词。这样的词汇在海德格尔之思中不胜枚举,此处试举一例——“此在”(Dasein)的形式指示构造过程。
在《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1921 年)一文中,海德格尔认为“生存”(Existenz)在形式指示中指向“我在”(ich bin)。“生存”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而言,首先是“我在”。“我在”是“一种作为原则性的现象联系及其所属问题的开端”[7]10,是指“拥有我自身”(Mich-selbst-haben)。“我与作为自身的我自己相遇,以至于我(在这种经验中生活的我)能够合乎其意义地追问我的‘我是’(ich bin)的意义。”[7]29也就是说,“生存”的意义、“我在”的意义是每个人在其具体的生存处境中体验(leben)到的自身(selbst)。不同的领会处境有不同的具体实行,“我在”这个形式指示词汇将我们指引向各自不同的“生存”处境中。接着,“我在”到《存在与时间》中成为“此在”(Dasein)。海德格尔将“我”(ich)这个第一人称代词“解构”为“某”(da),把“在/是”从第一人称直陈式现在时式“bin”还原为不分主体人称、不分时空的不定式“sein”,最终“ich bin”(“我在”)建构成为“da sein”(某种东西在某时某处存在),即“此在”(Dasein)。“生存”(Existenz)——“我在”(ich bin)——“拥有我自身”(Mich-selbst-haben)——“此在”(Dasein),这个构造过程体现了他一直不断还原、解构固定概念、尝试建构新的形式指示词的努力。每一次新的形式指示词都比原有的言语表达更能“指示”(anzeigen/Anzeige)、“开端”(anfangen/Anfang)①这里使用的“指示”和“开端”二词兼有动词义和名词义,对应的德语词同样兼有二义。形式指示兼有二词的动、名词义,二词相联系也可说明其特点:“指示着开端”(anzeigen den Anfange)和“用指示开端”(mit Anzeige anfangen)。。形式指示化的语言,是力求去固定化、去概念化的语言。
其次,除了一系列的形式指示词及词汇表达,海德格尔还强调了“发问”(Fragen) 和“对话”(Gespräch)的形式指示性质。在《存在与时间》中,他说:“我们不知道‘存在’说的是什么,然而当我们问道‘存在是什么?’时,我们已经栖身在对‘是’(‘在’)的某种领会之中了”[8]7。“发问”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形式指示,“发问”意味着先行领会,在观念化、对象化之前,对所问的东西已经有所经验、有所理解、有所实行。
同样,“对话”也是一种形式指示。海德格尔前期的语言思想主要集中在这三个形式指示词:逻各斯(λóγος),话语(Rede),语言(Sprache)。海德格尔首先对逻各斯进行了形式指示。他回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还原逻各斯的本义。他认为逻各斯不是后世理解的“理性、判断、概念、定义、根据、关系”[8]43,而是“有所展示的话语(apophantischen Rede)”[8]46。所以那句经典的定义“人是逻各斯的动物”,不意味“人是理性动物”,而是说“人是会言谈(话语)的动物。”“话语”先于人的存在,人这种存在者向来已活在对“话语”的理解之中,“我们一开始就同这个他人一道寓于话语所及的存在者”[8]231。这种“话语”不是流俗化理解的工具“语言”。海德格尔接着对“话语”进行形式指示。他认为“话语”是指“可理解性的分环勾连(Artikulation der Verständlichkeit)”,这种“分环勾连”的东西就是“含义整体”(Bedeutungsganze),即他在弗莱堡大学时强调的实际生活经验的“原初意蕴”(primäre Bedeutsamkeit)。这种“意蕴”可以“分解为种种含义(Bedeutungen)”,所以“话语”已是“解释与命题的根据”,是“可理解性”的来源。一般理解的“语言”是来自“话语”的,“话语”先于“语言”的,“言词吸收含义而生长”,“话语直接说出来就是语言”[8]214。
通过对这三个关键词的形式指示化,海德格尔前期的语言之思得以显示。“人是会言谈(话语)的动物”,人活在“话语”之中,不是“语言”被人用,而是人被“话语”用来说“语言”。人们之所以能够“对话”“交谈”中,是因为人们“先已‘分有’了话语所及的东西”,他们已经对“话语所及的东西”也就是“语言的含义”有所领会,所以他们才能开始“对话”,才能在“对话”中“说”“听”“答”乃至“沉默”。他在后期强调“诗与思的对话”,因为“对话”本身就能“指示”“开端”,就是一种不断形式指示的过程。
经过上述的梳理可以发现,形式指示的方法在海德格尔前期的思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托普的批评直指语言问题,形式指示从语言问题生发而来,最后也回到语言。海德格尔通过还原、建构、解构一般化、客体化的语言及其思想,以形式指示化的语言来指示、敞开现象的“原初意蕴”,追问“开端”,追问“存在”。他前期的思想路径实际处处隐含着语言思想,可以理解成:旧语言——形式指示——存在。
三、从形式指示走向语言之途
(一)前期的局限
海德格尔试图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尝试克服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第一开端”,开启思的“另一开端”。同时他也注意到运思与语言直接相关,他尝试用形式指示化的语言去克服形而上语言,以此去克服旧语言指示的旧思想。但《存在与时间》的未完不续,暴露了他前期思想的矛盾和局限。
学界大多认为,前期海德格尔的思与言对形而上学有所突破,但仍深陷其中。张汝伦认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使用的仍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旧语言,这导致了“它(《存在与时间》)内在新(思想)旧(形式)矛盾的不可调和”,最终“使它成了一部未完成的作品”[9]。孙周兴认为:“前期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还浸润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概念方式中。《存在与时间》等前期著作的用语,尽管有种种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新界定,但基本上还是形而上学的语言。这本身就体现了前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局限性。”[10]
联系本文对形式指示的梳理也能得出如下结论:海德格尔前期的语言方式——形式指示化的语言,对形而上语言有所突破,但它的基本环节——还原、建构、解构依旧较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形而上学的语言,新的形式指示词仍是在形而上学语言内部的突破。海德格尔后来自己也说,这不是一种“新语言”,而是一种“改变了与旧语言本质的关系”的语言[1]XXII。虽然已经有所突破和革新,但他这一时期的形式指示并不彻底,形式指示化的新词仍然有着再次被“形而上化”的风险,“第一开端”的语言与“另一开端”的思想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这也表明了他前期思想的不彻底,他尝试从“此在”追问“存在”,这种“发问”和“对话”的方式及对象,仍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之中。
《存在与时间》出版后,海德格尔也逐渐意识到其局限,转向直接思考语言问题,开启新的思想道路。他开始直接与独立于形而上学传统的“诗”对话,在对话中革新语言,走向道说。随着语言的革新,他的“思”也转向对“大道/本有”的直接发问。这一阶段,他的语言之途更明晰地显现出来,从形式指示转向道说,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他真切地走在“道”上。
正如本文一开始强调的,“海德格尔I”和“海德格尔Ⅱ”是不能完全分开的。语言是贯穿海德格尔前后期的重要的思路,形式指示的方法在前期开端,在后期也会继续发挥作用。下文将厘清海德格尔前后期语言思想的联系与差异,以期对海德格尔整体的语言思想作出全面深入的评析。
(二)后期的语言路径:旧语言——诗与思的对话——道说/大道
海德格尔后期对语言的思考围绕着道说(Sage)展开。他首先区分了两种语言观。一种是工具化、理性化的语言观,认为人使用语言,“语言是对内在心灵运动的有声表达,是人的活动,是一种形象的和概念性的再现”[11]13。他否定这种流俗的语言观,提出了另一种语言思想——道说(Sage)。道说是“语言本质之整体(das Sprachwesen im Ganzen)”,人是语言性的,人必须首先倾听道说才能言谈,不是人用语言说话,而是道说用(braucht)人说话[11]242。
道说用人说话的突出方式是“诗与思”(Dichten und Denken)。“作诗”与“运思”的语言是伟大的“将来者”倾听、跟随道说的语言。“思与诗的对话”能够将“语言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者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11]34。海德格尔以道路公式(Wegformel)解释他的语言观:“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die Sprache als die Sprache zur Sprache bringen)[11]250“诗与思”是作为“切合语言的本己因素”[11]240的语言,是“作为语言的语言”,它们来自道说,也指向道说。道说本身是人不可说的“寂静之音”(das Geläut der Stille),但人能以“诗与思”的语言开辟通往道说的道路。同时,道说是大道(Ereigneis)说话的方式,在道说的运作中,语言成其自身,“它——大道——成其本身”(Es — das Ereignis - eignet)[11]247。所以海德格尔的后期语言思想可理解为:旧语言—诗与思的对话—道说/大道。
(三)前后期路径的联系与差异
海德格尔前期形式指示的语言思想为:旧语言I—形式指示—存在。后期道说的语言思想为:旧语言Ⅱ—诗与思的对话—道说/大道。下面将逐一比较分析前后期两条思路的三点一线,指出其联系与差异。
1.旧语言Ivs旧语言Ⅱ
将前期的“旧语言”命名为“旧语言I”,后期为“旧语言Ⅱ”,这两个“旧语言”不是完全重合的。“旧语言I”如上文所述,主要指一般化、客体化的语言,也就是那托普批评的带有“反思”“描述”的理性语言——西方形而上传统的语言,包括日常中的流俗语言和哲学史中的学术语言。海德格尔后期对语言的区分更加明晰。“旧语言Ⅱ”不仅包括“旧语言I”,即他后期与“道说”区分的工具语言,还包括前期他自己思想中仍有形而上残余,没有彻底形式指示化的语言。
2.形式指示vs诗与思的对话
(1)诗与思的对话
海德格尔的“诗”指什么?广义上,他将“诗”看作“艺术”,它的本质是“存在者之真理的自行置入(das Sich-ins-Werk-Setzen der Wahrheit des Seienden)”[12]21。但实际上,他更多谈论的“诗”,只是他认可的德国伟大民族诗人的诗歌,包括荷尔德林、格奥尔格、里尔克等的诗歌。海德格尔之所以只选择这些“伟大诗人”的诗歌,是因为他们的诗歌源自“大道”,是对“道说”的“纯粹所说”(Rein Gesprochenes)。同时他也强调“人是言谈的动物”,人与语言是最亲近的,语言艺术自然比其他媒介艺术更贴近人的存在。道说是“语言本质的整体”,诗歌这种“纯粹所说”自然也与道说更为切近。除此之外,他在与手冢富雄的对话中谈到,“语言是存在之家”,那么“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11]85,他能返回的家园也只能是在德语中栖居的德意志民族之乡。
海德格尔指的“思”又是什么?海德格尔对“诗”的阐释就出自一种“思”的必然性,而他的阐释本身就是“诗与思的对话”。这种“思”是独属于海德格尔的“另一开端”的哲学,是他1964年在弗莱堡的一次神学谈话中强调“非客观化的思与言”(nichtobjektivierenden Denkens und Sprechens)[7]68。它既非现代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技术思维”,也非哲学传统中笛卡尔、康德的“对象”“客体”。这种“非客观化的思与言”如何可能呢?前期的海德格尔的方法是形式指示,但他后期认为只在形而上内部改造的语言是不彻底。他让“思”与“诗”对话,与独立于形而上传统的“诗”,与属于“存在历史”、来源于道说的纯粹诗歌对话。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与“诗”对话中的“思”与“言”才能突破前期的局限,真正返回到道说之中。
“诗与思的对话”,正是海德格尔后期对形式指示的具体推进。上文已经阐明他具体的推进思路,但这种语言与形式指示的语言究竟有何不同?下面将举一些“诗与思对话”的实例,并与前期进行比较。
海德格尔于1936 年发表的《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是一个经典的“诗与思的对话”,他的语言之思在其对荷尔德林之诗的阐释中显现出来。海德格尔在出版前言强调,他的阐释并非一种“文学史或美学的研究”,而是出自“思的必然性”,是“一种思与一种诗的对话”[13]7。他认为荷尔德林是“诗人的诗人”,他的诗“蕴涵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质”。接着,他把与荷尔德林之诗的对话集中在五个中心诗句上,“这五个中心诗句的确定次序及其内在联系将会把诗的本质性的本质端到我们眼前”[13]34。这五个中心诗句是:
①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第三卷,第377页)
②因此人被赋予语言,
那最危险的财富……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第四卷,第246页)
③人已体验许多。
自我们是一种对话,
而且能彼此倾听,
众多天神得以命名。(第四卷,第343页)
④但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第四卷,第63页)
⑤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第六卷,第25页)[13]33
这五个中心诗句道出了荷尔德林的诗思,也道出了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首先,一二句揭示了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诗的本质必须从语言之本质(道说)那里获得理解,但“在语言中,最纯洁的东西和最晦蔽的东西,与混乱不堪的和粗俗平庸的东西同样地达乎词语”[13]37,所以语言也是“危险的财富”。诗人倾听道说,形诸言词,他的“作诗”正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
接着第三句揭示了语言之发生。海德格尔认为:“人之存在建基于语言”(Das Sein des Menschen gründet in der Sprache)[13]38,人在语言中彼此倾听、对话,语言本质发生在对话之中,当语言作为对话时,“诸神便达乎词语,一个世界便显现出来”[13]40。只有作为对话,语言才是本质性的,必须通过对话才能打破旧语言。
但这种对话如何开始?谁来命名诸神?第四句揭示了答案:诗人。“诗人命名诸神,命名一切在其所是中的事物。”这种命名不是“给一个事先已经熟知的东西装配上一个名字”,而是诗人要说出“本质性的词语”,使“物之存在”达乎词语,让物通过命名而被指说为它所是的东西。所以诗的本质就是“存在的词语馈赠(worthafte Stiftung des Seins)”[13]41。也就是说,伟大诗人的“诗”是来自道说的“纯粹所说”,“物之存在”在诗人的“命名”中显现,成其本身。
第五句进一步指示了诗人的使命。诗人被抛入“之间”(Zwischen),处于“诸神与民族之间”,“诸神与人类之间”。诗人的使命是为他的民族谋求真理,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荷尔德林成了“贫困时代”中的伟大诗人,他创建的诗之本质具有最高程度上的历史性,他在“之间”中创建的诗意词语决定了人是否能“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海德格尔通过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在“诗与思的对话”中,使语言返回到“道说”中,使人返回到自己的存在家园中,“存有”在“大道”中“成道”。
在上述“诗与思的对话”中,海德格尔指示了他后期的语言思想:诗人处在诸神与终有一死者之间,它打破了旧语言的危险,创建持存的本源性词语,即诗人之诗。终有一死者聆听诗人之诗,以“思”与“诗”对话,在对话中思考“存在之真理”。“诗与思的对话”照亮了返回“道说”的道路,敞开了“大道”的领域。这也恰好对应了前文对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路径的总结:旧语言—诗与思的对话—道说/大道。
(2)形式指示vs诗与思的对话
首先,这两种方法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将“道”从“旧语言”导致的下沉趋势中突显出来,开辟通往“道”的道路。其次,二者的具体方法都与语言相关,都是想以一种特殊的语言,或者说是回归了“语言本质”的语言形式来开辟“思”的道路。形式指示的语言特征是“指示”“开端”,“诗与思”的语言特征同样如此。他们都是来自话语/道说的语言,都能够使现象返回到“原初的意蕴”中。前期的“逻各斯”“话语”,与后期的“语言本质”“道说”,指示着同样的方向,前后期的两种方法都能“指示”返回“开端”的道路。
两种方法都有共同的目标,其具体的语言形式和特征也有相通之处。二者的不同在于,“诗与思的对话”比形式指示的语言更彻底地否定了“旧语言”。形式指示的否定在形而上内部进行,形成的新的形式指示词仍难摆脱形而上学传统的阴影。在“诗与思的对话”中,“伟大之诗”是独立于形而上传统之外的,是诗人直接倾听道说形成的诗性智慧。海德格尔首先倾听“诗人之诗”,与之对话,所以他的“思”能够摆脱学院哲学的假定、推导、证明等逻辑化的言说方式,不再局限在形而上学内部,而是以诗意语汇来表达思想,使他的思与言处处浸润着来自道说的诗意之光。
海德格尔前后期的语言路径的目标和推进方式是一致的,都是想通过某种特殊的语言来指示通往“道”的路径。但不同在于,“诗与思的对话”引入了独立于形而上传统外的诗意语言,比形式指示的语言更彻底地打破了“第一开端”的语言及思想。
3.存在vs道说/大道
上文已经比较了前后期两条路径中的两点,现在我们来比较第三点“道”及整体的思想线路。首先,前期通达的“道”是“存在”,后期通达的“道”是“大道”。“存在”和“大道”都敞开了一个“道”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万物还其本原,是其所是,成其自身。
不同在于,通过对语言更彻底的思,海德格尔在后期更直接地开启了思与言的“另一开端”。海德格尔认为他前期的“存在”之思不彻底,而后期的“存有问题……克服了一切‘形而上学’”[14]。他前期从“此在”出发追问“存在”,后期则直接对“存有”发问。在前期,形式指示的语言路径并非完全显性的,“此在”的生存样态是他关注的核心,形式指示只是作为一种方法,相关的语言思想也处于重要但非核心的地位。在后期,语言的核心地位突显了出来。语言起源于“存有”,在思考这种存有时,必须同时“回忆语言”。这种语言是“我们的语言”,是“我们的母语”、是“我们历史的语言”。“存有”问题与语言的本源问题直接相关,所以他直接倾听“大道”之音,倾听道说,直接从语言切入思的道路。语言问题在后期是显性的、不可或缺的,通过“诗与思的对话”,直接倾听“道说”,才能更彻底地克服形而上学,开启“另一开端”。
四、结语
海德格尔敞开了一个“道”的领域,但他认为“道”不可为人所言说。“道”是存在之光的澄明,前期是“存在”,后期是“大道”。他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形式指示或者“诗与思的对话”抵达“道”,但“道”本身不可为人言所说,语言有风险,哪怕是“诗与思的对话”,都有可能像“鸣响的钟”一般,“为落雪覆盖而走了调”[13]7。思与言的矛盾,让他在使用每一个词语时都特别小心,一直强调它们只是思想道路上的不同路标。“道说”(sagen)即“指示”(zeigen),语言的本质是指示,不能被固化为形而上的概念。所以他说“道说”是“寂静之音”,“大道”是“空洞之空洞”,永远不能为人言所说。
虽然海德格尔认为“道”不可说,但他认为“道”与语言是亲近的,“道”可以且必须为某种语言所指示。这种语言在前期是形式指示的语言,在后期是“诗与思的对话”。虽然“道”不可说,但只有人才能对“存在”发问,才能走在“道”上。“人是话语的动物”,人要在对话的语言中切近“道”,语言是通达“道”的最亲近的道路。如他所说,“唯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之中。在没有语言处,譬如在石头、植物和动物的存在中,便没有存在者的任何敞开性”[12]61。他后期对“诗歌”这种语言艺术特别关注,他认为其他非语言的艺术也是“诗”,建筑、绘画等也能发生在“道”的敞开领域中,但“诗歌”这种语言艺术在“诗”中有着最根本的地位,“存在者之澄明早已不知不觉地在语言中发生了”[12]62。“诗歌”在语言中发生,语言才保存着根本意义上“诗”的原始本质。
“道”不可为人言所说,但必须为某种语言所指示,海德格尔通过他的思与言打开了一条通往“道”的语言之途。但凭借语言人真的可以切近“道”吗?是否存在任何语言都无法解释的人的体验境域?既然语言存在局限,那有没有通往“道”的其他道路?列维纳斯的“绝对他者”,布朗肖的“另一种夜”质疑了海德格尔潜在的主体思想,开拓出“道”在“存在之光”外的晦暗夜色,指出语言和主体均无法抵达的人类的生存境域[15]。罗姆巴赫超越海德格尔基于语言的“先在意蕴”,从“实体”“体系”到“结构”,从“解释学”到“密释学”,超越人类此在打开了先于语言的、总体此在的、世界结构意义的完整发生[16]。舒斯特曼认为“道”是一种非语言性的体验,反对“一切的领悟都是解释”的说法,借助禅宗、道家的智慧,强调身体训练,以身体美学开辟了通往“道”的其他路径[17]。这些问题线索指明了存在于主体之外的生存境域,暗示了超越语言的、具身化的领会处境。海德格尔整体的语言思想留下的启示和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