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
2023-02-05黄天骥
黄天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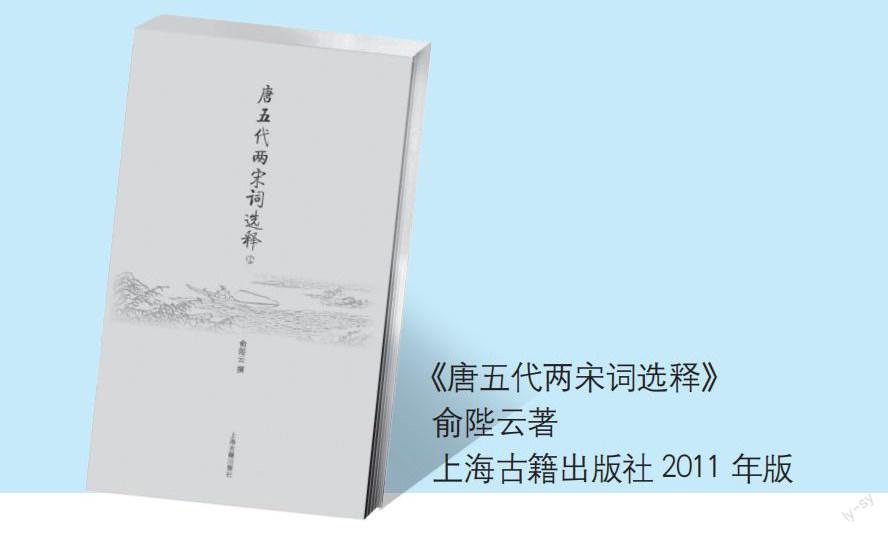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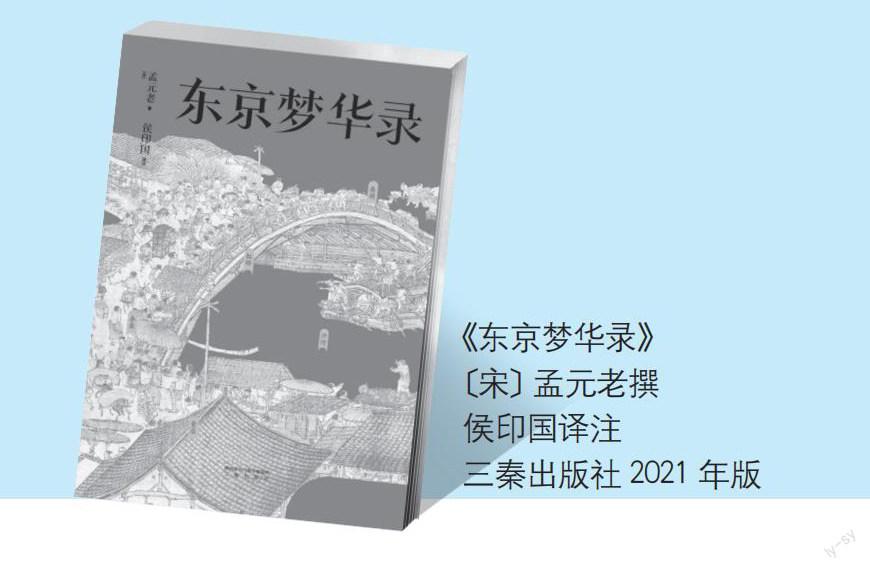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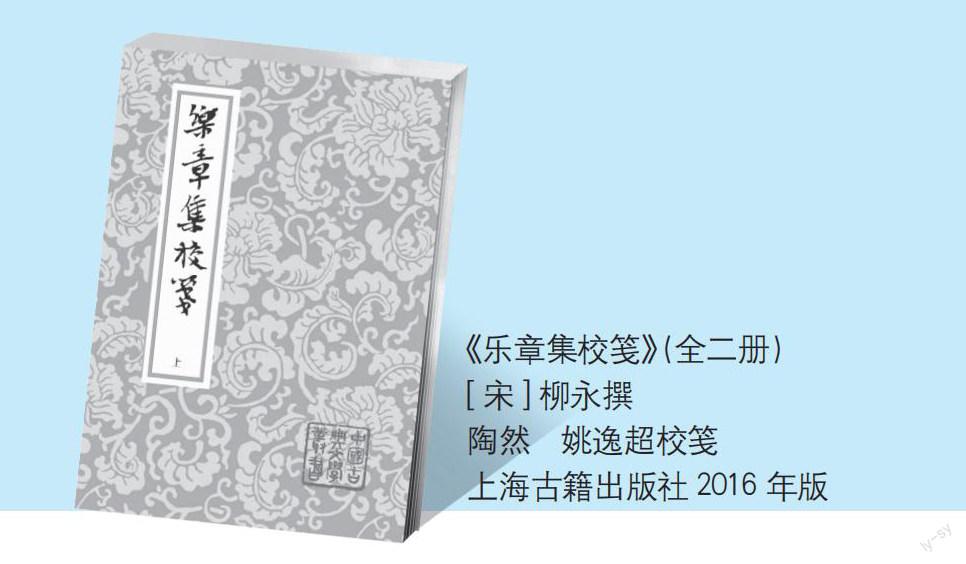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
柳永约在九八七年生于福建,字耆卿,又名三变,原属仕宦人家子弟。幼年时,跟着其父离开福建。二十岁左右,他到了杭州,便常和妓院中人交往。据杨湜《古今词话》云:“孙(何)知杭州,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之词,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欲因朱唇歌于孙相公之前。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府会,楚楚婉转歌之,孙即延耆卿预坐。”那首《望海潮》,尽态极妍地描写了杭州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繁华优美的景象。这后门走得巧,歌词又写得好,楚楚珠喉一啭,自然博得当时杭州知府孙何的欢心,立即会见了柳永。这首词一经传出,大受欢迎,柳永也声名不胫而走。特别在花街柳巷,“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还出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佳话。柳永风流倜傥,才貌双全,于是歌姬舞女皆慕名而来。
在江南,他混了好几年倚翠偎红的生活,后来便跑到当时的首都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谁知道屡试屡败。当时的仁宗皇帝,本来也是流行歌曲的拥趸,还唱过柳永所作的流行曲。但即位后,他要推行儒家思想,净化社会风气,便对柳永摆出一副不屑的样子,说他还考什么科举,“且去填词”吧!当时,包括晏殊在内等多位士大夫,也奚落柳永,不愿与他为伍。柳永也就索性自称“奉旨填词”,自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据知他“骨气高健,神韵疏宕”(郑文焯批校《乐章集》序),便当起了专业作家来。
在北宋初年,尽管边患不息,但中原和江南地区,经济稳定发展。特别是那些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人士,大量涌入都市,经营消费,城市也出现畸形繁荣的局面。据《东京梦华录》载,在首都开封,“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在那里,有许多豪华的酒楼,供人消费。“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歌姬舞女,喜爱柳永,需要他写词度曲。在《长寿乐》中,他写道:“太平世。少年时,忍把韶光轻弃。况有红妆,楚腰越艳,一笑千金何啻!”在《凤栖梧》中,又写道:“旋暖熏炉温斗帐。玉树琼枝,迤逦相偎傍。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
情与欲,是人性的表现,这在古代民歌中,早就有所描写。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男女接触的机会增多,礼教的藩篱日益松动,在文学作品中人性描写的一面,也无法遏止。
在北宋,柳永那些大膽的描写,受到上层人士的鄙薄,后来毛晋也说他写的多是“闺帏淫媟之语”(见《乐章集·跋》)。确实,这样的描写,会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但它之所以受到市民大众的欢迎,又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这恰好说明,即使是作为雅文学并且作者也多为受过儒家教育的北宋词坛,在农业经济受到商品经济冲击的情况下,也相应地会出现松动的状态,部分作者逐步迎合市民的情趣,也是难免的文学现象。而柳永,正好是在北宋词坛上,带着浓烈市民化色彩进行创作的领头羊。
就词作取材而言,柳永词作多与青楼情爱有关,这与晚唐的“花间派”作者温庭筠相近。但温词写的多是小令,辞藻华美冶艳,甚至“浓得化不开”(徐志摩语)。而柳永写的多是篇幅较长的慢词,节奏舒缓,用语通俗晓畅,更适合市民大众的口味。当然,这也与不同时代音乐发展的不同有关。沈曾植说:“五代之词促数,北宋盛时啴缓,皆由燕乐蜕变而然,即其词可悬想其缠拍。花间之促碎,羯鼓之白雨点也;乐章之啴缓,玉笛之迟其声以媚之也。”(《菌阁琐谈》)伴奏乐器的发展,特别是笛声可以让声音不间断地拖长,有利于慢词铺展内容,有助于展开歌词叙述性的描写。加以语言趋向通俗化,慢词让市民大众更容易理解。这正是柳永注意到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较多写慢词的原因。
不过,柳永和温庭筠一样,毕竟出身于官宦之家。尽管对于科举考试,有时柳永也摆出不屑的姿态,但终究把通过考试进入体制作为唯一的出路。因此,尽管在科场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到了五十一岁时,竟因有了“恩科”的开设,柳永被朝廷开恩录取,当了“屯田郎”,作为管理盐政的低级官吏,算是了却了当官的心愿。
当然,在长达三十多年屡屡铩羽而归的情况下,他也一直是满腹牢骚的。发为词曲,他便写了不少磊落不平以及漂泊之苦去国怀乡之作。毛晋在《乐章集·跋》中说他“尤工于羁旅悲怨之辞,闺帏淫媟之语”,这确是事实,它概括了柳永词作的主要内容。这两类作品,也恰好是柳永思想两重性的写照。当然,在词坛上产生广泛深远影响的,是他写的与闺帏情爱有关的词,一些以爱情为题材,写得情真意切的作品,闪耀着追求人性的炽热之光,上引的《雨霖铃·寒蝉凄切》,正是这方面的作品中最为成功之作。
柳永屡试不第,在四十二岁的时候,便离开开封,乘舟南下。上引《雨霖铃·寒蝉凄切》一词,描写的是他与所爱的人分别时的情景,抒发的是对爱情真挚的感受。至于送行者是谁,我们无从知晓。
这首词,选用了[雨霖铃]的词牌。据唐代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记载,安史之乱时,唐玄宗不得不让乱兵杀死杨玉环。到了四川斜谷,听到了雨声和房檐挂着的铃铛叮叮作响,他想念杨妃,悲从中来,便制作了[雨霖铃慢]一调。此调充满悲伤哀怨,柳永便选择了这曲调作慢词,用以表达和相爱者告别时,难分难舍的情感。
词的第一句“寒蝉凄切”,在音律的处理上,十分特别。按照词谱的制作,所谓“慢词”,整首曲调节奏的进行是舒徐缓慢的。就词谱来看,作曲者为了让听者在听觉上获得不同的感受,便在旋律节奏的速度上着笔。而节奏的缓慢或急促,则表现在押韵间隔时间长短的不同。凡是在一句或两句后,便押上韵的,这表示语气到了一个节奏点。节奏点愈密集,乐曲进行速度便愈显得急促。反之,如果在三句或四句后,才押上韵,押韵点相隔较远,乐曲进行的节奏速度,便显得悠悠慢慢。在《雨霖铃·寒蝉凄切》这首慢词里,多数的乐句,是三句才要押韵的。如“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韵押于“发”;“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韵押于“阔”。这都是三句之后才押韵。至于下阕的句式,也多是如此。所以,当歌唱这首曲词的时候,必然是节奏缓慢的,这和整首词的内容所要表现的情绪,是相互适应的。
有意思的是,《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开端,第一乐句,竟只有四个字。按舒梦兰所辑《白香词谱》,这里便须押韵,自成段落。这一来,说明它在全曲旋律的进行中,其节奏,和其他悠长的樂句,完全不同,有着特别重要的分量。于是,从音节的安排上,柳永首先下“寒蝉凄切”四字,一下子就令听众产生特殊的感觉。
首先,柳永通过听觉,点明了他和爱侣分别时的规定情景。这时候,他们听到了秋蝉发出的声音。在秋天,树上的雄蝉腹部鼓膜受到振动发出的声音,这是受到气候变化或求偶时,昆虫本能的一种举动。对蝉而言,它也无所谓感到“寒”或“凄切”的问题,是诗人把自己的情绪,赋予蝉声的反射。唐代虞世南以蝉鸣“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比喻自己的品格;李商隐写蝉,说它“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以秋蝉的鸣声,比喻自己的困境,无非都是以蝉自喻。而柳永在词的首句,排除了一切的声浪,独以单调颤抖的蝉声,响彻周遭,这分明是让读者感受到他和情侣别离时客观环境的凄清。由此,柳永当时的感情,也从他对场景的设置中透露出来。可以说,柳永在本来节奏徐缓的慢词里,劈头以短促的句式呈现,这让人猛然惊觉,感受到他们的分手,有一种异样的气氛。而柳永选择了[雨霖铃]这一独特的曲式,用以展现主观情感和客观环境的独特,也正好说明他艺术水平的高妙。
词的第二乐句:“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这句以“对”字领起,然后点出告别的地点、时间和天气。长亭,是人们在水边或路边修建的亭子,是供旅人休息或用作送行的地方,古人常有“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的说法。“晚”,是指天色昏暗下来了。作者选择了这一时间,和写在白天别离的情景,有所不同。如果在早上,分别时应是“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温庭筠《菩萨蛮》),或者是“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牛希济《生查子》)。早上分别的景色,自然也会引发当事人依依不舍的情愫。而柳永把分别的时间安排在昏暗的傍晚,这一来,在听觉出现一片寒蝉凄咽的感受中,在视觉惨淡的暮色中,他只感到前景一片昏暗,那低沉压抑的心情,也显得愈加浓重。而且,点明是在晚上的离别,显然也与下阕联想到第二天早上的心境,相互呼应。所以,柳永似乎不经意地下了一个“晚”字,其实有着千钧之重。
这还不够,柳永又进一步抒写他和恋人分别时突然遇到的景况,那就是“骤雨初歇”。骤雨,是指忽然来了一阵雨。请注意,柳永选用“骤雨”的意象,也是别有深意的。按词谱,这句第一、第二字,均须仄声,那么,要写下雨,选用“大雨”“夜雨”之类的词组,也是可以的。但作者偏偏写他将要长亭别离之际,下的是一阵“骤雨”。这雨,倏然而来,倏然而止。如果没有这意想不到的阵雨,远行人便应按时上路,不可能让他们多了一段宝贵的可以延误的时光。但是,柳永又指出,这雨只是“初歇”,至于它会不会再洒下来,把人淋成落汤鸡,谁也不知道。那么,该不该趁它初歇的机会,赶紧登程?又让他颇费踌躇。于是,柳永写这意想不到的骤雨,便让离人的内心多了一分矛盾和牵扯。更有意味的是,柳永运用的意象,只是雨的“初歇”,它刚刚停住,亭角树梢,雨水欲收未收,还在滴滴答答。天若有情,这就颇像相爱者在分别时,眼眶里强忍的泪水欲渗未渗、欲滴未滴的模样。当然,柳永写的只是“生离”,他和恋人虽然心中不舍,却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过于悲伤。显然,柳永让骤雨初歇的客观景象,和人的内心世界互相照映,其间意味深长,而又很有分寸。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柳永在这句之首,下一“对”字。就这乐句而言,它既属衬字,又有引领下文的重要意义。它承接这首词“寒蝉凄切”的第一句,引出了离人将要分手的时间、地点,但面对这一切,柳永使用的竟是“对”这一个不带任何情感的动词,似乎主观的情感和客观世界各自独立,互无干涉。就像唐代诗人张继在《枫桥夜泊》中写“江枫渔火对愁眠”那样,江枫是江枫,渔火是渔火,旅客是旅客,他们各不相干,各自默默相对。这表面上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对”字,正表现出张继在寒山寺引发出物我两忘的禅意。柳永在这一乐句,也使用这并不带感情色彩的“对”字,似乎发生的一切,在他脑海中只是一片空白,冥冥漠漠。其实,这无情无绪的动词,正是他凄苦到近于麻木的表现。在柳永的词作中,是很注意“对”字的运用的,在他另一首名作《八声甘州》的第一乐句,也写到“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詞的第三乐句:“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都门,指的是汴京的城门。这说明,他的恋人,不仅把他送出家门,而且远送到不能再送的城外。按惯例,人们要在帐幕里置酒饯行,这是不得不分手的恋人最为难受的时刻。元代的关汉卿,不是在《沉醉东风》中写过“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搁着别离泪”“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吗?不过,柳永却没有直接写他和恋人的痛煞煞,倒是说彼此“帐饮无绪”。这一反常态的表现,与上句那无情的“对”字相呼应。他们眼看着分手在即,千言万话,却无从说起,头脑中一片空白。
紧接着,作者写了“方留恋处”一句。这“方”字很重要,它说明,看来他俩知道骤雨停歇了,回过神来,麻木的头脑忽然清醒,知道立刻就要分手。这一下,紧张了,正要互诉衷情说些悄悄话的时候,撑船的艄公一看时间不早,不能再让他们磨磨蹭蹭,便催促着要开船出发。他们更急了,接着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在关键的时刻,他们只是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心里有千言万语,到嘴边却说不出,多少话语,像被堵塞在喉咙里。这两句,确是写出了伤心到极致的情态。在现代,交通发达,通信便利,天涯若比邻,人们不容易像古人那样感受到分离的痛苦。那“无语凝噎”的无声之恸,那憋在心里的痛楚,其悲伤的程度,更甚于哗哗啦啦地啼哭发泄。
就在写到伤心人心情极度压抑的时候,柳永竟又一笔宕开,接着是“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这长长的乐句。
这句以“念”一字领起,它由上阕最后的乐句开始,贯注到下阕,一直到整首词的结束。这是柳永由两人别离的情景,想到自己分别以后的处境。所谓“去去”,是去呀、去呀,越行越远的意思。当时,柳永走的是水路,江水连接千里,一路上烟雾茫茫、波浪滔滔,前边景色,也迷蒙地混成一片。他看到这时天色已晚,暮云低压。所谓“沉沉”,是越压越低的意思,它与“去去”,相互映照,从意义和声音上让这词添增了缠绵悠远的效果。柳永又想到,他将要前往的地方,是远离开封的南方,那在古代被称为吴楚之地。他的想象中,在广阔无垠的远空,也一定是茫茫寞寞,暮色低垂。离岸时,他从纵向看到低压的云,沉沉下压;遥望中,则从横向想象到江南辽阔的天。视界从近推到远,从实景想到虚景,从纵向联系到横向,纵横结合,浮想联翩。总之,这一切,让他既感到胸口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又觉得眼前是一片空虚,无限落寞。句首一个“念”字,便把眼前之景,推向心中之景。至于到底是情是景,则任由读者展开自己的想象。
柳永的词,常会写晚上离别的景况,像在《引驾行·虹收残雨》中,上阕开首写:“虹收残雨。蝉嘶败柳长堤暮。背都门、动离黯,西风片帆轻举。”这词运用的意象,也和《雨霖铃·寒蝉凄切》差不多,但艺术水平远不及后者。《引驾行·虹收残雨》只把残雨、蝉嘶、暮、都门等意象,作为送别的背景,一一罗列,用以衬托别意的凄凉。《雨霖铃·寒蝉凄切》的上阕,当然也是情景交融,但更重要的是,它着眼于抒发别离时情感的曲折变化。它首先从写蝉声引发离人凄切的情绪,接着陷入静默与麻木,忽又猛醒过来,知道分手在即,准备诉说离情,却又说不出口。这几句用语流畅平顺,又跌宕起伏。别离人对奈何天,柳永把那种曲折而又缠绵的心情,形容到极致。
在上阕,柳永已经细腻而激切地展开了他惜别情景的描写,经过了“过片”的间歇,沉重压抑的情绪稍得舒缓,词人便回过头来,以较为平静的笔触,表明他为什么对爱情如此执着。由于作者在上阕最后的乐段是以三句作为长乐句结束,这在慢词中,旋律节奏的进行也必然是舒缓的。那么,可以推想,这首《雨霖铃·寒蝉凄切》的“过片”,作为乐曲前后两段榫接的音乐“过门”,必然也有着相对延长的时间空隙。于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受体,便有足够的时间,既承接上阕所写别离的景况,又从压抑的氛围中,缓过气来,从而让下阕有可能展开另一种情味。
在下阕,诗人先以“多情自古伤离别”这具有普遍性的道理着墨,语势平缓。柳永这平实的诉说,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在登程前表现得如此悲伤。这句话以先退一步的蓄势,但紧跟着,他情绪又趋变化:“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更让他痛楚和难堪的是,他和恋人分别的时刻,正碰上最不该分别的日子。
清秋节,就是重阳节。在宋代,重阳节是很受重视的节日。据《东京梦华录》“重阳”条载:“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都人多出郊外登高。”那时候,重阳节亲友们要互相馈赠,一起宴饮,非常热闹。柳永深感,如果不是别离,他必然也会与恋人在一起欢乐。但他偏偏在这应该相聚的时刻,独自离开,冷落了应该欢乐的清秋节。
柳永在上阕,浓重地描写了分离的苦恼,下阕,从开始便连续写了两句解释性的大白话,悠长的语气,和上阕意象密集的写法,截然不同。但是,柳永正是以这似乎是淡淡说来的两句,给上阕中他所写的迷惘心结,做出无可奈何的自开自解。像是戏剧演员,在规定情景中经历了激烈的思想冲突之后,向观众展现的内心独白。接着,柳永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长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怎样理解这句词?它为什么能够让读者获得审美的感受?值得我们仔细探讨。近代词学大家陈匪石先生在《宋词举》中说:“‘杨柳岸’七字,千古名句。”“盖不独与写景工致,而一宵之易过,乍醒之情怀,说来极浑脱且极深厚也。”俞陛云先生也说:“客情之凄凉,风景之清幽,怀人之绵邈,皆在‘杨柳岸’七字之中。”(《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他们的意见,值得参考。但单独地抽出这七个字,不把它和整首词的构思联系起来,或会有武断之嫌。
陈先生说它是“千古名句”,自然是不错的,但它的妙处,却首先不在于“写景工致”,而恰好在于它的不工致。我认为,柳永甚至是有意让这七字写得比较含混、含蓄,而非写得工整细致。请注意,这七个字,实际上有四个词组:杨柳、岸、晓风、残月。它们之间,是没有任何连属关系的。例如说“杨柳岸”,到底是指有杨柳的堤岸,还是堤岸上有杨柳?是晓风吹拂着杨柳,是杨柳岸上挂着残月,还是晓风在残月的照影下飘忽?这些,柳永都没有说明,而任由读者自己领悟和联想。
在我國古代,文学评论家早就提出“意境”的理念。唐代的王昌龄就说过“诗有三境”,最高的境界,称为意境。如果读者能够获取作者在审美载体中抒写的意象,转化并进行再创造,就获得了司空图所说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这也是司马光所说的:“古人为诗,贵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温公续诗话》)他认为作家的创作,能够诱导读者进行再创作,才能让作品达到最高的水平。法国的哲学家、文学家萨特也认为:“精神产品这类既具体又臆想的客观,只有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并通过别人才有艺术。”(《境遇集》第二卷)
《雨霖铃·寒蝉凄切》中这被人称许的七个字,实际上柳永只是给读者选择了几幅图景。这几幅图景,各自有相对独立的意味。像“杨柳岸”,杨柳枝叶,摇曳扶疏,不同于松柏岸;“晓风”,当是吹过清冷飘拂的风,不同于寒风或狂风;“残月”,也当是天快亮时将要落下的光微影淡的月。这是几幅情调接近却又互不统属的图景,它们之间,既没有连接词,也没有动词。词与词之间没有联系,没有留下着墨的空间,此属“虚”写;但是作者又分明是在展开一幅又一幅的图景,是让观者可以捉摸得到的实景,这又属“实”写。于是,虚与实的结合,便能让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大脑皮质细胞自行组合,进行再创造,从而产生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这做法,正像现代电影拍摄中的“蒙太奇”镜头,通过不同画面的组接,让观众自行感受审美客体的意味。显然,正因为柳永在这七个字中,没有很明确的指向性,反而容易让人产生“读之皆若身历其境,惝恍迷离,不能自立”的感受(沈谦《填词杂说》)。这种虚实结合获得意境的艺术技巧,在柳永之前,唐代温庭筠写过,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在柳永之后,元代的马致远也写过,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些诗句,一直享誉文坛。看来,秉承中华传统哲学理念,派生出的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正是诗人们在创作上获得成就的基础。
我认为,不少人对柳永“杨柳岸”这一乐句的理解,往往是不确切的。他们以为柳永写的是实境,是他酒醒后看到的景色。其实,在这里柳永所写的只是他臆想中的景。我们要注意的是,《雨霖铃·寒蝉凄切》上阕最后的乐句,作者下的是“念去去”三字。这句由“念”字领起,一直统领到词的下阕以至全词的结束。这说明,从“千里烟波”开始,以至下阕所写的景色,都只是他想象之中的意象。如果“杨柳岸、晓风残月”,真的是作者当下之所见,那么,就与“今宵酒醒何处”,发生矛盾。因为他明明说的是“今宵”,亦即指别离当天的晚上。这一来,他怎能事先便看到隔天的“晓风残月”呢?如果真的是看到了晓风,除非上句改为“今朝酒醒”或“昨宵酒醒”。显然,这里他“看”到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是他心中之景。柳永在创作上的巧妙之处,正在于把自己心中之境,转化为人们可以感悟到的实境。至于他能把这心中之景,写得如此凄清,如此迷惘,是他掌握并概括了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性的意象,从而引发审美受体的再三寻味,提升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境界。
在《雨霖铃·寒蝉凄切》中,“杨柳岸”这句之所以让人获得美的感受,是和柳永艺术构思的精巧完全分不开的。他在上阕中,首先稠密地敷写种种具有压抑性的意象,强化沉郁的气氛,如写凄切的蝉声,骤雨的来临,船夫的催促,临别的凝噎,暮霭的沉沉,等等,一个又一个意象的堆积,让人简直喘不过气来。而经过了“过片”一段音乐的调适,便平静而又朦胧地展开了一幅萧疏淡泊迷离凄清的风景。于是,上片和下片形成鲜明的落差,取得移步换形、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这也是《雨霖铃·寒蝉凄切》获得意境的基础。冯煦说:“耆卿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蒿庵论词》)这评价,也可用作说明《雨霖铃·寒蝉凄切》的艺术特色。我们也只有从柳永对这首词的整体构思中,才能真正了解“七个字”的意境。
还需要注意的是,北宋词坛具有的特殊环境。那时候,城市经济繁荣,文士一方面向市井靠拢,另一方面,由于朝廷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文人大量进入政坛,面临着激烈的党派斗争,这一来,又产生了逃避的情绪。欧阳修不是说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吗?与此相适应,一时间,物我两忘,高雅脱俗,也成为北宋文士们所追求的审美情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山水画要有“三远”,亦即“平远”“高远”“深远”。这审美理想,正是当时整个艺坛追求把想象中的时空尽量延伸,以期达到心灵超脱的反映。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上阕,在以沉重压抑的笔触抒写离情之后,又逐步开放为萧疏平远的意趣,这和宋代(包括宋元以后)文人的审美追求,有着深远和密切的关系。因此,人们对《雨霖铃·寒蝉凄切》从上阕意象的浓密,转向下阕疏淡平远的构思,十分赞赏。这里面也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柳永的词既乐于在歌台舞榭中偎红倚翠,又夹杂着萧条淡泊娴静幽远之情,这正好表现出宋代许多骚人墨客的心态。
在压抑的情绪逐步疏离冷却以后,柳永蓦然想到自己今后的处境,情绪又趋于酸楚。他想到“此去经年”,即使有良辰美景,也是虚设的;即使自己有美好的情怀,也再没有知心人与他同享。他知道,等候着他的是长期的孤独。整首词,就在反问的口吻中结束,更显得意犹未尽,缠绵悱恻。
又,按词谱规定,柳永使用[雨霖铃]一曲,上阕只有开首的一个短乐句,在这以后,直到全曲结束,连续用的多是长乐句。这说明,柳永注意到乐曲的旋律节奏,需要和歌词内容完美结合,才能准确表达曲情和词意。像他那样既是音乐家又是诗人,懂得在诗词作品中,注意文学性与音乐性的和谐者,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人们把他婉转柔美的词风,视为开创了宋词婉约派的先河,也是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