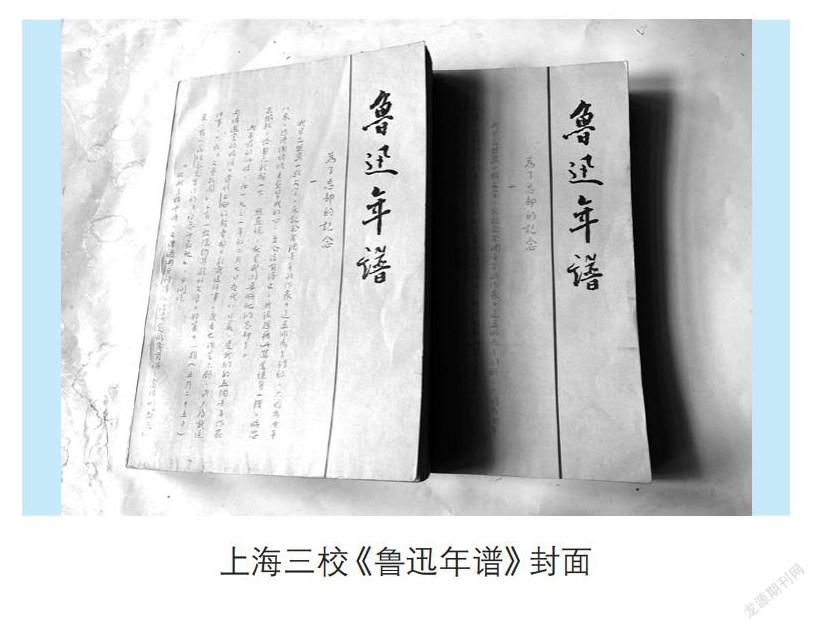上海三校《鲁迅年谱》编写经过
2023-02-05吴中杰
小引: 二○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接到古远清兄的电邮,说他正在编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时期的鲁迅研究史,“内有你们著的《鲁迅年谱》这一节,请提供资料,如主编写作背景之类,先谢谢!”次日,我即据他的需要,写了一篇回忆小文发给他。他收到后表示感谢,并说:“我在编书简续集,收你这两封可否?”古远清是一位多产作家,年过八十,还编写不辍,在疫情防控期间,也毫不怠懈,至少同时在编写两本书。但近日忽然从网上看到消息,古远清教授于二○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武汉逝世。这真太突然了!现即以这篇为他而作的文章来表达我的哀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来信,说他正在编写一本关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时期的鲁迅研究史,内中有一节要写我们上海三校集体编著的《鲁迅年谱》,希望我能提供一些具體材料,如主编是谁、写作背景如何等。这使我感叹时间的流逝,真如白驹过隙,当年所做的工作,已成为别人研究、追述的一段学术史,而参与工作的同伴,则大都已经作古,仅剩下我与龚济民二人,而济民兄远在美国,久未联系。我如果不将这本书的编写过程记录下来,也许就要流失了。虽然它在鲁迅研究史上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当时,也曾掀起一点波澜,远清兄要我叙说本事,也许还有点价值。
这本书的动议,是在一九七二年八月。那时,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一批教师,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这时,学校已重新开始招生,招进来的学生叫作工农兵学员。教师中有些人被分配到班级,辅导工农兵学员,另一些人则被安排在系资料室做资料工作,我就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叫我们管理图书资料,而是为一些文件和资料做注释。我不大想做这些事,就提出要编一部《鲁迅年谱》。系领导请示后通知我,鲁迅年谱可以搞,但不能由我一个人来编,可以在复旦、师大两校组织班子来搞。于是,就在两校组织起两个年谱组班子来编写《鲁迅年谱》。
这里要说明一下“两校”称呼的由来,以及它的范围。上海有中文系的高等学校,在一九六六年之前只有三所: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大学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组建的,当时还没有。七十年代初,忽然刮起一股并校风,华东师大与上海师院合并,称为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和上海政法学院,则并入复旦,仍称复旦大学。所以当时我们这个编写组就叫复旦、师大两校年谱组。到七十年代后期,师大、师院两校又重新分开,财经学院和政法学院也仍旧独立。但华东师大那时仍称上海师大,上海师范学院也还没有升级为上海师范大学,所以一九七九年《鲁迅年谱》出版时,编写者的名字,就署为“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鲁迅年谱》编写组”。这些称谓署名,都反映了一定的历史背景,不加说明,后人不易弄得清楚。
鲁迅年谱组成立之后,分为两摊:一在复旦,一在师大。复旦年谱组成员有:赵景深、徐震、刘国梁、秦家琪、王继权、潘旭澜、吴中杰。师大年谱组成员中常与我们接触的是龚济民和石汝祥,其他还有哪些人我不太清楚,当时也不便打听,后来事过境迁,也就忘了打听。曾经开过一次联席会议,讨论两件事:一体例,二分工。分工马上就定下来:师大年谱组编前期(1926年之前),复旦年谱组编后期(1927年之后)。讨论体例时,大家说,既然年谱的编写由我发起,自然应由我提供体例样本。我无可推辞,就答应下来,编写了一九三六年一年的年谱,作为样本,打印出来提供讨论。大家很快表示意见,说我的样稿基本可用,在细节上作了一些改善。这样就开始工作了。
当时复旦中文系设在仙舟馆楼上,我们年谱组就安排在楼梯边朝北的大房间里,隔着大草坪与登辉堂(现改名为“相辉堂”)遥遥相对。开始年谱组由徐震负责,不久徐震调走,改由刘国梁任组长。起初赵景深先生也天天来上班,跟我们这些小青年谈笑风生,后来系领导考虑到他年老体衰,家里离校又远,就照顾他不来上班了。但我仍常到他家借书看,主要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书籍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的小说。赵先生家藏书丰富,虽不是什么名贵版本,但小说、戏曲书籍很是完备。
初稿完成后进入修订阶段,刘国梁心脏病发作,就退出年谱组工作,回家休养去了。剩下王继权、秦家琪、潘旭澜和我四个人。师大那边,则剩下石汝祥和龚济民二人。定稿组就由我们六人组成。接着,又修订了大半年。
编写《鲁迅年谱》这一工作,当时并不被看好。教师们都以下班级参加教学活动为荣,即使不能讲课,跟班辅导也是一种荣誉,所以很看不起我们编年谱的工作。我知道这部书是出版不了的,只是想借此机会理清鲁迅思想的脉络,查明当时思想界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并多读一些书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而且按蒋天枢先生的说法,编写年谱是基本的学术训练。所以我倒是很认真地做这项工作的,并且常以编年谱的名义,要求系资料室调鲁迅文章所涉及的书来看,也要求去查阅当年的旧报刊。那时系资料室负责人是廖光霞,她很帮忙,拿着我们的书单,千方百计到校图书馆调书出来,满足我们的要求。我后来写《鲁迅传》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正是此时打下的基础。
大概系领导也发现了我们借编《鲁迅年谱》的名义来大读其书的倾向,就找我们谈话,说你们不能长期闭门修改《鲁迅年谱》,要限期修改好。那时,工农兵学员陆续招进,辅导教师不够分配,就把我们也分发下去。这样,我们就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匆匆结束了年谱的编写工作,准备下班级去。
我们《鲁迅年谱》的编写工作刚一结束,就有人来抢夺这部年谱,作为他们编写《鲁迅传》的参考资料。此事说来话长,我以前发表过文章,可供参考。
但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鲁迅年谱》又要回来了。这时收到李何林先生负责的鲁迅研究室的来信,说他们要编写《鲁迅年谱》,希望我们的《鲁迅年谱》能借给他们参考。我们早就读过李何林先生的书,知道他是一位正直的鲁迅研究先行者,所以就组织工农兵学员抄写了一份寄给他们。同时,我们自己也积极寻求出版。这时,恰好王继权的同班同学、在安徽大学教书的吕美生兄来沪出差。吕美生说,他们的同班同学朱兴华在安徽做出版局局长,不妨与他联系一下。朱兴华很热情,帮我们联系了安徽人民出版社的文艺组,很快就落实下来。这个文艺组,就是后来的安徽文艺出版社,当时各个专业出版社都合并在一个人民出版社内,压缩成一个出版组。潘旭澜当时回福建老家养病去了,我们五个人再将《鲁迅年谱》修订了一次,交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们很快就排印出来,王继权、秦家琪、我和龚济民四个人赶到合肥去看校样。书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出版,很受欢迎。第一版印了十二万册,很快卖完。本来说要再印,但好像并没有印,因为接着别家的《鲁迅年谱》也出来了,别的鲁迅研究著作也陆续出版,我们的《鲁迅年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鲁迅研究史上的一个存在。
我们这部《鲁迅年谱》没有主编,当时出版的书籍一般都署某某编写组或编译组编写,我们也循例,署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鲁迅年谱》编写组。后记里写了定稿人的名单:“参加本书定稿工作的有吴中杰、石汝祥、龚济民、秦家琪、王继权;参加大部分定稿工作的有潘旭澜。”这是我们的组长王继权所写。他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是因为这项工作是由我发起的,而且我也写得最多;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那是由于他的谦虚,其实许多实际工作都是他做的,贡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