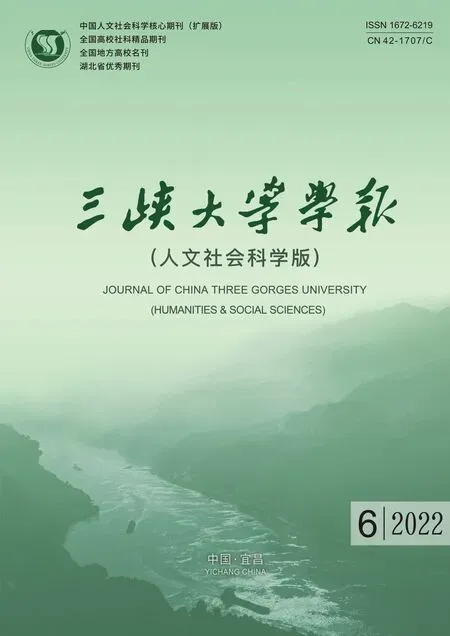英语世界唐代小说翻译的文学价值认同
2023-01-26何文静
何文静
(三峡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唐代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枝奇异之葩,被南宋著名文学家洪迈誉为“与律诗称一代之奇”[1];在古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大量译介,在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小说翻译整体关照中,呈现出了显著而独特的形态与特征[3]。从翻译动机来看,英语世界的唐代小说翻译呈现出了一定的非文学价值取向[6],但以“搜奇记逸”“叙述宛转”“奇幻怪诞”[2]见长的唐代小说在英语世界得到大量主动译介,很大程度上也是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在异域得到认同的结果①。具体地,汉学系统创造的译本以文学读物类为主,目的在于为英语世界的目标读者提供纯粹的文学读物,如翟理斯所译的《中国神话故事选》、叶女士的《〈唐代丛书〉选译》、倪豪士的《唐代传奇选》等以及白之、宇文所安和闵福德等编纂的文学选集。其次是文学读物和文化研究兼类,此类译作既为文学读物,同时又是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素材,如倭讷的《中国古代神话和传说》、杜桥德的《〈李娃传〉的研究、校勘及英译》、卡丽·里德的《中国怪异编年史:〈诺皋记〉》和《酉阳杂俎》等[3]。总体上,英语世界的唐代小说翻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目标文学和文化系统内再现唐代小说的文学价值。从大量译著(作)的序、跋、注等副文本以及专业译评等可以看出,目标文学和文化系统对唐代小说的文学价值的认同是英语世界的唐代小说生发的主要动因。这种认同表现为两种形式和层次,即译者的文学价值认同和目标文学系统的形式项引进。
一、译者的文学价值认同
文学翻译活动的发生过程中,译者(包括由译者、赞助人等众多个体或机构构成的译者系统)的翻译行为很大程度上具有自主性,尤其是翻译活动的早期阶段。具体到英语世界的唐代小说翻译,从汉学家翻译第一个篇目开始,很多文本的翻译很大程度上是汉学家的自主行为,这种自主性主要体现在汉学家文本选择环节对所选篇目的文学价值的判断上。汉学家译者的这种自主选择体现的是唐代小说在英语世界得到的基本认同,正是汉学家译者对唐代小说文学价值的认同,唐代小说在异域的翻译活动才得以生发。可以说,汉学家译者的文学价值认同是英语世界的唐代小说翻译发生的根本驱动力。
A·L·G在翟理斯所译的《中国神话故事选》序言中指出,翟理斯选择翻译包括《枕中记》在内的十数篇中国古代小说,意在将这一译著“与同一系列(高恩国际图书馆书系)中的《日本神话故事》配成姊妹篇”,因为“将两卷译作中的故事比较起来非常有意思:这些故事(相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而言)都显得非常离奇古怪,读来令人赏心愉悦;但是华夏民族精神与日本民族精神之间的迥然差异在这些作品中都淋漓尽致地得以体现出来”[7]。这里的序者无论是否这一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其表述也代表了包括赞助机构和译者翟理斯本人在内的译者系统对这些文本的认同态度——这些小说不仅“非常离奇古怪”,而且深刻刻画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系列丛书在内容编选上同时选取中国神话故事和日本神话故事并供读者将两者用于对比阅读,反映了译者英语世界的目标读者群体对神秘的东方充满期待和想象的预判,甚至这一意图本身就是这种期待和想象的表现与结果。韦利在《古文选珍(续)》中选译了两则唐代小说——《莺莺传》和《李娃传》,他对包括这两则小说在内的所有收录作品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烈的认同,仅仅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挑选了“几则自己感兴趣”同时又“可能会得到充分翻译”的作品,不过,从寥寥数语中仍然能看出他对包括唐代小说在内的中国古代小说的态度较为暧昧和隐晦。
如果说翟理斯对选译的这些小说的认同性评价并不明显和直接、韦利对两则唐代小说的认同比较勉强的话,其他很多汉学家的译本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赞助人、编者和(或)译者本人对唐代小说或包括唐代小说在内的中国古代小说选本的认同态度。
20世纪30年代,英国汉学家叶女士在清代学人陈莲塘编纂的《唐代丛书》基础上选译了数百个经典篇目。在译序中反复表述自己对唐代小说的看法:很多篇目非常“有趣”;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始有意为小说”的特定时期创作出来的作品,“这些数量庞大的短篇作品也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显著特色”,等等[8]。这些看法就是对唐代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学价值的肯定,也就是译者对文本积极的认同态度。又如,杜桥德认为他1989年在《译丛》上发表的三则唐代小说 “是一种公元八世纪前后流传于中国的、以凡人与神女(尤其是龙女)之间的婚媾为题材的传奇题材”“独具趣味”[9]。罗慕士在《中国神话和幻想故事》引言中指出,(包括6则唐代小说在内的)“这些故事每一篇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用朴实的腔调真诚地向我们讲述人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10]。美国汉学青年学者卡丽·里德在她的几种《酉阳杂俎》译作中谈到这部“奇书”之奇:从体例来看,这部唐代大型文集的确是一部“令人陶醉、值得研究”的作品,从中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内容,很多故事“情节复杂”“夹杂倒叙”“诗文相间”,有些采用“大量对白和细致描述”,巧妙利用“表现技巧”来推动故事向高潮和结局发展。“这些小说富有生动的戏剧性效果,细节描写栩栩如生”,绝非民间故事的简要记载,而是对轶闻逸事的刻意充实和加工[11]。
直接翻译中赞助人、编者和(或)译者对所选文本的认同意见尚需要从字里行间去捕捉,而转译本身就可以认定是对所选文本的绝对认同和全盘接受态度。1964年英文版的《金匮:二千年中国短篇小说选》系由德国汉学家鲍吾刚和傅海波1959年所译的同名德文版转译而来,其中包含《莺莺传》和《李娃传》等8个唐代小说经典篇目。由于德文版原译在西方读者中受到广泛欢迎,该译著先后两次重印。英译版中,傅海波的原译“绪言”部分也被全文转译,包括唐代小说篇目在内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篇目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中国古代的作家们没有遵循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的教导,我们今天应该对他们心存感激,因为如果他们严格遵循了孔夫子的这一训诫,中国古代文学不会产生任何杰作,我们也会因此缺少了一条有助于探究华夏文明精髓的途径——因为没有其它的途径能(像中国古代小说一样)帮助我们近距离接触中国人——华夏文明的承载者。因为,从文学产生以来,构成文学的真正主题的是人本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生命承受的重压之间的关系。[12]
傅海波的评价反映了他对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及人文价值的认同;同时,上述两个方面的事实也明显地体现出了转译者克里斯托弗·列文森对这些作品的认同态度:首先,该选集德文版在西方读者中的认可度是克里斯托弗·列文森认同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的重要参考依据和标准,毕竟德语文学和文化系统与英语文学和文化系统在文化属性上较为接近,德译版在整个西方读者群中获得的认可对英语世界的读者取向是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的,因此可以说,这些小说的德译版在西方读者中产生的既有影响在相当大程度上促使了克里斯托弗·列文森从德译版转译,而不是直接从中国古代小说中选定文本加以英译。其次,英译版全文转译德文原译的“绪言”部分,而且译者并未在原有译序基础上增加任何解释、说明和介绍等内容,说明译者对原译中的“绪言”部分的基本认同态度是完全接受的。
二、目标文学系统的形式项引进
文学翻译活动同时也是两个文学系统之间发生干预的结果。英语世界的唐代小说翻译也是英、汉两个文学系统相遇并“接触”的基础上,英语文学系统形式库对唐代小说的相关主题、情节、形象等产生某种程度的需求并形成基本认同、然后对其进行经典化加工的过程。
相较而言,英语文学系统在译者对唐代小说的文学价值的基本认同基础上,有选择地对重点文本进行翻译并作为形式项加以引进则是更高层次的文学价值认同,同时也是唐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文学系统中得以经典化的表现。
英语世界早期的唐代小说翻译活动,目标在于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提供具有异国情调的普通读本,这既是译者的期许,同时也是客观效果,比如,早期汉学家翻译的《南柯太守传》《枕中记》《李娃传》《莺莺传》等篇目的翻译即是如此。
随着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小说了解加深,汉学家译者们对作品的认同感不再停留在简单的“有趣”“独特”等层面上。因此,对所选择的作品的文学和文化价值也有了根本性的深化。同样是文学翻译,但在更高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其翻译动机不仅仅或者不再是为普通读者提供娱乐性的读本,而是希望为英语文学系统形式库提供用以欣赏、批评和研究的引进形式项。
《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故事在英语世界流传的译本比较多,在韦利以正式文学读物的形式将这则小说带给英语读者之前,民俗学家翟孟生的译本已经出现了十余年时间。但韦利认为,“由于这个故事版本至今未得到充分翻译和评价,我认为其值得重新翻译,补足相关信息;(读者)要充分理解这个故事的话,这些信息是非常必要的”[14]。在充分认同这则小说文学价值的基础上,韦利认为既有的文化研究导向出发的版本没有为读者提供充分的必要解读信息,对文本中的文学价值挖掘是不够的③,因而有必要为读者提供一个充分展示这些价值的文学性译本。至于另一则唐代小说《田昆仑》的翻译,韦利直截了当地阐明:“鉴于这则故事似乎在西方民俗学圈中鲜为人知,我认为其值得全文翻译(至英语中去),留待民俗学专家将其与他们业已熟悉的同类文本进行比较研究”[15]。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汉学家梅维恒认为《叶限》得以接受的范围仍然太有限[16],以往的那些“无知无畏的民俗学家们”总是力图将这则故事放置到全世界范围的“灰姑娘”故事进化史中去理解它,结果导致他们的译文存在阐释不充分、不准确,甚至对其中的中国文化特色把握失当等问题。为了“给今后对这一迷人的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们提供便利”“本译文提供了大量有助于汉学研究的注释、历史背景信息以及关于文化习俗和信仰的解释”,目的在于让读者“在阅读这一则极富魅力的故事时,能够充分领略其中的艺术价值”[16]。
叶女士对《唐代丛书》中的很多篇目的评价是“有趣”。但是,其系统性地翻译唐代小说,目的显然不仅在于此,其对唐代小说更深层次的看法,是将唐代小说放置在中国神话史的语境中去审视其文学价值和学术意义:系统全面地引入具有断代性质的中国神话系统[8]。她认为唐代小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唐代时期的社会风气、政治运作形态以及社会百态。因为唐代小说,即便是爱情小说的创作基础也大都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有些作品是前朝逸闻旧事的演绎和加工;包括“朝野逸闻、社会传言、爱情、惨剧、阴谋等内容”都可以作为爱情小说的题材,这一点与西方现代小说的题材来源是一致的。另外,当时的人事也是唐代小说创作的丰富题材来源,“这些材料是唐代知识分子非常欢迎的创作素材,因为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都与他们同一阶层的人或同僚有关联”[8]。
美国著名汉学家李伟豪选择翻译唐代著名的艳情小说《游仙窟》,体现了他充分认同这个文本在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和文化意义。他认为,这则小说“避却道德教化”,不仅“弃离儒家传统训诫”,而且对长期以来社会正统文化所避忌的情色性爱等内容大加描绘,真切自然,属于唐代小说反传统、反儒家的典型代表[17]。基于对文本这种深层价值的认同感,他明确地阐明了自己将《游仙窟》作为英语文学系统形式库所需的文学项加以引进的动机:
我对《游仙窟》的探究目的在于(在译本中)进行详尽的注释,为更多的西方读者提供一个切实可读的译本……我不但希望创造一个译本,而且还试图解开包括作者身份和版本等与该小说相关的若干复杂谜团以及该小说影响日本文学的方式等。我的主要目标不在于创造一个权威译本——因为时间非常有限,困难极大,创造这样一个权威译本是不可能的——而在于通过翻译引起西方世界的大批(汉学界的)全才和专家对这则小说的关注。[17]
很显然,李氏对这则作品的翻译并非出于猎奇心理将其当成普通的情色作品加以引进的动机,而是将其当成一个中国古代情色题材文学标本引入其母语文学系统的形式库以待深层次的“解剖”性阅读。《〈李娃传〉的研究、校勘及英译》就是很好的例证,杜桥德围绕《李娃传》的英译,参照西方传统的莎士比亚学文本考证方法和模式,试图“对《李娃传》文本形式之外的叙事进行探讨,从而发现它与儒家经典、诗学传统以及(文本产生时的)语言环境之间的关联关系”[18]。杜氏对这则唐代小说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分析和阐释,辅以细致的注解、考证、评点和翻译,成为西方汉学采用厚翻译模式翻译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范例,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杜氏的大量注疏和评点都是为西方读者(包括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解读《李娃传》译本这一重要目的提供服务的,所以本质上仍然是文本翻译的工具和手段。杜氏率先将这种模式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翻译中,标志着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古代文学翻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种翻译模式显然不再停留在以提供低端读物为目的的基本层次上了,而是将特定的文本作为引进的文学系统形式项进行解剖和分析,翻译的同时伴随着引进后的实践环节。
欧弗尔辑译《中国文选》时选择值得翻译的文本加以翻译,其对这些作品的认同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这些作品本身蕴含的文学价值——中国文学和文学观念;二是这些作品本身在中国古代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和价值:“此集仅对著名的、优秀的作家(之作品)加以收录”[19]。此外,文本选择和取舍标准还在于尽可能广泛地选取文本,充分展示中国文学的精髓[19]。这条标准很清楚地展示了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动机:通过翻译引进中国的文学作品充实自身的文学系统形式库。
相形之下,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这些翻译活动,其动机较20世纪初期前后的翻译活动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看出英语世界希望通过翻译有选择地引进中国文学作品,藉此对中国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了解。以美国汉学家倪豪士译介唐代小说为例:早在2002年,他就指出,“西方汉学界最需要一本像王梦鸥《唐人小说校释》那样有详尽注解的唐传奇英译本。本校计划在两三年内出版这样一部译著。”[20]经过数年精心译编,其参与翻译和编写的《中国唐代传奇选》两卷分别于2010年和2016年出版,其中选译的18则小说其实均已经过多次译介,但其认为仍有深入译介的必要。《中国唐代传奇选》“很大程度上以王梦鸥的《唐人小说校释》为底本”“试图(给英语世界的读者)提供第一个注释详实的译本”。因此不仅提供了由西方汉学学者和华裔学者共同参与创造的新译本,结合译本作了非常详尽的注释,而且还在译文之后附上“译者注”(介绍作者身份、文本创作和演变历史等)、“词汇表”(对原文本中的语言难点进行阐释)等内容,“以助唐代小说学习者更深入地把握这些奇妙的叙事文本的内涵和外延意义”[21],满足他们深入阅读和研究的需求。
文选的编纂是一种效率更高、层次也更高的文学系统形式项引进行为,因为英语世界的大多数中国古代文学选集就是供汉学研究者或大学专业学生使用的教材和读本;勒弗菲尔认为翻译文本作为教学素材在大学教育的有力推动下,会更好地实现在目标文学系统中的经典化[22],而文学的编纂会使得到选择的文本受到规模大得多的读者的接受,所以说,这是一种更直接、更有效的引进方式。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学文选编纂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如白之的《中国文学选集》(1965)、麦克诺顿的《中国文选》(1974)、梅维恒的《哥伦比亚中国古代文学选集》(1994)、宇文所安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1996)、闵福德等的《含英咀华》(2000)等,几乎所有文选都收入了数量不等的唐代小说。这些文选的出现,不仅是一种基于既有翻译文本基础上的认同,更是目标明确的文学形式项的引进;对于教材文选来说,这种引进直接将所选文本提升到了层次更高的“经典化”进程中。宇文所安谈到自己编纂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时说:
该著入选著名的“诺顿”系列,是得到权威机构认证的标准教材系列,凡是在校大学生学习中国文学,均需使用本教材……谨希望本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美国读者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23]
还有一些翻译活动也是一种同样直接的引进行为,比如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2011年春、秋季两个学期的《东亚古代文明》课程教学大纲中提供给学生课堂讨论读本《莺莺传》译文[24],讲授课程的伊若泊教授翻译这一小说的目的,在于借助《莺莺传》译本讲授“诗歌在唐代社会中的作用”,但客观上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文学系统形式项的引进行为。至于引进后的这些形式项在目标文学系统形式库中的地位如何,即译本在目标市场上的接受程度如何,则是另外一回事。
不难发现,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汉学家译者对这些唐代小说篇目的认同和青睐,显示出其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专家的眼光和品位,但当其扮演另外一种角色——译者的时候,这种选择和判断会自然而然催动其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上或者运用专业人士或权威人士的眼光去思考是否有必要将这些异质文学系统中的独特的形式项引入目标文学形式库(即母语文学形式库)[13]。往往这些选择和判断会转化成一种动机,即将这些形式项——他们自己眼中的唐代小说中某一类代表作品——加以引进。汉学家将大量唐代小说译入英语世界的主动翻译行为是确凿无疑的引进行为,目的就在于满足预期读者的阅读和研究等需求,客观上起到的作用却是对中国文学系统形式库中的相关形式项的引进和对英语文学形式库的补益;换言之,是对自身文学系统形式库的一种建构行为。
三、结语
翻译活动的发生动机是多元的,英语世界的汉学系统对唐代小说文化价值的认同也是其在英语世界得到大量译介的动因之一。从微观层次看,体现的是英语世界的译者希望将异域文学情趣传递给目标读者群体的意愿;从宏观层次看,其动机还在于文学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将其作为自身文学系统建构所需的形式项加以引进,以丰富和补充自身的文学系统。译者系统对唐代小说文学价值的认同是唐代小说文学价值在英语世界得到的基本认同;英语文学系统在基本认同基础上将其作为形式项加以引进则是更高层次的文学价值认同方式,它是唐代小说得到经典化加工、成功进入英语文学系统核心地带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唐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不断得到翻译的根本驱动力之一。
注 释:
① 此英语世界对唐代小说的主动翻译指汉学家的翻译活动,不包括华裔学者的翻译活动。
② 佐哈尔在多元系统论中提出这一术语,“意谓支配文本制作的一切规律和元素(可能是单个的元素或者整体的模式)的集成体”。
③ 梅氏认为《叶限》在西方的接受仅限于汉学界,在这个学术圈外知道和了解这个唐代故事的受众非常少,这个说法实际上也是不客观的,因为至少这个故事早在梅氏将其英译之前就已经由迪士尼公司制作成动画片(1981)以及被华裔译者艾琳·路易改译成儿童读本(1982),受到广泛关注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