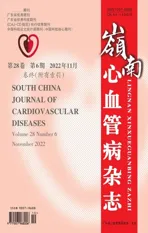Stanford A 型主动脉夹层术后不良事件风险预测模型的建立△
2023-01-24王秋吉邝俊涛冯玮琪于长江范瑞新
王秋吉,杨 珏,邝俊涛,冯玮琪,于长江,范瑞新
[1.南方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广州 510080;2.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心外科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州 510080;3.广州市白云区同德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疗部,广州 510407]
急性Stanford A 型主动脉夹层(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TAAD)是一种极为凶险的主动脉疾病,自然预后极差,院内病死率约10.3%[1],若未得到及时的处理,每小时病死率可提升1%~2%[2]。通过外科手术修复仍然是ATAAD 的主要治疗方法,但患者手术风险较大,若能及时识别高危患者,进行早期干预,降低术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可能是帮助患者改善预后的有效方法。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多的心血管手术评分系统是更新后的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估系统(EuroSCORE-Ⅱ),其具有更强的鉴别能力,模型校准度较好。然而,EuroSCORE-Ⅱ评分系统对于主动脉夹层手术的预测效能并不高[3],且我国ATAAD 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较西方国家低,然而从发病到手术治疗的时间却比发达国家要长[4],这使得患者预后差异较大。因此,建立一个能有效预测ATAAD 术后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event,MAE)发生概率的模型对此类患者围术期的诊疗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建立可靠且实用的风险预测模型,对ATAAD 术后发生不良事件的高风险患者进行早期识别和筛查并及时干预,提高ATAAD 患者预后情况。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 年9 月至2020 年3 月连续就诊于广东省人民医院并行外科手术的ATAAD 患者,所有患者均由主动脉全程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及超声心动图明确诊断及分型。排除标准包括:(1)术前肝及肾功能不全;(2)术前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分级Ⅲ级及以上;(3)术前凝血功能障碍;(4)术前存在严重的神经及精神系统疾病;(5)术前合并威胁生命的其他疾病;(6)术前死亡;(7)病历资料严重缺失。经筛选后,共342 例患者纳入本项研究,ATAAD 术后MAE 的定义:(1)任何原因导致的术后30 d 内死亡;(2)术后发生严重感染、出血;(3)心功能不全、肺损伤、肝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神经系统并发症如截瘫,脑卒中、多器官功能障碍。以术后30 d 内是否出现不良事件将入组患者分为术后MAE 组与术后非MAE 组。本研究经过广东省人民医院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伦理号:No.2017YFC1308003)。
1.2 数据收集
为了消除来自不同医院数据的选择偏差,本机构的数据比其他机构的数据优先考虑。如果转院患者因病情危重无法在本院进行检查,则使用其他机构收集的数据。收集所有患者的围术期资料,包括一般特征、病史、基础疾病、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资料、手术相关变量及术后结局等。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简单随机抽样以3∶1 将数据分为建模数据集(257 例)和验证数据集(85 例)。计量资料若服从正态分布时,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若为非正态分布时,以[M(Q1~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U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χ2)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统计分析。进行逐步多变量分析以确定与术后不良事件独立相关的变量。优势比(OR)以相应的95% 置信区间(CI)和P值表示;本研究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将P<0.05 的变量输入到Logistic 回归多元分析中,公式:logit p=ln[p/(1-p)]=B0X0+B1X1+…+BkXk。在该公式中,p 表示术后不良事件,每个B值表示为最终模型中每个独立风险因素的系数。在验证数据集中用ROC 曲线下面积与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对该模型的预测效能进行评价。此外,通过10 倍交叉验证将数据集随机分为10 个大小相等的样本集,将模型重新拟合到包含90%数据的10 个集合中的每一个,计算每个情况下未使用的10% 数据的ROC 曲线下面积,并对10 个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下面积取平均值。缺失数据不填补,排除资料缺失>20%的患者。所有数据采用SAS 9.4 软件包进行分析(Cary,NC,USA)。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及术前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资料比较
共342 例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全组患者年龄为(51.54±10.73)岁,男性295 例(86.3%),女性47 例(13.7%)。两组患者的年龄、吸烟史、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室间隔厚度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既往疾病史对术后不良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影响,详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术前资料比较 [n(%),±s]

表1 两组患者术前资料比较 [n(%),±s]
2.2 两组患者术中及术后资料比较
全组患者术后发生不良事件104 例,其中死亡24 例,发生率分别为30.4%和7.0%。71 例(68.3%)患者术后出现急性肾损伤;39 例(37.5%)患者术后出现肺损伤;2 例患者因术后大出血死亡;6 例患者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6 例患者死于神经系统并发症,其中脑出血患者4 例,脑梗死患者2 例;同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术中出血量>800 mL,体外循环时间≥250 min 等与术后MAE 有关,详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术中及术后资料的比较 [n(%),±s]

表2 两组患者术中及术后资料的比较 [n(%),±s]
2.3 术后发生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分析
将以上单因素分析得出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术前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120 U/L、室间隔厚度≥12 mm、CABG、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时间≥250 min、延迟关胸是术后发生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3。

表3 术前死亡风险评估模型
2.4 预警模型的建立及评价
将上述独立危险因素纳入Logistic 方程,建立模型,即:log p=ln[p/(1-p)]=-4.0.43+0.033×[年龄(岁)]+1.5109×(术前AST≥120 U/L)+1.0603×(IVST≥12 mm)+0.9455×(CABG)+0.7008×(CPB≥250 min)+1.6092×(DSC)。通过ROC 曲线下面积对预测模型的效能进行检验,该模型的ROC 曲线下面积为0.755(95%CI:0.686~0.823),通过Hosmer-Lemeshow 检验发现,观测值和预测值的分离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7.594,df=8,P=0.474),见图1。用此模型对验证组的患者进行预测并评价它的预测效能,验证组ROC 曲线下面积为0.714(95%CI:0.561~0.867),通过Hosmer-Lemeshow 检验得出P=0.460(χ2=7.735,df=8),见图2。10倍交叉验证的平均面积为0.716(0.507~0.841),这与验证集的结果非常相似,见表4。

表4 术后不良事件风险预测模型的10 倍交叉验证数据

图1 建模组ROC 图

图2 验证组ROC 图
3 讨论
ATAAD 患者病情演变极快,国外相关研究报道的患者术后住院期间病死率约为21.7%[5],国内孙立忠团队的研究结论为7.98%[6]。尽管手术策略在不断完善,医生的手术技术也在不断提高,ATAAD 早期术后MAE 发生率仍然较高,且术后并发症种类繁多,难以预测,如低氧血症、脑卒中、脊髓缺血、急性肾损伤、低心排血量综合征、术后出血等[7-9]。本研究通过建立简便、有效的预测模型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快速识别高危患者的方法,并及时做出相应的医疗决策。
在本研究中,年龄是一个术后发生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年龄大的患者容易合并多种疾病,如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等,这与Howard 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本研究入组患者的年龄为(51.535±10.732)岁,与Leontyev 等[11]的研究人群德尔年龄[(61±14)岁]相比较为年轻,可能提示国内ATAAD患者发病较国外趋于年轻化,临床工作中应注意对年轻人群的鉴别诊断,避免漏诊,延误治疗时机。
主动脉夹层累及冠状动脉造成冠状动脉灌注不足是致命性并发症,这类患者往往需同期行CABG,几项国外的研究认为CABG 不会增加主动脉夹层手术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12-13],但本项研究认为CABG 是术后MAE 的独立危险因素,这可能是因为我国患者从发病到手术所等待的时间较长,心肌缺血严重从而更易导致术后心功能不全所致。
在本研究中,CPB 时间较长是术后发生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Zheng 等[14]的研究一致。有研究表明延长CPB 时间会增加术后急性肾功能衰竭和脑损伤的风险[15],且CPB 时间每延长30 min,术后死亡风险增加57%[16]。但一项纳入了199 例患者的全主动脉弓置换术相关危险因素分析的研究指出,CPB 时间并不是术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17],这可能是由于此项研究患者例数较少所致。目前对于CPB 如何介导各组织器官损伤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需要更多的研究加以解释。
术中伴有心脏水肿、顽固性出血等并发症的患者若行一期关胸将导致心脏排血量降低,血压下降,延误二次开胸止血等,故近年来多行延迟关胸,待血流动力学稳定,凝血功能改善后再关闭胸腔,有利于提高手术成功率。延迟关胸是否会增加感染几率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Matthew 等[18]的研究认为延迟关胸不会增加胸骨及深软组织感染的几率,但是肺炎发生率较高,可能是因为延迟关胸使气管插管及重症监护病房停留时间延长所致。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患者多来自临近省市,导致本项研究存在选择偏移。其次,本研究终点为术后30 d 内是否出现MAE,其中包括了术后各种严重并发症及死亡,但对于存活的存在严重并发症患者中远期的情况并未进行跟踪随访。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索ATAAD 术后AME 对患者长期生存状况的影响。故今后还需开展大样本前瞻性研究和多中心合作,为临床工作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
总而言之,本研究分析了急性ATAAD 术后MAE 的危险因素,将年龄、术前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120 U/L、室间隔厚度≥12 mm、CABG、体外循环时间≥250 min、延迟关胸纳入预测模型,这些指标在临床中容易获取且符合术后MAE 的发病机制,它可以有效预测ATAAD 患者术后MAE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