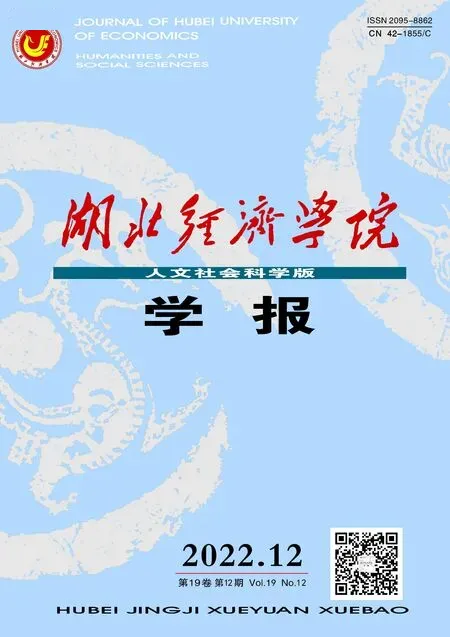从马克思的生产消费理论看中国古代宋明城市消费型文化的特色
——兼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城市文化比较
2023-01-24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56
高 路,孙 跃(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56)
自宋代到明清,中国城市生活里出现了一些世俗色彩浓厚的现象,被很多研究者视为历史的新变化。或有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或有“近世革命”说,或有认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等等。总之,将其视为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某种转折的一种表现,论者的依据大多是这段时期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世俗性”的市民文化的兴起。笔者认为,所谓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其实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很早都出现过,但这并非就意味着一个现代社会的必然到来。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但也认为自那以后中国社会就一直呈停滞状态。这个观点不无偏颇之处,不过认为不宜过分拔高宋代之后中国社会变化的意义,恐怕还是值得深思的。本文尝试根据马克思的生产消费观来对中西城市文化进行一个对比,以说明中国宋明时期城市世俗文化的缺陷。
一、马克思的生产消费理论和“现代”观
马克思关于生产消费的主要理论包含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资本论》等文章和著作里,其特色是将生产和消费看成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双方互相联系。他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1]
所以,生产为消费创造了对象、规定消费的性质,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和动力;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在这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被人化。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更是提出一个精辟的见解:消费不仅只是消费品的消费,还有生产资料的消费,即生产资料被用于生产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生产消费”这一概念。他说:“只有消费是这种生产消费,它才进入资本本身的循环;而这种消费的条件是,通过这样消费掉的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这和以维持生产者的生存为目的的生产,甚至商品生产,是很不相同的。”[2]87-88
以维持生产者的生存为目的的生产即消费的生产,只是一种简单再生产;为生产资料生产所进行的再生产即生产的消费,才是扩大再生产,即制造业。正是在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出工业革命。而在这种“生产消费”中,生产和消费已经成了一回事。
由是,马克思提出了“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区别:在古代社会,人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才表现为人的目的。古代社会主要进行的正是消费品的生产,即简单再生产;现代世界进行的则是“为生产而生产”,即扩大再生产。这里的“现代世界”,显然还不是古典资本主义,而主要是指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这个逻辑,欧洲资本主义相对于前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大进步,主要是表现在其“生产性”的勃发,而不是“消费性”的出现,或者说,“生产性”大大超过了其“消费性”,所以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欧洲资产阶级其实已经表现为一个“工业的阶级”。正是在这种意义的“现代性”前提下,才有可能发生工业革命。而马克思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称两大现代阶级,也是指和机器大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
人们习惯将现代社会视为人的自由解放意识觉醒的社会,马克思也致力于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只是他的“自由观”从来不是抽象的“人性解放”,而是同样和他的“生产观”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3]21这段名言被人广为引用,自由主义者也常引用这句话来说明马克思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但是,马克思在这里谈论的根本不是抽象的个体的人,而是“进行生产的个人”,生产劳动才是人的第一特性。他之所以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全面解放,一个重要理由是共产主义将人从分工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从而能够获得全面发展,而这种全面发展主要是一种生产性的自由发展,是劳动成为人的第一生活需要。“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4]22-23,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前提。人的自由解放,并不是抽象的人性解放,而是生产劳动能力的无限可能性的释放。这是其迥异于自由主义者之处。
马克思赞扬欧洲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性正是因为欧洲资产阶级曾经热烈讴歌生产阶层,与生产阶层一起反对不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促进了欧洲生产意识的解放,为人类生产劳动开辟了更多的自由。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肯定资产阶级在“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而他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也在于此:资产阶级自己并非真正的劳动者,在获得对社会的统治权后又反过来压迫真正的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并将他们创造的劳动果实占为己有,导致无产阶级日益贫困,而且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严密分工和管理制度将工人变成技术的奴隶,劳动愈加成为异己的存在,这就扼杀了人类生产性的进一步解放。因此私有制使“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5]68资产阶级实际上以人们平常意识不到的物的压迫来代替直接的人的压迫,从而把压迫普遍化,人的生产自觉性最终还是被资本、利润所泯灭。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一方面是推动了现代社会诞生的功臣,另一方面它自己又成为“反现代”的罪人。要实现彻底的人的自由解放,只有依靠无产阶级进一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人人成了自由的生产劳动者,人类改造世界的生产性才会得到彻底解放,真正的现代世界才算建成。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真正作为现代社会开端标志的,应该是生产阶层的崛起和生产意识的觉醒,而不是简单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繁荣作为现代社会兴起的前提。
如果我们将中西城市文化进行一个对比就更能够理解马克思的这种现代观了,既然普遍认为宋明时期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或城市革命或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那么我们就将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城市与宋明时期城市文化进行一个大致的对比。
二、从中西对比看宋明市民文化“现代性”的缺失
欧洲中世纪的城市革命中,意大利的城市里出现了炫富似的消费生活方式,城市显贵开始在城市里修建宏伟富丽的私邸、别墅和花园,16世纪晚期的那不勒斯出现了贵族修建宫室的热潮。罗马在教皇朱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时期掀起大兴土木之风,威尼斯城在17世纪盛行攀比式消费。不少人担心这种奢侈的消费方式会摧毁整座城市,不少城市政府曾制订过“禁奢法”试图扭转这种风气,但成效不大。可是,在另一方面,欧洲城市的“生产性”发展得一点不比“消费性”缓慢。在经济生活上,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市体系已经出现了一批生产中心,特别是北部、中部和东北部的工商业城市,都是生产技术革新和制造业的中心,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这些地方多是文艺复兴的主要阵地。若设菲尔德等地,则以专门制造生产工具为主,基本脱离了为生产消费品服务的经济模式。这些城市所形成的技术革新和科学知识,又成为欧洲日后工业革命的基础。并且,城市里的主要生产阶层——工匠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一部分在作坊里从事手工劳动的人,主要是从事绘画、雕塑和建筑设计的人开始成为“艺术家”阶层,其地位发生了很大提升,而这些人恰恰是文艺复兴文化的主要生产者。
正因为文化生产者和生产劳动阶层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所以在思想文化方面,欧洲市民提出了非常积极的崇尚生产劳作、创造美好世界的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波焦·布拉乔利尼曾说道:“没有一个人不渴望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东西;没有一个人不渴望更多的东西。因此,贪婪是自然的。……我们的城市是靠致力于人类事业的人维持和运转。如果一个人不生产超出自给自足的那部分,不说别的,我们都将变成农夫,只好亲自下地耕作了。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生产,那一切就会乱套……一切辉煌、精美和华丽的东西都将不复存在。如果所有的人只满足于自给自足,那么就不会有人修建教堂和宫邸,一切艺术活动都将停止,我们的生活和公共事务将陷入一片混乱。”[6]
布拉乔利尼这里面表达的不仅是崇尚生产的思想,还是宣扬为人类事业、公共生活而生产的集体主义思想。只有这种为集体生产的思想,才能打破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模式。另一个人文主义者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提出一套劳作观,“人生下来不是为躺着让自己腐烂而是为站着做事情,不是为了在无所事事中忧伤地消磨时间,而是为了从事宏伟壮丽的事业。”[7]这些话深刻表达出当时西欧城市市民对“财富”和“欲望”的看法:创造财富和实现欲望是人类天性,人类藉追求二者之冲动以达到改变世界、增进文明之目的。其反对禁欲主义不单单是为了享乐,更在于满足追求知识、文化、发挥改造世界潜能之欲望。《神曲》《巨人传》等名著都是宣扬人要追求美德与知识,相信人可以用科学和文化将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这正是体现出西欧市民消费观与生产观相统一的思想特色。他们一边张扬自己的欲望,一边却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改造社会的努力联系在了一起。不仅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生活在崇尚世俗化时,同时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继承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一思想,主张造就完整的人。他们热烈地讴歌人性,但他们所宣扬的“人性”一直是和人必须完成的人生使命联系在一起的。科鲁乔·萨卢塔蒂认为人的任务就是要在大地上建立起城市和社会,人只有完成自己的事业,才没有虚度年华。他本人也是积极参加城市政治生活,曾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长[8]。萨卢塔蒂的学生布鲁尼说:“在对人类生活所作的道德教诲中,最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和政府的那部分,因为它们涉及为所有人谋求幸福。如果说为一个人争取幸福是件好事的话,那么为整个国家争取幸福不是更好吗?”他主张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公众利益[9]。另一个人文主义者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也主张把个人生活和祖国命运结合起来。
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文化,既有欲望的放纵,却又坚守对城市和国家的责任;既肯定个人的享受,又提倡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既要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强调辛勤劳作和创造世界。消费与生产、“世俗性”和“政治性”在文艺复兴的城市生活中达到了高度统一。这种消费与生产的统一精神,一直被许多欧洲后世的城市所继承发扬,恩格斯后来就盛赞19世纪的巴黎“把追求享乐的热情同从事历史行动的热情结合起来了,这里的居民善于像最讲究的雅典享乐主义者那样地生活,也善于像最勇敢的斯巴达人那样地死去,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阿基比阿德,又体现了勒奥尼达斯;这个城市就像路易·勃朗所说的那样,它真的是世界的心脏和头脑。”[10]550彼时西方城市虽然崇尚消费、世俗化色彩浓厚,但其消费文化是随着一种“生产性”的发展而发展的,甚至“生产性”还超过了“消费性”,这样的市民文化方才能够成为他们走向现代社会的动力。这种消费与生产相统一的文化,又在后来被马克思所总结,提出了一整套辩证的生产消费观。当然,欧洲市民阶级所具有的这种“生产性”并不表明其一定具有道德的正义性,其后来向工业文明转化的第一桶金是凭借血腥的原始积累获得的。但这种“生产性”,却的确是马克思所极为重视的欧洲“现代性”的基础。
那么中国宋明时期的商业文化和市民文化是否也具有这样的“现代性”呢?我们可以通过时人的描述和学者的研究来考察这个问题。北宋东京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孟元老如是描述北宋时期的东京消费生活之繁华:
“举目则青楼画阁,繍戸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11]19
但这种消费文化并未令北宋城市产生一种生产的精神。冯天瑜教授认为,北宋东京充满着不事生产的消费人员,仍然是一个政治中心和消费中心,和中世纪欧洲城市有很大区别,欧洲城市已是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聚居地,是生产和消费相结合的经济中心[12]。
南宋时期临安虽然繁华,却仍是商业中心城市而不是生产城市。作为杭州返销所提供的商品主要是特产丝绸、瓷器、服饰品、漆器、贵金属加工品、香料等等[13]347,都是给王公贵戚、富豪官宦阶层提供的奢侈消费品。
金代随着中都成为国都,王朝皇室、王公贵族、文武官吏都集中到了都城,这里集中了大批为皇室、官僚服务的机构,促使了为这个寄生集团服务的消费产业和手工业的发达。这批贵族和官僚的需求,刺激了为这种需求服务的商业。各地商人由于中都市场的吸引,从四方贩运货物到中都城。大批商品的涌入,使得城市市场进一步扩大,城市的娱乐活动也极为兴盛。城市“风俗竞相侈靡”[14]2150,和两宋时期的城市文化并无本质区别。
元代大都“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15]237上都“自谷粟而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16]4可见,仍然是奢侈品商业在带动经济发展。非政治中心的泉州、扬州、杭州、广州等城市也十分繁华,这些城市基本是由于商品贩运而兴盛,成为达官贵人、富商大贾的聚财之地。
到了明代,《松窗梦语》里记载明代的北京“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御鲜华,器用精巧,宫室壮丽。”还看到了北京奢靡文化风气是与北京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自古帝王都会,易于侈靡,燕自胜国及我朝,皆建都焉;研习既深,渐染成俗,故今侈靡特甚。”“京师者,四方之所赴观;天子者,又京师之所视效也。九重贵壮丽,则下趋营建;尚方侈服御,则下趋组绘;法宫珍奇异,则下趋雕刻。”[17]76-77并且提到了这种表面经济繁荣和城市本身生产功能的脱节,“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
可以看到,自宋代以来,城市的商业资本和消费文化就十分活跃,而且,特别是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其消费产业和商业贸易就特别繁荣。在这种背景下,自宋明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出现了一大变化,便是商人阶层的兴起、壮大。道光年间的沈垚在《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里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18]明后期已经出现了颇多弃农就商、弃儒就商、致仕从商的事情。商人交通官宦,士大夫交接富贾,互通婚姻,已成风尚。许多商人更通过捐输纳官之法跻身仕侪,打破了以前商人不得入仕的束缚。在民间,商人也逐渐由人们所鄙视的社会阶层成为人们崇尚羡慕的阶层。明末的许多文人和思想家都有重视工商的思想,黄宗羲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清代许多下层士绅开始经商营利。
但是,这时兴起的趋利重商之风,对于传统等级制度虽是一种冲击,却并不必然使社会出现尊重劳动者、重视生产的风尚。一方面,社会上虽有“弃儒就贾”的现象,可商人自己仍是以士为尊,“习商而归于绅”的风气也并未改变,且一直持续到近代。近代有些民族商人有了名望后,就成了议长、乡董或乡绅,脱离了企业家身份,其心目中权力财富仍然高于生产事业。另一方面,这些变化只是令农和工反而从“士农工商”落到了四民最底层,何心隐在《答作主》中说:“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生产者阶层的地位还有所降低。并且,商人阶层的崛起还造成了更多士大夫崇尚金钱、鄙视生产的风气,权力和财富共同成为中国人的人生追求。明朝举国上下以经商为荣,从朝廷到民间都出现经商热潮,仅仅表现于对财富的渴望。如扬州“俗喜商贾,不事农业”,汾州“民率逐于末作,走利如骛”,可见相伴随的风尚都是是对生产劳动的进一步鄙视。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导奢导淫”,扮演先导人物的是缙绅士大夫。这些城市居民中的特权阶层“风尚奢靡”,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以奢侈为荣[19]。城市消费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脱离了“生产性”的风尚习俗中繁荣起来的。
在崇尚奢靡的风气下,盛行的是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却没有储蓄意识,人们乐于将自己所得全部用于享乐,“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杀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为别计。”[20]没有储蓄意识就不会进行资本积累,也就发展不出现代工业生产。当时的社会自然不是完全没有生产,任何社会都是既有消费也有生产,繁荣的商业贸易必然要有大量的生产品为基础,消费意识的增强也确实在很多时候可以成为促进生产的动力。但是当生产只是简单为消费服务的时候,这就只停留于生产消费品的简单再生产,而不是扩大再生产,尤其在为特权阶级的消费生活服务的这个目的下,传统中国生产的主要都是为城市王公贵族、官宦富豪服务的奢侈品,难以出现“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就很少出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消费”。如宋元时杭州盛产的丝绸就是贡品,南宋时还设有官营的“织锦院”;明代“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杨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骒,京师城隍、灯市之古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鳖,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21]这看似贸易繁荣,不过生产的商品几乎全是消费品,鲜有生产资料产品,这自然就不是“生产资料生产超过消费品生产”的“为生产而生产”的现代生产方式。
当然,“生产资料的生产”也不是完全没有,在明代出现了我们熟知的“机户机工”,这就是专门生产织机的行业,属于专门进行生产资料生产的制造业,但是人们的购买力限制了它们的扩大。若《二刻拍案惊奇》里的施复,“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施复也有扩大生产的愿望,但是现实制约了这种扩大,“如今家中见开这张机,尽勾日用了。”多数人家拥有一张绸机就只能维持温饱了,没有余力再去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织机的生产也不可能扩大。而大多数中国商人经商致富后都还是去农村购买土地,而不愿投资于制造业的发展,这只能说明中国的商人阶层更加倾向于变成占有土地的消费阶级,却难有投资产业的生产意识,这就导致像施复这样的小手工业者无力扩大生产,也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远远没有欧洲资产阶级那样的进步性。所以,中国的产业资本始终十分稚弱,即使真有了资本主义,也最多只停留于商业资本的形态,未必可以转化为工业资本形态。相比之下,从元代到明代的农村地区倒是勃发出了一种生产的活力,如黄道婆对棉纺织工具的改良、纺车的出现、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一批江南市镇的兴起等等。但是,城市如果不能成为生产中心,机器大生产就难以出现。宋明时期这样一种脱离了生产性的城市消费文化,和马克思所说的辩证统一的生产消费观截然不同。其消费未有能够很好促进生产,相反大量的消费活动将城市资本引向奢侈品商业,影响了工业资本的积累。
在思想文化方面,宋明城市消费生活的发展,虽然有利于突破森严的礼教纲常对于社会思想的控制,却只停留于以肉欲解放为目的的感性层面,难以升华出富有理性的思想文明,而理性的思想文明是和生产精神的解放结合在一起的。如宋代小说话本以爱情、公案为主要题材,里面虽然不乏平民意识的内容,却没有一种要改变既存现实、创造崭新世界的理想。相反,那些以讲史为题材的话本、说书中,还大量宣扬了封建正统观念,渲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理想。在明清时期城市里出现的市民文学,如《金瓶梅》《牡丹亭》《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里面也确实可以找到反礼教、追求个性解放、同情普通市民、揭露社会黑暗和上层统治阶级虚伪残忍等进步内容,这经常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或“资本主义萌芽”或“市民意识的觉醒”。可是这些文学在追求人的解放时并未有和提倡生产劳动的解放、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仅仅只是追求爱情和享乐生活的解放,这和文艺复兴时期《神曲》《巨人传》等作品里所表现出的对知识真理的追求、运用智慧和劳动去改变命运的坚定信仰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实有天渊之别。
在哲学思想上,从王阳明“心学”、泰州学派,到李贽、戴震、纪昀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确实有主体意识觉醒和个体存在价值提升的意味,但是这种意识所承认的自然人性,也主要只是停留在“私欲”的层面,即个人消费欲望的合理,并未有太多的崇尚生产劳动、探索知识智慧、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内容。最有叛逆性格的李贽也只是主张:“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利。”[22]表达的仍是满足世俗功名利禄追求的“私心”,并无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觉悟。这种世俗化倾向与商品经济互为呼应,支持着更多人弃儒就商,壮大商人队伍。经商赚钱成为更多人的人生追求,可是鄙视劳动生产的弊病还是没有多少改变。可见,宋明时期的中国城市市民文化不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现代性”,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文化也有很大不同。在他们心中,消费就是享受,生产则是下等人的事情。在这种与“生产性”脱节模式中出现的市民消费文化,很难让城市社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三、结语
笔者根据马克思的生产消费理论,认为中世纪孕育了欧洲与亚洲的“大分流”,一个表现就在于其孕育出了“生产”的精神。从“生产”意识发展到“为生产而生产”的精神,是导致西欧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文化根源。中国从宋代到明清城市文化确实出现了世俗化倾向,但这种世俗化倾向仅仅反映的是商业发展下的消费意识增强和对于奢华生活的向往。无论是世俗文化,如《牡丹亭》《金瓶梅》《肉蒲团》之类的市民文学还是如王艮、李贽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都更多凸显的是一种消费欲望的张扬,缺乏生产意识的觉醒。而这样一种市民文化又在近代的城市生活中延续了下来,民国时期虽然出现了具有现代化因素的城市和市政改革,但自宋代起通过奢侈品带动的商业繁荣和以上流社会的奢靡享乐来带动社会风尚世俗化的消费风气却进一步得到加强,近代中国城市仍然是一种传统社会的消费型城市。
中国文化一直存有以不事稼穑为荣的鄙视劳动传统和崇尚“述而不作”“厚古薄今”“法先王”的思想,这压抑了中国人的经济和文化生产能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变化,都未有能提高生产阶级的地位和对于生产活动的重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当然是在发展之中,而且诞生了很多辉煌璀璨的成果,但是这种发展自宋代以后或许越来越和黄宗智先生所形容的华北小农经济一样是一种“内卷式的增长”,或曰“没有发展的增长”。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其文化成果多是如小农经济一般在原有土地上的深耕细作,鲜有开拓空间、创造新型产品了。如果按照传统说法,中国自宋明时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么自此时开始到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也主要停留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层次,鲜有投资于产业发展,难以升级为工业资本主义。这一切似乎说明了一个道理:商业文化冲破农业文明的羁跘、商品经济促进工业革命发生,未必具有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说过:“在商业资本占优势的地方,过时的状态占着统治地位。这一点甚至适用于同一个国家,在那里,比如说,纯粹的商业城市比工业城市有更多类似过去的状态。”[23]39这足以说明,商业资本主义在冲破旧社会形态束缚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最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促使了中国生产劳动阶级的崛起,给全国人民输入了一种强烈的生产意识和精神。这是1949年后中国能够成功实现现代化、工业化运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