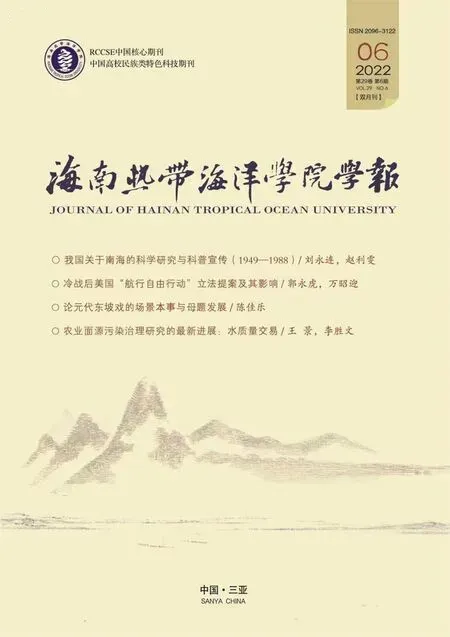诗与思的交错离合:海瑞文学思想的心性维度
2023-01-20黄天飞
黄天飞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海瑞的文学思想立足于明代中后期独特的学术语境和社会思潮。他处在明代国运衰败迹象日显而仁人志士仍在反复挣扎的特定时期。明代心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兴起,以图为世人解释纷乱谜团的世界,白沙心学与阳明心学就此大放异彩,迅速占据当时文化思潮的显明地带。陈献章(白沙先生)于弘治十三年(1500)逝世,距离海瑞出生还有14年,而王阳明则于嘉靖七年(1528)逝世,海瑞方才15岁。受此影响,心学也在海瑞的思想视域中处于主导地位,他认为开创心学的陆九渊才是道统的合法继承人:“圣人不废学以为涵养,是以《中庸》有‘尊德性而道问学’之说,贤人而下,不废学以求复初。是以孟子有‘学问之道,求其放心’之说。子思、孟子传自尧舜,陆子识之。”[1]323海瑞对于白沙心学和阳明心学兼有所取,然二者的实践工夫却相去甚远,前者重在“静观”“自得”,从内在的心灵体验而超凡入圣;后者则提倡知行合一,“必有事焉”。心学对于海瑞文学思想的渗透非常明显,然而学问与诗思之间存在心理构型上的诸多差异,既非儒士又非文人、以政治实干家为主要历史角色的海瑞与理学、心学也有现实语境上的错位,那么观察哲学特别是心学与海瑞文学思想的离合交错、对话互动就成为理解其文学心性观念的独特视角。
一、 合文道:天地精神以诗而骋
兹从三大方面论书海瑞对于文道关系的看法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一)一脉相承的心学论调
海瑞与当时唐宋派文学思想具有一脉相承的心学论调,故后者可作为观照海瑞文学思想的一种视角。唐宋派是受明代心学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文学流派,其代表人物与海瑞身处同一时期,如唐顺之(1507—1560)、王慎中(1509—1559)、茅坤(1512—1601)。双方受心学统摄而展开的文学思想言说也多有重合之处,如海瑞“无论何艺,时时流露性情”[1]337的作家主体素质论与王慎中“性情之效”的理论旨趣:“盖性情之效而非熔铸意义、雕琢句律之所及也。”[2]219又如海瑞写“吾之意”画“吾之神”[1]14的创作原则论与唐顺之“诗,心声也;画,心画也”的心源说“好文字与好诗亦正是从胸中流出,有见者自别”二者虽存在精粗详略之别,但心学之论调却甚为一致。海瑞文道观的心学色彩,还见于其认为学问与作文在致思方式的类似,其《青山挽诗序》认为诗歌能够“吟咏而思想”,即认为沉潜玩味的品诗方式与尽心穷思的道学策略可互通无碍。海瑞对于陈献章心学所提出的融会道学精神与诗学精神之“二妙”境界的态度更是超越式的,陈认为“二妙”之境是难以达到的,称之为“二妙罕能兼”[1]333,而海瑞则在《注唐诗鼓吹序》[1]333中表示出“二妙能兼”的期待,是一种积极的“文学进化”观。
(二)道德伦理色彩的减退
但海瑞的文道观亦不完全出自心学,如其《注唐诗鼓吹序》云:
他以“古先王”而非仁义道德开篇,接着继承自刘勰以来从天地人“三才”的角度确认语言文字价值的思路,又赋予其言说、发挥天道的神圣渊源,进而认为诗文写作的终极目的是传达出天地精神之纯粹精微的境界。这种观点在明代已颇有影响,但是海瑞独特之处在于其道德伦理色彩的减弱,这与其“从胸中流出”的文艺性情论和“出于天下之公卿黎庶”的诗教论在趋向于物化实用的理论逻辑相承接,主张言行一致,体用一原[4]。而王慎中在《与万枫潭》中也认为文为天地之所生,但是紧接着他又直接将文置于道德的绝对支配之下:“然是文也,天地之所设,圣哲之所传,使以仁义之人为之,固道也,非文也。”[2]海瑞与王慎中观点的差异实际上是理学、心学文道二分的认知方式与传统儒家上契天道下贯人心的认识论之间的分歧。《周易》、先秦儒家之所谓天道不同于类似于西方上帝的“创造性本身”[4],这种“创造性本身”不依附于任何诸如人体、文艺、工具等实物。天道与人不可分割,天道为人开出主体意识,使之可以“禀天地之精”。人特别是人之文则是道化生万物的枢纽,也即海瑞所谓“袭物感人,变化因之”。故而传统儒家并不存在道与文的冲突,也就不存在二程“作文害道”以及王慎中“固道非文”的轩轾。海瑞文道观更显出传统儒学的宇宙生成论范式而非宋明理学的道德本体论话语。
(三)由道向文的自我校正
海瑞文学思想中道德伦理色彩的减弱自然就为文学自身审美特征的突显留下足够的空间。与王慎中同为唐宋派的茅坤则有与海瑞“文道相合”颇为相似且更为具体的论述,其《刻檀孟批点序》认为文学写作“荷得其解,则庖牺氏画而奇,画而耦,并天地之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又何有于李斯篆、隶以下之点级淋漓乎哉”[6]380。这种以文章来对天地精神的摹写刻画的活动还可以使文“几于道”:“近且不欲为摹画,不欲为沾沾自喜,而独以天地间所当绘而成像,触而成声者,以为文章之旨,此则几于道矣。”[6]496再从茅坤的整体文论体系而言,“实际上他逐渐摆脱了明代儒学思潮对文学的侵蚀,把文学思想的基础整体建构在艺术经验之上,实现着由道学向文学的自我校正”[7]。海瑞作为一个政治实干家,其文论与之相比当然存在理论深度上的笼统与具体批评上的缺乏等不足,但是他基于“天地精神”而对文道合一的大致勾勒又与以茅坤所代表的唐宋派对儒家义理的游离、对《周易》和先秦儒家的体会、对人心性维度的整体观照等不无存在契合之处。故茅坤更为集中而精细的理论陈述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对海瑞文学思想的深拓与完善,显出其发展方向与衍化样式。
二、 求真心:“本真在我”“因触而诗”
探求客体的“天地精神”向主体领域的集中展开就是“真心”的呈现。海瑞的文学主体素质论内涵主要包括如下两方面:
(一)源于心学又超于心学
如果说海瑞的文学本体论更多地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那么其文学主体素质论则更多地接受了理学特别是心学的陶染。海瑞思想渊源继承陆王心学,并上推到尧舜心传和孟子,他认为天下未有一物一事出于心之外者的核心观念与陆王如同出一腔,因而在观照事物的认识方法论上,自然讲究向内致知而不假外求,学问之功为求放心而设,修养之能亦为求致思而立。这种思想转化为文艺理论,就自然出现“始谓忠臣烈士,无论何艺,时时流露性情”[1]337的表述。以文艺确认自我真实性情的创作范式还多次出现在其对具体诗文作品的论述中,如《注唐诗鼓吹序》评诗云:“本真在我,因触而悦,故亦因触而诗。”[1]333这里与上述茅坤“触而成声者,以为文章之旨”颇为相似,“触”所强调的是即景会心、实见感兴的创作动机。又如其《教约》评文:“文也者所以写吾之意也。吾平日读书,体认道理明白,立心行己,正大光明,吾之神也,作而为文,不过画师之写神者耳。”[1]14都是出于反对模拟剽窃、矫揉造作。
然而海瑞之求“真心”虽发端于心学却又与其文学本体论类似,也同样具有流溢出心学框架的倾向。海瑞哲学具有明显的“抑朱扬陆”[8]倾向。他曾反复指出朱学的过失,如其《朱陆》云:“朱子平生误在认格物为入门,而不知《大学》之道,诚正乃其实也。”[1]325他认为朱熹在认知程序上以格物致知为先是舍本逐末,而当以正心诚意为要。但是,陆王不假外求的认识方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人心可以具备万物之理,但是万物之理又不先验地存在于人心之中,单纯发自内心的想象无法激发出主观精神及其相关作用,而必须建筑在由外而内的客观求实基础之上。
(二)以真心弥合心学与政治的偏差
海瑞以正心诚意为首的认知策略与其作为政治实干家的身体力行存在矛盾之处,然而心学与政治的偏差却在文艺中可以得到相当程度上的弥合,文学创作的构思想象兼具精神意识和实践形式的双重性质,这一点海瑞有非常自觉的认识。他在《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中论探究学问的致思方式时指出:“作文之法,亦是如此。”[1]504基于此,心学内心与外求的错位自然可以在文艺活动中得到矫正而取得一致,表现为海瑞将人心性情借由文艺语言而真实流露出来的设定。他一方面认为“诗者心之声”,以我之笔写我之心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对主体人格心性的塑造与落实;另一方面他又非常重视读书体道功夫对于文学修养及其社会实践的功用。前者如其所谓“平日读书,体认道理明白,立心行己,正大光明”[1]14而后方可“作而为文”,后者则追认诗教的崇高地位:“古先王成就人才,由今考之,大抵六经并行,诗教为首。夫教以言行,诗亦言尔,何以益人而先之若是?”[1]332因而其强调的真心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心学的藩篱,具有内外兼修以求真用于世的现实路径。既是绕过宋明理学而对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理念的呼应,又隐约可见经世致用的明末实学意味。这种崇尚心学又绕过心学的思路是海瑞思想矛盾的体现,这与社会转型时期多元意识交锋有关,阎韬认为海瑞“在制度上的复旧与意识形态上的趋新并行不悖”[9]。
提倡本真性情的文学主体论对于“此心具足,不假外求”的心学认识论的发挥,实际上是以面向现实人生之“诗”来调剂高蹈于现实人生之“思”。一如其所谓“识其真心”的问题,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云:“公(指海瑞)……以圣贤教人,千言万语,只是欲人识其真心。率其真而明目张胆终身行之,卓然不牵于俗者,圣贤也。味其真而馁其浩然之气,不免与俗相为浮沉者,乡原也,非圣贤也。”[1]534行事认真、一丝不苟以求光明磊落的真心自然可以避免心“生之后蔽于物欲”[1]502的尘俗之累,传导至作文上,就是从“卓然不牵于俗”之心具象化为“不混尘俗而别为一局”[1]379之文。
1925年夏天,清华学堂筹办大学本科,请叶企孙前往,就这样,赵忠尧同叶企孙一同北上清华。第二年,清华大学成立物理系,叶企孙担任系主任,赵忠尧也正式成为清华的教员,开始担任实验课程。
概而言之,海瑞所崇尚的作文创艺之主体心性修养可谓是以“立心”为基础,以“行己”为门径,而又以求“真心”为指归的知行一致、由心学入而自实学出的体系化营构。
三、 崇思想:吟哦浩歌,胸中造化
海瑞文学思想诗与思的交错离合还表现在其文学创作思维论中,既追求文道一致、诗思相协又颇有超出诗学范畴的倾向。
(一)哲思对诗思的超越
海瑞《注唐诗鼓吹序》评陈献章诗云:
“子美诗之圣,尧夫有别传。向来称作者,二妙罕能兼。”唐而下,学诗非杜,人卑其诗,未有许可及康节者,乃公甫又若于康节独推焉。少陵爱君忧国,见之于野之获发之,视彼流连光景,漫无邑居为据,诚一人矣。吟哦浩歌,胸中造化,一动一静之间,天地人之妙也。少陵能之乎?盖不特文彩动君之夸,随鹿冷炙,不用为愧,一二不足道,拳拳君国之念,尧夫亦奴仆而命之矣。宋进士许洞诗会九僧,约以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禽日星鸟,无犯其一,九僧搁笔。夫天光物色,亦一时之触尔。本真在我,因触而悦,故亦因触而诗。假若周、程、张、朱,有洞之约,性真之悦出之矣,无待于外,能困之乎?子美除却君国诸作,一时曳白,料必九僧同之,可圣取哉![1]333
海瑞先是阐述杜甫与邵雍(尧夫)在作诗上的区别。他认为自唐以来,学诗者莫不推崇杜甫却没有称许邵雍,而陈献章认可邵雍可谓是慧眼独具。在海瑞看来,杜甫虽然“爱君忧国”,但他所感所兴的不过是个人一己之情,根本达不到追问造化之机、体悟“天地人之妙”的神圣境界,以至于其“拳拳君国之念”也出于胸襟视野的狭隘而显出某种奴性意识。之后海瑞又引用宋代许洞诗会九僧的典故来进一步说明哲人之诗对于诗人之诗的优越所在,他认为诗人情思多为“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禽日星鸟”等“天光物色”所困,一旦抽离了外物就不得不搁笔失语。但周、程、张、朱等理学家们面对同一境遇时,则能够“无待于外”而不为所困。这是因为理学家们以其超越性的主体意识将心物关系确立为“本真在我”而非不能离开客观自然表象的“本真在物”。此外,这里也透露出明代另一位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痕迹。“吟哦浩歌,胸中造化,一动一静之间,天地人之妙也”之论来源于邵雍,明显不符合陈献章“静中养出端倪”[10]的思想进路,反而更贴近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念。似乎流露出海瑞兼综白沙、阳明二派的努力。
(二)“二妙能兼”的可能性
《注唐诗鼓吹序》接着又引入严羽和与海瑞同时代的万士和(号履庵)的观点来分析陈诗的后半部分,即诗思“二妙”之分合的问题:
严沧浪说诗,方之妙悟禅道,曰:“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羚羊挂角”。万履庵鄙焉。夫水月镜象,言若荒诞,水诚有不可执著之月,镜诚有不可执著之象,而非诞也。文泥也,以诗之曲畅旁通随乐而与济之,文之妙也。履庵直据文理,或则古诗人同物之趣,无深会乎伊川程子指穿花点水之句,间言无用;惜工部一生之心,自少而老,止有三诗绝句,是亦履庵之见也。余尝谓唐宋诗人均尔,一知半解之悟,孰为唐高,孰为宋下。欲定说于沧浪履庵之间,仿佛“二妙”去取焉而未之及。[1]333-334
众所周知,唐诗以风韵见胜,而宋诗以理趣为长,二者分别侧重于“诗”与“思”的两端。严羽崇唐抑宋,其诗论追求性情悠远的空灵意味,这却遭到了万士和的鄙夷。万士和所欣赏的是如同程颐“穿花点水”那般富含理趣的诗境,并且认为杜甫、严羽等“古诗人”均未能体会到这种境界。可见出万士和论诗崇宋抑唐而偏向于“思”的一方,这正好与严羽相对。海瑞在这里所关注重点并非在于唐宋诗孰是孰非,虽然他曾为严羽辩护,认为万士和拘泥于现实逻辑而不知为文“曲畅旁通”之妙,但是他并没有在严、万之间流露出太多的倾向。他主要还是想借二人相对立的诗论,来试图证明陈献章哲思与诗思“二妙罕能兼”的观点。这种“证明”非常具有“证伪”的意味,因为他使用了“仿佛”一词,这就透露出他实际上并不完全相信“二妙”不能兼善。果然,他在文末又说:“礼义无穷,人心有觉,况赓歌风雅颂,诗法在焉。自是而后,又安知无有兼庄、陈、静修,出且入二妙而上之者乎?”[1]334可见陈献章将对诗与思的探索所凝聚出的“二妙”概念给予了海瑞文论不小的启发。
然而海瑞文学观念对白沙思想有承接亦有推进。陈献章的白沙心学作为陆九渊的象山心学向王守仁阳明心学的重要过渡,其一向以诗思相协为特色,特别关注道理学问与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性融通。如黄淳评其云:“先生之学,心学也。先生心学之所流注者,在诗文。”[11]903屈大均更是直言道:“以道为诗,自白沙始。”[12]海瑞肯定陈献章将杜甫和邵雍等量齐观之“二妙”的同时,又进一步突破了陈诗思并重的理论思路而更认可邵雍那般崇“思想”的哲人之诗,并且还表现出对于“二妙能兼”的可行性期许。这尤能见出海瑞继承白沙心学的同时又将其进行了提炼分化进而更趋向于文学本体层面,使其混沌色彩消退,更具心性体验上的清晰与逻辑演绎上的完整,是向阳明心学的合理归趋。
四、 尚含蓄:内见蕴藉,外著风韵
诗与思依照自身的特点而交错离合的状态,同样在海瑞由创作实践而反映出的文学审美理想论中得到落实。其《注唐诗鼓吹序》云:“盖人禀天地之精,言语文字之间,天地精神之发也。约而为诗,不多言而内见蕴藉,外著风韵。”[1]332-333他所欣赏的是清净简约、深有蕴含而又于外在感官上散发出无限艺术感染力的审美风貌。这一篇序文是海瑞为廖炳文(字锦台)的《唐诗鼓吹集》所作的,廖炳文与陈献章同为广东新会人,海瑞称其“有得于白沙”,再结合海瑞在同一文章中还有“余时以注白沙古近叩之锦台”的意图直述与上述海瑞对“二妙”的理解,不难发现海瑞自己亦是“有得于白沙”。故这里的“蕴藉”“风韵”很可能出于对陈献章风韵诗学的发挥。陈献章《批答张廷实诗笺》云:“大抵诗贵平易,洞达自然,含蓄不露。”[11]170又《与汪提举》云:“大抵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先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今之言诗者异于是,篇章成即谓之诗,风韵不知,甚可笑也。情性好,风韵自好,性情不真,亦难强说。”[11]203陈氏论诗标举自然之性情和含蓄之风韵,由上文可知海瑞文论亦重性情,其曾说:“忠臣烈士,无论何艺,时时流露性情。”[1]337陈献章与海瑞在审美风格上重视含蓄蕴藉之风韵的特点还表现在他们同样认可严羽,陈献章《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迹卷后》云:
昔之论诗者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夫诗必如是,然后可以言妙。[11]66
再将海瑞《注唐诗鼓吹序》的相关表述陈列如下:
严沧浪说诗,方之妙悟禅道,曰:“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羚羊挂角”。万履庵鄙焉。夫水月镜象,言若荒诞,水诚有不可执著之月,镜诚有不可执著之象,而非诞也。文泥也,以诗之曲畅旁通随乐而与济之,文之妙也。[1]333-334
二人对于严羽诗论的引用是一致的,而且关于成功领悟其中法门后所达到的诗歌美感都称之为“妙”。这种论述思路上的一致为从陈献章文论宗旨来推断、演绎海瑞文学思想意涵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陈氏反对宋人以议论为诗,而主张将儒学之“道理”与诗学之“风韵”彼此融合,交互影响,以表达出潇洒澄澈的人性本真和天地情怀。所以其诗学之“含蓄”其实是通向儒学之“涵泳”,“涵泳”被宋明理学视为个体与圣贤学问、天地万物冥合会通的精神体验,是人格修养中一种重要的致思方式,故海瑞之谓“涵泳从容,得养于正”[1]502。诗学“含蓄”与儒学“涵泳”都讲究曲尽其思、幽穷其理,于作者而言是为“含蓄”,于读者而言则为“涵泳”,故二者在创构的内蕴性与接受的反复性上存在思维结构的会通。海瑞对此更有深刻的认识,其《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云:
《学记》之书,开而弗达,则思之义也。开则人有不能不思之端,弗达则人不能自已致思之实。不能不思,君子之善于使思驱之也。昔之评文,有曰言有尽,意无穷。作文之法,亦是如此。[1]504
“开而弗达”出自《礼记·学记》:“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13]其本意在于要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的门径而非代替他作结论,是一种儒家做学问的合理方法,其要义就在于所谓“不能不思”“使思驱之”。海瑞进而认为“言有尽,意无穷”之诗学含蓄旨趣的达成亦是人主动思索以求领悟的过程,其对严羽“言有尽而意无穷”诗学理想的化用更进一步表明其“内见蕴藉,外著风韵”之“含蓄”诗论实际上是一种打通哲学精神与诗学精神的心理枢纽。其对这种观念还有更为精致直观的表达,其《青山挽诗序》对同乡王思学(号青山)诗歌有“是诗如存,后能吟咏而思想者”[1]337的称许,“吟咏而思想”正是兼具诗、思二义的“含蓄”之精义所在。
结 语
就上述四个维度的相互联系而言,虽各有侧重却基本能够对应文学的本体论、主体素质论、创作思维论和审美理想论四个层面,相互构成一个以诗与思的交错离合为逻辑线索的思想脉络。“合文道”是对文学本质生命何以存在的哲学设定,“求真心”则着力解决心学视野下内心与外物之于文学的关系,“崇思想”就涉及哲理与情思在文学中的表现优劣问题,“尚含蓄”则是将传统的诗学趣味面向心学的致思方式以求获得理想文风。再就四者的思想渊源而言,海瑞文学思想在心性层面上的诉求明显发轫于当时势头强劲的心学思潮,他一方面拓展了白沙心学对于思与诗的文学想象与艺术体验,另一方面又延续着阳明心学对文与人之本源本性的形上思考,超越学派区隔的独立意识而使其“未尝不言经术而无道学气,未尝不言理学而无头巾气”[1]640。这种以我为主的汇合式思想谱系再配合其自身清刚正直的独特秉性,在一定程度上熔铸出了一种更符合当时个性觉醒、时代风向的文艺标识。
依循海瑞文学思想的心性维度进一步推导,还可以大致归纳出其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具体意义。首先,可以海瑞既非儒士又非文人的政治家定位,来为理解明代中后期心学羽翼下的文学思想提供某种独特的现实材料和知识资源。其次,就与古代文化的关系而言,海瑞文学思想中传统儒学、理学、心学、实学的成分交互作用,折射出传统士大夫多维度的心理构型之于其文论表述的塑造过程。最后,在更大的范围上,还能够助推对于哲学与文学这两大人类意识领域交互属性的认知,促进诗与思双向建构的中国式内涵填写与意义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