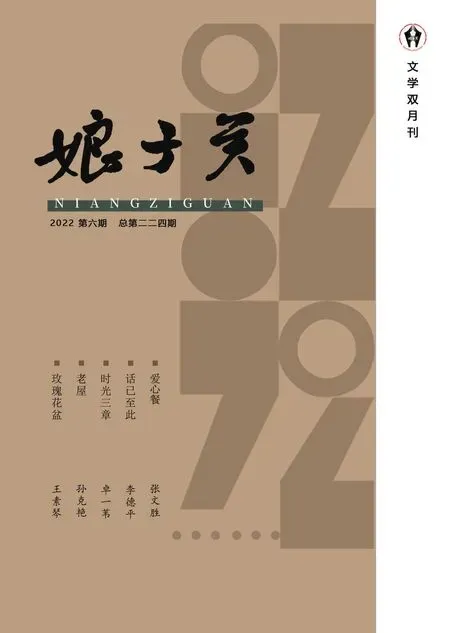窗口品云(外一篇)
2023-01-20柳林
◇柳林
如果大自然以天为封面,以地为封底,云便是最活跃最生动的文字,是情绪、是诗、是心象、是画。
坐在窗下,竟思慕起山居生活的明静清澈,怀念山中那些云絮、云霭、云带、云海。在城市,总觉云很遥远;在山里,却很贴近,云与我相互凝望、对语。有时,就在面前伫立,登上山顶,又在足下缭绕,归去,它挂在屋檐期待,未闭门窗,它会悄悄入室叩访;有时,追着云赶路,枕着云睡觉,不知不觉,云就成了伴侣。
山居的岁月,天地打开它们的书卷,读了山川、森林、花鸟这些实文,又读云这种虚文。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千古名句,不过是读云的一点心得,云,才是超凡的美学家。画家米芾、倪云林、八大山人,谁不是在云意中悟出美而再现与表现,谁不是云的弟子?当我们听见古典乐曲《彩云飞》或流行曲《故乡的云》,云又化为音符,在我们心里回旋,化为欢快和惆怅在我们心里弥漫。
读云,既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意义,更有一种审美的情趣与感悟。有时,云会很自然地再现你读过的那些诗的意境。孟郊的“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过去,被视作终南山风景,而当我走近云,又走出云,心想这诗句怎能用风景二字解释,分明隐隐含蓄着一种人生哲理,此刻,云,好像又是哲学家了。而“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当我做了游子后,又千百次凝望过山里浮云,惊讶除云之外,再难有这样贴切的对应物,这时,云不是理性,而是情性与物性了。
这么以诗悟云和以云悟诗,悟得的,还是古人的意境,这山中的云,岂是古人在诗中画中乐中能包揽与包涵?不仅在春夏秋冬不同的季候,它仪态万千,在晨昏或阴晴,更是景象各殊,在风里、雨里、雪里,也是不同的情调。云的面容、身影、色彩、性格、情趣、流韵,真是大千世界的大千气象,在无穷变幻中,展现造化的无穷。崛于千仞的峻峰,堪称雄奇了,云在峰巅,也作山势,更伟岸地升高,使高峰在它足下变成侏儒似的小丘。有时,又拉出大幅帷幕,遮住山的身体,只显出山顶,或者懒懒地睡在山谷里,做着自己的梦。它十分敏感,又很调皮任性,有时,同风在天空赛跑,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驰过,恍惚马鬃飞扬,草原上的马群,在天空驰骋。也许是败在风的手里,禁不住泪雨滂沱起来,痛快淋漓地宣泄,又永远挥洒不尽它的感情。雨后,总飘出云带,系在山腰,或浮出云朵,挂在树枝,表现它的情感,既是奔放的,又是缠绵的。这种缠绵甚至与奔放汇合,如钱塘大潮无声地铺天盖地涌来,淹没了大森林,我真怀疑,这是云海与林海的一种恋爱方式。云海与林海,不都是以“海”为其共性吗?它们有相同的气质、品性与襟怀,怎能不心心相印?一到拂晓,曙色初萌,云就在天边铺开产褥,迎接新的一天降生的孩子——太阳。
更多的时候,在山的那边,它是缕缕云烟,袅袅地升腾,使我怀疑山中有位仙人在炼丹,于是遐思不辍,联想山中每天吐出的日月,岂不是炼出的不老仙丹,育万物生生不息吗?天地这本大书中的云语,真是百读难尽,百读不厌。
隔窗观天
笠翁有言:“人之不能无屋,犹体之不能无衣。”即是古人房舍筑于山间泽畔,虽蓬门荜户,依窗而眺,往往生出隐居山林,超凡脱俗之惬意。
如今,人们大都入住仿佛密林般的水泥钢筋造就的拥挤、高大楼群之内,楼外楼,窗对窗,上仰一线天,下视一片杂乱无章。谁也无法享受“窗中列远岫”“列绮窗而瞰江”之情调,更领略不了“丹崖碧水,茂林修竹,鸣禽响瀑,茅屋板桥”(清·李渔《闲情偶寄卷四》)之山居窗外胜景。蜗居一隅,窗外则寂寞冷清;杂宿闹市,又喧嚣嘈杂。《释名》曰:“窗,聪也;于内窥外,为之聪明。”站在窗前,听到的是大呼小叫,看见的又是人如蚁阵,此时能耳聪目明吗?恐让人不置可否。
现代人多以居于城市为幸,且越大越好。想在山野中筑屋,非一般人所能及:一则缺少大量资金;二则不安全,担心做无谓牺牲;三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那生计不可或缺的诸如煤水电之类怎么办?于是,能在城中觅得一席地理位置不错,面积大些,楼层又满意的栖身立命之处,也算一种福分了。谁还敢生出其他奢望?至于窗外如何,怕是由不得你挑选,也顾不得那许多,只好听天由命了。
“窗,穿壁以木为交窗,所以见日也。向北出牖也。”《说文》古人的这一说法,大抵是“在墙曰牖,在屋曰窗”的意思。“窗”“牖”尽管叫法不同,但功能想必无什么大的区别。小时生活在北方农村,家中三间房屋每间都辟有南北两窗。虽居于泥土陋室,难以同当今城中的高楼广厦相媲美,但视野宽阔,满眼“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之美景,让人心醉。南窗外,有两株高大的枣树,一簇茂盛的果树,随着栽种的黄瓜、豆角、西红柿及各种一年生草本花卉的出土、长高、含苞欲放,再到结出累累之果,窗外便成了一座“花枝草蔓眼中开”的小小花圃,花草的清香沁人肺腑,果实的丰硕使人欣慰。归巢燕子呢喃,蜜蜂花间采蜜,小鸟枝头鸣唱,常有“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宋·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的景象发生,那儿童便是我和我的同伴了。北窗外则是一个很大的园,这不免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我家后面的这一园中虽无什么雅致的名称,更无百草园里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槐树、萦红的桑葚和轻捷的叫天子(云雀)、缠绕着的何首乌藤和木莲藤,更没有赤练蛇等。但螳螂舞刀,蟋蟀弹琴,颜色各异、大小不同的蚂蚱蹦来跳去,蜻蜓小憩于栅栏的枯树枝头等等,却是常见的。北面有一行高大的柳树,郁郁葱葱,树下一条潺湲的小溪流向村西的一座大池塘内,是“听取蛙声一片”的好地方。碧绿的菜畦倒有一大块,在园中的西面,均是供一家人饭桌上的各种蔬菜:白菜、生菜、萝卜、茄子、辣椒、葱蒜等,春夏秋三季不断。东边的一大片便是葱郁的玉米地,长势很旺。闲来无事我便跳过北窗,在园中转来转去,欣赏田园美景。在与邻居相隔的东栅栏下,以枯木为柱,野草、玉米叶子为盖,搭起一座足可容身的茅棚,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里面,炎热天防晒,刮风时躲风,下起雨来又可避雨,可谓望晴空丽日,听风听雨,听鸟虫吟唱,想必其中亦有诗的意境。只是那时年幼,说不出什么,虽无诗句吟成却有无限的乐趣。那感觉即是踏入城中的娱乐城、游戏厅、儿童乐园,抑或风光旖旎的名胜古迹、公园里,也无法寻觅到。
我如今栖身于人烟稠密的楼群之内,居住条件比儿时家中的泥土房不知好多少倍。屋中独辟一室作为书房,窗前置一案,或书或画,或读书,自有无言的情趣。然窗外的景致绝没有梁实秋先生寄身四川的“雅舍”时窗外的空旷,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土山坡。更比不得其旅居海外的“白屋”,窗前有花有草,有蓝天有碧树,有活泼蹦跳的儿童,有手捧花伞的男男女女,足以怡人倦眼,充溢情怀。
如今,我闲时伫立窗前,尽管有烟有酒有茶,但俯仰天地之间,眼前窄狭的一条通道,仅仅一线似的不再清亮的蓝天,不要说花草,就连像样子的树木也无几棵,人群的匆忙,商贩的叫卖,物欲的涌动以及人心的不可测……令人心烦意躁。无奈中只得关窗闭户,把这一切阻隔在外,且回到案前,任寂寞与孤独笼罩,挥毫欣成佳制,把卷喜得佳句,心远而淡泊,陋室自然清静,必沉醉于无牵无挂、闲适素心的大安详之中。每遇此时,便想起家乡泥土房窗外的迷人景致,还是梁实秋先生说得好:“临褚凄怆,吾怀吾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