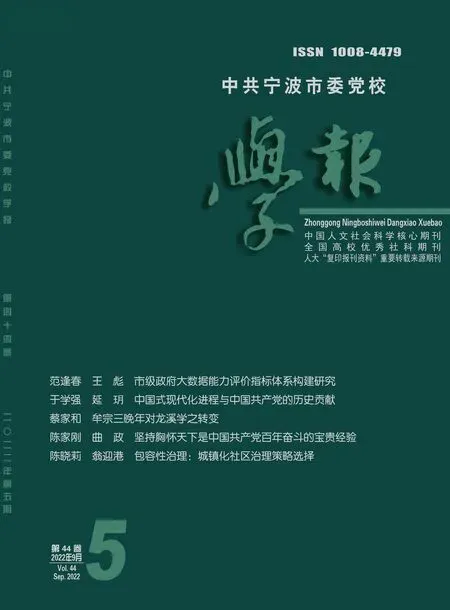从传统到现代:马一浮早期的思想演进
2023-01-08朱晓鹏
朱晓鹏
从传统到现代:马一浮早期的思想演进
朱晓鹏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1)
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创始人之一,其学术风格和言说方式虽然都十分传统,但其儒学思想具有自己的创新性,而且他在早年还有过激烈地反传统而追求现代西学的思想经历。马一浮弃旧图新、热衷西学、激烈反传统的早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促进了后来他向传统的回归,甚至可能构成了他形成自己独特的新儒学思想的必要张力。
马一浮;早年思想;热衷西学;反传统
马一浮(1883—1967)是学问渊博、涵养深厚的现代著名学者,与梁漱溟、熊十力一起被视为“现代新儒学三圣”。但是,与梁漱溟、熊十力颇为不同的是,马一浮并没有像他们一样在当时就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名满天下,而是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逐渐被人所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一浮的学术风格一向崇尚孔子的“述而不作”,没有刻意去追求所谓的创新,无论是其言说和写作的方法,还是其所关注阐述的理论问题,都刻意地保持了十分传统的方式。另外,马一浮乐于自隐、不务虚名,不愿进入现代大学及学术体制,也是原因之一。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甚至一些对马一浮有好感的人或研究者也同样认为他是继承传统有余而创新不足,是儒家而不是新儒家……即使像竺可桢这样欣赏马一浮,请他去浙江大学任教的人,也认为马一浮复古精神太过……以后一些像李慎之这样的学人干脆就说马一浮不属于现代学术了。”[1](p5)然而,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一下马一浮一生的思想演变过程,不但可以看到他有自己的创新性的儒学思想,而且还可以发现他在早年有过激烈地反传统而追求现代西学的思想经历。显然,考察马一浮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它又具有什么样的内涵等问题,对了解马一浮后来如何回归传统是必要的,甚至可能构成了他形成自己独特的新儒学思想的必要张力。这样看来,马一浮早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虽然学术界关注得还比较少,但还是值得展开深入系统的探讨。
一、弃旧图新
马一浮成长和活动的时代正在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腐朽愚昧的清王朝的专制集权统治之下,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在西方外来文明的强势冲击下已全面溃败崩解,使国家和个人均深陷于空前的苦难和危机之中。这些无疑构成了马一浮治学和思考的不可回避的时代背景,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一浮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故乡绍兴上虞度过的。在这山水秀丽的江南乡村,马一浮以勤奋和聪慧获得了神童美誉。1898年,16岁的马一浮应父命参加县试就独占鳌头、名震乡里。如果不出意外,马一浮应该会在传统的科举考试道路上走得很远很成功,“马一浮在家庭中受到的是典型的儒家教育,儒家的道德文章以及封建的八股取士、科场功名正是他的父亲对他所能唯一寄予希望的。”[2](p6)但马一浮却在17岁新婚后不久就先后去绍兴、上海求学,与好友谢无量等人一起学习英语、法语,其间虽因父亲病逝、妻子亡故曾短暂回乡,却在经历了这些人生中重大的不幸事件后仍坚定不移地回上海学习外文和西学,并与谢无量等人共同创办了《二十世纪翻译世界》,全力投入到对各种新学的研习译介中去,直至1903年6月赴美国工作和游学[3](pp14-15)。这长达五年的经历,对于年青的马一浮来说,无疑是其人生和思想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转变。
那么,这种巨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可以说,几乎所有马一浮的传记及相关研究都没有深入明确地解答过这一问题。而实际上,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是可以找到相关的主要原因的。
首先,要了解马一浮的这种思想上的巨变,就应先搞清楚马一浮此前的思想状况。马一浮在自述其一生学术路径时说:“余初治考据,继专攻西学。用力既久,然后知其弊。”[4](p771)可见马一浮在转向西学前曾有一段“治考据”的时期,对这段“治考据”时期,马一浮曾专门回忆过:“某幼时尝依张文襄《鞧轩语》求治经门径,及用力既久,方知此只是目录学,与身心了不相干也。”[4](p771)由此可见,马一浮最初治学,是依清儒通行的以考据、目录之学为主的路径进行的,而这个时期大概从早年求学、入绍兴府学直到1901年去上海游学为止。马一浮在这方面的学习成效,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从他在据说需以古籍集句成文的县试中考了第一名的成绩中可见一斑。但是,马一浮在深入研习之后,发现“此只是目录学,与身心了不相干”,最终予以放弃。这说明此时的马一浮已不满于考据、目录之学的外在知识性的学习,而要求能诉之身心的内在性体悟和自得之学,这显然是其思想认识上的一个巨大进步,而正是这一思想进步促成了马一浮放弃传统的知识体系和治学路径,转而投入当时正方兴未艾的西学东渐的洪流中去。
其次,促成马一浮放弃传统治学路径最直接原因应是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自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拥有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以一种强硬的方式宣示了其代表的现代器物、科技文明方面的巨大优势,也凸显了中国传统科举制度下人才教育和选拔上的落伍和积弊:科举的内容和形式都已无法为晚清社会提供足够先进的机械和新式武器的技术人才,更不可能据此培养出具有创新性思维能力的新式人才,所以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明确提出变法“莫亟于废八股、禁科举”[5](pp177-191)。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社会改革科举制度的需求,清政府及各省于甲午战争后的次年(1896年)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留日学生。马一浮参加县试那一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创办了京师大学堂,拉开了废除沿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及其整个皇朝专制制度的序幕。1901年清政府迫于内外严峻形势,明令变通了科举章程,190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制,代之兴办各类新式学校。显然,正是这种科举渐废而新学速兴的重大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趋势上的变革,成为决定马一浮无法再继续沿着科举制的道路前进的主要原因。与马一浮参加同一场县试的鲁迅就于同年去了南京,先后入读了新式学校南京水师学堂和路矿学堂,另一著名同乡杜亚泉于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郡中学堂数学教员,两年后又赴上海创办了中国近代首家私立科技大学——亚泉学馆,致力于西学的普及教育,成绩卓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一浮放弃科举的旧途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尽管“西学东渐”之风已愈演愈烈,新式教育也正在兴起,但像马一浮这样的选择毕竟还是属于“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先进分子的大胆作为,对于大多数仍受传统价值观影响的家庭来说还是一时难以接受的。据说马一浮父亲生前就十分反对他“远离家乡去读书这件事”[6](p153)。这也表明了年轻的马一浮很有自己的主见和胆识,也承受了不少压力。
当然,推动马一浮实现上述人生和思想路径上巨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应是马一浮对西学的热切向往。在近代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下,特别是在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激荡下,向西方学习以便寻求科技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真理成了当时先进中国人的普遍共识,马一浮和那些具有爱国抱负的知识青年一样,真诚地渴望新知识、追求新文化,所以他决然辞别老父和新妻到上海游学,就是为了能学习外文直读西方原著,了解西方最先进的思想文化资源,用以启迪自我、唤醒民众,谋求人类的普遍幸福。马一浮在1902年写的《故马浮妻孝愍汤君权葬圹铭》中说:
浮之为志,不在促促数千年、数十国之间。以为全世界人类生存之道,皆基于悲之一观念所发布,渐次而有家族、社会、国际之事,迄于今日,其组织规则,尚未有完全者,不改革全世界迷信宗教、黑暗政治之毒,则人类之苦无量期,而国种优劣存亡之故,尚为人类历史事实之小者。浮之言曰:吾欲唱个人自治、家族自治,影响于社会,以被乎全球。破一切帝王圣哲私名小智,求人群最适之公安,而使个人永享有道德法律上之幸福。[7](pp248-249)
此时的马一浮已吸收了很多西学中新的思想文化观念,转化为自己的全新价值观,他要求超越一家一族、一国一地的范围,而追求全人类最普遍的价值:“破一切帝王圣哲私名小智,求人群最适之公安”,“以为全世界人类生存之道”。所以“马一浮之志、之学、之性情,之意识”已不是简单的求知和个人在仕途、功名及道德上的自我实现,而是关乎全人类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和超越性的价值。显然,马一浮已开始超越一般传统知识分子的追求,成为具有新型知识分子特质的先进中国人中的一位。正如《马一浮评传》中所说的:“自1901年清政府迫于形势,正式明令变通科举章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或封建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受着民族危难的刺激和群众斗争的影响,纷纷走向清皇朝的对立面,成为清皇朝统治者无法控制的一股力量。”[3](p14)历史表明,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中一股重要的革命力量。马一浮在上海的经历,正是促使他蜕变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的关键。他在上海的几年中除了与好友谢无量等人一起发愤学习英、法等多种外文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译介进来的西方名著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各种进步书刊。同时,“马一浮还广交朋友,相继结识了马君武、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洪允祥、林同庄等一大批有识之士。”[3](p15)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及社会革命运动中的著名人物。马一浮还在《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上译介了大量西方的文学、政治、经济、哲学、社会等新思想,用实际行动与朋友们一起参与了这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和社会革命运动。
同样,对新思想、新文化普遍价值的追求也促使马一浮于1903年应聘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公署秘书赴美游学。马一浮在美游学近一年的时间里,利用工作之余阅读了一大批西学著作,“从(马一浮)当时的日记看,每隔三、四天就要去书店购一次书,购回以后常不顾酷暑严寒,夜以继日地口读手译,所读的书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及语法修辞、历史等方面的著作……在广泛阅读中,对卢梭、马克思的著作尤为喜爱。得到卢梭《民约论》说‘胜获十万金’,病中得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8]。青年马一浮与当时大批留学海外的留学生一样,希望去西方寻求一条救国的自强之路,更希望从西方文化中找到一种人类解放的普遍真理。正如他写诗自述的:“沧海飘零国恨多,悠悠汉土竟如何?”所以他要“万里来寻独立碑”[9](p620)。马一浮之所以对卢梭的政治学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予以重视,大概也是由于它们所蕴含的普遍的思想价值和社会革命意义。
更进一步来看,推动青年马一浮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变,还有其个人独特的人生际遇方面的因素。在马一浮的早年生活中,他所经历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生遭遇就是其家庭的衰落和家庭成员接连不断的死亡带来的家庭解体和深重痛苦。马一浮出身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先祖“世世以儒学著”[7](p216),其父马廷境曾任四川潼川府通判、仁寿县知县,“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物,儒学正统的一个典型”[3](p2)。后来,他挂冠归籍后,家道中落,但仍能以田园、骨肉之乐,切已躬践庭训,影响于马一浮。不过,家道的衰落也引起了家庭的经济困顿,这可能是导致其家庭成员不断病故的一个重要原因。马一浮从6岁随父母归乡后直到20岁,先后失去了三姐、母亲、二姐、父亲、妻子等五位至亲,这不仅让马一浮的家庭完全解体,使他从此几乎孤单一身漂浮于世。缺少家庭的亲情和温暖,也使一直专心治学的马一浮生活困顿,长期依赖他人照料接济。这种亲人的连续死亡和家庭解体对马一浮造成的巨大痛苦,无疑也会对其思想观念和性格产生重大影响。滕复在论及青年马一浮这些遭遇时说:“所有这些都对马一浮的思想造成强烈的冲击,不仅构成了他思想上的矛盾,同时也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创伤。”[2](p12)就像少年时期家道中落和经济困难给鲁迅的精神世界打上了难以抹去的烙印一样,青少年时期的这些痛苦遭遇既给马一浮的整个人生抹上了一层悲观的底色,更促使他努力挣扎,摆脱旧的束缚以求新的生命。马一浮原名“福田”,正是在20岁前后自己改名为“浮”,又名“一浮”。同时,他还自题旧照曰:“此马浮为已往之马浮,实死马浮矣。”[10](p19)显然,家庭灾难造成的极度痛苦已使马一浮万念俱灰,坠入了虚无的深渊,不得不宣告自己的死亡,即作为过去有着特殊遭遇的马浮的死亡。但实际上,马一浮仍是希望,通过这个旧个体的终结,是要让自己与“已往之马浮”作告别,挣脱以往的有限世界和特殊经历,而飞升向一个无限超越的新世界:“浮之为志,不在促促数千年、数十国之间”,即使是“国种优劣存亡之故,尚为人类历史事实之小者。”所以,他真正要追求的是“欲唱个人自治、家族自治,影响于社会,以被乎全球。破一切帝王圣哲私名小智,求人群最适宜之公安,而使个人永享有道德法律上之幸福。”[7](pp248-249)亲人的死亡、个人的苦难没有彻底摧毁马一浮,反而成为马一浮转向寻求新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展开一个新的思想创造进程的契机和动力,这正是马一浮自谓的“以为全世界人类生存之道,皆基于悲之一观念所发布,渐次而有家族、社会、国际之事”。[7](p248)这样,青年马一浮不顾一切地走出家乡,走向上海和国外游学,如饥似渴地钻研西学,正是他在努力寻求一种最普遍的真理。对马一浮思想演变中的这一特点,陈锐曾有较深入的认识,他指出:“过多的死亡使马一浮逃向江湖,逃向那无限的虚空和普遍的存在,并且还像叔本华和王国维一样,从人类的苦痛中到达普遍的升华,来认识世界和人生的真谛,并将整个人生的发展和生存建立在此种基础之上。”[10](p18)
马一浮所背负的深重痛苦几乎贯穿了他一生,他在多年后写的《哭二姐》诗中说:“金刀剜臂痕犹在,脯奠陈筵殡已迁。老泪何堪拚一恸,昨宵曾自向窗前。”[9](p619)二姐割股救父以至早亡的惨痛经历宛如眼前,始终挥之不去,多年后仍常在深夜辗转难眠扪心自问,难以化解。又如他在妻子去世后,一再谢绝友人劝告,终生未再娶。人问其故,他说:“人命危浅薄,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吾见室人临终时之惨象,惊心怵目,不忍入睹,自此遂无再婚之意。”[3](p16)马一浮后来几乎没怎么回过故乡,因为“人去楼空,回乡又添触景生情,不如其已。盖此是吾伤心之地也。”[3](p16)不过,难能可贵的是,马一浮能努力超越这些常人的痛苦和重负,通过这些痛苦和重负来认识世界和人生的普遍真理,不仅实现了自我拯救,使自我的生命获得了新的价值,塑造出了“将来之马浮也”,而且进一步升华为对更普遍性价值的关心和对整个人类生存发展之道的探求。也正是这种生命意义的升华,才为以后马一浮着力探求中国文化的再生及其普遍性价值、开创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境域打下了一个深厚的基础。
二、致力于西学
在青年马一浮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中,“弃旧图新”并没有停留在表象上,而是包含着切实内容:所弃之旧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那些落后的文化观念,“皇朝的暴主政体”、奴性的卑劣人格等,而所图之新乃是西方文化中全新的有关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及其人生观、价值观等新知识、新观念。这种弃旧图新的现象,从表层上来看,主要是由于近代中国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入侵和威胁后所作出的一种回应,呈现为一种典型的“刺激—反应”的被动现代化模式。正因此,以西方的全新知识系统为代表的现代器物、科技文明成果在戊戌变法之后逐渐主导了中国的教育、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主要方向。所以,转投西学,甚至留学西方,以求能更多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思想学说,是那个新旧交替时代有志青年们的普遍目标。马一浮游学上海和美日,同样也是怀抱了这种自救救人的热切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先秦诸子百家起源于“救时之弊”的时代需要一样,青年马一浮和当时那些先进青年一样,他们转投西学甚至留学西方,正是出于“刺激—反应”模式下“救时之弊”的选择。
不过,如果从更深层次上来看,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弃旧图新现象,正是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合法性危机”和“意义危机”大爆发的结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造成了原有社会的衰乱、秩序的解体和道德的堕落等,甚至达到了亡国灭族的毁灭边缘,而造成这一切可怕后果的外来因素终究是次要的,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有机体自身已腐败不堪,以致原有的一切价值和意义都已无所附丽,这才应该是最根本性的原因。所以,要探求解决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途径,首先要解决造成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合法性危机”和“意义危机”的有机体本身的腐败和更新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清末民初青年马一浮与他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一样已初步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十分可贵的,这说明他们已认识到必须借用西方外来文化中全新的政治、思想等工具对中国社会及文化作彻底的改造,否则别无出路。所以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论争,从“中体西用”为主的观念转向“西体中用”“全盘西化”等为主的观念,也证明了这是社会共识的转变。
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青年马一浮无论是在上海游学还是在美日游学,都十分热切地投身于西学,努力了解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从马一浮开始到上海求学,到1906年马一浮寄居西湖广化寺全力攻读《四库全书》,标志着其“治学的重点转向国学”[3](p158)为止,在这五六年时间里,马一浮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学习的确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因此大多数研究者都“相信他在短短几年间确实读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同时对西方学术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了解。”[2](p17)马一浮不仅广泛地涉猎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主义思想等,而且能利用在美日游学的机会,切实地观察分析西方社会的现实,为真正学习了解西方社会文化提供了更真实的路径。譬如据他在美国时的日记书信记载,他观察到美国人普遍热心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大量捐赠财物,与国人较普遍的狭隘、自私,“不顾社会之苦痛,而唯知营自身之快乐”[11](p49)相比,其强烈的集体精神和社会公德意识令人印象深刻。由此马一浮进一步延展到对中西方不同社会性质的认识,他认为,普遍的幸福与否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还是落后的标准,一个社会中凡痛苦多而快乐少,则为罪孽堕落的,而快乐多而痛苦少就是幸福进步的。欧美人正在致力于建造快乐幸福的社会,他们在为一个共同的社会整体奋斗的同时,每一个体也能享受社会进步繁荣的成果。而在中国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人人只知追求个体(自我及家族)的幸福,却不知没有社会整体的进步只会导致每个人更大的痛苦。所以,马一浮又将理想的社会形态分为“美的世界”和“恶的世界”,“美的世界”就是幸福快乐的社会,“恶的世界”就是罪恶痛苦的社会。西方文化“以科学哲学之抽象的美,而造成社会国家具体的美。今欧美人,可谓能造美的国家。惟于美的社会,尚有欠点耳。吾支那之国家、社会,则非美的而恶的也。吾支那人,惟够造恶的,日日生息陶铸于恶之下,以致自己丧失天赋之美性,可哀也哉!”[11](p44)所以,“文明之极边,人道之究竟,不过完全此‘美’而已。发达两者完全者,谓之‘文明’,反是则野蛮也。”[11](p44)应该说,马一浮的这些认识虽然还带有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论的局限,但他对中西方社会性质的认识还是富有洞察力的,达到了同时代人难得的深刻程度。对此,马一浮是有所自觉和自信的。他曾批评国内学人对西学的了解还大都停留在其“形而下之器”的层面,“是当世为西学者,猎其粗粕,矜尺寸之艺,大抵工师之事,商贩所习,而谓之学。”[7](p294)但马一浮相信,西方文化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化应该是体用不二,有体有用的,所以西学中不会只有一些器用之学,而是也应存在着一些更为根本的形而上的理论。由于这些形上之学“大抵推本人生之诣,陈上治之要,玄思幽邈”[7](p294),更多的是体现在不具实用价值的哲学、文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往往不为世俗所重,却被马一浮所喜好:“凡此皆国人所弃不道,甥独好之,以为符于圣人之术。”[7](p294)马一浮认为,国人只图实用,幻想走捷径抄近道,以为只师夷之长技就能制夷,这种浅薄之见已被甲午战争的惨败所粉碎。只有真正放下身段,承认并虚心研习西方文化中有关社会人生的大本之道,才能找到孜孜以求的真理,为中国的复兴找到可借鉴的路径。马一浮的这种西方文化观是十分富有远见,值得肯定的,居于那个时代的前列,因为熊十力、贺麟等人也是在几十年后才表达了与马一浮类似的坚信文化是体用一源、西方文化既有其用也有其体的观点。只可惜,青年马一浮的这些远见卓识未能在当时整理成文以广其影响。
三、激烈的反传统
马一浮对新的西方社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热切拥抱认同,是以他对旧的中国原有社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否定为前提的,正是在深层次上中国原有社会文化的有机体本身已腐败不堪,居主宰地位的统给者又骄横独断、愚昧妄行,使得社会的衰乱和秩序的崩溃已近于大爆发,整个社会文化的“合法性危机”和“意义危机”空前剧烈。而这些无疑构成了马一浮在西学的启发下对中国原有社会文化进行否定和批判的重要历史背景。
马一浮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清政府腐败、专制的揭露和批判。马一浮通过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思想学说的了解,特别是到美国游学后,对照、反观中国的社会现实,由此形成的强烈反差感,启发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特别是清王朝的专制集权和愚昧腐败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从而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愤恨之情。马一浮是怀着国破家亡的剧痛前往美国的,他写诗说:“国命真如秋后草”“沧海飘零国恨多”[9](p620),他认为,近代以来列强对我国的肆意欺凌、社会民众遭受的种种惨痛,最深重的根源无不在“暴主之政体”:“盖彼固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皆我之败种,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已失国际上之位置,比于亡国。”[11](p2)在马一浮看来,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毫无进步可言,不仅对近代合理的“群治”政治原理毫无所知,也不知道什么是作为“社会全体”共有之国家,而且民众贱若草芥,专制君主只会高高在上,成为独夫民贼,为了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无所不用其极,已成“腐臭政府”“暴主政体”。从最普遍的社会正义立场上看,这种罪恶累累的君王不仅不应再成为民众的合法统治者,反而已成为人民的公敌,如果无法变革,“则唯有扑灭,不少可惜。……必罪人灭绝而后群治可保、道德可全也。今政府为奴隶者何也?中国社会全体之罪人,何一非中国社会全体之公敌,何一非中国社会所诛灭者乎。”[11](p10)为此,他十分赞同近代革命派提出的推翻满清政权、重建文明中国的主张:“夫中国寸土一毛皆我汉种所有,彼政府正我家贼,不扑灭何待。览此不胜愤激,不知革命党运动何若耳!深愿一激不挫,从此推翻,吾辈即流血以死,亦复何憾。”[11](p7)马一浮虽然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来到美国的,但出于对其专制和腐败的痛恨,他到美国一星期后就剪掉了长辫子,其在日记中记载:“下午遂截辫改服,同住者皆笑而讪之,真奴隶种也!”[11](p3)马一浮怀抱“万里来寻独立碑”的目的,希望通过向西方寻求自由、民主、独立的普遍真理,达到“一凤孤鸣万鸟歌”“谁为吊魂找汨罗”[9](p620)的救民救国之理想,所以他到美后敢于公开地剪辫改服,明确自己反对满清统治的立场。马一浮到美后不久发生的上海《苏报》案,章太炎、邹容被清政府抓捕入狱,谢无量受牵连逃往日本,马一浮十分忧愤,写诗云:“一夜西风起,萧条万象收。残山皆筑垒,衰草已惊秋。贾哭因时悯,阮狂抱国忧。家乡三月史,遥寄海西头。”[12](p722)
客观来说,相比于当时革命派反对满清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新国家的先进思想而言,马一浮的认识并不见得太独特,应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但马一浮至少没有落伍于时代,至少不是一个后世大多数人印象中的保守主义的典型。
二是对软弱、奴性的民族性的痛切批判。青年马一浮在揭露和批判清王朝的专制和腐败,视之为罪所当诛的“中国社会全体之公敌”的同时,也对民族自身普遍具有的软弱、奴性和自私的特点深感痛恨,尤其是他身处异域,看到别国国民充满蓬勃生机的美好生活,“闭目内忆我国之悲境”,不能不充满了感慨,正如陈锐说的:“在马一浮居留北美的这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中充满了热情,对中国民族的奴性充满了批判,而对美国和日本都处处流露出赞美。”[1](p75)正是在强烈的对比中,他对故国是持了复杂的感情的:既对中国社会历经患难的现状深抱同情哀痛之心,又对国民的衰弱和奴化现象深恶痛绝。他看到动物园里几只凶猛的狮子被一个纤纤女郎驯服得俯首摇尾、任其驱使,不禁感慨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已被君权和儒教扼制驯化不断衰弱和奴化,真如被驯化了的狮子一样:“中国经数千年来,被君权与儒教之扼,于是天赋高尚纯美勇猛之性,都消失全无,遂成奴隶种姓,岂不哀哉!”[11](p55)中国人在历经长期的极权统治奴役之后,已普遍地丧失了纯美勇猛的天性和活力,就连那些已身处自由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们,其坚牢的奴性都难以改变。“哀哉,我同胞乎!入自由国,受自由教育,而奴性之坚牢尚是吾族富有豸耶!”[11](pp30-31)譬如,据马一浮于1903年8月17日的日记记载,这一天为“中国满洲君主载湉之生日,同在诸狗子皆摇尾巴叩头,写一纸牌曰‘皇帝万岁’,以供奉之。直言病狂学鬼,诚可哀怜。予辄坚卧不起,彼曹度在亢,不敢来嬲也。”[11](p10)所以马一浮对身边那些奴颜婢膝的同住者都鄙弃地称之为“狗子”“学鬼”。他们已经丧失人的自尊自强之心,只热衷于动物般的逐利求官:“前观某君报告书云:‘欧洲中国留学生之骄情无志气可为太息,彼人见欧人之尊礼印度贵族,则思求官,以为亡国后可蒙欧人之一盼;又见南非洲之富人面目漆黑,而巴黎之贵女有与之同车者,则又思发财,以为吾虽亡国,萎黄之人种,但得拥巨金,尚可匍匐于美人之前。’呜呼!此种留学生适成其为同治时代派遣之留学生耳!安有半个之人物耶!哀哉!”[11](p40)可见,马一浮对这些懦弱、自私的留学生十分鄙视,斥责他们已完全不像个人了。这些留学生们关心的不是民族的尊严和危亡,反而是“‘我学生当造成辅佐朝廷之资格’之语,嗟乎!至于今日,苟尚有一点人血者,尚忍作此语耶?因又念此种崇拜暴主之政体,天赋之贱种,真不足与语也。”[11](p30)
三是对传统礼教的批判。马一浮在批判中国民族性中的衰弱和奴化倾向时,不仅把其罪责归于统治者专制集权的“暴主政体”,还把病毒根源挖到了传统儒教之害,认为正是儒教配合君权扼制了中国民众达数千年,使整个民族都丧失了自由、纯美的天性,陷于被奴役的命运。马一浮说:“中国经数千年来,被君权与儒教之扼”,“宋明以来,腐儒满国。”[11](p48)传统儒学所崇奉的礼义道德本来是用来教化社会、促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然而,自秦汉以后,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儒学被改造利用成为国家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之后,也就逐渐沦为了专制与腐败的温床:“一方面是愚忠愚孝,大多数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森严的礼教制度下,礼教已经沦脊夹髓,深入人们的头脑,主宰人们的生活,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则是少数人(统论者)的特权、腐败和堕落。这正是过去中国历史的全部写照。”[2](p11)尤其是在儒教所最为注重的道德和教育领域,其流弊也最为深重,这也正是中国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在这些方面批判最有力的原因所在,如对礼教吃人的批判、要求废除科举制等。青年马一浮生活在一个谨守礼教的家庭中,而他所遭受的个人和家庭中一系列重大不幸和痛苦,如二姐、妻子的先后早亡,应该都与传统的纲常伦理中的孝亲、节义的异化和误导有根本性关联[1](pp47-60),如马一浮二姐在其父病中,不解衣带四年侍于床侧,“时时思得终殉先君”[7](p229),并割肉救父,病甚遂卒。而马一浮妻子新婚不久就去世,据丰子恺说是“汤氏夫人被封建礼教所杀,真是可怜。”[13](p6)青年马一浮所遭受的这些惨痛经历,使他对传统礼教和家庭伦常的残酷有最切身的感受,应该也是促使他在父亲、妻子先后病重乃至去世后仍一再逃离家庭的重要原因。这种逃离,是青年马一浮面临巨大灾难和痛苦时出于本能的自保自救行为,正像陈锐指出的:这些离别行为“也许能传达出当时的道德风俗和伦常名教给马一浮带来的复杂感受;或者也可能传达出饱受忧患的马一浮要逃离家乡,逃离这个笼罩着恐惧和死亡的家庭的愿望。”[1](p57)的确,当时那个时代确实有许许多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马一浮一样从旧的家庭、旧的社会环境里逃离出来,投奔当时居国内最西化的上海甚至欧美日本游学和工作,以求得自我的新生命、新生活,同时,它也是青年马一浮对传统礼教的反抗和初步觉醒的象征。马一浮在给妻子写的祭文中说自己因“念家道之酷,终不能相保,计不知谁先死者”而前去上海,“奔走游学江海”时[7](p232),马一浮的妻子却不可能像马一浮一样逃避那些沉重的家庭责任,不得不忍受着各种礼教的压力,终日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马一浮写道:“君以弱质留,奉几筵,承祭祀。茹饮万毒,轮转百辛。……君归浮家三十四月,无日不在悲愁惨怛之中。”[7](p248)年轻的马一浮妻子独自在家侍亲守礼的生活竟然是“茹饮万毒,转轮百辛”,“无日不在悲愁惨恒之中”,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在家庭伦理和名教制度的温情外衣下,竟包藏了这么多对个体生命的无情摧残和对自我价值的残酷否定!所以,当马一浮说中国人数千年都遭受“君权与儒教之扼”,以致普遍地丧失了自由、独立的人格和纯美、幸福的生活时,无疑是以自己切身的惨痛经历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马一浮在其二姐、妻子早亡后要一再地写诗文哀悼纪念她们,诗文充满了深沉的悲痛、愤怒和歉疚的复杂感。其悲痛和愤怒是感于她们成了纲常礼教的牺牲品,其歉疚是虽自逃于苦海,却未能挽救她们于水火之中。
总的来看,青年马一浮以西方文明为镜鉴,在批判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专制的同时,对中国民族的软弱、奴性和自私以及传统儒教表现出了强烈的痛恨和厌弃。尽管他的这些认识还缺乏系统的分析阐述,但在那个时代已属难能可贵,已超前了许多人的认识。正像陈锐说的:“他的这些语言和愤激之情,对民族传统和劣根性的批判,在十几年后新文化运动中倡导西化、批判传统的鲁迅、陈独秀那里,才真正成为社会和知识界的普遍潮流。”[10](p2)而且,马一浮早年这种激烈地反传统而追求现代西学的思想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促进了后来他向传统的回归,甚至可能构成了他形成自己独特的新儒学思想的必要张力。不过这些问题的具体探讨,只能留待另文进行了。
[1] 陈锐. 马一浮与现代中国[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2] 滕复. 马一浮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3] 马镜泉, 赵士华. 马一浮评传[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
[4] 乌以风. 问学私记//吴光主编. 马一浮全集: 第一册[M]. 虞万里, 徐儒宗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5] 严复. 救亡决论//卢华、吴剑修编. 严复论学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6] 马镜泉. 马一浮传略//毕养赛主编. 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7] 马一浮全集: 第二册[M]. 吴光主编, 朱晓鹏执行主编.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8] 汤彦森, 丁敬涵. 学融百家一代宗师——略述马一浮先生的治学精神与学术思想[J]. 古今谈, 1989(03).
[9] 马一浮全集: 第三册[M]. 吴光主编, 徐儒宗, 董平编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10] 陈锐. 马一浮儒学思想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1] 马一浮全集: 第五册[M]. 吴光主编, 王冀奇执行主编.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12] 丁敬涵. 蠲戏斋佚诗续辑//马一浮全集:第三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13] 陈星. 隐士儒宗[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6.
D
A
1008-4479(2022)05-0046-09
2022-06-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群经统类’的文献整理与宋明儒学研究”(13&ZD061)之子课题“马一浮与宋明儒学”
朱晓鹏(1963-),男,浙江丽水人,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道家哲学、阳明学和生态伦理学。
责任编辑 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