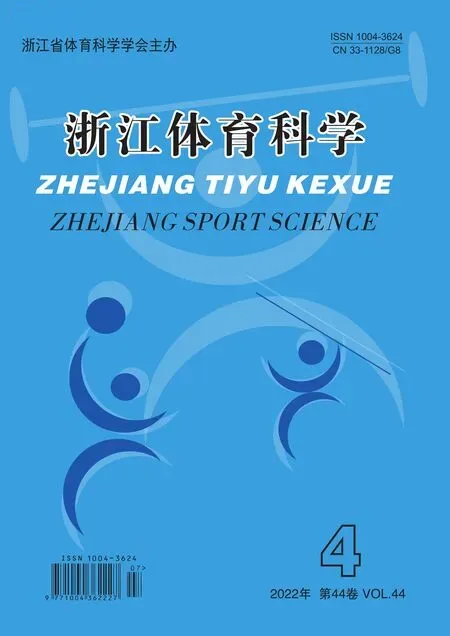“功夫足球”电影的文化精神释义
2023-01-07周震宇花家涛
袁 胜,周震宇,花家涛
(1.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2.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2)
体育电影是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中国体育强国梦、展示体育文化精神、宣传体育文化价值观”的大众传媒文化,促使人们在深入了解和欣赏体育文化魅力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而功夫电影在以武术技击为内容的功夫呈现范式中,促进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塑造”[2]。西方足球电影表征足球运动对个人与国家的“家国情怀”,为足球运动文化的全球传播做出重要贡献,尤其是《胜利大逃亡》《足球流氓》《我爱贝克汉姆》《一球成名》等,在我国更是耳熟能详。而将功夫与足球进行视域融合而联结成“功夫足球”电影——较有影响的《波牛》《京都球侠》和《少林足球》,则在文化隐喻、符号象征、神话意识等层面有了更为复杂而深刻的文化精神表征。本研究运用罗兰·巴特符号文本观——“从研究作品转向研究文本,即从视文学作品为具有确定意义的封闭实体……转向视它们为不可还原的复合物和一个永远不能被最终固定到单一的中心、本质或意义上去的无限的能指游戏。”[3]——对这三部功夫足球电影进行文本分析,揭示其隐含的体育文化精神及其社会意义。
1 文化隐喻:地方性功夫与世界性足球的文化视觉融合
隐喻是解读图像符号意义的重要手段,指在两个本质上并无直接和必然联系的不同事物之间形成指代关系[4]。在功夫足球电影中,功夫的民族文化形式与足球的世界性文化含义,通过文化隐喻而在“身体技术文化关联”、“文化资本再生产”、“文化精神日常生活回归”等方面形成特定的含义。
1.1 功夫与足球身体技术文化的视觉关联
中国功夫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身体文化,是一种社会存在方式[5];而源于英国的现代足球运动,作为一种外来西方文化逐渐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6]。在功夫足球电影中,两者的视觉融合首先体现在各自身体技术方面的巧妙迁移。
1983年公映的香港功夫足球电影《波牛》,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将功夫与足球结合的作品。由元彪饰演的主人公李堂(以原亚洲球王李惠堂为原型)展现了深厚的足下功夫:在乡下生活中用脚捡鸭蛋、用脚打水赶鸭群以及用脚舂米的一系列镜头中,不仅表现出功夫与农家日常生活的关联,同时也表达出功夫注重下盘稳固与灵巧并重的技术特征;在庙会“夺珠比赛”中,双手被束缚仅用双脚攀登独木桥继而用脚“摘取”寓意祥瑞的“珠宝”,体现了脚下动作的干净利落与细微动作精准的实践特征。作为文化隐喻的本体,功夫展示人体下肢技术以实践运用为目的的灵巧性,以此指向作为喻体的足球技术特点,即隐喻足球是用下肢进行的身体运动,需要扎实的下肢力量和技巧,并且以实际运用为目标指向。因此,下肢身体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将功夫与足球联系起来,形成地方性文化与世界性文化的第一层次、也是基础性的关联。
1.2 社会阶层流动的文化资本再生产
中国社会,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途径有传统时期的科举制度,现代的学校教育[7]。现代中国的阶层分化朝着多样化和深层化发展,但由区域、性别、年龄、种族、文化等因素带来的区隔是影响阶层流动的障碍[8]。由体育训练而形成的身体技术是文化资本积累乃至阶层再生产的一种形式,在现代中国成为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一种新渠道。
在电影《波牛》中,李堂因在庙会“夺珠比赛”中误伤乡绅之子而无法继续留在乡下,在其叔叔的推荐下到香港讨生活,并与生存于香港“贫民窟”中、没有正经工作、酷爱踢足球的小孙(张国强饰,以原亚洲著名球星孙锦顺为原型)结识,两人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具有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等资本构成了在社会空间中的外在生存条件,即固化下来的阶层特质和社会属性,成为影响他们社会流动的壁垒[9]。虽然相似的生存状况和条件使他俩具有相似的习性,构成一个阶层,从而处在相似的社会空间之中。但小孙生活在城市,因其社会轨迹的特殊性造成个体习性的差异。故而小孙有着强烈的靠踢足球比赛来获得工作机会以及其他生存资源的诉求。在小孙的支持下,李堂阴差阳错地被足球俱乐部招募为新队员,而李堂因其自身的功夫底子,成功地将功夫与足球技法结合起来,在一次俱乐部联赛中,因偶然的机会上场比赛,获得了观众与代表上流社会的俱乐部老板的认可,从而成为该俱乐部正式职员。在小孙的帮助下,两人经由刻苦训练,将功夫身体技术成功转化为足球身体技术,终成足球明星,从社会底层实现对人生命运的反转。电影为我们展示了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可以通过个体文化资本积累,即以身体为载体的潜在行为系统的习性养成,最终实现阶层壁垒的突破。
1.3 生活世界的文化精神回归
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精神,是由历史沉淀而成的一种共同信念,关乎人们的信念、态度和行动以及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背后是集体身份的深刻认同[10]。当前,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精神需要走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文化精神的养成本是生活的、实践的,文化精神的指引作用也要回归生活实践[11]。以足球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神注重实践态度,以功夫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注重审美态度,中、西文化精神的融合在生活态度中达到一致,在功夫足球中文化精神回归生活世界的隐喻中寻求实践美学的态度[12]。
《波牛》在讲述身体技术的文化资本再生产之后,便将镜头聚焦于功夫足球的文化精神领域:文化精神坚守与文化精神失范的对抗。电影讲述了一位在崇高、理想、严肃、神圣等文化精神方面全面失守的俱乐部老板,欲以高额资金贿赂李堂和孙锦顺踢假球,遭到他们的断然拒绝,便与“球王金”勾结成功。反映了足球运动中出现运动员成名后价值观丢失、精神世界沦丧等现象,深刻讽刺了踢假球行为。电影展示了乡下叔叔来到李堂家中,获悉李堂通过踢足球取得人生进阶之后非常愤怒,回忆起自己当年也是叱咤风云的球场明星,因不同意踢假球而得罪资本家终被暗算,其断腿之痛不想再次出现在侄子身上,便劝阻李堂与“球王金”的“生死决战”。但在小孙“你难道忘记球王金是怎么折磨你的了吗?你难道忘记球王金是怎么打假球的了吗?你难道忘了我们说过要铲出这些球坛败类了吗”的一席话点醒了李堂与叔叔:“明天的比赛就算踢断了腿也要参加”。踢假球、赌球、球场外暴力,这些都是足球运动中不良现象,电影中强烈讽刺这些行为。最终在大雨中赤脚踢球赢得了球赛,战胜了体育精神失范者。与电影开始时的赤脚镜头相呼应,从生活到社会再回到生活中,完成了功夫足球的文化精神诠释。
《波牛》将中国功夫与足球运动相融合,在审美与实践中形成实践美学新文化精神,不仅对武术和足球作为体育运动项目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更加能够展现出功夫足球电影的文化价值以及体育运动的价值。从回归到生活层面的意义上也开创了本土性或地方性文化与世界性文化价值的糅合,将来源于生活中的体育文化精神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最终回归到朴实的生活中,完成生活-实践-生活的文化价值意义回归[13]。
2 符号象征:功夫与足球的民族主义展示
“以物征事”的功夫足球电影还通过象征手法,借助于地方性的功夫文化与世界性足球的具体形象的关联,表达了“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强烈的参与世界并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渴望”[14]。功夫足球电影《京都球侠》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自我认同”的民族主义想象中表达了国人借助足球运动与世界平等交往的真挚感情和深刻寓意。
2.1 在参与足球竞赛中建构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与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文化符号、集体记忆、地域空间以及精英推动等因素息息相关[15]。公映于1987年的《京都球侠》,是一部集武打、球艺与滑稽为一体的功夫足球电影,演绎了一群民间“球侠”自发组队与欧洲足球俱乐部联赛冠军“海盗队”的国际比赛,并以鲜血和生命来维护中国人尊严的传奇故事[16]。
电影以一段国际足联主席若·阿维兰热不容置疑的旁白——“足球,当今世界第一运动,足球的胜利能使一个国家举国欢腾,可以使一个弱小民族燃起希望,赢得尊严;足球的失利常使一个国家遭受创伤般的痛苦”;“足球起源于中国,它在中国有着千年的历史……”拉开了1904年一场有关足球赛事民族主义叙事的帷幕。影片起始的第一场球赛是以天坛为比赛地点,在欧洲“海盗队”与西方“驻华使馆联队”的赛事中海盗队获胜。同时出场的还有不知足球为何物的清庭官员,他们与“撒泡尿也会围上个几百人看个大半天”的街头百姓在得知足球源于中国,发出“闹了半天祖宗原来在咱这儿”的酸楚感叹。
“海盗队”队长、海军陆战队员、中锋哈里得意忘形,猖狂地用将球踢向围观群众,用足球侮辱中国人,恣意挑衅中国人。江湖义士周天(张丰毅饰)将足球反踢回去,并击中目标,洋人震惊。公使道格拉斯以外交使节的身份向清政府提出和中国举行足球对抗赛的挑战,围绕中西足球大赛的叙事主题从此贯穿整个电影。受到足球踢击的“翁老鳖”一直嚷嚷,“一定报这一球之仇 ”。有着英国留学经历的原翰林院编修周天不甘屈辱,斗胆签下赛约,并冒着被清廷捉拿问斩的生命危险遍访京城,邀约一批身怀绝技的民间侠士组成“青龙队”,为民族尊严与“海盗队”哈里对抗。精英代表人物周天大义凛然道:“临阵叛逃岂不让洋人戳咱们脊梁骨?”街头混混公孙弟(姜昆饰)也明确表态:“跟洋鬼子踢,我非上不可”。
电影在“海盗队与青龙队之间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争斗”、“皇家紫禁城队与民间青龙队之间民族国家代表权的争斗”、“紫禁城队对抗海盗队只输不赢的太后命令与部分具有民族大义官员力争胜利的争斗”等三重矛盾之中,把所有的民族主义情绪压抑到不得不爆发的情况之下,最终以“青龙队”克服重重阻碍获取比赛胜利结局,接受“海盗队”鞠躬,赢得尊重,象征近代中华民族在对抗西方侵略者的战争中排除艰难险阻最终取得胜利。功夫足球在这一层面表现出国人顽强不屈对通过足球“实现国家尊严并对民族国家的高度忠诚”[17]的民族认同感。
2.2 在对外交流中展现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群体的一种身份构建和归属,反映族群的一种共同体意识,是一个民族国家富有凝聚力的保障。文化认同的本质在于对文化精神的体认与接续,深刻反映在文化主体日常生活的文化事项之中,并在文化交流中得到加强。近代国门被打开之后,足球所代表的世界性文化与功夫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交流与碰撞,以自身民族文化为其思潮和情感的逻辑起点[18],形成以功夫文化为底色的中国足球文化,在功夫足球电影《京都球侠》文本中,以绝活+足球的形式表征民族文化认同。
首先,在文化争斗中强化文化精神认同。以“紫禁城足球队”总管德太监为首的昏庸腐败者,在以足球为媒介与西方文化交流中极度缺乏自信,当惊闻道格拉斯言说,“说不定这玩意哪一天就在中国开花了呢”的时候,立马表态:“倘有这一天,便启奏太后,像禁鸦片一样禁止,中国五千年传统岂容破坏?”并在应对西方足球挑战时,有官员声称,“冒犯大清国官员之头,就是冒犯大清国神圣不可冒犯之尊严,就是冒犯大清国”,“大清国人才遍地都是,西洋鬼子到头来还是孙子辈”,自大、狂傲、无知又渴望胜利的心态毕露无疑。在中西方官员的对话中显示出鲜明的文化立场:西方渴望文化交流传播,而清王朝仍旧以保守禁锢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为避免产生外交事端,足球赛惊动慈禧太后颁布诏令,“紫禁城”队参赛只准输不能赢。电影《京都球侠》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义和团运动失败,中国领土和主权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狂潮之时,民众对于西方人既害怕又憎恨,这时周天作为英雄出现,接受挑战并为战胜“海盗队”而寻遍京城拥有“绝活者”,表征了中国人不惧怕争斗而且勇于争斗的文化民族品格与人文精神。
其次,在面对中西足球大赛方面,官、民截然不同的态度,体现了在认同差异中强化文化传统的价值回归。“青龙队”是由街头功夫表演者刘二、刘三,小偷赵狐狸(陈佩斯饰),义和团成员郝豹子以及囚犯铁爪篱等“三教九流”的底层人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其中公孙弟三次请求出战球赛:“让洋人看看真正的中国人”,渴望与洋人对抗,打破洋人“能够战胜我们的中国人要下个世纪才能生出来”的观念,展现中国男人气概。而“紫禁城队”则是由慈禧御林军组成,整齐划一听从指挥,在足球比赛中丢尽颜面,与人民自发组织参与对外的抗争形成鲜明对比。“玩命”加“绝活”象征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文化精神,而功夫打斗在电影中象征着足球对抗性的身体文化。功夫足球在这一方面展现出对于国家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
2.3 在抗争压迫中完成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是在与他者对话和交往中确立的,一方面要在交往中回答“我是谁”的根本性问题,另一方面在他者的注视中完成自我展示,还要在追求他者的平等承认中实现自我认同[19]。“球侠”们藐视朝廷而获得“犯上作乱”之罪名,在冒着被清庭鹰犬追杀与缉拿的风险中,坚持与西方足球对抗,最终在足球比赛中获胜与在官民交往中获罪的矛盾冲突中实现精神意志的升华和自我价值的确证。
在周天与詹妮(角色为法国汉学家)交流的情境中,道出中国人的精神价值所在:“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不管身上的担子多重,不管多难,最后都要站起来”。从被西方列强羞辱到取得胜利,期间经历无数磨难,功夫足球表现为对抗外来侵略和封建制度压迫的载体,承载人们的希望与期待,在与帝国主义势力作斗争和官府强压的过程中完成自我价值认同,首先表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群众渴望获得和平解放,获得尊严,从“萃华堂”群众奋起与周天一同参与足球比赛到公孙弟搭救众人再到人民无条件为“球侠”们准备食物补给,充分展现人民渴望抗争的胜利和反对政府压迫的愿望。其次,社会底层各个身怀绝技的“球侠”组成球队,刘二、刘三街头卖艺毅然决定与英雄同路,义和团时期的“盖世神功”郝豹子与兄弟从“不想为大清国出力”转变态度决定组队,官员查龙不惜违反朝廷与众人一同参赛等,展现社会各个阶层将生死置之度外也要参加积极反抗的民族意识觉醒。最后在球场上,球侠们各展绝活,彻底打败强悍的“海盗队”,为国家和人民赢得尊重和尊严。但由于朝庭腐败,众球侠的义举被视为犯上作乱而要被判处斩首。周天放弃詹妮的解救与同伴共赴刑场,正是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球侠”们正是在这样的对抗中完成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人,中国汉子”的回答:中国人不畏压迫,敢于接受挑战,敢于在竞争中奋力拼搏,“乌合之众”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获得洋人的尊重,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冲突对抗中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认同和精神的升华。
中国作为曾经的世界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大国,在文化自信驱使下不可能放弃足球这样的跨文化交流实体的存在价值,从大国意志层面上也不希望在足球这样的世界文化中失去话语权[20]。功夫足球作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物,具有“国家至上、民族优化以及社会进化的象征性意味”[21]。足球比赛的胜利可以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22],《京都球侠》这一功夫足球电影在其象征意义上表现出中华民族特殊的民族主义含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保持一致,同时展现中华民族对参与到世界足球舞台与生俱来的渴望。
3 神话意识:功夫足球实践于梦想和现实之间
神话意识,是在人神相通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关于人类自身的想象和认知;并借助人类特有的想象力将自身对象化、身体化和人性化的结果;并生动美丽地体现了主体和对象、身体和精神以及自然和神灵的统一[23]。集足球、动作、功夫、喜剧为一体的功夫足球电影《少林足球》(2001年),导演运用了神话思维,在少林功夫发扬光大与重返赛场踢赢足球的两个主人公人生奋斗的经历中走向了二者的融合,即实现少林足球的美好梦想。
3.1 “咸鱼翻身”的少林功夫足球队
“人类全部生存行为都是从自己的身体出发,并以其作为识别、判断和自身行为的根据”[23]。将身体对象化的认识与实践,正是《少林足球》电影通过大力金刚腿阿星(周星驰饰)和其少林师兄弟铁头功(黄一飞饰) 、鬼影擒拿手(陈国坤饰) 、金钟罩铁布衫(田启文饰) 、轻功水上漂(林子聪饰) 、太极馒头阿梅(赵薇饰)等身怀绝技的城市“小人物”,通过足球竞赛而经验到、体会到和想象到的实现梦想的途径。
街头拾荒者阿星一直怀揣梦想,面对明峰(吴孟达饰)的挑衅,大声宣称:“扫地只不过是我的表面工作,其实我的真正身份是一个研究生,从事如何有效率地发扬少林武功的研究工作”。其他几位师兄弟皆生活困顿,而致使曾经的功夫光环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用武之地”,功力也几乎消失殆尽;并因长期挣扎于养家糊口之中而逐渐遗忘“将少林功夫发扬光大”的师傅嘱托。不甘于现实世界的无奈,阿星与大师兄以少林组合的形式在酒吧唱歌,梦想在其不伦不类的风格中遭遇老板一顿暴打之后而破灭。面对现实,大师兄叮嘱:“我劝你呀,脚踏实地地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阿星道:“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和一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大师兄道:“你连鞋都没有,那不就是咸鱼一条啦”。
瘸着腿、挺着大肚脯的20年前“黄金右腿”明峰,因被其队友强雄(谢贤饰)设计陷害而沦落街头,但一直梦想着带一支自己的球队参加比赛;遇到阿星的大力金刚腿技能之后,灵光乍现,认为其有足球天分,一心要成立“少林功夫足球队”。两个怀有梦想的“落难人”一拍即合,奇思妙想着试图走一条少林功夫与足球合二为一的道路。其他诸位师兄弟终在现实与梦想之间选择了实现梦想:以足球来弘扬少林功夫,使不同身份、不同工作、不同绝学的“江湖人士”因梦想走到一起,开始追逐梦想和“翻身”的征程。
3.2 “无所不能”的功夫足球技术表演
实现梦想的冲动总是拥有无穷的诱惑力,刺激和推动着人们不断产生令人兴奋和激动不已的认知与行为。面对少林功夫与足球技术融合的困难,阿星呐喊道:“我心中的一团会是不会熄的”,为成功地将少林绝学转换为踢球技艺表明了坚持不懈的恒心以及对足球胜利渴望的信心。
“无所不能”的少林功夫足球炫酷技术,在训练中以“地球—头部—足球”的图像与少林十八罗汉拳法取得联系,呈现功夫与足球身体文化的关联。首先,大力金刚腿与踢假球断送前途的“黄金右脚”街头偶遇,“球,并不是这么踢滴。”当阿星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得到有一种能量就要爆发,在“腰马合一”中道出功夫足球的身体性本质。其次,在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展现“轻功”、“铁砂掌”等正宗武术元素,正如阿星所说:“功夫绝对是适合男女老幼的,打打杀杀只是人们对它的误解,功夫更加是一种艺术和一种不屈的精神”。而踢飞易拉罐、帮助工人搬运货物、太极功夫做馒头等生活性功夫展现得淋漓尽致,阿星在与地痞的街头打斗中首次将功夫与足球结合,功夫足球初现,产生“功夫真的可以用来踢球”的美好畅想。最后,开始足球基础训练,进入功夫足球的“入化”:“铁头功”“大力金刚腿”“鬼影擒拿手”“金钟罩铁布衫”“轻功水上飘”“旋风地堂腿”等少林功夫绝技与足球技术产生身体上的共鸣从而追求功夫足球的“出神”。
六名少林球员在教练明锋的组织和指导下,进行了足球基本技术的训练,成功习得足球竞赛技能。在一场街头友谊赛中,面对“霸王队”轮番上演的各种暴力行为,教练道出:“真正的比赛就是打仗”,实则是对这支球队的考验,“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了,那就不要再踢球了”。师兄弟在丧失原有功夫的情况下,因不堪暴力而投降,这个全新的组合就要在“我要回家”的呐喊中而覆灭,由于不甘受辱而奋起反抗的阿星喊道:“我佛慈悲亦惩恶”,在佛学理念的感召下,少林师兄弟的身体机能被唤醒。师兄弟几人使出各自看家本领,带给观众的是一场精彩的功夫足球技术表演,将各自的绝技与足球技术无缝衔接,最终少林绝学力克对手,夺得“友谊赛”胜利,并成功收编“霸王队”,彻底完成球队组建,壮大了“少林功夫足球队”。“欢迎各位师兄弟归位”,功夫“上身”表现出“无所不能”的踢球绝技,是自我精神的觉醒,是功夫与足球在文化精神上的完美融合,用他们自身的“绝学”,为人生创造出精彩和辉煌。
3.3 “降神附体”的功夫足球集体无意识
“降神附体”是对“无所不能”的神话解释,学理上是指一种可转化的宗教体验,“当神(或灵)下凡并附入一个人体内后,这个人便上法了”[24],在《少林足球》中是以努力寻找被现实击溃而丢失的奋发精神来呈现的。即阿星所说的内心“一团火”,熊熊燃烧的希望和梦想之火,在总决赛中与魔鬼队的终极对抗中凤凰涅槃,最终实现精神世界回归以及自我精神价值的伟大超越。
外围赛第一场比赛,少林队40:0大获全胜,令魔鬼队老板强雄大吃一惊。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少林队如鱼得水,一路凯旋,顺利闯入决赛。魔鬼队与少林队,注定是一场尖峰对决,也是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能的对抗:一群注射了药物的“超人”与几个具有内力的血肉高人的比拼注定波澜起伏,惊心动魄。当“魔鬼队”的守门员一只手拦下阿星威力迅猛的射门时,对“少林足球”的美好期待变为了残酷的现实,接下来对方守门员一次次把球扔给阿星,但却始终无法破门得分,球场上的气氛变得愈加紧张。在多次进攻无果之后,“少林队”的进攻暂告一段落,转而“魔鬼队”开始发动凶猛的攻势。在防守时,守门员小龙在对手狂轰滥炸的射门中遍体鳞伤,终于在魔鬼队的轮番进攻下倒下而被担架抬下,“站着是一座峰,躺下是一座山”,用自己的身躯捍卫着球门,捍卫着“少林队”的尊严。中场休息时“少林队”产生分歧与争吵,有队员无法忍受比赛带来的巨大痛苦选择退出下半场的比赛,那群配角队员退了场,把艰难的下半场比赛和成就辉煌的机会留给了“少林正宗”。此刻这些“少林功夫”的传人不会、也不可能选择放弃,他们甚至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
下半场比赛,“小人物”们内心大无畏的集体主义精神被激发出来,6名队员在球门前“叠罗汉”的造型颇具几分无厘头效果。遗憾的是,还是敌不过魔鬼队的攻势,一个个相继倒下。三师兄(金钟罩铁布衫)挺身而出担任门将出场,用血肉之躯对抗“魔鬼队”的残忍进攻,用自己的少林绝技一次次挡住凶猛的射门,寻找机会制造出一次绝佳的进攻,将几大少林功夫绝学再一次与足球技巧完美结合,最后由阿星完成了极具威胁的射门,却被“魔鬼队”门将机智地化解,球被门柱弹回,三师兄用尽最后的力量挡住了射门,结果身受重伤被担架抬下。接下来的比赛时间所剩无几,少林队仅有七人应战,并且没有门将,就在这无比悲壮的千钧一发之际,馒头店小伙计“太极”阿梅出场,担任守门员,“借力化力、以力打力”,球门前出现了一张“太极两仪图”,阿梅使用太极拳“以柔克刚”的技巧成功化解了魔鬼队凶猛的射门,众人惊愕,阿梅与阿星渴望胜利的笃定眼神,他们已然“将神附体”——完成功夫与足球最后的融合,随着星爷一记惊天动地将对方球门摧毁的大力射门,让邪恶饱尝了恶果,战胜了强大的“魔鬼队”。“少林足球”赢了,少林功夫在于邪恶的战斗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电影最后生活镜头中踩到香蕉皮摔倒的漂亮姑娘学会了“轻功水上漂”,泊车的女白领学会了“铁砂掌”,修剪树枝打工仔学会了“独孤九剑”,而那个电影开场时邋遢的拾荒青年转身变成了少林功夫的推广人……影片最后随着一群等公车的人群跳上疾驰的汽车而去结束。电影《少林足球》将功夫与生活的意义贯穿整部影片,完成了小人物们“将神附体”式的梦想与精神的实现与回归。
在与现代科技的比赛对抗中,队员们勇于牺牲,团结一致,在重重阻碍面前坚决不低头的决心,正是功夫足球“降神附体”式的精神价值,球员们完成了生命的自我完善及精神上的自我超越。
4 结束语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部功夫足球电影,《波牛》《京都球侠》和《少林足球》,就其文本描述的长时段历史已有100多年,在功夫足球的文化体验上表现出一种深邃的历史纵深感:首先,在功夫与足球的身体技术层面,视觉符号融合中表现出两者下盘功力的技能迁移,从而在文化隐喻上表征出地方性功夫通过世界性足球运动在日常生活、社会进阶与阶层流动上实现了足球的社会价值。其次,在功夫与足球的文化交流层面,电影文本通过中西方分别以功夫与足球为各自民族文化符号的象征载体,从而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自我认同中提升了足球的文化价值。第三,在功夫与足球的价值实现层面,运动竞赛形式体现在足球借鉴功夫的实践美学理念,将运动竞赛结果视为“降神附体”的超人表演,从而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升华了足球的人性价值。总之,功夫足球电影隐喻了从中国传统“功夫”的思想中寻求解决国人对足球参与到世界舞台焦虑的办法,也展现了中国积极参与走进到世界舞台中心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