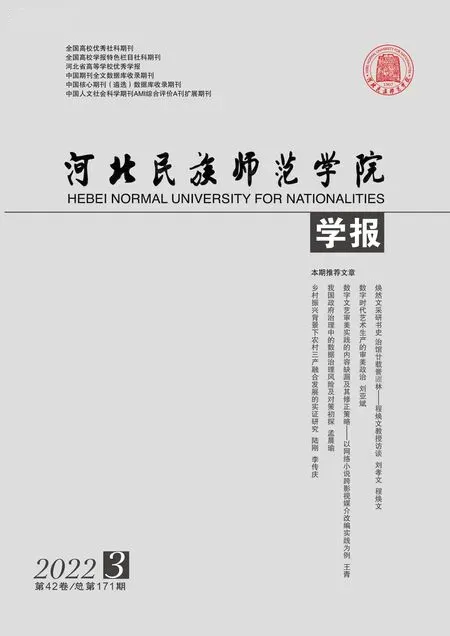辽朝官赙考论
2023-01-06李月新
李月新
(赤峰学院 党委宣传部,内蒙古 赤峰 024000)
赗赙是中原传统丧葬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荀子》中称“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服曰禭,玩好曰赠,玉贝曰唅。”汉何休释:“赙,犹覆也,赗,犹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礼。”[1]由此可知,赗赙即是生者向死者或死者家属馈赠钱帛物品以示哀悼和吊唁,因其有财物馈赠,同时也有“助葬”之义。而所谓的赗赙制度,即指赗赙赠赐的原则、赗赙的具体内容以及赠赐赗赙的具体仪式环节等。契丹人始兴朔漠,过着挽强射生,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其社会中有尚勇武之风,对待丧事则有“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2]的习俗。因此在传统的契丹社会之中,并没有这种以“助生送死”为目的的赗赙习俗。辽初阿保机引进中原礼制,赗赙礼也在此时随之进入契丹社会,并成为辽朝丧葬礼仪的组成部分。①学术界关于辽代丧葬制度的研究主要围绕墓葬发掘展开,如贾洲杰:《契丹丧葬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第56~61页;李逸友:《辽代契丹人墓葬制度概说》,《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1990年,第80~102页;彭善国:《辽代契丹贵族丧葬习俗的考古学观察》,《边疆考古研究》2003年第2辑,第298~308页;张国庆:《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民俗研究》2009年第1期,第95~109页等,仅张国庆:《辽代丧葬礼俗补遗——皇帝为臣下遣使治丧》(《辽宁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90~95页)、王凯:《华风与夷俗:辽朝皇帝丧葬仪相关问题刍议》(《宋史研究论丛》第17辑,2015年,第546~560页)等论文中,在讨论辽代丧葬礼仪时提及赙赠行为,但目前尚未有对辽朝赗赙礼的专门研究。本文以辽朝时期的“官赙”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对辽朝官方赗赙概况的考察,整理国家官赙的主要内容,分析其制度特色。
一、辽朝官赙概况
神册三年(918年)“秋七月乙酉,于越曷鲁薨,上震悼久之,辍朝三日,赠赙有加。”[3]13这是《辽史》中首次出现的官方“赠赙”记载。耶律曷鲁是阿保机腹心部的重要成员之一,拜为阿鲁敦于越,所谓“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拟,以曷鲁为心云”。[3]1348即说明曷鲁在辽初契丹统治集团中拥有较高的地位。案《辽史》记载,辽朝曾于太祖七年(913年)参考中原礼制始定吉凶二仪。此时曷鲁去世之后的哀悼、辍朝、赠赙等行为,都源自中原礼制范畴,当是遵照执行了新订辽朝凶礼仪程的结果。由此可知,早在辽朝建立之初,官赙就已经作为王朝制度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发挥其在维护宗室,抚慰官员等方面的政治功能。
会同二年(939年)赵思温薨,辽太宗“赙祭”,且赠太师、魏国公。赵思温本卢龙人,神册二年(917年)降辽。入辽后历经两朝,参与了灭渤海,援立石晋等重大事件,并获赐“协谋静乱翊圣功臣”号。作为辽朝时期归降汉官的代表人物之一,赵思温是契丹统治者笼络、安抚的重点人物。因此,死后国家给予其赗赙、赠官之殊荣。太宗时期除明文赙赠外,对重臣还有“礼葬”之实。刻于会同五年(942年)的《耶律羽之墓志》中有“有司备仪,送终之礼既伸,易号之彝无废,谥曰文惠公,礼也”的记载。这表明太宗时期延续了太祖七年制定的凶仪仪轨,并且治丧之仪中还包括了赠谥的内容。另外,对于敌对政权的忠贞义士,契丹国家也有出于表彰的葬礼仪轨,如张敬达,虽不降辽,但太宗因嘉其忠,仍“命以礼葬”。[3]41
世宗天禄二年(948年)辽初归附契丹的汉官耿崇美去世,其墓志中记有:“加赙赠以非轻痛股肱而遄逝,敕其元子蒇以葬仪,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4]14据史文记载可知,耿崇美于阿保机时期举家入辽,凭借其胡人身世背景及较好的汉学基础,在短时间内得到契丹统治者极大的认同感和信任,并因功得赐“推忠佐命平乱功臣”。死后加赙赠且赠官既是契丹统治者对耿崇美去世的哀悼,同时也是对耿氏一族的恩赏与笼络。辽朝官方对耿崇美的赙赠,也说明即便是在内政不稳的世宗统治时期,太祖时期的吉凶礼制仍然被遵照执行。
其后辽朝诸帝统治时期,尤其是圣宗朝以后,官赙记载增多。综合来看,皇族、后族、附属政权统治者及以汉官为多数的官僚群体,包括他们的配偶都被纳入了辽代官赙的范畴。
此外,还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官赙行为,如国家福利性质的赙赠。统和三年(985年)八月,故南院大王谐领已里婉妻萧氏奏夫死不能葬,诏有司助之。[3]123-124此即为因家贫无力治丧,由国家出资营葬。对于死在契丹境内的北宋使臣,辽朝政府也行赙赠之礼。如重熙三年(1034年)正月丁卯,宋使章频卒,诏有司赙赠,命近侍护丧以归。[3]243《宋史·章频传》称:“契丹遣内侍就馆奠祭,命接伴副使吴克荷护其丧,以锦车驾橐驼载至中京,敛以银饰棺,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卫送至白沟。”[5]又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正月,宋贺正使王严卒,以礼送还。[3]301可见,道宗时期对在出使途中去世的宋朝使臣是按照先例办理丧事的。即说明辽朝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礼仪制度,用以对待死于出使途中的宋使。这套礼仪制度中,包含了遣使治丧、赙赠(葬具、鼓吹羽葆等)及指派甲兵护丧归国等内容。
从目前已知辽代各类资料的记载中,可以发现有赠赙、赙祭、赙赠、赗赠、赙赗、赙恤、赗赙、赗禭、赙赗含禭、晗禭赙赠等诸多名目。这一方面说明辽朝时期对赗赙礼的称呼并不统一,同时,也证实了官赙作为政府对死亡勋戚官僚等的主要抚慰制度,成为辽朝丧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辽代官赙的具体内容
《辽史》中并没有保存辽朝时期赗赙礼的相关记载,但是从一些具体官赙事例中,依然能够获得有效信息,了解其制度运行的概况。
从目前已掌握的材料来看,唐朝时期主要的官赙物资(粟米、布帛)也是辽朝时期赗赙的主要内容之一。如圣宗统和七年(989年)六月,宣政殿学士马得臣卒,除诏赠太子少保外,还获得钱十万,粟百石的赏赐。[3]145耿延毅死后获赐的赙赗为“白金二十斤,布帛三百段,钱二十万,衣三袭”。[6]160
从圣宗赗赐耿延毅的情况可以发现,除布帛外,衣服也是国家恩赏的物品之一。如道宗大康元年(1075年)萧德温去世,“□与皇太后闻问,为之零涕伤悼者累日。出宫中衣一袭以敛之,厚其赗赠。”[6]372萧德温为萧孝穆之孙,宗天皇太后之侄,身为禁内之华姻,身份非常显赫。因而以宫中衣为殓是对其贵戚身份的彰显,带有明显的荣宠之意。此外,据《辽史·耶律韩八传》载,韩八“死之日,箧无旧蓄,椸无新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兴宗遣使吊祭,给葬具助葬,赐衣为殓,也合乎情理。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以衣衾为主禭一直是官赙的内容之一。但是,唐朝时期官赙实物中以布帛为主,淡化了衣衾部分的内容。辽朝时期的官赙中保存了衣衾的赠赐,①在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之中不仅有木制小帐、雕绘石棺等高级贵族葬具,而且墓主人身着十余件衣裳,头戴高翅帽,覆有面纱,着手套和靴,身上还盖有缂丝尸衾。因无出土墓志,因而无法断定是否为官赙。但从墓葬形制及墓主人身份推测,并不排除官赙的可能。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第26~30页。说明契丹国家的赗赙礼并未完全照搬唐制,亦有溯及中原古礼的可能。
辽代赗赙内容有别于唐制,还在于辽代官赙中钱币的出现频率较高。如马得臣得赐钱十万;耿延毅获赠钱二十万等。另外,圣宗去世时,西夏也曾遣使者进赙币,这也说明辽朝时期钱币是赗赙中的常见内容。而在《韩橁墓志》中提及,对于韩橁的去世,兴宗除正常的赙赗外还额外赐钱五十万。[6]206虽然墓志中点明此非常例,但由此亦可知,辽朝时期直接以钱币作为赙赐内容,应当是较为普遍的。只是五十万的数额巨大,并非官方标准。
葬具也是官赙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巴林左旗博物馆,清理了辽代韩匡嗣及其妻子的合葬墓。据发掘报告可知,韩匡嗣墓葬规格较高,由墓道、天井、墓门、甬道、前室、左右耳室、后室前甬道、主室及排水系统组成。室内做仿木结构,且饰有彩绘壁画。遗憾的是,此墓遭数次盗掘扰动,主室内仅残存的木制小帐及浮雕石棺,无法复原其完整葬制。[7]虽然如此,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信息。据相关研究可知,木制小帐是辽代贵族墓葬之中极具特色的葬具之一,使用者都是皇亲国戚和契丹大贵族。[8]韩匡嗣为辽初汉官韩知古的第三子,史言其“以勋旧之胤,有干济之才”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用,历经三朝,官至宰相,号“推诚奉上宣力匡运协赞功臣”,封秦王。所谓“忠孝卫社,富贵逼身”,是辽初政治地位较高的汉官之一。《辽史》本传称其去世后,“睿智皇后闻之,遣使临吊,赙赠甚厚”。而《圣宗纪》中则记为“赐葬物”。由此可知,韩匡嗣墓葬中发现的木制小帐,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官赙物品之一。
自汉代开始即作为皇帝赐予臣下的高规格的葬具——东园秘器,也在辽代官赙之中出现。如《萧莹墓志》记有“……使敕祭具,礼营葬事,给班剱、箫□、鼓吹,赐东园秘器,凡赗赙加等,赠龙虎卫……”案东园,属少府,掌为棺器;[9]442“秘器,棺也”②《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李贤注,第1523页。此处对“秘器”的注释,基本上能够代表唐时的官方观点。。且《汉书·礼仪志》引《旧汉仪》载“上林给栗木,长安祠庙作神主,东园秘器作梓棺,素木长丈三尺,崇广四尺。”[9]3148可知东园秘器应该是一种高级别的棺椁。据相关研究可知,唐代东园秘器作为一种高规格葬具,理论上归由将作监督造,其材质经历了一个由木质到石质的变化过程。[10]辽代设官多循唐及五代制度,亦于太府监下设有将作监,其职司应大略相仿,很有可能承担督造辽代官赙之中的东园秘器、秘器之类棺椁明器的职责。同时,于辽墓之中发现的贵族特色葬具——木制小帐,很有可能就是辽代名之为东园秘器的葬具。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新资料的发现。
此外,在辽朝的官赙中出现了“牲”的内容。如应历九年(959年)《驸马娑姑墓志盖刻记》:“衣服二十七封,银器十一事,鞍十一面,白马一匹,驄马一匹,骠尾黑大马十一匹,小马二十一匹,牛三十五头,羊三百五十口。”陈述先生在其后按语称其应系皇室所赐赙赠物品,或殉葬物品单。[11]娑姑志盖中所记除各种良马之外,仅羊即有三百五十口的规模。而圣宗时韩橁奉使沙州,请求增援时即求“食羊三百口,援兵百人”。[6]206可见三百只羊,应该是一笔数目不小的财富。按此志盖上所记物品,十分丰厚,虽属于巨额财富,但是较之其他契丹贵族墓葬的随葬品来说,品种过于单一。并且在考古发掘之中,于主室内发现柏木护墙一周,构造如小室,柏木棺床及帷幔,符合辽代贵族墓葬规格。虽早期被盗,但仍见有马具、衣帛、饰品、瓷器等随葬品,[12]但未见有马、牛、羊等殉葬的痕迹。由此可知,墓志盖上所列的应当是国家赙赐之物的清单。而国家赗赙除助葬外,还带有赙恤丧者及丧者亲属之义,并不一定要求全额陪葬,因此,随葬品中没有发现大量的殉牲也在情理之中。
辽代官赙中除了财物、葬具之外,还有赠官、赠谥等内容。从一些具体官赙事例中,可以发现辽朝时期国家赙赠官职基本上有着皇族勋贵赠爵,汉人官僚赠官的规律。但也存在宗室赠官的情况,如耶律庆嗣薨,“诏下丞相府曰,若公之勤可记,乃赠中书令”。[6]457在国家赙赠的官职中,汉官群体获赠“尚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官的频率较高。另《耶律庆嗣墓志》中称:“将葬请谥,礼官曰,公之行可迹,按谥法云:图国忘死曰贞,佐国遭忧曰愍,遂以贞愍而赗之。”《耶律宗政墓志》中有“太常议行,谥曰忠懿”之语。可知,辽朝时期礼部亦履行按死者行状拟谥的职责,且有较为完善的谥法。[13]
此外,兴宗时期开始,在官方赗赙中出现羽葆、辂车、班剱、箫笳、卤簿鼓吹等内容。《耶律宗允墓志》记“备卤簿鼓吹”;《萧福延墓志》记“备卤簿鼓吹,旌旐□□”;《耶律弘世妻秦越国妃墓志》载“其牲币、涂蒭,洎卤簿、笳箫之数有差”;《萧莹墓志》载“班剱、箫□、鼓吹”等。案“舆驾行幸,羽仪导从谓之卤簿,自秦汉以来始有其名。”[14]汉代以来官赙卤簿送葬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辽史·仪卫志》载太宗南下入汴收后晋卤簿法物,其后世宗即位随之归于上京。[3]1022中原卤簿仪卫之制被正式引入辽朝,世宗时期卤簿法物备而不用,穆宗始有依嗣圣故事用汉礼之诏,自圣宗之后,礼仪制度日臻完备,卤簿仪卫之设遂为常事。《辽杂礼》称“朝会设熊羆十二案,法驾有前后部鼓吹,百官卤簿皆有鼓吹乐。”[3]992由于资料较少,目前无法判断辽朝官赙中卤簿鼓吹是否也存在等级差别,但是官赙卤簿鼓吹送葬属朝廷殊礼当无疑问。辽时能够得到官赙卤簿仪卫者均为地位显赫,声望极高的皇族、后族成员。如耶律宗教,辽史无传,但据《墓志》可知其为景宗之孙,耶律隆庆之子。《墓志》篇首即以“皇兄”称呼,表明其与兴宗之间亲密的血缘关系。耶律宗教一生历经两朝,八次出任要职,不仅掌握辽朝军政大权,而且在契丹宗室中也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威望。因此,耶律宗教死后,兴宗思极哀荣,用崇典礼,诏济州判史孙文世,持节监护襄事,“备羽葆辂车之饰,用旆常箫□之仪,导王之神柩”。[6]750
另,从零散的资料中可以发现,辽朝时期为地位尊崇的官员治丧,有皇上讣闻,有震悼、轸悼甚至哭临之礼。有司具仪,并由发引使、勅祭使、勅葬使等共营丧事。虽有赗赙之礼,但是并未专门设置赗赙使。国家赙赠之事应该也有祭葬使等一并负责。在赗赙的内容上,除了米粟、绢帛之外,辽朝时期还多以钱币、金银、马匹等恩赏臣下,对于功勋卓著者,还有赐丧葬地、赐宫户守冢、卤簿鼓吹送葬等内容。另外赠官、赠谥等也作为特殊荣耀,成为辽朝国家官赙的组成部分之一。
虽然在《辽史》及相关史料中,并未发现有关辽朝时期国家赗赙的赠赐标准规定,但是种种迹象都已经表明,辽朝时期国家赗赙已经形成一定的赠赐标准。如《韩匡嗣墓志》载,韩匡嗣死后,国家“祭赠之恩,有加于常典。”①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4页。另,《辽史》载韩匡嗣死于乾亨四年(982年)十二月辛未,而《韩匡嗣墓志》记韩匡嗣死于乾亨五年十二月八日,两者唯一的共同点即是都记韩匡嗣与景宗死于同一年。又《义和仁寿皇太叔祖妃萧氏墓志》中称皇太叔祖和鲁斡去世时,“凡厥赗赠窀穸之事,皆视常制者逾等。”[4]275墓志之中所记之常典、常制,应该就是辽朝时期国家有关赗赙制度的具体规定。那么辽代官赙中的常制如何规定?圣宗时宣政殿学士马得臣所获赙赠的记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据载,马得臣所获赗赐为钱十万,粟百石。殿学士始设于唐,五代、北宋沿袭,且皆有创制,虽无职守,但出入侍从,备顾问,实为宰相、执政官出任外调所带职名,品位有从二品,正三品之设。[15]辽朝仿自中原官制亦创设有宣政殿、观书殿学士。其职掌、品位也应与之相仿。据《通典》载唐代诸执事官的官赙标准可知,能获赐粟百石则需官居三品。[16]马得臣官职、官赙均与《通典》所载唐制相类,由此可以推知,辽朝时期官员的赗赙制度可能也遵循了“准品给赙”的原则,有部分参考唐制的可能。
结语
赗赙作为中原封建政权政治性、社会性的抚恤礼仪,彰显了国家的制度关怀。而官赙所起到的维护宗室,抚慰官员,稳定政权的作用在辽王朝建立之初,即被契丹统治集团所重。又因赗赙具有抚生助丧的世俗功能,更容易为契丹人所接受。因此,自太祖初年开始,辽朝的官赙行为十分频繁。
从目前已知的辽朝时期官方赙赠情况来看,有证据表明契丹国家已经仿效中原政权制定了相应的赠赐制度。赙赠的范围涵盖了皇族、后族、汉官群体及其配偶,赙赠内容有因袭唐宋制度的一面。但是,以金银钱币、牲畜马具以及木制小帐、帷幔、网络、面具等葬具为主的赙赠内容,又体现了辽朝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契丹民族特色,反映了契丹统治者在官赙制度运行中根据自身特点进行改造的真实情况。另外,辽代既有官方赗赙的常制又有视常制者逾等的现象存在,也说明契丹政权官赙根据赠赐对象身份的差异制定了不同的标准,这种等级鲜明的标准也体现了对皇权及封建国家制度的维护。同时,由于官赙的对象和内容在实际上引领了辽代社会的道德风尚,因此在维持辽代社会秩序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