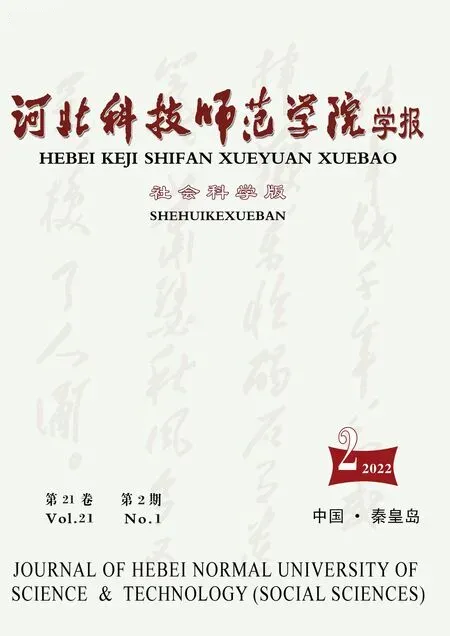谷斯范现代长篇小说文体范式研究*
——以《新水浒》《新桃花扇》为例
2023-01-06董卉川赵艺佳
董卉川,赵艺佳
(青岛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谷斯范,1916年3月4日生,浙江上虞人。谷斯范的文学生涯有两部长篇作品,均撰写于1940年代,分别是1940年5月文化供应社初版的《新水浒》,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章回体形式描写抗战的长篇小说,“利用旧形式的长篇小说,似乎还不多见:谷斯范先生的‘新水浒’第一部‘太湖游击队’,因此是值得我们注意的”[1]1;1948年5月新纪元出版社出版的《新桃花扇》,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对于两部作品的创作,谷斯范均采用了古典章回的文体形式,这文体形式实际是为文体内核(内容)所服务的。谷斯范对黑暗的社会世相——政治的腐败、人性的丑恶充满了愤懑与不满,对民众的疾苦和悲惨的命运充满了同情与怜悯,因此,他的思想情感急需一种文体外型与之相适应。面对孤岛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高压集权的恐怖统治政策,他只能以民族形式——古典章回的文体外型来迂回、曲折地呈现自我的思想主旨。文体外型与文体内核又决定了这两部作品的语言范式必定具有以白话为主、文言为辅的文白杂糅特质。谷斯范的现代长篇小说中渗透着作者个人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以及现代学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但谷斯范的“新”系列长篇小说——《新水浒》《新桃花扇》,在以往的文学史中却罕有提及,不似张恨水、谭正璧等人的历史小说或通俗小说创作,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谷斯范的现代长篇小说撰写并没有得到学界充分的重视,使他成为了文学史上的被遗忘者。
一、古典章回的文体外型
1940年代,是历史剧、历史小说创作的高峰期,这一时期创作历史剧的代表作家为郭沫若,从1941年11月到1943年3月间,共创作了六部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冠草》。阿英的《海国英雄》《洪宣娇》《李闯王》,于伶的《大明英烈传》,也是个中翘楚。写作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则为谭正璧、张恨水,尤以谭正璧为最,谭正璧于1940年代撰写了如恒河沙数的历史小说,“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还有别的一些作家也写作历史小说,但无论作品数量还是在艺术质量上,他们都逊色于谭正璧”[2]295。张恨水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主要有《水浒新传》。受此风潮的影响,谷斯范在1940年代也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新桃花扇》。以及仿历史小说的通俗创作——《新水浒》。
无论是谭正璧、张恨水的写作,还是谷斯范的《新水浒》《新桃花扇》,均采用了古典章回的文体外型,表现出了典型的民族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气派。
谷斯范的《新水浒》《新桃花扇》均为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一大章节均设置回目,章回小说的回目非常重要地起着概括本回内容,提示读者的作用”[3]100。文化供应社1940年5月版的《新水浒》全书共为28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的《新水浒》为谷斯范于1982年9月重新写作的,新版《新水浒》改动较大,全书由28回改为24回。新纪元出版社1948年5月版的《新桃花扇》全书分为“引子”和“正文”。正文共38回。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8月版的《新桃花扇》改动较大,将引子去掉,虽然为38回,但回目名称全改为通俗章节名,这样的改动,是出于普及的需要。
谷斯范的《新水浒》和《新桃花扇》,均是以回目概括本回内容,每回内容(故事)相对独立,前后勾连,首位呼应,由此使全书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文化供应社1940年5月版的《新水浒》和新纪元出版社1948年月版的《新桃花扇》的回目明显更倾向于古典章回小说的回目设置,“遣词造句颇费功夫,所用两个句子不仅要字数相等,富有韵律感,而且前后文字还要像律诗一样讲究对偶”[3]100。1949年之后改写的《新水浒》和《新桃花扇》每一回的回目则打破了对仗工整、讲究韵律的传统习惯,而是以更为通俗随意、简洁明了的形式建构。
章回小说的另一大特质即为“有诗为证”。“章回小说几乎全用诗、词开篇,其诗、词有的是作者自己创作,或采用现成的名人之作。有的是初成书就有,有的是流传时被后人加入的……利用诗、词开篇,或点明全书的题旨,或咏怀作者对人生的感悟。”[4]1以谭正璧194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的代表作《梅花梦》为例,每一章均以一首七言绝句开篇,如第一章的“锦繍江南信可哀/六朝金粉尽成灰/何如我有生花笔/写出神仙眷属来”[4]1,又如第二十六章的“风流俊逸是何郞/容态难忘旧日狂/傅粉只今成往事,落英满地梦犹香”[4]124。
而谷斯范在创作《新水浒》和《新桃花扇》之时,一方面摆脱了“有诗为证”的窠臼,另一方面则继承和发扬了“有诗为证”的古典章回小说的文体特质。在《新水浒》中,每一回均无诗或词开篇,而是直接开宗明义、开门见山地进行叙述。在叙述过程之中,也会穿插一些“诗词”:
第十一回,罗三爷面对国破家亡的现状,吟诵了陆游的《夜间秋声感怀》:“西风一夜号庭树,起揽戎衣泪沾襟,/残角声摧关月坠,断鸿影隔塞云深。/数篇零落从军作,一寸凄凉报国心!/莫倚壮图思富贵,英豪何限死山林。”[5]75第十二回,郑团长想到宋梦云来到军队已经三年,起了韶光易逝的感慨,遂写诗感慨:“可恨光阴如水流,又是残冬风雪夜;/劝君努力须及时,等闲莫白少年头。”[5]86第二十回,黄杰得到华中战局危殆的消息后,心中郁闷,想起了崔灏的诗句:“日暮关乡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5]147第二十五回,罗三爷想起自己家破人亡后,背诵了陆游的“书愤”:“白发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鉴孤忠;/阨穷苏武餐毡久,忧愤张巡嚼云空。/细雨春芜上林苑,颓垣夜月洛阳宫;/壮心未兴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5]184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诗或词,则是以歌曲为主:
第二回中,士兵们在困境中所唱的“铁血歌”:“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可以救中国!/还我河山誓把倭奴灭,醒我国魂誓把奇耻雪!”[5]20第十四回,徐明健在父母坟墓前想念双亲和爱人时,悲哀颓然所唱的“万里寻兄曲”,“从军伍,少小离家乡;/念双亲,清泪空凄凉!/家成灰,亲墓生青草;/我的妹,流落他乡!”[5]100第二十三回,六师爷在王小寡妇家中饮酒作乐时所唱的“桃花宫”:“寡皇酒醉桃花宫,瞠瞠瞠!/韩素梅生来好容貌,瞠瞠瞠!”[5]164第二十五回,苏光庭因抗日游击队发展壮大而欣喜不已时所唱的“王佐断臂”:“听谯楼,打初更,玉兔东上!/为国家,秉忠心,尽夜奔忙。/想当年,在洞庭,逍遥放荡!”[5]184上述穿插于文本之中的诗词或歌曲并不再是必不可少的。
《新桃花扇》与《新水浒》类似,仅在引子之中,以七言绝句开篇:“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6]1每一回均无诗或词开篇。但作为一部典型的历史小说,且出场人物均是学富五车、饱读诗书的文人雅士、高官贵胄以及才气俱佳的秦淮名妓,因此,不同于《新水浒》中少量出现的“诗词”,《新桃花扇》的每回中,会穿插着大量的诗词。譬如第一回中,朝宗面对山河破碎的现状,吟诵起曹操的《短歌行》:“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譬如朝露,/去日苦多!”[6]5苏老头初到蔡益所的中堂,朗吟起钱牧斋写的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6]5每一回有一首甚至多首诗词嵌入文本之中。
章回小说由讲史话本孕育而生,因此讲史话本中的一些表现方式会被章回小说因袭。“如在讲述故事时必用‘且说’‘话说’‘正是’……但小说话本中没有‘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但在章回小说中都是每回结尾必有的。”[3]101-102张恨水《水浒新传》的某些章回中会有“且说”“俗话道”等表述。谭正璧的历史小说《苏武牧羊》《忠王殉国》《木兰从军》《绝代佳人》《梁红玉》,每一节(章/回)的末尾均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节分解”的形式结尾。与张恨水、谭正璧的创作不同,谷斯范的《新水浒》《新桃花扇》完全去除了古典章回小说中某些常见的表述方式,完全不见“且说”“话说”“正是”“且听下回分解”等套语。
谷斯范的《新水浒》《新桃花扇》在文体外型上具有典型的古典章回小说的特质。“这一本书的出版,至少是向文艺界提出一个关于民族形式的实例。”[8]4在发扬民族形式的同时,对章回小说体裁形式的选择,实则是迫于某些时代因素。此外,也是为其文体内核所服务,“形式是内容的形式”[9]90,古典章回的外壳包裹的是现实观照的文体内核。
二、现实观照的文体内核
在文体外型上,谷斯范的《新水浒》《新桃花扇》虽然承继了古典章回小说的某些体裁形式,但在文体内核——思想内容上,却以严肃深刻的笔调,与抗战的时代洪流紧密相连。“这是在上海沦陷后,才在‘译报’连续登载的。原来的名称是‘太湖游击队’,故事的背景也是在山明水秀的江浙,并不是在产生绿林大汗的山东。发表时为了顾到孤岛的环境,才改用‘新水浒’这书名。和战时许多的新事物一样,名称和内容本来不一定要一致。”[8]2也是对黑暗时代的以古喻今、以古讽今,艺术化的再现了历史,使遥远缥缈的历史变成有血有肉、触手可及的现实生活,与社会时代紧密结合。“写这部作品的日子,正是蒋介石集团统治下最黑暗的时代,政治腐败,特务横行,那批祸国殃民的官僚、卖国贼,本质上与三百年前南明社会的腐败统治集团,极有相似之处……写作时为了‘借古讽今’,故意添加了一些东西,明讽暗讥。”[10]322-323
首先,是对丑恶人性的暴露。“历史小说的写作,第一是人性的发掘。”[11]1两部作品中均有一个浓墨重彩的典型反面人物——《新水浒》中的六师爷和《新桃花扇》中的阮大铖。“倒是在反派人物方面,作者赋与了比较复杂的性格;最明显的例子,是那位‘六师爷’。”[1]2他们不仅有着丑恶的人性,还有着病态的国民性。他们的恶和病态极具代表性,是千百年来中国封建思想糟粕的集合与缩影。
不同于双桥镇上的权贵士绅,六师爷(马兆麟)原本出身民众阶层,只因做了镇长的亲信,在镇公所谋得一份差事,便以师爷自称,甚至以双桥镇的二把手自居。他麻木愚昧,对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现状毫不在意,对共属同一阶层的民众也毫无同情怜悯之心。与他同样麻木愚昧的以阿七、阿七嫂为代表的民众,误认为驻扎在镇上的部队召开民众大会是要抽壮丁,便去贿赂在他们看来属于权力阶层的六师爷,试图摆脱被抽壮丁的命运。当郑许国团长宣布不会抽壮丁,并探查何人散布谣言扰乱民心时,收了阿七贿赂的六师爷竟然倒打一耙,出卖指认阿七。张镇长得知日寇要进攻双桥镇的消息后,带着家人细软连夜逃离,六师爷便趁乱作了代镇长。之前面对以郑团长、张镇长以及佩有枪支的士兵为代表的强者时,他甚至甘心叫“爸爸”。而当他获得权力之后,马上摆起比张镇长还要阔气的派头、还要狠辣的手段。“老金已被派定职司,出门时跟来跟去当‘跟班’,在家时给六师爷烧茶煮饭;稍不随意,便要摆出主人架子,请他‘吃生活’,甚至连叫声六师爷都要‘吃生活’。”[5]38-39六师爷变得更加嗜血麻木,渴望攫取更大的权力。在郑团长败走双桥镇后,立即投靠汉奸赵章甫,以谋求更大的职位和权力,乐于做侵略者的走狗,对民众更是肆意压榨欺侮,恶事做尽。在六师爷身上,淋漓尽致地呈现出丑恶的人性,尤其是愚昧无知、麻木冷漠、奴性十足的病态国民性。
阮大铖则是统治阶层中权奸的代表,在天启朝时投靠魏忠贤,拜其作干父,认熹宗乳母客氏作干母,陷害忠良排除异己。在位时,大肆贪污受贿。朱由检继位后,阮大铖被罢免官职,便蛰伏于南京,伺机而动。他在南京建造了奢侈华丽的石巢园,用以宴请拉拢南京的权贵,利用在位时敛下的万贯家财四处贿赂讨好南京的官员。后来终得马士英赏识,做了他的心腹,与马士英一道拥立福王监国,后登基,由此重新进入国家的核心权力层。他记恨曾经的政敌,尤其是与他发生过冲突的“复社”人士,重获权力后利用一切机会对其进行打压迫害。作为一个政客,他对国家人民漠然视之,一心只为谋得权力、巩固势力。正是他的自私狭隘、麻木冷血、残忍偏执、厚颜无耻,导致了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悲剧、更是加速了南明的覆灭。面对清军的进攻,阮大铖竟想利用清军的势力来消灭异己。扬州被围后,他冠冕堂皇地拒绝发兵支援,“扬州局势并没有如大家想象中的严重!史可法天天告急,吵着请发救兵,这是他的调虎离山计!他扮的苦肉计!他知道左良玉已在铜陵惨败,快被全数歼灭,才危言耸听,故意渲染江北局势的严重,哄我们调兵北上,使左逆残余能虎口留生,保全一份实力”[6]295,由此导致了扬州惨案的发生。他的人性丑恶扭曲到了极致。
其次,是对腐败政治的批判,主要呈现在《新桃花扇》之中。“你看那政治的内幕,那对内的压迫、对外的昏庸和屈服,那些政治舞台上的权奸。”[11]3
当北京传来崇祯自缢的消息后,南京的诸官员不是思悼逝者也并非担忧国运,而是私下感到一阵窃喜,源自陪都南京正式成为首都,留守南京的官员们必然会平步青云、仕途顺畅。众人于是开始谋划拥立璐王或福王为新主,以巩固自身势力。“太子是他们朱家的子孙,福王也是他们朱家的子孙,谁会真心来争这些,大家争拥立的功,抢几顶纱帽戴才是真的。”[6]124当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监国、登基后,独揽朝纲。对内实行恐怖高压的集权统治,禁止民众议论国事,派遣锦衣卫抓捕异己。纵容官兵行凶,兵匪时常冒充清兵公然抢劫民众、强抢民女。同时加收苛捐杂税、压榨百姓,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对满清则卑躬屈膝、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历史上向外国借兵平乱故事多着,每次酬谢些金帛女子,就敷衍过去;再不然,名义上委屈些,向他们上表自己称儿子,包你平安无事……北方几省早已是流寇的天下,满清去向流寇‘收复失地’,我们乐得‘坐山观虎斗’,等待他们两败俱伤的有利时机!如满清果然实力坚强,像南北朝那样,还可过几百年太平日子。”[6]175当清军即将攻入南京时,弘光帝犹疑不决,听信马士英、阮大铖谗言,决定主和,割地赔款。当清军包围扬州时,阮大铖献毒计借清军之手消灭左良玉三十万大军,同时暗下命令,示意四镇不可受史可法调遣,以此消灭两大政敌。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代表的南明统治阶层,大肆卖官鬻爵、贪污受贿,面对国破家亡的危局,依然终日夜夜笙歌、花天酒地、寻花问柳、纸醉金迷,最终导致南明灭亡。而他们早在城破前,就已经带着搜刮贪污而来的无数财宝逃之夭夭。
再次,是真实描写了世相的悲惨和民众的苦难。“他们的命运,也不该老在惨杀压迫暗无天日的世界过日子。”[11]1在《桃花扇》中,孔尚任是以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在此基础上再渗透进一些对政治、对人性的描写。而在《新桃花扇》中,谷斯范则是以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悲剧为切入,来实现自我对现实的观照。因此作品力图呈现的并非是爱情,而是世相——民众的苦难和民间的疾苦。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政府不顾民众利益,只知一味增加苛捐杂税,致使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增了几次钱粮,又征‘辽饷’‘练饷’,老百姓被搜刮得只好吃树皮草根。”[6]34南京城内涌入了各地的难民,有一家人从湖广逃难而来,在无为州时这家人的媳妇被一军官看中,便谎称他家儿子通匪,绑出去直接砍杀,只剩老人与孙女流落南京,为了果腹只能把孩子卖给库司坊。南京城内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与之相对的是,秦淮河畔却依旧灯红酒绿、夜夜笙歌。马士英、阮大铖拒绝史可法的发兵请求,致使扬州失守。统治阶层为了一己私利和政治斗争,枉顾百姓的生命,扬州沦陷后,清帅多铎下令屠戮城中八十多万军民。多铎攻陷扬州后,继续进攻南京,统治阶层竟抛弃民众独自逃难。《新桃花扇》中种种黑暗、混乱、悲惨的世相,极具跨越世代的特质,谷斯范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古讽今、以古喻今,民众的悲苦命运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派捐派款,绑票勒索,我们老百姓被打入十八层地狱。”[12]87尤其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普通民众的命运更是如浮萍般风雨飘摇、凄惨无助。“村庄被烧得乌焦一片,沿途全是尸首;他的爷娘和九十一岁的老祖母,还有个远房叔婆,全被杀得精光。”[5]44谷斯范在《新水浒》和《新桃花扇》中,揭示了千百年来,中国民众那无法摆脱的悲惨命运。两部作品均以战乱为背景,展现了战争对弱势民众的无情损害,面对凶恶、残暴的侵略者,面对冷血、残酷的统治阶层,民众始终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
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发表时为了顾到孤岛的环境”[8]2,谷斯范决定以章回的形式和历史的题材去观照现实。因此,无论是古典章回的文体外型,还是历史题材的撰写,均是为作者观照现实的思想情感所服务的,“作者选取的历史题材,总是因为所处时代发生的事件与历史事件有某种相似。”[13]1这就决定了通俗小说《新水浒》和历史小说《新桃花扇》的文体内核是现实观照——暴露丑恶人性、批判腐败政治、描写悲惨世相,从而呈现出谷斯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三、杂糅共生的语言范式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维过程……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14]332对于文体来说,更是同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文体学是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文体风格的学问”[15]1,作为文体学重要一支的文学文体学就是研究语言在文学中的运用情况,“它以语言学的方法为工具,对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语篇进行描述和解释”[15]1。英国学者雷蒙德·查普曼也提及文体研究不能脱离语言,要以语言为突破口,“文学与其他文体不同,不会也不可能排除语言的任何方面”[16]23。因此,语言范式是谷斯范《新水浒》和《新桃花扇》文体范式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切入点。
谷斯范的《新水浒》和《新桃花扇》最为突出的语言范式特征即为杂糅共生。一方面,虽然《新桃花扇》改编自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典型的历史题材的创作,并且,《新水浒》和《新桃花扇》又具有古典章回小说的文体外型,但是,两部作品的文体内核和思想主旨决定了其语言应为白话而非文言。《新水浒》《新桃花扇》均是要传达现代人的思想和情绪,担负着向大众传播启蒙的社会功用。另一方面,古典章回小说的一大特质即“有诗为证”,因此,两部作品中自然又会有数目或多或少的以文言谱就的古诗注入。此外,为了表现思想主题的厚重与角色人物的历史深度感,这就要求历史题材作品《新桃花扇》中人物角色的语言并不能全部采用白话,适当加入一些文言反而有利于与角色的身份背景相匹配,从而更好地展开剧情、彰显主题。因此,谷斯范现代长篇小说语言范式的特质为以白话为主、文言为辅的文白杂糅。
在《新水浒》的第十一回,罗三爷吟诵过陆游的《夜间秋声感怀》。在第十二回,郑团长自己写作诗歌。在第二十回,黄杰想起过崔灏的诗句。在第二十五回,罗三爷背诵过陆游的《书愤》。上述诗词均为文言谱就,而谱就作品的语言则为典型的白话。作品中,以郑团长、黄杰、罗三爷等为代表的角色,其身份背景均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或现代教育,因此,他们能够吟诗作对,其语言表述方式更为优雅。而以六师爷、赵章甫等为代表的角色,其身份背景则是不学无术的无赖流氓,因此,他们的语言表述十分粗鄙,更不会吟诵任何诗词。这就自然实现了文白杂糅、通俗与高雅并置。“在通俗化这点上,作者是做到了。用语,句法,结构,都是中国式的,没有欧化的气味……一面他力避欧化,一面他也力避中国旧章回小说中惯用的滥调套语……这些文言文的字汇,尚非滥调……现在‘新水浒’对于文言文的字汇,也是极力避免了的……字汇固可采用大众口头,句法则有待自制……作者使他的人物都用了夹有地方语的普通话。”[1]3
在《新桃花扇》的第一回,朝宗吟诵过曹操的《短歌行》,苏老头初到蔡益所的中堂,朗吟过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在第二回,有人仿写了刘禹锡的《堤上行》。在第三回,《板桥杂记》的作者余怀写过一首赞美香君的诗歌,香君送别朝宗时为其吟唱过诗歌。第四回,香君唱过《牡丹亭》。第五回,黄太冲和钱牧斋吟诵过王叔明的诗歌。第六回,作品呈现了妥娘的组诗和一首词,钱牧斋为她写的诗,妥娘还吟诵过自己写的一首诗歌。在第九回,郦飞云吟诵过诗歌,还唱过两首词。在第十一回,周仲驭朗吟过王阳明的散曲《南双调步步娇》。在第十二回,朝宗吟唱过方密之的诗作。在第十二回,钱牧斋送杨龙友王叔明的横条,上题王叔明的诗作。在第十四回,马士英家藏有倪云林的真迹诗作《二月三日玄文馆听雨》。在第十六回,香君吟唱过妥娘所做的词《浪淘沙》在第十七回,柳如是寄给钱牧斋诗作,被其反复品鉴吟诵,钱牧斋翻看《咏怀堂诗初稿》时,看到诗作《送吴伯纯还皖上》,高声朗诵。在第二十四回,杨龙友看到朝宗所赠香君折扇上所题的五绝诗作。在第三十回,郦飞云吟唱过多首词曲。在第三十三回,赛月吟唱过多首词曲。在第三十八回,柳敬亭朗诵过夏允彝就义前所作的绝名词,朝宗为香君朗诵过他新作的诗歌。
上述穿插于文本之内的诗词均以文言谱就,除了诗词外,作品中出现的公文、书信等也均以文言谱就。黄澍请斩马士英的奏章:“湖广巡案御史奉旨监宁南侯军臣黄澍奏一本……奸督马士英有十可斩之罪,仅详列,以求圣断,以质公论事:痛自乱贼猖狂,宗社失守,幸皇上应运中兴,大张挞伐……”[6]185又如左懋弟出使满清前的奏本,“臣此行生死未卜,请以辞阙效一言:愿陛下以先帝仇耻为心,瞻高皇之弓剑,则思列圣之陵寝何在……”[6]194田仰离开南京后,派人押送两万两白银给马士英,并附上亲笔信件,“晚托老相国鸿福,一路舟行平安,于本月十八日傍晚抵扬州,次日即往东平伯官邸,贺其加爵大庆,东平伯对老相国照拂之意,感激殊深,云草莽之身,荷此厚恩,不知将何以为报耳……”[6]178马士英和阮大铖倒行逆施,引起公愤,各地清君侧的檄文传入南京,“除诰命赠荫之余无朝政,自私怨旧仇而外无功能……而乃冰山发焰,鳄水兴波,群小充斥朝端,贤良窜逐于崖谷……”[6]275建安王府镇国中尉朱统类邀请杨龙友出席宴会的帖子,“良辰美景,一去不再,秉烛夜游,古称达士;前线捷报频传,我等更宜及时行乐,谨订今晚酉时正,泊舟长吟阁埠头,恭候大驾光临”[6]299。
在第三十四回“扬州十日惨绝人寰”中,谷斯范对扬州惨案具体经过的写作方式,并非以全知全能的第三视角进行摹写,也并非借作品中某个角色之口进行叙述。作者谷斯范亲自进入文本之内,直接与读者展开对话,“明遗民王秀楚着‘扬州十日记’,是一部亲身经历的作品,且用白话摘录几段在下面,以见惨状一般”[6]305,由此呈现了扬州惨案的详细经过。《扬州十日记》是明末王秀楚所写的关于清兵在扬州屠城的一部约八千字的史书,因此,原著必然是以文言谱就。而谷斯范将此文本呈现给读者时,并不是摘录原文,而是将文言的原文变为白话再展现给读者。原文中穿插的诗词、公文、书信以文言的方式写作,这是与作品的文体外型和题材背景相契合。而《扬州十日记》以白话的形式呈现,则是由现实观照的文体内核所决定。谷斯范创作《新水浒》《新桃花扇》的根本目的是对普罗大众进行传播启蒙,以清兵屠城来隐喻现实中的南京惨案,令民众警醒,这是作者的主旨所在。因此,在《新桃花扇》中,更加明晰地呈现出文白杂糅的语言范式。
谷斯范现代长篇小说文白杂糅的语言范式一方面是由其文体外型和历史题材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服务于他的现实观照的文体内核。尤其对于《新桃花扇》这样一部“旧瓶装新酒”的作品,用白话叙述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主旨、作者的情感。用文言来朗诵吟唱诗、词等,更能展现其所蕴含的历史意蕴。在创造过程中,文言和白话的交汇使用十分自然,没有半点突兀,文白杂糅的语言范式使作品迸发出强烈的艺术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结 语
在1940年代,以谭正璧、谷斯范为代表的小说撰写,采用了古典章回的文体形式,在题材上偏爱历史新编,实则是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17]。新的生命便是现代人的思想情感——现实观照的文体内核,作品中以文白杂糅的语言范式来实现“夫子自道”:“我虽然不曾自比过歌德,但我委实自比过屈原。就在那一年所做的《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那里面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7]79即借历史人物、作品角色之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所想与所感,抒发自我的情绪、表达自我的见解,借古讽今、借古喻今,描写当下的社会世相,矛头直指统治阶层,使读者可以直接联想到某个独裁者、某个统治集团的丑恶嘴脸与卑劣手段,从而痛斥了现实社会的黑暗与统治阶层的无耻。但长期以来,谷斯范的文学创作特别是现代长篇小说撰写一直被学界所忽视。谷斯范的文学创作,特别是现代长篇小说写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浙江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写作实属一座有待开掘的文学富矿。通过对谷斯范长篇现代小说创作的阐释回溯,不仅能够钩沉还原其完整的文学创作风貌,重审其文学史地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谷斯范的“重新发现”,亦是一种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