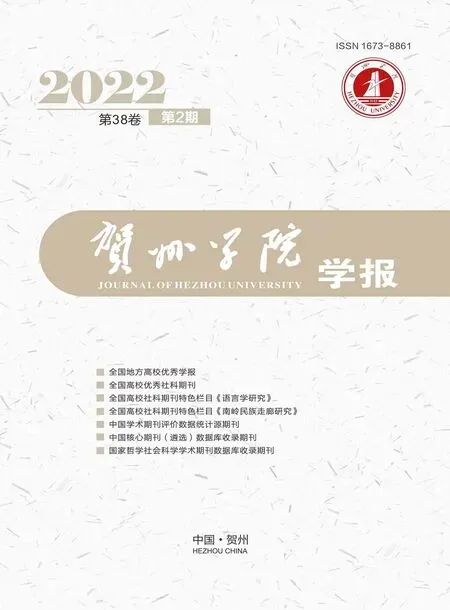抒黼黻之华,怀忠爱之意
——论清初遗民赋的家国书写
2023-01-06易永姣
易永姣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辞赋骈文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明朝甲申之变,李自成攻入明之都城北京,明政权灭亡,随后清军入关,定鼎中原,君临天下。明清易代,是王朝兴衰替代的展示,更是对中国古代士人“尊华贱夷”传统观念的强烈冲击,特别是那些拒仕新朝的明遗民,在朝代更替存亡中对家国的感受更为独特。崇尚气节的文士面对新朝和异质文化,不仅有禾黍之悲,而且还有身份归属的焦虑,他们或避居乡里,韬光养晦,待时守分而动;或坚定地忠于故国,不仕新朝,甚至以各种形式积极地参与反清复明活动。清朝虽然由满族建立,并且经历了明末大动荡,但是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大力调整和发展,国家政权渐趋巩固,社会相对稳定,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康乾盛世”。政治秩序的重新构建,特别是社会动乱形势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广大文士特别是清初遗民的生存抉择并使其心态发生微妙变化。
一、黄宗羲:风饕雪害,独立不移
黄宗羲是清初明遗民的代表,曾参加复社反对阉党阮大铖。南京弘光政权覆灭,他组织“世忠营”响应起义兵抗清,多次被清廷通缉,但仍坚持为鲁王提供抗清信息。其《避地赋》就是对这段经历的相关记叙。从避难小岛开始,然后逃到山中,又渡海去日本,至长崎岛、萨斯玛岛,乞师无果又返而西行,再避居于万山,转迁于他乡市廛、城廓,直至返回故居。据《清史稿》可知,这些都是黄宗羲当时参加抗清活动,遭受清廷追捕之真实情形。赋文以逃难空间的转换为叙事构架,在空间的变换和场景的描绘中,展示其逃难生活。每一处避难的场所,就是一个临时安置的家,如避地万山:“绝村落之烟火兮,支土锉于岩畔。接十寻之瀑布兮,使受役于城旦。”“与猿鸟而争食兮,偕憔苏而相乱”①,于荒郊野外支架瓦锅,混迹囚徒从事艰苦劳役,与猿鸟争食的慌乱等等生活片断,真实展现了作者当年流离失所、随地草草营家、简易艰苦的生活。再如避难山中,藏身墓地:“复有苦鸟鸣夜兮,林花莫不为之憔悴。处处哭声,朝朝丧櫘”“抱膝而坐蒿里兮,墓林纸钱又乘飚而突戾”,哭声丧櫘,纸钱突飞,通过听觉、视觉的感知展现出墓地的阴森恐怖;深秋霜夜,白发孤灯,就寝无眠,窗外麋鹿出没,猛虎横行,漂泊孤寂的凄楚苦难,孤苦无依的仓惶惊悚,这些特定空间内最直接,也是最真实的心理感受,写尽了逃难者内心对家的感知。赋文写长年的避地生涯,还用大量笔墨自然穿插、叙写当年避党祸的缘起及社会时势,在家难的背后彰显出国家政治风云突变的大背景。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专政,阉党横行,“嗟我生之不辰兮,逢家难于髫年。”“兰芽之方茁兮,霜雪从而萎焉。覆巢无完卵兮,羌变姓于佣保之间。”作者幼年遭受的家庭变故,正是缘于其父黄尊素因东林党狱被阉党迫害而死。“霜雪”之于“兰芽”,“鸟卵”之于“鸟巢”的生动比喻,不仅写出了政治对个体的摧残,也道出了家难与国运的密切关系。“幸先皇之御历兮,大憝授首而鲸鲵之。维时哭祭于阙下兮,醢奸骨以为牺。先皇登万岁山而见之兮,曰此忠死之孤儿也。虽红日之照融兮,实魑魅之繁徒。”真实地呈现了其父遭受迫害后,他与阉党的斗争经历。崇祯帝即位后,魏忠贤等阉党被惩治,黄宗羲赴京为父鸣冤,并上书请诛阉党余孽,在刑部会审时,他利用出庭对证的机会,刺杀许显纯,痛击崔应元,并拔其须归祭父灵,还追杀杀害其父的牢卒,被明思宗称许为“忠臣孤子”。
在国难家仇的叙写中,赋中更有令人动情的志节书写和家国情怀的呈现。黄宗羲归乡后,“益肆力于学”[1]13103,赋中“自比于管乐,宁窭篓于篷荜”一语,表现出他济国经世的宏远志向;“彼两京之颠覆兮,曾不偿孔壬之恩雠。我亦何罪何辜兮,窃独罹此横流。朝不坐宴不与兮,私天下为一家之忧。”遭受清朝廷的追捕缉拿,他还去日本乞师,渡海至长崎岛、萨斯玛岛,虽然自身命运多舛,但心中所虑依然是国家命运。在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阮大铖大兴党狱,受尽欺凌迫害,被阉党逮捕而逃至海中小岛,但作者于逃难中,目之所见却是“草木无所附丽兮,但见饥鹰千群之倏忽”,很显然,作者“自比于管乐”的济世忧民之心,受自身经历和自然景观的双重刺激,在这自然景观的描绘中隐现出当时百姓孤苦无依、贫困交加的社会现状;也正是因为这份济世忧民之心,才自然生发“想文山之竭蹶”“昔光尧于是乎至此”,感叹文天祥于倾危之际,倡义勤王;宋孝宗赵昚曾立志收复河山、积极备战,身处古人所经之地,想国家之巅危,故而有去日本乞师之举。
《避地赋》以逃难生活为主线,展示了个人遭际与社会时势的密切关系,也展示作者无家避地的苦痛和抗清复明的昂扬志气。在明清社会突变时期,黄宗羲对家国的特别感受,还可以从其《孤鸽赋》中得到印证。此赋咏家中孤鸽,旨在表现鸽之不事迁徙与依恋重情的习性,对照作者身世可谓意蕴深厚。赋开篇即论说鸽子栖迁成群的生活习性,但赋文重点却在表现“一朝星散,孤鸽不去”的独特不移,极力渲染孤鸽“孤影在壁”“怀旧维故”“飞不出于一域”“死别而吞声”的孤高桀骜和坚贞品性。作者展示孤鸽在伴侣离去之后,孑然独处,深情守候的形象,并将其对比失偶之孤鸿“犹遂队以南北”、失群之鹦鹉“犹淫声以媚人”,极力彰显孤鸽绝不肯追逐流俗的高洁品质。《孤鸽赋》大约作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康熙为笼络遗民群体,于康熙十七年(1678 年)征诏“博学鸿儒科”,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御试博学鸿词,其宽容、尊崇的态度使得原本与清政府对立的一些文士开始转变立场,甚至接受官职,俯首称臣。黄宗羲不仅拒绝参加博学鸿儒科的考试,而且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其赴京修《明史》时,他又以年老多病坚辞,并停止讲学,悉力著述。更具意味的是,在赋中,作者不仅对孤鸽形象作细致描绘与揣度,而且还将其与自身对照,从其“吾不知其所思兮,夫亦忧心之无界。仆也块然独处,俯首陈编。唾壶不缺,昨梦已残”的感叹,我们可以体悟到作者身经易代的巨痛,和面对新朝,不愿随波逐流的傲然心态。赋文描绘在草绿麦黄的春天,当群鸟飞翔、鸣声四起时,孤鸽羌然独立,“仰华屋之寥寥兮,昔啸侣而命俦;今故巢之阒阒兮,羌敛翼而明眸”,其沉郁静寂、坚毅执着,可以说正是作者“俯首陈编”遗老形象的生动写照。
黄宗羲还作有《海市赋》。海市(蜃楼)是指因为光的折射和反射,有时会在平静的水面、雪原、沙漠或戈壁等地方,出现楼台、城廓、树木等幻景。可见,人们所看到的海市蜃楼不过是主观幻想的虚像。从序言看,作者也并不曾见过海市蜃楼,赋中所绘是听他人言说而成的想象之作。但赋中所写城邑:“其为城也,雉堞崔嵬,丽谯炜晔。三里七里,勾股可摄。于焉戎马,乘城蹀躞。照白窃骊,雨鬃风鬣。俨烽火之告严,危黑云之将压。”在作者笔下,海市蜃楼竟然雉堞崔嵬,戎马奔骏,呈现出烽火告严、黑云压城的战争气氛。联系作者经历,抗清失败后,他隐居故里,著书讲学,多次力拒清廷的征召,可见其内心故国丧痛之沉重。但他虽然自己拒仕,却推荐弟子万斯同并支持儿子黄百家去修史,可知其对清廷的政治态度已有所改观。因此,不难想象,赋中所绘之海市蜃楼,心中的虚幻城邑笼罩着战火硝烟,无疑与明清交替时期的惨烈战争在他心中留下的阴影有关。由此也可推理,赋中所绘之楼观:“绮窗朱琐,明星萦绕。神妃杂沓,凭栏渺渺。其语可闻,若在妆晓。有时而现为黄幄,深檐婀娜,绣带悠扬。”绮窗朱阁的明朗华丽,神灵往来的笑语欢颜,洋溢着仙境的安宁与美妙。特别是其写单门聚落:“屋瓦参差,门户洞开。嗟朝烟之不起,岂井白之生埃。”其宁静与平和,宛如世外桃源,更有作者之感叹“固职方所不纪,亦战争所不灾。”足可见,作者内心对战争的痛恨,对和平、宁静生活的渴盼。
黄宗羲的上述赋作写尽了遗民流离失所、避地逃亡的苦楚。作为反清志士,他的赋也展现了饱经战乱后,人们对故国的伤痛和对和平、安稳生活的渴望。
二、钱澄之:往事满目,遗迹怆怀
同为明末爱国志士,也曾逃避党祸的还有钱澄之。钱澄之(1612—1693 年),初名秉镫,字饮光,一字幼光,晚号田间老人、西顽道人,与同期的顾炎武、吴嘉纪并称“江南三大遗民诗人”。钱澄之少有大志且慷慨激昂。崇祯初,曾挡住御史车驾,当众痛斥其勾引奸党、贪赃枉法的劣迹。当阉党余孽阮大铖死灰复燃,疯狂打击迫害“复社”时,他与陈子龙、夏允彝结“云龙社”应和“复社”,接武“东林”。南明王朝成立后,阮大铖等专权擅政,迫害复社文人,钱澄之参与起义,反抗清兵,失败后,他逃入闽中,入桂后,曾任永历帝的庶吉士,但终因对南明朝廷丧失信心而辞官归乡,结庐先人墓旁,闭门著书以终。不同于黄宗羲赋作的叙流离之苦,他的赋写归家之痛、失亲之悲。其《感旧赋》真实地呈现了他回归旧居时的感受。“兰委绝而荒砌兮,燕已去而垒虚。网蟏蛸以乍启兮,物尽散而无余。犹嫁时之床在兮,俨凝尘之未除。顾北窗之幔卷兮,钩至今其末下。”作者以久别归家者的视角,环顾庭院,摄取兰圃荒绝、燕去巢空、蛛网密布三处最富有代表性的经典意象,已尽显家之荒凉芜败,并且今日之荒败已暗蕴着往日之繁盛,而“物尽散而无余”的感叹,则满蕴着家道衰败的伤痛。在这样一个荒败、伤痛的场景氛围中,再接之以对嫁床驻足凝视这一极富深情的动作,引出对家中人事的叙写。由尘灰满床,幔卷乱飞的细节发现,而追忆亡妻生前夜中缝裳佐读、壮年游归馈食及兴疑自伤的场景,回想其助逃时的誓言与劝慰,再论亡妻赴水之情形。用一系列日常细节,追叙家中往事,回忆与亡妻生活的点点滴滴,在抒情议论中渗透着对妻子的挚爱与深情。特别是骚体句式的运用,骚体的婉曲悱恻将归家的落寞与情伤渗透纸笔。这种亡妻的凄苦之情在他的诗文中可以得到印证。如《小除夜梦亡妻》:“残年时序偪青阳,楚俗吴风忆故乡。祠龟香炉通夜炷,迎神钟鼓五更长。也知破寺无灯火,谁向荒江醨酒浆。贞魄不辞关路阻,几回幽梦诉凄凉。”该诗通过往事的叙写表露出对亡妻的深深哀悼。而此赋结尾之今昔对比更具深情:“念绕床之笑语兮,空只影以徘徊。凄往事兮满目,感遗迹兮怆怀”,以往昔欢笑的回忆,对比现在之凄苦,可谓倍增其苦;“家人劝吾以出户兮,毋独坐而增哀。吾出而将安往兮,吾室其何情以再开”,通过家人劝慰的典型场景的描写,把自己孤影独坐,无处安身,无以遣怀的悲怆形象呈现于读者跟前。
钱澄之的《感旧赋》通过回归故里,览观旧居,在静态、单一的家园空间内展示物是人非的悼亡之叹,展现了在社会交替的巨变时期,家破人亡的深沉悲痛。其《哀故园赋》则通过故园的书写直接揭露战争与社会时势和个人际遇的关系,更多表达的是对“国”的感知。赋文首先叙写明末战争导致其亡命天涯:“遭狂寇与饥岁兮,委田园于烽燧。欸小子之亡命兮,历万死而来归。”将其历经劫难的罪责直接归结于战乱。但作者之哀痛远不只于此。“爰构丙舍,依我先陇,既虑之尽灰,惟一卷以坐拥”,归乡后,他于田野间筑庐,意欲隐居著书。又躬耕劳动,以养家糊口,砥砺气节,并以此逃避清朝廷的注意。但灾祸并未就此停息。其长子法祖被盗贼杀害,但县令却不敢追查,钱澄之据理力争,而县令反而庇护被告,被告由此与他更加结仇。赋文真实地叙写了其子被害,为防仇人他不得不再次移居的情形。为防仇人他有家不敢回,唯有隐忍吞声,望家兴叹:“指林壑之在望兮,瞩朝夕之炊烟。念烝尝之久废兮,欲归欤而不敢前。”将那种迫于恶人与强权,欲归而不能归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仇人死后,他终于得以回归西田:
时倚仗于旧馆兮,迷旧址之所在。松桂摧为薪兮,群豕践为荒秽。忽梵音之出墙兮,系樊圃之吾庐。吾子于此陨命兮,爰捨宅与僧居。星已周夫一纪兮,吾过门而不忍入。闻修竹之蔽窗兮,念清阴而饮泣。历昔人之行坐兮,览故物其奚存。陟荒台兮废户,窥虚室兮无门。盼东皋之兰若兮,余蒿莱之满院。穿陇亩以檀乐兮,惜往昔之不见。上冢墓而哀号兮,使我去此者其谁与。
作者以细致的描绘展示家的破败,但相比于上次归家,这次家园呈现的不仅是荒芜景象,更是伤痛的记忆和仇恨的心绪。抚景追昔,儿子于此离世的苦痛渗透纸背,作者于墓前的哀号,对仇人的责问,表露出内心无以承受的巨痛。结尾衔幽恨而不能言的呼号,更是让人倍感凄惋。清代学者唐甄说:“饮光先生,忠直立身,以藏为用。”“先生遭变革,行患难,立身之善,处世之宜,自少至老,所历多矣。……其为人如彼,其所学如此,皆本性达情,无所庸其支饰,故其为文,如泉之流,清莹可监,甘洁可饮,萦纡不滞以达于江海,使读之者目明而心开。”其赋作中对家园的书写正是其人生经历的写照,是明清交替的特殊时势下,众多百姓患难人生的缩影。
三、朱之瑜:赤手纵难撑日月,黄冠犹自拥旌旄
清初遗民朱之瑜,字楚屿,又字鲁玙,号舜水,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朝中国五大学者”。朱之瑜少有经济之志,因见世道日坏,便慨然绝进士之怀,多次征召均不就。但明亡后,他却漂泊海岛,参加反清复明运动,并多次远赴海外,为鲁王政权筹钱,作为鲁王特史,联络各地反清力量。南明王朝灭亡后,他东渡定居日本,先后在长崎、江户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是日本“水户汉学”的开基者。其《游后乐园赋》据赋文可知作于“已酉春,三月十九日”,即1669 年,其70 岁时。序文交代事之缘起:“水户侯宰相公,以宛中樱花盛开,集史馆诸臣以赏之。因特史相招,况前已夙戒,余即时遄往。”“水户侯宰相公”,指日本水户藩德川光圀。德川光圀好学勤政,礼贤下士,欲修文德以致太平。他听闻朱之瑜志节高峻,学问渊博,便派人拜谒、聘请朱之瑜到江户(今东京)讲学,并以隆重礼节,亲自迎接至水户,尊之为宾师,终身自称门生。朱之瑜在《与安东守约杂札》中,记载其在水户讲学的光景时,曾赞叹日本学者对中国儒学的热爱:“水户学者大兴,虽老者白须白发,亦扶杖听讲,且赞儒道大美,颇有朝闻道夕死而可之意。”赋文所咏之“后乐园”,是德川光圀的私人庭园,其命名是因为听取朱之瑜的意见,依据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名之为“后乐园”。朱之瑜70 岁时,德川光圀在后乐园中设宴为他举行养老之礼,亲授几杖,竭诚尽敬。朱之瑜在赋中赞赏后乐园景致极美、设计恰到好处:“不肥不瘠,亦精亦雅。远近合宜,天然高下。耕稼知勤,杂作田野。水流山峙,茅店潇洒。小桥仄径,纡回容冶。则未有若斯之胜者也。”认为“就吾游览之所至,斯园殆甲于天下矣”。朱之瑜在71 岁时曾立誓:“老在异邦”,“非中国恢复,不归”,即便死后,非满清败亡,骸骨不“归葬”中土[2]619,表达了他对明王朝的忠贞。因此,在这篇赋中,他虽然身在日本,在水户藩德川光圀的私人庭园后乐园中并享受隆重的礼待,但却流露出身处异邦的愧疚:“余以异邦樗朽,倚蒹葭于玉树之藩”。听闻园中有伯夷、叔齐古祠,“吾未得过而礼,于心不能无歉歉矣”,很显然,这份深深的愧疚感不仅仅是缘于不能到寺礼拜,恐怕更多的是出于对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忠于商朝,抱志守节之大义的景仰。在赋文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他在后乐园的游赏行为与观感,从而领会到他身为遗民的特有心理:“于是暂休召伯之堂,容与苏公之陂”。“召伯”即姬奭,又称召公(一作邵公),辅佐周武王灭商,并辅佐周成王、周康王两代君主,开创了“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之治”。“苏公”指苏轼,“苏公之陂”即后乐园中的东坡堤。在后乐园的建造过程中,因为有朱舜水的参与,在庭园设计中融入了很多儒家思想的元素,除了赋中所提到的伯夷、叔齐祠,“东坡堤”,园中还随处可见以中国名胜命名的景观,如西湖、庐山等。苏轼一生筑过多条长堤,任徐州知州时,黄河决口,他组织军民修筑了一条防洪长堤;出任杭州时,为了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组织民工开浚西湖,修造堤堰闸门,并将挖出的湖泥葑草堆积湖中,筑成长堤以来往行人。正如赋中所言:“大夫无夙退之委蛇,则君侯无燕寝之暇逸。”“虞万几之丛脞,争得效十亩之闲闲。”朱之瑜主张实学,“不以循行数墨为学,而以开物成务,经邦弘化为学”[2]786“圣贤要道,止在彝伦日用”[2]561,他强调实理实学,要安邦治国,安民济众,而此刻他却作为一介遗民寄身异国,当此游览之时,将自身处境对比两位实政为民、卓有成效的古人,必然会给他带来强烈的心灵冲击和精神创伤,因此,赋中“兀焉震慄,使我戃恍。感圣人于川上,汩英雄于逝波。苟混混而如是,嗟沦胥兮几何!”这种时间飞逝,自己日渐沦丧的伤感,显然与此有关。朱之瑜参与后乐园的规划和建设时,将中国元素的注入设计之中,本身就与朱之瑜身处他乡为异客、怀念故国家园的情思有着莫大的关系。这种身在他乡而忠心故国的情思在其《坚确赋》中有更为鲜明的书写。朱之瑜曾以安南会安(今越南会安市)为基地,并在海外筹款、组织反清力量。但却被鲁王误解为耽心享乐,为了证明对明王朝的坚贞,他曾接受永历王朝官职,准备回国,但安南国王却想把其留下收为己用,他因此而经历了“供役之难”。在被囚其间,安南王曾派人送一“确”字来试探他,于是他写下了慷慨激昂的《坚确赋》,其中有一段写他在安南逃亡时,居住异乡的情形:
块然环堵之中,匏也茅茨之下。异桃李之芳园,奚文章之相假。形凄影其,何对月兮三人;己独人皆,存流风乎一我。乃有白叟能钟,踯躅踟蹰,抱持乐器,就坐簷隅。拳匏外向,孤弦内腹。弹拨难调,非丝非竹。齿踈涙浥,疑歌疑哭。不足以陶我神情,适足以扰我慎独。铁逸兴之遄飞,慕觥筹兮相遂。饭蔬水兮愆期,况流觞而听肉。身枯槁兮神驰,搴芳兰兮川谷。
虽然是简陋茅屋,身处萧然环堵之中,但已为白头老叟的作者即便是形凄影单,孤寂清苦,却逸兴神驰,坚守道义,他以自身形象表现了他的爱国之心,赋中他对“坚”“确”二字的释义,更是强调了他的坚定与执着。
朱之瑜的赋作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示出清初遗民即便是身处异国,也不改对故国的坚贞与深情。
四、冒襄、傅山:有头朝老母,无颜对神州
相比之下,冒襄的《后芜城赋》则突破了个人遭遇的述说,从国家、民众视角,叙写家园的芜败与战争的残酷,特别是清廷入主中原的残暴。冒襄(1611-1693 年),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又号朴巢,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今江苏如皋)人。冒襄十岁能诗,“少年负盛气,才特高”[1]13851。明朝末年,太监弄权,朝纲倾颓,他参加复社,与陈贞慧、方以智、侯朝宗诗酒唱和,抨击阉党,议论朝政,希望改革政治,挽救国家危亡,时称“四公子”。入清后,无意用世,不受博学鸿词荐,日与友朋文酒为乐。冒襄《后芜城赋》之芜城,指广陵城,即今之江苏扬州,而冒襄是扬州府泰州如皋人。公元前319 年楚国修筑广陵城。西汉刘邦封其侄刘濞为吴王,筑广陵为都城。广陵地势重要,成为三国时期江淮一带的军事重地,又是南北朝时的交通枢纽,市容繁华,是长江北岸的重要都市和军事重镇。南朝宋竟陵王刘诞作乱,城邑荒芜,遂称芜城。南朝鲍照著有《芜城赋》,极写广陵城今昔荒芜繁盛,抒发了历史变迁、王朝兴亡的感慨。冒襄所作《后芜城赋》,相比鲍照之赋,同样也是采用跨时空的场景对照,先写广陵山川胜势和往日全盛之日商贾纷集、邑屋帝宇绚烂富丽的繁华,再写眼前楼台倾圮、城郭凄凉的破败,虽然都是同一空间的今昔对比,但是相较之下,冒襄赋的指向更为明确,情感注入也更为强烈。在赋中,他写往日盛况,着意突出芜城“攻守齐备,高卑不一”等军事重镇的优势地位与“固获永基,君民咸益”护国保民的重要。在渲染今日荒芜景况时,又直接抒发议论:“岂越历朝而下,值丧乱之屡经,何当六百余载,更烽烟之未宁。潜锋鍉之格斗,焚琬琰于疆场。狼烟日炽,天堑罗殃。怒雨惨烈,迅风飘扬”,沉痛抨击历代丧乱不止,烽烟不宁的现象和“兵戈振荡,甲士流亡”的惨况。但是根据赋之标题下标注的“甲辰”二字,我们可知此文写作时间和创作意旨。1644 年,是甲申年,清军入关;1645 年乙酉年,清军包围扬州城,城中军民抗拒不降,艰苦守卫,清军在占领扬州后,便以不听招降为理由,下令屠城十日。据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记载,此次屠杀共持续十日。而冒襄赋后有“广生谨案:申酉之间,高杰兵杀戮至惨。吴梅村挽董宛君诗,所谓高家兵马在扬州也。此值是一篇有韵扬州十日记文。”明确地把此赋看作记载清军扬州暴行的又一详细记载,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扬州屠杀事件的关键性人物高杰。可见此文的写实性和明确的政治意旨。
傅山,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市)人,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傅山博艺多才,重气节,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明亡,傅山闻讯悲痛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诗句,并出家为道,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即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如石之坚,表示自己决不屈服于清朝。顺治十一年(1654 年),傅山因“甲午朱衣道人案”入狱,被指欲反清复明而遭受严刑拷打。据《清史稿》记载,他“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最后其门人用奇计将其救出。但出狱后,傅山却做诗表示其生还的羞愧之心:“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有头朝老母,无颜对神州。”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下诏征“山林隐逸”,他坚辞不赴。缅怀亡友,并收养东林、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晚年穷困潦倒,靠卖字度日。他自述道:“献岁八十,十年来火焚刃接,惨极古今!墓田丙舍,豪豪尽踞,以致四世一家,不能团聚。两子罄竭,亦不能供犬马之养;乃鬻宅移居,陋巷独处,仍手不释卷,笑傲自娱。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表现了他以明遗民自居,淡泊明志,决不仕清的心态和节操。其《无家赋》之序更是直接表明反清志向:“某尝读汉将军霍去病传,以未灭塞外匈奴为家,曰:嗟哉,天乎!斯何时也!桑弧蓬矢,我非男子也哉?顾孱弱不振,痛哭流涕之不遑,尚安能汲汲室家也者?”当此外族入侵,民不聊生之时,作者感叹自己身为男儿却无能为力,因而痛心不已。
冒襄、傅山的家国叙写不仅对社会动乱的政治斗争予以无情鞭挞,而且从宏观视角用最深沉的笔墨关注民生和民族动乱,对饱受兵祸灾难的人民大众给予无限同情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忠贞不屈和面对现实时势却无以更改的沉重悲痛。
结 语
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盛极一时,经历了易代之痛的清初遗民,面对新的社会形势,他们强调关注现实,追求济世安民的实际功效。如黄宗羲不满明代文坛的摹拟剽窃风气,倡导文学的经世致用:“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后世流为词章之学,始修饰文句,流连光景,高文巨册,徒充污惑之声而已,由是而读古人之书,亦不究其原委,割裂以为词章之用。”[3]502认为古之圣贤著书皆为济世救民,而后世则泛为流连光景、虚词丽采,流为脱离实际的词章之学。他主张为文应当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反映社会现实。朱之渝也主张:“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2]406认为学术要远离性理空谈,当以社会实际问题为主要内容。傅山一生“坚苦持气节”,而且秉持“文章生于气节”的文学主张。他在《历代名臣象赞·韩文公》中评论韩愈:
北斗泰山,起衰八代,人无间然,知公诸以文论。诸道兵不堪用,佐晋公时,入汴说韩弘协力。廷凑之变,慨然入镇,数语动悍藩,复使命。可仅目以文章士乎?肤论之士,辄与扬雄并称,殊非伦。即公亦每称雄,何也?世之人不知文章生于气节,见名雕虫者多败行,至以为文、行为两,不知彼其之所谓文,非其文也。[4]141
傅山不仅以确凿史据盛赞韩愈在文坛和政治军事上的功绩,而且批评世人“仅目以文章士”的错误作法。他认为韩愈称雄文坛,是因其文、行并重,并由此提出了“文章生于气节”的文论主张。傅山此论体现出清初遗民重视气节的基本文学价值观。他们在赋中的家国书写所体现出的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崇高精神,就是“文章生于气节”的最好例证。
傅山在《家训·文训》中提出:“文者,情之动也。情者,文之机也。文乃性情之华,情动于中而发于外。是故情深而文精,气盛而化神,才挚而气盈,气取盛而才见奇。”傅山认为“文”是作家情感被触动激发的产物,情是文的内在驱动,“情深”才能“文精”,并由此提出“文乃性情之华”的文学观。因此,主张为文当抒发真情,抒发个人情志,要做到“不事炉锤、纯任天机,淡处、静处、高处、简处、雄浑处”[4]674,不假雕饰,追求“拙”“野”“朴”等审美追求。他极力赞赏杜甫五言诗乃“全不事锻炼,放手写去,粗朴萧散,极有令人不著意处,而却难尽见其义”[5]83。在清初赋的写作中,以黄宗羲、钱澄之、朱之渝、冒襄、傅山为代表的遗民,分别从不同视角,对自身经历作真实叙写,特别是在明清易代的特殊时期,他们在避难生涯中对家的感知、对故国的坚贞、对新朝的抉择,由此所表现出的家园之痛、故国之思、战乱之愤、失亲之悲、行路之难等等,都是内心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故天机自得,不刻而工。
注释:
①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年。以下辞赋作品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