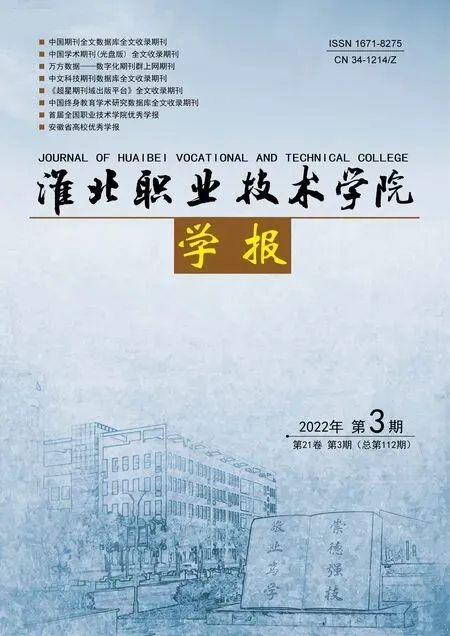从《红楼梦》中花、鸟意象看林黛玉形象的深层内涵
2023-01-06王敏
王 敏
(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花、鸟意象在中国文化里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承载着自远古至当下的缘物抒怀传统。在《红楼梦》之前,“花”与“鸟”常出现在诗词、绘画作品中,因而,它们被视为诗意的化身。细阅《红楼梦》,花、鸟意象俯拾皆是,这正是其诗意盎然的原因之一。林黛玉作为《红楼梦》的女主人公,气质典雅、才华出众,又是众多悲剧人物的代表,而“悲剧是崇高的集中形态,是一种崇高的美”[1],因此,可以说林黛玉正是因为悲剧而美,亦因为美而悲剧。故作者不吝笔墨,用繁复的花、鸟意象对其进行衬托、诠释,塑造出一个多才多情,又多愁多悲的黛玉形象。
1 太虚幻境以花、鸟意象预示悲剧命运
太虚幻境是天机所在,前世缘分、今生命运在这里都可一探究竟。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宝玉在秦氏屋里入睡那一刻就已置身太虚幻境中,“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处觅闲愁。”[2]71这是宝玉在太虚幻境所闻第一声。太虚幻境乃“清净女儿之境”[2]79,警幻仙姑受宁荣二公亡灵之托,将宝玉引来“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2]80。这所闻第一声就是警醒的开始,暗示大观园中众儿女终将如春梦、飞花一般消失殆尽,而黛玉作为这一段风流公案的始作俑者当然不会例外。据警幻仙姑“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2]73的自白,可见,宝黛缘分其实是为偿还一段情债,消解一腔怨痴。当初,黛玉自愿“下凡造历幻缘”[2]8,只说以泪报恩,并不求终成眷属,此动机就是宝黛爱情悲剧的开始。薄命司对联“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2]74中“皆自惹”正是指黛玉的悲剧因她自己而起,黛玉就是自己的系铃人。
警幻仙姑为引宝玉领悟,特意请他饮茶品酒,闻香听曲。那茶名“千红一窟”[2]80,甲戌本侧批:“隐‘哭’字”[3]161;酒名“万艳同杯”[2]80,甲戌本侧批:“与千红一窟一对,隐‘悲’字。”[3]161茶是“以仙花灵叶上所带之宿露而烹”[2]80;酒是“以百花之蕊,万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凤乳之麯酿成”[2]81,都与花有很大关系。“红”“艳”本用于形容花的颜色,因此,也常被作为花的代称。在《红楼梦》中更是大观园众女子的代称,在这里,作者明确指出大观园中女子的结局都逃不出“哭”和“悲”。回顾本书第一回,僧人说黛玉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为报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情而下凡,报恩的方式就是把一生所有的眼泪都还他,可见,还泪是黛玉一生的使命。既然黛玉为流泪而生,自然泪尽而亡,这就决定了黛玉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悲剧形象,注定她是一个悲愁加身的伤心人。
警幻仙子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正曲第二支《枉凝眉》将黛玉比作“阆苑仙葩”[2]82,暗合黛玉绛珠仙草的前世身份。“枉凝眉”注释为“曲名意谓徒然悲愁”[2]82,联系曲词“枉自嗟呀”[2]82“空劳牵挂”[2]82,可知,黛玉即便泣尽血泪,亦不过是为前世的绛珠仙草偿还一段恩情罢了,林黛玉终究是《误终身》里的“世外仙姝寂寞林”[2]82。
《红楼梦》十二支演到最后一曲《收尾·飞鸟各投林》,最末一句:“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2]86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黛玉来说,还泪就是她的食粮,在食尽之后,她这只鸟儿必将回身投林,这暗示着黛玉在泪尽之后将与世长辞。实际上,关于黛玉还泪的谶言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就已出现。黛玉初入贾府,众人问病,黛玉转述癞头和尚的话道:“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亲友之人,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世。”[2]39可黛玉偏为还泪而来,既要还泪,必然要哭泣,又必然要进贾府,如此,癞头和尚所说的两个禁忌都触犯了。依据癞头和尚的话,即知还泪一事是造成黛玉与病相伴直至死亡的直接原因,故而,以“鸟为食亡”来形容黛玉的悲剧确实贴合。
2 红楼世界以花、鸟意象衬托凄美孤高形象
2.1 宝玉之喻
在宝玉眼里,黛玉的美不只是旁人形容的风流婉转。第三回,宝黛初见,宝玉就认为黛玉形容与众不同。宝玉看黛玉:双眉如烟,双目含露,有一股缥缈仙气,体态举止更是出奇,宝玉用“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2]49来比喻。“姣花照水”可见黛玉娇美恬静,尽显其贵族女子之神韵;“弱柳扶风”以示黛玉“翩若惊鸿,婉若游龙”[4]之姿态。但自古“柳”在诗词中象征着离别,相聚即暗示着分离,这偏偏又是透过黛玉的形象来暗示,似与他人并无关系,这就使黛玉的悲剧形象在首次正式出场时就塑造出来了。
除了以“姣花”“弱柳”形容黛玉容貌姿态,宝玉还以“凤凰”为喻凸显黛玉的高贵、高洁。第十七至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为潇湘馆题匾时,宝玉见潇湘馆翠竹掩映,梨花芭蕉相衬,又有游廊甬路,意境清幽不俗,特题“有凤来仪”[2]222四字。元妃试才,宝玉为潇湘馆题诗,首句就是“秀玉初成实,堪宜待凤凰”[2]246,在宝玉看来,潇湘馆的清雅足以与高贵的凤凰相配。后接元妃谕,安排众人进园里去住,得知黛玉钟情潇湘馆,宝玉拍手称快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样,我也要叫你住这里呢”[2]311,原来黛玉就是宝玉笔下潇湘馆等待的那只凤凰。凤凰是传说中的灵鸟,在《庄子·秋水》中有“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5]的描述,恰与黛玉孤高不群、不肯俯就的品性相合。
进入大观园后,花、鸟与人共处一园,同感一情。第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心事,潇湘馆春困发幽情》,被晴雯拒之门外,黛玉不禁气动情发呜咽起来。黛玉一哭,感动花、鸟与她同悲,作者形容道“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2]360后又附诗云:“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2]360令人不禁联想到诗圣杜甫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6]2404林黛玉自艾自怜之绪与诗圣哀国伤时之情虽然不可相提并论,但前者竟也能够使花、鸟动容,足见黛玉感伤情绪沉郁复杂。黛玉这一哭有两层含义:一为自己身世,二为心中情愫,并且二者常常同时发生,由此及彼,相互助长。黛玉身边的人常认为她是小性儿,反倒是花、鸟成了她的知己。
2.2 花签之示
但凡提及以花喻人,都不会绕过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众姊妹丫鬟为怡红公子庆生,掷骰摇签,作者借花签上所题诗句暗示抽签人的性格与命运。看黛玉的花签:“只见上面画着一枝芙蓉,题着‘风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道是:莫怨东风当自嗟。”[2]872众人笑说:“这个极好,除了他,别人不配做芙蓉。”[2]872李白有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6]1752联系第八十九回,《人亡物在公子填词,蛇影杯弓颦卿绝粒》,宝玉看黛玉:“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2]1246可知,在众人眼里,黛玉为人、形容如清水芙蓉不加雕琢,傲然独立。回头看“莫怨东风当自嗟”,此句出自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永叔作此诗,意在抒发昭君之遗恨,表达对妇女命运的同情。“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7]诗句大意为:但凡美貌的女子,大多命运不济,不必怨天尤人,却应自己叹息。正如前面提到的,与生俱来的还泪之事,宝黛初见的预示,加上这里的花签诗句,无一不是在将黛玉悲剧的根源指向她本人。
2.3 紫鹃、雪雁、鹦鹉之寓
再看,在潇湘馆常与黛玉做伴的是她的丫鬟紫鹃和雪雁,还有一只鹦鹉。紫鹃、雪雁都是以鸟命名,“鹃”即杜鹃,中国古代就有“望帝啼鹃”的传说,在古典诗词中,杜鹃常与悲苦之事相联系,又因其啼声宛如“不如归去”,令人触动乡愁,多被用于抒发乡愁。因此,紫鹃的命名其实寓意着黛玉日夜思念家乡和双亲。“雁”在古诗词中也很常见,如:杜甫《孤雁》中“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6]2551。失群的孤雁,不思饮食,想念她的同伴,拼命追寻雁群。雪雁跟随黛玉由南方来到京都,又是自幼就随身,可见,她也如黛玉一样远离故土、永别双亲,作者如此安排是为了烘托出黛玉“孤雁”一般的处境和心境。因此,读者便不难体会黛玉出门前特意吩咐紫鹃:“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2]368的苦心了。一个去乡离家的人,连鸟儿是否顺利归巢都关心不已,是不愿再见到同自己一样的失巢之鸟。
在第六十七回,《见土仪颦卿思故里,闻秘事凤姐讯家童》,林黛玉见了宝钗送来的家乡土物,“触物伤情,想起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寄居亲戚家中”[2]928,故而又伤起心来;第八十七回,《感秋深抚琴悲往事,坐禅寂走火入邪魔》,黛玉抚琴低吟:“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2]1225足见黛玉思念故土、双亲之情切切,并且这样的身世之痛时刻淤塞心间。这还不止,每当触及身世之痛就又连带出情爱之痛来。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含耻辱情烈死金钏》,黛玉无意间听见宝玉与湘云对话,得知宝玉待自己与他人不同,又多出了一番思虑:“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泪来。”[2]433再也回不去家乡,再也见不到父母,如此境遇直接又导致了无望的爱情,黛玉正如那日夜啼血的杜鹃、失落雪中的孤雁。
黛玉所养的鹦鹉在《红楼梦》中虽只出现了一次,但其“言行”大有内容,不可忽视。第三十五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黄金莺巧结梅花络》,黛玉同紫鹃回来,心中正悲戚着,廊上鹦鹉“嘎的一声扑了下来”[2]461,黛玉道:“作死的,又扇了我一头灰。”[2]461后鹦鹉长叹一声“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2]461,接着念《葬花辞》。鹦鹉这一扑将黛玉的感伤情绪一扫而光,又能模仿黛玉叹气、吟诗,可见,黛玉常逗鹦鹉玩耍,教鹦鹉念诗。这些自然而然的日常小事体现出鹦鹉平日与黛玉非常亲近,黛玉也常常以鹦鹉为伴打发漫漫白昼,鹦鹉是黛玉重要的精神伴侣之一。
鹦鹉羽毛色彩艳丽,聪明巧言,被认为是会说话的鸟,人们喜欢将其养在笼中。古诗词里的鹦鹉或与深闺怨女相伴,或以身不由己、思念旧林笼中鸟的形象出现。例如:“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8]747(晁补之《南歌子》);“鹦鹉怨更长,碧笼金锁横”[9](冯延巳《菩萨蛮》)都是抒发闺阁女子的幽怨愁思。又如:“雕笼悲敛翅,画阁岂关心。无事能言语,人闻怨恨深”[6]5797(张祜《鹦鹉》);“鹦鹉含愁思,聪明忆别离。……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6]2521(杜甫《鹦鹉》),与黛玉“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烦忧”[2]1226的感叹如出一辙。黛玉远别故乡,囿身侯门,终日忧思,就如笼中鹦鹉一般境遇。再看张祜《再吟鹦鹉》中诗句“美人怜解语,凡鸟畏多机。……雕笼终不恋,会向故山归”[6]5797,又与黛玉因聪慧被人忌惮,遭人嫉妒、诽谤的遭遇相合。黛玉在历经“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2]371陷入绝望之后,终于抱恨长逝,重归太虚幻境,也如诗中的鹦鹉,最终回归故山。
3 深闺诗社以花、鸟意象自叙宿命心性
3.1 《葬花吟》《桃花行》之预见
《红楼梦》之所以被视为诗的国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文中有许多文采斐然、感人至深的诗文。每逢起社比诗,黛玉的诗作总能脱颖而出,让人耳目一新。黛玉闲时独处深闺也常醉心于吟诗写诗,与笔墨为伴。《毛诗序》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0]从黛玉的诗里,我们不仅能读出她的品格、性情,还能感知到她对自己宿命的预知,可以说,黛玉正是通过一首首诗来完成她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诉说。
《葬花吟》是黛玉的代表作,堪称《红楼梦》中诗作之冠,并且在《红楼梦》中的表现形式别具一格,黛玉葬花时以哭声道出。黛玉“葬花”与“哭”这两个行为与《葬花吟》的诗文内容水乳交融,凄楚悲戚,以致宝玉“不觉恸倒山坡之上”[2]373,令脂砚斋“身世两忘,举笔再四,不能下批”[3]326。对读者而言,《葬花吟》是悲剧抒情诗,是悲啼,更是摄人心魄的葬花图,可谓有声有色有情。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2]371起句渲染出漫天铺地的凄凉气氛,“花谢”寓意生命的终结,“红消香断”指死亡的到来,“有谁怜”是自问自答,无人怜惜之意;“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2]371暗示屋在人亡,预示黛玉之死;“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2]372,“难留”是命中注定,正如黛玉泪尽之日即是仙逝之时,都是前生既定;“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2]372暗指黛玉死亡日期在春残花落时节,人与花一道春尽而去,从此诀别。
黛玉幼年丧母,自小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就连所依恃的外祖母之爱也很有限。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病潇湘痴魂惊噩梦》,黛玉做噩梦,在梦里,“众人不言语,都冷笑而去”[2]1158,“老太太呆着脸儿笑道:‘这个不干我事’”[2]1158,又说黛玉“在此地终非了局”[2]1159,最后命鸳鸯把黛玉送出去。第九十回,《失绵衣贫女耐嗷嘈,送果品小郎惊叵测》,提及宝玉婚姻,贾母道:“自然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再没有先是外人后是自己的。”[2]1254黛玉在外祖母眼里尚且是个外人,在旁人那里更是无足轻重了。又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黛玉已到弥留之际,贾母让凤姐为其预备后事,说道:“咱们家里这两天正有事呢。”[2]1332可见,黛玉的死生大事在金玉良缘面前竟不值一提,这一切又恰好应了黛玉之前的噩梦,真正是“红消香断无人怜”了。
黛玉诗作中,能与《葬花吟》相提并论的就是《桃花行》,二者都是黛玉以花自喻的代表作。正值初春,万物复苏,然而,黛玉一首《桃花行》使宝玉看了悲痛流泪,说:“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2]967实际上,《桃花行》就是黛玉对自己生命最终归宿的预见,是属于她自己的哀音。
从“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2]966到“侍女金盆进水来,香泉影蘸胭脂冷”[2]967,都在描绘人与花惺惺相惜,佳人伫立桃花下暗暗饮泣的情景,但及“香泉影蘸胭脂冷”后,情绪突然急转直上,有“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11]之气势。佳人在水中看到了自己的满面泪痕,更觉自己可怜、可悲,才有了接下来的:“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2]967从花解怜人到花如血泪、花飞人倦,情与花相融,花与人结合,并一同走向消亡、寂静。“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2]967与“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2]372一样,直接指向最后的死亡。因此,可以说黛玉在《桃花行》中已经明确发出了自己的死亡预告。
3.2 海棠与菊之寄托
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探春带头起诗社拟咏海棠,潇湘妃子写道:“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2]492-493李纨点评道“风流别致”[2]493。“冰”“玉”“梨蕊白”“梅花魂”尽显黛玉冰清玉洁、孤傲不群的品性;“半卷”“半掩”“拭啼痕”等,正是黛玉日常深居简出、时时抹泪的情形;“缟袂”“怨女”表现出不胜悲戚,心境凄凉的意味。黛玉此处借咏物以抒怀,“表白海棠形神之美,寄寓悲愁怨恨之情”[12]250,将自己的心志、行为、情绪一一表白出来,就如创作了一幅自画像。
海棠诗社第二次活动,黛玉又以《咏菊》《问菊》《菊梦》三首咏菊诗夺魁。黛玉在《咏菊》的首联和颔联,塑造出一个满怀诗情、热爱创作的诗人形象,从构思到提笔,再到对月吟哦,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这正是黛玉本人痴心于读书写诗的日常写照。行至颈联,笔锋一转“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2]511又转回到自己的哀愁情绪中去了,自怜无人能解她一腔“素怨”。尾联又回到咏菊,赞扬菊孤高自傲的“千古风高”[2]511,读者自然联想到黛玉孤傲不群的心性。
第二首《问菊》,黛玉以菊为知己,倾吐自己心中疑虑,“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2]512正如湘云所说:“真个把个菊花问的无言可对。”[2]515黛玉问菊就是问自己,你这般“孤标傲世”有谁能与你为伴?你为何总是孤芳自赏不与他人同乐?庭院深深,大雁南归,蟋蟀悲鸣之时是否激起了你的相思?发问之间黛玉将自己的孤独、乡愁一并倾吐出来,可谓“问的细、问得深,要而不繁,感同身受,句句问到了菊花的痛处”[12]270。
《菊梦》是写菊花的梦,当然也是黛玉自己的梦。在梦中,忆陶潜之风雅、同大雁南归,获得了短暂的满足,最后被蟋蟀鸣叫声惊醒,美梦破碎而幽怨无人可诉,只能寄托于“衰草寒烟”[2]514。黛玉仍是接以上《问菊》继续抒发寄人篱下的忧伤和思乡怀人之情,表露出惶惶不可终日的生命常态。
3.3 诗中“燕子”之诠释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黛玉的诗作中,“燕子”这一意象出现的频率较高。首先,第十七回至十八回,黛玉替宝玉作《杏帘在望》一首,其中:有“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2]247句;再有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之《葬花吟》中“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2]371句;再次,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黛玉作《唐多令》起句便是“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2]971。黛玉多次以燕子入诗,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潇湘馆里就住着一只大燕子,二十七回,黛玉出门前特意叮嘱紫鹃:“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2]368足见黛玉待那只大燕子如同家人。
杜甫《归燕》有句:“四时无失序,八月自知归。……故巢傥未毁,会傍主人飞。”[6]2421燕子筑巢在宇,年年春回寻旧巢,与人关系亲密,因而承载着人们诸多情思,譬如:羁旅行愁、相思怀远、兴亡之叹等,而林黛玉笔下的燕子则寄寓着她对自身处境与心境的感知和诠释。
作《杏帘在望》时,黛玉对自己的情感归宿心怀希望,故诗中燕子是穿梭桑榆间、筑巢房梁上的愉悦燕子;后因误会与宝玉赌气,心内感伤失望作《葬花吟》时已是梁空巢倾、一去不返的无情燕子,希望破灭之后,黛玉预见了自己人去屋空的结局。燕子楼因形似飞燕,又有许多燕子栖息于此而得名,在诗词中,“燕子楼”这一意象始终与燕子意象紧密相连,如:苏轼《永遇乐》“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8]389;张孝祥《木兰花慢》“紫箫吹散后,恨燕子、只楼空”[8]2148。在这里,“燕子楼”中只有燕子,表达出空虚、失意、惆怅的心绪,据黛玉《唐多令》中:“飘泊亦如人命薄……叹今生谁舍谁收?……凭尔去,忍淹留。”[2]971-972可知,黛玉笔下“燕子楼”意在感慨自己身世飘零的孤寂和悲愁,还包藏着无枝可依的绝望叹息,可以说,《唐多令》是黛玉接下来所作《桃花行》之先声。通过对黛玉笔下燕子意象的对照,黛玉进贾府后的心境、处境的转变不言自明,用“每况愈下”“日益艰难”来形容并不为过。
4 结语
纵观《红楼梦》全篇,林黛玉应该是曹公最偏爱的人物,所以,才将其塑造得如此纯真清俊、才华出众,又是那样的高不可攀。从太虚幻境到红楼世界,再到林黛玉自己,一事一物、一言一行都在对她进行衬托、渲染,将其从《红楼梦》那个花鸟之境中缓缓托起,直到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永恒的女主角。从林黛玉的身上,读者能感知到其清虚性灵、真诚恻怛的人性之美,亦得以领悟预言式宿命的权威力量,同时,还能窥见作者曹雪芹高雅的诗人气质和可贵的悲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