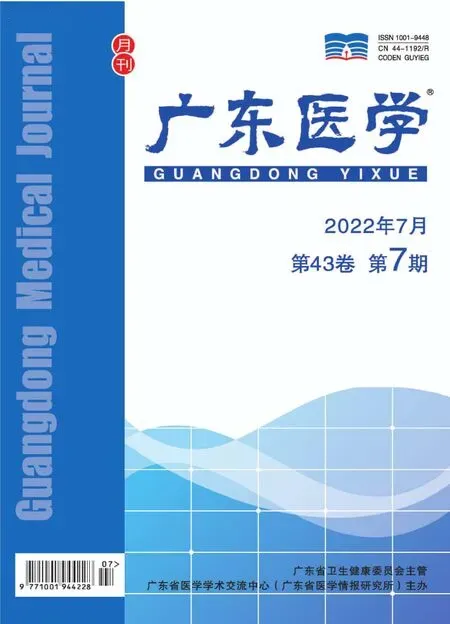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新进展
2023-01-06罗秋敏陈佳李智鹏揭育胜林炳亮
罗秋敏, 陈佳, 李智鹏, 揭育胜, 林炳亮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广东广州 510630)
乙型病毒性肝炎严重威胁人类健康,2019年全球乙型肝炎病毒(viral hepatitis B,HBV)相关死亡人数高达82万,中国大约有8 600万HBV感染者[1]。在过去30年里,我国采取献血筛查、新生儿普遍接种乙型肝炎(乙肝)疫苗等措施,使乙肝防控取得巨大的进步,2014年我国一般人群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率已降至5%~6%[2],意味着我国已经从乙肝的高度流行国家转变为中度流行国家[3]。2016年WHO提出了“2030年全球消除病毒性肝炎重大公共卫生威胁”的战略目标[4],要求到2030年,HBV感染诊断率达到90%,抗病毒治疗率达到80%,病毒性肝炎相关的病死率下降65%,而得到及早的诊断和治疗是降低病死率的最重要举措。然而,截止至2020年,我国仅有22%的HBV感染者得到诊断,而慢性乙肝(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抗病毒治疗率仅为17%[5],与WHO的目标有显著差距。因此亟需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加强对慢性乙肝的诊断及治疗,争取早日实现WHO的战略要求。所谓更加积极的措施,包括治疗观念的更新及治疗手段的改进,即更宽的抗病毒适应证和更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案。
1 慢性乙肝治疗观念的变迁
近十几年来我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进行了多次更新,在抗病毒治疗适应证上体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从2005年版指南[6]中建议“对HBV DNA≥1×105Copies/mL(HBeAg阴性者,HBV DNA≥1×104Copies/mL),谷丙转氨酶(ALT)≥2×ULN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逐渐发展到2019年版指南[7]建议“对HBV DNA阳性,ALT持续异常的患者给予抗病毒治疗”。再到2022年的《扩大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的专家意见》[8],一方面下调启动抗病毒治疗的ALT阈值,另一方面则建议:对于HBV DNA阳性者,无论ALT水平高低,只要有乙肝肝硬化或肝细胞癌家族史,或者年龄>30岁,均建议抗病毒治疗。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科目前正开展一项前瞻性“核苷酸类似物治疗HBV DNA阳性且ALT正常人群的随机对照研究”[9]及一项“聚乙二醇干扰素α-2b治疗非活动性慢性乙肝的真实世界研究”,以探究慢性乙肝治疗关口进一步前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为早日实现WHO的战略目标,医院已初步形成一套院内乙肝筛查转诊流程,引导在非感染专科筛查发现的HBV感染者转诊至专科进行诊疗及随访,以达到对慢性HBV感染“应诊尽诊、应治尽治、应访尽访”的目的。
对慢性乙肝治疗观念的变迁不仅体现在抗病毒适应证的扩大,还对疗效有更高的追求,即期望达到临床治愈。现行的一线抗病毒药物有核苷(酸)类似物(Nucleoside/Nucleotide analogue,NAs)和聚乙二醇干扰素α(Peg-IFNα)。NAs服用方便、安全性高,在长期NAs治疗中,慢性乙肝患者HBV DNA不可检测率可达到85%以上[10-12],然而对HBsAg的清除率却远低于1%/年[13],意味着单纯NAs治疗实现临床治愈的可能性低,因此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服药,这是目前众多乙肝患者治疗的困境,也是影响患者治疗依从性的主要原因之一。Peg-IFNα在有限的疗程内可以达到高于NAs的HBsAg清除率,研究显示,治疗前HBeAg阴性、HBsAg<1 500 IU/mL,以及治疗12周或24周HBsAg<200 IU/mL的患者是Peg-IFNα治疗可获得临床治愈的优势人群[14-15]。由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发起、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牵头执行的“中国慢乙肝临床治愈(珠峰)工程项目”正在开展,该项目以提高CHB临床治愈为目标,截止至2022年4月底,全国共362家医院参加,累计有效入组患者20 693例,中期数据显示,PP分析集治疗满48周患者的HBsAg转阴率达到32.8%[16],意味着在部分优势患者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然而,对于非优势人群疗效仍不乐观,且Peg-IFNα需皮下注射,部分患者可能出现不良反应,同时存在较多的用药禁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临床应用。
2 新型抗病毒药物的研究进展
由于目前的一线抗病毒药物尚不能满足大部分患者临床治愈的需求,亟需继续开发新的抗病毒药物、研究新的治疗方案在有限的疗程内提高HBV的临床治愈,目前在研的新型抗病毒药物主要分为靶向病毒生命周期的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和参与免疫调节的间接抗病毒药物。
2.1 DAAs HBV的复制经历多个步骤(图1[17]),首先病毒通过与肝细胞膜上的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sodium taurocholate cotransporting polypeptide,NTCP)受体结合进入肝细胞(入胞抑制剂作用靶点);核衣壳易位、脱壳,松弛的双链DNA(relaxed circularDNA,rcDNA)进入细胞核(衣壳组装调节剂作用靶点);rcDNA转化为共价闭合环状DNA(covalently closed circular DNA,cccDNA),并以此为模板转录产生病毒RNA(cccDNA沉默剂作用靶点);HBV RNA翻译产生HBsAg、HBeAg和核心蛋白等病毒蛋白(RNA干扰的作用靶点),HBsAg被释放到细胞外(HBsAg释放抑制剂作用靶点);前基因组RNA(pregenomic RNA,pgRNA)和病毒聚合酶一起包装到核衣壳中(衣壳组装调节剂作用靶点),并在此完成逆转录形成新的rcDNA(核苷酸类似物作用靶点),新的病毒颗粒被释放到细胞外,完成HBV的整个复制过程。
2.1.1 小干扰RNA 小干扰RNA(small interfering RNA,siRNA)是一种可靶向结合、沉默mRNA的双链RNA,能阻断HBV蛋白的翻译。与VIR-2218单药治疗相比,联合Peg-IFNα治疗24周可以使HBsAg下降更为显著(分别为1.89lg IU/mL和2.55lg IU/mL),且耐受性良好[18]。JNJ-3989(siRNA)联合NAs治疗168 d,HBsAg平均下降1.93lg IU/mL,98%患者HBsAg下降>1lg IU/mL[19],19.1%患者在治疗48周达到主要研究终点(HBV DNA低于检测下限,HBeAg阴性,HBsAg<10 IU/mL),而JNJ-3989、NAs和JNJ-6379(一种衣壳组装调节剂)的三联方案,达到上述终点的患者为8.5%[20]。提示JNJ-3989与NAs联合,可以显著降低HBsAg,疗效甚至优于联合衣壳组装调节剂,因此尚需更多的研究以探索siRNA的最佳联合方案。
2.1.2 反义寡核苷酸 反义寡核苷酸(antisense oligodeoxynucleotide,ASOs)是短单链RNA,可以抵抗核酸酶,同样能够阻断mRNA翻译[21]。Ⅱ期临床试验中[22],初治患者接受Bepirovirsen治疗4周,HBsAg平均降低1.56lg IU/mL,NAs经治且维持稳定的患者联合治疗后,HBsAg平均降低1.99lg IU/mL,显著优于安慰剂组;23.5%患者在治疗结束后HBsAg<0.05 IU/mL,然而在随访期间(第85天开始)均出现HBsAg再次升高,提示该药能快速降低HBsAg,但持久性不足。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绝大多数是轻中度,ALT升高呈自限性,且只发生在HBsAg下降的患者,整体耐受性较好。
2.1.3 基因编辑沉默cccDNA表达 CRISPR/Cas 9系统具有核酸酶、解旋酶、整合酶和聚合酶等活性,被证明能有效地切割HBV基因组,包括cccDNA,但也可能导致宿主基因组的双链断裂,导致病理后果,因此安全性限制了其临床应用[23],在此基础上,新研发的CRISPR/Cas介导的“碱基编辑器”,通过引入无义突变而不裂解整合的HBV基因组,从而提高了安全性[24]。锌指核酸酶可以直接切割cccDNA的特定序列,使cccDNA沉默,从而抑制HBV复制[25]。这些药物还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2.1.4 入胞抑制剂 NTCP是HBV进入肝细胞的特异性受体,Bulevirtide(BLV)是NTCP抑制剂。Ⅱ期临床试验[26]中,相比BLV 2 mg/d单药和Peg-IFNα单药治疗,BLV 2 mg/d联合Peg-IFNα治疗48周效果最好,治疗结束时46%患者HBsAg下降>1lg IU/mL,HBsAg转阴率20%,停药后24周HBsAg清除率27%。这表明BLV与PEG-IFNα联合治疗,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可在有限疗程内获得HBsAg清除,提示BLV在未来HBV治疗方案中具有潜力。BLV最主要的不良反应是总胆汁酸升高,但在随访至50周时,总胆汁酸已恢复至基线水平。
2.1.5 衣壳组装调节剂 衣壳组装调节剂(CAMs)主要的作用机制是加速衣壳的组装,破坏核心蛋白的稳定性,形成空的或异常的无功能衣壳[27],其次是导致核衣壳解体,使cccDNA暴露于降解酶中,减少cccDNA的循环[28-29]。Vebicorvir(VBR)的Ⅱ期临床试验[30]中,NAs经治的病毒学抑制患者联合VBR治疗24周,pgRNA下降1.74lg IU/mL,优于NAs单药组(0.09lg IU/mL),而HBsAg下降不明显;HBeAg阳性初治患者接受VBR联合ETV治疗24周,HBV DNA和pg RNA分别下降5.3lg IU/mL和2.34lg IU/mL,同样优于ETV单药组;所有患者继续接受52周的联合治疗后停用VBR,均在停药4周出现pg RNA的明显反弹[31],提示52~76周的VBR治疗虽然可以大幅降低pg RNA,但疗效并不持久。不良反应主要是轻度的皮疹和ALT升高,整体耐受性良好[30]。
2.1.6 HBsAg释放抑制剂 核酸聚合物(nucleic acid polymer,NAP)可抑制HBV亚病毒颗粒的组装和释放。Ⅱ期临床试验[32]显示,75%的患者在接受NAP+TDF+Peg-IFN的三联治疗10周内HBsAg下降4~6lg IU/mL,比TDF+Peg IFN二联方案的HBsAg下降更迅速且幅度更大;在完成48周的三联治疗时,60%患者HBsAg≤0.05 IU/mL;停药随访48周,维持临床治愈率达35%。然而,联合NAP组发生ALT升高的比例更高,90%的三联组患者ALT升高>3 ULN,最高的ALT升至1 748 U/mL,而二联治疗组这一比例为30%;同时还观察到ALT骤升与HBsAg下降相关。这表明NAP+NA+Peg-IFN的联合方案可以获得较高的临床治愈率,但安全性需要特别重视。
2.2 间接抗病毒药物:参与免疫调节
2.2.1 固有免疫调节剂 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7和TLR-8均可触发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应答,TLR-7主要诱导产生IFN-α和IFN-β,通过破坏HBV衣壳和抑制HBV转录起到抗病毒作用[33-34]。TLR-8诱导产生IL-12和IL-18,前者可以重建HBV特异性T细胞功能,两者联合可刺激固有淋巴细胞产生IFN-γ,继而促进感染肝细胞的非细胞毒性HBV清除[35-38]。TLR-7激动剂可明显降低小鼠HBV DNA和HBsAg[39],TLR-8激动剂的Ⅱ期临床试验[40]显示,治疗24周停药随访,HBsAg清除率5%,HBeAg转阴率16%。提示TLR-8激动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HBsAg的清除能力,研究中均没有严重不良反应发生,安全性好。
2.2.2 治疗性疫苗 长期HBeAg、HBsAg等抗原的暴露使HBV特异性T细胞耗竭,治疗性疫苗则是为了激活体内特异性免疫来达到病毒清除的作用。现开发的治疗性疫苗包括病毒载体疫苗、DNA核酸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多肽类疫苗、免疫复合物疫苗等。古巴研发的NASVAC是一个重组蛋白疫苗,含有HBsAg和HBcAg,研究显示其对HBV DNA有相对持久的抑制作用;12例患者治疗结束时HBeAg仍为阳性,但随访2年后8例转阴[41];85%的患者在治疗期间出现ALT升高,但在治疗结束时均恢复正常,整体安全性较好[42]。YIC疫苗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治疗性疫苗,含HBsAg-HBIG复合物,以明矾为佐剂。Ⅱ期临床试验[43]显示YIC组的HBeAg血清学转换率优于对照组(21.8%和9%)。Ⅲ期临床试验[44]增加了样本量及给药次数后结果并不乐观,YIC组HBeAg血清学转换率反而低于对照组(14%和21.9%),推测YIC的过度刺激可能引起机体免疫疲劳,反而降低疗效。εPA-44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纳米颗粒脂肽疫苗,安全性良好,Ⅱ期临床试验[45]显示,在28周内接受6次治疗,HBeAg血清学转换率显著高于安慰剂组(38.8%和20.0%),也优于目前NAs和Peg-IFNα的疗效。然而,εPA-44抑制HBV DNA的能力却不及NAs,但与NAs停药后易出现HBV DNA反弹不同的是,获得HBeAg血清学转换的患者在εPA-44停药后HBV DNA继续下降。值得注意的是,Peg-IFNα和(或)NAs治疗应答不佳的患者中,有41.7%实现了HBeAg血清学转换和HBV DNA下降,表明εPA-44可能在目前一线抗病毒治疗无效的患者中获益。该研究中并没有患者HBsAg转阴,且HBsAg下降幅度不大,因此尚需进一步优化方案来追求临床治愈。目前εPA-44与NAs序贯治疗的研究正在开展中。
2.2.3 单克隆抗体 HBV单克隆抗体可以减少循环中的乙肝抗原,抑制HBV进入肝细胞。CHB患者每次注射Lenvervimab(一种人重组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后24 h HBsAg降到最低,随后出现反弹[46]。进一步研究[47]发现HBV DNA的E164或T140碱基突变,可能是引起HBsAg反弹的原因。而当Lenvervimab与NAs联用时,表现出显著的抗原中和活性。因此,未来若要控制免疫逃逸变异株的产生,可考虑与NAs联合治疗,该药正在进行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
2.2.4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PD-1是一种表达于活化T细胞表面的跨膜受体,其配体PD-L1通常在树突状细胞或巨噬细胞表面表达。PD-1与PD-L1的结合可抑制T细胞的活性[48],2021年PD-L1 Envafolimab在我国被批准用于晚期实体肿瘤患者,它在体内可解除T细胞免疫抑制,慢性乙肝患者的Ⅱ期临床试验[49]显示,Envafolimab治疗24周HBsAg较基线平均下降0.38lg IU/mL,其中基线HBsAg≤500 IU/mL的患者降低更为显著(0.7lg IU/mL),并有3例(19%)获得HBsAg清除,相比之下,安慰剂组HBsAg没有明显变化。治疗期间没有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但有60% HBsAg明显下降的患者出现ALT骤升,因此,安全性还需引起重视。
总之,在研的新型抗病毒药物因其治疗靶点不同而各有特点,总体耐受性较好。ASO能快速降低HBsAg,但持久性不足;NAP在实现临床治愈方面显示出不错的效果,但需注意NAP诱发ALT骤升的问题;CRISPR/Cas 9系统能沉默cccDNA,但也可导致宿主基因组断裂而造成病理后果,对此,已在研发更安全的基因编辑药物;CAMs可以快速降低pgRNA,但存在停药后反弹的问题,长期服用NAs抑制病毒复制的基础上联合CAMs可以提高疗效;治疗性疫苗在HBeAg血清学转换方面显示出优势,但是对HBsAg的影响小;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体现出较好的降低HBsAg的作用,但需要注意其诱发的免疫性肝损伤。单药治疗难以实现满意的疗效,DAAs与免疫调节剂和NAs联合的方案更值得期待。
3 展望
目前,靶向HBV生命周期各环节的新药研发正如火如荼进行中,部分新药单用或联用的Ⅱ期临床试验给我们展现了令人欣喜的结果;且随着抗病毒治疗适应证的扩大,覆盖的治疗人群在大幅增多,慢性乙肝的治疗未来有望由部分“可控制”进入全面“治愈”时代。但基于HBV整个生命周期涉及到多环节、多部位(细胞核、细胞质)的复杂性及cccDNA池的存在,患者达到临床治愈停药后是否会再次出现HBV复制仍需引起大家关注。
利益相关声明:本文所有作者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说明:罗秋敏、陈佳:论文撰写;李智鹏:资料搜集整理;揭育胜:审校及修改;林炳亮:总体设计及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