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与“大众”评《人民的北京人》
2023-01-05臧龙凯
臧龙凯
一 导言
舒喜乐的《人民的北京人:二十世纪中国的大众科学与人之本质》(ThePeople’sPekingMan——PopularScienceandHumanIdentityinTwentieth-CenturyChina,图1)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政权对人类起源理论与古人类学发展的影响,对有关迷信、大众科学和大众文化的问题进行了再梳理。首先,该书叙事沿着鲜明的群众路线,在传统科学史叙事中加入民间参与科学的讨论,也就是所谓的“大众科学”,其包括科学普及和群众参与科学。大众科学是在“反迷信”的背景下展开的,作者并未从正面讨论“迷信”这一复杂的话题,而是巧妙地将“反迷信”作为舞台来展现群众、精英与科学的互动。其次,该书从文化史的视角关照“大众文化”或者“迷信”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古人类学发展的影响。作者希望通过展现官员使群众参与科学的矛盾心理,论证大众文化与科学文化互相促进的作用,来批评“迷信话语”下对大众文化多样性的忽视,提倡科学与大众文化积极平等的愿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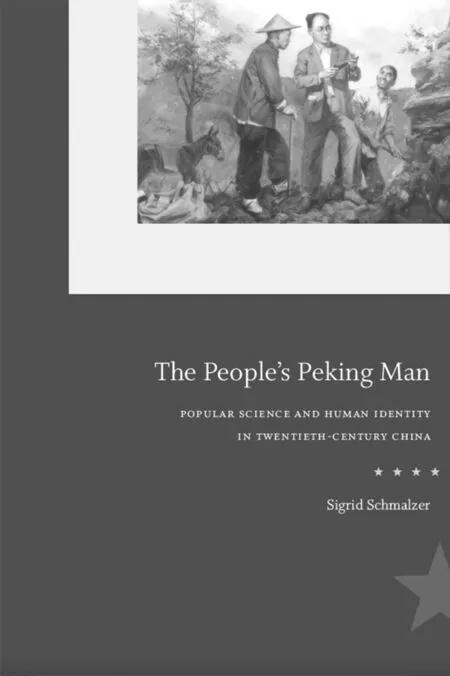
图1. 《人民的北京人》书影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舒喜乐十分关切科学理论(人类起源理论)如何贡献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如何发动群众科学和科学普及运动,进而影响科学(尤其是古人类学)的发展。标题里的北京人并不是指现在生活在北京的智人,而是20世纪20年代末考古发现的曾经生活在北京一带的直立人(homo erectus)。对作者来说,北京猿人和野人这两个看似无关的概念在20世纪40年代及以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对二者的探讨展现出大众科学、大众文化与科学整体发展的丰富互动。北京猿人的发掘和呈现,及其所代表的人类进化理论本意味着科学研究的进展,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对科学普及、群众参与科学的强调,古人类学与群众产生了紧密的关联,北京猿人在学界和官方被应用于中国人起源、原始共产主义图景等论述中,同时在大众文化中凸显出传说性质。而野人原是伴随着抨击迷信、用自然主义解释迷信现象诞生的民间传说,以一种独特魅力在大众文化中流行开来。但却随着改革开放,学界和民间形成一股野人热,以至于野人成为了科学考察、研究的对象。
关于北京猿人作为中国人祖先的历史问题,已有不少重要研究。早在2001年,沙伯力(Barry Sautman)就已经撰文提出这个问题,他通过分析大量官方媒体材料,用民族主义和政治手段来解释北京猿人何以成为中国人的官方祖先、多地区起源学说为什么在中国学界成为主流[1]。舒喜乐此书第八章对沙伯力做了针对性的回应,她认为民族主义并不能够对中国古人类学进化理论现状的充分解释,相反,通过透视非官方媒体的史料,她提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包括科学界内部关于化石形态的争论、中国科学界在国际科学的地位以及其他非民族主义因素[2]。在舒喜乐之后,针对这个问题,严晓珮(2014)从20世纪上半叶亚洲中心主义进化学说入手,考察了参与北京猿人发掘的西方学者的理论贡献,以及相关理论如何成为北京猿人作为中国人祖先的理论依据[3];程映虹(2017)主要从遗传学角度切入,通过分析遗传学者和古人类学者的争论,讨论中国人起源问题的政治内涵[4]。
“迷信”一词古已有之,但经历了几番言语的变迁才成为现代含义的“迷信”。晚清之时,“迷信”一词并没有直接贬义,用来翻译英语 superstition,在广泛使用中形成了新义,大致类似笃信或着迷的信仰,与民国所称非理性、非科学的信仰习俗不同[5]。“迷信”较现代的内涵是在19世纪末从日本传来,直到新文化运动成为负面的概念。民国时期,“迷信”除了包括传统的民间信仰、传统、民俗和实践,如卜筮、命相、星占和风水等方面[6],还逐渐纳入宗教,成为非理性的代名词,站在了科学的对立面。在民国精英看来,“迷信”已成为和封建、传统思维绑在一起的糟粕,而为了实现现代化,需要全力革除迷信,这种迫切的程度是极其强烈的。但仔细去看,即使是抨击迷信的最盛时期,迷信的定义和范围也很难说形成了共识,尤其是关于宗教是否是迷信,还有很多论辩的空间。
尽管这本书主要写给西方读者,但中国读者依然能从舒喜乐的精心叙事和深入讨论中获得对我们当代问题的启发。
二 鲜明的群众路线:“反迷信”与“大众科学”
舒喜乐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对群众这一群体的描绘。在近代科学史的大部分叙述中,诸多史料、讨论都是围绕科学家以及科学机构的,往往会忽视民间的科学参与者。但是舒喜乐将很大一部分重点放在“大众科学”的理解上,不仅关注科学精英、科学管理者,还在大量民间史料中找寻群众参与科学、理解科学的历史足迹。“大众科学”在《人民的北京人》的论述中是一个较为核心的概念,它既包括自上而下的科学普及活动,也包括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科学,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中国科学事业的主旋律。
舒喜乐对“大众科学”的关切是以“反迷信”为背景开始的,“反迷信”作为一种话语,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普及和群众参与科学的动力和共同奋斗目标,其基本路径就是用科学来解释“迷信”。但“反迷信”并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产物,作者这样论述也是为了更好地将大众科学与古人类学这一主题联系起来。将民间信仰的鬼神用自然主义的科学去解释,这本身并不稀奇,在西方也有很多对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问题,舒喜乐就谈到了UFO的例子(2)舒喜乐主要用这个例子来说像野人研究这样的“边缘科学”,往往很难辨清支持者和反对者:主张用自然现象解释UFO的人也分两派,一派认为UFO就是星象、气体、动物之类,另一派认为UFO属于某些秘密武器、超地飞船等非常规科技产物。([2],页218)。而且,破除迷信也不是现代性的独创,对民间信仰的批判古来有之,它是精英世界对民众世界思想和行为传统改造和叙述的延续。中国传统皇权统治下的社会,一直有对民众信仰系统改造的惯例,如历来官府禁止淫祀,捣毁妨碍维护统治秩序的民间崇拜场所[7]。
作者在从五四时期的“反迷信”运动谈起,它既是北京猿人在周口店被发掘的社会背景,也为后来二十世纪中后期反迷信活动的延续提供思想来源([2],页28)。在本书接下来的几章里,作者着重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政府官员和科学精英成为“反迷信”行动的主角和践行者,将民间旧习俗传统的活动和信仰革新成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新事业。在作者的叙事方式中,“反迷信”串联起社会主义政府官员、科学家和群众,把科学与大众紧密结合起来,更紧凑地讨论“大众科学”,即科学普及和群众参与科学运动。假使从正面来谈群众“迷信”,除了涉及谈到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等宗教,还包括各种卜筮、命相、星占和风水等内容,这些民间文化与古人类学很难紧密联系起来,叙事不免冗余和零散。因此,舒喜乐针对性地围绕“反迷信”来谈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大众科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人类起源、进化的知识和理论被用作自上而下科学普及的工具,使迷信消除、唯物主义得到广泛理解。在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反迷信运动,最早可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各个阶层在根据地向民众传播科学知识的活动。为了消除人们对鬼神等的迷信,解放区干部重排了白毛女剧目,将原来群众中的长毛野人传说转化为封建压迫下穷苦人的故事,并在结局中宣扬反对剥削的阶级斗争([2],页58)。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通过组织政治大课、建立博物馆、设立科协等科学普及机构,开展自上而下针对群众的扫盲、传播知识活动,尤其是普及关于物种进化的知识。进化论不仅促进传播唯物主义理念,还帮助大众理解曾被认为怪诞灵异的事件,以及抨击当时被认为是毒害的宗教,是反迷信的重要工具。其中,恩格斯关于劳动、工具在人类进化扮演重要角色的论述得到了大力宣传,即劳动成为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因,劳动创造了人的本质([2],页62—77)。而北京猿人,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为官方背书的中国人远古祖先。当文科受到重点批判而不能参与人性的讨论,古人类学作为自然科学担起研究和普及人类本性的重任。
这一时期,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科学的程度大大提高,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实际上,群众参与科学在古人类学这里很早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古人类学的田野实践自始至终就依赖群众的参与,舒喜乐在第一章里梳理北京猿人发掘过程时,着重讨论了参与发掘的技工和劳工的作用([2],页38)。1949年以来,群众一直是提供化石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且古人类学学者们在当地的工人帮助下进行发掘活动。没有群众的参与,古人类学的实践几乎很难完成。但群众的参与也不断困扰官员和科学家。过度提升群众参与科学的资格,也难免遇到群众领导科学的局面,甚至有群众作为外行批评科学家的活动。此外,群众提供了各种各样关于“龙骨”的信息,但并非所有都是有用的,科学家也困扰于如何评价被认为科学素养薄弱的群众提供的信息。
改革开放以后,科普活动和群众参与科学延续了前一阶段的热情,同时科学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专业化路径,迷信与科学的关系就显得更加微妙。随着改革开放,“迷信”不再是政治红线,前一阶段一直受到压抑的民间文化得到自由挥发的空间,舒喜乐称之为“百花与毒草共生的花园”。西方文化再次走入中国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的大力推广带来群众对科学的关注和参与,也引起群众对身边各种奇闻怪事、甚至对气功等“迷信”的着迷([2],页191),而“野人文化”就在这场科学普及运动中迅速发酵。“野人”从民间传说故事走入进化理论解释范围,并且成为科学考察的对象,同时又激发更多有关野人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想象。从舒喜乐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当科学家也参与曾被认为是迷信的研究中,科学与非科学在这里便模糊了边界,这也是在回应科学史界对科学与伪科学的争论。
三 文化史的视角:“迷信”与“大众文化”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在科学史的叙述基础上,融入了相当多文化史的视角讨论“迷信”或“大众文化”。在舒喜乐的论述中,以“迷信”称论民间信仰贯穿全书,而后两章关于新的时期的叙述和结论中突然开始较多使用“大众文化”指代民间观念,“迷信”与她所谓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有何关系?“迷信”等于“大众文化”吗?
舒喜乐对此并没有专门讨论,但从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二者在内容上没有本质区别,“迷信”更多是一种被强加给“大众文化”上的有色标签。她认为“大众文化”是指通过社会关系网产生和维持的想法、信念和实践,而非政权或者相关文化机构产生的。但是,“迷信”在舒喜乐这里并非是实体概念,是为了理解时代所需要使用的话语。
在舒喜乐看来是“大众文化”的东西,被20世纪50—70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官员与科学家看作是“迷信”。批判“迷信”,是科学家和政治精英共同的任务,“迷信”在这一时期本身就是精英属性的、主要为精英使用的,而“大众文化”则相对中立一些。对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迷信”是封建贵族和精英强加给百姓的观念,抨击“迷信”并非消灭大众文化,而是为了铲除那些阻碍人民对科学产生贡献的错误信仰。显然,舒喜乐并不认可这种说法。她指出,不管科学家和官员如何声称,在那个时代批判迷信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指向批判大众文化([2],页134、135)。因此,她在肯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动群众参与科学的同时,也批判那些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看法,他们把阻碍进步的因素归咎于传统的毒害,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清除迷信而不是填充知识的缺陷([2],页295)。
在舒喜乐看来,“大众文化”并不应该受到“迷信”这样的待遇。如果说抨击迷信是为了传播科学,那么大众文化并非科学的对立面,与科学传播和普及并不矛盾,而且与科学文化多向交融,互相推动;大众文化也不需要科学的最终解释权,它有自己生长的逻辑,甚至她反对过度提升科学家的特权([2],页244、245)。
舒喜乐希望借助对“迷信”与“大众文化”的历史反思,来表达她对大众文化遭到不公待遇的不满。她着重关注20世纪社会主义政权对迷信的反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家和政治精英都共同参与粉碎迷信、传播科学的运动之中,比较起英国科学传播的模式(认为大众对科学的认知如白纸一般可以被各种知识填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则认为大众思想已经被旧文化占据,这种旧封建迷信荼毒百姓,与新思想不兼容,所以需要先消除迷信才能够传播被认为是唯物的、正确的科学知识([2],页75、76)。舒喜乐在书中批判了这种对大众的看法,认为大众文化自有其发展,甚至在推动科学文化上有独特的力量,“群众被迷信裹挟”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她认为理想的状况是科学不再用作批判大众文化是非的绝对标准,科学家也从精英主义的位置上褪去光环,科学真正走向大众。当然,舒喜乐也清楚,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是对社会有益的,但是她认为,对迷信发动的抨击运动并没有很大帮助,这更多是基于对大众文化与科学关系的错误理解([2],页296)。
作者批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官员和科学家的矛盾心态:他们既提倡群众参与甚至领导科学,又担心群众带着迷信的成分来干预科学。作者认为,假使这些官员和科学家不把民间文化纳入到反迷信的运动中去,他们可以很好地理解群众科学的精妙。这当然是理想的状况,大众文化不再被作为迷信或者科学的对立面来看待。但仅仅指出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能在这里像舒喜乐在书末所提倡的,反事实地问一下“为什么这些官员没有想到把‘大众文化’从‘迷信’中拯救出来?”,呈现历史为何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的现象,或许能更帮助读者理解那个时期人们对“大众文化”理解的时代局限性,即“反迷信”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如何让管理者无法区分“有害的大众文化(即迷信)”和“无害的大众文化”。
四 结语
舒喜乐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在论述中添加了大量“群众”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既想展现出群众作为科学接受者和科学参与者展现的强大文化力量,又希望描绘出中国群众多样的面貌,这些群体既为科学家提供化石信息和参与发掘、又用政治批判科学、还组织和加入野人科考等等。为了展现改革开放时期群众的“野人热”,作者甚至诉诸文学研究来展现大众文化不同于科学文化的一面。不过,对群众的关注仍有需解释的地方,作者始终没有讲清楚“野人热”到底是什么,这一时期的野人热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野人的关注性质上有何差异也未谈及。此外,作者提到了群众参与泥河湾遗址的化石发掘([2],页160),但并未解释群众如何分工,我们也就无从得知当地民众到底如何贡献科学知识的生产。总之,尽管对群众的刻画仍有更多需要阐释的空间,但是作者在中国近代科学史研究中将群众纳入知识生产的主角之一,依旧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
进入新时代,“反迷信”运动早已淡出时代的主旋律,科学随着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发展,越来越将群众限制在高高的教育门槛之外,要弄懂前沿科学不上大学几乎不可能,普通公众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看法的机会几乎为零。例如,在新冠疫情中,有关疾病、疫苗的知识都是由实验室完成的,不仅是群众的科学参与越来越边缘、倾向博物学,那些非生物医药、非公共卫生专业的科学家也很难参与到新冠疾病的知识生产中。科学的参与似乎又回归到了精英培养路线,大众依然被认为缺乏参与科学知识生产的必要条件,“民间科学家”始终是一个科班科学家避讳谈及的词汇。但至少科普栏目再也不是用自然主义解释怪异离奇事件的路径,后疫情时代“谣言”代替“迷信”成为新的话语,科学普及更迎来又一个春天。
致谢:感谢陆伊骊副教授和舒喜乐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