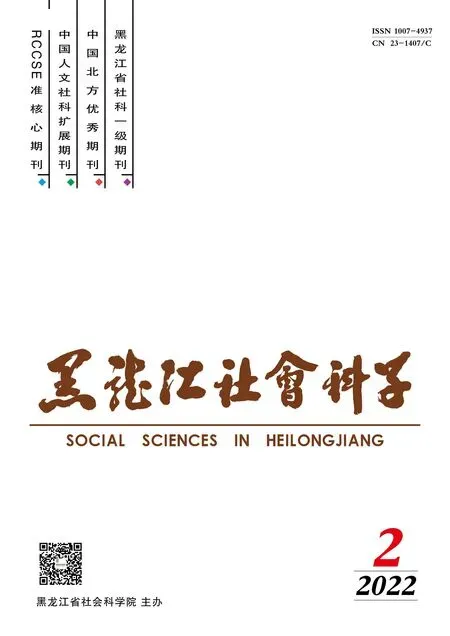汉代属籍与宗室差序管理
2023-01-05陈鹏
陈 鹏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宋儒朱熹有言:
(汉代)宗室惟天子之子,则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则嫡者一人继王,庶子则皆封侯;侯惟嫡子继侯,而其诸子则皆无封。故数世之后,皆与庶人无异,其势无以自给,则不免躬农亩之事[1]。
这是朱子鉴于宋代宗室管理之弊而对汉制作出的褒扬。汉代宗室管理,实有赖属籍制度。属籍是著录宗室成员的名籍,既往研究从官制、户籍、谱牒等角度,对其性质和功能进行了考察[2]。不过,有关属籍制度的关键问题之一,即著录宗室之范围,仍有待进一步澄清。
汉代宗室主要指汉高祖父刘太公(太上皇)后代,规模较大,但并非一切宗室都能著录于属籍。从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来看,汉代宗室存在“五属内”和“五属外”之别。所谓“五属”,唐人颜师古曰:“谓同族之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也。”(《汉书·韦贤传附子玄成传》注)[3]3122“五属内”宗室载入属籍,“五属外”宗室则不能。但这是否为两汉共同的制度,则尚存争议。此外,照颜师古之说,汉代属籍制度受到儒家丧服“五服”的影响,然前贤对此亦不无疑义。本文拟在既往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辨汉代属籍著录宗室的范围,探讨丧服“五服”与汉代属籍的关系,揭示汉朝如何通过属籍制度对宗室施行差序管理。
一、汉代属籍著录宗室范围
秦商鞅改制,令“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4]2710。汉代属籍制度虽与此不同,但亦不包含所有宗室。如上所述,汉代宗室分“五属内”和“五属外”两部分,仅前者著录于属籍。不过,有学者认为这是西汉的制度,东汉则不再遵循[5]。但1971年出土的“甘谷汉简”令这一说法破产,其明确将东汉宗室划分为“有属/五属内”和“属尽/五属外”两类[6]396-398。然而关于西汉属籍的情况也存在争议,例如邢义田即主张西汉国家律令不用“五服”来界定亲属亲疏关系,以“五服”界定宗室亲疏和是否享有特权是东汉新制[7]529-533。是故,我们有必要对此稍加考辨。
《汉书》对西汉宗室的记载,存在“有属”或“有属籍”之说。《汉书·哀帝纪》称哀帝即位时“赐宗室王子有属者马各一驷”[3]334,颜师古注曰“有属,谓亲未尽,尚有服者”,即将“有属”解释为丧服“五服”内宗亲。类似记载,《汉书》还有数处:《文帝纪》载文帝四年(前176)“夏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3]120;《元帝纪》载元帝初元元年(前48)夏四月诏“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初元五年夏四月诏“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3]279、285;《成帝纪》载成帝建始元年(前 32)二月赐“宗室诸官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有属籍者”[3]303;《平帝纪》载平帝元始四年(4)二月赐“宗室有属籍者爵”[3]357。在这些记载中,皇帝赏赐的宗室都是“有属籍”者。与此相对,必然也存在“无属籍”宗室。更言之,西汉宗室存在“有属籍”与“无属籍”之别。
《汉书》还有“宗室属未尽”之说,例如《宣帝纪》载宣帝地节元年(前69)夏六月诏书曰:“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3]246;《平帝纪》称平帝元始元年正月,诏“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其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3]349。正如学人所论:“所谓‘属籍未尽而罪绝’,即属籍尚未到正常该绝之时因犯罪而遭尽绝的处罚。由此可以推断,即便没有犯罪,也有自然正常的应该尽绝的时候。”[8]所谓“属未尽”与“属尽”,当即依据亲属关系远近来划分的;“复属”,即重新载入属籍。《汉书·武帝纪》也提到元光元年(前134)四月“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颜师古注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国反,故绝属。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属籍于宗正也。”[3]160这些宗室得以重新载入属籍,正是由于他们“属未尽”,亦即为“五属内”宗室。《后汉书》也载有和帝元兴元年(105)、顺帝永建元年(126)“宗室以罪绝”而“复属籍”的情况[9]193、251-252,可知为两汉通例。
以上讨论表明,西汉宗室同样存在“有属”与“属尽”之别,与“甘谷汉简”所见东汉宗室有“有属/五属内”与“属尽/五属外”之别相应,因此基本可断定西汉属籍著录的是“五属内”宗室。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有关宗室子弟减刑条文,也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旁证:
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简82)
吕宣王内孙、外孙、内耳孙玄孙,诸侯王子、内孙耳孙,彻侯子、内孙有罪,如上造、上造妻以上。(简85)[10]
这里,“公”指公室、皇室,“内公孙”指皇孙[11],“耳孙”指曾孙[12]。《二年律令·具律》中可减刑宗室的范围可整理如下:第一,皇帝之孙、曾孙、玄孙、外孙;第二,诸侯王之子、孙、曾孙。按照丧服“五服”之制,玄孙、外孙正处于服制最低的一等(缌麻),所以上述范围恰与皇帝“五属内”子孙相吻合。《二年律令》一般认为是吕后二年(前186)颁布的,而《具律》中吕氏子弟可减刑者范围与吕宣王(吕后父)“五属内”子孙相合,是当时吕后家族与皇室地位相埒的表现。由此可推定,至晚至吕后二年时,汉律对享受减刑特权宗室范围的界定,已与皇帝“五属内”子孙相合。不过,《二年律令·具律》没有使用“有属”“属尽”或“五属内”“五属外”等更明确的概念来表达享受减刑特权宗室范围,透露出当时属籍制度可能尚不完善。太史公曰:“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4]4010正是这一情形的写照。
汉初属籍制度不健全,从《二年律令·秩律》二千石一级没有“宗正”亦可得证。有学者认为“当时朝廷的宗正有职无人,所以《秩律》不列”,甚至猜测“那是吕后的刻意压抑宗室之举”[13]。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和《楚元王传》,汉朝第一个有记载的宗正刘郢客,正是吕后二年任命的[3]753、1923。故《秩律》未载“宗正”似与吕后压抑宗室无关,况且即便“有职无人”,律令亦不应不注明秩级。《汉书·高帝纪》称高祖七年(前 200)二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3]64,但不见于他处记载,也未提到何人任宗正。当时,刘邦之兄弟、诸子年长者皆封王就国,不得担任汉朝宗正,宗室中似无位望堪任宗正者,这不能不令人质疑汉高祖时是否确有宗正官。很可能至《二年律令》颁布时,要明确享受减刑特权的宗室范围,朝廷才任刘郢客为宗正,设属籍管理宗室。
检诸文献,关于“属籍”的记录,最早即为上引文帝四年“夏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其次为景帝时除楚元王子刘蓺、休侯刘富等人属籍[3]143、1925,以后渐多。禇少孙补《史记·三王世家》明确写道:“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4]2575属籍制度很可能是吕后时初创,历经文、景二朝走向完善。此后,直至东汉,汉朝属籍皆将“五属内”宗室作为著录范围。而《二年律令》对汉代宗室的划分,反映了初创时的面貌,并给后来属籍制度的完善奠定了法律基础。
最后,有必要阐明的是,所谓“五属内”宗室,究竟是谁的“五属”?沈刚提出“有属籍”宗室“限于皇帝或诸侯王五服以内”[5];袁延胜则称属籍著录的是“宗室各王侯五属内的亲属”[14]21。然前一说未言明是在位皇帝或诸侯王,还是包括先帝、先王;后一说更嫌模糊。王尔春认为“五属”当是“在位皇帝以及所封诸侯的五属”[15]。笔者赞成“五属内”宗室是指在位皇帝之“五属”,“五属内”宗室随着皇位传承而变化。成帝时匡衡论汉家宗庙毁立称“太上皇非受命而属尽,义则当迁”[3]3122。太上皇被称作“属尽”,正是以成帝“五属”而论的。至于在位诸侯王“五属”,较诸在位皇帝“五属”,往往存在一代人以上的差距。在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裁撤王国宗正官前[3]741,王国宗正所掌王国属籍,或以在位诸侯王“五属”为限。此后,宗室属籍皆由汉朝宗正职掌,不大可能迁就诸侯王。其实,从上引《二年律令·具律》条文来看,皇帝子孙与诸侯王子孙的减刑范围即不同,前者比后者多出一代,宗室特权上已更倾向与皇帝的亲疏。因此,“五属内”宗室应指在位皇帝“五属”而言。
二、丧服“五服”与汉代宗室属籍
有学人否认西汉属籍以“五属”为限,源自对西汉人用丧服“五服”划分亲属关系的质疑。丧服“五服”是战国以降儒家揉合古礼、斟酌损益而成,由《仪礼·丧服》《礼记·丧服小记》等礼学篇章记述下来。例如《丧服小记》曰:“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16]1495丧服因分成不同规格,遂令“五服”既可用于界定一个有限的宗族范围,又可区分宗族内部的亲疏层次。不过,汉代人用“五服”来划分亲属关系的实例较为罕见。冨谷至提出,秦汉家族缘坐以同居、同户籍为范畴,“五服”作为家族缘坐范畴是东汉末期开始的[17];邢义田认为,五服“不曾成为法律中界定家族亲属范围和权益的原则,也不曾真正普遍成为一般百姓生活中共守的规范”,主张“放弃单单从儒家服制看秦汉社会伦理的旧思维”[7]516、536。
上述观点有助于纠正将“五服”视作西周以降亲属伦理体系的观点。不过,否认“五服”对汉代社会的影响,似亦有矫枉过正之嫌。上博简《诗论》有云“吾以《折(杕)杜》得雀服”,晁福林释“雀”为“绝”,认为“雀(绝)服”为《礼记·大传》“绝族无移服”之意,即超出“五服”亲族关系[18]。战国时人或已用丧服等级来划分亲属关系了。不过,“五属”与“五服”在亲属范围上虽然一致,但汉代人几乎不用“服”来表示亲属关系,而多用“属”来表示[19]。以“五世”划分亲属范畴,似是当时一种较普遍的社会认识,上引《二年律令》关于可减刑宗室范围下及内玄孙的记载即可见。贾谊《新书·六术》载“人有六亲”[20],也“正是同姓直系五服内亲属”[21]110。“五属”是从此类社会认识中提炼出来的亲属范畴概念,而丧服“五服”则是儒家将之“礼制化”的结果。随着儒学作为政治文化进入汉廷,得到皇帝和朝廷公卿接受,丧服“五服”与“五属”联系起来,给属籍制度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
从传世文献来看,儒家“服制”的推行,始于武帝朝。武帝即位初,在窦婴、田蚡推动下,推行儒术改制,即包括“以礼为服制”和规范属籍[4]3439。司马贞《史记索隐》对此解释道:“其时礼度逾侈,多不依礼,今令吉凶服制皆法于礼也。”“以礼为服制”可能已涉及属籍制度。不过,这场改制以失败告终,“五服”伦理对属籍制度可能未造成实质影响。
武帝以降,丧服制度在汉朝政治中的影响逐渐增强。宣帝朝的石渠阁会议上,宣帝与诸儒探讨礼制,涉及丧服制度尤多。正如学人所论,这“反映出当时‘依礼行服’可能已是社会普遍的要求”[22],其结果则推动了“丧服的法律化”[23]。宣帝与朝臣对丧服制度的重视,无疑会强化“五服”伦理在属籍制度上的影响。元代龚端礼《五服图解》记载:元康二年(前64),宣帝与群臣“讲论丧服”,宣帝提出“古宗枝图列九族,世俗难晓”,谏大夫王章参考巴蜀养鸡所用鸡笼形状,画出一种五服亲属关系图——鸡笼图[24]。吴飞认为,“鸡笼图非常充分地展示出尊长五服图的复杂情况,直观而具体”,令人可“清楚地看到自己在丧服图中的位置”[25]。有关“鸡笼图”记载之真实性,或可争议;但就宣帝君臣对丧服制度的重视程度来看,当时出现此类丧服图则颇为可能。宣帝朝,丧服“五服”对亲属伦理的影响,当得到朝廷认可。
元帝以降的庙制改革,则进一步推动丧服“五服”观念走向实践。改革者贡禹、韦玄成、匡衡等,认为在位皇帝五世以外的宗庙“亲尽宜毁”[3]3116-3125,依据的正是丧服“五服”制度。比如《礼记·丧服小记》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16]1495;《礼记·大传》曰:“六世亲属竭矣。”[16]1507尤值得注意的是,匡衡将“五服”与“五属”联系了起来,上书有云“天序五行,人亲五属”[3]3122。庙制改革虽未尽全功,但随着改革的进行,皇帝、公卿逐渐认同“五服”界定的亲属结构,元帝诏书即称“盖闻明王制礼,立亲庙四”“立亲庙四,亲亲也”“存亲庙四,亲亲之至恩也”云云[3]3118、3120。这种观念必然影响到属籍制度,试想当朝皇帝五代以前的先帝尚被认为“亲尽”,要遭到毁庙,“五属外”宗室又有什么理由进入宗室属籍呢?在“五服”观念下,宗室属籍以在位皇帝“五属”为限,显得上合经典,下符人伦。
综上所述,武帝以来,丧服“五服”对亲属伦理和属籍制度的影响逐渐增强,至宣、元以降可谓尤甚。倘将视野拓展至出土文献,则可发现这一影响的发生时间或许更早。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有帛书《丧服图》,研究者对《丧服图》之图、文虽有不同理解,但存在两点共识:第一,《丧服图》图、文内容虽与《仪礼》《礼记》诸书载丧服制度有出入,但同样存在“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这一丧服“五服”差序等级;第二,《丧服图》与后世之“九族五服图”类似,划分了父系亲属层级[26]。马王堆三号墓葬于文帝十二年,以上两点共识表明,至晚在文帝朝,丧服“五服”已被用于划分亲属关系。而且,《丧服图》文字有云“三年丧属服”[27],有学者认为“属”指“有属”“五属内”[28]。倘此说成立,“五属”作为亲属范畴概念,已与“五服”建立联系。而这与上文推断文、景时期宗室属籍制度趋于完善,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要言之,汉朝属籍著录“五属内”宗室,可能本源自以“五世”划分有限宗族的一般社会认识。但随着儒学对汉朝影响加深,丧服“五服”渐与“五属”趋同,并给后者提供了礼学和经典上的支持,从而影响到汉朝属籍制度。当然,在亲属伦理方面,汉人仍习惯用“属”来表达。比如西汉刘向《列女传》称“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29];甚至东汉郑玄注《仪礼·丧服》亦曰:“亲,谓在五属之内。”[16]1124“五属”仍是汉人表述较近宗亲范畴之习用概念。
三、差序格局下的汉朝宗室管理
汉朝把宗室分为“五属内/有属”和“五属外/属尽”,并仅将前者著录于属籍,呈现出一种差序管理模式。《续汉书·百官志》称宗正“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9]3589;汉人胡广也称宗正“岁一治诸王世谱差序秩第”[9]3589。所谓“亲属远近”“差序秩第”,正是依据宗室成员与在位皇帝的亲缘关系来划分的。
《续汉书·百官志》称,郡国每年上计时要上报“宗室名籍”,而据东汉“甘谷汉简”,“五属外”宗室“受郡县管理,已经和普通编户无甚区别”,但仍拥有宗室身份[14]20。郡国所上“宗室名籍”应包括郡国内所有宗室,而不仅是“五属内”宗室。宗正则根据郡国每岁所上“宗室名籍”,更新宗室属籍,将新生的“五属内”宗室或“复属”宗室补入,将“属尽”或“以罪绝”宗室除籍。在皇位更替之际,宗正则要参考“宗室名籍”,按新帝之“五属”更新属籍。
《续汉书·百官志》称宗正“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即指掌管各诸侯王支系名籍,亦即胡广所言“诸王世谱”。清人姚振宗撰《后汉艺文志》,将“诸王世谱”视作一部著作,置于史部谱系类[30]。这可能误解了胡广之说。“岁一治诸王世谱差序秩第”,当指宗正将郡国每年上报的“宗室名籍”整理到各诸侯王支系名籍中。有学者认为“属尽宗室”著籍于当地,不上于宗室名籍[14]20-21。此说恐难以成立,相反有证据表明宗正所掌“诸王世谱”亦包含“属尽宗室”。首先,《汉书·平帝纪》提到平帝元始五年时,“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3]358;《续汉书·百官志》注:“哀平之际,刘氏遍于四海,宗正著录,遂以万数。”[9]3628如此庞大的宗室数量,显然不可能皆在“五属内”。不过,既然能统计数目,且由“宗正著录”,当存在某种专门名籍。其次,东汉建武二年(26)十二月,光武帝诏恢复王莽所废宗室列侯“故国”,若列侯身死,封拜其子孙[9]31。倘没有各诸侯王支系名籍,是无法做到这点的。最后,灵帝时,卢植上书论封建,称“今同宗相后,披图案牒,以次建之”[9]2114,可推论宗正职掌各诸侯王支系“图牒”,亦应包含“属尽宗室”。此外,上文提及汉朝“以罪绝”宗室不乏“复属籍”,当也是以宗正所掌“诸王世谱”为据。
简言之,宗正掌管的“宗室名籍”,除“属籍”外,还有“诸王世谱”。前者仅著录在位皇帝“五属内”宗室;后者则记载各诸侯王支系的宗室,包括“属尽宗室”。依据宗正所掌“诸王世谱”和郡国“宗室名籍”,宗室子孙即便“属尽”,不再著录于属籍,仍拥有宗室身份。汉朝宗室不仅被区别为“五属内/有属”和“五属外/属尽”,“诸王世谱”亦关注“王国嫡庶之次”、各诸侯王支系的“差序秩第”。显然,汉朝的宗室管理,极重亲属远近差序。《周礼》称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16]766,汉朝宗室管理同样“辨亲疏”,呈现出一种“差序管理模式”。
费孝通曾就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提出“差序格局”说,大抵指以自己作为中心,按关系亲疏,周围划分出不同层次的圈子[31]。杜正胜注意到“差序格局”与丧服“五服”结构的一致性[32];周丹丹、李若晖则认为“差序格局”“更近于昭穆制而非五服制”,前者“只论世次,不计亲疏”,而后者重亲疏远近[21]104-105。汉代宗室分为“五属”内、外,显然重亲疏远近。《续汉书·百官志》及胡广之说,明言汉代宗室管理注重“嫡庶之次”“亲属远近”和“差序秩第”,其以在位皇帝为中心,划分出“皇帝—皇弟、皇子(诸侯王)—有属宗室—属尽宗室”的亲疏层次,当是一种“差序管理”。杜正胜据“五服”将亲属划分成家庭、家族和宗族,“家庭的成员主要是父己子三代”,“大功以外至缌服共曾高之祖而不共财,算作‘家族’;至于五服以外的同姓虽共远祖,疏远无服,只能称为‘宗族’”[33]。照此说,“有属宗室”是皇帝家族范畴,“属尽宗室”则属皇帝宗族范畴。
汉朝宗室的差序管理,不仅合乎礼制,更有着实际功能。汉朝属籍著录“有属宗室”以在位皇帝“五属”为限,随着皇帝更替而变动。正如学人所论,“有属宗室”的数量增长,“应该不会很快”,“在汉代还不至泛滥成患”[15]。而“有属宗室”与“属尽宗室”,在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特权,都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在政治上,汉朝给“有属宗室”赐爵,比如《汉书·平帝纪》称平帝元始四年“赐九卿以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属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3]357。赐爵时,将“有属宗室”与“九卿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相提并论,且赐爵“五大夫以上”,已属二十等爵中高爵,显然“保护了宗室的特殊利益”[5]。
其次,在法律上,优待宗室主要针对“有属宗室”。《续汉书·百官志》称宗室“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9]3589。但从东汉“甘谷汉简”来看,五属内宗室“有罪请”,五属外宗室“便以法令治”[6]396。岳庆平指出《续汉志》所言“是指五属内宗室”,“非指所有宗室而说的”[34]。
最后,在经济上,宗室往往具有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但“有属宗室”的经济特权更突出。上文引《汉书》有关“有属籍”的材料,即有赏赐“有属宗室”马匹和复除等内容的记载。
在差序管理下,汉朝享受各种特权的主要是“有属宗室”,无疑减轻了特权者带给朝廷的负担。此即宋儒朱熹称赞汉代宗室管理的原因。
余 论
西方学者贾志扬对宗室有一个精到定位:“宗室绝非自然的宗族组织”,“它在本质上是专制政体的延伸,是皇帝出于皇权目的的造物,并为政治因素所塑造”[35]2。汉朝宗室属籍制度和差序管理,将宗室区分为“五属内”和“五属外”,无疑也是塑造宗室的产物,并构建起以皇帝为核心的宗亲体系。
“宗室属籍”和“诸王世谱”起到了凝聚刘姓宗室的作用。在汉代,父系意识尚未成为亲属伦理中唯一主导,母族仍有重要影响,作为实体组织的父系“宗族”甚至可以说不存在[36]。但“属籍”和“诸王世谱”的存在,令宗室诸刘依据父系具备特殊身份,推动宗室成员父系意识得以强化,遂使皇族成为汉代少有的实体宗族。《后汉书·孝殇帝纪》载诏书:“诸官府、郡国、王侯家奴婢姓刘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务令实悉。”[9]198令刘姓奴婢“皆上其名”,以备恢复他们的良人身份,足见东汉朝廷对刘姓宗亲的重视。
研究者评价汉代宗室管理道:
如果用以下两个标准来衡量汉代的宗室政策,它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是看它是否成功防止皇室后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第二,当皇帝的直系后裔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即位时,看它是否能够提供潜在的继承人[35]5。
汉朝对宗室施行差序管理,即解决了数量巨大的宗室带给朝廷的负担。“宗室属籍”和“诸王世谱”著录宗室世系、名讳,则有助于确保帝位和王侯爵位的继承。昭帝即位时,宗正“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4]2575,即展现了这一点。
总之,汉朝把宗室区分为“五属内/有属”和“五属外/属尽”,前者著录于“属籍”,享有政治、法律和经济特权,从而呈现出差序管理模式。汉代以降,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宗室管理虽有变化,出现从“名籍”到“谱牒”的发展[37],但基本遵循了上述原则,比如唐代皇室成员按“五服”区分为“宗”和“族”[38]。直至宋代,宗室管理才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大量享受特权的宗室遂成为宋朝政治和经济负担之一,因而受到朱熹等士大夫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