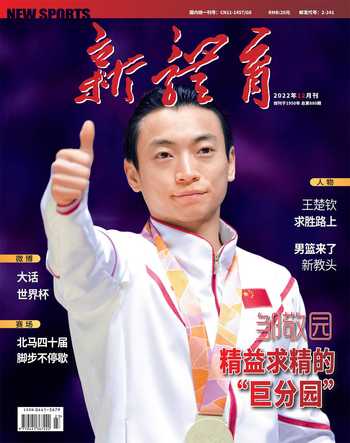北马四十届脚步不停歇
2023-01-03李战哲

2022年,第40届北马成功举办。
今年的北京马拉松是第40届比赛。在疫情背景下能够举行这么大规模的传统竞赛活动,再度感受万众奔跑的独特气氛和生命的活力,几十年长跑活动中的往事仿佛就在眼前。
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创办于1981年,由于疫情原因,中断了两年。这项比赛是改革开放后体育界的一件大事,当年由中国体育服务公司主办,日本三得利公司赞助。三得利跟公司签署了从1982年开始的十年赞助合同。这是首次进行现场直播的国际马拉松赛,只有几十名运动员参赛,国外选手有20多名,国内有39名运动员,北京市有3名运动员参赛。但是,观看比赛的观众大概有几十万人,在长安街两边为运动员加油。
后来,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改了地点,起点终点都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我正在铁道部党校上大专班,得知这个消息后,就积极做准备,加强业余训练。那时的训练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没有很好的运动装备,我训练穿的就是4块钱一双白色的田径鞋。
当时,脚经常受伤,因为田径鞋的鞋底儿很薄,我爱人为了避免我受伤,就给我剪了很多海绵垫子,垫在我脚底下,这样可以增加一些弹性。我每月训练跑量400到500公里,自己在公路上跑。我的教练崔云海老师是著名的北京春节环城赛三届冠军。他经常周末陪着我从北京邮电学院跑到颐和园,再折回来,30多公里,他骑自行车跟着我。
1982年的北京国际马拉松赛,给了北京市25个名额,参赛的运动员都是从各区选拔出来的,优中选优。北京市体委对我们这些运动员挺重视,专门抽调教练为我们组织周末集训,每天补助8毛钱伙食费,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不错了,每月工资才39塊8,伙食补助就达到了24块钱,几个月下来有100多块,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是很大一笔钱了,我们很珍惜这些经费。我的爱人很支持我,经常给我改善伙食,增加营养,这对训练也很有好处。
那一年有200名左右的运动员参赛,有三四十名是国外的特邀选手,其余就是国内各省的优秀马拉松选手。日本三得利公司赞助服装装备,耐克公司也提供一些装备。国内选手有内蒙古的单长明、上海的张远达、安徽的方嫩顺、云南的彭家正等,他们的水平是比较高的。国内运动员最好的名次就是彭家正,第15名。

1981年,第一届北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在天安门开跑。
我们从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发,跑向长安街,再一直向西,在花园桥折返,经过前三门回到工人体育场。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有几十万群众涌向长安街沿线,为我们加油,场面很壮观。虽然才有200名运动员参赛,但是我们受到了很大的精神鼓舞,感觉跑在路上很神圣和骄傲,那情景令我很难忘。
听说有一位作曲者创作了一首马拉松歌曲,很鼓舞人心,工人体育场里面播放这首歌,非常好听,“马拉松,马拉松,全世界人民的象征”,运动员起跑之前听到这首歌很振奋。
我们到赛场集中后,组委会发下新的跑鞋。每个运动员都得到了赞助的服装和运动鞋,是国外进口的。我们自己的跑鞋都是很低廉的,质量很差,训练量大了很容易受伤,穿上赞助商的跑鞋,大家跑起来非常有劲儿。年轻人穿上这些跑鞋和运动服,觉得特别时尚,特别精神,国内的产品达不到那个水平,很多没有参加北马的人都很羡慕我们。穿上新跑鞋新袜子比赛,太激动了。跑完之后,脚底下都磨起了大泡。后来,从1983年到1986年,我参加北马的时候,改成穿旧的跑鞋,再没有磨泡,教训变成了经验。我现在还保留着两件1983年和1984年北马发给我们的运动服,几十年也没怎么穿,就是做个纪念。
1982年的北京马拉松,我跑出了2小时46分48秒的成绩,排在第107名。这是我第一次跑全程马拉松,真要感谢观众给予的力量。
1983年的北京马拉松,天气很热,有人跑到最后虚脱了,有不少选手没能坚持到终点。我跑出了2小时49分01秒,获得第47名。

1982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成绩证书

1982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完赛奖牌

1984年北马发给每位参赛者的运动服

奖励给跑完世界六大满贯马拉松跑者的六星奖章,李战哲是中国第六位获奖选手。
我一直保留着1982年、1983年和1984年参加北京马拉松的奖牌,现在看,这些奖牌制作比较粗糙,质量也很一般,但它是很珍贵的历史纪念,代表着参赛运动员的心血。那时候,北京市坚持业余长跑的可能有几千人,每年举行春节环城赛跑,有2000多名业余运动员参加,长跑运动还是具有基础和传统的。
北京马拉松开创了中国城市马拉松的先河。城市马拉松在世界各地兴起很多年了,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是1897年创办的,到现在已经120多届了。世界上很有影响的六大马拉松,美国的波士顿、纽约、芝加哥,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柏林,日本的东京,都是有至少几十年历史的城市马拉松赛。北京马拉松也可以列入世界十大马拉松赛之一了。
前5届北马比赛过程中,当时没有好一点的照相机,什么照片都没有留下,只有媒体拍的一些照片,但是普通运动员拿不到这些照片,是个很大的遗憾。
北京马拉松圈儿里,有几个非常优秀的跑者,像邓乃龙、刘大勇、李燕琨、关宇、林玉山、郭光辉,都是我的跑友,40年前在一起参加各种马拉松赛。著名教练程军老师为我们这些业余马拉松选手做出了很多努力,坚持为我们进行各种辅导,每次都陪着我们一起训练,很辛苦。
关于北马的竞技水平,早期规定的“关门”时间是3小时15分,因为交通管制时间有限,到时还没跑完的就不算成绩了。由于参赛的大都是专业运动员,这个标准虽然很高,也还可以实行。经过几十年发展,比赛规模扩大了100多倍,报名人数限制在3万人,必须考虑到广大业余长跑爱好者的实际水平,放宽“关门”时间,今年北马的规定是6小时15分。其实,国外很多马拉松比赛,甚至世界六大马拉松比赛的“关门”时间都不会定在3个多小时,比赛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专业竞技是少数,业余参与是多数。
今年北马,我没有参加比赛,但是我特意到37公里处,为参赛的运动员加油鼓劲。37公里是跑马拉松最难受的“撞墙期”,这时候给运动员加油,送上一句鼓励的话,可能对他们都很有用。有不少跑友认出了我,叫“李老师好”,我很高兴。我为他们加油,他们也为我加油。
说到社会对马拉松运动的关注程度,当年比赛感觉和观众非常接近,可以清晰地听出观众为我们加油喊的什么,兴奋之情使人忽略了身体的疲惫。沿途的道路两旁站满了老百姓,不时有人伸过手来和运动员击掌。一方面是那时赛道没有现在这么宽敞,另一方面,有电视机的家庭还不多,想看到比赛盛况,就得上街。几十公里的赛程,运动员不过200多人,看上去像迎宾车队似的,一下子就从眼前跑过去了,只剩下越來越远的背影。市民为了看这么一眼,早早等候在马路旁边。那时候管理不那么严,人们自觉遵守比赛秩序,一点不影响比赛,我们真觉得离不开观众的支持。
现在的马拉松比赛,很多人选择看电视,甚至满足于从手机上了解信息,赛道宽敞了,运动员跟观众的距离也远了,对形成马拉松文化,将大众长跑融入城市生活,还是有所影响的。几十年来,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变化很大,道路拓展,大厦林立,很漂亮。不过,马拉松比赛运动员一路上哪有心思欣赏风光、景观、建筑,途经这些美景是设计路线时的刻意安排,但都不如观众的呐喊更起作用。一项马拉松比赛经过多年积累,能不能具有品牌效应,不光看竞赛水平,还要看比赛产生的社会影响。在这方面,北京马拉松应当发扬传统,带个好头。
今后,我以参加半马比赛为主,跑一些10公里、5公里的活动,把自己多年来跑马拉松的经验传给年轻一代,当好他们的顾问和教练,这是我应该做的。毕竟已经70岁了,到了这个年龄,一要坚持跑步,二要保养身体,这样才能更长久更健康地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