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曲无终
2023-01-03想听歌的
☉想听歌的
最前卫的实力派
对大多数人而言,坂本龙一是一位世界级的音乐家,他总是身着黑色服装,顶着一头优雅的银发,以及戴着标志性的黑框眼镜。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沉静、内敛和风度翩翩,似乎很难与叛逆、前卫、潮流扯上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年轻时的坂本龙一,可以说是亚洲最前卫的实力派音乐人。
1978 年,26 岁的坂本龙一与细野晴臣、高桥幸宏成立了先锋乐队YMO(黄色魔术乐队)。这支被东野圭吾形容为“天才”的乐队,是早期电子音乐的先驱,影响了各种不同的音乐流派。
在一段YMO 早期的影像中,坂本龙一身穿白色T 恤,搭配黑色西装马甲,一头黑发向后梳成大背头,随着音乐摇摆身子,眉眼间有种说不出的风华,他看起来既帅气又有魅力。有粉丝精辟地评论道:“沉浸在自我麻醉中的扬扬自得,一副不愿意清醒过来的样子。”
坂本龙一“教授”的绰号也是从那时传开来的。他是东京艺术大学的研究生,所以被高桥幸宏打趣:“东京艺大的研究生呀,以后肯定会是教授。”
这样的傲气似乎有迹可循。坂本龙一从小就沉浸在艺术和文学的氛围中,他的父亲是作家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的编辑。他从小受到正统的音乐训练,从6 岁起就开始接触艺术和古典音乐,学习绘画和钢琴。
在自传《音乐即自由》中,坂本龙一写了少年时期的自己。刚进中学时,他了解新同学的方法,就是逢人便问:“你知道披头士乐队吗?”如果对方不知道,他就不再理会这个同学。而当他在机缘巧合下听了德彪西的音乐后,逐渐将自己与德彪西混在一起,认为自己是德彪西转世,甚至反复在笔记本上练习德彪西的签名。
做100 年后人们还会听的音乐
1983 年上映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是世界各地的乐迷都不想错过的一部电影。
影片改编自南非作家劳伦斯·凡·德·普司特的小说《种子与播种者》,而比起原著,更迷人的是这部电影中的原声音乐。由坂本龙一创作的经典曲目《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广为流传,影响力甚至超越了电影本身。
彼时的坂本龙一还是个初出茅庐、异常傲气的年轻人,和现在谦和有礼的形象截然不同。当时导演大岛渚邀请他出演电影,他颇有些狂放地对大岛渚提出要求:出演可以,但条件是自己负责给电影制作音乐。
坂本龙一后来回忆说:“本来我想欣然接受导演的邀请,但我的性格比较别扭,于是我就跟他说,要是让我给电影配乐,我就扮演角色。”
坂本龙一的电影配乐生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赶上喧嚣、耀眼的电子时代,他的个人音乐创作正式进入高产期。

坂本龙一
参与《末代皇帝》的配乐工作真正让他在国际影坛声名远播。1988 年,坂本龙一凭此片获得第60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此后,他接连获得多项大奖。
然而,他的矛盾和挣扎也愈加凸显。坂本龙一不喜欢明星式的生活,他承认反讽和服装是抵挡注意力的盾牌,他每离聚光灯远一步,就会感到更快乐一些。
人们将“年少有为”“有才华”“大众的偶像”这些标签打在坂本龙一身上,但他说:“要用音乐去拯救别人,是绝对做不到的事。因为它就是一群认为自己无可救药的人所创作的悲叹曲。”
他一边否认着音乐,一边又创造着音乐,他不讳言自己的消沉,但他更奉行“悲观思考,乐观行事”。
对坂本龙一来说,找到自己想要的音色,或是任何一种有趣的、不同的声音,是他在音乐生涯中一直坚持的。而寻找“永恒的声音”这个想法,在他突然被确诊罹患癌症后愈加坚定。“我只做10 件事当中的那一两件,可能因为只有这一两件事,才是我真正想做的。100 年后,人们还会听的音乐,才是我想做的音乐。”
“与癌共生”的日子
2014 年,坂本龙一被确诊为咽喉癌三期,他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在声明中,他向那些在不同领域与他有合作的人道歉,“毫无疑问,因为我给所有人都添麻烦了”。
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展现了坂本龙一确诊咽喉癌前后5 年的工作和生活情景。
他因为癌症而过着克制和有规律的生活:癌症使得口腔中的组织非常容易感染,他非常仔细地刷牙,慢慢地吞咽食物,每天服下定量的药物。因为病情,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停下了创作,开始接受密集的治疗。
对于这段经历,他曾说:“几乎有一个月,我没办法聆听、演奏或者创作音乐,因为我太紧张了。”
治疗一段时间后,他开始陷入更大的焦虑,一方面因为整整一年没有创作而焦躁,另一方面又想尽全力治疗,尽量不让癌症复发。“我得小心防止癌症复发,能延长生命却没那么做是可耻的。”坂本龙一说。
第二年的春天,他接受了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的邀请,再次回归到音乐中,为《荒野猎人》配乐。半年后,他完成了这部电影的配乐工作,乐曲简单、纯净,大段的留白引领观众进入荒野猎人的内心深处,这无疑是坂本龙一患癌后的心声——浑厚饱满,沉重、悲悯以及宏大的时空感,配乐没有止步于绝望,反而迸发出在绝境里挣扎求生的强烈欲望。
他像一个敏感的浪漫主义者,一直在寻找自己喜欢的声音。《坂本龙一:终曲》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为了寻找合适的雨滴落下敲击物体的声音,他将一个玻璃罐放在门外,认真地倾听,然后拿回来告诉摄像师,瓶子太厚,没发出什么声音。他又换了一个塑料桶,将它举起来,套在自己头上。雨淅淅沥沥地滴落在那个套在头上的塑料桶上,坂本龙一显得无比虔诚。
但坂本龙一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几年前的一场采访中,他说:“我总是在意识深处问自己,什么是音乐?我们为什么要做音乐?这几乎是人类共同的话题,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总是关注每一件事。”
看到塑料垃圾导致海洋生物死亡时,他很悲观,但又相信人类还有希望。反过来,他“相信希望”,是因为他看到了“没有希望”的一面,他总是比别人看到得多。
“从2009 年左右开始,我就意识到了音乐中的死亡主题。”坂本龙一说,“钢琴声音的衰败和消失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生命的终结。这并不让人难过,我只是沉思着。”
他似乎对死亡持乐观态度。在很多次访谈中,他都引用电影《遮蔽的天空》中那句著名的台词:“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去,所以人们以为生命是一口不会干涸的井。但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限的,多少个迷人的童年下午,回想起来,还是会让你感到如此深沉的温柔?也许只有四五次,也许还没有。你还会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大约20 次吧,但这看起来无穷无尽。”
然而,生活像对他开了一个玩笑似的,他接受了数年咽喉癌的治疗,病情好转不久后,又被诊断出患有直肠癌。2021 年1 月21 日,坂本龙一发布消息称自己“已顺利完成手术”,正在接受治疗,手头的工作将在接受治疗的同时尽力去完成。而此后的日子,他将“与癌共生”。
病痛并没有结束,因癌细胞转移到肝脏和淋巴,2021 年10 月和12 月,他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切除直肠的原发灶和肝脏的两处转移灶,后又切除已有癌细胞转移的淋巴结。到目前为止,他身上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处理的所有肿瘤都已经被切除。但他的身体内依旧有病灶,并且还在不断增殖中。他与病魔抗争的日子仿佛看不到尽头。
2022 年6 月,坂本龙一在接受《新潮》杂志采访时透露,他的癌症已经到四期,也就是发展到病情的终末阶段。
“患上新的癌症,如今迎来70 岁,虽然不知道在今后的人生中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但算是难得的活下来了。我希望能像敬爱的巴赫和德彪西一样创作音乐,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坂本龙一说。
我做不到视而不见
“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弹奏一架溺水的钢琴。”
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的开场,坂本龙一弹奏着一架在2011 年日本大地震所引发的海啸中幸存的钢琴。
纪录片的一部分影像是他在福岛核灾区的现场奔走,鼓舞人们去反对日本政府的不作为。
他在原避难所——一所中学的操场举办音乐会。音乐会开始前,他温柔地说:“大家很冷吧,冷的话站起来活动一下也无妨,请以最舒服的方式听吧。”然后他弹奏了那首经典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
“我做不到视而不见。”坂本龙一自述道。
2001 年9 月11 日,坂本龙一在纽约的家中听到窗外传来几声巨响,便来到窗前,他看到慌乱的人群,而就在不远处,世贸大厦正冒着滚滚浓烟,整座城市笼罩在从未有过的恐惧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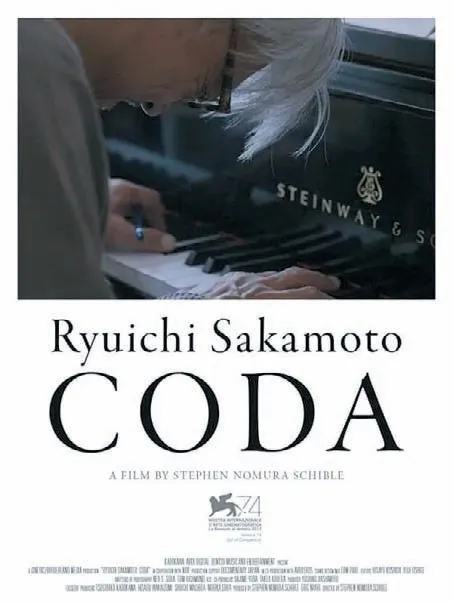
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海报
这之后的一周,包括音乐在内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他和身边所有亲历“9·11”事件的人一样,陷入无尽的沉默。
恐惧、无措、悲伤的情绪完全压制住艺术创作,坂本龙一当时甚至觉得在巨大的灾难面前,音乐的作用不值一提。可是,一个星期之后,当街上的悼念活动出现,年轻人在时代广场用吉他弹唱起披头士乐队的《昨日重现》,他才仿佛重新认识到:在悲剧面前,人类需要与之相反的力量继续前行,生与死之间需要一种介质去融通、和解,音乐正是作为这样的力量和介质而存在。
“9·11”事件激起了坂本龙一对于大自然力量的反思,他开始积极参与各种有关社会环境问题的公益活动,甚至跟着一群科学家前往北极考察气候变迁的实际情况,探寻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新的可能。他的环保主义是作为他的艺术的一个功能而呈现的。尽管他表示这和社会责任心无关,但从事这些活动,似乎都体现着他极力想把自我力量付诸某些社会现实的诉求,即使改变是极微小的。
2020 年3 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身处美国纽约的他通过预录好的30分钟即兴演奏视频与大家见面。当晚让无数中国观众感动的一个细节是,坂本龙一在演出当中所使用的乐器——吊钹,上面有“中国武汉制造”的字样,画面定格了几秒钟。演奏结束后,他直视着镜头用中文说了句:“大家,加油。”这个小惊喜,让网友感受到他对武汉乃至中国的关怀与鼓励。
回过头看,作为音乐家的坂本龙一,一生当中做了许多与音乐无关的事情。也许他想以此证明,音乐是可以让人撑过苦难的,但“如果只以此为目的,仅仅只是安慰、感动受灾者的话,音乐和艺术也就到此为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