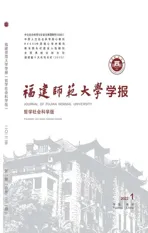“诗笔”叙事演进及其与赋体文学的互动
——兼谈传统叙事诗发展缓滞问题
2022-12-28孙敏强吴雪美
孙敏强,吴雪美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叙事笔法出现于先秦不同文献的书写中,是一种于诗、文、史皆通的书写技巧。先秦叙事依循文体殊异,有“史笔”“文笔”与“诗笔”之分途(1)学界对先秦叙事传统的研究,如陈文新(《论先秦时代的三种叙事类型》,《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第132-136页)将先秦叙事类型按史家散文、诸子散文和辞赋进行划分。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从先秦《诗经》、史传散文、诸子散文等文本书写方式探讨先秦叙事传统的形成。,并大致形成三条演进路径:一是入史传,二是入文体,三是入诗体。三种叙事笔法相互交融、共生互进而又各具特色。本文拟以“诗笔”叙事演进及其与赋之关系为核心,结合文学发展实际,论证“诗笔”叙事未在早期叙事诗体中发展起来,而是于汉初转入赋体文学创作之中,并将赋体铺陈特征推向高峰。此后,随着大赋衰落与赋体嬗变,“诗笔”叙事以赋为媒介,通过文体互渗从赋体转出,分化叙事诗体的发展方向。笔者试图以“诗笔”叙事演进为逻辑起点,以期为传统叙事诗发展缓滞现象的考察提供一种新的解读视角。
一、问题缘起与“诗笔”叙事内涵
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文化浪潮的兴起,西方文学理论与经典史诗文本译介和传入,国内学人在惊叹于《荷马史诗》结构之宏伟、语言之绚丽、神话体系之丰富的同时,反观中国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发现汉文学缺失《荷马史诗》般的长篇叙事诗,且认为上古时期神话凋零、不成体系。这一现象引发诸多关注,于是汉文献有无史诗文本、上古叙事诗何以不发达成为探讨的焦点。汉语“史诗问题”(2)林岗:《二十世纪汉语“史诗问题”探论》,《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31-142页。汉语“史诗问题”涉及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汉文献是否有史诗文本;二是汉文学为什么没有史诗;三是上古时期叙事诗为何长期处于发展缓滞状态。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被推上学术前沿。
在西方文论话语中,“史诗”相当于“叙事诗”。艾布拉姆斯(M.H.Abrams)将“史诗”概念界定为:“史诗(epic)或英雄史诗(heroic poem)在严格的意义上是指起码符合下列标准的作品:长篇叙述体诗歌,主题崇高庄重,风格典雅,集中描写以自身行动决定整部落、民族或人类命运的英雄或近似神明的人物。”(3)[美]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1页。相比西方较早成熟的叙事诗理论体系,中国古典文论对叙事诗的探讨起步较晚且不甚清晰。“叙事诗”一词最早见于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诗,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众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4)(宋)胡仔集纂、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 第221页。魏泰认为白居易《长恨歌》“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对其艺术价值评价不高。《朱子语类》评:“《生民》诗是叙事诗,只得恁地。盖是叙,那首尾要尽,《下武》《文王有声》等诗,却有反复歌咏的意思。”(5)(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2129页。朱熹弟子义刚将《生民》视为叙事诗。此外,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存《叙事诗话》条目,然已亡佚,内容不得而知。清代文学批评对叙事诗的探讨逐渐增多,然一直到清代末期,随着西方史诗文本的传入,传统叙事诗发展问题才成为热点话题。
本文对“诗笔”叙事的探讨,正是基于对“史诗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史诗问题”虽为中西方诗学碰撞下引发的学术命题,然而通过这一问题聚焦传统叙事诗的发展状况,至今仍备受关注。(6)学界对叙事诗发展问题的关注如:高永年:《由先秦至唐代:汉语叙事诗之成熟》,《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52-158页;陈来生:《中国传统叙事诗不发达原因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19-124页;陈来生:《说唱叙事诗与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状况的辩证考察》,《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12期,第87-91页;许并生:《先秦叙事诗基本线索及相关研究考察》,《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第139-143页;傅修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变革》,《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第60-68页。
先秦文献无“叙事”一词,“叙”和“事”指涉不同,将其连缀起来则有按照一定顺序叙述或记录事情之意。“诗笔”在文章学领域最早指向文学分类。魏晋有“文”“笔”之分。如刘勰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7)(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55页。有韵之“文”包括诗、赋等押韵体裁,无韵之“笔”指诏、策、书信、议论等无须押韵的体裁。随着南北朝诗歌发展与声律论的兴起,有韵之文体以诗歌、辞赋及骈文为代表,“诗”与“文”逐渐成为有韵之文的统称,而“笔”则演变为实用性散文的代称。古人通常将“诗”“笔”对举,如“三笔六诗”(8)(唐)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第594页。《梁书·刘潜传》记载,梁刘孝绰兄弟中孝仪行三,长于笔,孝威行六,长于诗,孝绰乃云“三笔六诗”。“沈诗任笔”(9)钟嵘《诗品》:“彦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后人“沈诗任笔”之说,指沈约以诗著称,而同时人任昉以表、奏、书、启等擅名,二人各有所长。这里“诗”指作诗笔法,“笔”指作文之章法与技巧。“晓笔暮诗”(10)(南朝陈)徐陵著、许逸民校笺:《徐陵集校笺》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78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曰:“夜琴昼瑟,是自娱怀;晓笔暮诗,论情顿足,其利三也。”“孟诗韩笔”(11)(唐)赵磷:《因话录》卷三,见李肇等撰:《唐国史补 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82页。原文曰:“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这里“诗”主要指诗歌创作技巧,“笔”则为散文创作技巧且偏向于实用性文体。宋赵彦卫云:“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12)(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5页。于此将“诗笔”与“史才”“议论”并称,论述唐代传奇小说创作文体特点。陈寅恪从创作技巧与表现手法角度将赵氏所论“诗笔”解释为:“所谓诗笔系与史才并举者。史才指小说中叙事之散文言,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其笔字与六朝人之以无韵之文为笔者不同。”(1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页。
为更好理解“诗笔”的叙事内涵,可将其与“文笔”“史笔”进行对比:“史笔”叙事“以文运事”,以《国语》《左传》等史传文学为代表,自“记言”至“记事”,“国别”至“编年”,“散记”至“专篇”,叙事特征与演变路径单向稳定,自成一脉,承载语言文字记录之功。“文笔”叙事“因文生事”,滥觞于商周甲骨卜辞、爻辞、铭文、盟诅辞等早期文本,亦以记事为主,至春秋战国以诸子散文为代表,述情说理、引典征史、虚实相生,叙事笔法不拘一格。反观“诗笔”叙事,发展于早期叙事性诗歌文本,以“诗”为体,取“诗体”语征,使“诗笔”铺陈,融诗之句式、对偶、声韵、唱诵、修辞等形式特征,构成区别于“史笔”“文笔”叙事的独特内涵与艺术技巧。简言之,“诗笔”叙事即以诗之语言、诗之形式、诗之审美进行创作的书写笔法。
综上,“诗笔”叙事源起于诗歌体裁,于叙事诗体中演进与发展。那么,早期叙事性诗篇发展状态如何?“诗笔”叙事对叙事诗的独立与发展又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以下将要论述的主要问题。
二、叙事诗不发达与“诗笔”叙事的消融
王国维云“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14)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96页。,认为传统叙事诗发展到元明时期,仍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15)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96页。,指出叙事诗发展缓滞问题。胡适持相似之论:
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少见的一个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实是仅有风谣和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世;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16)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胡氏认为“故事诗(笔者按:即叙事诗)在中国起来的很迟”,并将其归咎于汉字书写尚简,以及先秦简牍、绢帛等文献载体不适宜长篇书写。此后就“史诗问题”的探讨,国内学者将目光转移至《诗经》文本,以冯沅君、陆侃如提出“周的史诗”一说为典型代表。其文曰:
我们若把《生民》,《公刘》,《绵》,《大明》,《出车》,《采芑》,《江汉》,《六月》,《常武》等十篇合起来,可得一个大规模的“周的史诗”。……我们常常怪古代无伟大史诗,与他国诗歌发达情形不同。但我们若肯自己安慰自己,作“聊胜于无”之想,则上列十篇便是很重要的作品。说也奇怪,我们要想在这十篇以外另找一篇记载周代大事的诗,再也找不着了。这样整齐的篇数(十),使我们疑心原作者有意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周的史诗”的,不过被不解事的人拆散罢了。(17)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上),参见袁世硕、张可礼主编:《冯沅君陆侃如合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64-66页。
冯、陆将《大雅》中《生民》《公刘》《采芑》《江汉》等叙述周人历史且具叙事性的组诗称为“周的史诗”,认为它们具有史诗性质的、是小规模的、没有缀连成长篇的史诗文本,并从文学技术“缺乏想象力”“缺乏组织力”等角度,解释汉语史诗文本缺失原因。
文学史撰写者普遍承认《大雅》周族史诗为先秦叙事诗文本。(18)详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4页;刘大杰:《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40年,第28页;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5页;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6-88页。同样,不少《诗经》研究学者亦将周族史诗视为不发达之叙事诗。如褚斌杰认为:“若一定以荷马史诗为标准衡量,那么无须讨论,《诗经》中的确没有那么长的叙述历史传说的史诗。”(19)褚斌杰主编:《〈诗经〉与楚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8页。叶舒宪云:“我们在《大雅》中看到的《生民》、《公刘》、《绵》、《皇矣》、《文王》、《大明》六首诗,从相对的意义上说,都是发育不全的史诗性质的作品。”(20)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3页。陈来生认为:“在《诗经》里已能见到一些史诗篇章,甚至在《尚书》里也能看到原始史诗的影子。不过,《诗经》里的那些史诗,虽然已经具备史诗的一些基本条件,但不论从篇幅、容量还是艺术表现手法上看,都还很简短落后,远远够不上发达史诗的标准。……中国古代史诗既不发达,又不长大,只能属于不发达史诗的范畴。”(21)陈来生:《史诗·叙事诗与民族精神》,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2、3页。明确指出《诗经》叙事诗是不发达的叙事诗文本。
从“史诗问题”角度考量先秦叙事诗的发展问题,并不偏离中国文学发展实际。早期“诗笔”叙事以《诗经》为依托,具体指涉作品有《生民》《公刘》《皇矣》《大明》《绵》五篇,以及《崧高》《烝民》《韩奕》《思齐》等叙述周人政治历史的诗篇。其中“周的史诗”以铺陈为主,纯用“赋”笔,不假比、兴,因而被视为先秦最早的叙事诗文本。
需要说明的是,《诗经》中的叙事诗没有发展起来,其叙事性特征在先秦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及礼乐文明构筑的文化母体中被消解,失去了如西方史诗“再创作”之机会,无法敷衍成长篇叙事。如葛晓音所论:“《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叙述后稷建国到武王灭商的周代创业史,既有类似民族史诗的内容,形式也颇接近于后代的叙事诗,可见叙事诗早在周代已经萌芽,只是从《诗经》到乐府的四百年里,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民歌数量极少,从中几乎找不到叙事诗发展的线索而已。”(22)葛晓音:《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社会科学》1984年第12期,第64页。就传统叙事诗不发达的原因,学界论述颇多。如朱光潜认为儒家理性文化是导致长篇叙事诗不发达的重要原因。(2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52页。陈来生认为古代经济生产方式与政治文化限制了叙事诗体的发展,此外“史诗作为一门语言艺术,与古代语言文字的关系特别密切。……《诗经》二二拍的声音节奏,限制着诗歌的意义节奏,使其容量、篇幅和具体描绘等方面都受到限制”(24)陈来生:《史诗·叙事诗与民族精神》,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2、3页。,亦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解释。饶宗颐指出:“古代中国之长篇史诗,几付阙如。其不发达之原因,据我推测,可能由于:(一)古汉语文篇造句过于简略,(二)不重事态之描写(非Narrative)。”(25)饶宗颐:《澄心论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8页。再如“哲学思想平易与宗教情操浅薄说”(26)此说以朱光潜《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一文为代表。“儒家理性思维限制说”“先民想象力匮乏说”(27)鲁迅于《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上古先民“故重实际而黯玄想,不更能集古传而成大文”。(《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24页)“汉字尚简及书写隐晦说”(28)胡适、饶宗颐等持此说。“抒情诗占据诗歌创作主流说”(29)持此说者众多,为传统叙事诗不发达最常见的解释之一。等,皆各有所据。
于此引述前贤之论,主要在于阐释两个基本问题:一、《诗经》中的周族史诗为先秦时期没有发展起来的叙事诗;二、“诗笔”叙事源于《诗经》叙事诗文本,却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而是走向了消融之势。须知,从史诗角度探讨先秦叙事诗发展问题尚不全面,因为先秦时期具有叙事性质的诗篇还包括“国风”中的篇章,如农事诗《甫田》《七月》、婚恋诗《静女》《溱洧》等。“诗中叙事”与“叙事诗”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需要谨慎处理。《诗经》以抒情为传统,抒情诗亦可叙事,然叙事诗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则不包括以抒情为主导而辅以叙事的篇章。本文思考先秦叙事诗发展与“诗笔”叙事演进之关系,“诗笔”叙事笔法主要指向叙事诗,而非“诗中叙事”即带有叙事性特征的诗篇。
三、入于赋体:“诗笔”叙事转移及发展成熟
“诗笔”叙事作为一种颇具生命力的书写笔法,在早期叙事诗文本中得不到发展,形成于战国末期的赋体文学成为其演进的新机遇。以下从两汉诗歌发展、赋与《诗》之关系、赋体特性及赋的诗化等角度进行说明。
第一,汉代叙事诗发展状况。两汉诗歌以乐府诗和文人诗成就最高。诗歌创作叙事笔法集中于汉乐府,“盖乐府多是叙事之诗,不如此不足以尽倾倒,且轶荡宜于节奏,而真率又易晓也”(30)(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67页。。如《东门行》《妇病行》《十五从军征》《相逢行》等,最引人注目的是长篇叙事诗《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后者是现存最长的叙事诗篇,王世贞评价:“《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31)(明)王世贞著,陆洁栋、周明初批注:《艺苑卮言》,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30页。然汉乐府采自民间,内容围绕底层民众生活“苦与乐”“爱与恨”“生与死”等主题,格调清新,语言活泼,句式长短不一,以新体裁的形式出现,更接近于《诗经》中的“风”诗,与庙堂颂赞周族史诗之庄重整肃不同,非先秦叙事诗流脉。从内容与题材角度而言,乐府叙事性诗篇与《诗经》周族叙事诗迥然有别。回顾文学发展史,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叙事诗直到唐代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乃至清代吴伟业“梅村体”的出现才逐渐成熟,其发展的缓滞性明显可见。
第二,赋与《诗》之关系。班固从讽喻角度将赋视为“为雅颂之亚”,从赋体渊源阐释赋与《诗》之关系。此外,还有一种较常见说法,即赋体是从《诗经》“六义”直书其事之“赋”笔演变而来。学界对赋与《诗》关系的探讨,为“诗笔”叙事转入赋体提供了间接的论证。如马积高提出“诗体赋”的概念,其曰:“用三百篇中的诗体作赋始于屈原的《天问》。荀况《赋篇》中的《佹诗》、《楚申君赋》也是诗体赋。”(32)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页。他认为早期的诗体赋句式承袭自《诗经》,汉初诗体赋以四言句式为主,篇幅简短,语言质朴典雅,与骋辞大赋华丽辞藻不同,如邹阳《酒赋》、刘安《屏风赋》、扬雄《逐贫赋》等融入大量情感的书写,抒情与叙事相融合。随着汉末抒情小赋及文人诗的兴起,魏晋辞赋进一步抒情化与诗化,在诗歌声律论的推动下,赋体中的五言、七言句式与文人诗之句式十分接近。如曹植《蝙蝠赋》、左思《白发赋》“以诗为赋”,语言诗化十分显著;沈约《愍衰草赋》有一半以上的句式为五言,与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十分接近;庾信《小园赋》以“小园”意象为中心,在对景物的铺陈中抒发个人情怀,抒情言志与写景叙事融为一体。以上都是赋体诗化的表现。
第三,赋体之叙事。刘勰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33)(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34页。(《文心雕龙·诠赋》)李善曰:“赋以陈事,故曰体物。”(《文选注》)祝尧谓:“人徒见赋有铺叙之义,则邻于文之叙事者。”(34)(元)祝尧:《古赋辨体》卷九,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36页。从文体演进来看,每一种文体从诞生到成熟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赋却不是如此,它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并迅速繁荣,然后开始嬗变并走向衰落。这其中的缘由无疑是复杂的,然赋体用诗之语言进行铺陈,这与“诗笔”叙事笔法在赋体的发展不无关系。“诗笔”叙事在《诗经》叙事诗文本中是不成熟的,在四言句式束缚下,整齐划一、篇幅简短。如《大雅·生民》通篇四言为主,偶有以“诞”字领头的五言句,“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后稷之穑”(35)④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见十三经注疏编委会:《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1、1255、1144页。,故事叙事、人物描写、情节变化等皆简洁明了,没有铺叙开来。
最后,“诗笔”叙事于赋体中的演变。一、“赋”笔入赋:“简叙”变“繁铺”。《大雅》周族史诗为轮廓式叙述,着重对全局进行概况。如写战争场景:“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④寥寥几句就将武王陈师牧野的宏大场面渲染出来。然汉赋铺陈变“简叙”为“繁铺”,穷尽图貌之极,如司马相如所言“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将铺陈笔法发挥到极致,充分扩展了汉赋题材与内容。二、句式入赋:“四言”变“杂言”。汉赋延续“诗笔”叙事句式特点,将“四言”句式纳入赋体,然在散文性质与创作技巧影响下,衍生出五言、六言、七言等不同形式的句式,打破了《诗经》传统四言的束缚。“汉代四言赋拟效《诗》‘四言’,但却去除了《诗》四言的‘雅正’风格,而出之以‘游戏之言’。四言的‘雅言’传统,被以赋为代表的‘直言’传统赓续,由此带来了文本载体句式的变迁,突出征象是汉赋用《诗》将‘四言’改造为‘五言’‘七言’和‘六言’骈化。”(36)王思豪:《汉赋用〈诗〉“四言”之拟效与改造》,《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第38-48页。在两汉辞章之盛趋势下,“诗”的句式得到丰富与发展。三、韵律入赋:“韵字”变“韵语”。《大雅》周族史诗押韵相对简单,仅对句尾“韵字”有要求,然汉赋中的押韵情况较为复杂,具有一定规律性,用语方面追求“声对”“义对”“典对”等具有一定体系的韵语,不再是简单的句尾“韵字”。四、诵唱入赋:“乐唱”变“诵读”。先秦“诗笔”叙事将《诗经》唱诵节奏移植到赋体,然由于赋体容量的扩增、篇幅的扩大,“配乐演唱”演变为诵读。以上为“诗笔”叙事转入赋体从而带来创作的发展。
综上,赋作为一种独立体裁,用“诗”的语言极尽铺陈之能事,“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竟为奢丽闳衍之词”的书写方式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汉以后,赋体创作题材仍不断拓展与创新,然赋体铺陈逐渐弱化,“诗笔”叙事在大赋体制中难免遭遇瓶颈,“赋在叙事这个方向上逐渐走向了穷途末路。然而必须看到,赋倒下之后以自己庞大的身躯孳乳了后起之秀”(37)傅修延:《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第26-38页。,开启了不同文体交叉互动、古代叙事理论与古代文论并进(38)方志红:《论古代叙事理论对当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借鉴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78-82页。的新局面。
四、出赋路径:“诗笔”叙事演进与文体交互
赋与不同文体的交互是辞赋演进中的常态。“诗笔”叙事通过文体互动从赋体转出且“多途取道”:“以赋为文”“以赋为诗”“以赋为词”“赋入戏剧”“赋入小说”等,将诗体之铺陈笔法融入不同体裁的创作之中,分化叙事诗体发展方向。
其一,“以赋为文”,文章创作对赋体养分的吸收与接纳。“以文为赋”和“以赋为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体现文体对赋体的影响,后者主要反映辞赋对文章创作的渗透。赋的综合性特征是实现其与不同文体互动的前提,“中国文学上的分类,一向分为诗、文二体,而赋的体裁则介于二者之间,既不能归入于文,又不能列之于诗。可是,同时另有一种相反情形,赋既为文,又可称之为诗,成为文学上属于两栖的一类”(39)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0页。,这一属性促使赋体可以游走于诗文创作之中。赋于诞生之初,即受诸子散文、纵横之文的影响,以“文”的体式组织“诗”的语言,反过来影响“文”的创作。宋项安世云:“大抵屈、宋以前,以赋为文。庄周、荀卿子二书,体义声律,下句用字,无非赋者。自屈、宋以后为赋,二汉特盛,遂不可加。唐至于宋朝,复变为诗,皆赋之变体也。”(40)(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2页。项氏认为铺陈叙事是文章创作的重要笔法,汉赋将其发挥到极致,乃至唐宋诗歌的创作都受到赋体的影响。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
长卿《子虚》诸赋,本从《高唐》物色诸体,而辞胜之。《长门》从《骚》来,毋论胜屈,故高于宋也。长卿以赋为文,故《难蜀》、《封禅》绵丽而少骨;贾傅以文为赋,故《吊屈》、《鵩鸟》率直而少致。(41)(明)王世贞著,陆洁栋、周明初批注:《艺苑卮言》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王氏认为司马相如《难蜀》之绵丽文风是“以赋为文”的结果,贾谊引文入赋,故其骚体赋“率直而少致”。清刘熙载谓“用辞赋之骈俪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此后邹阳、枚乘、相如是也”(42)(清)刘熙著、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2页。,认为两汉赋家的文章创作受到辞赋句式的影响。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云,“枚乘抽其绪,邹阳列其绮,相如骋其辔,子云助其波。气则孤行,辞多比合;发古情于腴色,附壮采于清标,骈体肇基,已兆基础”,(43)(清)刘开:《孟涂骈体文》卷二,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96页。指出文章的骈俪化趋势始于汉赋,魏晋骈文的形成亦是赋体走向文体的结果。从文学史演进实际分析,骈赋与骈文的发展几乎处在同一阶段,皆重视文本对偶、用典、辞藻、音律等特征,创作手法亦相当接近。此外,清代骈文集中收录了大量辞赋篇章,如王友亮《双佩斋骈体文集》收赋11篇、高继珩《养渊堂骈体文》收赋5篇、乐钧《青芝山馆骈体文集》收赋6篇、胡承珙《求是堂骈体文》收赋4篇,这一现象亦体现赋与骈文的交互,以及清人对“赋”与“文”之文体边界的扩容。
唐宋古文创作对铺陈笔法亦颇为重视。唐柳宗元曰“前再上表,请加尊号,实以功德俱茂,典礼宜崇,然而不能铺陈,无以动寤”(44)(唐)柳宗元:《柳宗元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55页。(《为文武百官请复尊号表》),从奏疏文角度说明铺陈的重要性。“以赋为文”最直观的表现是增强文体叙事与铺陈特征。欧阳修《醉翁亭记》为“引赋入文”的典型,该文注重对场景的铺叙,语言典雅,多用对偶,句式工整,融入了骈体赋创作的形式特点。祝尧曰:“后代之文,间取于赋之义,以为文名;虽曰文,义实出于赋,故晁氏亦以为古赋之流。所谓流者,同源而殊流尔。”(45)(元)祝尧:《古赋辨体》卷九,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35-836页。其《子虚赋》题注云:
此赋虽两篇,实则一篇。赋之问答体,其源自《卜居》《渔父》篇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此体遂盛。此两赋及《两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盖又别为一体,首尾是文,中间乃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辞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便,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性情益远,六义澌尽,赋体遂亡。(46)(元)祝尧:《古赋辨体》卷三,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49-750页。
祝尧认为“后代之文,间取于赋之义”,赋体对文体创作影响深远,后世文章或从赋中取材,或借鉴赋的铺陈技巧,从而走向注重对偶的骈俪化趋势。此外,《两都赋》《二京赋》《三都赋》等大赋中以散体形式书写、具有说理性质的序言或篇尾论辞,发展至宋代,在宋人好议论文风的影响下,赋体与散文进一步交融,“以文为赋”和“以赋为文”并行发展,赋体铺陈逐渐弱化,以议论说理为特征的新文赋悄然兴起。总之,赋与文的交互是“诗笔”叙事转入文体创作,与“文笔”合流的重要方向与路径。
其二,“以赋为诗”,“诗笔”叙事回归诗体,诗歌创作对铺陈笔法愈加重视。魏晋时期山水诗开始兴起,文人对山水的刻画重在描摹,主动借鉴枚乘《七发》、班固《终南山赋》、蔡邕《述行赋》等对山水景物的描绘技巧,“汉魏时代赋最盛,诗受赋的影响也逐渐在铺陈词藻上做功夫”(47)朱光潜:《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1页。,因而魏晋山水诗具有“巧构形似,穷形尽相”的艺术特色,如谢灵运的庄园山水诗与远游山水诗吸收了赋的特点。初唐“四杰”在六朝抒情小赋影响下,创作了大量的长篇歌行,如王勃《临高台》、卢照邻《长安古意》等。骆宾王《帝京篇》是“以赋为诗”的典型,该诗用长篇七言歌行叙写帝京盛况,借鉴京都赋的铺排方式,如其开篇:“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48)(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王群栗标点:《骆宾王集》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9页。以赋体铺排的笔法描绘长安的壮阔景象。《帝京篇》在语言上融合了诗与赋的特征,全文多用双声叠韵,注重对偶与辞藻。再如中唐韩愈《南山》诗,此篇亦为唐人“以赋为诗”的代表之作。《南山》以长篇五言叙写三次游历终南山的经历,诗中对终南山壮丽的景色进行铺排,尤其代表了韩愈险怪奇崛、铺张排宕的风格。如文中对山势的描写:
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辏。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或背若相恶,或向若相佑。或乱若抽笋,或嵲若炷灸。或错若绘画,或缭若篆籀。或罗若星离,或蓊若云逗。(49)(清)方世举著,郝润华、丁俊丽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2页。
此段文字与汉赋对景物的铺排十分相似。宋人云:“读谢灵运诗,知其揽尽山川秀气。读退之《南山》诗,颇觉似《上林》《子虚赋》,才力小者不能到。”(50)(宋)胡仔集纂、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第8页。引文出自“国风汉魏六朝下”中《雪浪斋日记》条。项安世《诗赋》亦云:
尝读汉人之赋,铺张闳丽,唐至于本朝,未有及者。盖自唐以后,文士之才力,尽用于诗。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叙事丛蔚,写物雄丽,小者十余韵,大者百余韵,皆用赋体作诗,此亦汉人之所未有也。(51)(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2页
项氏认为李、杜“叙事丛蔚”之歌行“皆以赋体作诗”,吸收了赋体铺陈的特点。宋人作词亦十分重视铺陈与叙事笔法。如李清照云“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词论》),认为晏殊、贺铸词虽好,却缺少铺陈叙述。王灼云:“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52)(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4页。柳永之词擅长铺叙,于叙事写景中融入情感的表达,进一步将词体雅化。总之,“以赋为诗”的创作实践是“诗笔”叙事笔法从赋体入诗,将赋之铺陈特征融入诗歌体裁的生动表现。
其三,“赋入戏剧”,“诗笔”的介入使剧本创作诗化与雅化。作为一种叙事体裁,戏剧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问答与宾白,作者主要通过虚构场景与人物对话来展现故事的进展与情节的变化,这与汉赋的设辞问答极为相似,二者在体制上有共同点。以《子虚》《上林》为例,此二篇虚构了“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之间的对话,以人物铺陈讲述的方式结撰赋篇,这与后世戏剧中人物的宾白与对话可谓异曲同工。清刘熙载云“词如诗,曲如赋”(《艺概·词曲概》),从语言角度说明戏剧铺叙的特点。总体而言,赋对戏剧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剧本中大量引入赋典。如汤显祖《牡丹亭》中就有多处援引自辞赋典故。第一出《标目》云“三年上,有梦梅柳子,于此赴高唐”,“赴高唐”引自宋玉《高唐赋序》,借楚怀王游高唐与巫山神女幽会之事,喻指男女恋情;第二出《言怀》云“无萤凿遍了邻家壁,甚东墙不许人窥”,借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之典故,表达柳梦梅对爱情的真挚与专一。第二,赋文入剧本,即用赋体的形式对戏剧中的场景进行刻画。如高明《琵琶记·朝辞》第十六出“点绛唇”后有六百多字的大段宾白,后人称之为“黄门赋”。其文曰:
银箭铜壶,点点滴滴,尚有九门寒漏;琼楼玉宇,声声隐稳,已闻万井晨钟。曈曈曚曚,苍茫红日映楼台;拂拂霏霏,葱蒨瑞烟浮禁苑。袅袅巍巍,千寻玉掌,几点瀼瀼露未晞;澄澄湛湛,万里璇穹,一片团团月初坠。三唱天鸡,咿咿喔喔,共传紫陌更阑;百啭流莺,间间关关,报道上林春晓。(53)(元)高明著,胡雪冈、张宪文辑校:《高则诚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0页。
这段文字描绘蔡邕早朝升殿的景象,叠字排句较多,纯用赋体铺陈笔法,音韵协调、抑扬顿挫、雅俗混融。清人毛声山评价《琵琶记》“丹陛陈情”一节:“此篇即黄门一赋,已是绝奇绝妙文章,看他连用无数双声叠字,此四六中之创格也。”(54)(清)毛声山:《毛声山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见侯百朋编:《〈琵琶记〉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47页。“今读东嘉黄门赋,则诗词中之奇句,不得专美于前矣!”(55)(清)毛声山:《毛声山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见侯百朋编:《〈琵琶记〉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47页。充分肯定“黄门赋”于创作上的成就。剧本借用赋典或“引赋入文”的书写方式,实现了戏剧语言的雅化与诗化,这也是“诗笔”叙事渗入戏剧文本中的表现。
其四,“赋入小说”,“诗笔”使小说文本呈学问化与诗意化。小说是成熟较晚的一种文体,至明清才开始繁荣,其语言俚俗、诙谐,内容以虚构为主,因而发展早期的文学地位不高。赋与小说在虚构方面具有相似性。明人胡应麟云:“子虚、上林不已,而为修竹、大兰;修竹、大兰不已,而为革华、毛颖;革华、毛颖不已,而为后土、南柯。故夫庄、列者诡诞之宗,而屈、宋者玄虚之首也。后人不习其文而规其意,卤莽其精而猎其粗,毋惑乎其日下也。”(56)(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75页。胡氏的见解比较独特,他认为小说的虚构性可追溯至辞赋,然后是诗文,小说和辞赋同源异流,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的虚构景象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想象的空间。郭绍虞认为“假使明白小说与诗歌之间本有赋这一种东西,一方面为古诗之流,另一方面其述客主以首引,又本于庄、列寓言,实为小说之滥觞,那么对于小说与诗歌的混淆,便不成问题了”(57)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87 页。,从问答与虚构的角度阐释小说与赋的关系。
从创作实践来看,魏晋志怪文本中有以山川地理、域外方物等为题材的“博物”之作,如《玄中记》对远古神话、精怪故事、他乡异民等的刻画,与汉代“游仙赋”的虚构内容极其相似。再则,小说家将辞赋引入小说的内在动机是提高小说的文体地位,让小说和赋一样具备彰显才学的功能。赋对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言的书写,“援据赋典、摘引赋句、化用赋意、结撰赋篇、申言赋论”(58)丁涵:《以辞赋为“说部”——论〈花月痕〉小说中的用赋艺术》,《明清小说研究》2020年第2期,第193-209页。,使文本创作学问化。如唐代李玫《纂异记·许生》对鬼魂相聚于甘堂的场景,用诗之笔法对五鬼饮酒赋诗的场面进行了细致刻画;《梅妃传》叙梅妃与杨妃争宠之事,梅妃为重获皇帝恩宠,亲作《楼东赋》以表明心意,其文哀怨婉转,生动传达了梅妃的境遇。明清小说,《西游记》用短篇赋作对景物的描写,刻画灵动,极具诗情画意;《镜花缘》有关于习赋和考赋的专门描述,女科殿试中的《天女散花赋》即“可冠通场”;《花月痕》则大量出现与赋相关的片段,如化用辞赋中的典故、引用前人辞赋或在文中植入赋篇,如第二十三回中的《菊花赋》的书写,使小说语言尽可能雅化了。
总之,小说创作引入赋体创作的案例不胜枚举。须知,古典小说对赋的运用与借鉴是多元的,“其范围由文言而白话,由短篇而长篇;形式由夹杂在叙述性的文字中变为独标出,内容由传统的基本题材,拓展向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用则由单纯的景物描写,发展成兼具抒发情感、沟通情节、寓示创作意图等多种用途,从而使赋体文成了古典小说创作中不可忽视和低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9)曹明纲:《赋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57-258页。,由此“诗笔”以赋为媒介进入小说文本,不仅彰显了作者才华,也增强了小说叙事的诗意化特征。
五、结语
文学创作体裁有别,技巧却是互通的。“诗笔”叙事作为源起于先秦时期的一种书写笔法,其演进路径与赋体文学密切相关。汉初,赋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并迅速繁荣,成为两汉“一代文学之胜”,得益于其众体兼备的文体特点及“诗笔”叙事的发展。汉末,随着抒情小赋兴起,赋体文学逐渐走向诗化或骈化,“诗笔”叙事将诗的属性特征充分吸收到赋的创作之中,韵律开始成为衡裁赋体的重要标准。汉以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体裁相继兴起,赋与不同文体之间的互渗愈加明显,有纵向并行的发展,也有横向交叉的扭结。以宋代文坛为例,“‘破体为文’的种种尝试,如以文为诗、以赋为诗、以古入律、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赋为文、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等,令人目不暇接,其风气日益炽盛”(60)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7页。,文体发展与嬗变随处可见赋的痕迹与踪影。
总之,“诗笔”叙事正是在文体交互的过程中,完成“入赋”与“出赋”的演进路径,这也间接影响了传统叙事诗的发展:一是“诗笔”叙事笔法进入赋体,转移了早期叙事诗文本的发展空间;二是“诗笔”叙事从赋体转出,分化了叙事诗体的发展方向。于此再次审视“史诗问题”,汉文献缺失西方《荷马史诗》般的长篇叙事诗,虽不免有些遗憾,然中国古代有璀璨夺目的辞赋文学,有体系庞大的史传文学,“诗笔”与“文笔”“史笔”相互融通,共同构筑了古典叙事文学的独特景观与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