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妈妈
2022-12-26臧蔓
我从小就非常依恋妈妈,依恋家。对那时的我来说,“家”这个词的意义是有妈妈的地方便可称之为家。在我的记忆里,妈妈的周身总是围绕着温暖的空气,凝结着甘美的雨露。妈妈的身体所带出来的温热包裹着细腻、美好、幸福的感觉。我依恋妈妈的身体,柔滑、细致,隐藏起毛孔的皮肤没有一点突兀的转折,像水流过鹅卵石那样圆润地趟过去,消失在视线背后的圆弧外。妈妈的身体总是温热的,散发出的雾气持续地吸引我,让我不由自主地围绕着妈妈的身体转圈,一万圈、一亿圈……我吸收着雾气里的养分。
由于妈妈的身体原因,我三个月就断奶了。妈妈为了让我喝上新鲜的母乳,总是把我抱到和她一起怀孕生子的好朋友那儿,让我试着喝她的奶水。妈妈后来告诉我,那位阿姨有喝不完的奶,乳房总是胀得生疼。可我拒绝饮用那片乳汁的大河,不管她俩用什么方法都不行。那会儿,我只要一待在妈妈的怀里就会发出“呼呼”的声音,颤抖地试图凑向妈妈的乳头,总是探寻,但却得不到。可能在那时,我就在妈妈的体内种下一颗渴望的种子,随时等待从那收获什么。

我生长在一个和谐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和善负责的人。总体来讲,我是个幸福的孩子,不缺少爸爸妈妈对我的爱。但可惜的是,我缺乏和他们共同生活的经历和交流的机会。我的爸爸可谓一个创业家,他精力充沛,从不停下前进的脚步。他的事业让他在外奔波,也把妈妈从我的身边带走了,带走了太长的时间。我开始习惯一个人看书,有时是倒着看,因为那时我还不认字。我会一个人坐在地毯上玩过家家,一个人孤独害怕地等妈妈回家。后来,我被送到爷爷奶奶家生活,在那里我过着备受长辈瞩目的生活。每天,我吃着最喜欢的菜,看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给爷爷所剩无几的白头发编小辫子,晚上睡觉前听奶奶讲“人参娃娃”的故事,奶奶只会讲这个故事。再后来,我随父母去了海南,在郊外的一所寄宿学校就读,半个月回家一次。从高中开始,我离家在外读书,直到现在。在如此漫长的过程中,我持续地依恋妈妈,依恋家,心底最深处总有一团空洞。
在我三四岁时,我们搬到了坐落在大池塘边的屋子里。在那里,我学会了织围巾。妈妈很耐心一针针地教我。我们的客厅总是充满阳光,在金黄色中,我贴着妈妈坐着,和她一起织。她织得很快,用小拇指缠着一圈线,轻柔流畅地为针头送线。而我几个手指头总是掰不开,不仅把围巾织得很紧,还总是丢针,把围巾弄出个大窟窿。每当这时,妈妈就接过来帮我退针,把围巾织得松些,再让我继续。织围巾让我很有成就感,每织出一小段,都让我感到很满足。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创造价值,在这个世界上,通过我的手能留下东西。而这是妈妈教给我的。
有一次,我和妈妈从单位回来,在街上看见卖一篮子小雏鸡的摊子,毛茸茸的很可爱。我就吵着闹着让妈妈给我买。妈妈同意给我买两只,我们挑了两个比较活泼的。回家后,妈妈找了个鞋盒子,在盒底铺了报纸,把买来的小雏鸡放了进去。妈妈说小鸡很不好养,他们怕冷,很容易生病死去。妈妈泡了一些小米,让我撒给他们吃。小鸡仔很可爱,黄黄的一团,我喜欢把它们握在手心里,只露出一个小脑袋。每当这个时候,它们就会用好奇的小黑眼睛望着我,不时地转着小脑袋瓜,以便从不同角度认识我。没过几天,强冷空气来了,一只小鸡没能扛过去,拉稀死了。令人欣慰的是,另外一只活了下来,并且长成了健康的母鸡。每天,妈妈会把一些菜叶子剁碎,拌在剩饭里喂它。她还会把吃剩下的鱼骨头或鸡蛋皮剁碎喂鸡,她说这样可以给母鸡补钙,好让鸡下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母鸡一两天就能下一个蛋。妈妈会留下这些鸡蛋给我做溏心蛋吃,黄灿灿的蛋黄吃起来很香。
后来,爸爸的电子琴班越做越大,妈妈陪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到了晚上,妈妈要骑车到很远的地方上课,留我一个人在家。她会事先把被子铺好,给我倒上一杯水,准备一些画纸和笔,或是几本书。出门前总会给我布置任务:画一张画,喝一杯水,然后尿一泡尿,上床盖好被子睡觉,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北方冬天的夜晚特别冷,窗外一片黑暗。等待妈妈回家的夜晚总是很难熬的,妈妈一走,家里变得寂静得可怕。每当这样的夜晚来临,恐惧便向我袭来。我觉得周身寒冷,担心鬼魂或小偷出现在家里。我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默默地把媽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钻到被窝里的那一刻,像是掉进了冰窟窿。一个人在家等爸妈的时候越来愈多,他们回到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有几次,妈妈回家时,看见睡着的我眼角上挂着泪珠,心疼得很。那以后,她每次出门工作都会把我送到爷爷奶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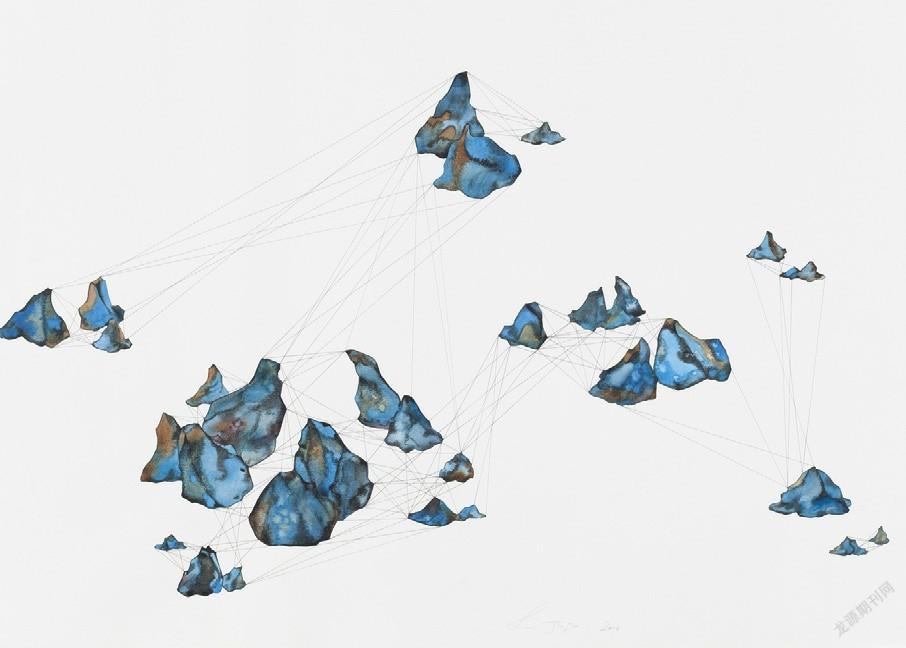
我的童年时期,除了上幼儿园,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和爷爷奶奶度过的。在爸爸妈妈去东北办学的几年,我彻底在奶奶家安营扎寨下来,几个月才能见到妈妈一次。因此,爸爸老说我是和奶奶长大的,和奶奶最亲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奶奶对我再好,也无法和妈妈的爱相比。在奶奶家的日子,我没有一天不想念妈妈。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每天走在上下学的路上,或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妈妈,非常期盼她早点回来看我,搂着我亲亲我。妈妈离家在外的日子里,我总是感到很孤独,即使有爷爷奶奶和同学的陪伴,我仍旧感觉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一样,很难喘息。只要得到妈妈要回来的消息,这种内心的阴云立即散去。妈妈刚回来的前两三天,通常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妈妈会给做我最喜欢吃的饭菜,和我聊天,交换心情。可两三天一过,我就开始倒数妈妈离开的日子了。我的心情也随着日子的临近,越发忧郁起来。我希望时间能停下来,或倒转到妈妈回来的那一天。我总是在做这样的白日梦,可时间不会停下来。
这些经历回忆起来,总让我有些悲伤。一直以来,我渴望有一个温馨平稳的家,渴望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即使一个人在家等待他们回来都不要紧,只要我能每天都看到他们,听到他们说话就够了。可他们担负着比这些小情思更重要的使命:为家庭创造价值,而一切都要为家庭事业让路。
在我们举家搬到海南后不久,我就被送到了郊外的寄宿学校。在那里,我不幸經历了校园暴力,忍受着孤独、失落和悲伤。这种痛苦的经历难以名状,我想,人最怕忍受的就是长时间被周围人冷落、抛弃,在孤独中生活,人会失去希望的。而对当时的我来说,妈妈是我唯一的希望,我期待她能把我从这种无法控制的局面里解救出来。我每隔两周才能回家一次,而这样的短暂假期是我得以暂时喘息的唯一机会。我向妈妈诉说我在学校的遭遇,以及积郁的心情。有时,我告诉妈妈自己无法在那里继续呆下去了,我想转学。妈妈很为我的境遇感到难过,她会花很长时间听我诉苦,然后语重心长地教我如何与别人相处,告诉我与人交往的重要性。为了加强我的人际交往能力,她还给我买了如何与别人沟通的书,她希望我能通过这些书籍和社交技巧来缓和甚至解决我与同学之间的问题,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两人当时也并没有意识到我所承受的这种伤害会给我带来长久性的影响。它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当时所受的委屈和冷落,更多的是随之而来伴随人生的心理阴影。
妈妈是一个看起来温柔且有些虚弱的女人,她对我的爱都来自于她脆弱且敏感的神经,如此细弱绵长,像潺潺的小溪,平缓地流着,却永不干涸。她不太爱说话,不喜欢热闹。如果工作闲下来,她总是喜欢安静地呆在家里做做家务。在生活上,她显得缺乏情趣,她对于各种娱乐活动,都表现出一种迟钝的态度,有时会流露出一种无奈的疲倦感。所以,我们一家三口同游的机会不多,但我非常珍惜我与爸爸妈妈一起玩的那些记忆。
至今,我还忘不了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市里大公园玩的情景。我们一大早起床,带上布单、香肠和面包,准备到公园去野餐。我们在河边的柳树下照相,长长的柳条一直垂到水里。我们到小山坡上赏花,到儿童乐园乘坐双飞人和海底珍珠。妈妈虽然对于出来玩的建议提不起太大的兴趣,可一旦出来了,她总是显得特别开心。脸上一直挂着甜美的微笑。在我们穿过一个浅浅的池塘时,她搂着我的小肩膀,边指向水塘,边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曼曼,你看!红色的鲤鱼。”
由于爸爸出差的关系,我们一家还去过杭州旅游,就住在西湖旁的一家旅馆里。我们欣赏湖水,爬山,到竹林里去。在林子里,我们灌了一瓶子清凉的山泉水,挖了好几颗竹笋。我们一家三口还在林子里喝茶,吃银耳羹,买了两把檀香扇。这在我童年的经历里,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算是奢侈的享受。
爸爸妈妈在东北工作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带我去了长白山。八月份,长白山已经非常寒冷,空气里凝结着雨露。我们穿着毛衣和外套,还冻得发抖。那时候,前往天池的道路只是一条由人们踩出来的路,相当陡峭,上面的岩石随时都会松动滑落下来。我和妈妈没往上爬,而是沿着原路返回。那天的路异常难走,妈妈拉着我的手,我们都快冻僵了。我们走了很久,在山脚转弯处,看到一家村民开的狗肉汤店。店里没有客人,显得空荡荡的。我们在椅子上坐下,要了一碗汤。没过多久,盛在大瓷碗里的汤端了上来,冒着热气,碗底有零星的几条肉丝。我和妈妈轮流端起碗喝着,感觉味道异常鲜美,暖意一下子就进入身体里来,冻僵的身体也不再发抖了。喝着滚热的汤,吃着碗底的小肉丝,看着妈妈逐渐泛红的脸颊,全身一下子就充满了无限的满足感。
这些都是我记忆里最宝贵的珍藏品,是让我回味一生的最纯净的故事。而妈妈带给我的童年记忆不仅仅是这些。平日里,一句温柔的话语,一个简单的拥抱,一个甜美的微笑,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让我感觉到无比幸福的激励。
如今,我虽不像以前那样依恋妈妈,却很恋家。而“家”对于长大以后的我来说,包含诸多含义。虽然这种依恋的对象发生了些许变化,但其实也是一种依赖母体的继续。它象征着妈妈的保护,以及所带来的安全感。时光飞逝,我与妈妈的故事,还在继续……
臧蔓简介
臧蔓
原名藏小曼
青年艺术家。
自由撰稿人。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
工作生活于北京。
不局限于媒介的使用,
以开放的心态重构充满奇幻与未知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