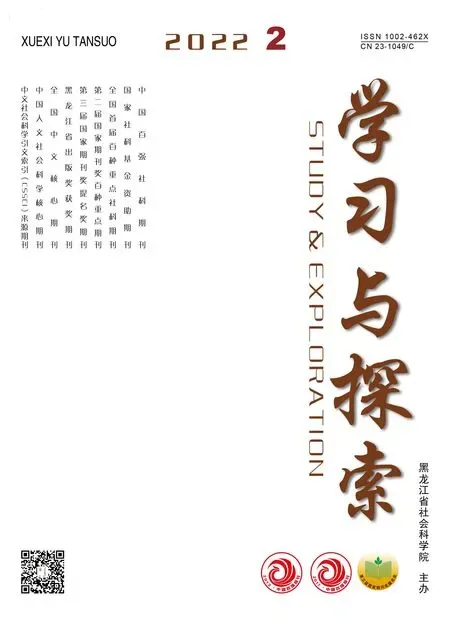从哲学人类学看语言的发生学
2022-12-18邓晓芒
邓 晓 芒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学院,武汉 430074)
语言是人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估计不会有人反对,甚至还被看作是常识。然而,当我们以哲学人类学的眼光来看待亚里士多德对“人”所下的定义——人是“逻各斯(Logos)的动物”时,我们会发现这一定义远不是“人是能说话的动物”那么简单。我们必须深入分析Logos这个希腊词在第一个将它引入哲学中来的赫拉克利特那里的哲学含义。但自从赫拉克利特提出这一概念之后,西方哲学家们基本上是沿着把它解释为“理性”这条思路来运用它的。在20世纪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者们那里,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意思也就是“理性中心主义”,甚至是“逻辑中心主义”。但逻各斯最初的意思决不仅仅是合理性的逻辑话语(海德格尔所谓“陈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除了具有理性(尺度、分寸和规范)的含义之外,原本还具有暗示性的含义。“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1]逻各斯的这一方面在后来的西方哲学家们那里差不多全都被忘记了。(1)格思里认为,把逻各斯理解为“一般原则或规律”以及“理性的力量”,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才开始并通行起来的。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7页。但逻各斯一词的本义是语言,而决不仅仅是理性。
如果我们恢复逻各斯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最初提出时的全面丰富的含义,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亚里士多德的“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一定义的确揭示了人的语言(不止是理性)正是人和动物的分界线。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逻各斯的语言在这里既不止是遵照严格语法逻辑的科学语言,也不是无法理解只能信仰的神的启示(圣言),而是同时具有逻辑理性和诗的暗示性的人性语言。要了解这种语言的现实来源,我们必须追溯人是如何拥有它的,为什么其他动物、哪怕是高等灵长类动物都没有能够获得这样一种神奇的能力。这就把我们引入到了哲学人类学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猿之别。
一、人猿之别新解
在我的《哲学起步》一书中,我重新审视了从古至今有关人的各种定义,试图从中探寻人从动物产生出来的契机。我发现,在古人关于人的本质定义中,无论是西方哲学家(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还是中国古代对人的定义(如“礼”“仁”“良知”等),我们都很难从中找出人类产生源头的蛛丝马迹,那都是在已经产生了人类的前提之下对现有人类的某种本质特征的描述。但这种特征究竟是如何来的,是如何受到人类起源的决定性影响的,却全都语焉不详,而归之于自然界的天经地义或是神的预定。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人类的起源追溯到高等灵长类在一定环境中的自然进化,才给这一问题的现实解决提供了初步的线索。然而,达尔文和赫胥黎的假设还只是一个极为粗略的大致猜想,虽然获得了现代考古人类学大量田野考察和考古挖掘的实证材料的支持,但具体的进化过程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提出了在这方面目前最具有解释力的经典命题即“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入了一个正确的轨道,也成为现代人最为广泛接受的看法。这是一种最朴实、最可设想的观点,即由于制造、使用工具来进行名副其实的“劳动”,人由此而进化成了人。这一观点集中表达在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他在该文开篇就谈道,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因此“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373-374。为了论证这一命题,恩格斯所采取的是当时流行并且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普遍认可的一些解释,首先是着眼于直立行走习惯的形成。恩格斯说:“这种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在攀援时手干着和脚不同的活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平地上行走时也开始摆脱用手来帮忙的习惯,越来越以直立姿势行走。由此就迈出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2]373-374接下来,两腿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手的解放又导致了工具的制造,使手成了劳动的器官,同时又成了劳动的产物[2]375,而共同劳动加强了人这种群居动物的社会联系,从而促成了语言的产生。因此,“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2]377,这就使人的各种感觉器官都发达起来。接下来就是肉食、用火、渔猎和畜牧、农业的产生等,由此进入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类社会。虽然因为当时的考古发现还极其贫乏,恩格斯的这套假设还是粗线条的,大半是猜测性的,某些论断在细节上也受到后来的质疑,但在大的方向上,恩格斯无疑是对的。这个大方向包含两个主要论点,一个是劳动使猿变成了人,另一个是语言产生于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要求。
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学的大量考古发掘和发现,我们对人类的起源和语言的发生过程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这些了解在上述粗线条的范围内基本上并没有超出恩格斯所提出的假设,但在细节上无疑更加丰富和更有实证的说服力了。但20世纪同时又是一个形而上学日益走向衰亡的世纪,是胡塞尔所谓“欧洲科学的危机”的世纪,尤其是在人类学、考古学和心理学这样一些领域,研究者们受到近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非常深刻,几乎已经很难再具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气魄。因此,一百多年来人们虽然在人类起源的某些考古证据和细节上、在年代的确认上、在类人猿和儿童心理学的旁证材料等实证经验上都有了巨大的进展,但在全面综合地建构一种人类起源、包括人类语言的起源的哲学人类学理论体系方面却几乎还停留在原地,甚至很大程度上还被错误的理论框架所误导。直到最近,人类的语言如何产生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学术界的一大难题,不仅卡西尔用“系统描述”回避或取代了“发生学”问题,其他人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大卫·克里斯蒂安在《起源:万物大历史》中发问:“我们人类究竟如何,又为何能够获得超强的语言能力以至激发出如此强大的变革驱力呢?对此,我们还是不清楚。”[3]珍妮·古道尔有关黑猩猩也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重要发现,也给“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经典命题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然而,我提出的有关人的本质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给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新的曙光。(2)最早明确提出这一定义是本人的《人类起源新论:从哲学的角度看(上)》一文,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新华文摘》数字版2016年第6期全文转载。的确,尽管其他动物有些也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如黑猩猩、乌鸦),但在劳动过程结束之后乃至日常生活中仍然随身携带工具却唯一是人类的特点。
我主张,人在制造和使用工具后的携带工具,使工具成为人随身自带的“符号”,它以不变应万变,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扩展性;但它又决不只是一种无用的装饰,而是有其具体的使用对象和适用场所——这一切,都与卡西尔所说的“符号形式”的特点相吻合,即它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并且是在感性活动的时间进程中实现着这种统一。这并不仅仅是卡西尔所说的人类语言的特性,而且是人类一切现实活动、首先是生产劳动的特性。早期人类在所有动物中这种独一无二的行为方式(即随身携带工具),也带来了独一无二的心理模式,一个是形成了在时间中一贯的自我意识,再一个是对周围世界(自然界和他人)形成了“民胞物与”(3)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的“世界感”(海德格尔所谓“共在”的领悟)。而谈人类语言的起源,撇开人类的这种心理模式是不可能的。(4)伽达默尔说:“解释者运用语词和概念与工匠不同,工匠是在使用时拿起工具,用完就扔在一边。我们却必须认识到一切理解都同概念性具有内在的关联,并将拒斥一切不承认语词和事物之间内在一致性的理论。”见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44页。这里的“工匠”指现代的劳动者,而不是原始人类的劳动者。是劳动的异化使人与工具脱离,这种区别类似于人类使用工具和黑猩猩使用工具的区别,前者是人文性的,后者是临时性的和单纯技术性的。奇普·沃尔特断言“语言和意识是一同出现的”[4]141,又说道:“我们的自我意识以非常具体的形式出现,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所有的人都有身体,这是我们存在的最直接表现。从最基本的层级来看,这就是我们区别自我和身外世界的做法。”[4]142但他并没有解释这种意识出现的原因,他只是就事论事地说,“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自我’完全是同一回事”这样的感受“全部都是我们在脑中制造出来的”[4]143。他相信布罗卡医生给人类大脑所划定的“布罗卡氏区”,凭借语言神经和运动神经在脑部这一区域中很“接近”,就表明了人的这两种功能相关联。但这是一种倒因为果的想法。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原因?这里就来解决这个难题。
有一点是可以同意的,即人的肌肉的操作功能和人的语言功能是相关的。但是如何相关?并非任何肌肉功能发达就导致语言功能发达,只有持续地携带工具并将其当作自己的肢体来支配的肌肉功能,才能形成与语言功能接近的大脑回沟。但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肌肉功能,而是身心一体的功能了。因为说到底,正如人手对工具的使用一样,语言也无非是人的发声器官对一种“感性的自然界”即声音的有意识的控制和支配;正如人随身携带的工具延长着人的肢体一样,这种用喉部控制和支配声音的能力也装备着人的思想,成为人的“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5]。“‘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6]所以,人随时携带工具的劳动方式和人随时具备语言能力(掌握词汇和语法)以达成和他人的思想交往这两件事是完全同构的,不但同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这才能解释所谓“布罗卡氏区”中两组神经元为什么会如此接近,它表明的不过是同一种行为方式的自行分化但又紧密相联。
二、语言因携带工具而发生
我们知道,人的劳动是社会性的,但为什么是社会性的?与动物如蜜蜂和蚂蚁的劳动的社会性有何不同?显然最大的不同在于,人在劳动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本能,而是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人通过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大脑活动功能(即所谓“读心术”)而将人与人联系起来,而这中间语言(包括手势语言和表情语言)起着不可缺少的中介作用。意识和自我意识在类人猿那里已经有了萌芽[4]145,但只有当人能够随身携带自己制造的工具而使之成为自己延长的肢体时,意识和自我意识才凭借工具这一客观中介而得以最终确定地建立为人类的基本心理模式,而不再只是偶尔的灵光闪耀。一般的意识只是对于“对象”的意识(对象意识),即意识到对象与自己不同,这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就可以产生;(5)严格说来,对象意识在自我意识产生之前也不是真正的对象意识,因为在把“自己”和对象区分开来时就应该已经具备对“自己”的意识了。但考虑到整个过程从模糊到清晰的渐进性,我们这样说也大致不差。自我意识则是“从对象上看到自己”的意识,这必须达到能够携带工具才有可能形成和定型,即只有当人把工具这样一个自然对象当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带在身上时,自我意识才能成为人的固定的心理模式。(6)马克思说:“人来到世间,既没有携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这个“别人”在马克思这里体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但在人类产生的初期则是人所携带的工具,它和商品一样都是人的外在的“镜子” 。当然,人此后也可以依次把其他自然物、最终把整个自然界都当作自己的身体,人生活在大自然中,整个自然界(包括火、甚至包括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是为他所用并且随时可用的“工具”,继而成了他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人在自然界中对万物“互渗”的意识(7)“互渗”(participation)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ühl,1857—1939)提出的对原始人的思维方式的一种解释,他给“互渗律”下的定义是:“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参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9-70页。同时是自身,又是其他东西,这基于一种“自否定”的结构,它是由于工具被携带变成了人自身的东西,同时又是自然物,从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式。和人在社会中最初的“类意识”是一回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的“精神”和他所面对并处身于其中的“无机自然界”才成为一体的。
在这里,一方面,自我意识的产生是语言产生的前提;但另一方面,语言的产生给自我意识从个人的小我提升为覆盖整个世界(自然和社会)的“大我”(“我们”)提供了证明。正如携带工具使工具从有限的自然物提升为无限的人化自然一样,掌握语言也使个体的人上升为社会的人。这里的语言不一定指有声的言语,也可以是无声的语言,并且首先是以无声语言(手势语)来奠定基础的。人类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大概一直是在用手势语(加上表情语)交流,有声语言的诞生无疑大大加速了人脑的进化,但无声语言以同样的法则为有声语言的诞生作了心理准备。有研究显示,“在学会讲话之前先使用手势来沟通的孩子,在生命后续阶段能发展出较高的智商”[4]95。托马塞洛则通过对类人猿手势的研究认为:“与声音相比,类人猿的手势沟通,最有可能是后来演化为人类沟通的先驱。”[7]23从哲学上说,自我意识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个对象只要是“感性的自然界”,不一定限于声音(即听觉的对象),也可以是视觉的对象甚至触觉的对象。手势语言运用的就是视觉对象;运用触觉对象在原始人中似乎还没有发现,但在现代盲文中则是大量运用的,只不过需要搭配由老师按照正规语法而开设的课程,(8)卡西尔在《人论》中举了两个盲、聋、哑儿童通过刻苦学习而成为著名学者的事例,说明语言不一定是有声的。尤其是著名作家海伦·凯勒,她从小失明、失聪、失语,居然考上并且毕业于哈佛大学,精通五门外语,出版过十四部著作,简直是奇迹。参见《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注释①。表明其中有前人的有声语言所形成的规范作基础。这反过来也证明无声语言在有声语言之前也能够自发地形成自己的语言规范,只是时间要漫长得多。
无论是有声语言还是无声语言,一个共同的要素就是必须在一个统一的时间中安排符号的节奏,即articulation。该词原意为“清晰地发音”或“分音节的表达”(中译也作“分环勾连”),但在无声语言中则是有规律地前后相继的手势或表情。而这种统一的时间表象是由于携带工具才首次在人的头脑中建立起来的。“携带工具”这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动作,从实质上说,不过是把制造和使用工具时人和工具的主客联系在时间上保持或延续下来而已,它本身就是原先一次性地使用完工具便弃之不顾的那种直接实用性行为的自否定,但却出自一种间接性的实用考虑,即“下次”要用工具不必再临时去寻找或制造,我自己身上就带着。但它也不仅限于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种“想到明天”的“经济预见”,而且也带来一种自我超越的眼光,即用一种更高的“我”来支配和评价我的一切行为举止,从而使“我”的行为具有了自我意识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体现于工具的保持在手,在语言中则体现于符号的前后相继,两者的原理是一样的。皮亚杰曾用婴儿两岁前的“感知运动图式”的形成来解释语言的发生,认为在这个阶段,“各种感知运动图式开始内化,成为表象或形象图式。这个阶段出现了语言,标志着婴儿期的结束。儿童开始用表象和语言描述外部世界不在当前的事物,并用语言开始与人交际”[8]。根据这一原理,我进一步引申出了人类语言的起源:
可以说,语言产生之前的原始人,相当于人类的婴儿期,他通过携带工具所掌握的运用符号的能力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感知运动图式”,而语言则是这种图式或行为模式在人的心理中的“内化”的产物,也就是由外部行为内化为心理模式,再由这种心理模式外化表达为语言。所以,携带工具和掌握语言这两种外部现象是出自同一种心理模式,而这种心理模式首先是由携带工具形成的[9]。
这种心理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的“递归”(recursion),即通过类比于当前事物去推算(并非当前的)过去和未来的事物,也就是皮亚杰所说的,从“前运算阶段”进入到“运算阶段”。这在萨顿多夫那里被称为“心理时间旅行”的能力:“心理时间旅行不管是穿越到过去还是未来,涉及的是同一种能力。尚无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他动物拥有这一能力。我们提出,这一能力的出现很可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原动力。”[10]111有研究表明,经过人训练的猿类尽管“可以谈及刚刚发生或是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它们没有能力通过时态或者符号来表达时间转移——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与它们一同感怀往事,也不能讨论遥远的未来。不管我们多么期望它们可以问出一些重大的问题,它们都不会提及自己从哪里来,是什么,去哪里这样的题目。”[10]104这种“把自己投射到未来的能力”使人类获得一种超越直接经验而建立假设的能力,不但可以据此进行逻辑和数学的推理,而且可以对未来的前景进行身临其境的构想,而“感怀往事”则产生出历史记忆和神话;这些就是马克思所谓“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这也引发了一个最具人类性的心理现象,即对“我会死”以及一切人都会死的意识[10]110。可以说,人类迄今为止一切文化上的进步,都离不开这种做假设的能力,即一方面把族群的历史作为传统来继承,另一方面把尚未发生的事情作为自己短暂生命的目标、动力或理想,其意义极为重大。
萨顿多夫虽然意识到“语言和能够穿越时间的心智能力是共同携手进化的”[10]96,但却没有想到,这一切最终都起源于人的携带工具这一贯穿时间前后的举动,这一举动把有限的工具推向了对无限可能性的预测。正是携带工具这一带有时间意识的行为,使人的心理建立起了某种“嵌套思维”(embedding)模式,即所谓“递归”的模式。“递归也是语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关系从句可以是一个关系从句加上另外一个任意的关系从句”。诺姆·乔姆斯基甚至认为,“这种被人类普遍使用的可衍生语法,是所有语言产生的基础。他和他的同事们认为,递归从最狭义的角度定义了语言机制”[10]89。(9)这种单从语言的逻辑递归关系定义语言的做法虽然把握到了人类语言起源的一个方面的根源,但近年来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可参看迈克尔·托马塞洛:《人类沟通的起源》,蔡雅菁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19-220页。我认为这种做法的症结在于,乔姆斯基不仅把这种关系假定为先验的,而且也忽视了其他方面的作用,尤其是隐喻、象征和体验的作用。
如果说携带工具给人类心理在时间中的递归提供一种自否定模式,因而提供了形成语言的语法基础,那么它也给人类在空间中的互相认同提供了最基本的媒介,这是另一种自否定模式。(10)这是萨顿多夫讨论人类起源时所采用的“两条腿”:“构建并反思场景的能力,以及渴望就它们进行沟通的能力。”见托马斯·萨顿多夫:《鸿沟:人类何以区别于动物》,刘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20、329页。前者相当于嵌套思维(递归),后者相当于主体间意识。前文已经说过,携带工具使人的意识提升到自我意识,工具成为人自身的见证,体现着他的与外界打交道的全部能耐,甚至是“另一个我”。从结构上说,自我意识不仅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的意识,而且是主体间的类意识或“我们意识”。(11)在这里我不直接说“主体间性”或“主体间意识”,因为原始人类还没有把主体当作主体,而是主客一体、天人合一的。我甚至认为他们在语词的使用上很可能先有“我们”,在“我”之前他们多半用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如两岁以前的幼儿那样,虽然他已经能说“我们家”,但还不会说“我”。有了这种“我们意识”,在类人猿那里早已形成的群居社会也就不再只是一个求生本能导致的聚合体,而且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社会。凭借主体间意识,人类才能懂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才会互相模仿、互相交谈、互相切磋和达成共识。也许有人会说,自我意识不需要携带工具作为契机,单凭群居的社会经验就可以产生出来,自我意识就是社会意识或群体意识。(12)例如,可参看社会行为主义者米德的观点,他认为:“自我,作为可成为它自身的对象的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并且产生于社会经验。”见乔治·H.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但这种说法的漏洞也是很明显的,因为过群居生活的动物还有很多,例如黑猩猩的社会生活还少吗?为什么只有人类发展出了自我意识?这正说明了携带工具在人类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不可缺少性和基础性,因而也是人类语言形成的必要前提。有了这样一个前提,社会关系的经验才能起作用。
当然,从操作性上看,群居生活所导致的模仿能力也是一个语言世界形成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灵长类动物一般都有极强的模仿能力,有些鸟类(鹦鹉、八哥等)也能够模仿多种声音,但这些模仿都只是对表面动作和声音的模仿,而不理解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动物的模仿给它们带来的是新的生存机会,也使个体的成功经验迅速扩展到整个群体,但却无助于从心理上形成整体的社群纽带。
人的模仿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代表着人身上由携带工具而带来的“主体间”属性。(13)托马塞洛说,“行为模仿的能力,最初是从人类使用、制造工具中演化出来”。参见迈克尔·托马塞洛:《人类沟通的起源》,蔡雅菁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39页。沃尔特也说:“制造工具不只是制造出工具,还让我们的大脑重新组构,所以大脑才能仿效我们制造工具的双手,依循双手和世界互动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见奇普·沃尔特:《重返人类演化现场》,蔡承志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70页。但他们两人的意思都是仅限于人们观摩现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行为,而没有涉及携带工具所形成的“它就是我”的自我意识,这就仍然停留于动物模仿的层次。当人在进行前述“心理时间旅行”时,他实际上已经在对过去或未来相似的场景进行一种“内模仿”了。(14)这里借用了移情派美学家谷鲁斯(Karl Groos,1861—1946)的“内摹仿”概念。谷鲁斯认为,审美是一种在内心进行的摹仿性的游戏,它“只是一种象征而不是一种复本”。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19页。正如同萨顿多夫所言,“我们模拟过去和未来事件,以及模拟别人所想的内容,涉及的是相同的心理机制”[10]142,只不过前者依据的是时间,而后者则扩展到空间。人类通过模仿和互相模仿带来互相理解,此外还有自娱自乐的游戏,以至于群体的狂欢。这都是动物所不具备的。“学步期儿童通常在两岁时开始表现出假扮游戏的行为……当孩子们把一件事物假装成另外一件时,他们正在经历两个世界:周围能够被感知的世界,以及被他们创造出的想象场景。……可惜动物学领域几乎没有任何有关野外假扮游戏的证据。”[10]55动物界有打闹游戏,但只有人类的孩子才有“假扮游戏”,在这种假扮游戏中,如果有其他孩子参与,这将大大提高孩子们游戏的兴致;如果没有其他参与者,孩子也能够把自己分身为两个或几个角色,玩得津津有味。她或他所享受的正是自否定的乐趣:我现在不是我,而是妈妈或爸爸。
但又有谁能够想到,这种假扮游戏、这种有意识的自我欺骗能力恰好也正是命名和语词的起源呢?萨顿多夫进一步指出,这是一种“为模型建立模型的能力”,它“可以洞察一个符号和它代表的含义之间的关系”,在心理学上称之为meta-representation(可译作“元代现”)。这一能力的用途很广,“对于任何由随机符号组成的语言的进化过程来说,这一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10]82。(15)“元代现”原译作“元表征”,意思不明。其实该词就是指用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去代表或假扮成那个想要表示的东西,“元”意味着一点都不像却要代表,这种代表就是原创性的,正如川端康成《雪国》中第一个用“美丽的蚂蟥”来比喻驹子姑娘的嘴唇那样。这里“代现”(Repräsentation)采用的是倪梁康对胡塞尔该概念的译名。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10页。例如,除了像声词外,“大部分词语的发音听起来一点也不像它们代表的物体”,但这对语言来说没有任何关系,语言甚至可以通过这种假定的(其实并不相似的)相似性来“代现”(代替表现)那些抽象意义的词,如“平等”“进化”等[10]83。(16)佐藤信夫主张的“创造性(或发现性)认识造型”是修辞的起源,其实在我看来也是语言命名的起源,或者说,语言本身起源于修辞的创造性。参见佐藤信夫:《修辞感觉》,肖书文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这就是语言的万能的魔力,也是语词和命名的秘密。我明明知道这个发音和那个对象毫无关联,但我既然这样叫它,它就是那个发音的名字了,并且谁先叫出来谁就具有命名的权力,正如考古人类学家对人类始祖“露西”的命名那样。所以不同民族的语言对同一个对象的叫法不同,这完全没有关系,只要你学会了那种语言,你就会觉得这很正常,就该这样叫,时间长了,甚至会觉得这样叫“很像”,不这样叫反而“不像”了。只有初学外语的人才会觉得一个词这样叫有点“怪怪的”,他的“有意识的自欺”能力还未来得及跟上。
按照沃尔特的思路,人类语言的产生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首先,“DNA的随机拼凑方式、变动的气候以及后撤的丛林,甚至移动的山脉,这一切都引出了大脚趾,于是我们的灵长类动物也才站得起来”;其次,“大脚趾也促使大拇指——以及凭此打造出来的工具——得以成真,从而演化出具有语言能力的心智,就这样造就出一种号称伟大无比的工具”;最后,“语言让我们得以凝聚众多心智,共同开创文化,同时还把我们转变成具有自我意识的物种”[4]261。简单说来,这个顺序就是:地质气候变化—基因突变—直立行走—大拇指的分化—制造工具—语言产生—自我意识和文化。这个顺序表面看来言之成理,也得到了当今人类学和考古学界广泛的认可,(17)例如,近年来风靡一时的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一书,一开始就引用了这一模式。但其实一经推敲,就显得似是而非,甚至漏洞百出。首先,“基因突变”是不用说的,任何生物变异靠的都是基因突变(再加上自然选择、包括性选择)。其次,说地质和气候变化导致了直立行走,这也不是必然的,例如从树上下来在平地上生活的大猩猩、狒狒,以及树地两栖的黑猩猩、倭黑猩猩,都并没有直立行走。再次,直立行走“促使”大拇指形成,也没有什么道理。他的解释是,我们的祖先“当它们放弃了指节行走方式,改花较多时间挺身直立,它们就能腾出双手,也更有余力来握持、携带、抛掷,最后还操作制造出更多东西。倘若早期的莽原猿类没有开始直立行走,拇指就永远不会演化出现”[11]57。但“腾出双手”既不能导致大拇指的形成,也不是制造工具的必要条件,黑猩猩仍然用指节行走,但已能制造工具了。大拇指的确便于握持和携带工具,但这反过来不正说明,恰好是长期携带工具、不放松地握持工具的需要,才促成了大拇指?最后,“打造出来的工具”是如何“演化出具有语言能力的工具”以致造就出语言来的,仍然未得到说明。
如果由我来安排这一顺序的话,我就会这样说:类人猿(如黑猩猩)在林中空地上已经学会了制造工具;但由于气候改变导致森林的消失,食物稀少,类人猿在草原上必须走更远的距离才能找到食物,如果还用四肢行走,它们只能将用完的工具随手丢弃,那就花不来了。由于必须将工具带到另一处有食物的地方再用(短距离携带工具的倾向在黑猩猩那里已有了(18)猩猩在野外“也会在短距离内携带工具”,它们“使用石头来砸开坚果,它们有时会携带着石头跨越约一百码的距离来到坚果掉落的地方”。见萨顿多夫:《鸿沟:人类何以区别于动物》,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2页。),也由于在突然遇到猛兽来袭时,或者看到一只小动物(老鼠或兔子之类)突然窜出来时,随身携带着棍棒比赤手空拳或临时去找东西显然是一个明显的优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随身携带工具的习惯。而由于要携带工具,也就不得不直立行走。(19)这时的工具肯定不再是黑猩猩用的那种草茎了,既然黑猩猩能想到用草茎钓白蚁,人类祖先也会想到用棍棒去捅其他动物的巢穴。而再强大的猛兽在遇到手持棍棒的直立人类时,也得畏惧三分(所以武松仗着一条哨棒就敢独自上景阳岗)。形成携带工具习惯的个体比那些没有这一习惯的个体工作效率更高,看起来也更威风、更酷,在性选择中就会占尽优势。经过若干代,携带工具的直立人就成了人类祖先的共同形象。又由于人随身携带工具,工具成了他的“另一个我”,也就形成了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扩展开来,(20)人在劳动中形成的自我意识如何扩展为社会意识,朱光潜在《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一文中有很好的描述,他说:“在劳动过程中人就由‘浑沌’状态变成有自我意识的。有了自我意识,同时也就有自己与旁人关系的意识,即社会意识。人开始认识到生产不仅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可以满足旁人的需要,他的手只有他自己能使用,他所制成的石刀旁人却可以一样地使用,他从此认识到自己与旁人有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制造石刀的能力乃至其他只有人才有的共同点。”参见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333页。虽然他还没有发现劳动如何能够使人具有自我意识,但基本的方向是对的。使得他的群体也成为一个“大我”,互相进行着频繁地意识交流。这种交流最初体现为手势语和表情语(这种无声语言的结构,与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有同构性),直到喉部的生理结构进化到能够发出清晰而又连贯的音节(大约20万年前),才终于把无声的语言转化成更加快捷有效的有声语言。所以我设想的公式是:制造工具—携带工具—大拇指分化及直立行走—自我意识产生—手势语和社会沟通—口头语产生。
这就是我所提出的语言发生学公式,它与旧公式的差别一目了然。
三、自我意识和语言的社会性
这一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是携带工具如何导致自我意识的产生,这个原理只有提高到哲学人类学高度,也就是超越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实证科学的层次,在心物一体关系的现象学哲学的形式指引(21)“形式指引”(die formale Anzeige)是早期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术语。“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形式指引思想,是主动超越理论化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充分强调一种以‘实行’为核心的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精神。”可参见井琪:《海德格尔“形式指引”概念的起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3期。这里撇开海德格尔对哲学人类学的偏见不谈,只取其现象学的方法。之下,才能得到合理的阐明。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至今为止那么多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儿童心理学家,即使意识到了制造工具与语言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却无法具体说明其中的发生学关系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没有站在哲学的视角来揭示携带工具这一看似不起眼的现象在决定人的类本质方面的重要意义,而受限于实证科学的狭隘眼光。以迈克尔·托马塞洛为例,他在《人类沟通的起源》一书中基于与类人猿和人类婴儿的比较,而对人类的语言最初发源时的手势特别是“以手指物”的意义作了细致的分析,在大量实验和观察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三个“关于人类沟通起源的假说”,这就是:
(1)人类的合作式沟通,最初肇始于手势这个领域(以手指物和比划示意);(2)这个演化由共享意图的技巧和动机所促成,这些技能与动机最初则是在合作互相活动的背景之下演化出来;(3)只有在本身就带有意义的合作活动中,并在“自然”的沟通形式如以手指物和比划示意的协调下,完全任意的语言惯例才会诞生[7]231。
这本书可以说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假说而展开的,很多分析非常经典。但他之所以仍然把它们称作“假说”,是因为它们的最根本的起源并没有显露出来,而只是描述了语言在起源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以及根据这些现象而设定的、使这些现象之所以可能的逻辑前提。这个前提就在于“合作”的意愿和能力。但人类为什么会有这种合作意愿和能力,它们本身的起源又是什么?对此作者并没有找到实证的根据。当然也不可能找到实证根据,不光是因为这种根据不可能由考古工作“发掘”出来,而且是因为它本质上只能是超经验的,必须运用哲学思辨并借助于现象学直观,才能从感性经验中“看”出来。换言之,这个根据就是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构成,而这最终又是由携带工具产生的。这是该书作者完全没有涉及到的,也许是为了“言必有据”而有意回避的。
例如,他发现的“很关键的一点”是,即使经过人的训练,猿类也“无法发展出除了要求或命令以外更高深的以手指物的功能”,即“不会基于提供信息,指着某物告知对方可能想知道的事,但是人类幼儿从很小开始就会这么做”[7]26。但这是为什么?他的解释是:猿类“多半还只是用命令的方式沟通,叫别人来替自己做事,它们似乎无法理解合作式的告知是怎么一回事”[7]29。这种解释等于重复了问题。猿类为什么无法理解合作式的告知?如果引入自我意识的学说,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猿类尚未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在它心目中,“自己”是自己,“别人”是别人,如果能够叫别人来替自己做事,根本用不着让别人知道事情的原委。但如果有了自我意识,就会懂得将心比心,替别人着想,知道只有让别人像我一样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别人才能像我一样希望促成这件事情。而这恰好就是人类的情况,也就是凭借自我意识而懂得了“合作式的告知”。猿类的请求或命令本质上是功利性的、自私的、一阶的,人类的请求或命令即使可以有功利性,也是二阶的、带有共享性的,而且有时可以是完全非功利的(如纯粹讲一个故事、告知一个信息,或者请别人来欣赏自己的作品)。所以,虽然猿类也可以了解别人的意念并据此推测别人的行动,“它们能够做出实际的推理,这种推理正是灵活的、策略性的社会互动与沟通的根基”[7]34,从而凭借手势达成猿类的社会沟通,但这不过是一种纯粹凭经验摸索出来的生存技巧,与人类自我意识的物我同一、“民胞物与”基础上的合作共赢或共享根本上不是一回事。(22)很少有人否认语言是为了与他人沟通而产生出来的,但皮亚杰是一个例外。他在考查儿童的语言时主张,“我们要避免这种常识的见解,以为儿童是利用语言来沟通思想的”,例如儿童常常自言自语、独白,这时“儿童对他自己说话,似乎他在大声进行思考。他并不是对任何人说话”。参见让·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傅统先译,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4页。显然,皮亚杰的这一结论也是由于不了解自我意识的超越性(自否定)结构,他将儿童的独白就理解为“自我中心”的表现,而不知道即使他对自己说话,也是在对自己心中的他人说话。但他在解释这种自我中心时又说,“如果儿童互相不理解,这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已经互相理解了”(见《儿童的语言与思维》第122页),却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恰好推翻了他的上述结论。他的同行玛格丽特·唐纳德逊也指出了他的这一错误,见其所著《儿童的智力》,蔡焌年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21-24、55页。可见心理学家如果没有哲学,几乎可以肯定会在最关键的地方出问题。
所以,人类的共享合作意图的基础是复数的主词“我们”,也就是“大我”。“共同基础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它使人超越自我中心的观点来看事情”。正如瑟尔(Searle)所言:“[共享的]意图先入为主地把对方视为能合作共事的伙伴……这是所有集体行为和所有对话的必备条件。”[7]50、52自我意识恰好是把自己看作对象、把对象看作自己这样一种意识,能够把别人当“另一个我”来看,所谓“我们”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所以在人类沟通过程中,哪怕是手势语言,也已经具备了三种不同的语法模式,即“请求的语法”“告知的语法”及“分享和叙事的语法”,也就是力求使他人在知、意、情三方面都与自己同一;而猿类和早期人类“只具备请求的语法”,只针对当下在场之物,即意愿和欲望的对象,别人只是达到这一对象的手段,而非另一个“我”。人类的“告知的语法”的功能则可以针对不在场之物(单纯认知对象),因而可以让(在场和不在场的)事件在“时间定位”中彼此相关,并从中“追踪参与者在不同事件中的动向”,因而“促成了分享和叙事的语法”[7]230-231。这也就是萨顿多夫多次谈到过的“心理时间旅行”,也就是所谓“嵌套思维”(或沃尔克所说的“递归”)。人具有的这种推想能力导致了某种“读心术”,比如“我以为你觉得每个人都知道那件事”,这是三层嵌套;或者“我认为你怀疑我想要让你相信这个”,这是四层嵌套;还有“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了”,等等[10]148,如此以至无穷。
但无论是萨顿多夫也好、沃尔克也好,还是托马塞洛也好,都没有指出这种无穷递归或嵌套的能力本来就是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这一结构早在笛卡尔的时代就已经被发现了,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其实说的是:我思故我思(两层嵌套),因为他所谓的“在”不是指肉体存在,而就是“思”本身。这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个“递归”结构:因为我知道,所以我知道我知道。后来斯宾诺莎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真观念不是递归,而是直观:“为了寻求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可以无须另外去寻求别的方法来发现这种最好的方法,更无须寻求第三种方法来发现这第二种方法,如此递推,以至无穷。因为,这种办法决不能使我们得到对真理的知识,甚至决不能求得任何知识”;所以“要知道一件事物,无须知道我知道,更无须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相反,“要知道我知道,我首先必须知道”[12]。他以这种直观来反驳笛卡尔的递归,其实这两者在自我意识中恰好是辩证地相关的。自我意识就是不断地跳出自我而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自我,而当他这样看自我时,他已经立足于第四者的眼光了,如此以至无穷;但在此途中任何一环停下来,自我意识都会发现并不需要无穷追溯,这种无限性是当下呈现的。自我意识的这种无限递归起源于携带工具所展示的递归:每一件工具都是制造工具的工具,因而也是工具的工具的工具……能保持这种无限性是因为手中持有工具,只要中途把工具丢弃,这一链条就中断了。这就是黑格尔提出的“真无限”的概念。黑格尔认为,“在过渡中、在别物中达到的自我联系,就是真正的无限”,“当我们说我时,这个‘我’便表示无限的同时又是否定的自我联系”[13]。真无限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是在有限中直接体现出来的无限,这就是自我意识的自否定结构。
托马塞洛也说,“实际沟通的心理现实,也不全然是在这种不断往返地知道别人知道我知道什么,而只是简单地全都知道我们都一起看到、知道或关心某事:我们‘共享’了这些知识,也具备各种启发性知识,能找出我们与他人之间有哪些共同基础”,他把这种能力称作“反复读心术”,还指出这种“反复的回旋并非无限,只是不确定;……但多半时候我们根本不会这样演算,只会通过某种启发性知识,注意到互动伙伴是否与我们有共同点”[7]66-67。他说这些话时,无意中接近了黑格尔的“真无限”的想法。但他显然并没有深入研究过自我意识的结构,而只能从技术上对人类沟通的条件加以归纳:“人类的互助活动与合作沟通,都要依靠反复看穿意图,也要依靠人类有提供协助、自主地告知他人讯息的这种倾向,但类人猿的团体活动和有意沟通,却不需要这些条件。”[7]120但他不知道,所有这些条件都已经包含在人的自我意识的本质结构中了。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懂得高深的思辨哲学,但至少我们可以指出,在人类及其语言的起源问题上,很可能正是在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困难中隐藏着思辨哲学的答案。而一种“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也只有沿着这条上升之路才有可能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