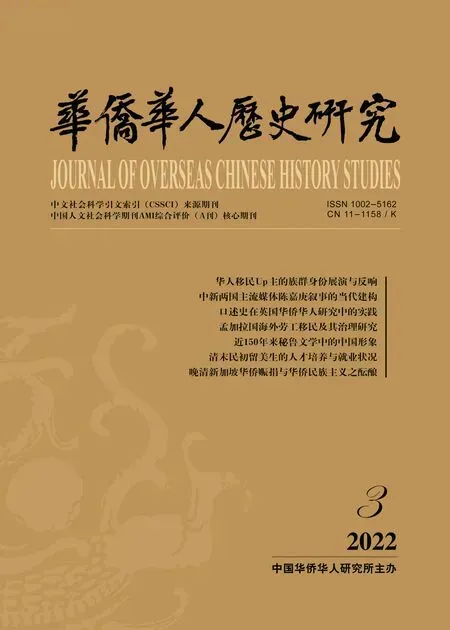晚清新加坡华侨赈捐与华侨民族主义之酝酿*
2022-12-17张书
张 书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长期以来,华侨与祖国之关系,是华侨华人史研究的重要议题。20世纪80年代,颜清湟在《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一书中指出,1900—1911年为海外华侨与中国本土关系的过渡时期,其间,海外华侨从对中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转变为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逐渐具有全国性的国家意识。[1]在颜氏研究基础上,黄建淳从新马华侨赈捐活动入手,进一步探讨了新马华侨民族主义的酝酿和发展问题。黄建淳重点分析了新马地区的捐例章程与赈捐流程,认为清廷随捐诰封的官职爵衔将华侨的文化认同升华为对国家的认同,从而将华侨国家认同形成的时间提前至晚清时期。[2]黄建淳之外,也有其他学者将南洋华侨赈捐活动与清朝的鬻官制度联系起来进行了探讨。[3]
黄建淳等人对于赈捐活动与捐纳制度的研究,凸显了华侨对清政府的政治认同,进一步深化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然而,民族是一个“带有政治性的社会文化范畴”,[4]社会文化内涵在华侨民族主义发展脉络中的基础性地位也不容忽视。笔者认为,赈捐活动中,南洋华侨对来自中国民间求赈声音的积极回应及自行组织助赈行为,体现了南洋华侨超越政治制度的社会文化认同,也同样是华侨民族主义酝酿的重要表现。本文在黄氏政治史研究基础上,通过社会史的视角,梳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从政治制度认同发展为超越乡土观念的民族意识这一历史脉络,从而进一步推进这一问题的探讨与深化。
一、赈捐活动的出现与良性关系的强化(1877—1889)
晚清时期,由于社会观念和政治格局的变化,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设驻外使馆保护侨民,并“劝诱”海外华侨为中国捐款。[5]1877年,清政府采纳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建议,在新加坡设立第一个驻外领事馆。[6]清政府华侨政策的改变,增进了海外华侨与祖国的联系。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也随之开展起来。1877—1878年的“丁戊奇荒”期间,丁日昌选派绅商前往香港及南洋各埠劝捐,其中新加坡、小吕宋等处华商“捐定者共三万余元,将来尚可扩充”。[7]新加坡华侨的助赈,开启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的第一阶段,同时也巩固了新加坡华侨与中国社会刚刚建立起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华社领袖、华文报刊与赈捐活动的组织
时至1883年,上海协赈公所已在新加坡设置代收处。《申报》刊登的《上海陈家木桥顺直山东等处赈局同人公启》刊列了赈局的代收处,新加坡招商局陈金钟已名列其中。[8]1884年,上海陈家木桥协赈公所同人更是发函至《叻报》报馆,称“欲借重贵馆日报代将敝所刊入《申报》中公启、捐款清单按日摘要录登,俾南洋各善士习见习闻,奋兴输助”,并开列南洋各埠劝收赈捐善士地名清单,新加坡招商局陈金钟为叻地①新加坡亦称为石叻、叻,音译自马来语selat,意为海峡。负责劝收赈捐的唯一善士。[9]实际上,陈金钟早在1881年即曾以个人身份捐助直隶赈银一千两,被嘉奖“自行建坊”,并给予“乐善好施”字样。[10]此后,陈金钟还参与并组织了新加坡多次赈捐活动。
1888年,河南郑州因河流决口发生水灾,并波及安徽、江苏两省。盛宣怀电请严佑翁等人前往勘救,并致电绅商李秋坪详述河南灾情。李秋坪认为“后路尚须速筹,万难延缓”,故函托由陈金钟负责的新加坡振成号为之劝捐。[11]随后,陈金钟将李秋坪之电文嘱新加坡当时唯一的华文日报《叻报》登载,报馆将其命名为“劝募河南水灾赈捐启”。[12]1888年2月底,《叻报》首次刊登了由陈金钟提供的捐册一则,捐册中所录之捐款人数为59人,捐款数额从2元至60元不等,所列款项为762元。[13]由于缺乏其他捐册的相关信息,此次筹捐款项的确切总数尚不可知,《叻报》称“近来河南郑州捐务复得陈君金钟劝赈,已集有成数,筹解灾区”,[14]加之陈金钟也因筹赈皖灾的行为受到清廷的嘉奖,故可推断捐款总额应已达到一定规模。陈金钟在此次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中充任了组织者的角色,劝集赈款,1900年,清政府“予新嘉坡福建绅商兼充暹罗领事、候选道陈金钟传旨嘉奖”。[15]此外,陈金钟还单独捐助一千两赈济灾民,李鸿章请旨“俯准陈金钟自行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16]
1889年,皖省旱涝荐臻,居民荡析流离。上海道龚照瑗劝办皖捐,直接致函中国驻叻领事官左秉隆,求为劝赈。[17]左秉隆接到函件后,迅速筹划赈捐皖灾的活动,在新加坡汇合了中西绅商的力量进行劝赈。1889年2月,左秉隆参与了由新加坡参政司组织的会议,会议延请中外诸官绅商协商劝捐事宜,陈金钟被选入劝捐董事之列。[18]诸劝捐董事带头认捐,在聚议之时,陈金钟已题认4000元。[19]《叻报》也对此次中西官绅合办捐务之事特加报道并予赞扬,认为“人心之踊跃如是,则巨款有不难于集成”,并对英国诸官绅参与赈捐大加称道。[20]由此可见,以陈金钟为代表的新加坡华社领袖以及《叻报》在新加坡华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借助华社领袖、华文报刊的力量也成为清廷推进赈捐活动的有效手段。
(二)捐款人群与筹款数额
“丁戊奇荒”期间,《申报》专门报道了新加坡华侨的助赈行为,指出新加坡华商于1877年已有一次捐助,1878年复捐洋银一万一千,称赞中国商人虽久离桑梓,仍急公好义。[21]据光绪五年(1879年)丁日昌所书《为南洋华商捐赈请颁匾额事奏折》,其派往南洋劝捐之员绅曾在新加坡潮州会馆祷告以求风帆安稳,且在南洋集成巨款,南洋各埠绅商称,“经手晋豫赈捐,除照章请奖外,另存银三万零九百三十三两二钱二分三厘。”[22]
为了扩大赈捐活动在新加坡华侨社会中的影响,组织赈捐者经常将捐册在《叻报》刊登。1889年筹赈皖灾期间,《叻报》多次刊登中国驻叻领事府提供的赈捐清单,详列赈捐人之姓名与捐款之数额,并指出“诚以本坡旅处之华人,其籍多为闽粤,则于江皖各地虽为同国,然已非桑梓之关怀,乃亦慨然赈之,是谓能周局外也”。[23]中外官绅的合作,中国驻叻领事左秉隆的努力,加之《叻报》的积极宣传,筹捐活动成效显著。至1889年3月,新加坡五大帮群加上烟酒公司捐款共计20799元。[24]5月,因赈务结束,《叻报》刊登了此次南洋题捐江皖赈务的捐款结册,称“另除费用银四十一元,所存共银十万零九千零六十七元零八占”,并详细列出南洋各地所集捐款之明细,其中新加坡所筹捐款最多,超3万元,吉隆坡地区捐款数额为2万元,白蜡和槟城两地亦在1万元以上。[25]此结册所列款项乃属陈金钟经手,加上其他劝捐董事所募之款,南洋地区所筹捐款总额当在10万以上。[26]
(三)清廷对赈捐活动的事后奖励
此一阶段的历次赈捐活动中,尚未见清政府颁布正式的捐例章程,清政府对捐输巨款者多在事后予以嘉奖,此种事后请奖的特点更符合捐输制度的定义,故不能将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统归为清政府捐纳制度在南洋地区的推广。①捐纳与捐输之区别:捐纳是由政府事先定例,捐纳者遵照政府的定例购买相关资格;捐输是事先并无定例,在捐输者自行捐输之后,政府采取事后请奖的方式奖励捐输者。可参考江晓成:《清代捐输制度研究(1644—1850)》,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多与清政府的捐输制度相关。捐赈事后由清政府传旨嘉奖的特点,在历次赈捐中多有体现。
1879年,为表彰南洋绅商的捐款行为,丁日昌奏请颁给新加坡潮州会馆关帝、天后御书匾额各一方,“以顺舆情而资激励”。[27]陈金钟也因其积极组织赈捐活动,多次被清廷嘉奖自行建坊,并给予“乐善好施”字样。1889年江皖赈务结束后,龚照瑗向曾国荃请示嘉奖左秉隆的劝赈之功,曾国荃认为左领事“设法筹劝苏皖赈捐,集成巨款,洵属得力”,“容俟邻省暨本省劝捐委员办理给奖时,再行斟酌出之”。[28]为旌表中西官绅的积极助赈行为,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请予以旌扬,伦敦府尹、暹罗国王、新加坡福建帮、新加坡潮州帮均被赐予匾额,华商吴新科、郑景贵等也被称为“乐善为怀”“慈祥普被”。[29]
虽然未有事先公布捐例的吸引,新加坡华侨仍积极援助中国灾民,这与《叻报》《星报》等报刊对赈捐事务的积极报道、对中国传统慈善话题的宣扬密不可分。首先,强调新加坡为南洋都会之区,商业繁盛,筹款理应比南洋其他各埠更加积极。《叻报》对吉隆坡甲必丹叶致英赈济粤东水灾之举极为推崇,并感慨新加坡“为南洋通商口岸第一繁盛之区,向有都会之称……筹款于叻应较他处为倍易”。[30]其次,宣扬英国官绅助赈之行为,以说服新加坡华侨赈捐。对于施制府积极筹赈皖灾之活动,《叻报》评论道,“今施制府曁蜚礼申等诸公均英人也,其于中国本属风马牛之不相及,然则中国遇灾,而诸君坐视是亦人情之常……乃施公等则不然,……无分畛域,出而劝助”。[31]最后,华文报刊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慈善话题的阐发,对新加坡华侨形成了较大的感召力。中国传统慈善福报观念强调人的恻隐之心,认为慈善源于人的内心,是人天性良善的自然流露。[32]1889年,《叻报》刊登文章《赈灾宜亟说》,劝说新加坡华侨为皖省灾民捐款,认为解囊助赈之行为乃出于“恻隐之心,仁慈之念”。[33]对于吉隆坡甲必丹叶致英的助赈行为,《叻报》评论“修德获报,行道有福,可于叶君拭目俟之”。[34]此类宣传策略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加之中国驻叻领事与南洋华侨领袖的积极劝募,赈捐活动的参与人数与筹款数额均达到了较大规模。
总体而言,赈捐活动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政府侨务政策的改变,尤其是清廷驻新加坡领事馆的设立,拉近了华侨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新加坡华侨主要来自闽、粤两省,他们能破除帮派隔阂与畛域之见,对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的灾民解囊相助,表明他们对祖国的关注并未局限于家乡,已经具有了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基于中国传统慈善观念的感召,新加坡华侨积极响应募捐之举,打破了清政府与海外侨民互不关心的状态,华侨与中国的联系不再局限于宗亲与侨乡,新加坡华侨与中国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得到疏通,新加坡华侨与祖国的良性互动关系得以建立,为华侨民族主义的酝酿奠定重要基础。此后,清政府不断出台对华侨的保护政策,而新加坡华侨也对中国的发展予以积极支持,华侨民族主义在双方的积极互动中酝酿而成。但此一阶段的赈捐活动,未在新加坡设立相应的劝捐机构,尚缺乏足够的组织性,①1888年5月23日,《叻报》论说《劝赈篇》在赞扬吉隆坡甲必丹叶致英为粤东水灾首倡劝捐时,也感慨新加坡尚未议及筹赈之举,而其原因则在于未有人倡议于先。就此而言,组织性在赈捐活动中是非常重要的。捐款人数及筹集款项均相对有限。此后,清政府有针对性地往南洋地区派出劝赈官员,并公布捐例章程以吸引更多华侨的捐助。
二、赈捐活动的发展与华侨对清廷政治制度的认同(1889—1900)
1889年,清廷制定了劝捐章程,并刊登于《叻报》,这开启了赈捐活动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清政府还直接委派官员长驻新加坡组织劝捐事务,新加坡华商也积极配合清政府官员的组织工作。在劝捐章程的吸引之下,新加坡华侨在赈捐活动中表现得更加积极,筹款规模更大,使得捐助祖国灾民的行为在新加坡蔚然成风。这一阶段新加坡华侨对清廷赈捐机制的积极参与,反映了他们对清廷政治制度的认同。
(一)1889年劝捐章程的刊布
1889年,山东告灾,水旱洊至,二十余州县同告灾骎。10月,新加坡德源号吴进卿、文行堂吴夔甫两观察已奉委在叻开设劝赈分局,广劝捐输以筹巨款。[35]山东巡抚张曜还委命新加坡华绅章芳琳在叻劝捐,章君奉札之下立即捐银四千元以资赈款。[36]此次赈捐则开具官阶职衔以为奖励,苑生号章芳琳将山东筹赈劝捐准奖贡监、虚衔、封典所有章程实银登报声明,章程规定捐取相应官阶职衔所需银数,其中由贡监生捐取道员需银最多,为一千六百七四九点三六两,从九品、未入流由俊秀捐银二十五点六两即可。
章芳琳自承办劝捐事务以来,自己捐银共有八千之多,其子亦奋勉题捐至数千元之款,《叻报》评论道“洵可见急公好义,将来崇衔待赐,想举家均受荣封矣”。[37]《叻报》多次接到章芳琳所寄之赈捐名册,并为之登载于报,还及时刊布告示,请题捐诸君携带实收前来换取部照与监照。劝捐章程在《叻报》公布后,前一阶段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所表现出的事后请奖之特点,逐渐被按例交银以购买指定官阶职衔所取代,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进而与清政府的捐纳制度产生了更多的联系。
(二)清廷派遣官员赴新加坡劝赈
1890年,浙省发生水灾,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最初仍由当地华商组织,薛福成抵叻时曾面委振成公司陈金钟在叻地办理浙省赈捐。[38]此种仅利用新加坡当地资源组织赈捐活动,即委任当地华商或驻新加坡领事在叻地劝捐的形式在1890年苏浙赈捐中被改变,两江总督曾国荃此次派出金陵苏浙赈捐总局委员汪之淇携带钤印、告示、实收前往新加坡劝捐。[39]清廷官员初至叻地,对当地情形并不熟悉,还遭到当地华侨的怀疑,叻地之人谓“此次携来印文与前次不符,办捐殊不足信”,捐生心生惶惑,劝捐活动遇到困难。[40]为此,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发电至江海关道聂观察处询问,并将所接之复电登诸报端以“靖谣喙而释群疑”;叻地华商陈金钟亦发电至曾国荃处询问,后得复电称“委属无讹”。[41]此外,汪之淇还禀请曾国荃,欲请叻地闽商邱忠波、粤商张弼士共劝捐务,此事得苏浙赈捐总局核准,发给札谕与邱、张两绅。[42]办赈官员为了打消叻地华侨的疑虑,并扩大劝赈活动之影响,到叻后通常先请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开办告示登报以取信于人,并会同当地绅商共同办赈。
1890年9月,汪之淇结束叻地的劝赈差事返回上海,回国后却因病去世,叻地报捐者都担心会影响后期部照的发放。[43]之后,谢宾门被委派赴叻接办汪之淇的工作,并携带部照前往发放,“以便报捐诸君就近换给,俾昭诚信而重赈务”,此后苏浙赈捐的部照发放工作便由谢宾门负责,其多次在《叻报》登载告示以提醒报捐诸君前往换取部照。[44]此后,谢宾门参与组织叻地多次赈捐活动,直至1897年2月返回中国。
1890年五六月间,苏浙赈捐尚未结束,顺直等处又发生水灾,李鸿章奏请开办顺直赈捐,各省一体劝办,粤藩王灼棠则委派爱育善堂绅董李芝田携带章程、实收等赴叻劝赈,捐局初设朱广兰号。[45]此后,闽浙督宪又札委在叻开办顺直赈捐,闽省汀漳龙道派候选知县举人王宽、候选县丞邱鸿玉、龙溪县学茂才庄嵩龄到叻与陈金钟共办捐务,捐局便设于振成公司内,振成公司之负责人陈金钟亦列为奏办顺直赈捐委员之一。[46]同时,奉命接办苏浙赈捐的谢宾门也负责顺直赈捐事务,声明“如有报捐贡监、衔封、翎枝等项,或慨捐巨款欲奖何项升阶,请速赴老巴虱土库街万兴号内本分局面议”,其告示落款为“委办顺直、苏浙赈捐核奖分局”。[47]
至1891年4月,李芝田携带的实收业已用尽,故登报声明,“日内即行北渡销差,奉到部照再行布告招领”。[48]9月,顺直赈捐之期将满一年,谢宾门登报劝说诸人从速纳捐,“如过八月初十日后不到局报捐,本局即将空白实收奉缴”。[49]年底,顺直赈捐已结束,谢宾门再次接到山东筹赈总局的文件,委任其继续劝办山东赈捐。[50]谢宾门也善于利用华商力量组织劝捐活动,“请本坡公正绅士吴进卿方伯、邱忠波观察、吴夔甫太守、曾兆南司马会同劝募以广招徕”。[51]之后,还请吉隆埠之华绅叶甲必丹、福山公司邱绅、槟榔屿之万兴栈主邱绅、谦益公司陈绅、望加锡埠顺源号等会同劝募。[52]此后,谢宾门还会同南洋华商劝办顺直赈捐[53]、江苏赈捐[54]、鄂湘赈捐。[55]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阶段,清政府委派赴叻劝赈官员的努力,对赈捐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谢宾门在叻地办赈,得到当地华侨的认可。首先,谢宾门积极结交当地中西绅商,以扩充劝赈力量。初至叻地,谢宾门便请叻地绅商吴进卿、吴夔甫会同劝办,又添请吉隆埠之甲必丹与福山公司、槟榔屿之万兴栈主等设立劝赈分局。[56]1896年,鄂湘赈捐即由谢宾门会同新加坡安和号东主闽绅吴寿珍设法劝办。[57]《叻报》评论道,“叻中诸君子莫不重其才品,争与订交而居停,邱忠波观察乔梓辈尤加敬礼焉。”[58]其次,充分利用《叻报》等平台发布劝赈信息,及时为报捐者换领执照。《叻报》频繁刊发劝谕启示、捐册名单、换领执照公告,鼓舞了叻地华侨积极赈捐。最后,谢宾门办赈尽心尽力,获得了新加坡华侨的信任和支持。除在新加坡组织赈捐活动外,谢宾门还多次前往外埠劝赈,“屡赴槟城、吉隆、白蜡、西贡、仰光及荷属三宝陇等处沐雨栉风,为民请命”。[59]叻地“诸善士信托同深,莫不踊跃之题助也”[60],而谢宾门所办诸赈捐“著有成效”,“上游知其才猷练达,故迭委接办顺直、山东等处赈捐”。[61]1897年谢宾门返回中国之际,《叻报》专刊《送谢宾门司马东归序》一文,概述其在叻地劝赈之活动,并予以肯定,评论道“今司马因为俄鸿求哺之故,不辞艰阻,远涉重洋办赈,多年成效卓然”。[62]
(三)赈捐成效
1893年,山西告灾,中国驻叻领事黄遵宪得知消息后,起初心怀犹豫,“欲出而劝募,恐同于竭泽而渔,欲隐忍不言,又同于视死不救”,后考虑到“居此有年,毫无善政”,故决心为山西灾民筹赈。[63]此次赈捐活动同样得到了除新加坡之外的南洋各埠的支持,望加锡汤祥堑欲捐米一千担寄赴上海,吉隆福山公司闽帮总董事邱道南筹寄来银三千元。[64]为早日筹集赈款,黄遵宪还决定停发图南社月例奖银四十元移充晋赈,图南社诸生捐银以示支持。[65]当所收捐款达到一定数额后,黄遵宪即将钱款通过汇丰银行电汇李鸿章查收,以便救济灾民。根据《叻报》刊登的告示,可知黄遵宪在1893年7月6日至9月2日期间共汇款10次,汇款数额多者达一万三千元,少者为五千五百元,总计九万二千五百元。①汇款次数以及汇款数额根据1893年7月6日至9月2日《叻报》刊登的相关告示整理而得。但黄遵宪在相应告示中自述“合前次所寄,共银一十万七千元”。[66]二者出现不一致可能与报纸散佚导致信息缺失有关,但据此可掌握此次赈捐所集款项的大致规模。
虽然没有精确的数据来比较1889年前后两个阶段新马地区赈捐活动的参与人数及筹款数额之多寡,但从《叻报》刊登的历次赈捐名单、对南洋各地捐助赈款之表彰告示,我们可以发现,此一阶段有更多的南洋华侨协助中国官员办理赈务,赈捐活动在南洋地区的影响范围更广,筹款规模也更大。恰如黄建淳所说,南洋各埠华侨之所以踊跃捐输、报效情殷,固然得力于中国领事、华侨领袖,甚至殖民地政府的谕示劝赈,然而,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清政府随捐诰封的官爵职衔。[67]南洋华侨对官爵职衔的极大兴趣,对赈捐活动的积极助力,体现了他们对清廷政治制度的认同。
(四)赈捐活动的组织与奖励流程
此一阶段的赈捐活动,涉及的程序也更为复杂,赈捐活动具有了更强的组织性。黄建淳梳理了新马地区的赈捐流程图,基本概括了从国内设立赈捐总局,到新马地区成立赈捐核奖分局,以及捐资报效者获得实收、执照的过程。[68]黄建淳整理的赈捐流程图大体符合史实,但有两处值得商榷。其一,赈捐分局与核奖分局的区别,黄氏认为专员开设的称为核奖分局,而富商开设的为赈捐分局。其实并非如此,二者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界限,赈捐活动多由专员与富商会同办理,而很多分局名称亦为赈捐核奖分局。赈捐更强调筹款过程,而核奖则更侧重筹款后的执照发放或专折请奖。其二,关于执照的填发,黄氏认为均由赈捐总局负责,但根据《叻报》多则“招换执照”的告示可知,执照多由户部或国子监颁发寄送至叻地,而筹赈总局只是根据捐册详咨请奖,并未负责颁发执照。
在整个赈捐流程中,与报捐者关系极为密切的步骤包括:报捐者向赈捐核奖分局捐银请奖,分局据其所捐银数填给实收,待分局将所筹款项汇解中国后,户部颁发执照寄到叻地,报捐者便可携带实收前往调换执照。故在1889年后的《叻报》中,频繁出现“招速领照”“催速换照”“传换部照”[69]等告示,开列赈捐分局所收执照对应的报捐者姓名以备换领,而这也是之前赈捐活动中所未曾出现的。此外,清政府也延续了1889年以前对筹赈有功者、捐资巨款者进行事后嘉奖的先例。1894年,南洋槟榔屿等处华商郑嗣文等,因募助赈捐,清廷传旨嘉奖。[70]1899年,因新加坡潮州侨民捐助东赈,清廷颁新加坡天后庙匾额曰:“曙海祥云”。[71]
此一阶段,清政府不仅公布了劝捐章程,还选派官员亲自前往南洋地区组织筹赈活动,赈捐活动与清政府的捐纳制度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清政府所提供的官爵既符合新加坡华侨传统价值观念中光宗耀祖的思想,也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华侨社会中的影响力,对新加坡华侨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1889年后,新加坡华侨在历次赈捐活动中表现得更加积极,筹款规模更大,赈捐活动在新加坡华侨社会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新加坡华侨对清廷所提供的官爵职衔的热衷,反映了清政府统治政策在华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他们对赈捐机制的积极参与,也凸显了对清廷政治制度的认同。
三、回应民间求赈与超越乡土意识的民族认同(1900—1911)
在前两个阶段的赈捐活动中,主要是新加坡华侨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在1900年之后,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与中国的民间力量产生了更多的关联。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声音,新加坡华侨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此种自发行为体现了华侨超越乡土意识的认同,华侨民族主义得到进一步酝酿发展。
(一)回应民间求赈
1898年,广东全省奇荒,米价腾贵,香港东华医院两次致电新加坡同济医院,请求从速备赈。[72]接电后,同济医院迅速在院内组织筹捐事务,“即经众举,粤商七家为董办赈捐值理,旋由总理朱广兰号暨七董事即日捐款项计共六千五百元”。[73]几天后,同济医院又接到粤垣爱育善堂电文,请求助赈。[74]作为民间力量之间的交往,捐款者无法购买相应官阶,同济医院对此有所说明,“除给回收条存据外,另将芳名捐款照登日报,以示表扬而昭征信”。[75]同济医院除了在新加坡劝赈外,还号召吉隆埠[76]、仰光[77]、芙蓉埠[78]等地区的绅商进行劝募。
1898年,厦门米价亦一日三涨,时任兴泉永道的周子迪,联合厦门绅商在厦门设立平粜总局,同时致电外洋吁求各埠乡侨集款助赈,新加坡闽商接电后集议于天福宫,在叻地创办厦门平粜局,此次南洋各埠所筹平粜捐款达十万元之巨,配送至厦门、泉州、漳州三地的平粜大米计有四万余担。[79]
6月,叻地绅商复接到汕头同济善堂黄副戎金福、万年丰会馆公电,言及潮州、汕头等处米价大涨,贫民无从谋食,请求赐赈,叻坡诸绅商决定成立“劝办汕头赈捐董事”,由募赈诸君设立缘簿,出而劝赈。[80]此次汕头赈捐也得到了蔴坡、砂朥越、麻六甲、廖内、槟榔屿等地华商的支持,[81]《叻报》多次刊布赈捐缘款名单。此后,因筹集赈款之需,叻地还成立了“福州平粜局驻叻董事”、“琼州平粜总理”、“驻南洋劝办永春平粜诸同人”。[82]
1908年广东发生水灾,新加坡同济医院与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共同组织筹捐活动,并布告南洋各埠中华商会暨华商会馆协力筹赈。[83]这是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首次参与新加坡赈捐活动,也得到了南洋其他地区中华商会的支持。峇厘中华商务总会、望加锡埠华商总会、安班澜中华商会均将所筹赈款汇寄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或直汇粤垣以赈济灾民。[84]
(二)捐款数额
1898年9月,赈捐活动告竣,同济医院将进支清单登于《叻报》,此次同济医院共筹得赈款接近四万元,除少量费用支出外,均汇往香港东华医院以备赈济。其中新加坡所筹款项最多,为二万七千四百八十一元,其次为吉隆、仰光,二地捐款数额在五千元左右,赈款除用于支付往来电费、马车什用、叻星两报告白费外,分九批汇寄中国,收支相抵后所余三十二元留存同济医院以作为善款使用。[85]
1908年,新加坡同济医院与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共同组织筹捐活动,以赈济广东灾民。此次赈捐所筹善款达四万元,其结册广告中详列支出情况,所筹款项大多汇寄粤垣救灾公所,部分汇往四邑救灾公所、粤垣自治研究社。[86]
面对来自民间而非官方的求赈声音,新加坡华侨的赈捐行为并不能获得明确的奖赏,但他们自发组织和参与筹赈,表明他们与祖国的联系不再只是对清廷政治制度的认同,而是具有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认同的意味。当然,此一阶段仍有部分赈捐活动延续了此前的特点,由政府委派官员携带钤印与实收前往劝赈。1900年,福州多地遭遇水患,福建省会善后总局委派周有基前往南洋各埠劝办赈捐,新加坡华商不仅帮助周有基劝办赈务,还主动垫款,吴寿珍、林志义各先垫银三千元,陈群英二千元,邱新再、林威重各先垫银一千元,合计一万元由汇丰银行电交福州善后总局饬收发赈。[87]1901年,李鸿章奏请开办顺直赈捐,并派杨村通判时楚卿太守携带部照、实收至南洋劝赈。[88]
这一阶段,新加坡华侨对来自祖国民间求赈声音的回应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特点。这些赈捐活动虽未有清政府官阶职衔的吸引,但所筹赈款的总额亦不在少数。面对中国民间力量所发出的求赈呼声,新加坡华侨同样予以积极的回应,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这说明在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之外,他们对中国社会已经具有了超越乡土意识的民族认同。这体现出华侨民族主义得到进一步酝酿,华侨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意涵进一步得到发展。
四、结语
晚清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与中国本土社会有着多层次的联系,其中也包含着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的发展脉络。1877—1889年,新加坡华侨积极响应募捐之举,强化了新加坡华侨与祖国政府的联系,为此后华侨民族主义的酝酿奠定了基础。
清政府于1889年颁布了劝捐章程,以官爵职衔吸引更多的华侨捐资助赈,使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达到较大规模。官爵职衔之所以对新加坡华侨产生吸引力,是因为官衔具有光宗耀祖的作用,并且能够带来社会声望,最重要的还是清朝的官衔有助于承认和确认华侨在华族社会的领导地位。[89]新加坡华侨对官爵职衔的需求与认可,也说明了清政府统治政策在新加坡华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而新加坡华侨对清廷赈捐机制的积极参与,反映了他们对清政府政治制度的认同。
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声音,新加坡华侨的捐助行为,虽然无法获得明确的奖赏,但他们同样予以积极回应,利用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这就更进一步说明在功利性的考量之外,晚清时期新加坡华侨在情感上对祖国超越乡土意识的民族认同。新加坡华侨非官方的自发行为,包含了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意味,是晚清华侨民族主义酝酿的重要表现,这种超越政治实体的认同是华侨民族主义的基础底色,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有突出表现。随着保皇派与革命派将目光投向南洋地区,南洋华侨的政治认同在清政府、保皇派、革命派三者之间出现分化,但华侨民族主义在三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并非从一而终,而是与时俱进,最终选择了代表时代趋势的革命派,民族主义在超越乡土认同基础之上得到进一步升华。
[注释]
[1]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原序第28页。
[2]黄建淳:《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以赈捐投资、封爵为例》,台北:海外华人研究学会,1993年,第163~194页。
[3]参见颜清湟著,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1877—1912)》,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第49~88页;蔡佩蓉:《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第79~89页;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0~238页。
[4]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6页。
[5]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6~153页。
[6]《使英郭嵩焘奏新加坡设立领事片》,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3~15页。
[7]《丁日昌劝捐得力片》,光绪四年五月十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79页。
[8]《上海陈家木桥顺直山东等处赈局同人公启》,《申报》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六日,第三版。
[9]《上海陈家木桥协赈顺天直隶山东水灾公所粤闽江浙同人书》,《申报》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三版。
[10]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414页。
[11][12]《劝募河南水灾赈捐启》,《叻报》一八八八年一月四日。
[13]《捐款列登》,《叻报》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1.2.1 试验设计 试验于2018年3月26—27日在贵州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制茶研究室试验车间(贵州省湄潭县)进行。以团队前期研究结果为参考[9]选取各试验参数(表1)进行L9(34)正交试验设计,其中,揉捻压力为茶叶放入后加盖往下压紧实时的压力,即揉捻机加压力度。记录试验过程中叶相变化特征,检测其碎茶率,综合干茶样品的感官审评结果,筛选揉捻做形的最佳工艺参数。
[14]《乐善社宣讲聖谕恭纪》,《叻报》一八八八年三月三日。
[15]《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八九,光绪十六年九月甲午条。
[16]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201页。
[17]《求赈书函照录》,《叻报》一八八九年一月二日。
[18]《劝赈情殷》,《叻报》一八八九年二月九日。
[19]《捐款录闻》,《叻报》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三日。
[20][23][31]《论南洋中外官绅劝赈中原灾况事》,《叻报》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一日。
[21]《客民助赈》,《申报》一八七八年二月十五日,第三版。
[22][27]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1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30~131页。
[24]《赈款略登》,《叻报》一八八九年三月一日。
[25][26]《赈捐结册》,《叻报》一八八九年六月十八日。
[28]曾国荃著,梁小进整理:《曾国荃全集》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443~444页。
[29]《赠额旌扬》,《叻报》一八八九年八月十二日。
[30]《劝赈篇》,《叻报》一八八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32]周秋光、李华文:《中国慈善的传统与现代转型》,《思想战线》2020年第2期。
[33]《赈灾宜亟说》,《叻报》一八八九年三月四日。
[34]《桑梓情殷》,《叻报》一八八八年五月十九日。
[35]《赈务开捐》,《叻报》一八八九年十月三日。
[36]《报效情殷》,《叻报》一八八九年十月十七日。
[37]《第三次山东赈捐芳名登录》,《叻报》一八九〇年一月六日。
[38]《浙省赈捐》,《叻报》一八九〇年三月六日。
[39]《苏浙赈捐》,《叻报》一八九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40][41]《劝捐示谕》,《叻报》一八九〇年五月十六日。
[42]《札谕录登》,《叻报》一八九〇年七月四日。
[43]《有始有终》,《叻报》一八九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44][47]《劝办顺直赈捐兼换苏浙请将执照纪事》,《叻报》一八九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45]《开办赈捐》,《叻报》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46]《赈捐宜亟》,《叻报》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三日;《委办顺直水灾劝捐启》,《叻报》一八九一年一月三日。
[48]《义捐踊跃》,《叻报》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49]《停捐期届》,《叻报》一八九一年九月三日。
[50]《续劝东赈》,《叻报》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51]《劝募东赈》,《叻报》一八九二年二月四日。
[52]《东赈展办并添设分局告白》,《叻报》一八九二年五月十九日;《添请绅商劝募东赈》,《叻报》一八九二年五月三十日。
[53]《劝赈急启》,《叻报》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54]《开捐片稿》,《叻报》一八九三年一月五日。
[55][57]《鄂湘求赈》,《叻报》一八九六年六月十九日。
[56]《东赈展办并添设分局告白》,《叻报》一八九二年五月十九日。
[58][59]《送谢宾门东归序》,《叻报》一八九七年二月二十日。
[60]《远游助赈》,《叻报》一八九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61]《为民尽瘁》,《叻报》一八九六年五月五日。
[62]《送谢宾门司马东归序》,《叻报》一八九七年二月二十日。
[63]《劝募山西赈捐叙》,《叻报》一八九三年六月三十日。
[64][65][66]《来函照登》,《叻报》一八九三年七月十二日、十三日、九月二日。
[67][68]黄建淳:《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以赈捐投资、封爵为例》, 1993年,第187、178页。
[69]《招速领照》,《叻报》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四日;《催速换照并声明捐案告白》,《叻报》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传换部照》,《叻报》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七日。
[70]《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四〇,光绪二十年五月辛巳条。
[71]《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四三,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丙午条。
[72]《劝办粤东全省奇灾急赈启》,《叻报》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73]《急赈粤东奇灾第一次捐款照录》,《叻报》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74][75]《同济医院公启》,《叻报》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76]《隆商捐赈粤灾缘款照录》,《叻报》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77]《急赈粤东续捐善款芳名列》,《叻报》一八九八年五月九日。
[78]《粤东赈捐天字第八号缘部芙蓉埠安泰号经手》,《叻报》一八九八年五月十八日。
[79]李勇:《海外华人庙宇个案研究:天福宫组织、结构与功能(1840—1915)》,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主编:《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9~210页。
[80]《汕头请赈》,《叻报》一八九八年六月六日。
[81]《蔴坡华商捐赈汕荒第一次缘款录登》,《叻报》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五日;《砂朥越华商捐赈汕荒第一次缘款录登》,《叻报》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麻六甲华商捐赈汕荒第一次缘款录登》,《叻报》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廖内华商捐赈汕荒第一次缘款登录》,《叻报》一八九八年六月三十日;《槟榔屿华商第一次捐赈汕饥芳名录》,《叻报》一八九八年七月十九日。
[82]《捐助福州平粜第一次芳名录》,《叻报》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二日;《第一次捐办琼州平粜芳名录》,《叻报》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二日;《永春平粜征信录》,《叻报》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83]《坤甸商会电款赈灾广告》,《叻报》一九〇八年七月三日。
[84]《峇厘商会汇款赈捐广告》,《叻报》一九〇八年七月十日;《奉扬仁风》,《叻报》一九〇八年八月四日;《兹将安班澜中华商会募集粤省水灾赈捐芳名列》,《叻报》一九〇八年八月四日。
[85]《办理粤东急赈进支清单详列》,《叻报》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四日。
[86]《结册广告》,《叻报》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87]《垫赈灾黎》,《叻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四日。
[88]《劝捐改派》,《叻报》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89]颜清湟著,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1877—1912)》,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第49~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