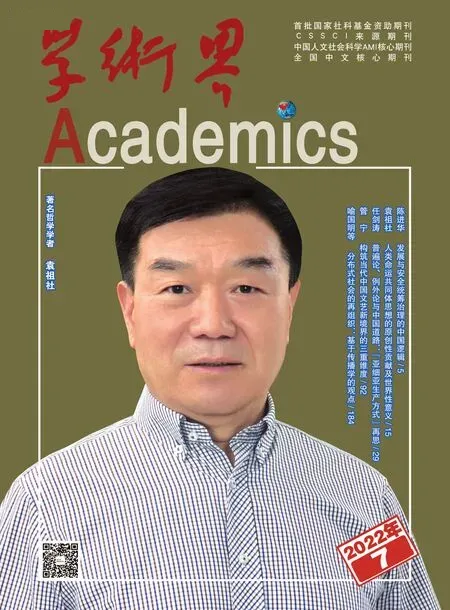当代文论的生产模式及“理论”话语的生成〔*〕
——以建构、语境和先验等概念为中心
2022-12-15罗崇宏
罗崇宏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贵州 贵阳 550035)
一、引 言
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理论中出现了所谓“理论死亡”、“后”理论、理论贫困等言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代“文学理论”愈益与“理论”叠加在一起,也即文学理论未必就纯粹地等同于关于“文学”的理论。正如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所说,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不存在“某种仅仅源于并应用于文学的独立理论”。〔1〕不仅如此,在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实践中,“从现象学和符号学到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并非仅仅(simply)关注‘文学’书写。相反,它们都出现在人文研究的其他领域,且都具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意义”。〔2〕究其原因,在当代“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之后,文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文学领域之外的“文本”,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书写”。〔3〕这些理论涉及到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电影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等,它们能从其他领域“旅行”到文学理论之中,是因为“它们提出的观点或论证对于那些并不从事该学科研究的人来说是启发性和生产性的”。〔4〕
当然,文学理论与理论的混同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重合,而在于人文科学之间理论的共通性。一方面“理论”可以被文学理论“拿来”使用,另一方面文学理论虽然终究是基于文学的理论,但“文学理论一经形成,就绝不仅仅关乎文学,还可以逸出文学的牵扯,以独立的方式表达对于社会、人生的理解”。〔5〕这就意味着文学理论与其他领域的“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渗关系,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各种观念和理论也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6〕不过理论之间的“旅行”也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经过了改造、融合和重新发现。如文学中的修辞旅行到史学领域便促使其生成了“叙事转向”。史学中的这种“叙事”是将过去的历史事件纳入到语言结构之中,并赋予这种结构某种意义,这样就把过去那种实证性的历史事实转变成为历史话语。
基于此,本文把当代文学理论生产概括为建构性、语境性和先验性等三种模式,以期对作为“理论”的当代文学理论有新的思考。
一、文化转向与建构主义
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建构性”与当代文艺思潮中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有很大关系。这种转向在史学领域也被称作“叙事转向”(the Narrative Turn)或修辞转向,也即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
从本质上看,这些“转向”的生成大多与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有关,或者可以从语言学理论中找到新理论知识生产的突破口。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说,“‘语言’给文化与表征的运作提供了一般性的模式(model),尤其是在广为人知的语言学方法中更是如此,作为符号科学的‘语言学’是作为建构文化意义的工具而被人们所研究的”。〔7〕这样一来,研究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性”势必要回到语言学的“元”理论——索绪尔的语言学。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分为“能指”(signifiant)与“所指”(signified)两个部分,它们就像一张纸的两个面一样不可分割,“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8〕不仅如此,能指和所指之间还是任意性的关系,也即“语言符号是任意的”。〔9〕不过,索绪尔随即对这种“任意性”作了补充说明,“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10〕实际上,语言的任意性中包含了约定俗成性和强制性,从而保证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保持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符号的语言就可以通过符号之间的对立或差异性关系来指示意义。不过,索绪尔只注意到语言的客观意义通过符号之间的对比来体现,却较少考虑到语言在使用中的意义问题。在这一点上索绪尔的语言学与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分析哲学之间有些相通之处。也就是它们都没有注意到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意义的复杂性,只是从语言的逻辑形式中寻找意义,认为“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形式而成为知识”。〔11〕于是,知识就成为了一种客观性的语言表达和陈述,而“陈述的意义取决于构成陈述的词或单个符号的意义,以及这些符号结合起来形成陈述的方式”。〔12〕
可见,不论是索绪尔、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语言哲学,他们的理论缺陷都是显而易见的。也即他们都大致遵循着一种“科学主义”的思维模式,认为语言与意义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语言可以表达一个较为明确的意义。但解构主义者德里达抓住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这个“漏洞”,认为这种“任意性”导致语言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能指与所指间的“错位”,也就是说语言不能表达单一而明确的意义。为了增加理论的说服力,德里达还生造了一个新词“延异”(Diffêrance),以此来打破西方“语音中心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这样一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语言观就为当代的“语言学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并认为真理或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由使用者在言语行动中建构而成的。此外,语言学理论向语用学方向的转向,使得语言哲学进入“日常语言学派”时期。这一学派的代表理论家J.L.奥斯汀(J.L.Austin)、约翰·塞尔(J.R.Searle)等人提出“言语行为理论”(A Theory of Speech-Acts),并将语言看作人的一种行为,而“言语行为不可能完全由一个句子显著的语义内容所决定”,〔13〕而是人为赋予的,也即意义存在于使用者实际的言语行动之中。这就将说话视为一种动力机制,它不仅要表达某种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表现了一种行为,因为“说出句子本身就是做我应该做或正在做的事情”。〔14〕
可见,“文化转向”之所以常与“语言学转向”勾连在一起,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转向借鉴了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所关注的是意义或知识如何从具体的言语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强调这种意义的生产过程所涉及的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冲突并达成协议的动态过程,并在此过程中真切地展现社会生活的固有逻辑。可以说,“文化转向”的核心是从语言/符号出发,关注意义/知识生产的话语机制,意义/知识并不是固定于文本中有待“发现”的实体对象,而是在语言/符号的运作中逐渐生成或呈现出来的,从而体现出其明显的“建构性”。
基于此,我们看到语言能够给知识/意义的生成提供一个动力机制,而不仅仅是知识/意义的承载者。这就使得对于知识意义的关注从“语言”延伸到了“话语”,而“话语‘合并’了语言和实践”,〔15〕其主体性与生产性决定了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机制具有“建构性”特征。事实上,当代文学思潮在经历了“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之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随之也出现了明显的“话语转向”。这种“转向”所带来的新的文学理论生产方式就从过去的“实证性”研究转向了“建构性”研究。因为“自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以来,意义与其说是被简单地‘发现’的,还不如说是被生产(建构)出来的”,〔16〕其重要标志就是将“话语”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架构。与之前的实证研究不同的是,“话语”研究的“建构性”使得传统意义上人的“主体性”被拆解,以至于何为“主体”常常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实,这当中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关于知识/意义如何生成的问题。在传统文学活动中,意义的流动大致经历了从作者→文本→读者,作者成为文本意义的中心和发源地,寻找意义“就是重现作者的世界”。〔17〕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观类似的是,E.D.赫斯(E.D.Hirsch)认为语言的类型和方式是文本意义的根据所在。〔18〕
然而,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法国的“作者”理论,以及接受美学旅行到中国之后,理论界也开始质疑:意义真的是从作者(起点)到读者(终点)吗?基于同样的思考,福柯与巴特分别撰文质疑作者在文本意义中的权威性和决定性作用。如福柯就对写作过程中的“语言”作了详细的描绘:
词语默默地和小心谨慎地在纸张的空白处排列开来,在这个空白处,词既不能拥有声音,也不能具有对话者,在那里,词所要讲述的只是自身,词所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闪烁。〔19〕
可见,在福柯那里“作者”是缺失的,在场的仅仅是自行其是的“词语”,那么究竟“谁是真正的作者”?〔20〕或者说是谁在说话?巴特的回答“是语言而不是作者在说话;写作是通过作为先决条件的非个人化,达到只有语言而不是‘我’在起作用、在‘表演’”。〔21〕于是,写作成了非主体性的行为,或者说作者的主体性被语言所剥夺。既然如此,“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22〕这样一来,作者并不是文本意义的唯一来源,甚至意义根本不来自作者而是来自多重性的社会关系,并汇聚于读者那里。与传统的文本意义从作家→作品→读者的流向相反,文本的意义不在起源处(作者)而是在终点(读者)。不过,作为意义“源点”的读者并非是“个人”,而是主体的制造者——话语,它是能够生产“主体”的更大的“观念结构”,以至于“一切有意义的存在都在话语之中”。〔23〕
此外,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兴起的“文化研究”理论范式,带动了“话语”主导下的“建构性”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paradigm),〔24〕源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话语将生活现实视为文化的“建构物”而非先天性的存在,现实生活是由复杂的结构构成的文化整体,尽管它是被“建构”而成的,但却不会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作为新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不再把“文化”视为客观的、需要对之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对象,而是将其看作意义生产的动力系统,“通过它,社会现实被建构,被生产,被阐释”。〔25〕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去寻求一种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26〕
就研究方法而言,文化研究不是对文本进行“实证性”研究,而是对之进行解释。在此过程中,文化研究“介入话语分析的模式而将‘社会’也视为一种‘文本’,从而已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文本研究”,也就是把文本的生产与消费也纳入到对文本意义的建构之中。“作家的写作意愿并不是独立自持的,而是已被纳入到了一整套文化生产的环节之中,而这又是与消费人群的需求紧密相关,也就是市场的生产与消费开始成为文本生产的导向性力量”。〔27〕由此,不但文本的意义在整个“文化循环”中被建构起来,而且即便是“作者”也被这个过程所建构,因为,“作者死了”,作者只存在于读者的消费需求之中。
总之,“建构论的主要特征是它认为知识(日常的和科学的)是其背景所形塑的建构物”。〔28〕而不论是“语言学转向”还是“文化转向”,在强调知识的“建构性”的同时,也将建构的过程置于一定的“背景”也即“语境”之中,因为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性与语境性生产是相伴而生的。
二、语境主义的生成
任何理论知识生产都离不开特定的语境,这在本文中特指文化研究意义下的“语境”(context),它类似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到的“场域”概念(field),是由不同位置间的关系构成的网络,而“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或潜在的境遇所界定的”。〔29〕在文化研究中,“文化不是某一社会集团的客观经验,而是一个生产意义和经验的领域”。〔30〕由此,本文把文化研究看作一种语境性的话语实践,它强调“语境”在生产意义/知识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此规避传统的普世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东西,因为“文化研究的本质是语境研究”。〔31〕
近年来,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之间的论争,其焦点就是“本质主义”的问题。本质主义所坚守的是“审美主义”的文学观,它常常将对文本的分析纳入到“宏大叙事”之中;而文化研究则强调文本的“语境性”,也就是文学场中的权力运作。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从“本质主义”思维模式转向“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的美学追求也从“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32〕向“日常生活审美化”〔33〕(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转移。关于美学的这种转移,在理论界还出现过一些激烈的争论,如从2003年起,在《文艺争鸣》《文艺研究》《河北学刊》等学术刊物上展开了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中心的学术论争,这是当代文学理论范式转移的典型事件。尽管以童庆炳为代表的老一代文艺理论家所坚守的“文化诗学”影响广泛,但以陶东风为中心的新一代理论研究者所推崇的“文化研究”理论范式最终占据了上风。
具体而言,虽然当代持“精英化”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其美学立场与黑格尔的美学观念有所不同,但本文姑且以黑格尔的美学立场说明之。黑格尔美学观念的核心就是认为“美是理念,即概念和体现概念的实在二者的直接的统一”。〔34〕很显然,黑格尔继承了自柏拉图以来的“理念论”,并提出“无论就美的客观存在,还是就主体欣赏来说,美的概念都带有这种自由和无限;正是由于这种自由和无限,美的领域才解脱了有限事物的相对性,上升到理念和真实的绝对境界”。〔35〕可以看出,黑格尔不仅将美视为“真”和“理念”,而且将它看作“无限”和“绝对”的东西,不受人的“知解力”和现实关系的影响。
与之相对的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仅把“美”从传统的象牙塔转移到“日常生活”,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美的无限性和绝对性,并将文学艺术置入“日常生活”这个特定的“语境”中去审视其美学意义和价值。于是,在当代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甚至生活也可以转化为艺术。此外,在以“消费”为主导的文化语境中,充斥于生活中的各种实物,作为特殊符号的表征而被赋予特殊的美学意义。如在商品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所消费的对象不仅是商品的“物”,更是商品所指示的文化符号。换句话说,在消费过程中与其说消费的是“物”,不如说在消费“符号”,也即符号所代表的地位、尊严和成就等,因而“无论是在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征逻辑里,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36〕
实际上,当代由“大众”话语所建构的“语境”/“场域”,最典型的就是“媒介环境”。而将媒介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语境”,得益于“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概念的启示。“媒介环境学”是从media ecology一词翻译而来的,media ecology开始被翻译为“媒介生态学”,后来经过国内媒介理论研究者何道宽与北美Media Ecology的主席林文刚共同提议,遂将Media Ecology翻译为“媒介环境学”,〔37〕其目的是“把媒介当作环境来理解”。〔30〕在“媒介环境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加拿大的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讯息”〔39〕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此后,在媒介与文化的关系中,不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文化选择论”,它们大致都将媒介视为一种“环境”/语境。即便是“文化选择论”认为媒介是文化的一种选择,也仅仅是在讨论“媒介”与“文化”孰先孰后的问题。
不过,在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那里媒介环境又被视为背景媒介(blackground medium)。为了阐明作为背景的媒介的力量,美国理论家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将麦克卢汉与哲学家海德格尔相提并论,并指明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如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和事物的遭遇并不呈现到意识中,而是静默地依赖于一种缄默的背景”。〔40〕哈曼的媒介背景论彻底地批判了技术决定论者(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的观点,认为将“媒介即讯息”理解为技术决定论,是“将背景中被隐藏的起着主导作用的媒介引到台前,可能会导致人类被贬为无望的傀儡,受制于非人类的背景媒介”,〔41〕因为任何媒介都不可能永久存在,只有人类能够决定下一个媒介的到来。而“媒介即讯息”真正表达的是,“加密的背景(cryptic blackground)总是比可见的表象更有力量”。〔42〕
基于此,本文在讨论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时候,将媒介视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语境的具体形式。尽管自近代以来,媒介与文学的关系一直密不可分,但当代大众媒介尤其是电子网络媒介兴起之后,媒介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生产语境或文化语境,媒介参与了文学意义的生产与运作。最典型的是在纸质媒介时代,在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这四个要素所构成的文学活动中,人们往往更关注作家的创作对于作品和读者的影响;而在电子媒介时代,电子媒介不仅仅充当文学的载体,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媒介语境中,新的文本特性得以生成或强化如超文本性、文本间性等使得一个文本可以以超链接的形式与多个文本链接起来。此外在网络媒介语境中,人的主体性也变得扑朔迷离,主体间性得以生成。
由此,当代新媒介语境中,“间性”理论逐渐成为热门话题。据黄鸣奋考证,“‘间性’(inter-sexuality)亦称‘雌雄同体性’(hermaphrodism),本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术语,指某些雌雄异体生物兼有两性特征的现象”。〔43〕在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中,“间性论”凸现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后现代特征,而文本间性、主体间性、媒体间性等新问题域的生成,也与新媒介所建构的新的话语语境不无关系。
三、文学理论的先验性
在进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时候,学界常常简单而固执地将理论源于实践经验视为唯一正确的途径,由此而将一种先验的理论生产看作空中楼阁式的、脱离经验事实的知识构建。殊不知,先验观念从来没有否认过经验的始源性意义。这里借用康德的“先验的”(a priori)概念,并非要去寻找那种独立于一切感官的、先天的知识,而是借用康德“先验”概念的部分语义,去阐释那种独立于经验的,甚至与源自经验的知识对立的理论知识。从知识的脉络来看,胡塞尔的逻辑学继承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也即知识或认识都“从经验开始”,但却并不由此都“源于”经验。虽然心理学的个别实在性是基于一种具体的直观,但逻辑学则基于有规律性的明见性,也即“纯粹性”(摆脱了经验杂质的)。
实际上,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经验性与纯粹性的区分。由此,本文借用“先验的”概念意在与源自文本实践的经验性理论知识相区别。这样一来,“先验的”文学理论知识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从其他学科“旅行”而来的理论知识;二是在已有理论话语的基础上进行延伸、改造和拓展而生成的新的理论知识。
前者是较为普遍的理论知识生产现象,因为“理论首先是由其他非文学领域产生的著作,不管它是哲学的、语言学的、心理学的或知识史的著作所组成的”。〔44〕实际上,当代生成于西方却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诸如心理批评、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存在主义,包括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它们并非来自纯粹的文学实践活动过程,而更多的是来自其他领域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从根本上看这些文学理论知识并不是从文学实践中获得灵感,而是把源自其他领域中的理论资源“移植”到文学理论之中,然后再与具体的文学实践相结合,构建起新的文学理论知识。
后者同样是常见的理论知识生产模式,如“后”理论话语语义场的生成、从“作品”到“文本”等概念的替换与流变等。“后”理论话语的生产在语词的使用上,最常见的就是在已有的理论语词前加上前缀词“后”,由此构成新的理论语词。与此类似的,还有加前缀词“超越”“新”“元”等构筑新词的也不乏其例。此外,就是类似于用“文本”替换“作品”的理论生产模式,通过概念的流变彰显理论话语的变迁。尽管从“作品”到“文本”仅仅是概念用语的变化,但概念的流变本身可作为文学理论变化的表征。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文化语境从“精英”向“大众”转移,同时与作品意义的稳定性相比,文本是一个意义无限的、无中心、可生产性的东西。〔45〕对于罗兰·巴特来说,从“作品”到“文本”的转移绝不是概念用语的变动,而是标志着罗兰·巴特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思想的转变,也即由把作品视为有确定意义的实体,转向把作品看作一个永远不能固定到一个单一的中心、本质或意义上去的无限能指的游戏。于是,作品和文本也各自成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对象和标志。可见,“文本”取代“作品”成为当代文学理论中的新“知识”,其背后所彰显的是理论思潮的更替,因为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是未完成的(un-finished),它本身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的实体,因而“文本概念所提供的是一个本身不完整的对象,而且该对象在互动性的阅读过程中将向自行出现的可能性开放。这一文本概念还把阅读活动置入过程之中,因为它不再像是一个消费的契机,而更多地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生产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自身又向尚难以预料的新的可能性开放”。〔46〕
不可否认,这些理论首先得益于丰富的文本实践的经验性总结,但这种理论知识的生成却大多是“先验性”的,它们甚至常常独立于文学的文本实践,进而遵循着“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这种“先验性”的知识生产悬置了经验性的文本活动和话语实践,直接通过理论演绎的方式建构起新的文学理论知识,似乎是在象牙塔里建构“空中楼阁”,但如果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直接移植西方理论资源的实际情形来看,很多理论的确是在西方强大理论资源的诱惑与冲击之下生成的。
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大众文化兴起至今,“大众”话语大致经历了从“批判”到“分析”再到“多元化”话语并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术界对于“大众”所展开的“法兰克福”式的大众批判遍地开花。后来很多学者不断地撰文对这种“大众”批判话语进行反思。如陶东风就认为“机械套用西方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而没有充分顾及中国本身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从中提出问题、理解问题,缺乏历史的眼光”。〔47〕
显然,对“大众”的文化批判与人文知识分子既有的“精英化”文化立场有关。但他们所择取的理论资源大多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即将“大众”视为“文化工业”时代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所宰制的、缺乏文化辨识力的对象,是一个被否定和批判的“Masses”群体。然而,西方的“Masses”批判话语是置身于“现代性”批判的时代语境之下的产物,“原因在于进入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进入了反现代性的语境之中,人们有感于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文明的倒退,进而向往前工业化时代的‘有机社会’,以此来批判被工业文明毒害的‘Masses’,这些‘Masses’已经成为只有‘群性’而没有‘个性’的零散而冷漠的原子符号”。〔48〕
之所以说这种“大众”批判话语不适合我们的实际情形,不仅在于中西“大众”包含着截然不同的群体,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言说语境也有天壤之别: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种种阵痛,所需要的恰恰是西方社会反思甚至唾弃的“现代性”力量。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实,即便是西方社会自近代就开始反思并试图遗弃的“现代性”,却是中国社会到了20世纪末也尚未完成或需要完成的社会进程。因而,将“大众”批判话语置入中国当代文化,其盲目性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与当代的“人文精神”批判相契合,但从根本上说,这种理论生产方式依然是“先验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具体情形,而是先入为主地将西方固有的理论知识置入中国的土壤之中。
诸如此类的理论移植还有“现代性”的话题。自近代以来中国理论界一直在呼唤现代性的发生,然而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现代性”常常处于未完成(un-finished)状态,“它只能在后来的革命和战乱中得到延伸”。〔49〕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亦步亦趋地沿用源自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话语,去分析和评判中国本土的文化现象和文学思潮。可以想象,这种“先验”式的理论生产带来的“理论错位”在所难免。
不过,由此也带来了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理论知识的问题。“先验”的理论知识生产势必会出现“水土不服”,但这是否意味着放弃或拒斥西方理论知识,从而彻底改变这种“先验的”理论生产模式呢?就目前本土理论知识生产的现状来看,这种做法显然也是不可取的,或者说这种绝对拒斥西方,完全回归本土的做法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实际上,近几年来理论界在有关“后殖民”的讨论中,所涉及到的诸如“东方”与“西方”的问题,或者说“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以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等,都与这种“先验”式的理论建构模式有许多相通之处。然而这些“旧题”之所以一再被提及,根本之处在于无论是拒斥“西方”还是全盘接受之,都将被置于两难的境地。其实,我们本土理论生产能力的贫弱才是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症结所在。正如汪琪在《本土研究的危机与生机》中谈到的,“全盘承袭西方理论”不是问题的结果,“自己不事理论论述”才是原因。正因为如此,“没有自己的理论,就只能借用现成的理论架构来从事一些数据分析的工作”。〔50〕
不可否认,“先验的”理论生产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但也同时认为知识“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的理念,〔51〕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打开了便捷之门——移用现成的理论知识,尽管它未必都来自文学的文本实践经验。而目前国内理论界提出的所谓“理论死亡”“反理论”,以及对理论阐释力的质疑等言论,的确指出了理论生产与理论指导实践的诸多问题。但目前学界普遍存在的热衷于文本实践研究或“实证”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理论生产能力贫弱的境况。尽管缺乏文本实践经验的文学理论知识会流于空谈。但从逻辑上说,我们一旦拥有了文本实践的经验知识,那些“先天的”理论构架就开始起作用。
事实上,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必然会将理论的构建,建立在已有的中国古代文论以及西方文论的基础之上,并以此展开“先验”式的理论演绎,而非纯粹的原创。就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具体情形看,当代文学理论一方面从中国传统中去寻找理论资源,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则是从西方引进新的理论知识,而这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主要知识源泉。
可以说,理论的先验性一方面说明理论知识未必都来自于文本实践经验,而是在既有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逻辑演绎和推理;另一方面,理论的先验性也彰显了理论的不可实践性,也就是说理论上的论证未必都要在实践中去验证,很多时候也无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它可能仅仅存在于理论层面上是“通”的。然而,无法验证的或者不需要验证的“理论”未必就意味着它的非真理性,比如理论上说人人都会死、地球和宇宙最终都会走向毁灭等,尽管我们无法进行完全地验证,但我们依然认为它们带有“真理性”。
目前,在国内与文学理论“先验性”不谋而合的,还有学术界刚刚兴起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学术观点。〔52〕而在国外,类似的理论观点也很普遍,库恩的“范式”(Paradigm)理论就在某种程度了暗合了理论知识的先验性。正如英国史学家昆廷·斯金纳(Skinner,Quentin)所说,“我们赖以检验我们信念的是各种事实,而我们进入事实的路径总是经过过滤的,而从事过滤功能的就是库恩所称的我们已有的‘范式’,或者理解框架。说得更明白一点,本来就没有任何事实独立于我们用来解释它们的理论”。〔53〕换言之,任何从文学实践得来的知识都需要借用某种“先验”的理论进行阐释,从而在实践知识的基础上出现“添加部分”。如前文所述,本文移用康德的“先验”概念,并非否认文学理论知识源自文学文本实践,而是强调理论知识相对于文学文本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就像范式知识的继承性那样,“人们从前辈那里接受过来作为研究开展的基础,继而在研究中发展和完善它们,然后再以发展完善的形式,作为被接受的知识传递给下一代人”。〔54〕尽管“理论先行”一直为学界所诟病,但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先行”却是理论知识生产的常见形式,更何况这种“理论先行”还常常体现在对理论知识的继承上。
综上所述,如果说文学理论知识源自文学文本或经验性材料,那么,这些材料本身也具有先验性。实际上,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简单地遵循着从实践到理论的路数,也即遵循源自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精神”或“实证主义”(positivism)。在孔德那里,与“实证”概念对应的语义场大致有“真实”“有用”“肯定”“精确”等,〔55〕而“实证精神”则是指“按照实证词义的要求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审慎缜密的考察,以实证的、真实的事实为依据,找出其发展规律”。〔56〕具体而言,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人们通常会认为文学理论一定是从文学文本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实证性材料中总结出来的。而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首先需要针对文本实践或材料提出问题。在这一点上,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如科林伍德就认为“历史研究并不是从搜集、思考那些未经解释的粗糙事实开始,而是要先提出问题,这个问题会让历史学家去寻找有助于解答它的事实”。〔57〕这么说,很容易让人产生理论先行的错觉,实际上“要提出问题,就得具备对各种可能史料最低限度的认识”。〔58〕也就是说,作为文学理论的研究材料,其先验性并非是指文学理论完全脱离开具体的文本实践或文学事实,而是在对基本的文学“材料”了解的基础上,带着问题意识去重新发现和搜集材料。因此可以说,没有材料就不会有问题,反之,“不提出问题,更不会有资料。正是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使过去留下的痕迹变成史料和资料”。〔59〕如在研究五四时期“新文学”特质的时候,我们的关注点不外乎是这种新文学大多使用现代白话文写作,以及新文学区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精神。就这个问题来说,那些依然延续古典文学样式的古体诗和文言文等就不会成为有关“新文学”问题中的“材料”,甚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书写都很少关注那些古典文学的文本实践。
四、“理论”话语的生成
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大多是在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的理论视域中完成的。这当中经历了建构主义、语境主义以及先验性等几种生产模式,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历时性逻辑关系,而更多的是基于语言论基础上的共时性关系,因而可以把当代文学理论生产模式概括为一种语言论模式。后者之所以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总体模式,就在于语言论将文学的意义视为在具体的文学活动中生成的,而非实证性地蕴藏于文学文本或文学活动之中。这样一来,文学研究就从以“文学性”为中心的美学研究,转向语言如何生产意义,以及话语表征的后果及影响等研究,也即转向文化的诗学与政治学。〔60〕于是,文学意义的源头就从经典文学作品扩展到同样具有文学性的社会文本,也就是所谓文学性的泛化,其外在表现是将传统意义上非文学性的事物诸如大众文化、社会文本以及一些承载特殊意义的符号等,都纳入文学的问题域中进行关照,进而探究其诗学与政治学。
如此一来,由文化转向带来的建构主义、语境主义和先验性等话语模式,在进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同时也促使文学理论走向理论,也即理论转向。这就意味着,文学理论并不仅仅是“研究文学普遍规律的学科,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任务”,〔61〕或者仅限于研究文学的原理、范畴和标准,〔62〕而是吸收了文学领域之外的理论资源,诸如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媒介批评等,它们成为文学理论,大多是其他领域的理论旅行至文学领域的结果。毋庸置疑,精神分析的对象是人的精神心理;女性主义则主要讨论妇女的权力和地位,在对抗男权文化的过程中彰显女性的性别意识;媒介研究则将文学的载体或传播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此讨论媒介在文学意义生成中的独特作用。这些作为文学理论的“理论”,其思考的对象显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涵盖了文学性泛化之后的社会文本。
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研究逐渐渗透于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之中,其结果是“作品”渐次为“文本”所取代,因为“影响作品概念的新变化,并不一定源自其中的某一学科的内部更新,而是来自这些学科的相遇,它们所汇聚的这个对象传统上并不属于它们的范围”。〔63〕这种学科之间的相遇过程也就是“从作品到文本”的生成过程,并促使文本理论逐渐成为当代文学理论中的“显学”。而文本理论生成的前提条件是,“旧的学科体系之稳固状态瓦解时才有可能,甚至要动摇通行的方式,从而产生一个新的对象、新的语言,它们都不属于人们可以平心静气面对的科学场域”。〔64〕可以肯定的是,罗兰·巴特所说的“学科体系”主要针对的就是“文学理论”知识体系。而一直以来为学界所耳熟能详的“文学理论”则基本沿用了英美新批评的话语模式,也即将文学理论视为“研究文学普遍规律的学科”。〔65〕
于是,文学理论的定义可以修改为“研究文本普遍规律的学科”。与之相对应的,作品、文学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大,最终文学理论也被更具涵盖力的“理论”所取代。对此,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以“理想-类型”(ideal-type)来概括“理论”,认为“理想类型的形成是由片面地强调一个或多个观点,并将大量弥散的、离散的、或多或少存在或偶尔缺失的具体个体现象综合起来的,并根据这些片面强调的观点排列成一个统一的分析结构”。〔66〕简单地说,韦伯将理论概括为一种统一的“分析结构”(analytical construct)。在这一点上,当代美国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理论”观点与之不谋而合,“理论是分析和推测”(analytical and speculative)。〔67〕同时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lser)也提出“理论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思维工具”。〔68〕而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则用“句法特征”(syntactic feature)、“规范性结构”(normative structure)等概念概括其“宏大理论”(grand theory)思想。〔69〕由此,国内学者黄卓越将这些言论表述为“对世界事物的概念化抽象,当然不是抽象到本体论之上,而是对社会、人性、文化等经验事物的区域化、类分化抽象,从而将之视为一种均势化与理想化的知识解释模型”。〔70〕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特指某个特定领域的“分析结构”,作为概念的“理论”就变得异常抽象和难以界定,因为即便是一些大理论家的理论话语也大多具有明确的专业指向性,而不是给所有的学科知识立法。C·赖特·米尔斯对此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宏大理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对思维层次的最初选择,这种思维层次如此笼统以致于实践者无法从逻辑上深入观察”。〔71〕关于何为纯粹的“理论”(theory)而非文学理论的问题,也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文学理论入门》一书的开篇就把它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而对于各种理论充斥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单独将“理论”作为问题提出来总让人有些不知所措,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的确是意想不到的困难。它既不是任何一种专门的理论,也不是概括万物的综合理论”。〔72〕
可以说,理论话语的生成与文学性的泛化、从作品到文本等文学事件不无关系。而“理论”取代“文学理论”不仅仅是概念术语的更替,“‘理论’已经使文学研究的本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73〕尽管依然作为研究文学的“理论”,但它“不是对于文学本质的解释,也不是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的解释”,“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著作”。〔74〕当代从西方旅行而来的诸如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空间研究等,它们能够成为研究文学的“理论”,是因为“它们提出的观点或论证对那些并不从事该学科研究的人具有启发意义”。〔75〕与之类似的是,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认为“某种仅仅源于文学并仅仅适用于文学的独立理论”是不存在的。〔76〕
从卡勒和伊格尔顿的理论话语可以看出,走向理论的文学理论其源头并非仅仅来自于文学,而是可以从其他学科知识领域旅行而来,也即文学理论源头具有“先验性”。与之相呼应的是,国内以金惠敏为代表的学者则提出文学理论服务对象的“先验性”,也就是“正如文学作品可以反作用于社会一样,文学理论也可以不经介入创作而直接地作用于社会”。〔77〕不过,关于文学理论的这种“先验性”言论,也被以张江为代表的国内学者视为一种割裂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忽视中国文学研究的本土性和地域性,进而导致文学研究从理论到理论或唯理论倾向的“强制阐释论”。〔78〕
不可否认,强制阐释论很好地概括甚至击中了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要害之处,也就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或文学作品之间的脱节。不过,强制阐释论以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热议的“文论失语症”,〔79〕在批判“理论至上”以及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的同时,批评者本身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尽管理论生产者从理论到理论进行逻辑演绎的确脱离了文学实践本身,但也应该看到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本身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它们应该有区别于具体文学实践的理论特性,也即前文所述的“先验性”。而且,即便是提出“文学性”(literariness)概念,并将文学理论视为研究文学本质的形式主义者,也并不认为文学理论就是关于“文学”的“理论”,他们认为“文学理论的对象不是作品,而是文学话语,而文学理论也将与另一种话语科学一样,这种话语科学将必须是为每一种语言而建立起来的”,或者说形式主义者“并不关心对任何具体作品从其自身着眼所作的评价和描述,它不是文学的批评,而是对批评的假定事实、文学对象及其各局部的本质的研究”。〔80〕从根本上说,以文学性的探究为理论旨趣的形式主义,重在将现代语言学理论或科学话语先验性地应用于对文学叙事中“如何”(how)的研究之中。
总之,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的建构主义、语境主义和先验性等模式,为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的观念转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构主义和语境主义强调文学意义的生成性与流动性,而先验性生产模式则直接将文学与理论疏离开来。前者将其言说基础建立在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的理论视域之中,使得文学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将文学基本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后者则将“跨学科”思想引入文学理论知识的构建之中。由这三种文学理论生产模式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文学理论走向理论,也就是“理论”话语的生成。
五、结 语
将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划分为建构主义、语境主义和先验性等三种模式,其核心意旨在于强调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的话语表征。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划分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建构主义和语境主义意在突显以语言论思维为重心的文学意义的生成性,而先验性则主要关注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的“独立性”,也即区别于文学实践的特殊性。而不论是建构主义、语境主义抑或是先验性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它们既是当代文学理论的生产模式也是生产方式,其生产的结果都可称为“理论”。
在当代学术界,这种以语言论为中心的建构论、语境以及先验论常常以“话语”的形式呈现出来,由此生成了所谓的“话语转向”(the discursive turn)。而话语转向的理论资源除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discourse)之外,还包括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一切均在文本中”(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81〕以及以此引申出来的“一切均在话语中”(nothing exists outside of discourse)等言论。〔82〕其话语核心在于强调“语言对世界具有强有力的客观化功能。依据这一原理,现实世界其实并不是在语言活动之外的自在自为的存在,毋宁说,现实是经由人的语言活动建构的产物”。〔83〕
尽管学界早已指出以“语言论”为基础的文学理论有其理论的局限性,却没能找到好的解决方案或突破口。于是,事件论和批判实在论的兴起,以及由此生成的各种“后理论”,试图寻找一个不同于语言论甚至“反语言论”的理论生产路径。〔84〕与语言论不同的是,事件论在“连通物我、统合文史、融通背景与前景”中,强调文学事件的过程性、生成性、历史性和物质性;〔85〕而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则明确“选择物质而不是事件,静止而不是流变,自主而不是情境,非关联而不是关联,独立而不是建构,某物是什么而不是能做什么”,并认为像情境、关联和建构等曾经具有创见的哲学范畴,已经不再具有解放的力量。〔86〕
从根本上说,不论是事件论还是思辨实在论都是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论的反驳,在此基础上出现的诸如“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超越语言学转向(transcendental linguistic turn)〔87〕等都试图在语言学转向理论的“贫困”之处有所作为。而“后人类”(posthuman)则直接宣称它“不是后结构主义的,因为它不在语言转向或者其他解构的形式下发挥功能。因为不是由意指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建构而成,后人类主体并不一定要在一个本质上无力予以应有重视的体系中寻找自我存在的充分表征”。〔88〕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由于‘理论’就建立在主流语言论基础之上,主要盛行于英美学界的后理论引入事件思想作为推进口,便是很自然的选择,这也使得后理论研究超越似乎正在慢慢陷入某种瓶颈的英美范式而介入欧陆动力,获得了内在中介与新的生长点”。〔89〕然而,实际情形却是,不论是英美还是欧陆都在延续并深化语言论。在这种情形下,事件论抑或是实在论能否全面取代语言论而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更有可能的是,实在论或者事件论实际上并没有推翻自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以来的语言建构论,而更多地是对语言论的一种补充或深化。
注释:
〔1〕〔2〕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6,pp.vii,vii.
〔3〕〔4〕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3,4.
〔5〕邢建昌:《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6〕Edward 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26.
〔7〕〔16〕〔23〕〔60〕〔82〕Stuart 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London:Open University Press,1997,pp.6,5,44,6,6.
〔8〕〔9〕〔10〕〔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8、102、104页。
〔11〕〔法〕高宣扬:《实用主义和语用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87页。
〔12〕Michael Dummett,Frege:Philosophy of Language,London:Gerald Duckworth,1973,p.2.
〔13〕JohnR.Searle,“Literary Theory and Its Discontents”,in Daphne Patai and Will H.Corral,eds.,Theory’s Empire:An Anthology of Dissen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149.
〔14〕J.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6.
〔15〕〔英〕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孔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9页。
〔17〕E.D.Hirsch,“Objective Interpretation,”PMLA,vol.75,no.4(Sep 1960),p.478.
〔18〕E.D.Hirsch,Vilidity in 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p.27.
〔19〕〔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393页。
〔20〕〔22〕Michel Foucault,“What is an Author?”in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 eds.,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Tallahassee: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48,148.
〔21〕〔法〕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作者之死》,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07-508页。
〔2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25〕〔30〕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15、15页。
〔26〕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p.5.
〔27〕黄卓越:《“文化研究”若干问题再探》,《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8〕〔英〕吉尔德·德兰逖(Gerard Delanty):《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张茂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
〔29〕〔法〕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31〕〔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我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郎静译,《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12期。
〔32〕〔34〕〔35〕〔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42、149、148页。
〔33〕M.Featherstone,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2nd edition),London:Sage,2007,pp.65-72.
〔36〕〔法〕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6-67页。
〔37〕何道宽:《媒介环境学辨析》,《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38〕〔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39〕McLuhan Marshall,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California:Gingko Press,2013,p.17.原文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40〕〔41〕〔42〕〔86〕〔美〕格拉汉姆·哈曼:《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黄芙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2-133、136、135、242页。
〔43〕黄鸣奋:《网络间性:蕴含创新契机的学术范畴》,《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44〕〔美〕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理论中的文学》,徐亮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页。
〔45〕〔63〕〔64〕〔法〕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钱翰译,周启超主编:《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第2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154-157、153、153页。
〔46〕McGowan Kate,Key Issues in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New York:Open University Press,2007,p.13.
〔47〕陶东风:《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48〕罗崇宏:《浅议西方语境中的“Masses”理论及启示》,《新疆社科论坛》2015年第5期。
〔49〕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序”,第1页。
〔50〕汪琪:《本土研究的危机与生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5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页。
〔52〕这一观点的支持者有金惠敏、肖明华等人,他们大致从美学的和文学性的角度讨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相对独立性,与本文的基本观点类似。
〔53〕〔54〕Skinner,Quentin(ed),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0,89.
〔55〕〔56〕〔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3-34、iv页。
〔57〕〔58〕〔59〕〔法〕安托万·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增订本,王春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4、79、80页。
〔61〕〔65〕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3、3页。
〔62〕〔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今言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页。
〔66〕Max Weber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dward A.Shils And Henry A.Finch,Glencoe:The Free Press,1949,p.90.
〔67〕〔72〕〔73〕〔74〕〔75〕〔美〕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16、1、1、4、4页。
〔68〕〔德〕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lser):《怎样做理论》,朱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页。
〔69〕C.Wright Mills,Sociological Imagin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33-37.
〔70〕黄卓越:《理论的降解与泛论文化的趋势》,《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71〕C.Wright Mills,Sociological Imagin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33.
〔76〕〔英〕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二版序,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77〕金惠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页。
〔78〕张江:《理论中心论——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说起》,《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
〔79〕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80〕〔美〕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页。
〔81〕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163.
〔83〕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84〕这方面的著作有国内学者刘阳的《事件思想史》、张进的《物性诗学导论》,以及美国学者格拉汉姆·哈曼的《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迈向思辨实在论:论文与讲座》等。
〔85〕张进、张丹旸 :《从文本到事件——兼论“世界文学”的事件性》,《文化与诗学》2017年第1期。
〔87〕〔加〕南希·帕特纳等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55-587页。
〔88〕〔意〕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后人类》(The Posthuman),宋根成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6页。
〔89〕刘阳:《当代事件文论的主线发生与复调构成》,《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