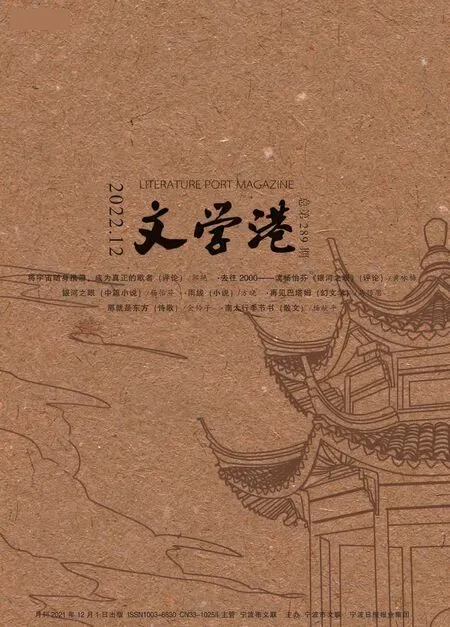去往2000
——读杨怡芬《银河之眼》
2022-12-13黄咏梅
□黄咏梅
“到2000年就好了。到那时候,每个人都有闲心读诗写诗了。2000年啊,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到那个时候,物资丰足,大家过上了平等和体面的生活……”两个城里的年轻人,跑到舟山峙中岛,在这个“比大地尽头更远的地方”,意气风发,各怀心愿,畅想2000年。彼时,是1984年。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都有过在描红本上描绘自己2000年的理想的经历,这个时间节点,可以说是伴随着我们“70后”一起成长的。而事实上,对这个巨大又浩瀚的未来,我们大多是处于迷瞪年纪中的认知——2000年=理想。而理想是少年时代的易变物,大多指向逃脱现状的彼岸。16岁的海岛少女小葵也有自己的理想——“她看到了进了城的自己,说着好听的普通话,说着同样好听的英语,穿着好看的裙子,对着她好看地微笑。”听起来,这不能算是理想,而是某个少女的心愿。但这的确就是一种理想,是她的,也是整个渔村的,更是那个年代所有乡下人的。到城市去,在上世纪80年代大多乡下人眼中看来,就是去往2000年。
杨怡芬的小说《银河之眼》里,不断出现“乡下人”,以及在那个年代与之天然相对立的“城里人”,这两个词,两者之间,仿佛天堑,又仿佛与舟山本岛隔着海水的一个个孤岛。既有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写乡下人努力改变命运进城的小说,势必也是一个弱者成长为强者的过程,作家要极尽能力将这两个词之间的桥梁、坎途搭建起来,需要有付出,有丧失,有强烈痛感,甚至耻感。读者阅读这些故事,势必想要从中读到一种逆袭之爽,或者读到与当初自己履历对应得上的种种慨叹与唏嘘。这类小说多如牛毛。好在,杨怡芬并没有遵循这种人为的写作 “传统”。在 《银河之眼》里,看不到所谓的弱与强,落后与先进,卑微与傲慢之类的二元对立,城与乡之间,如同敲开的一只鸡蛋,蛋黄是中心,蛋黄被蛋白清清淡淡地包围,而不是侵略。获得这种阅读感受,得益于杨怡芬对“乡下人” “城里人”这两个阶层宽厚的理解,并通过年代感十足的生活细节将这些理解细腻地传达出来。
虽然是乡下人,小葵却出生在一个略有不同的家庭,她有一个不断会从海外寄钱过来的爷爷,这些经济收入往往作为小葵父亲梦想的投资,投入“那些无用的,却把他和周围的人区别开来的东西”,譬如水泥地坪、卡式录音机、邓丽君磁带、 《Follow Me》磁带、时髦的洋装等城市物标,这些东西,具体地一点点地将城市想象注入小葵的成长中,小葵对城市以及城市人的理解注定与其他村里人不一样:她知道未来会有煤气灶,她觉得电视上看到的城市女孩跟自己没太大区别,她读过很多小说,从《嘉莉妹妹》那里略略领悟了一点乡下女孩不可丢失的尊严感,她甚至已经拥有了一条为城市生活准备的漂亮裙子……某种程度上看,她已经被局部城市化。这是原生家庭带给她的影响。不过,即便这样,杨怡芬并没有刻意去回避乡下人对城市的向往,也没有修饰乡下人对城市人的迎合讨好。小说从开篇就在预备一次隆重的招待——小葵哥哥领着城里的同事小张、小章来渔村玩。为了小葵哥哥能留在城里,举全家之力招待单位领导的儿子,不惜卖掉小葵那头心爱的牛,仅仅为了城里的这两个人来小住时能追上连续剧《血疑》。这是小说里唯一的乡下人与城里人面对面的碰撞。举全家之力奉献出来的“精华”,的确挽回了一些城里人对乡村的傲慢与偏见,但没有自来水、不通电的小岛、用便桶之类的乡村现实,不可避免地助长了两个城里人的优越感。杨怡芬并没有配合这些优越感。如同两个城里人问岛上一个老妇这样是不是生活不方便时,老妇回答: “有蜡烛啊,还有煤油灯。有井水啊,还有溪水。没啥不方便的。”这回答令两个城里人相当失望。显然,这回答也不是历来这类小说的“标准答案”。在小葵因为这回答生出感动的同时,我也被打动了。本来就是啊,这就是生活本身,不夸大苦难,不卑不亢,不为了凸显某个阶层而故作贬损姿态。杨怡芬真实淡然的人生态度,在这篇小说里使得贫穷处处获得了尊严。

最能体现杨怡芬这个小说匠心的,我认为是对小葵两段“性遭遇”的处理。她的初吻,被从小一起长大的田雷哥哥夺去了,她没有允许他更进一步,因为知道他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人,更不能接受的是,他预判她的未来会跟大多数乡下的女孩子一样,嫁人生子,而他笃信在农村守着政策的变化,命运会带给他好运。与其说小葵不喜欢田雷,不如说她不喜欢被这样轻慢。另外一段写得非常精彩,城里来的小章在跟小葵短短的相处之后,一个晚上,躺在满天璀璨的星空之下,将手伸向熟睡的小葵的身体。小葵先是被吓住了,接着有了生理反应,最终,这双手没能继续游走下去,它终止于一阵他人翻身的声响。这个情节,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被“侮辱与损害”,一次城市人对乡下人的亵玩。说实在的,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点担心小说会落入那种常见的套路,担心小葵终于要像“嘉莉妹妹”那样,跌落通往捷径的陷阱。好在,这是杨怡芬笔下的小葵。在往后的若干年中,在一步步依靠自己的努力走向城市的过程中,小葵会不断回味起那双手,回想起那个文艺兮兮的小章,最终还找了个像小章那样的丈夫,甚至成为一个城里人后与小章邂逅,还幻想能再续那段“少年事”。那双手,散落于小葵成长岁月的角角落落,小葵对那双“手”的态度,是喜欢的。她当年的不拒绝并不是出于虚荣,更不是为了讨好城里人,而是伴随性意识成长萌生出来的一次混杂着好奇、愉悦与享受的体会。之所以没让自己这种喜欢漫溢出来,是因为,小葵一贯清醒地知道:一个人一喜欢你就对你动手动脚,那么,这喜欢里头,有几分尊重呢?小葵要尊重,多过喜欢。而这份尊重,人家也不会轻易给,只有自己慢慢挣,可能,比攒钱还难。这种处理方式,与其说是对同类作品的一次反转,不如说就是杨怡芬的宽阔和真实之处。小葵是照着人的逻辑生长的,她在杨怡芬的笔下获得了尊严和光彩,也使这篇小说具有了高级的品质。
小说的结尾,那些站在1984年的年轻人终于来到了2000年,他们得到了各自的人生。小葵通过读书、考试,按部就班成了城里人,工作稳定,吃皇粮,结婚生子;好不容易留在城里的哥哥遭遇了下岗;紧跟制度脚步的田雷果然当了副乡长,过着老婆孩子在城里、他在城乡之间两头跑的生活;那个城市人小章呢?那个小葵青春期喜欢过的人,泯然成为一个平庸的中年人,当某一天,他们不期而遇,平等地站在同一片天空之下,他逃走了……这结局,并不是反转,更谈不上逆袭,这不是小说给出的结局,而是事实,是时代的浪卷,将他们拖曳到了这样的命运里。而这一切,发生在那双银河之眼的注视之下。
跟我一样,杨怡芬也是艾丽丝·门罗的忠实粉丝。门罗有很多小说热衷于书写农民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并不是为了体现某种对立或和解,而在于对那些津津有味、精工细作地把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区隔开来的做法进行嘲讽、戏谑,甚至败露出他们的不堪、脆弱、虚伪。杨怡芬从门罗那里得到了力量。 《银河之眼》里所涉及的乡下人、城里人两个阶层,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尚未开启城乡转换之前,从任何角度看分野都很显著,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大量的文学作品呈现乡土女性进城,着力突显她们被侮辱和损害的困境,《银河之眼》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常态,小葵是在无任何外力破坏下自然成长,她跟我们这些“70后”女性一样,于时代的波澜中起伏,于起伏和摇摆中,逐渐坚定了自我。不能说杨怡芬对乡下人和城里人的态度扭转了一种既往的认知,但起码是有所改变的。小说借小葵反驳大城市男朋友的话,巧妙地说出了作者的看法: “跟那些发达国家的人比,你可不也是一个乡下人?”所谓的阶层之分,哪里是一成不变的?那几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城里人不都难以逃脱命运之网?所谓阶层高下之偏见,亦不过是不完整的自我在动摇在作祟。我觉得这既是杨怡芬的见地,也是她的勇敢。
我特别欣赏《银河之眼》对那个时代的还原,物候、氛围甚至一些标志性的流行物,于我而言都特别亲切。大概因为我跟杨怡芬同属“70后”,成长背景相近,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时借由小说返回那段少年时光,会回忆起那个去往2000年途中的自己。与小葵不同的是,她是顺时光面朝未来,而对一个迈入中年的“70后”读者,2000年已经是逆时光回首往事,如同月亮刚好行经星河拱桥之下,我与小葵在顺流逆流中也正好相遇。这一切,也都是在那双眼的注视下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