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外交研究 服务大国外交
2022-12-12任远喆
任远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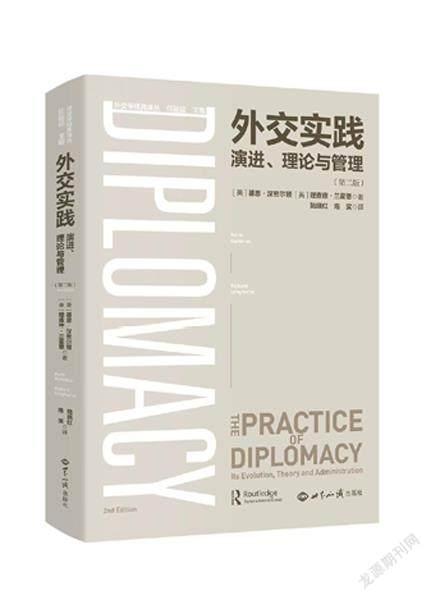
外交是跨越历史的实践方式。透过人类学家的视角,外交在人类不同群团关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外交是文明发展的产物,避免了国家间关系被武力单独主导。外交随着不同时代的政治特性时而备受推崇,时而充满争议。外交是安邦治国的艺术,历史上大国兴衰无一例外都面对军事与外交之间的张力,天平向哪一方倾斜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其根本目的是塑造国家昌盛、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良好外部环境。从上述意义来看,专门进行外交研究的外交学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
在社会科学的知识谱系中, 外交学是一门蓬勃发展的年轻学科。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 dNicolson)在20世纪初出版了经典的《外交学》一书,奠定了外交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体系。此后,国内外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外交学著作相继问世,从历史、思想、规则、方式等方面逐步构建起学科体系的“四梁八柱”。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外交“普遍忽视”,导致外交研究门庭冷落、成果寥寥,几乎完全成为国际关系的“附属品”。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发展使外交活动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日渐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外交学研究的复兴和繁荣,其学理建构日臻完备,学科边界日渐清晰,学术共同体日益形成,“找回”外交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外交学的发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交研究理论化有所提升。一直以来,外交学始终带有“重实践、轻学理”的标签。理论来自实践,高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冷战结束后,丰富的外交实践为外交学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土壤,同时外交理论化也因远远落后于实践而饱受诟病。以美国学者保罗·夏普(Paul Sharp)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一直努力将外交学理论化,也取得了积极成效。
第二,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深入。外交学从建立之初就带有跨学科的特点。除国际关系学科之外,外交学借鉴了许多其他学科的智慧,包括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等。随着外交领域的不断扩展和外交方式的极大丰富,外交学交叉融合学科的属性体现得更加明显。最近几年具有代表性的外交研究成果中,这一特点多有体现。例如,美国学者马库斯·霍姆斯(MarcusHolmes)将社会神经科学运用于国家间意图的判定,强调外交官之間的会面对理解彼此意图具有实质性影响,应该更为积极地开展面对面外交。
第三,聚焦外交沟通的新模式。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带来的外交变革一直是外交学界关注的重点。牛津大学科尔内留·波乔拉(Corneliu Bjola)教授团队围绕数字外交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在国际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云外交、虚拟访问等新的外交方式层出不穷,正在以实践发展引领数字外交的理论创新。当然,数字外交永远无法取代面对面的外交,但是科技创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重构外交制度。外交沟通在逐步适应数字时代。
外交学的发展还得益于人们对于外交兴趣的不断上升。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乌克兰危机影响深远、大国博弈与地区热点交织、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新冠疫情持续延宕、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许多问题都成为外交需要应对的重要议题。
今天的中国,正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外交工作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形势和任务不断变化。这不仅对外交实践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规模日益壮大的中国外交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外交学研究的经典著作、最新成果和学术前沿可以为构建中国外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借鉴,助力我们早日实现当年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提出的“把外交学中国化”的夙愿。
(本文为“外交学经典译丛”总序,本刊有删节,题目为本刊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