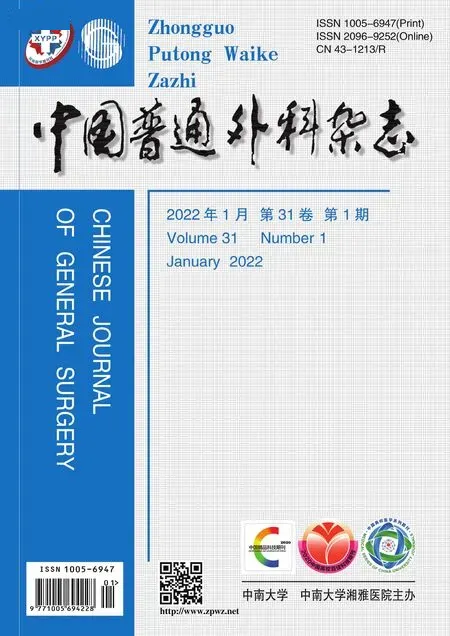脾切除对肝硬化门静脉高压脾功能亢进患者影响的研究进展
2022-12-12王建雄魏丰贤谢文强马尚贤王满才郭小虎王哲元魏振刚张亚武徐小东
王建雄,魏丰贤,谢文强,马尚贤,王满才,郭小虎,王哲元,魏振刚,张亚武,徐小东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普通外科,甘肃兰州730000)
肝硬化(liver cirrhosis)在全球多发,我国发病率尤高,以病毒性肝炎后肝硬化为主;失代偿期肝硬化以门静脉高压症(portal hypertension,PHT)及肝功能减退为临床特征。PHT 常致脾大、脾功能亢进(简称脾亢),食管胃底静脉曲张(gastroesophageal varices,GOV) 及腹水。在我国,有85%~90%的肝硬化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PHT,其中约30%合并脾亢[1]。而PHT 患者中每年约有5%出现GOV,其中20%~30%的患者出现上消化道出血,而GOV 患者初次上消化道出血时院内病死率在25%以上[2]。目前PHT 患者脾切除其目的在于减少门脉血流而降低门静脉压力及改善脾亢所致的外周血三系减少。但近年来,随着对脾脏功能的新认识,对脾切除术进行重新考量。
本文通过系统综述现有的研究现状和进展,以期提高临床的认识和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避免因盲目和常规切除脾脏而对机体和后续治疗产生不利影响。
1 脾切除对血流动力学和门脉压力的影响
门静脉压力的增加,是门静脉阻力及血容量增加所致[3]。据以往研究表明,PHT 患者行脾切除后可降低门静脉压。一是消除脾血流量而减少门脉回流量;二是使肝脏中内皮素1 (endothelin 1,ET-1)和一氧化氮代谢物(nitric oxide productions,NOx)浓度正常化而降低肝内血管阻力[4]。脾切除后,可能通过消除脾源性ET-1,使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HSC) 松弛和肝门静脉血管阻力降低,以及减少门静脉血流而降低门静脉压力。脾切除在减少门静脉血流的同时,可增加肝动脉血流量。有报道[5],脾切除联合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会增加肝动脉的血流、减少门脉的血流,术后入肝总血流量下降,但肝动脉血流所占比例增多,入肝血流供氧增加。增加肝动脉血、从而增加肝脏供氧,可以改善患者的肝功能。然而,亦有研究表明,PHT 患者门体静脉交通支及肝动脉与门静脉的交通支大量开放,压力高的肝动脉血流灌入压力低的门脉系统,这时增加肝动脉的血流量反而会增加门静脉压力[6]。门脉压力是门脉阻力与门脉血流量的乘积,门脉阻力在其中的权重占到70%[7],而脾切除后并未解除门脉阻力。再者PHT 患者脾静脉及其属支与冠状静脉及腹膜后Retzius 静脉所形成的交通支,具有自体分流的作用,脾切除后门脉压能否下降,还受经脾静脉的回流量与经脾静脉分流途径的门脉血流量之差的影响[8]。故针对PHT 患者外科治疗时,更重要的是对冠状静脉及其属支的处理[9]。另外脾次全切除术,作为保脾术的一种,似乎有较大的优处,脾次全切除术后,残脾既可以消除门脉的高压状态,防止脾大、脾亢的复发,又可作为门体分流的桥梁,分流高压门静脉流入体循环[10]。
故笔者认为,脾切除后是以减少门脉的血流及平衡舒缩血管物质的含量来降低门静脉的压力。门脉血流减少,作为代偿肝动脉入肝血流量增多,可能会改善肝功能。而脾切除后,在门脉阻力未改善的情况下,门脉压力是否有较满意的降低,取决于脾静脉在门静脉血流量中的占比。对患者的生存及生活质量是否有提高,亦需进行大量临床研究去支持。为了降低门脉压力而行脾切除术,以期改善患者的临床状况,目前缺乏有力的证据,有待进一步做前瞻性对照研究;即不建议以切脾作为降低门静脉压力的常规手术。
2 脾切除对肝功和血系的影响
PHT 患者常存在脾亢,即外周血细胞的减少。脾切除可以解决脾亢所致的血小板(platelet,PLT)减少,而且能改善凝血功能,尤其是对于肝功能Child-Pugh B 级及C 级的患者[11]。但临床上时有发现脾切除后,血细胞计数并未完全恢复。有研究[12]指出在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 水平高的患者中,通过脾切除解决脾亢来改善PLT 减少的效果是有限的。说明肝功能可能在血系改变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肝硬化所致PLT 减少可能是多方面的因素,如脾亢时PLT 破裂、脾池化和骨髓产生PLT 功能受限等。故脾切除对缓解PHT 患者脾亢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认识。临床中,约50%~75%以上的患者PLT 较低(<150 000/μL),只有1%~11%的患者PLT 低于50 000/μL。而PLT 低于20 000~30 000/μL 时,才会出现轻微创伤后的出血;PLT 低于5 000/μL 时,则会出现内出血[13]。在既往的研究中,无临床数据表明低PLT 会致使GOV 出血,也无临床研究表明输加PLT 以增加数量会影响GOV 出血患者的预后。在PHT 患者并发GOV 出血,脾大、脾亢且PLT 高于50 000/μL 时采用保脾的腹腔镜下断流术有较高的安全性[14]。脾亢及免疫作用导致的PLT破坏增多,表现为PLT 数量的减小,而血小板平均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MPV)增大。
综上,脾亢可能会引起PLT 减少,但MPV 会增大,患者也较少见由于PLT 减少而引起严重的并发症。这可能是一种机体的代偿作用,体积大的PLT 可能会释放更多的凝血物质,从而弥补数量的不足。在临床上,肝硬化患者中一半以上会有PLT减低,没有临床研究表明纠正脾亢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脾亢的严重程度与脾的大小或门脉高压的严重程度亦无直接关系。故用切脾的方法去改善脾亢而单纯提升PLT 的数量,以期改善患者的出血或预后,有待进一步研究。
3 脾切除对门静脉系统血栓形成的影响
门静脉系统血栓形成(portal venous system thrombosis,PVST)是指门静脉分支及其属支内部分或完全性血栓形成,是PHT 脾切除后的常见并发症。肝硬化患者PVST 的发生率为6.0%,脾切除后PVST 发生率为22.0%[15]。PVST 会导致肝功能损伤、缺血性肠坏死及门静脉压进一步增高致GOV出血等。PVST 有诸多危险因素。脾静脉直径是门脉系统血栓发生最有效的预测指标,10 mm 是准确的脾静脉直径截断值[16]。术后PLT 数量、术后D-二聚体、门静脉血流速度为PVST 发生的主要独立危险因素[15,17]。PVST 发生的风险与不同手术方式亦有着直接的关系,腹腔镜脾切除术后PVST 的发生明显高于开腹,可能是CO2气腹会使机体处于高凝状态,超声刀的高频振荡或者热能对血管内皮的影响有关[18-19]。血栓慢性化可导致门静脉压力进一步增高,致使肝外门静脉扩张和门静脉海绵样变(cavernous transformation of portal vein,CTPV)。而一旦发生PVST 及CTPV,可使门脉系统的血流不能充分入肝,致肝供血不足,对肝功能有损害[7]。肝硬化患者脾切除术后PVST 组的门静脉血流量减少49.2%,非PVST 组仅减少6.6%[20]。且脾切除后发生PVST,进一步增高门脉压,增加肝移植的难度和感染风险以及术后移植物失活的概率[21]。也有相关报道,脾切除易形成门脉血栓,会增加肝移植手术难度和时间,但不会增加肝移植术后并发症风险,不影响术后生存[22]。
由此可看出,脾切除后使得PVST 发生的机会增加,腹腔镜脾切除可能形成PVST 的机会更高,影响后续行肝移植手术,亦会增加术后治疗难度。但现在随着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等检查手段的提升,早期可以发现PVST,并采取积极抗凝治疗。所以即使发生PVST,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临床上也较少见引起严重的不良后果。
4 脾切除对机体免疫力及肝癌发生发展的影响
脾脏在免疫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参与体液免疫的B 细胞和浆细胞在脾脏中成熟。T 细胞及其产生的细胞因子在这些淋巴细胞的成熟过程中有重要作用[23]。研究[24]发现PHT 患者合并脾大、脾亢时,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低下。而支持脾切除者[24]认为,切脾可以起到改善患者免疫和抗肿瘤功能。PHT 患者门静脉的高压状态,会刺激脾脏纤维化,纤维化后脾脏的免疫功能明显降低,表现为外周血CD4+T 细胞亚群比例和CD4+/CD8+T 细胞比值下降,脾脏产生促吞噬肽(tuftsin)的能力明显降低,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NKC)的活性降低[1]。而脾切除后PHT 患者外周血中,CD4+T 细胞与CD8+T 细胞比例有所上升,说明免疫抑制有所改善[25]。在腹腔镜下脾切除的相关研究中,相比于开腹手术,全腹腔镜脾切除联合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有利于患者免疫功能的早期恢复[26]。
在抗肿瘤免疫方面,脾切除术后患者的肝癌发生率明显降低,一是因为脾切除可促进T 细胞亚群比例及辅助性T 细胞(helper T cell,Th),Th1/Th2 比值的恢复,提高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功能,预防肝癌的发生及复发;其次,脾切除可以减少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TGF-β)的分泌[1]。但近年研究[27]表明,脾切除后机体免疫功能显著下降,患者术后感染增加,肿瘤发生增加。有学者[28]认为,肝硬化患者切脾后外周血T 淋巴细胞必然发生改变,导致其细胞免疫功能进一步下降。尤其在PHT 患者脾切除后,术后凶险性感染(overwhelming postsplenectomy infection,OPSI)的终生风险增加了5%,医源性无脾可能与肺动脉高压,动脉硬化和冠状动脉疾病风险增加有关[29-30]。临床发现,一旦发生OPSI,病死率高达50%以上,常见的肺炎链球菌感染的病死率在脾脏切除术后的患者中高达60%[7]。对于保脾手术的脾次全切除术,似乎有较好的前景,解除高压后的残存脾组织可增强免疫,减轻炎症,免疫组化显示,术后T、B 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单位面积计数较术前明显增加[10]。全脾切除与保脾术对比研究显示,全脾切除组患者手术时间、失血量、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指标均大于部分脾切除组,术后部分脾切除组CD4+T 细胞和CD4+/CD8+T 细胞高于全脾切除组[31]。实验表明,肝硬化大鼠脾切除后表现为NKC 活性持续降低,肝癌发生率增高,肝硬化进展增快[1]。亦有报道,根据肿瘤TNM 分期,在TNM I 期患者中,肝癌切除联合脾切除组患者的无瘤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明显短于肝癌切除组,所以在早期肝癌患者行脾切除后,患者并不获益[1]。
至于PHT 患者的脾脏是否有正常的免疫功能,目前仍未有定论。脾切除后,患者是否因免疫功能改变而获益或产生不良后果,临床及实验研究尚不足,需要进一步在临床及实验方面进行长期、大量的对照研究。目前笔者认为鉴于脾切除后患者的感染等相关并发症发生危险上升,不建议为改善患者免疫而进行脾切除。
5 脾切除对肝纤维化进展的影响
关于脾脏与肝纤维化的研究。PHT 合并脾亢时Th2 优势的脾淋巴细胞迁移至肝脏,使细胞因子平衡向Th2 优势方向发展,促进肝纤维化[32]。Th1细胞因子如干扰素对HSC 活化有抑制作用,而Th2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IL-4 和IL-13 可以促进HSC 的激活和肝纤维化的进展。多种细胞因子与HSC 的活化和增殖有关,如TGF-β、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IL-6、IL-1 等[33]。HSC 激活后也可分泌TGF-β 等细胞因子,并通过自分泌进一步维持自身的活化状态并激活临近HSC,活化的HSC 增殖,转变为表达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的肌成纤维细胞,合成并分泌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导致肝纤维化的发生[33]。
在实验大鼠脾切除后,则会降低肝组织TGF-β与α-SMA 的表达水平[34]。亦有实验,在肝硬化大鼠模型中, 脾切除可以稳定肝内库弗细胞(Kupffer cells,KC) 的功能,维持肝内TNF-α 数量,激活静止期肝细胞进入有丝分裂期,使受损肝细胞得以修复[35]。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可以降解ECM,减轻肝纤维化,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tissue inhibitor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TIMPs)对MMP-1活性有抑制作用,肝纤维化时,激活的HSC 是TIMP-1 的主要来源细胞,脾切除可降低患者TIMPs含量,升高MMP-1 含量[36]。脾切除后,肝硬化患者的肝脏中KC 积聚,随即中性粒细胞浸润肝脏产生MMP-9 蛋白,说明KC 介导的中性粒细胞募集在纤维化消退中起重要作用[37]。 KC 也通过产生CXC趋化因子配体9(CXC-chemokine ligand 9,CXCL9)和MMP-13 延缓纤维化的进展[38]。脾亢时,红细胞破坏导致铁在肝脏中沉积会引发氧化应激和炎症,致使肝内ECM 沉积,加重肝纤维化[39]。脾切除后会使血红素氧合酶1(heme oxygenase 1,HO-1)表达降低,从而减轻肝纤维化。脾切除后PLT 会增多,PLT 中有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在肝纤维化的情况下,HGF 可以降低TGF-β 的表达,通过降低TGF-β 而升高MMP-9 以促进肝再生来减轻肝纤维化的进程[40]。在PLT 减少症小鼠实验中,PLT 减少本身可加剧肝纤维化,原因可能是PLT 具有抑制I 型胶原表达而发挥抗肝纤维化的作用[41]。在正常大鼠行脾切除后再进行肝硬化诱导时,肝纤维化进程缓慢;肝纤维化期行脾切除后,肝脏病理状态迅速缓解;肝硬化期行脾切除后,肝脏炎性改变和纤维化程度也有一定减轻,提示切脾越早,对肝纤维化的延缓作用越大[42]。另外在肝硬化脾亢时,门脉输送给肝脏的过多促炎介质及免疫细胞是肝硬化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肠道微生态改变及肠黏膜屏障损伤,炎性介质、微生物毒素等通过门静脉入肝,形成所谓的肠-肝轴,会促进肝硬化发生发展[43]。切除脾脏,减少经门静脉对肝脏免疫微环境的干扰,可能有助于延缓肝硬化进展。脾脏通过门静脉向肝脏输入的某些细胞因子,如人脂质运载蛋白2(lipocalin 2)可能调节KC 功能,有利于缓解肝硬化[7]。
当然,脾切除后对肝纤维化的研究,仅在实验观察阶段,通过切脾后改善纤维化以改善肝功能后是否对患者的临床预后有积极的影响,目前还不明确。对于肝纤维化不同阶段的患者而言,脾切除后对肝纤维化的减轻程度亦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能仅凭血清中肝纤维化相关指标、及促炎因子有所改善而确定脾切除可以让患者延缓肝纤维化进展而使临床后果有所获益。
6 脾切除对临床获益的影响
有报道[44]提出,脾切除断流术能够降低患者上消化道再出血率,改善生存率,亦可缓解患者临床症状,且患者的心理状况将得到显著改善[45]。亦有研究,对合并严重脾亢且符合米兰标准的肝癌患者,肝癌根治联合脾切除可提高患者整体生存。但以上报道都缺乏长期的随访对照研究,故对于患者的生存时间、质量和预后仍需进一步研究。
7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PHT 合并脾亢且伴有血液三系细胞减少患者通常未见明显增加的严重临床后果。虽然切除脾脏后可一定程度改善肝纤维化,但目前仍缺乏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来表明其对于患者生存质量和生存时间的临床获益。同时在相关免疫学研究方面,目前亦缺乏明确证据,来表明切脾或保留的脾脏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对PHT脾亢合并GOV 者而言,目前指南明确药物和内镜为一线治疗。外科手术的定位自始至终是内科治疗无效的二线选择,即是一种保底治疗手段。内镜治疗次数多,一般需要多次套扎才能达到较满意的结果,且内科治疗通常无法有效解决脾亢的问题。目前快速发展的腹腔镜门脉高压手术相比于传统手术显著降低了创伤,并具有恢复快和住院时间短等优点。至此,对于PHT 脾亢合并重度GOV 者,是否同时切除脾脏在目前临床工作中可能对于选择继续内科治疗抑或腹腔镜手术有重要的实际应用和参考价值。
综上,目前尚无有力证据表明PHT 合并脾亢患者脾切除后,其免疫改善、肝纤维化或硬化程度减轻而使患者的临床预后获益。如PHT 患者肿大的脾脏未引起生活中的明显不适即腹胀感等,则暂不建议以切脾作为降低门静脉压力、改善患者外周三系血细胞减少的常规手术。
对于保脾和切脾孰优孰劣,笔者认为仍需要大量、长期的前瞻性对照研究,但目前较为明确的是需要进一步提高临床认识,积极避免因盲目和常规切除脾脏而对机体和后续治疗产生不利影响。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