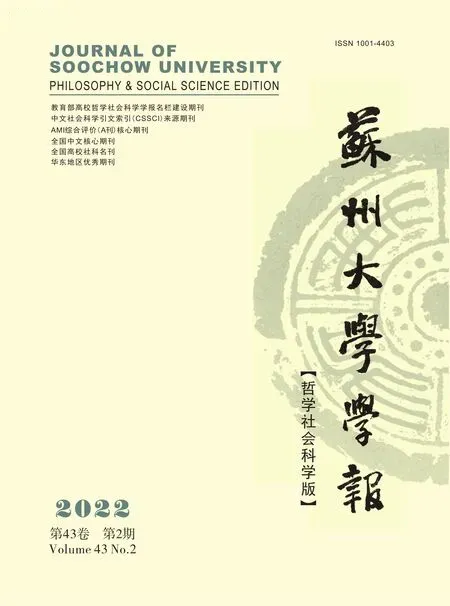文本于经:清人惠周惕经解的文学在场
2022-12-07王祥辰
王祥辰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若论起清代学术史上的汉学家族,很难不提到东吴惠氏一门。顾千里有言:“国朝右文稽古,鸿儒硕学辈出相望,遂驾宋元明而上。……惠氏四世传经,为讲汉学者之首。”(1)顾千里:《思适斋文集序》,《顾千里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7页。焦循亦曰:“东吴惠氏,四世传经,至于征士,学古益精。”(2)焦循:《雕菰集》卷六《读书三十二赞(有序)》,《焦循诗文集》,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115页。卢文弨则说道:“惠氏四世传经,其最著者为半农先生、红豆先生,乃定宇之祖若父也。”(3)卢文弨:《题九经古义刻本后(甲辰)》,《抱经堂文集》卷一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9页。清代学者再三肯定东吴惠氏“四世传经”,直言经学研究贯穿惠氏家族学脉。赵尔巽等人甚至视惠氏家族为清代汉学研究第一家:“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4)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八一《惠周惕》,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78页。东吴惠氏家学宗脉的起始,多被归结在惠周惕身上。周惕为很多人视作东吴惠氏与乾嘉吴派的奠基人,对此张舜徽有过介绍:“惠氏累世传经,其有著述行世,实自周惕始。”(5)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1页。
惠周惕,原名恕,后改今名,字元龙,号砚溪,颇精于经学,在《周易》《诗经》的研究方面很有造诣。尤其是他的《诗说》,被学界看作清前期《诗经》学史上的关键著述。(6)参见林叶连:《中国历代诗经学》,学生书局1993年版,第361-367页。而事实上,惠周惕除了经学研究外,在文学研究和创作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沈德潜《清诗别裁》给予了惠周惕的诗歌很高的评价:“诗格每兼唐宋,然皆自出新意。”(7)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2页。漆永祥谈到惠周惕的文章时也说:“皆质实有理,不涉虚论,不失名家风范。”(8)漆永祥:《前言》,《东吴三惠诗文集》,“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第21页。不过经过数十年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作为经学家和思想家的惠周惕名声大振,而作为文学家的惠周惕则暗淡许多,至今罕见围绕其文学成就的专题探讨(9)以笔者所见,除了赵四方:《从汪琬到惠栋:“师法”观念与清初〈诗经〉学的转折》,《中国经学》2015年第2期,第103-116页;王祥辰:《“根柢”重构、“诗史”追寻与家学接续——论惠栋的诗学旨趣》,《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53-160页,对惠周惕的诗学观、文章观略加论述以外,尚未见到其他专题研究论文。。这种偏至经学而忽略文学的现象,折射出乾嘉文学研究与吴派经学研究的双重“失衡”,广泛深入地讨论惠周惕辞章之学的空间依然很大。就惠周惕而言,钩沉他诗文中读书作文之法,可以发现与其《诗说》的内核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讨论其辞章理论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不但能深化对惠周惕其人及其学术思想的理解,同时能使乾嘉吴门学术全貌得以完整呈现。
一、从“文本于经”到“以经解经”
辞章之学在传统清儒的视阈中,一直处于经学研究的从属地位。从《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的排序,即可一窥此种现象。戴震则将这种现象解释得更为显豁,他认为较之理义、制数,文章是末流的学问:“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10)戴震:《戴震文集》卷九《与方希原书》,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3页。清儒对文学的轻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但刘师培在总结清代汉学家经典研治与文学创作关系时,就不这么以为了,他说:“惟笃守汉学者,好学慕古,甘以不才自全,而其下或治校勘、金石以事公卿,然慧者则辅以书翰词章。”(11)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在刘师培看来,只有最为聪明的汉学家,才能在经学研究以外,兼顾辞章之学。辞章之学虽不及单纯的经学研究重要,却是展露经学家才情的重要手段。而惠周惕就是刘师培所认为的重经典而不废辞章的聪慧之人。惠周惕也从来没有试图掩饰过对辞章之学的重视,甚至在他的《历科文录序》中就表明,他少年时期初涉儒家经典,更多关注的,其实是经典章句透露出的文学创作规则与技巧,而非经典内部的“微言大义”。
据惠周惕《历科文录序》自述,他少时即“通《五经》章句,间取一读之,辨其对偶,别其体裁,以为时文之法度,如是而止矣”。而后在熟读《五经》,辨析文章体例,掌握时文写作的方法后,他又将学术视野扩大到史学典籍上,以唐、宋散文为根柢,培养古文创作的技巧:“将有志于古文,斥之为不足学,每读《史》《汉》、唐、宋之文,爱其文笔驰骋,锐意欲效之。及为制义,辄仿佛其气象,模拟其字句,自以为古文矣。或出以示人,或持以应试,亦无不以古文许之也。”中年以后,惠周惕因丁外艰,遂不起,之后“奔走四方,渡江绝淮,溯河入济,历鲁、卫、齐、赵以抵京师,览其山川”且结交有识之士,方才发现过去所自以为古文者,“非也”。于是惠周惕“退而读书,上自《六经》,下及秦、汉,因以沉潜乎唐、宋大家,熟复乎元、明诸子,探其源流,极其变化,乃始恍然以为文章在是”。当他掌握文章之法后发现:“以其法质之诸子,诸子是也;证之诗歌,诗歌是也;即极之浮屠、《老子》、稗官、野乘与夫古人之山镵冢刻、小小载记,无不皆是。”最后,惠周惕总结了从儒家经典、史学典籍及诸子百家中悟出的古文创作之法,说道:“盖其开合、起伏、顿挫、擒纵之法,一本于古文,特其辞少异耳。”(12)惠周惕:《砚溪先生遗稿》卷下《历科文录序》,《东吴三惠诗文集》,第206-207页。
惠周惕用数百字,洋洋洒洒地诉说他如何参透时文、古文创作的法门。而实际上,惠周惕《历科文录序》通篇所强调的,都是儒家经典、史书文献、先秦诸子、唐宋文章等对他文章观建构的影响。尤其是儒家经典的原本,是他文章理论形成的根源。质言之,在惠周惕看来,文学创作需要以经典为基础培根固柢,而这种基础不仅体现在文章的思想上,同时也展示在文学创作的手段上。惠周惕也不止一次表达过儒家经典之于诗文创作的范式作用:“文字用对偶,自《左传》《国语》已然。”(13)惠周惕:《砚溪先生遗稿》卷下《论文十一则》,《东吴三惠诗文集》,第213页。他为潘双南诗集所作序中,亦赞赏潘氏诗曰:“上本《风》《雅》,下及六朝,而约取于唐之开元、大历诸名家,龂龂不失尺寸。”(14)惠周惕:《潘双南诗序》,《砚溪先生文集》,《东吴三惠诗文集》,第143页。
此外,惠周惕自己的诗歌创作,也都很难隐去儒家经典的影响。比如在他的《题画史册子次恺功韵四首》中,就提到“比量文体笺尔雅,好读毛诗试画蝇”以及“箇中雅郑谁能别,应得诗人与细陈”(15)惠周惕:《砚溪先生诗集》卷七《题画史册子次恺功韵四首》,《东吴三惠诗文集》,第106页。。又如《画史黄生索诗书此以答》中,则有“须君小笔通灵手,一绘豳风七月篇”(16)惠周惕:《砚溪先生诗集》卷七《画史黄生索诗书此以答》,《东吴三惠诗文集》,第123页。。当然,不只在他的诗歌中能看到儒家经典的印记,周惕大多数的文章也都有着经学的底色。譬如《萧母程孺人八十寿序(代)》一文,惠周惕写道:
夫《六经》论孝,至于养抑末矣。孔子之告子游,则斥为“今之孝”。而曾子之语公明仪,亦谓“参直能养,不能孝”。盖以养者,人子之所易,而三代以后之贤者顾难之,殆有不可解者。然吾尝读《礼》而叹古人养之之难也。(17)惠周惕:《萧母程孺人八十寿序(代)》,《砚溪先生文集》,《东吴三惠诗文集》,第136页。
惠周惕所提及的“今之孝”,出自《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而惠周惕所说的“参直能养,不能孝”,则由《礼记·祭义》出:“参直养者也,安能为孝乎?”
在清代,将先秦文献中的典故融入诗文,并不罕见。众多文人受到考证学风的影响,特意引经入诗、引经入文,从而彰显自己学识的渊博。但值得注意的是,惠周惕是王士禛的学生。王渔洋还曾赞扬惠周惕的《诗说》,并强调周惕为其门生的身份:“吴郡门人惠周惕著《诗说》三卷,言博而辨,不主故常,可备说诗一家之言。”(18)王士禛:《居易录》,《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919页。要知道,渔洋诗是以其“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性灵说”饮誉清代诗坛的。而惠周惕重视儒家经典对诗文创作的影响,带有“文本于经”的意识,这显然与王士禛的诗学逻辑并不相契,有着鲜明的个人文学特色。
惠周惕也将少年时期诗文创作“文本于经”的态度,带到了后来经学研究的过程中。他给薛孝穆回复的书信有道:“仆立说之旨,惟是以经解经。”(19)惠周惕:《答薛孝穆书》,《砚溪先生文集》,《东吴三惠诗文集》,第165页。惠周惕为经学研究找到的出路,就是“以经解经”。而他在自己实际研治《诗经》的过程中,也确实做到了“以经解经”。如惠周惕解说何为“颂”时说:“比音曰歌,举其词曰颂也。岂宗庙之诗,既歌之,而复诵之欤?抑歌者工,而诵者又有工欤?既比其音,复诵其辞,俾在位者皆知其义,所以彰先王之盛徳,故曰颂。至于所刺、所谏,欲闻其人之耳,故亦曰颂也。”(20)惠周惕:《诗说》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为了印证“颂”与“诵”为同义,惠周惕一边罗列《公羊传》《左传》等《春秋》传说,力图从史实的维度沟通证明“颂”与“诵”的内在联系,一边抬出《礼记》《孟子》等书从周代礼制的维度予以佐证:
《公羊传》曰:“什一而税,颂声作。”《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然雅诗“家父作颂,以救王讻”,《左传》“听舆人之颂,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刺亦可言颂矣。《国语》“瞽献典,史献诗,师箴,瞍赋,矇诵谏”,亦可言颂矣。按:《礼》:“学乐、诵诗、舞《勺》。”《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孟子》:“诵其诗,读其书。”《左传》:“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太师辞,师曹请为之,遂诵之。”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师古注曰:“夜诵者,其言或秘,不可宣露。”(21)惠周惕:《诗说》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第123页。
虽然说,“颂”究竟能否训为“诵”还有很大的争议,四库馆臣就借助郑玄注《仪礼》和《周礼》的内容指出“歌”与“颂”是两种不同的说法,从而佐证既歌之,亦可诵之,驳斥了惠周惕这里的立论基础,以说明“颂”和“诵”不能等同。(2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页。但不论惠周惕在这里的论说正确与否,他为了证明“颂”就是“诵”,广泛地征引《公羊传》《左传》《礼记》《孟子》等经典,还是能够展现他“以经解经”的经学考证思路。
回顾清代学术史,“以经解经”的经典考据逻辑为大多数汉学家所采用。惠栋甚至将这种经解思路带到了文学研究中,他在训纂王士禛的《渔洋山人精华录》的时候就强调“以王书证王诗”的观念(23)参见王祥辰:《〈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的朴学范式及其诗学启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82-89页。,明显接续了祖父惠周惕“以经解经”的学术传统。但实际上,清前期,汉学在学术界尚未完全得势之时,“以经解经”并不为所有人接受。以至于惠周惕利用“以经解经”手段注解《诗经》时,遭到了友人的排斥。惠周惕论“归宁非礼”时说:
愚尝求之孔子之意,而知“归宁”之说非也。于何知之?于《春秋》知之。《春秋》庄二十七年冬书“杞伯姬来”,《左氏》曰“归宁也”。杜氏曰:“庄公女也”。庄公在而伯姬来,则正与归宁之礼合,而《春秋》何以书之而讥之?以此知“归宁”之说非也。不宁惟是,《春秋》桓三年,齐侯送姜氏于讙;庄二十七年,公会杞伯姬于洮,皆讥也。齐僖于姜氏、鲁庄于伯姬,父子也。父之于子,犹不可送焉,会焉,况女之来归于父母乎?以此知“归宁”之说非也。(24)惠周惕:《诗说》卷中,《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第126-127页。
《左传》中载庄二十七年冬“杞伯姬来”,为“归宁”之意。而惠周惕认为,如若“庄公在而伯姬来”,是合乎礼义的,那么为何孔子在《春秋》中会讥讽该事件呢?显然,《左传》的说法是存在谬误的。惠周惕利用《春秋》原本来反驳《左传》,可以看出他“以经解经”的思路,不仅停留在利用《十三经》相互解释上。在《十三经》内部,其亦有严格区分。《左传》仅仅是“传”,是作为《春秋》解释的存在。《左传》在与《春秋》内涵一致时,并无太多问题,但若与《春秋》存有抵牾,那么即便《左传》的载录,亦可被视为谬误。惠周惕的思路虽然显得略有些极端,却符合他一直强调的“以经解经”的经解手段。但他的朋友薛孝穆并不认可他的观点,而认为经典内部之间理应可以做到相互佐证,依《左传》解《诗经》是符合经学传统的,周惕的“以经解经”观过于严苛。
但惠周惕对于薛孝穆的主张并不认可,他说:“然仆据孔子《春秋》以驳《左氏》、赵氏,不为无据,足下欲反吾说,亦必证据于《六经》而后可与仆合要,今但引仆所驳《左氏》一语,则仆之所据者《经》,足下之所据者《传》,以《传》驳《经》,已为轻重失类,而又无他事可援,则足下为不能举其契矣。”(25)惠周惕:《答薛孝穆书》,《砚溪先生文集》,《东吴三惠诗文集》,第166-167页。相对而言,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惠周惕会选择相信《左传》经传的片段式记载,而在经典原本的材料足够支撑他判断大义时,惠周惕则更倾向于理解与回归到经典原本。讨论清儒“以经解经”的经解思路,似乎应该回到《十三经》整体的系统中去。可倘若忽视惠周惕这种较为严格却又可能偏颇的“以经解经”理念,则又难以明晰缘何东吴惠氏家族历代延续,终究走上了汉学为指归的乾嘉学术正途。
观察惠周惕的文论所强调的“文本于经”,投射在他的经学研究中,实质上是一种更为严苛的“以经解经”手段。“文本于经”,文学研究、创作以经史等文献为根柢,与他的“以经解经”,从本质上来看高度一致。我们甚至可以说,“文本于经”的文学表达,也就是“以经解经”的经学展示。他的文学创作理念与经学践行手段处于共同的疆域,由根本依据出发是他最惯常也最为合理的辞章之论的经学实践方式。惠周惕谈到自己的诗文作品时,这样说:“吾辈作诗文,皆有来历,有法度,不得草草耳。”(26)惠周惕:《与目存上人》,《砚溪先生遗稿》,《东吴三惠诗文集》,第216页。而汪琬表彰《诗说》则道:“吾门惠子元龙,好为淹博之学。其于诸经也,潜思远引,左右采护,久之而恍若有悟,间出已意,为之疏通证明,无不悉有依据。”(27)汪琬:《诗说序》,《诗说》,《丛书集成初编》第1740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与其说,作为文学家的汪琬认可惠周惕《诗说》的新解频出,不如说,他是看到了惠周惕诗文写作、经学研究“无不悉有依据”的根本特征。
二、从“会通变化”到“无所专主”
惠周惕“文本于经”的文学观,以及“以经解经”的经解思路,展示着他对实证之学的重视程度。不过惠周惕并非一个将自己关入书斋,躲进故纸堆,不问世事的学问家。由于曾官拜翰林,他的诗文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酬和之作,而这部分作品虽然还是浸润着经典的特色,但与社会现实挂靠得已然非常紧密。即便在他的《诗说》中,我们也能看到不少针砭时弊的痕迹。比如他解读《伐檀》《硕鼠》时就说道:“俭非恶德,而魏以之亡国,何哉?盖俭之极者必贪,《伐檀》《硕鼠》之所以作也。国小民贫,剖克不已,安得不亡。”(28)惠周惕:《诗说》卷中,《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第132页。又如他释讲《十月之交》则强调:“平王乘乱东迁,依人立国,所以容此跋扈之臣。若幽厉虽衰,威令尚行,未必如此不振也。”(29)惠周惕:《诗说》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第136-137页。
实际上,服从经典并不是他文论和经解的唯一特色。重视文献,认可前人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范式价值,只是他文学、经学研究其中的一种手段。惠周惕在诗文创作、经典研治过程中不断向外界透露,他并非只使用一套规则构造自己的文学观、经学观。惠周惕《论文十一则》就淋漓尽致地呈示了另一种思路。是文中,惠周惕从文体、文法、文意等三个不同维度出发,归纳文学创作的要义。
细玩惠周惕《论文十一则》,不论是辨体、立意、行文,他都在强调“变”的重要性。惠周惕这种以“变”为根柢的文学创作思维,要求创作者不墨守成规,只要不违背文章写作的基本规则“眉不置目之下,口不居鼻之上也”(30)惠周惕:《砚溪先生遗稿》卷下《论文十一则》,《东吴三惠诗文集》,第212、212、213、213页。,其他任何的变通都能为他所接受。但不是说惠周惕论文一味强调变通,就忽略了经典文本的价值。如果变通带来的结果是对经典文献、前人成果的漠视,那么所谓的“变”,似乎也与惠周惕“文本于经”的辞章理论,以及“以经解经”注经方法大相径庭。事实上,惠周惕辨体、立意、行文,从未放弃过对经典文本的依赖,他的变通与学术传统、文学规矩的关系是辨证的。“法必谨布置,而拘挛自困者,非法也;才不受羁绁,而偭背规矩者,非才也;气必贵浩瀚,而一往易竭者,非气也”一则,最能体现他是如何处理客观文献与创作者主观意图间的关系。而“文章体格,递相摹拟,古人亦有之,然非摹拟其字句也”一则,则意味着惠周惕已经关注到模拟古人成文的重要作用。但他的反诘“昔人谓朱文公《大学或问》等文,是学南丰体,曾有一字类南丰否”,展现出他对时人文章写作模式的反思。在惠周惕看来,真正好的文章的确汲取了前人文章的写作经验,但并非千篇一律的重复。
惠周惕多数文章都能做到据经典而不失新意,譬如他的《与薛孝穆书》:
仆闻古人之书,非古人自镂板以行世也。退之之文,李汉序而行之;永叔之文,子瞻序而行之。二公之名在天下,文在人口久矣,而犹慎重不轻如此,况其下焉者乎!苏子瞻自悔其少作,朱晦翁亦尝云尔。盖临文下笔,出于一时兴会,或考证之未详,或立论之未当,后将更而张之,一镂板便流传人间,不可复改,不知者遂藉是以相訾謷,昔人所以慎重而不轻出也。今足下朝为文章,暮即付刻,足下诚自度无后悔耶?则足下之才识,在苏子瞻、朱晦翁之上,仆不得而知也。(31)惠周惕:《与薛孝穆书》,《砚溪先生文集》,《东吴三惠诗文集》,第166-167页。
惠周惕为了规劝友人不要轻易刊刻文章,指出李汉《序》后,韩愈文集才行世;苏轼《序》后,欧阳修文集才刊行。惠周惕将宋人典故所含之理,与友人当下面临之事相勾连,一方面表现出对友人劝诫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则藉前人事迹使读者有所启迪。惠周惕《与薛孝穆书》短短数百字,援古为今,既具理趣,又兼情谊,激人感发。漆永祥谓该文“切中时弊、议论剀切”(32)漆永祥:《前言》,《东吴三惠诗文集》,第21页。,评价甚高。
又如惠周惕《寿萧母程孺人八十序》:
吾闻古者天子六乡、诸侯三乡、卿二乡、大夫一乡,皆有乡先生教之,故乡之民,孝弟行于家,渊睦行于族,患则相恤,而喜则相庆,《豳风》所谓“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不独为其父母祝也。顾古礼之不复久矣,而徳州父老子弟独能师其意而行之,有古者尊尊亲亲之风,是孰致之而然?《记》曰:“烹熟羶芗,尝而荐之,非孝也。君子所谓孝者,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谓孝也已。’”则先生有以致之矣。(33)惠周惕:《寿萧母程孺人八十序》,《砚溪先生文集》,《东吴三惠诗文集》,第172-173页。
惠周惕将友人韩坡为母亲贺寿之事与《诗经》《礼记》所涉礼制结合,肯定韩坡为母祝寿合乎礼制的同时,赞赏了韩坡的孝道。惠周惕叙事严谨,立论、行文皆由经典而出,却没有忽视现实考量,张弛有度,质实有理。
注重经典,沿用古人文章创作方法,并不等于完全参照前人。将古代文献与本人认知糅合,且能够相互转换,以求得新知,可以使文章既有根基又不失新意。如此,才是惠周惕推崇的创作境界。当然,惠周惕变通的思维不只体现在文章上,谈到诗歌,他亦屡次强调“变”的重要性:“大凡作诗一首,先立一意,一意之中,有开合顿挫,自无重沓不属之病。其句法要变,字法要新,所最忌者,陈俗现成耳。”(34)惠周惕:《砚溪先生遗稿》卷下《与目存上人》,《东吴三惠诗文集》,第217、218页。为了解说什么是“陈俗现成”,惠周惕举例道:“齐师诗勉依韵和到其‘徊’字,别无他押,亦无佳意。大约用韵最忌‘优游’‘悠悠’‘踟躇’‘徘徊’等字,盖太现成故也。”惠周惕诗作极重诗格,而在满足诗格条件后,他又能做到融情于景,妙笔生花。以他的《从赤城至国清寺》为例:
千山万山渺何处,塔影层层国清路。斜阳林外送微风,布袜萧然蹋云去。……人生如此竟何为?空使惨戚凋朱颜。誓从今日抉尘网,卜宅愿傍天台巅。桃花流水跣足渡,嵬峨半醉来参禅。(35)惠周惕:《砚溪先生诗集》卷四《从赤城至国清寺》,《东吴三惠诗文集》,第58页。
惠周惕此诗写国清寺幽静的环境,并与他过去的经历相对照,情景交融。最后三句“人生如此竟何为?空使惨戚凋朱颜。誓从今日抉尘网,卜宅愿傍天台巅。桃花流水跣足渡,嵬峨半醉来参禅”,利用经历曲折与环境静美的冲突,表达一种对人生境遇的无可奈何,却又豁然开朗之感。而“凋朱颜”实出自李白《蜀道难》“使人听此凋朱颜”(36)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蜀道难》,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4页。,“尘网”出自陶渊明《归园田居》“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37)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二《归园田居》,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页。,“卜宅”出自杜甫《为农》“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38)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九《为农》,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9页。,“嵬峨”则出自白居易《戏赠萧处士清禅师》“三杯嵬峨忘机客,百衲头陀任运僧”(39)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一八《戏赠萧处士清禅师》,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2页。。结合《从赤城至国清寺》全诗内容,惠周惕典故运用可谓别具匠心。沈德潜点评该诗“但写国清之幽旷,易于平直,得平生道长一段,以往日之艰辛衬目前之游衍,弥觉翛然物外,趣味无穷矣。七言古须于平直中寻出曲折”(40)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页。,可谓切中肯綮。
在关系数据库中,关系模式是有概念模式生成的。概念模式的表示方法一般为E-R图。在E-R图中,包括实体和联系两个元素,实体与实体之间的联系类型有“1对1”、“1对多”和“多对多”三种,根据一定的规则和规范化要求,可以导出由实体和联系生成的关系模式。因此,关系模式可以分为实体关系模式(实体表)和联系关系(联系表)模式两类。根据关系数据模型的参照完整性要求,关系表之间存在主外键的约束关系,形成了关系图。
在经解层面,惠周惕《诗说》则通过反思前人《诗经》研究成果,展示他辞章理论中强调变化,会通融合的特点。之前我们已经提到,在大多数的清儒认知中,汉学是东吴惠氏的家族宗脉。东吴惠氏四世传经,学脉赓续,才有了“讲汉学者之首”的美誉。作为东吴惠氏家学传承的关键,惠周惕似乎理应将汉儒经说放在经典研治至关重要的位置上。但实际上,惠周惕对汉儒《诗经》注疏一直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在《乐园记》反驳郑玄道:“惜哉毛、郑之释《诗》者未及此,而后世陆玑、陆佃、罗愿诸人,徒纷纷于草木之名类,或谓檀似六驳,谓谷为楮,或以为构,或曰非也,其言乖剌不一,不足道。”(41)惠周惕:《乐园记》,《砚溪先生文集》,《东吴三惠诗文集》,第142页。
值得一提的是,惠周惕否定毛、郑,并非是对宋儒的回护。从他驳毛、郑,再到反对陆玑、陆佃、罗愿,可以看出,其考辨《诗经》并未带有任何学术立场。惠周惕藉着议论毛亨、郑玄,过渡到陆玑、陆佃、罗愿等学者身上,将先秦至宋代《诗经》学研究梳理出一条简明的线索。而这条线索上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是他反思的对象。与此同时,这条链接上的每一个接触点,也可能是其论《诗》的支撑。
惠周惕谈《诗经》“风、雅、颂”与“赋、比、兴”时,就直接展现了他对前人《诗经》研究的集中检讨。他先是解说道:“盖风、雅、颂者,诗之名也;兴、比、赋者,诗之体也。名不可乱,故雅、颂各有其所。体不可偏举,故兴、比、赋合而后成《诗》。自三百篇以至汉唐,其体犹是也。”而后举《毛传》说法:“毛公传《诗》,独言兴,不言比、赋,以兴兼比赋也。人之心思必触于物而后兴,即所兴以为比而赋之。故言兴而比赋在其中,毛氏之意,未始不然也。”
尽管惠周惕以为,《毛传》只言兴,而不言比、赋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说:“然三百篇惟狡童、褰裳、株林、清庙之类,直指其事,不假比兴,其余篇篇有之;《传》独于诗之山川、草木、鸟兽起句者,始谓之兴,则几于偏矣。诗或先兴而后赋,或先赋而后兴,见其篇法错综变化之妙。”但之后惠周惕又指出:“毛氏独以首章发端者为兴,则又拘于法矣。”(42)惠周惕:《诗说》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第123页。
在贬斥毛亨之余,惠周惕还搬出了朱熹有关“赋、比、兴”以及“风、雅、颂”的解读。饶富意趣的是,他并不是想要利用朱熹为自己站台反对毛亨:“文公传诗,又以兴、比、赋分而为三,无乃失之愈远乎?”在惠周惕看来,毛亨虽然有误,但毕竟“人之心思必触于物而后兴,即所兴以为比而赋之”,尚且有说得通的地方。而朱熹的主张,则没有任何道理可循。惠周惕继续解释说:“故毛公不称比、赋。朱氏又于其间增补十九篇而摘其不合于兴者四十八条,且曰《关雎》兴诗也而兼于比,《绿兮》比诗也而兼于兴,《頍弁》一诗兴、比、赋兼之。则析义愈精,恐未然也。”
惠周惕分析“赋、比、兴”“风、雅、颂”,检讨前人的主张,做到了既不宗毛,亦不尊朱。尽管现在看来,惠周惕杂糅“赋、比、兴”“风、雅、颂”,将《诗经》修辞与体裁一通浑说,否认赋、比、兴的独立性,未必恰如其分。但其疏通、更订前人之说,并由此提出本人见解的治学方式,与他诗文研究、创作领域显现出的“会通变化”的特色一以贯之。
四库馆臣谈到惠周惕《诗说》,评论客观允当:“无所专主,多自以己意考证。”(4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二,第133页。清人周中孚则认同馆臣给予惠周惕《诗说》“无所专主”的评定,他引述田雯意见道:“盖有汉儒之博,而非附会,有宋儒之醇,而非胶执。”(44)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八,上海书店2009年版,第128页。顾颉刚也称赞《诗说》曰:“惠周惕《诗说》固偏向《毛诗》,但于讲不通处实未尝回护。”(45)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8页。惠周惕“无所专主”的经解方式,突出了“我”在解经过程中的重要性。前人的意见与看法,其实都只不过是惠周惕加以利用的工具罢了。不是规定,更不是限制。这与其孙惠栋将主要精力投入在汉学上,并将汉人言论当作注经标准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恰恰是这种不立规矩的治经方式,使得惠周惕可以关注经典文本之余,观照到自身。我们也很难用是否存有“门户之见”的标准,来评论惠周惕《诗说》的经解特色。但惠周惕不以任何学人意见为唯一标准,“无所专主”,以己为重,任意变化的研究手段,还是与他“会通变化”的文学观达到某种巧妙的重叠。
三、《诗说》中经学、文学的模糊界限
李泽厚谈及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特征时说:“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我以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4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6页。由于宗法血亲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使得我们关注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考察他的祖辈和后代。而这类社会学维度的思考,虽然会让我们更全面地审视研究对象,但同时也会因为过分强调宗法传统的延续性,影响到我们的某些客观判断。
惠周惕与东吴惠氏家族,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其子惠士奇《易说》《礼说》,以及其孙惠栋《易汉学》《周易述》《古文尚书考》等著述重要的学术价值,引领一时风气。故而使得学术史编纂言及惠周惕,都会一并强化其汉学大宗的身份。可事实上,惠周惕虽然以经学名世,但目前只有《诗说》一部经学作品流传(47)参见漆永祥:《东吴三惠著述考》,《国学研究》第十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页。,且从我们之前实际考察结果来看,《诗说》本身也不是一部汉学烙印鲜明、朴学手法成熟的学术著作。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惠周惕的诗文集有多种版本流传。此外,与他的经学成就屡有争议不同,有关他诗歌、文章的评价多为正面,鲜有批驳。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言及惠周惕辞章之学时,就不吝赞美之词:“诗奉王士禛之教,清词丽句,出于学人,弥觉隽永,文亦雅洁,《杜立德墓志》颇具史法。”(48)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页。诗文皆善,邓之诚给予惠周惕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刘师培指出清儒围绕辞章之学所持的意见有二:其一是“鄙词章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薄而不为”;其二则是以为“考证有妨于词章,为学日益则为文日损”。(49)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89页。质言之,在刘师培看来,不论是强调辞章之学为小道也好,还是认为经史考证阻碍了文学发挥也罢,在绝大多数清儒的眼中,辞章之学与考证之学本就是割裂的,二者难以统一,达到共生。而亲值乾嘉汉学鼎盛时期的姚鼐的一席话,更加印证了刘师培的观点:“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50)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六《复秦小岘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以桐城派古文名世的姚鼐,一再强调文章与考证、义理的并列关系,并将文章置于考证之前,且认为三者不可废其任一,本身也说明了辞章之学在乾嘉学坛的不利地位。周惕之孙惠栋谈到文学时,甚至带有一些轻蔑的口吻“诗,小伎耳”(51)惠栋:《九曜斋笔记》,《丛书集成续编》第9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514页。,还认为,正是诗学的发达,造成了经学的进一步衰落:“经学盛于汉,汉乐府皆奏之郊庙,东汉始有拟作。汉末建安七子及魏以后黄初、正始之间,五言始兴,六朝尤盛,唐以后则有专攻诗者。诗学盛而经学衰,则始于魏以后也。”
在辞章之学与考证之学关系的问题上,惠周惕显然与大多数朴学家的看法不一。以他的《诗说》为例,因为其考察对象《诗经》的特殊性:一方面,《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在经学史上有着无可辩驳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诗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文学史上也是卓然的存在。而惠周惕《诗说》重点解决的四个问题,包括:“《大雅》《小雅》的区分”“《诗经》的正变之分”“二南所涉对象孰为”以及“赋、比、兴如何定义”(52)参见鲁梦蕾、宫辰:《论惠周惕〈诗说〉在诗经研究史上的地位》,《黄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104-108期。等,不只与经学研究相关,同时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而惠周惕用经学考据手段解决上述问题,本身就很难切割清楚辞章之学与经史考证之学之间的关系。此外,惠周惕自己也指出,会作诗之人研究《诗经》,抑或《诗经》研究者有诗歌创作功底,都能读出《诗经》的不同内涵:“然吾闻君子之读《诗》也,于《诗》之草木鸟兽,非以为草木鸟兽已也。”(53)惠周惕:《乐园记》,《砚溪先生文集》,《东吴三惠诗文集》,第142页。可见,惠周惕自己在《诗经》研究的过程中,有意愿从根本上连接辞章之学与考证之学的关系,这显然有别于多数清代考证学者。
惠周惕为了化解辞章之学与经史考证内部的不平衡,在考订《诗经》的过程中,加入了不少文学相关的评论,用一种文学化的方式进行经学实践,模糊了辞章之学与考据之学的边界。惠周惕在《诗说》谈到“赋、兴”关系时,有以下论述:
《传》独于《诗》之山川草木鸟兽起句者,始谓之“兴”,则几于偏矣。《诗》成,先“兴”而后“赋”,或先“赋”而后“兴”,见其篇法错综变化之妙。《毛诗》独以首章发端者为“兴”,则又拘于法矣。文公传《诗》又以“兴”比“赋”,分而为三,无乃失之愈远乎?(54)惠周惕:《诗说》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第124页。
显然,惠周惕是基于一个诗人的立场,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讨论《诗经》。他认为《诗经》具体篇章的撰作中,不论先用“兴”之方法,还是先用“赋”之手段,都可以彰显出诗歌内容篇法的精妙变化。“兴”与“赋”的使用,需要按照具体诗歌创作的语境看待,不能有明确的规定限制。若单纯强调诗歌创作先“兴”后“赋”,或者先“赋”后“兴”,都过于机械,展示不了诗歌特色。这与我们上文谈到的,惠周惕强调诗文创作应该有“会通变化”的态度,若合一契。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后的行文中,惠周惕并没有和传统经师一样,通过引出郑玄、朱熹等先儒之论佐证自己的观点,而是笔锋一转,拉出刘勰的《文心雕龙》为自己站台:“毛公述《传》独标‘兴’体,以‘比’显而‘兴’隐。”惠周惕用文论著作考证经典,其经学实践的文学思维昭然若揭。
惠周惕《诗说》所涉辞章之学的内容,当然不止于此。他在谈到《鄘风·蝃蝀》一诗时,为了解答缘何《蝃蝀》直称该诗主人公为“女子”,带有一种贬低之意。他特意从诗人创作的视域出发,力图由诗人写作心态的角度说明“女子”的用法:“曰此某氏之男,某氏之女,则显然有卑不得配尊,贱不得配贵,同姓不能通昏姻之义。此诗人之微旨,《春秋》之笔法也。”(55)惠周惕:《诗说》卷中,《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第130、132页。惠周惕讨论《王风·扬之水》为讽刺何人之诗时,利用该诗的写法来证明《扬之水》其实是刺桓叔的观点:“既见君子,云何不乐?云何其忧?不直言乐而言何不乐,不直言不忧,而言何其忧,皆抑扬其辞以见意也。”
不论是利用文论作品考证《诗经》,还是从诗人心态和写作方法角度解读《诗经》的具体篇目,惠周惕的《诗说》,都更像是一个文学家运用文学思维,完成的经典解读作品。而非纯粹意义上,严格的经典考证之作。或者说,惠周惕本就是想要通过《诗说》,关联辞章之学和考证之学,使二者达到相对的平衡,所以他才敢于利用解读《诗经》的过程展现他诗人才情的一面。田雯称赞惠周惕《诗说》“庶几得诗人之意”的同时,又强调周惕“以诗、古文明于时”(56)田雯:《诗说序》,《诗说》,《丛书集成初编》第1740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大概也是发现了周惕不同于清代朴学经师的另一重面向。
四、小结
晚清学者叶昌炽曾在他的《藏书纪事诗》中对惠周惕“红豆先生”的称号做过说明:“研溪所居曰红豆书屋,在吴城东冷香溪之北。吴郡东禅寺有红豆树,相传白鸽禅师所种。研溪移一枝植阶前,因自号红豆主人。”(57)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19页。我们很难将一个以实证为主要工作,严格冷峻的学问家,与“红豆主人”这一颇具浪漫气息的名号联系在一起,也很难想象清代会有二百余文人骚客以“红豆”为题与周惕《红豆诗》《红豆词》唱和(58)参见李开:《惠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463页。。而通过对惠周惕其人、其诗、其文的考察后,能够发现,较之于其子惠士奇、其孙惠栋,惠周惕身上文人气息更浓,辞章之学色彩着墨更重,汉学家的身份意识也更为淡薄。近人柴德赓有言:“然三惠之中,周惕、士奇实兼词章,非专汉学。”(59)柴德赓:《清代学术讲义》,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2页。不论是惠周惕的诗文创作方法,还是文学研究心态,都对他的经学考证手段和立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诗说》的实际内容来看,惠周惕的经学考证,其实是他辞章之学的一种特殊的延续方式。罗时进就敏锐地指出,东吴惠氏不仅有经学传统,自惠周惕起始亦有文学家数:“学术与文学兼优可以打通仕宦的道路,而仕宦又需要以学术与文学维持其社会雅誉,扩大文化交友圈。这一特点影响了文学创作的风格特征。……惠氏家族数代仕宦,数代治学,余事作诗,形成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交融的文学家数。”(60)罗时进:《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7页。由此说可溯及周中孚之论:“砚溪以诗古文鸣于时,而于诸经潜思远引。”(61)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八,第127页。周中孚将惠周惕诗歌古文的成就置于他的经学考证之前,可能也是因为周惕的经学研究难脱文学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