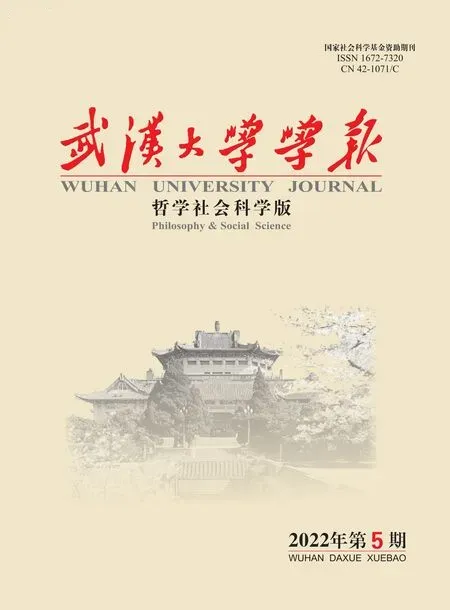数字亚文化的建构及其价值
——对虚拟偶像景观的考察
2022-12-07孙金燕
孙金燕 金 星
缘于技术发展与“元宇宙”概念加持,国内虚拟偶像市场近年呈高速发展趋势,虚拟人物正逐渐打破圈层引起大众关注。尤其是虚拟偶像特殊的技术与文化实践,高度契合二次元文化消费市场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个性需求,在2019年其国内关注群体即已近4亿人,“95后”至“05后”用户渗透率达到64%的基础上[1],2020-2021年更是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真实偶像活动的持续限制,虚拟偶像迅速拓展进当代青年的关注领域,为他们的自我表达与文化姿态构建出一个创造自由空间、保存和建立自身意义储备的场域,形成一种特殊的数字亚文化景观。
在此景观中,青年群体以虚拟偶像为符号资源构筑“微型共同体”,形成偶像/粉丝、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的相互交织与召唤,参与文化的创作与阐释、生产与消费等活动。虚拟偶像在回应市场期待的同时,也承载着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审美趣味与艺术洞见,并对其避开现实世界的规训机制,在虚拟世界中扩展自己的空间以表达价值取向、文化心态与身份认同等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深入勘察与透视。本文以虚拟偶像的样态变迁、景观表征等为线索,探讨虚拟偶像景观中数字亚文化的建构与价值。
一、虚拟偶像发展样态:二次元粉丝文化与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破壁”式演进
虚拟偶像,顾名思义,指非真实的偶像,主要是依托影像制作与投影、音声合成等数字技术,嵌入人格化外形、声音、性格等打造而成的二次元拟真人物形象。虚拟偶像的诞生及发展样态的变迁,本质上与数字技术、二次元文化和粉丝文化的交互影响有着紧密关联。
虚拟偶像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科乐美(Konami)公司在“培育国民级虚拟偶像”计划中推出虚拟游戏女主角赢蜂(Winbee)[2]。这一阶段的虚拟偶像虽已具有鲜明的数字化特征,但基本框限于作品,宋汶珈将其称为影像时代没有自主思想,单纯呈现主创团队单向思想力的虚构视觉形象[3](P13-16)。虚拟偶像的这种初级形态也为其后来的定位带来若干争议,一种观点质疑这些纯影像角色受作品形象限定且未在现实世界留下痕迹,是否可以作为具有独立人格设定的虚拟偶像[4](P89-114);与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绊爱”(Kizuna AI)、“泠鸢”(yousa)等优客(YouTuber)、虚拟主播等并非产生于AGCN(动画Animation、游戏Game、漫画Comic、轻小说Novel)的符号被归入虚拟偶像,其“归类的准确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5](P12-20)。
真正将虚拟偶像带入大众视野的是2007年音源拟人化偶像“初音未来”开启的“歌姬时代”。“日本V家”“爱生活(LOVELIVE)”“中国V家”及中国的“洛天依”等虚拟歌姬均出现于这一时期,它们依靠歌声合成软件(Vocaloid)语音合成的音源库及计算机动画(CG)、增强现实(AR)或全息投影技术等打造形象,不仅在形象上远超1999年以不成熟的计算机图形建模技术打造的世界第一个CG虚拟偶像“伊达杏子”[6],而且在技术上可供用户自主编辑进行歌姬“人设”的自主选择与创作,实现用户与虚拟偶像的强互动。此一时段,虚拟偶像的内涵得到拓展,如被定义为基于某种算法与绘画、动画、CG技术,在互联网等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中存在的无真实本体的架空形象[7](P15-18)。
2018 年,虚拟主播、虚拟上传主(Uploader)作为新一代虚拟偶像大量涌现,进入虚拟偶像新纪元。虚拟偶像不仅在数量上随短视频、直播的快速发展呈爆发式增长,而且来源丰富、运营模式多元:除传统形式外,虚拟主播开始大量占据优兔网(YouTube)打赏榜,品牌虚拟形象成为照片墙(ins)网红,动漫、游戏、电影中已有角色被打造成虚拟偶像,甚至真人明星也利用其IP效应,在二次元领域推出虚拟形象,释放明星的经济价值以延长产业链。此一阶段,虚拟偶像进一步实现对二次元文化能指的超越,向现实世界破壁。首先,实时演算与动捕软件、声优配音等技术升级,促使虚拟偶像实现了对真人演员进行3D人物成像,甚至基于人工智能、情感计算框架,打造出3D可交互虚拟偶像“微软小冰”模型,能脱离手工参数输入而自行学习并演绎不同人类歌手的演唱风格。其次,技术赋能虚拟偶像的生产机制、营销方式愈发趋近真人偶像运营模式,以歌手、舞者、主持人等拟社会化角色,广泛参与广告代言、选秀、综艺、直播带货、秀场走秀、记账陪聊乃至线下陪玩,不断借形塑商业模式以实现其价值。所以,基于虚拟偶像的业界发展,喻国明、耿晓梦将其定义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等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中进行偶像活动的架空形象”[8](P23-30)。
总体而言,虚拟偶像类型不断更迭,内涵不断扩张。它的发展样态从早期源于作品的二维视觉形象,逐步向以智能终端与全息成像为呈现方式、可与受众交互的虚拟角色分野;其概念界定虽同样具有流动性,却持续锚定向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一是技术能力,二是现实世界,标明虚拟偶像从二次元向三次元“破壁”的持续性技术努力,并越发加强对现实世界更广范围粉丝的吸引,驱动资本逻辑下虚拟偶像景观的到来。
二、虚拟偶像景观化表征:拟像在场、拟社会互动及拟人格设定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E.Debord)曾以“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概念指认现实生活的景观化积聚与表征化呈现,景观化过程是影像取代真实并异质其本源的过程[9];这种使真实乌有的纯粹拟仿自身,又被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称为“拟像”(simulacra)[10]。虚拟偶像作为一种抽象文化产品,以技术为载体建构虚拟影像,拓展进消费领域获取生存空间,它以算法模型的数据流为运转内核,以数字符号为媒介构筑拟真世界,呈现出多种景观化表征。
(一)拟像在场:“超真实”幻境中的感知体验延伸
身体是人类感知世界的根本,身、脑的物质交换以及二者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使人类感知世界成为可能,并据其与世界形成融合模式[11](P5)。然而,技术不仅改变世界,也改变人类的经验和感知。提出“具身主体性”的法国符号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即认为,人与技术是“具身”和“嵌入”的关系,以技术为中介,身体可以嵌入环境以充分感知世界[12](P116)。陈嘉映则进一步区分新技术与传统技术对人感知世界的变革:以往的技术更多造成世界的直接改变,从而间接改变人的经验和感知;而以人工智能(AI)技术为代表的当代技术则直接改变人的经验和感知[13](P39)。如同复杂性科学奠基人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所指认的,生物正在变成技术,而技术也正在变为生物[14](P231-233),诸如当下最为突出的两种现代技术实践,基因工程技术使人变得像机器,AI技术则使机器变得像人。
虚拟偶像的内容输出需要以技术赋能其成为人类强关系的延伸为基础。基于技术升级,从CG、3D建模技术到智能音声合成技术、AR/VR、3D全息成像技术、5G乃至智能信息技术的推进,虚拟偶像实现以“虚拟身体”的展演与受众互动交流,交互方式从最初的触摸交互向多模态拟人交互变革[15](P68-73)。虚拟偶像经由智能技术建构出一整套符号意义系统,维持与证实自身的存在,在现实世界构筑出“超真实”与在场的幻象,如虎牙直播2019年推出的虚拟偶像养成类直播节目“电波偶像X”,在构建全三维环境的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技术、算法大数据平台、边缘网络、流媒体处理等技术节点上进行突破,在虚拟人物、场景、受众之间的糅合、互动中发掘其虚实相生内容生产模式的最大可能性,消弭二次元与现实世界的边界,技术嵌入受众实在身体的知觉中变得“透明”[16](P78),受众在沉浸式体验中与虚拟世界形成“通感”,延伸感官并重构认知方式,且延展了对“真实”的理解。
(二)拟社会互动:“幻化”的身份建构与社会交往方式
现代技术与资本已形成一个首尾贯通的系统:一方面,资本的逐利特性驱使科学—技术有组织、有计划地增进生产效率,并在产品的迭代研发中实现自身的不断增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需要资本的投入支持,技术的“有用”需要在资本系统中获得兑现,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17](P197)。作为智能化时代的新型偶像,虚拟偶像受技术加持,其“有用”与否取决于是否能捕捉受众需求以获取资本转化。
虚拟偶像高度依赖用户生产内容(UGC)模式。网络发展驱使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准社会关系,由传统的单向情感关系加剧向强互动的亲密关系转变,尤其在新世纪数字化语境下,粉丝与偶像的互动渗透进生产与商业运营的各环节,使得“偶像制造实现了从‘媒介创造’到‘粉丝养成’的变革。”[8](P23-30)资本将粉丝裹挟进虚拟偶像的生产—运营环节,使其深入参与产品的创作、消费等,进一步增强与偶像的黏性及忠诚度。典型案例如虚拟主播“洛天依”的运营模式,她的粉丝常自称“洛厨”且广泛参与到它的生产、传播、消费之中:其形象来自全国征集、最终由自由画师飞蛾(MOTH)所提交的“雅音宫羽”形象进行重绘而成,其所演唱歌曲、演出服装等由网络投稿或投票来确定。此外,粉丝还能充分发挥歌姬的音乐工具功能,成为自行制作音乐并收获自己粉丝的P(Producer)主。这种开放虚拟偶像生产与运营权限的方式,无疑能吸引粉丝与偶像的深度互动,增强粉丝对偶像的“养成感”“拥有感”,带来交往模式的革新。
然而从本质上而言,粉丝与虚拟偶像二者之间的交往方式,仍属于三次元现实世界向二次元虚拟世界的投射,即由施密德(H.Schmid)与克里姆特(C.Klimmt)所归纳的“拟社会互动”(Parasocial Relationship)模式[18](P252-269),粉丝经由与角色形象的关系假想而舒缓归属需求,依然是在“幻化”中进行的自我身份的想象性建构,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拟社会交往,他们对虚拟偶像的情感投射与反馈,是经由数据流编码的形式来完成的。“洛天依”的假唱风波或可为这一拟社会交往状态做注脚:2020年4月21日在淘宝网的头部主播李佳琦直播间,“洛天依”在为欧舒丹品牌带货并进行歌舞表演时,由于声卡故障导致其直播了一分多钟音乐伴奏“被消声”的舞蹈。对此,娱乐媒体称其为“假唱”,粉丝则纷纷留言对其进行安慰,“洛天依”也在官博上进行了回应,整个互动过程无论是数字虚体“洛天依”被视作“真人”,进行能力、品行的评判以及情感共鸣,还是其制作团队在微博平台的拟人化反馈,双方的互动仍然是基于数据流形式与数据流所建构的虚拟对象的交互,是对现实社会交往的一种模拟。
(三)拟人格设定:完美偶像想象的表达载体
虚拟偶像有着可供编码的人格特征,其人格形象源于特定的设定与运营需要,或者是主创设计团队基于算法模型的人设创建,根据市场需求以及受众使用中的反馈,实时调整、改进数据参数,智能化打造虚拟偶像人格设定;或者是随着创作团队对创作权限的开放,受众以技术为媒介对偶像的自主编辑与亲身“调教”,受众可依据自己的喜好设计虚拟偶像的外在形象与内在特质,打造各自心中的完美偶像。
在形象设定上,虚拟偶像的容貌、性格、衣着等均可进行多重拼贴,满足受众的各种心理需求。2019年由集映画工作室推出的虚拟偶像“集原美”,在人设上不仅不完美,反而有较多缺陷,她就像众多的年轻人一样,喜欢吃零食、逛街、玩游戏、看漫画,对自己的未来有不确定的迷惘。2022年2月26日退出虚拟主播(VTuber)圈的虚拟偶像“绊爱”,自2016年诞生起便常常在与粉丝的互动中扮演“人工智障”的角色,她没有偶像包袱,爱笑、会生气与伤心,迷之自信却又常常出错。种种萌点使虚拟偶像与粉丝受众之间没有距离与隔膜,更容易获得情感的亲近,并且其年龄和外观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变,无需承受来自身体变化带来的风险。
在业务能力上,虚拟偶像也能在技术上获取常人难以企及的超高水准,承载粉丝对偶像专业能力的强诉求。作为数字技术编辑的产物,虚拟歌姬以专业发声系统集合真人音调采样而成的声音数据库为基础,用户可以通过软件选择性地排列音库中的音调数据组合成完整歌曲,经由反复调整参数而机械合成的声音,最终使其仿佛是“天生歌姬”。被奉为“B站”神作的歌曲《普通Disco》,实力歌手汪峰和李宇春在翻唱它时,均对其中的高音和不换气操作表示难度很大,需降低难度才能演绎,虚拟歌姬“洛天依”则能游刃有余地完成演唱。
此外,源于真人偶像的诸种不稳定因素与风险评估难度,越来越多的企业看重虚拟偶像的“人设不会崩塌”,启用其做品牌形象代表:其一,是邀请既有的虚拟偶像担任代言人,如2016年推出的虚拟模特米奎拉(Lil Miquela),是被设定为住在洛杉矶的20岁巴西西班牙混血女模特与歌手。作为“Z世代潮流引领者”,她自2018 年起便不断被香奈儿(Chanel)、普拉达(Prada)、苏博瑞(Supreme)、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等国际品牌邀请代言;其二则是打造品牌自有虚拟偶像,如花西子品牌在2021年推出同名虚拟偶像“花西子”,日本计算机动画(CG)公司模拟咖啡(Modeling Café)在2018年推出虚拟偶像艾玛(imma),这家鼓励女性打破外界限制的品牌,主要通过艾玛在社交媒体展现早晨健身打卡、惬意享受早午餐等理想生活,传达理想化自我的品牌理念。
虚拟偶像的智能化使其能在企业与受众之间构建“生产—传播—互动—反馈”的良性循环,打造可塑性强、完美的偶像人设,契合二次元文化青年群体的无菌审美诉求,进一步驱动其成为青年亚文化表达的新型载体。
三、从“符号游牧”到“微型共同体”:虚拟偶像景观中的数字亚文化建构
“亚文化”主要指偏离主流文化标准的特殊行为方式或小众群体。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在假定阶级实践有其同质性的基础上,认为亚文化是以行为、语言等符号体系建构的风格特征来协商其阶级的[19](P126-127)。随着历史语境变迁,后续的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等学者的文化研究,则以“区分”(distinction)、“游牧”(Nomadism)等概念超越了对亚文化根植于阶级的固态化、实体化认知,强调亚文化身份的建构与再现是一个重视个体化、碎片化经验的文化实践过程。数字亚文化作为数字信息化时代亚文化的新型样态,主要借助数字媒介获取个体审美与情感经验,构筑亚文化身份并进行圈层联结等。虚拟偶像在数字技术、二次元粉丝文化等的交互影响下,其生产、流通、消费过程都呈现出明显的数字亚文化特征。
(一)“符号游牧”:数字技术加持下的文本意义再生产
亚文化本质而言是一种人为的符号建构。符号表意兼有规定性与任意性,符号过程(semiosis)是推理的(inferential),而非指示的(index),它通过思想或约定的结合体进行表达,并根据解释者的推断来进行指称[20](P33)。而解释者对符号的意义推断,除了符号本身既有的意义规定与沉淀,还主要源自其对语境(context)的领受,一是符号所处的上下文表意压力,二是整个社会文化场域(champ)的张力[21](P224-244)。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符号脱离其原有语境而被置于新语境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原有意义,衍生出新的意义。符号表意的这种特质,使符号拼贴成为亚文化风格建构的主要方式:通过将不协调符号加以混合重组,使其所表征的不同文化分支碰撞进行意义再生产,为亚文化成员表达文化态度与价值立场提供方便法门[19](P132)。
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詹金斯(Henry Jenkins)等文化研究者均发现符号拼贴的深意,并以此为基础发掘文本的“游牧”(Nomadism)与“盗猎”(poaching)特质,分析电视亚文化粉丝通过挪用、拼贴等方式所进行的参与式文化生产[22](P23-26)。与电视亚文化粉丝相比,虚拟偶像粉丝对文化生产工具有着更多的掌握渠道,游牧式地盗猎、挪用各种符号的可能性更大,参与文化生产的权力更强。依前所述,资本逻辑与智能技术驱使虚拟偶像的生产运营门槛下移,开发者可以仅设定虚拟偶像的基本数据,用户则以此为基础参与偶像构建,尽管因参与程度不同而有原创上传(UP)主、“同人创作”等的粉丝分层,但基本都涉及调动数据库自身的规定性与变幻莫测的随意性过程:通过征调网络符号,对“御”“宅”“佛系”等各种风格的人格表征进行挪用、重组、集成,在虚拟偶像智能化数字身体的风格展演中,使各种不协调甚至彼此矛盾的符号超越形式的限定与束缚,以其不合逻辑、非理性的交织,在解构—重构过程中建立偶发的、片段性的秩序,消解逻辑谨严的现实世界的确定性,传达内心对真实世界、主流文化的反叛与再解读。
以2020年国内首档虚拟偶像综艺节目“跨次元新星”为例,作为一档将二次元虚拟偶像与三次元导师、观众进行连接的节目,其受众主要是二次元爱好者,20多位参赛虚拟偶像以古风、朋克、嬉皮士等二次元着装风格,演艺摇滚、“鬼畜”、说唱(rap)等个性化音乐,间或融入“动漫梗”,呈现出与主文化话语完全不同的秩序体系。其话语表述方式如虚拟新星的自我介绍词:“人间能得几回闻,次元最美的女人(苏芷羽)”“我花开后百花杀,表情比较冷酷吧(二娘)”“日出江花红胜火,最近可能晒太多(江浩宇)”[23]。这些来自不同语境的符号拼合,一方面使不相干的、意义断裂的意象仅源于尾韵的联结需要而被混杂,因打破理性叙事结构而显得支离破碎;另一方面,它又构建了一个奇特而自足的符号世界,诗词、俗语裹挟着各自的原语境,以藕断丝连的方式参与新语境的意义阐释,形成诙谐风格,带来无拘无束的感官印象。如“人间能得几回闻”,在杜甫《赠花卿》原诗中,兼有赞美乐曲玄妙与指摘花敬定有违乐制之意,与“次元最美的女人”并置,既以字面义指示虚拟偶像苏芷羽的美貌,又能拼接原诗句中的暗讽之意,使虚拟歌姬的自诩美貌有才华略呈戏谑与自我调侃。从单人介绍而言,它呈示出一本正经、卖萌、无厘头的多层次风格碎片;而从整体而言,这些风格碎片又碰撞出较为随性的新秩序与新意义,区别于主流文化话语秩序的严谨结构。
与此相类,当虚拟歌姬们的“萌萝莉”形象与“鬼畜”“梗曲”“暗黑”等音乐风格拼接时,会在诸种符号的反差、对峙、杂糅中,形成反讽的趣味和戏剧性的情感传达张力,以及对自认为具有整体性的世界的弱抵抗。可以说,虚拟偶像的用户强生产参与方式,是其对大众文化新需求的回应,用户对各种符号的挪用、组合看似偶然,实则仍是基于其文化立场的慎重拣择之后的必然,既是再造意义以重构世界话语权的努力,也是以创造表达对文化去中心化的热情。
(二)“微型共同体”:自我意识确立与群体身份认同
虚拟偶像亚文化建构具有后亚文化的特征,如马费索利所指认的,它是在流动中结成的统一,其群体认同更多沿着情感的、审美的、消费的模式与实践,而非来自传统的阶级结构的[24](P21-27)。受众共享虚拟偶像的某些普遍特征以建立个体自我意识,并进行群体认同与类别化以构筑“微型共同体”。对虚拟偶像的共同文化参与是成员表达身份认同的一种手段,也是达成群体成员主体间共识的符号表征:一方面,虚拟偶像粉丝成员通过对虚拟偶像的心理与行为认同来构建自我同一性,并获取基于特定娱乐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观念的群体归属,实现自我生命意义的扩张;另一方面,则以此为基础构建群体公共话语以形成与“他者”“他群”的区隔,在不同的虚拟偶像粉丝群体之间,更在虚拟偶像粉丝亚文化群体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之间,建立心理的、社会的差异结构与话语边界。
首先,虚拟偶像作为技术催生的产物,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开创了技术形态的粉丝社群关系。对技术及其所建构的拟态情感交互形态的认同与奇异幻想,是后现代景观社会中虚拟偶像粉丝构筑自我意识与群体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也是区隔虚拟偶像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群体的重要边界。粉丝对虚拟偶像的认同尽管可以从虚拟世界向现实世界蔓延,但不同“次元”之间的区隔依然明显。虚拟偶像亚文化粉丝群体对偶像的新型技术设定、拟态社会交往方式及其美学价值的期待,对围绕着虚拟偶像“数字身体”所营造的拟真世界的种种回响[25](P37-50),于普通大众甚或实体偶像的粉丝群体而言,则是无法逾越、难以理解的“次元壁”。
其次,粉丝群体通过共享虚拟偶像相关知识和资源,构建一套特定的象征符号系统与阐释规则,以此确立或强化粉丝身份,以及通过群体中他者眼中之我,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此认识自己和感知世界。虚拟偶像的代表作品、生活背景、周边产品、演艺活动等知识和资源,对于粉丝而言不是单纯的符号游戏,而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所指,对这些知识和资源的分享与掌握程度,是深化粉丝内部理念认知的方式,也是粉丝群体因共同的兴趣、视野、行动而集结或区分的标志:诸如虚拟歌姬的粉丝,既有将其视为乐器的工具粉,也有将其视为人物角色的偶像粉,他们既分立又交叉,能在各自的知识路径中联结成不同的“微型共同体”。
再次,虚拟偶像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符号,消费同样是粉丝建构与表达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如詹金斯对新媒体语境下消费特征所做的总结:“消费呈现出更多的公共和集体的特征——不再只是个人选择和偏好的事了,而是成为公众讨论和集体审议的话题”[26](P327),消费不仅是粉丝与虚拟偶像之间的互动,也是粉丝群体成员之间进行联结的重要方式。通对虚拟偶像的冲数据式打榜、馆藏式应援等消费活动,粉丝进入“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不由自主地互相牵连”[27](P70),以此获得个体与群体的想象性情感联结,甚至可以使个体消融在群体的物化狂欢中释放快感。此处需要提及的是,如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在讨论有闲阶级与炫耀性消费的关系时所提出的,不同级别的消费能力是身份差别与社会地位分层的重要符号[28],在资本逻辑下不同等级、段位的虚拟偶像粉丝身份认同与公共话语实现,仍然会通过消费能力来确认,个体话语优势是资本优势在其虚拟世界中的现实再现。
整体而言,虚拟偶像特殊的技术实践与参与式文化实践,方便粉丝成员进行文本符号游牧、自我意识建立、群体认同等亚文化身份建构与巩固,也赋予了亚文化成员获取文化资本与思考现实世界主流文化秩序的空间。
四、虚拟偶像景观中数字亚文化的价值思考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狂欢化理论曾区分两种迥异的世界:其一是科层制等级谨严的现实世界,教条且令人恐惧;其二是自在而平等的理想世界,娱乐而随意[29]。虚拟偶像以其颠覆性与边缘化等特征吸引青年亚文化群体,他们在虚拟偶像景观中娱乐狂欢的过程,既是在虚拟世界中获取平等自由的过程,也是逃逸与抵抗科层谨严的现实世界的过程。
(一)符号虚幻区隔中的感性诉求与情感投射
消费行为是对梦想、欲望等的曲折表达,这是消费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30](P18-19)。虚拟偶像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符号,消费内在于虚拟偶像本身,消费主义则贯穿于虚拟偶像的生产运营,它的审美超越与情感体验方式,迎合了粉丝关于梦想、欲望的感性诉求与情感投射。
虚拟偶像亚文化之所以获得其成员的理解、认同、追随,并得以在其中安身立命,主要源于其形式与成员对世界的主观经验以及现实处境有同构性[19](P107-108)。一方面,虚拟偶像的主要受众是二次元文化中的青年消费群体,他们既被社会期待,又暂时无力成为社会主导,其急于寻找施展权力突破口的诉求,正好与具有颠覆性与边缘性的虚拟偶像生产实践方式达成共鸣。他们被吸纳入虚拟偶像亚文化群体,张扬个性以反抗父辈主导的主流权威文化[31](P35-41);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消解一切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所带来的快速流动感,引发人际交往的暂时性与个体孤独感,使青年受众无法在现实世界获得情感的安妥,转而将情感投射向虚拟世界,通过虚拟偶像的拟像在场,与其进行拟社会交往,完成亲密关系的想象性建构,以此获得情感补偿[32](P83-101)。
尽管如前所述,受众与虚拟偶像的亲密关系建构是基于数据流形式,与数据流所建构的虚拟对象的拟社会交互,但受众所投射的情感却是真诚的。技术革新带来新的时空感,也导致引发审美超越方式的改变,在巫术—宗教—艺术—技术的审美超越历程中,与传统媒介及其塑造的偶像在传播上的“单向性”相比,虚拟偶像作为媒介技术演进和偶像文化发展的产物,它在生产—运营方式上的开放性与强互动性,使其更易成为受众情感投射的具象对象。由数字媒介构筑的二次元虚拟世界,以其特殊的编码方式与现实世界形成符号区隔,使受众与现实世界产生距离,沉浸于虚拟世界与虚拟偶像产生情感共鸣。受众在虚拟偶像拟真语境中,被邀约建立一个共识,共同经验一段情感旅程,其认知模态可简单描述为:“知”(know)其为假,却愿意“信”(belief)其为真[33](P125-126)。
以此为基础,受众利用虚拟偶像的再生性文本体系,将其当作投射内心需求的容器,构建一个自我的拟像符号,以自己喜欢的自定义形象,做自己在现实世界想做而未能实现的事情,为自己拓展出一个独特的生存空间。此时,受众在技术的普遍性中实现了一种虚幻的同一性,他们对虚拟偶像的形塑过程是主我与客我协调一致的过程,也是实现自我情感认同与群体情感认同的重要方式,不仅在一种“乌托邦”式想象创造中体验到情感的归属,而且在迥异于人际日益疏离的现实世俗生活的社群想象共同体中,获取亲切体验与亲密感。
(二)参与式文化背景下粉丝权力的有限扩张
最初的媒介研究认为权力集中于技术媒介,消费者包括粉丝没有生产性可言;辗转到文化研究则开始关注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实践,关于粉丝的阶级分析与消极受众论,才在法兰克福文化工业理论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推动下盛行[34](P164-172),但其研究依然呈现出精英主义的批判立场;直到文化研究发生消费转向,粉丝文化的积极功能才得以被正视,德赛都用“游牧”概念指称积极的粉丝像游牧民族,他们的文本阅读行为就像在别人的土地上迁徙与盗猎,不受私有制的限制,掠走那些有用的东西作为新原料,制造新的意义[35](P174);詹金斯则继承了前者的理论,努力发掘粉丝对意义的操控、建构及创造性,诸如电视粉丝对文本有规范其意义的正面影响作用,粉丝社群价值与娱乐产业商业利益具有矛盾关系等[22](P25-26)。
与传统偶像传播的专业生产内容(PGC)模式,以及粉丝处于相对边缘和弱势地位不同,虚拟偶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消费符号,它更新着社会大众的文化生产模式与消费方式,智能数字媒介技术为虚拟偶像粉丝提供了参与偶像内容生产的可能性,粉丝进入虚拟偶像商业文化生产方式渠道增多,从偶像文本的创作与消费到偶像知识的传播与分享,都可以自下而上地参与偶像的个性化、私人化定制。虚拟偶像成为粉丝自主文化内容创作的载体,粉丝由文化符号的被动接收者转化为主动生产者,在话语权上实现了相应扩张。
一方面,这种对传统粉丝文化权力关系的突破,正与青年粉丝创造与享受文化支配能力的诉求相契合。依据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在隐喻的意义上,包括内在于个人的知识、修养的文化资本是一种能力,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36](P91)。青年粉丝深度参与虚拟偶像生产、传播与消费以获取文化资本,并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如作品收入、受欢迎程度所带来的粉丝圈地位等,以此维护和改变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与话语权。
另一方面,虚拟偶像粉丝的权力扩张,使其作为一种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支配集团、资本等有了博弈、协商的空间。在伯明翰学派看来,亚文化主要经由意识形态和商品化两种相互交织的形式被收编,前者是统治集团对越轨行为的重新界定,使其成为正常的或古怪的,通过否定其差异性或丧失差异分析性,安妥于主流意识形态之下;后者则将亚文化风格符号流通于市场,通过将其庸俗化为消费风格,抹杀颠覆力量[19](P114-117)。虚拟偶像粉丝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支配集团、资本等两者之间,前者试图营造抵抗与协商的空间,后者则意欲“收编”(incorporate),双方进行话语权的争夺与博弈。但事实上,二者也存在相互利用的关系。主流文化、支配集团、资本等既要借助虚拟偶像吸引青年粉丝群体的支持,同时又为粉丝群体提供表达其个性与权力诉求的平台。
(三)智能虚拟文化中的主体同质化与文化失真
需要注意的是,虚拟偶像粉丝亚文化所进行的抵抗与协商,看似能动性较强,但又都在主流文化、支配集团、资本等构建的各种框架之内,其变革的潜能相对有限。
人作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37](P37),总在利用各种符号来建构自身与创造文化。技术拨动下的虚拟文化的勃发,虚拟偶像的拟真幻象所带来的感官“震惊”,会使人们在短暂的“陌生化”中错认其拥有独到的个性,甚而因虚拟偶像的参与式生产机制,而将其所表征的数字文化理解为“个体赋能”的文化,如研究者鲍海波所指出的:与前现代、现代指导社会生活的分别是“神”与智者相比,后现代指导社会生活的则是个体自己[38](P122-128)。然而在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的驱动下,虚拟偶像技术审美所提供的“个性化定制”背后,是技术与资本对虚拟文化隐形控制之下的无差别模式。消费社会力求消灭异质化(heterotopischer)的他者世界的差异性和可消费性,一切都作为消费的对象变得整齐划一,韩炳哲对数字时代带来的“同质化恐怖”的分析[39](P1-8)适用于粉丝以消费为路径在虚拟偶像符号化身体中寻求个性表达的弱抵抗行为,这些可以被定制同时意味着需要被优化的符号身体,本质上是充盈着空虚的功能客体,在视觉的、交际的生产与消费中被迅速达成同质化状态,随之被裹挟的则是虚拟偶像粉丝主体的同质化。
此外,随着技术工业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经历逐步的“技术形态化”[40](P1)。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在2018年曾发表《启蒙运动如何终》(How the Enlightenment Ends)一文,旨在讨论人工智能的种种不确定性及其隐患,诸如其虽能达到人们的预期目标,但无法解释抵达结》目标的过程即无法明确给出得此结论的原因,此外更为重要的则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思维和价值观的改变[41]。基辛格的讨论触动了启蒙现代性中关于“祛魅”与“复魅”的问题,人类以为依靠智能技术能够洞见与明晰世界的混沌,殊不知因其对人本身的改变,恰恰反而使世界更加晦暗不明。
当下广泛涌现的虚拟偶像,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智能技术时代的文化表征。它是技术文明与社会文化合力催生的结果,以智能技术赋予的符号意义系统构筑虚拟体验型文化,尽管随着智能技术升级,虚拟偶像以其拟真幻象不断弥合与“真实”的罅隙,然而在本质上它仍是算法模型的数据流,无法以真实的人格情感来感受现实世界,它回馈受众的是虚拟生命的虚拟情感。与此同时,受众与虚拟偶像的互动过程,不仅是文化消费与体验的过程,无形中也是思维与价值立场逐步被改变与形塑的过程。受众置身于虚拟的文化生活中,与虚拟偶像达成一种幻化的社会交往形态,对“真实”的认知不断地受到调教。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20多年前的预言在当下似乎正在悄然实现,人类将一代比一代更加适应数字化生存[42](P272),随着智能技术建构拟态环境能力的深化,以及对现实生活环境偏离程度的加剧,如同虚拟景观对真实本源的异质替换,受众也将不断深度消解对真实本源的认知,转而越发依赖具有“真实感”的数字化“摹本”,驱使社会文化进一步失真与虚拟化。这将是进一步推动虚拟偶像成为文化生产力时需要格外警惕的部分。
景观制造欲望,欲望决定生产,生产为景观所缔结的假象所控[9](P16),这是居伊·德波对景观社会生产的总结,也可视为是虚拟偶像的拟像生产状态。虚拟偶像的景观化,是数字技术时代青年亚文化群体生存状态的一种折射,疏导着青年们对现实世界的欲望诉求。而弊端在于,虚拟偶像景观的技术幻象对真实的淹没与消弭,会引导青年亚文化群体置身虚拟文化空间,流畅地交出自我以获取清浅与短暂的欢愉,逐渐消解人的主体性及其批判意识与超越维度,深化社会文化的虚拟化。这也是亚文化群体在虚拟偶像景观中,以消费实践为路径进行权力生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