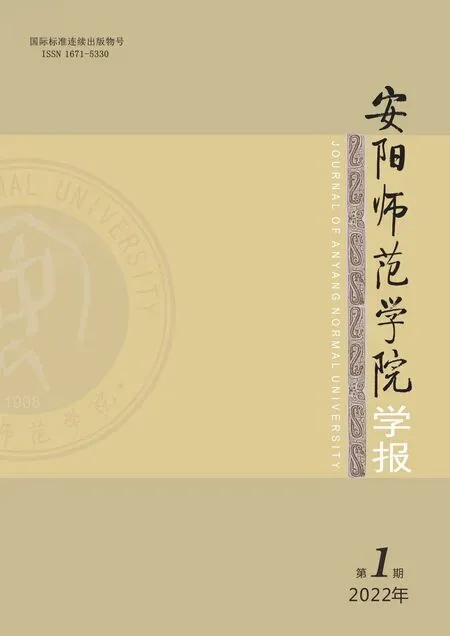叙事学视角下先锋文学中的人物解析
——以余华著《一九八六年》为例
2022-11-27景坤
景 坤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余华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其早期作品充斥着对暴力、血腥和死亡的描写,《一九八六年》这部中篇小说作为余华的代表作品之一,更是将先锋文学的写作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目前,关于《一九八六年》的研究多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余华“暴力美学”和“身体叙事”的研究,将人与世界的黑暗面直接暴露在大众视野之下;二是通过对小说中“刑罚”意象的研究,阐释历史的残酷命题和个体的反抗;三是通过对“疯子”的个人形象分析,来审视生命和人性的意义。关于《一九八六年》的研究中对其他人物的关注及其人物关系的解析则相对较少。
人物叙事在叙事学中的位置至关重要,人物是行动的主体,如果没有了人物,行动就无从发生,也就难已构成叙事作品。莫言认为:“小说的核心是人物,是作家创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核心是作家的思想,也是作家不同流俗的思想的反映。”[1]由此可见,人物是小说的灵魂,是小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通过人物的设置与串联,可以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中心思想。先锋文学由于无主线、无逻辑、无中心的写作特点,一反传统小说拘泥于清晰的“时间、地点、人物”的写作规则,导致其阅读难度大大增加,读者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从叙事学角度入手,将作者在文中所设置的人物关系梳理清晰,分析人物关系的设置及其原因,从而更好地体会作者所要表明的意图,使读者可以读出作者那些“没有说出的话”,更加深入地理解先锋小说背后的意义。
一、基本人物的构建
在叙事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主要人物贯穿故事的始终,起着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次要人物则是起着对故事进行解释和补充的作用。作者通过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设置,代表小说中不同的身份和立场,增强小说内容的冲突性。
故事的主要人物是一位疯子,可这位疯子在成为疯子之前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喜欢研究古代酷刑的历史教师,他有幸福的家庭,体面的工作,风平浪静却又自给自足的生活。就连他被带走又离奇失踪后,他的妻子从售货员嘴里听到的评价也是“你丈夫平时对我们学生不错”[2](P2)。疯子因为自己之前对学生很好,所以被带走之后免于被施加暴力和迫害,只是被关起来写交代材料。但他在被关禁闭期间亲眼目睹了因为暴力而带来的死亡,他开始看到映在墙上的头颅的影子和对着他荡来荡去的皮鞋,听到紧张的喘息和野兽般的吼叫。通过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的结合,讲明了疯子由正常转向不正常的原因,突显出了这样的一个曾经的“好人”,在“文革”结束重新回到小镇上时,却只能以一个蓬头垢面的疯子形象出现的悲哀场面。作者在小说的开头便将两种冲突非常明显的人物形象放在同一个人身上进行对比,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和冲击。
在小说的次要人物中,有两位比较重要,分别是疯子的前妻和女儿。作者对前妻的笔墨主要放在了她和疯子奇妙的心灵感应上。她的噩梦开始于自己曾经的丈夫被带走的那个漆黑的夜晚,而她噩梦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每一个漆黑的夜和丈夫被带走时拖鞋嚓嚓的脚步声。她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拼命想要将这个黑夜埋葬。于是她要逃离,她改嫁了他人,不仅如此,还要将自己女儿的名字改掉,因为女儿原来的名字与过去有着太多的联系。在这样不停地逃避与自我麻醉中终于日子要变得风平浪静了,可这个时候,疯子又出现在小镇上,她的噩梦又重新开始了,她又听到了这么多年来折磨着她神经的脚步声,于是重新变得惶恐不安起来。她情绪的突然变化与疯子的突然出现在小说中构成了一种相互呼应,从侧面表明了疯子的真正身份;同时也通过疯子妻子对疯子归来的一系列反应,揭露出历史对人们造成的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心理创伤。
小说对疯子女儿的描写主要偏重于疯子对女儿的追寻上。每一次疯子在看见翩翩起舞的红蝴蝶时,作者会立刻把笔锋转向疯子所追逐的主人公——他的亲生女儿。小说的整体情感基调是伤痛的、绝望的,疯子的世界是血腥的、破坏性的,如果说在他眼中有什么是特别的,那就应该是那抹刻在他潜意识里的红蝴蝶了。红蝴蝶从前落在他妻子的辫子上,如今又出现在他女儿的辫子上。在疯子的眼中,他看到女儿头上的红蝴蝶,就会唤起自己内心深处对妻子的想念。红蝴蝶对于疯子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对红蝴蝶有着本能的渴求,所以才会“心里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不由朝辫子迎了上去”[2](P14),目光永远都会在一片“四分五裂的行尸走肉”中被红蝴蝶所深深吸引,并不由自主地想要去靠近。整部小说通过穿插着对“红蝴蝶”意象的描写,反映出疯子在遭受伤害、在这个冷酷的世界行走了这么久之后,无论是妻子还是女儿,对于他来说,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温暖,都是心中无法湮灭的本能的爱与渴望。
小说全篇没有出现具体的人物姓名,作者通过“噩梦”和“红蝴蝶”这两个意象将小说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以主、次要人物之间相互呼应为基础,说明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明确了三位基本人物各自所处的立场,搭建起了小说的基本框架。
二、人物关系的阐释
虽然不同的人物有着不同的功能,但从叙事技巧来看,人物与周围的事物有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小说在讲述疯子与其妻女之间的关系以及疯子与旁观者之间的关系时,通过利用不同人物关系的组接,来表达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读者更能感受到情感的冷暖。通过人物之间各种关系不断地交织对比,反映出暴力与平静的不相容,以及破坏毁灭和美好幸福的两种人生形态。
小说并没有对疯子和妻子的关系进行直接描写,甚至也没有安排两人见面,而是将疯子不断加重的自残行为映射在疯子妻子不断加重的恐惧心理上。疯子在自己的想象中对别人施加着暴行,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进行血腥的自我伤害。他满眼皆是死尸和鲜血,满心皆是刑罚与暴力,与这个安静祥和的小镇格格不入,唯独在看到红蝴蝶的时候,内心产生了异样的渴望。疯子对妻子满心思念,妻子对他的归来却并不感到欣喜。她感觉到失踪很多年的丈夫回来了,她精心埋葬的噩梦也回来了,她睡不好觉、情绪失控,不敢出门上班也不敢见光。她对疯子的态度是“逃避”的,疯子代表了她不愿面对的那段日子。这段关系的描写,暗示着疯子的归来,同时也将本来已经时过境迁的经历与当下的联系建立了起来。
疯子的亲生女儿与疯子的关系交集是若隐若现的,一方面他的女儿并不知道她多次看到的疯子其实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在她的眼里,疯子仅仅只是一个疯子。在第一次见到疯子时,“疯子的模样叫她吃惊,叫她害怕。她看到他正朝自己古怪地笑着,嘴角淌着口水。她不由惊叫一声拔腿就跑”[2](P15)。她对疯子的印象永远是冷漠、厌恶的,即使是面对着“一团坐着的鲜血”,也丝毫没有掀起她的情绪。而她的母亲却随着疯子越来越严重的自残行为而越发恐惧,恐惧几乎使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她对自己的亲生父亲是厌恶的。因为她的亲生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被带走,导致了她与自己亲生父亲的疏离,对于她来说两人并没有感情基础。她心里只有后来的父亲,她并不希望自己的亲生父亲回来,因为害怕会把自己现在的父亲挤走,害怕母亲因为原配丈夫的回归而唤起不好的回忆变得疑神疑鬼,打破现在幸福和谐的家庭。她十分讨厌这样的局面,这也加深了她对自己亲生父亲的厌恶。于是她对疯子只能是同他人一样,是一名可悲的看客,一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
说到看客,自然就不能不提到小说中疯子与除妻女外其他旁观者之间的关系,在小说中,疯子与旁观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看与被看”的关系。“这些旁观者们,他们就如同鲁迅小说中那些形形色色的看客一样,他们不分男女老幼,没有姓名和样貌,只有一个动作——看”[3]。他们是自私狭隘、冷漠麻木的,没有人在意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更没有人在意他是遭受了怎样的伤害才会变得如此,他们对这样一个初春时节衣衫褴褛的可怜人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同情心,而仅仅只是拿疯子当作他们取笑娱乐、吸引别人眼球的工具。在疯子开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忘乎所以地进行肉体的自我摧残的时候,这些人像蚂蚁一样涌向疯子的周围。这些人都是来看“热闹”的,他们在最开始时冷漠地围观着疯子的自残行为,后又因为被血腥惊吓到一点一点散去。正在疯子生命中最后一次自残时,他们害怕地把他捆了起来,却没有一个人想过要去救他,他们将疯子就这么扔在街口,任由他把血流干,自生自灭。他们是疯子眼中的行尸走肉,是观看嘲笑疯子的另类的冷漠的精神行刑者。大街上奄奄一息的疯子成了他们聚在一起吃饭时的谈资,这些人以观看谈论疯子的自戕行为为乐,他们不会在意疯子疯掉的原因与自戕的真相,更不愿意去想自己是否也活在历史的压迫之中,他们面对这些仅仅只是觉得有趣,然后继续过着自己麻木不仁的生活。
作者通过对人物关系的阐释,表达了历史给家庭和个人所带来的灾难:夫妻分离、父女陌路、家庭破碎。同时运用极端残酷的文字,将血腥暴力的画面描摹的极其细致,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并通过这些看客冷漠的目光,毫不留情地批判着人性。
三、人物的意义诠释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位疯子,疯子的“疯”是区别于其他正常人的,除疯子外的所有次要人物都是主要人物的对立面。如此叙事不仅能够将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也可以将疯子与周围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人与周围的环境,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4],通过环境的对比和衬托,可以从侧面呼应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历史留下来的痛苦的记忆已经烟消云散,人们走出寒冬,走出黑暗,走过那段压抑的日子,过着他们风平浪静的生活。疯子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小镇的,“他也走进了春天,和他们走在一起”[2](P10)。但疯子的世界依然是充满着暴力与血腥的,脑子里依旧还是他曾经研究过的那些刑罚和在被关起来写材料的时候所看到的迫害。他不知道十年前的那场浩劫已经过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知道人们已经选择将那段历史忘却和掩埋,去迎接他们的美好生活。他仍旧活在十年前,活在那段使他疯癫的日子里没有走出来,停留在那个满是死亡和暴力的年代。疯子脑海中总是定格的画面是他被带走之前,“他自己正在洗脚,他的妻子在床边坐着,扎着两根辫子,上面系着红蝴蝶结,女儿在床上睡觉。”[2](P3)他感受不到时间的前进,认为自己还处在曾经的水深火热之中,直到他因为自戕被围观的人们捆起来,最后失血过多濒临死亡,才如回光返照一般地清醒了。疯子清醒之后感觉自己只是昏迷了一场,认为刚才自己所想到的一切都发生在昨夜。他的脑海中依然是那个定格的画面:他被带走之前,自己正在洗脚,妻子在床边坐着,女儿在床上睡觉。可他认为的只是过了一个夜晚,其实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妻子改嫁他人,对外绝口不提自己曾经丈夫的事情;女儿改了名字,心里只有后来的父亲和家庭,对亲生父亲只有陌生和排斥。所有人都向前走了,只有他还独自停留在那个年代,停在原地,被人们所忘却,被隐没于历史的洪流中。
作者虽然将他们同处于一个历史时间和社会环境下,但个体的心理时间的表现和社会环境的感知却是不同步、不协调的。这种由环境侧面映射人物命运的叙事安排,其实暗示了疯子最后死亡的必然性。因为疯子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比起铭记,选择逃避痛苦的回忆是更为轻松的。在那段记忆已经成为过眼云烟,美好又重新回到人们身边的时候,疯子作为一个受害者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不断提醒着那场浩劫的真实存在,昭示着那段晦涩的历史还没有走远”[5],历史留下来的阴影还依然存在,疯子的出现打破了他们佯装的平静和美好。疯子是社会的牺牲品,虽然他用极端血腥和暴力的方式,但是却依然无法唤醒麻木的灵魂。在他死去以后,他的痕迹只用了一泼水,那么容易就被抹去了。社会不断前进发展着,人们的生活日渐丰富多彩,只有疯子,他的永远地停留在了十年前那个他被带走的夜晚。
疯子无疑是可悲的,是历史进程中饱受摧残的牺牲者,他的回归不断提醒着“文革”所带来的伤痛的烙印,那是人们不愿想起、不断逃避的日子。“他死得那么惨烈,却又那么寂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哪怕是自己妻女的理解和痛惜”[6]。如此叙事所描绘出的情景,使人背脊发凉又沉痛无比,暗示了“文革”对人的残害所酿成的令人惋惜的悲剧。
“作为先锋作家,余华的写作背离日常生活经验,揭露人性之恶的本质”[7]。作者通过《一九八六年》这部小说,运用直接描绘和侧面描绘两种人物叙事手法,塑造出“正常”与“非正常”的一组人物对立,在清醒与浑噩、虚幻与真实、历史与当下的矛盾结合中揭开了“文革”时代残忍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健忘又麻木的国民特点。通过隐喻和象征的写作手法,连接起了疯子与看客、行刑者与被行刑者、肉体与精神、过去和未来联系;打通了生存与死亡、人性与暴力之间的隔墙。以此来提醒后世“文革”留给人们的阴影与教训,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