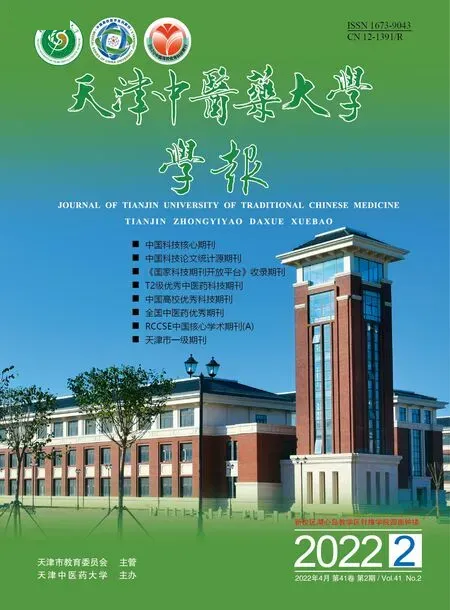“清感饮”组方思路及新冠肺炎特色探讨*
2022-11-27昝树杰雒明池王凯付鲲周胜元张硕封继宏倪道艳
昝树杰 ,雒明池 ,王凯 ,付鲲 ,周胜元 ,张硕 ,封继宏 ,倪道艳
(1.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381;2.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天津 300250)
1 “清感饮”的由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下同)疫情已进入常态化防控的阶段,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压力仍旧严峻。尤其秋冬季的到来,会伴随季节性流感高发。据统计,季节性流感在成年人中的罹患率约为10.7%[1],全人群普遍易感,是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对于慢性基础疾病患者及老年患者。疫苗虽作为季节性流感预防的主要手段,但中国流感疫苗的接种率较低,平均每年仅有2%左右[2-3]。更为关键的是季节性流感的临床表现与新冠肺炎较为相似,若两者叠加发病,将打乱现已形成的高效、敏感的疫情监测体系,影响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对刚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经济造成二次影响,因此当下对季节性流感的防控格外重要。张伯礼教授基于对流感防治的临床经验[4],结合武汉新冠疫情防控经验创制了“清感饮”系列中药代茶饮,主要用于防治季节性流感,降低其与新冠肺炎叠加的风险,从而巩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并根据四季邪气特点以及儿童体质特点,将“清感饮”系列制剂分为春饮、夏饮、秋饮、冬饮、童饮5种。
2 “清感饮”组方思路
2.1 宗疫病辨病防治之理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属于中医学“疫病”的范畴,相当于“时行感冒”病。在与疫病斗争的两千多年里,中医一直有着“大锅熬药”防治疫病的传统,借助“通治方”可以迅速实现广大人群的药物覆盖,对于保护易感人群、截断病势、控制疫情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另一方面说明了“辨病论治”是疫病防治的主要模式。因此,“清感饮”组方首以辨病论治确立“辟秽化浊,清利咽喉”的防治大法,目的是在四季交替、疫病流行之时,针对慢性基础疾病患者、老年人等易感人群提前服药避免感染,未病而先防。对于出现咽痒、咽痛、流涕、打喷嚏等早期上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及早服药可避免病情加重,阻断疫病的传播流行,欲病而先治,既病而防变,充分发挥了中医对疫病“辨病论治、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理论优势。
2.2 效温病辟秽化浊之法 《温病条辨》言“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认为疫病的发生与感触秽浊之气密切相关。喻嘉言在《尚论篇》中提出瘟疫治疗应“预饮芳香正气药……升而逐之,疏而逐之,决而逐之,兼以解毒”,创立三焦逐秽解毒法。吴鞠通“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创制了银翘散,并在霍乱、疟疾、痢疾等疫病治疗中“重用芳香,急驱秽浊”[5]。《神农本草经》云“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除邪辟秽也”,药物芬芳之气为清正之气,可鼓舞人体正气而祛邪;并且芳香药物兼具疏散之性,可疏通气机,开宣毛窍,走肌表而引邪外出。“清感饮”制方效仿温病辟秽化浊之法,选用气味芳香之金银花、紫苏叶,其中金银花可通利肺系,宣达上焦,《重庆堂随笔》言其“解温疫秽恶浊邪”,现代药理研究证实金银花可通过抑制病毒活性、降低炎症因子释放、促进淋巴细胞增殖等途径发挥抗流感病毒的作用[6]。紫苏叶既可开宣肺气,又能行气和中,以芳香之性开化中州、除湿逐秽,两药共用,上、中二焦之秽浊可除。当下世人饮食多肥甘厚味,恐助痰湿化浊,故方中配伍焦山楂,其性平和,入中焦脾胃而专化食浊,且“化瘀血而不伤新血,开郁气而不伤正气”,条畅气血则秽浊不自内生。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中药调节呼吸道、肠道的黏膜免疫功能是预防流感病毒的重要靶点[7]。而山楂多糖、紫苏挥发油均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改善肠道的黏膜免疫功能[8-9]。辟秽化浊法所选芳香类药物的主要成分为挥发油,不宜久煎以免降低药效。故“清感饮”遵循“银翘散”的煎煮古法,以沸水浸泡诸药10 min后即温服,意在防止挥发性成分在煎煮沸腾过程中随水蒸气一起挥发殆尽,从而保证了芳香药物的药效,并且遵循了“肺药取轻清”“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之旨。
2.3 重外感清利咽喉之术 《温疫论》言“从口鼻而入……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咽喉为肺之门户、息道之关隘,其上承口鼻,下接肺胃,是清浊之气往来的必经之处。外邪自口鼻而入最先侵袭咽喉,故咽喉为疫病邪气早期侵袭的关键部位。现代解剖学发现咽喉部淋巴组织丰富,具有吞噬细菌病毒、发挥免疫功能的作用[10]。因此咽喉部健康与否对于疫病预防意义重大。但由于中国居民饮食习惯、生活环境等因素,慢性咽炎的发病率极高[11],尤其是对于教师、烟民等人群。慢性咽炎患者因咽部抵抗力下降,每在季节交替气温变化之时,黏膜的免疫调节能力减弱,细菌和病毒易于在局部定植,继而伺机通过气管侵犯肺脏,发生呼吸系统感染。“清感饮”防治疫病重视“清利咽喉”,选用牛蒡子、射干、桔梗,三药皆入肺经,为张伯礼教授临床治疗急慢性咽炎的常用药队[12]。其中牛蒡子性味辛寒,既可疏散风热,又能宣肺利咽消肿;射干性味苦寒,能降火,为治疗喉痹咽痛之要药;桔梗性味辛苦,可“疗咽喉痛,利肺气,治鼻塞”。搭配甘草“生用凉而泻火……利咽痛”,与桔梗共用寓清喉要剂“甘桔汤”之义,并伍赤芍,病急热盛可凉血,病久成瘀可活血,以助清喉利咽。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牛蒡子、射干、甘草、赤芍均具有抗流感病毒的作用[13-16]。另外“清感饮”服法要求“含口慢饮,徐徐咽下”,效法传统“呷服”之法,以增加药物在咽喉部的接触面积和作用时间,内服与“外用”共奏其效,不但于萌芽之时消灭了病原微生物,而且恢复了咽喉部黏膜的免疫屏障作用。
2.4 扬中医三因制宜之则 “三因制宜”即因时、因人、因地制宜,是中医基本治疗原则之一,体现了中医治病的全面性与灵活性。天津为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属较为典型的北方气候特点。“清感饮”组方化裁因时制宜,不但考虑四季“寒热温凉”的气温变化,而且兼顾“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气机变化。春季气候初暖多风,风热邪气易于侵袭人体,多见发热头痛、鼻塞流涕、咳嗽痰黄、咽喉肿痛等症。故“清感春饮”加用连翘、草果。连翘味苦性凉,可疏散上焦风热。草果辛温,可辟秽化浊、温助阳气,顺应春季生发之势。夏季雨水旺盛,暑热蒸腾,故暑多兼湿。暑热易伤津气,湿邪易阻气机,起病常见发热汗多,身重乏力,头脑昏沉,食少纳呆,恶心腹泻等症。故“清感夏饮”加用藿香、薄荷。藿香辛而微温,芳香温煦而不燥热,既能解表又可兼化中焦之湿,行脾胃之气;薄荷辛凉发散,可清热解暑,宣散阳气,顺应夏季升浮之性。秋季气温渐凉且干燥,燥邪易伤肺津,常症见口鼻干燥、干咳无痰或痰中带血等。故“清感秋饮”加用沙参、桑叶。沙参甘寒,可清肺热、润肺燥;桑叶甘苦寒,善走肺络,可轻宣肺燥,亦可平抑肝阳,顺应秋收之性。冬季寒气主令,易伤阳气,人体感受风寒后可见恶寒重,发热轻,头痛无汗,四肢酸痛,咳痰清稀色白等症。故“清感冬饮”加用黄芪、虎杖,黄芪甘温,可益气扶正固表,收敛阳气,以应冬藏;虎杖味微苦,性微寒,可清肺解毒、止咳化痰。
小儿肺常不足,易于发生外感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球每年约有20%~30%的儿童罹患流感[17]。“清感童饮”则是因人制宜,专为儿童而设。《叶天士医案》中记载“稚年纯阳体质,热症最多”,儿童为纯阳之体,其感邪后易于化热且传变迅速,故“清感童饮”将原方中金银花改为连翘、薄荷,以增强全方清解发散之力。小儿脾常不足,常因饮食失宜而生湿为患,故加用薏苡仁健脾利湿,并可培土生金以养肺。射干性苦寒,有小毒,《别录》云“久服令人虚”,小儿“脏腑娇嫩”不宜长期服用,故去之。
3 清感饮处方特色——茶药结合,防治并施
古谓“茶为万病之药”,纵茶叶有诸多功效,但其单用药效甚微。中药代茶饮简称“药茶”,临床使用已有悠久的历史,是将中草药与茶叶共同配制,加以煎煮或冲泡,用于防治疾病的一种便捷手段。“清感饮”借鉴传统中药代茶饮剂型,采用现代制作工艺,将药茶炮制成粗粉,在特制的纸袋中分装,患者服用时将纸袋药渣在沸水中浸泡,去除纸袋后饮用药液,具有体积小、方便服用、溶出快的特点,最大限度的保留了中药汤剂的优势与特色,并且口感温和,预防与治疗均可,百姓易于接受,便于临床推广普及。
“清感饮”根据季节选取相应的茶基,与传统饮茶习惯相统一,继承发扬了中国的茶文化。“清感春饮”茶基为花茶,因春天万物复苏,人体阳气待兴,此时常觉困意,花茶甘凉,气味芳香辛散,饮后令人精神振奋,头脑清醒。“清感夏饮”茶基为绿茶,因夏季炎热潮湿,人体津液因出汗而大量丢失,绿茶苦寒,清鲜爽口之余略有苦味,饮之既可补充津液,又有清暑燥湿之功。“清感秋饮”茶基为菊花茶,因秋季万物凋零,气候干燥,肃杀之气弥漫,菊花于秋季采收,性甘微寒,具有疏散风热、清肝明目的作用,《本草纲目》载其“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制火”,尤适秋燥。“清感冬饮”茶基为红茶,因冬季寒风凛冽,红茶性味甘温,入口香甜醇厚,富含蛋白质,冬季饮用可补益身体,增强机体抵抗力,生热暖腹,以御寒冬。
4 结语
中医药在抗击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全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清感饮”系列制剂是中医药继续参与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重要举措之一。“清感饮”基于中医疫病防治传统理念,从经典出发并结合张伯礼教授临床经验,创立“辟秽化浊,清利咽喉”的防治大法,择药配伍因时、因人、因地制宜,组方严谨合理,并以中药代茶饮的剂型推广,普惠广大百姓,且相对于疫苗具有“简便廉验”的优势。2020年10月,“清感饮”系列制剂正式纳入天津市医保支付范围,并在全市400余家各级医疗机构进行推广使用。同年11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组织专家组共同制定了《“清感饮”系列制剂临床应用专家共识》,为“清感饮”的临床使用提供专业指导[18]。为了更好地推广“清感饮”,将开展“清感饮”相关机制研究以及大样本的真实世界研究,从而对其疗效和安全性进行客观评价,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干预作用,发挥中医“治未病”的优势。
致谢本文曾蒙张伯礼教授审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