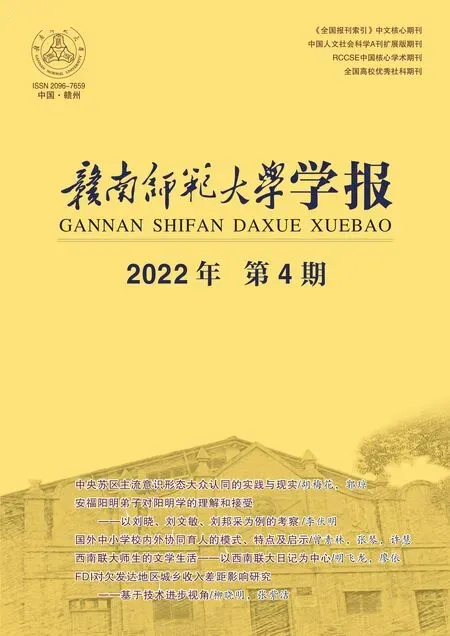虚幻与现实之间
——析《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的后现代叙事*
2022-11-27何惠清
何惠清
(暨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州 511400)
20世纪5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方,而彼时恰逢英国当代女作家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18—2006)小说创作生涯的发端。作为深受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法国“新小说派”影响的作家,斯帕克同样注重小说形式与技巧的创新。可以说,她的作品是“完全实验性的”。[1]自其代表作《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1961)问世以来,国内外学者们对该文本的后现代与叙事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或从玛利的人物命运着手,剖析文本的叙事伦理;[2]或立足于文本的叙事时空,探讨时空合力下的叙事秩序。[3]大卫·洛奇也曾指出,斯帕克“将频繁跳跃的时间与第三人称叙述相结合”,[4]77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策略。
事实上,斯帕克的作品不是小说技巧的堆砌物,隐匿于后现代语言游戏表面之下的,是女作家对于人类道德与社会的深切体察。鉴于此,本文从分析斯帕克的后现代叙事着手,探讨《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故事与话语的照应关系,揭示小说家如何通过后现代实验性叙事策略,将虚幻与现实、文学与历史并置,在时空的诗性跳跃中,凸显现实的混乱以及人性的异化。
一、时空错乱:虚实边界的模糊
马克·柯里将线性特征总结为“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这样就撑起了意义的整个系统”。[5]可以说,贯穿于事件安排的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暗含了时间上的因果关系。传统小说中的情节大都是按照这种有序的线性模式展开,旨在传达出既定的意义、展现逻辑的现实世界。然而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小说家们抛弃了对于意义的终极追求,因而“时间是迷混的、断裂的、非线性的……时间在话语中不能以确定的方式来控制或确定。”[6]25根据被讲述故事的时间顺序与文本中所呈现出的时间顺序之间的关系,热奈特将叙事文本中的时间分成两种:一种为故事时间(story time),即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一种为叙事时间(narrative time),即故事在叙事文本中所呈现出的时间状态。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之间所具有的差异则被称为“时间偏离”(chronological deviation),或是“时间倒错”(anachronies)。[7]在《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斯帕克充分发挥小说家的虚构特权,自如地操控叙述时间、编排故事情节,意图通过这种断裂式的叙述来打破以因果性和整一性为内核的叙事成规,用颠覆性文本解构现实世界的时间观与价值观。
在《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各个事件之间的时间关系都极为复杂,但通过文本细读,小说的故事时间范围可以框定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可以概括为:在马西亚·布莱恩女子学校中,6个小学女生被布罗迪小姐独特的教学方式与思想所吸引,无论是行事方式抑或穿衣打扮方面均追随布罗迪小姐的脚步,并因此被戏称为“布罗迪帮”(the Brodie set)。即使进入中学时期,布罗迪小姐仍深深影响着女孩们。与此同时,布罗迪小姐利用自己在帮中的“权威”,妄图主宰女孩们的人生。当女孩们步入中学高年级后,独立意识渐渐觉醒,便开始对布罗迪小姐的控制欲产生反感。之后,布罗迪小姐被其最为信任的学生桑蒂背叛,被迫提前退休,并在不久后病逝。如果故事按照这样的线性时间叙述则具有明显的因果逻辑,因为叙述中的时间链实际是一种因果关系链,而“因果链完整是整一价值观的体现”。[8]这样看,似乎反面人物终将得到应有的报应与惩罚就是小说所要传达的道德价值观念。然而,女作家并未按照这样的客观时间顺序来叙述整个故事。
斯帕克认为,因果关系并不具有时间意义上的持存性:“一件事的发生并不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诱发另一件事”。[9]如果说“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撑起了意义系统,使得历史有必然的因果规律可循,那么斯帕克的时间观则是对意义进行了具有本体意味的颠覆。在小说开头处,故事就如荷马史诗般从中间切入,通过布罗迪小姐之口交代了文本中出现的第一个确切时间点:“现在是一九三六年”。[10]12彼时,“布罗迪帮”中的女孩们已经16岁。之后,时间追溯回6年前,即1930年,布罗迪小姐在榆树下给女孩们上历史课的场景,这才是故事时间的真正开端,而小说的开头其实是一段预叙。到了第二章开头处,时间突然跳到了14年后,作者再一次采用预叙的手法,提前揭示了玛利24岁时将在旅馆因大火而亡的结局,之后,时间又回到了1930年。在之后的叙述中,帮内其他女孩的命运以及“谁背叛了布罗迪小姐”这个问题的答案也都以预叙的方式一一揭晓。
在小说中,女作家并不青睐悬念游戏,也不让时间在横轴上水平发展,而是通过穿插预叙与倒叙来打破事件因果发展的线性规律,一旦这种线性规律被打破,情节就变得破碎不堪,失去了有序的情节,整齐的道德价值体系也就无从建立。布罗迪小姐的控制和桑蒂的背叛孰是孰非难以言明,因为人性本就是复杂与无法系统描述的。小说中的叙事时间在过去、现在与将来之中反复游走、跳跃,种种事件脱离了故事时间的延续性和顺序性的束缚,斯帕克通过这种非时间化的叙事手法,以小说世界中时间的无序来暗示后现代社会的混乱状态。
除此之外,小说家还采用了后现代的“拼贴”(collage)技巧,丰富了文本的空间层次,拆除了文本与现实、文学与历史的本体界限,由此展现现实的荒诞与断裂。所谓“拼贴”,原本是绘画艺术中的一种表现手法,它指的是将不同形式的素材收集起来并贴于某个表面,从而展现出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后来这种手法被小说家广泛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并成为后现代小说常用的技巧之一。在后现代语境下,作家们刻意将小说中的各个成分相互分解、颠覆,因他们认为“文本是开放、异质、破碎、多声部的, 犹如马赛克一样的拼贴”。[11]在小说混乱时序的叙述与时空并置的转换中,作者嵌入了数个幻想性叙事片段,进一步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壁垒。桑蒂在故事世界中的幻想天马行空,跨越了时空的距离。当布罗迪小姐在课堂上朗诵诗歌时,桑蒂便幻想着与诗歌中的主人公夏洛特夫人对话;当布罗迪小姐带领着学生们在爱丁堡老城散步时,桑蒂又幻想着与19世纪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笔下《绑架》中的人物艾伦·布雷克交谈。在桑蒂的幻想中,她既可以与《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先生进行会话,又可以是一位与巴甫洛娃并驾齐驱的芭蕾舞蹈艺术家。
这些虚幻的片段与小说中的现实世界交替更迭出现,看似随意搁置,让读者雾里看花,不知所云。但细细品读,会发现这些幻想与小说情节发展以及主题表达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在桑蒂与夏洛特夫人对话的幻想片段中,夏洛特夫人用悲怆的语气对桑蒂说,“那个女子如此年轻如此美貌,爱情必遭不幸”。[10]38而夏洛特夫人所说的“那个女子”便指的是布罗迪小姐。桑蒂的幻想披露了布罗迪小姐坎坷的爱情经历,在后文中,从布罗迪小姐与休阴阳两隔的悲惨爱情,与劳埃德的婚外恋,到与娄赛无疾而终的恋情,均应验了布罗迪小姐“爱情必遭不幸”的预言。桑蒂幻想中的人物无缝整合进了她的人生中,她脑海中那些天马行空的幻想世界也与小说中的世界交替更迭出现,幻想甚至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这也使得原本就失去秩序的故事时间与空间更加混乱。通过拼贴的技法,女作家模糊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可以说,在《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现实就是虚幻的集成物。
在后现代主义作家看来现实并不是单数,世界也不是单数,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时常可以看到种种世界的冲突与交叠。[6]50作为斯帕克笔下虚构的人物,桑蒂既可以和同为虚构人物的布雷克以及罗切斯特先生交谈,又可以打破异质空间的壁垒,转而与客观世界中的俄罗斯舞者巴甫洛娃对话。女作家这种虚实并置、真伪并行的叙述凸显了现实世界的不可认知性与不可解释性,同时也是对建立在普遍经验模式上单一真实观的否定,展现了后现代社会中真实性难以确定的本质。
二、元小说:虚构性的呈现
20世纪下半叶,小说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进入所谓的“枯竭”与“死亡”时期,而元小说,作为一种“对整个叙述方式都有着强烈自我意识”,[12]并且“使人们注意到其虚构本质和创作过程”[4]206的实验性小说,成为后现代派小说家们驳斥“小说死亡论”的策略性武器。在传统小说中,作家们竭尽所能地将故事说得栩栩如生,努力掩盖、甚至抹去叙述的痕迹,因他们认为艺术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与摹仿,然而在后现代派小说家们看来,客观世界是“一片混乱,不可捉摸”的,是“寻不到任何规律,因此无法去描写”的。[6]33所以,在典型的后现代元小说中,作家们喜好玩弄文字游戏,甚至在文本中直接暴露作者的存在,展现出浓厚的自我意识以戳穿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虚构性。在《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斯帕克也采用了元小说的叙事策略来突出故事的被讲述性和话语的非实在性,从而拆解虚实之间的绝对界限,以影射后现代社会人类内心以及生存状态的混乱。
《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的元小说特征之一,就在于其嵌套式的叙事结构。帕特丽夏·沃认为,元小说会使用诸如“故事里套故事”的框架结构来唤醒读者对框架的意识,由此使其意识到“世界的意义和价值都是如何被构建的,并且可以通过何种方式去挑战和改变”。[13]30-34斯帕克正是通过这种框架策略有意识地模糊虚幻与现实的边界,以凸显文本的虚构本质。小说中,斯帕克在描写布罗迪小姐人生起伏的主叙事层中嵌入了数个以学生桑蒂和珍妮之名拟写的虚构故事:“笔记本上写着:‘《高山房舍》,作者桑蒂·斯特林杰、珍妮·格雷。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故事,写的是布罗迪小姐的情人休·卡路特斯’”。[10]30更为典型的是,布罗迪小姐在学校与美术老师劳埃德以及音乐老师娄赛三人之间的暧昧关系也被学生二人捕捉到,于是二人便坐在一个山洞前面,完成了关于布罗迪小姐和音乐老师的“创作”。[10]147在二人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她们意识到“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把握好布罗迪小姐作为正、反两方面人物的分寸”。[10]147-148女作家借桑蒂和珍妮合写故事这一元小说情节透露出其自身在小说创作与人物塑造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展现出了她对于文学创作的深刻思考。同时,这些嵌套式的故事与小说的主叙事层相互交织,多个虚构世界一同形成了嵌套式的叙事迷宫,让人难分虚实,使本就混乱的情节更加扑朔迷离。斯帕克以虚构中套虚构的方式彻底颠覆了叙事文本的真实性,并借此对故事背后现实世界的确定性与统一性进行了本源性的消解。
此外,小说中另一个明显的元小说特征是小说人物“角色扮演”属性的展现。正如沃所言,通过“对人物在小说中进行‘角色扮演’的主题进行探究以审视小说的虚构性,是元小说最精简的形式” 。[13]116在《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布罗迪小姐也总是沉浸在虚幻的自我世界中。她常常声称“我正处于事业的鼎盛时期”,[10]12并坚信“只要给我一个处在可塑年龄的女孩子,那她的一生都将是我的了”。[10]11她根据自己的幻想杜撰出情人死于战争的情节以塑造自己长情的形象,达到控制学生的目的。不仅如此,她声称教育是“要将学生灵魂中固有的东西引导出来”,[10]70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她却一再地将自己的喜好与信仰强加给学生们。在布罗迪帮中,正如桑蒂所想,“她以为她就是天意,她就是加尔文的上帝,她预见到了太初与终结”。[10]249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指出,现代社会异化的根源之一在于“人的存在与他的本质相疏远,人在事实上不是他潜在他所是的那个样子”,[14]这种存在和本质之间断层式的落差让人分不清虚实,加速了人性的异化。在布罗迪小姐不切实际的臆想之中,她视自己如上帝,认为自己拥有无限的魅力,事业处于全盛时期。然而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爱丁堡“有一大批像她这样三十多岁的妇女”,在这些妇女之中“布罗迪小姐算不上与众不同”。[10]81-82虚幻的上帝角色与现实的普通妇女之间的矛盾使得布罗迪小姐的精神世界愈发病态,她错把虚幻当成现实,最终致使事业走向毁灭,间接加速了她的死亡。斯帕克以主人公的这一结局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后现代社会中人性异化所带来的悲剧,并通过故事主人公“角色扮演”的虚幻之举来凸显现实世界的荒诞与矛盾。
谈及小说叙事的虚构性时,艾丽斯·默多克曾表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为自己创造虚构的故事或是背景,并被这种虚构所控制。他们被困在自我虚构的世界中,同时邀请他人到自己虚构的故事或是背景中来扮演某些特定的角色,而有些小说家就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在作品中将之体现。[15]作为与默多克同一时代的作家,斯帕克正是处于“敏锐地捕捉到”现实本身就充满了虚幻的小说家之列。斯帕克通过元小说的框架策略与展现人物“角色扮演”的属性使虚幻与现实交织重叠、相互融合,彰显出后现代语境下人们对于真实与意义之确定性的质疑;通过小说主人公编造故事以试图控制他人的行为来影射传统小说家们通过文本操纵意义的创作倾向,而曾被动接受故事的布罗迪帮中女孩们的觉醒也暗示着,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只有积极思考,才能摆脱控制,认清本质。
三、视角变换:主题意蕴的延伸
视角是传递主题意义的重要媒介。在《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斯帕克通过全知叙述与内聚焦视角的交错转换使文本的主题意蕴得到延伸,通过不同的视角多维度地展现人性的复杂性。
在全知叙述中,叙述者“具有对人物进行各种评论的极大自由”,[16]212他置身于小说世界之外,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一般,俯瞰一切。在叙述过程中,他时常利用自己无所不知的能力毫不掩饰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以此来展现优越性。在《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全知全能型叙述者的叙述影响了读者对于人物形象及性格特征的判断,使读者提前知晓人物的结局,剥夺了小说中的人物自我言说的权力以及主宰自我命运的能力。小说中对于玛利这个人物的叙述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小说中,玛利被认为是“众所周知的蠢丫头和大家的出气筒”,[10]21布罗迪小姐也常常责备玛利,并对她说“从来也没见过像你这样笨的孩子”。[10]24在评论时,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一般具有绝对的可信性,因此,叙述者利用自己的优势也加入进来,不断地告诉读者玛利“笨得连撒谎都不会”。[10]16从故事开头对玛利的介绍到后面对发生在玛利身上种种事件的描写,叙述者通过反复地使用诸如“笨拙”和“蠢”等词,与读者暗暗地进行交流,加深了读者对玛利的刻板印象,使读者相信玛利“是个蠢丫头”的事实。因此,在小说第二章的开头,对于玛利失败的恋爱、在妇女皇家服务队时常常遭受责骂的现实,以及在20多岁时死于旅馆大火的预叙都自然地合理化了。处于故事外的叙述者居高临下地进行干预性的评论,使得玛利这样的人物完全丧失了自我言说与自我主宰的能力,她们的命运早已被注定。作者通过这样的安排来体现叙述者强大的操控力,就如同布罗迪小姐试图塑造帮中女孩们的人生一样,独裁且专断,强化了小说中的控制主题。
然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并未让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总是处于高高在上、目视一切的位置。申丹认为,在传统的第三人称小说中,故事外的叙述者一般都是采用自己上帝一般的眼光来进行叙事,但是“在20世纪初以来的第三人称小说中,叙述者常常放弃自己的眼光而转用故事中主要人物的眼光来叙事”。[16]186在《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全知全能型的叙述者在话语层面上充当了叙述声音的角色,控制着小说人物的价值判断,但从故事层面上看,桑蒂这个人物的视角,则是对全知全能叙述者那看似权威叙述的一种反抗。在小说的前三章中,斯帕克透过叙述者之口提前预示了桑蒂这个人物的重要性。她既是布罗迪小姐最信任的学生,又是背叛布罗迪小姐的人。她帮助校长麦凯小姐举证,控诉布罗迪小姐在教学过程中宣扬法西斯主义,并因此导致布罗迪小姐提前退休,结束教学生涯。
洛奇认为,桑蒂这个人物是“读者的眼睛”(the eyes of the reader),是小说中的“感知意识”(the perceiving consciousness)。[17]布罗迪小姐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但斯帕克并未让叙述者毫无保留地表现出布罗迪小姐的内心世界;相反,是桑蒂的视角更多面地展示了布罗迪小姐的形象。一开始,桑蒂对布罗迪小姐的故事深信不疑。但是桑蒂渐渐成熟,在一次和布罗迪小姐谈话时,布罗迪小姐说着她与劳埃德以及娄赛三人之间的爱恨纠葛,桑蒂在想“这未必是故事的全部内容”。[10]12025年后,桑蒂回首,才真正明白过来,如果当时认真想一下,“便会看清布罗迪小姐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10]175桑蒂就像电影院中坐在暗处的观众一样,沉默地观察着一切。在娄赛家中时,桑蒂看着布罗迪小姐与娄赛:“他很瘦,也比布罗迪小姐矮。他以充满爱的目光看她,而她却以严峻和充满占有欲的眼神看他”,[10]182-183透过桑蒂的视角,读者能够感受到布罗迪小姐那快要溢出字里行间的控制欲。桑蒂对于布罗迪小姐直接抑或间接的评价与想法深深地影响着读者对于布罗迪小姐形象的构建,可以说读者对于布罗迪小姐的看法是随着桑蒂一起转变的。透过桑蒂的视角,布罗迪小姐那隐藏在无私奉献于学生表面之下的自私、专制与独裁暴露得一览无遗。如果说桑蒂的人物视角是对全知全能叙述者所构建出的叙述权威的一种消解,那么桑蒂在小说中的一系列行为——与劳埃德老师保持暧昧、背叛布罗迪小姐、皈依天主教——就是对布罗迪小姐所代表的权威的一种反抗。
正如查特曼所言,当采用小说中的人物视角时,此时的视角属于故事层面,但叙述声音却总是处于故事之外的话语层面上的。[18]在《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斯帕克通过桑蒂的人物视角与全知全能叙述,使故事与话语达到了有机结合。在全知全能叙述者与桑蒂的人物视角所形成的叙述张力中,作者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丰富了小说的主题意蕴。正是这样的安排,反映出斯帕克在叙述方式上不断创新与探索,使得其文极具张力与魅力。
四、结语
在《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女作家利用时间与空间的相互交错突破了传统小说线性的叙事观,三维时间的并置与跳跃、异质文本的嵌套与交融模糊了虚幻与现实的边界,同时恰如其分地展现出小说人物混乱与矛盾的内心状态,也使得小说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空间感与立体感。此外,女作家通过采用元小说的惯用手法:嵌套式的结构以及刻意展现人物“角色扮演”的属性以揭露小说叙事的虚构本质,凸显了后现代社会的荒诞性与无序性。同时,视角的灵活变换所形成的叙事张力充分显露出人性的复杂,丰富了小说的意义空间,创造出奇特的艺术效果。可以说,《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极富后现代叙事风格。
在斯帕克的实验小说中,传统叙事中宏大的叙事与有序的情节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纷繁复杂的叙事迷宫。通过虚幻与现实、艺术与真实的并置,女作家打破了文本到读者之间交流的单线性,构建起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多维交流空间,展现了后现代语境下女作家对于小说创作与阐释的深刻思考。斯帕克的作品需要细细的品味,也值得一读再读,以真正感受到隐藏在字里行间中的睿语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