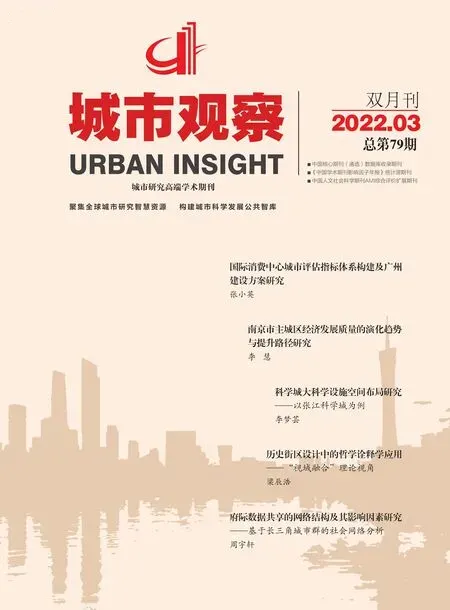数字化交往:数字媒介时代社会交往的路径重构与思考
2022-11-27周文俊
■周文俊
一、全新的社会交往类型——数字化交往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平台对日常与公共生活全方位的渗透嵌入,人类社会进入新的阶段——数字媒介时代。数字化社会背景下,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媒介技术的发展迭代和新的媒介形式及人群的不断涌现,构建和形塑着更加广泛多元的社交关系和交往空间,也形成了全新的社会交往文化——数字化交往。数字化交往作为交往主体合目的性表达的重要途径,将全新的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精神导入传统的媒介研究、人际关系学研究、心理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等领域,预示着相关学科的学术范式将被改写,甚至诞生具有转折和范式意义的新研究门类。
(一)数字时代:社会的媒介化
在数字媒介时代,传统的社交关系和方式及对媒介的释义已显得过于狭隘。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及实证主义传播学在内的主流传播学派,将媒介与大众传媒划上等号,认为其作为一种显性的存在,更多地发挥着信息和价值观念传递的工具性功用,并且只有那些被专业地用于信息传递的传播介质才可以称为媒介[1]。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观拓宽了对于媒介的理解,包括语言、文字、服饰、住宅、货币、时钟等在内的所有延伸人身体功能感觉和借以体验社会和自然的“中介物”,均被划到“媒介”的“能指”域[2]。“媒介”被广义地界定为“人的任何延伸”[3]。媒介不再仅是一种中性的、工具性的存在,已经成为连接人类与世界的桥梁,甚至成为人们生活的底色。
20世纪30年代,曼海姆(Karl Mannheim)最早将“媒介化”这一学术概念呈现在大众面前,提出了“人类关系的媒介化”[4];Hjarvard将“媒介化”视为“媒介拥有了更大的权利,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结构性转型过程”[5];Schulz认为媒介化是一个延伸、替代、融合和接纳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带来传播媒介和社会的变化[6];而唐士哲认为,媒介化的表现是,媒介形式“介入”了当代生活的不同层面,正如音乐演奏形式由现场到录音的转变[7]。社会交往中,媒介技术延伸了人类沟通的边界,增强了个人和群体间的社会联系。数字技术所提供的沟通场景、社交线索以及极大的便利性,使社会的媒介使用程度日益加深,交往习惯得以重塑,形成一种莫比乌斯环式(Mobius band)的数字交往趋势:一种媒介越是不限于传达信息、越是混同于数字社会行为,就越具有“新媒体性”;而一种媒介应用越具有“新媒体性”,就越具有“数字交往性”[8]。
数字时代升维式的技术发展,媒介已经如自然环境般遍在[9]。麦克卢汉“地球村”的预言和宏伟愿景在数字化生存的当下彻底变为现实,人类交往也在数字媒介技术的加持和推动下,变得可触可感,更加真实。信息从古罗马时期借助蜡版和莎草纸得以传播,到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直至今天5G、区块链、人工智能甚至连接现在与未来、融数字化技术为一体的终极数字媒介“元宇宙”等主导的数字信息时代[10],人类的交往方式及对自身和人际关系的许多传统认知不断被刷新。“云端交往”“数字化交往”日益成为社会交往在深度媒介化当下的重要表征,在引发社会基本结构变革的同时,也逐渐演化成为社会的基因。
(二)数字化交往:社会交往的新实践
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不仅需要物质资料交换作为生存基础,也需要人际交往承载情感。但传统的人类交往活动受到时空范围、文化背景、交往手段、权利结构等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媒介技术的发展破解了人类交往的困局,使受场合等制约的信息系统开始受到侵蚀:折叠时间、延展空间、扩大交往自由、实现交往意志。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在传播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呈现出更广、更深的趋势。各种社交媒体渗入生活的各个角落,构建起一个与“线下空间”并置的“虚拟交往空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实和虚拟之间的无缝衔接,不仅改变了人际关系的内涵、逻辑和意义,也催生出新的社交生态。杜骏飞从传播学视角将以互联网传播为背景的虚拟世界数字化交往定义为“虚拟社会中的交流—行动[11]”。笔者将“数字化交往”更加具体地理解为——基于数字媒介技术连接的线上社会和线下社会中交往主体去中心化、交往时空无界化、交往关系个性化等普遍的数字关系。
数字化时代的交往特点在主体、社会关系、时空结构等层面得以彰显。数字化交往关系“意味着传统神圣物的退场,自我崇拜成为每个个体内心的新神圣物”[12]。主体性是数字时代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构建自我价值的内在基础。
在当下多维交叉和去中心化的交往网络中,现代媒介作为交往的核心力量,打造了越发多元的主体维度,提升了主体的流动性,延伸了主体的交往实践路径,也全方位加速了人的主体性在数字交往中的嬗变。人际交往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关系,为交往者带来充分的交往自由,使主体镜像的呈现越来越个性化、空间化,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自我意识得到培养和提升。媒介技术的生产性变革使数字时代的交往“鼓励每一个个体平等参与……吸引每一个个体参与到社会交往中来……包容和鼓励个人的全面和个性化的发展”[13],改变了交往主体面对信息时被动接收的局面。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智慧语音等技术,使人们信息交互的体验感得到极大丰富与延伸。数字化交往借助智能技术增强“现实”的特质,综合调动个体视觉、听觉、触觉等多个感官,发挥了主体身体感官和思维的最大效力。可以说,数字技术引发传播工具发生变革的同时,重构了身体作为媒介的地位和意义,极大增强了数字化交往过程中的主体性。
关系作为人际交往的核心,在交谈和互动过程中得以建立和巩固。而社会的媒介化及数字化发展,必然带来人类社会交往关系、文化价值体系的变化乃至重构。媒介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长驱直入,使得充满未知、“距离产生美”的线上关系揭开了神秘面纱。发生和形成交往关系的“场”突破了身体观念上的躯体边界,场地空间的封闭与固定性被打破。比如,在线教育和在线会议用云计算构建线上教室与会场,让个体得以在数字空间中互动交流[14]。承载交往关系的“场”已经由线下转移至线上。
查尔斯·伯格(Charles Berger)在其不确定性递减理论中指出:无论在何种媒体或环境中,人们总有一种本能动机,就是希望减少对他人的不确定性,并且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15]。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普泛化,为个体与他人建立关系创造出更多可能,在新型社交场景中产生了真切的“社会临场感”。正如个体在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上的“转赞评”行为,即便没有和他人进行可触可感的直接互动,在线的参与也会激发一种联结感。此外,大数据算法也会根据检索和浏览痕迹进行精准的内容推送,客观上拓展了人们对未知的线上关系的好奇与探索。个体间及个体与群体间的交往圈层被极大拓展,形成一种不再受制于地理方位、权利结构等束缚,而是基于数字化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共性话语的“普遍交往”的人际和社会关系。
二、技术可供性下的媒介逻辑——社会交往的路径重构
从个体之间的微观交流,到整个社会的互动变迁,媒介已深深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情境之中,无所不在地不断创造和呈现新的时空结构、存在方式和交往路径。
(一)作为基础设施的社交平台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社交媒体,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基础设施,而不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渠道和对传统交往的简单扩充。作为组织和生成社会的平台,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们参与交往行动的方式和路径。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社交媒体扮演着象征性黏合剂的角色,拉近了媒介使用者与媒介间的距离。技术加持下的媒介所具有的便捷性与其对交往成员体貌特征、思维方式及交流场景和社会语境的拟真,使人们产生“媒介即世界”的感觉与认知,甚至构建出一种“由于过于生动、具体和全面,以至于比世界的本来面貌更加真实的‘超现实’”[16]。就像Livingstone所宣告的那样,“所有事物媒介化(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17]的时代已经到来:日常沟通需要通过即时通信软件;餐饮住宿要看第三方消费点评平台上的打分;网络购物需要参考店铺评价和“买家秀”;规划出行路线需要借助导航软件……个人通过媒介这个巨大的平台与世界建立起连接。这一系列体验得以实现都依靠着数字时代强大的技术支撑,如同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诗意般书写的那样:“船将海洋转化为了天然的媒介……如果没有船,大海将只是一个‘物自体’而无法出现在人类认识的地平线上”[18]。平台通过广泛接入与触达来实现社会关系连接、社会资源重组,其所呈现的作为一种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基本特征与功能指向,也早在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等人的定义之中:“一种可编程的数字化建构,用来实现使用者、公司实体和社会公众的互动。”[19]
越发基础设施化的社交平台伴随着技术的演进,解构了以往的传播关系,以其所具有的开放连接、去中心化的特质,实现了连接程度、交往实践等前所未有的飞跃。开放、共享、控制等平台逻辑连接起作为节点的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链条,进而编织出巨型的传播网络,并改写了网络社会的传播规则。参与其中的个体作为公共空间中的一员,在时空折叠的数字场域中进行着自我呈现和身份构建,并使人际交往更多地发生在“云端”。在这里,人们的社交行为和交往场景不断被融合、延伸、替代,实现了从“面对面”的具身互动到“节点对节点”或“终端对终端”的离身连接,形成了复合重组(remixing)的全新交往空间。
(二)“公私”边界交错,交往互动的新场域
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中设定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相互影响、始终在线的虚拟世界,人类可以自由游走于现实与虚拟世界之间”[20],这一似乎遥不可及的场景在数字媒介时代逐渐走向现实。媒介改变了个体参与者界定社会情景、使用何种传播途径、定义互动领域界限的能力[21]。人们借助媒介在多个平行情景下快速地转换。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1974年提出“流动的藏私(mobile privati⁃sation)”这一概念,指代个人隐私随着电视普及而逐渐走向公共空间[22]。微信、视频博客(Vlog)等个性化的媒介平台越来越多地成为个体记录生活、表达自我的重要载体,为用户个人情绪的扩散与强化提供了虚拟的网络空间和场域,私人领域的公共性也日益凸显。社交媒体平台交往中,个人账户的建立实现了节点对节点式的用户私密社交期待,甚至产生了“隔音室”效应。正如阿伦特所言:“现代的隐私就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庇护私密性而言,不是作为政治领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社会领域的对立面被发现的。”[23]
个人情感、情绪的表达以一种比以往更加直白和外显的方式体现在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各环节。正如威廉斯所认为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情感结构也将变得显而易见[24]。数字媒介时代,微信、微博等移动社交媒体能迅速满足人们交往过程中情感表达的需求。交往主体在媒介平台上通过发布、讨论生成内容,传情达意,同时也影响着他人的情绪状态。微信朋友圈的记录分享、微博热搜下的点赞评论、哔哩哔哩视频中的实时弹幕、直播间内的滚屏互动等,公众带着情感走进媒介技术形塑的一个个信息场景公共空间并参与其中互动,形成一个全新的场域。
(三)虚实混融,人机互动新关系
数字媒介技术增强了交往主体间的交往动机和欲望,延伸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现实与虚拟、人与媒介、机器间的边界也在高度沉浸式的传播网络中被重置。现实中的人在虚拟空间中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和情感连接,拥有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越来越多脱离生物身体的非人类交往主体,如社交机器人与虚拟数字人,开始融入人类的社交圈层。
人机之间变得可协调、可沟通,在由智能技术构建的新型人机关系中,机器(技术)不仅通过嵌入、融合等方式增强和延伸了人的身体机能,更通过将其技术经验融入身体知觉系统进行深度学习,从而形成对世界更为丰富、多元的体验感知,使之超越人的感官能力和自身经验[25]。完全外化于身体的智能系统已经开始模拟人际传播的应用场景。智能主播、虚拟偶像通过动态捕捉、语音合成、全息投影等技术出现在人们的交往视野中,满足了与受众进行身体和心理互动的条件,并重新定义了主播与听众、偶像和粉丝间的关系。“Siri”“小度”“小爱同学”等智慧语音助手不仅用语音识别技术给用户带来全新的语音交互体验,还可以采集并学习用户的情感信息。人机交互不再局限于服务领域,在生活陪伴、精神慰藉等方面,也将更具临场感与对象感,逐渐演变为社会交往中最具具身性体验的传播方式[26]。
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非对立、一体化关系在数字媒介支持下得以建立,它们不再是两个对立的事物。人、技术/物、社会三者之间也相互融合、相互建构,形成多元的社交场景和“液态化”交往趋势,共同建构了新的社会交往范式和新的社交图景。
技术的可供性赋予社交媒体更加完备的功能,但其功能本质还是社交。学者颜景毅从杜威的传播“参与观”和符号互动理论出发,对数字时代的社交媒体和交往关系进行解读,并将数字化传播与传统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进行比较,认为社交媒介在技术层面完成了加入和分享的参与机制,技术为个体参与提供了更广袤的空间和更宽阔的平台,使得社交媒体既有人际传播的情感力量,又有大众传播广泛的社交性[27]。随着社交媒体的深度嵌入,参与式的交往方式已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常态。社会成员可以通过主动表达,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寻求他人的情感支持和认同,借助这种参与式的交往不断扩大社交圈层、获得社会性、创造出意义共同体。
三、数字媒介时代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的悖论与困境之思
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介助力人们维持人际关系、创设交往情景、开拓新的交往路径、获得更多交往选择、建立新的社交范式和图景……在这种全新的数字场域内展开交往互动,节点化的主体与其社会关系也产生了新的交集,但同时也引发新的争议。媒介的自决权和其他权力“迫使”其使用者必须遵循媒介的逻辑,由此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困境。
(一)“强关系”和“弱关系”
数字技术为人类编织了一张“崭新”的社会关系网。自网络社交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之日起,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虚拟网络空间的社交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都发生了变动。媒介平台从信息传递的中介工具演化为关系交往的基础设施,因而现实生活中毫无交集的陌生用户和群体之间也可以构建网络亲密关系,人际关系也在不断自我展现的过程中被层层建构。强弱关系之间的模糊性和流动性由此引发各方的关注和思考。
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1973年发表的《弱连接的力量》一文中首次提出关系力量的概念,并从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度和互惠交换等四方面将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28]。他认为,强关系网络中,人们的认知和信息的同质性较强,人际关系更为紧密,如家庭、亲属、同学之间的关系。而弱关系网络中,人们异质性强,人际关系没有太多情感维系,信息和资源传播与交换的范围却可以更广,更多地充当信息桥梁的作用,如同处一个微信群中却素未谋面的“陌生朋友”。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29]。具有先天社会背景和人际交往优势、有较强情感连接、个体信任度高、互动深入且关系稳固的强关系一直在人际交往中起着主导作用,构建和编织着包括血缘、地缘等在内的关系。但沿用到互联网技术全面融合、连接与重组的数字媒介时代,空间异化使得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以物理距离的远近为主要凭据,“熟人社会”理论无法体现出社会环境的变化给人际关系带来的影响,也无法解释互联网对于人际关系造成的革命性影响。
按照经典的强弱关系理论,基于社交媒介的交往,因交流时间和深度有限,且未知对方真实身份,理应被归纳为一种“弱关系”。但媒介的智能化和深度嵌入使强弱关系间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和模糊性。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弱关系”也明显显示出强关系的特性。人们出于各种目的游走于社交媒体平台,基于平台的开放性,用户可以轻松把控交往的时间和关系的强弱程度[30]。不少陌生网友之间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条件筛选等功能来寻求身体和情感层面的亲密关系,甚至发展成网恋。他们彼此间可能并不知道对方的样貌,仅仅依靠线上互动实现由完全陌生到亲密关系的转变。线下的社交行为也越来越多地从社交媒体“加微信”“扫一扫”等线上方式开始,曾经只是一面之缘的“陌生人”逐渐通过在朋友圈点赞、评论等数字化社交行为,变成可以合作办事、交流思想的“数字化熟人”。假如将1971年世界上第一份电子邮件的发出作为网络社交媒体的起点,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借助网络社交媒体的发展,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发展为“无主体熟人社会”[31]后,又飞速地迈入“数字化熟人社会”。
同样,传统意义上基于血缘和地缘进行高频率互动交往的强关系也逐渐瓦解。人们挣脱了时空的束缚,线下未建立联系的陌生人在线上平台认识后,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方式熟络起来,虚拟空间在此发挥着情感连接的功用,帮助人们实现数字关联、数字约束、数字互助及数字共享。例如,背井离乡去往都市打工的劳动者由于长年累月的异地生活,其日常生活运作逐渐异于“熟人社会”的逻辑,他们与外部世界建立起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人际网络。身体的不在场和“熟人社会”中情感体验的缺失,形构了一个边界流动而模糊的“无主体熟人社会”。而数字技术使这一社会中的关系结构再次发生变动。正如简·梵·迪克(Jan Van Dijk)所言,数字技术赋予个体灵活的生活方式和地理分散关系的纵横交错景象[32],重构了传统熟人社会基于血缘和地缘为载体的自然和社会边界。外出务工者可以通过加入“老乡群”或“工友群”,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取新奇、维系情感、结识朋友,从而建立起一种基于“地方感”的关系连接。但虚拟的数字化联结毕竟缺乏面对面互动,长时间流连在“云端”可能导致现实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更加疏远与冷漠。
(二)媒介依赖与社交倦怠
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全面渗透,使数字化时代的媒介不再仅仅是纯粹的信息提供者。人们对于手机社交软件等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加深,日常活动都与媒介密切关联并依靠这些媒介进行管理。依靠媒介进行的数字化生存成为习惯,各种网络平台、应用软件成为人们的“影子”,在处理工作生活事务时形影不离,逐渐描绘出人类一种全新的生活和交往方式。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群体性孤独》中写道:“人们通过移动设备把自己牢牢地拴在网络上,从而获得一种自我的新状态。”[33]
在个人、社会与媒介的互动中,如若没有新的路径出现,个人在使用和借助媒介进行合目的性表达和行动时,往往会对媒介产生依赖[34]。以手机为主的移动设备几乎承载了一个人包含身份信息、生物特征数据、银行卡信息等在内的众多个人数据,嵌入手机界面的各种软件程序逐渐对人们的社交乃至生活形成了全面的掌控,路径依赖也因而形成[35]。利用搜索引擎查找所需信息、通过气象软件了解未来天气、以第三方评分软件为标准选择要看的电影……媒介的存在是对人本身的延伸,媒介的丢失则是对人生存的截断,暂离网络的不安凸显出媒介依赖的常态。
人们一边享受着高连接性带来的方便,一边面临着过度连接的重负。地理界限与网络界限的消亡、公域与私域界限的模糊、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的不适感,都在催生着人们的倦怠和压迫感。刘易斯·芒福德在《历史的城市》中描绘的17世纪“家庭与工作场所的逐渐分离”仿佛当下数字化时代生存境遇的反写。今天家庭与工作场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共存,其后果是更多的工作时间侵占了个人时间。“钉钉”“腾讯会议”等即时办公软件被广泛应用后,个体即便在下班时间也可能处于工作状态,数字劳动的界限越发模糊。正如罗萨(Hartmut Rosa)所说,我们无法将所体验到的时间变成“我们自己的”时间[36]。
数字化时代的人们在完美地诠释着戈夫曼的“前后台”理论。为了营造良好的“人设”,人们通过朋友圈中精心修饰的图片与文案,来展现自身积极的形象,然而随着点赞、评论的减少以及来自现实的冷漠,人们发现其打造的“人设”并未受到太多的关注,从而厌倦了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泡沫里。人们日常被各种群聊、关注的公众号等非现实亲密关系所占据,过量的信息荷载和社交负担也催化着对数字化媒介的逃离。人们相聚“云端”的根本原因是寻求更高的社交效率,但实际上它只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非亲密关系,真实的社交生活需求和空间却被大幅挤压,如何克服媒介依赖与社交倦怠成为当下亟须思考的问题。
(三)时空重构与灵韵消散
时空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尺度。吉登斯认为,时空关系是社会系统的构成性特征,它既深嵌于最为稳定的社会生活中,也包含于最为极端或者最为激进的变化模式中[37]。在传统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时间和空间通常是不可分割的一对,人们很难跨越时空范畴交往和生活。数字化媒介时代,场景传播正式成为互动交往的加速器。
信息传播的时空关系在场景介入之后被重构,人际交往连接也被空前拓展。正如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中认为的那样:人们在空间中的行为表现和角色扮演在媒介的作用下发生了改变,电子媒介越来越多地介入空间结构划分的场景,以前传播中的种种限制,包括传播变量中的时间、空间和物理障碍也被轻松绕过[38]。网络空间在人们将原有的现实社会以比特形式复制和重塑时极速扩展,加之以微信、QQ、微博为主的社交媒体迅猛发展,使人与人之间仿佛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不断满足人们“缺席的在场”和“在场的缺席”的交往需求。同样,“在场”的意义也被重新构建和解读,人们能真正借助媒介载体,以自身的视角与身体去感受媒介内容,从而接近最大限度的“感同身受”[39]。例如,人们在2020年通过央视发起的以5G技术为支撑的移动终端在线直播,异地实时了解武汉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进度。
苏格拉底认为交流必须发生于灵魂与灵魂之间,交流双方必须同时亲身在场,在亲密的互动中进行,而这种互动必须专门适合于交流的参与者[40]。只有这种交流才能让信息在“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不丢失任何其原本的意义,原封不动地得到传达,从而最接近交流的本质。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提出,有形艺术的重要价值在于其“光韵”,而在机械复制时代,这种光韵消失了[41]。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艺术形式上,在社会关系中也同样适用,隔着屏幕的“在场”与真实生活场景中的“在场”是有明显区别的。数字化交往放弃了“此时此地”,将“共时”变成“历时”。在微信聊天中,即使面无表情,仍然可以对屏幕那端的人打出“哈哈哈哈”或发送笑脸表情包,这时,人们想要表达的内容语境坍塌(context collapse)了,交流似乎变成了一种“对空言说”。场景传播数字化的发展究竟是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是加速了交流本真的“灵韵”消散,值得深思。
四、结语
“任何新的媒介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生物裂变的过程,它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42],“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43]媒介不断演进至今天的数字化生存时代,技术通过其强大的逻辑给人类的生存、生活和信息传播带来了根本性变革,使人们能够拓展更广阔的交往领地、探索更多的实践空间以及实现更多样的交往体验。
人、信息、媒介和社会彼此融合共在,不断形塑现实生活世界,现实生活中主体间的交往重组为合目的性的数字化间接交往。数字化交往虽然已成为社会进程中无法忽视的维度,但伴随其中的强弱关系的转变、媒介依赖、交往倦怠和“灵韵”消散也使人们更难把控人际关系、社会交往以及自我的生存空间。怎样在技术遍在、信息浩如烟海的数字化交往中把握自身的主体性,坚守交往的初心和本真,构建理想的交往图景,一系列不确定性和问题值得身处这一时代的每个个体或群体思考。数字化已成为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全新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