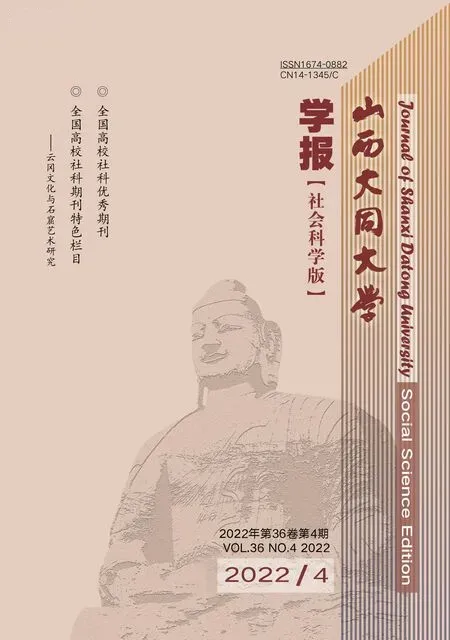《玉石人像》的审美现代性
2022-11-26牛晋玉李时学
牛晋玉,李时学
(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福建厦门 361000)
审美现代性冲破了工具理性的顽固藩篱和桎梏,带给社会现代性一种思想的纠偏和指正,它对社会现实和人的关怀,体现在解放人的自然生命,使人获得一种精神自由,这是审美现代性所特有的人文情怀和特殊功能。
19 世纪后期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在小说《玉石人像》中,借助审美感性和审美想象来超越现实生活,在回归自然与宗教救赎中呼唤人性与道德的复归,描绘了一个理想的艺术的审美乌托邦、一个诗意的人类栖居地。作者据守现代艺术的自律性,抗拒异化的社会现实对人类精神的限制,试图在物质文化中探寻一条人类社会的出路。
一、“人间乐园”在现代文明中失落
《玉石人像》是霍桑旅居意大利期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唯一一部以异域为背景的长篇著作,这个遥远、神秘的国度为这部罗曼史提供了一个诗意的仙境般的发生地。霍桑在小说中描述的梦幻贝尼山庄园、农牧神和水泽女仙的迷人传说、多纳泰罗的自然天性和欢乐的家族史等,令人无限遐想,充满了对自然的向往,带有典型的浪漫主义叙事特色。如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所说:“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1](P8)故而,浪漫主义迈出了导向审美现代主义的第一步,它“对进步与理性的批判导致了现代审美文化的诞生”。[2](P108)
霍桑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远离都市的贝尼山庄园,这座梦幻的贝尼山庄园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生活与古都罗马的文明社会截然不同。肯甬应多纳泰罗之邀到贝尼山庄园拜访,霍桑从肯甬这个社会人的视角描述了贝尼山庄园的生活景致,追溯了贝尼山家族定居于此的绝妙时代和幸福生活。在这片阿卡狄亚式的森林里,群山环绕中隐藏着一座幽静空阔的小山谷,其间流淌着汩汩清泉,周围青草满布、鲜花丛生,无花果树和葡萄树的藤蔓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垂下它们的果实。林间美景纷呈且野趣众多,多纳泰罗的族类时常在林中取乐,他们在灌木丛的阴凉中嬉戏,在芳香的葡萄园中酿酒,他们还有与自然界相通的本领,能够召唤天上飞禽、林中野兽,与各类花草树木交流。
这个异域的贝尼山庄园在霍桑的笔下化为一处“人间乐园”,阿卡狄亚式的田园和森林、幸福自由的乡村生活、纯朴善良的人民。作品中的人物身处其间能够忘却世俗的喧嚣和现实社会的种种异化,一切燥热或是忧怨都能够得到抚平和慰藉,从而获得一种心灵的平静。都市罗马中失落的道德、人性和温情,在贝尼山庄园中被重新寻回。
“在这一片阳光灿烂的林间空地周围,似乎再现了黄金时代,把人类从冰冷的礼仪中融化了,把他们从烦人的限制中解脱出来了,让他们在这种稚童式的嬉戏中混杂到一起,而鲜花则在他们的踩踏下欣欣向荣。”[3](P75)《玉石人像》通篇渗透着对人们曾经拥有、但已然逝去的黄金时代和人间乐园的惋惜,这种审美现代性观念蕴含了对前现代的田园牧歌的怀旧倾向和对社会现代性的种种反思批判。贝尼山庄园祥和欢乐的和谐氛围、纯朴真诚的人际关系,展现了人身处自然状态中的纯真和自由,具有审美理想的性质。作者对自然之景绘声绘色的描绘与社会的混浊丑恶形成了鲜明对照,作为对社会现代性的疏离和反叛,霍桑开拓了我们的审美视野,由此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他所期望的理想的生存状态。
二、自然与宗教回归
(一)自然与天性 18 世纪,现代都市逐渐成形,日夜轰鸣的蒸汽机、冒着浓烟高耸的烟囱、绵长黢黑的铁轨、行进缓慢的火车,现代因子在这些物质意象中躁动烧灼着,工业革命开始显示出它暴虐的一面,竭尽所能地摧毁和吞噬着自然。
卢梭厌恶文明社会的虚伪腐化、制度和权力等对人的束缚,厌恶人类愈来愈重的贪心和欲念,提出了“回归自然”的思想,认为人类应该返回自然寻找自由和德行。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卢梭引导读者回到远古时代,漫步于无边的森林和草地,追溯自然状态下原始人的生活,从身体素质、精神状态、语言、社会道德和怜悯心等方面与处于社会状态中的文明人相比较,展现了人原本的自然天性。卢梭认为,生活在原始状态中的自然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居所,生活简朴孤单,语言也互不相通,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无法互相接近、互相需要,但这样一个以天地为被、山川为枕、与日月同榻的生灵,他们体魄强壮、精力充沛且心灵平静、自由无羁,绝然不比在社会状态下生活宽裕舒适,却受无穷欲望煎熬的文明人悲惨。无论是《新爱洛伊丝》中让人流连忘返的日内瓦湖、风光旖旎的瓦莱山区,还是《爱弥儿》中幽雅僻静的蒙莫朗西森林,漫步林间呼吸新鲜空气、倾听枝上鸟鸣;抑或是《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圣皮埃尔岛的潺潺流水和布洛涅树林的迷人曲径,卢梭都在礼赞自然的美景和质朴的田园生活,执着地寻找着一方“人间乐土”。
卢梭被尊为“浪漫主义之父”。浪漫主义者继承了卢梭的思想基调,寄情自然,肯定与“理性”相对的“感性激情”,提倡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作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霍桑继承并延续了卢梭崇尚自然,推崇“自然人”的观念。在《玉石人像》中,作者详细探讨了多纳泰罗这个“自然之子”从自然性的外露到犯罪后自然性的消失,再到自然性回归的整个过程。
传说贝尼山的血脉源于远古时普拉克西泰尔斯的农牧神,一个在森林中土生土长的生灵。多纳泰罗作为贝尼山家族的嫡系子嗣,从小生活在欢乐的贝尼山庄园,嬉戏于托斯卡纳的林间,他的身上延续了祖先血缘中的自然天性,开朗善良、强悍活跃,时时富有激情。同时,多纳泰罗的身上又带有原始的野性和动物性,在理智和心灵上有所欠缺,行为有时野蛮狂暴,从来不受社会法律的约束。这一人物形象延续了古希腊原欲型的人本传统,与理性主义价值观相对立,具有反理性和崇尚自由的意义。
当多纳泰罗旅居古都罗马,爱上米莲,卷入她的恩怨,沾染了城市的邪恶、欲念和阴郁后,这个单纯少年的天性就被戴上了枷锁,渐渐腐化沉沦而误入歧途了。多纳泰罗在冲动之下将纠缠米莲的幽灵模特儿推下悬崖,日日惶恐苟活于罪孽的重压之下,先前在他身上生机勃勃的神气和纯朴乐天的个性全然消失不见,连他再度回到贝尼山庄园,想要低声呼唤曾经作为玩伴的林中生灵时,也没有任何生物愿意给予他回应。“它们拒绝了我!整个自然界都退避着我,在我面前发抖!”[3](P209)如今,多纳泰罗独特的自然性已然被这座庞大的文明古城吞蚀得所剩无几了。
以多纳泰罗为代表的未受文明污染的自然人的形象,隐含了作者对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失落的田园牧歌的感伤怀旧,对被理性和文明压抑而丢失的人类自然情感的痛惜,以及对纯真人性的渴慕和对感性欲望的追寻。“在我们今天,在生活中要求有目标和目的是铁的规律。这样的规律使我们都成了追求进步的一项复杂的计划的一部分,其结果只能使我们到达一个比我们出生时更冷酷、更可怕的境地。这样的规律还坚持要所有的人都把一些东西,加到只能使我们的后人比我们承担更沉重的思想和更过度的劳动的那一堆有用的东西之上。我们要一切都十全十美的决心过于强烈了,反倒使一切都乱了套。”[3](P200)
《玉石人像》中多纳泰罗犯下谋杀罪后逃离罗马,回到了他的故乡贝尼山庄园“疗伤”。几近自然状态的贝尼山庄园在这里被看作是某种精神境界的象征,它既可怡情,又可益智。在与自然的交融中,在宗教忏悔的修行中,多纳泰罗的头脑得到了奇妙的升华,不仅其天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得以复苏,更启迪了他的理智和良知,使他的思维和智性活跃起来。多纳泰罗对纯然天性的追寻以回归自然为起点,以超然于世俗的宗教理性为终点,人性、自然、神性达到高度统一,最终成长为一个兼有人性之美和深邃思想的人。
(二)宗教衰落与精神“荒原” 现代性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宗教的衰落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解体,使以宗教为中心模式的传统社会分化为各自独立自主的价值领域,摆脱了宗教神学话语权的控制。从宗教一体化的传统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就是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科学的、审美的和个人领域的分化自治的过程,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社会事务和文化事务相分离,现代科学、道德伦理和审美艺术不再以宗教教义为裁判服务宗教,而是依据自身的内在价值和合法性形成了自己的判断标准和依据。现代科学领域的独立、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启蒙运动宣扬的“理性”“自由”“平等”等叙事概念,消解并取代了宗教神学观念,使世界祛魅化。
然而,理性占据高地后,启蒙主义者所期冀的更高的秩序并没有出现,工具权威和目的功利对现世的重压,使人们狂热地追逐着尘世的物质欲望,而不再向往遥远的彼岸世界。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上帝的退隐、宗教的衰落造成了道德界限的模糊和瓦解,人类在精神上陷入迷茫和混乱,甚至一度在世界的无常中幻灭。宗教信仰体系的崩溃意味着人类精神信念和精神支柱的崩塌,人类的手中一无所有,普世的道德法律和价值标准的失去引起了人类对现存秩序的怀疑和幻灭。社会出现的信仰上的“断裂带”造成了人类内心的恐惧和焦虑,人类迫切需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体系和秩序来重估一切价值,挽救人类的道德危机。
几个世纪以来,从表现人的个体本位意识和自由意志、肯定人的自然原欲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到以神为本、宣扬忏悔苦行、禁欲修道的中世纪教会文学;从复兴古希腊文化、以人为本、肯定现世生活和人的个性自由、情感欲望的人文主义文学,到复兴古罗马文化、表现王权意识和政治热情的“带着镣铐跳舞”的新古典主义文学;从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理性尚未成熟的启蒙主义文学,到鼓吹非理性和反传统、强调唯美和个性自由的浪漫主义文学;从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取代上帝成为社会支配者、描写人性畸形和社会病态的现实主义文学,到“上帝死了”、理性支柱崩塌、非理性主义思潮泛滥的现代主义文学,人类一遍遍诚挚地踏足神圣的宗教殿堂,又一次次推倒和亵渎着神像,赤脚走在精神的“荒原”和废墟中摸索着一条出路,循环往复地企图为自己寻找一个精神的家园和依托。在《玉石人像》中,霍桑力图超越清教的局限和严苛,描绘了一种渴望中的普遍、宽容的宗教氛围,蕴含了作者回归宗教的意识。
多纳泰罗在犯了谋杀罪回到故乡贝尼山庄园后,投入了基督信仰的怀抱,时时在城堡中祈祷忏悔。而后,为了帮多纳泰罗摆脱自我封闭的状态,肯甬陪多纳泰罗出发旅行,旅途中所见的十字架、神龛、教堂等,使多纳泰罗臣服于救世主的永恒光辉,开启了赎罪的朝圣。对宗教信仰的膜拜与思考,使多纳泰罗的头脑和自身升华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高度,在寻找到精神的自我,和米莲享受了最后的愉快时光后,多纳泰罗坦然地自首入狱了。因传递了一个错误眼神的米莲,也在小说的最后跪拜于万神庙中心的穹顶之下,以求自己的祈祷可以直达天听。而目睹米莲和多纳泰罗犯罪被无辜卷入心灵折磨的希尔达则常常出入大教堂,或是沉浸于宗教建筑的宏大神圣,观察教徒祷告的画面,或是在各色圣坛和神龛之间徘徊寻求着救援,终于在与教士的谈话中卸下了灵魂的重负,找回了内心的平和。因为一桩谋杀罪而深陷人性分裂和心灵矛盾的多纳泰罗、米莲和希尔达三人,分别在宗教信仰的神光中,摆脱了灵魂的痛苦与折磨,找到了精神的自我和内心的宁静,最终完成了与自我的和解,灵魂得以升华。
霍桑回归宗教救赎并不意味着愚昧守旧和向神本主义的屈服让步。他肯定了宗教存在的必要性和为道德服务的目的,作为一种“绝对精神”,在解除了对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后,它应该回归精神信仰的领域,回归最原始的宽容博爱的宗教教义和宗教人本意识。通过步入深层心理和感性世界,使人更贴近精神和心灵的自我,在对善恶的思考、对无限与永恒的渴慕中,超脱一切有限性,进入“一个永恒真理、永恒宁静、永恒和平之领域”。[4](P1)
三、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的反叛
随着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货币经济的出现使得一切客观事物都被物化了,在效益原则和金钱利益面前任何东西都可以被量化和交换;社会组织形式的愈发完善以非人性化的可计算性为原则,排斥了一切非理性化的、人的情感成分。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日渐渗透和蔓延,形成了一个自我约束的刻板矩阵,遏制和压抑了人的主体性和个性发展,社会现代性的弊端逐渐暴露,并出现了危机和衰败之势。一方面,理性崇拜成为专制力量,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被强加在个人精神之上,以进步为宗旨、用科技来谋利,社会、个人之间贫富差距悬殊、阶层分化严重,拜金观念与功利主义思想靡然成风,投机者幻想着飞来好运、耽于炽热的金钱梦,野心家妄想着平步青天、登上权力的顶峰,人际纽带被冷漠和算计斩断,温情的面纱被金钱和欲望撕碎;另一方面,科学的力量不断壮大并向上帝发起攻击,上帝被驱逐后,人成为世界的主宰和自己的上帝,没有了天堂和地狱的禁忌,没有了上帝对世俗善恶的监督和统摄,传统的人伦道德和是非善恶观念便被颠倒混淆、发生蜕变,宗教的衰落造成了人自我的失调,使人对生命的价值和信仰的意义等问题产生了怀疑。如此,现代社会业已陷入了政治、经济和道德分裂的困境。
于是,现代性内部发生了裂变,作为对社会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审美现代性出现了。卡林奈斯库[2]指出现代性处于一个复杂的张力结构中,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是现代性自身的内部张力问题,两者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工具理性作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人的思想和行为被无意识的支配和操纵,现代性无可避免地陷入片面发展。物质发展的绝对速度导致了人精神和道德层面的断裂,社会现代性表现在有形物质层面的金钱、权利、名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追逐的对象,但精神层面出现的许多问题似乎逃逸和被忽视了,人类从原始社会一路进化到现在,器物和科技的成熟先进与精神和心灵的倒退堕落渐相背离。而审美现代性作为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它迥异于现代社会的主导范式,厌恶现代社会冰冷的工具理性和世俗的现代价值观。作为对社会现代性的否定和超越,审美现代性具有内在的反思性,它揭示时代的裂缝和扭曲,控诉现代社会生存状况,肩负着批判现存社会秩序的使命。
审美现代性作为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摆脱了传统艺术对社会权威的附属地位,与社会现代性相对立,呈现出反叛性和颠覆性。作为一种独特的表意实践活动,其目的是通过文学活动参与社会对话,对隐含的符号、象征、语言和意义进行交流、提供解释,批评和塑造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它超越了美学和审美的艺术局限性,参与到社会文化领域和真理的讨论中来,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构想的艺术世界绝不只是关乎美的艺术和想象,而是带有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和思考。“在生活的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发展下,艺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自觉把握到的有独立价值的世界。不论怎么来解释,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5](P342)
霍桑构筑的“贝尼山庄园”作为一种理想的审美的生存家园,正是寄托了一种艺术救赎的渴望,明媚闪烁的阳光和醇香的美酒、清澈的溪流和绿叶上跳跃的水珠、郁郁葱葱的森林和四处漫步的小生灵、天然的花园和袭人的花香等意象充满了自然之美和感性情调。诚然,在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对抗中,“自然”作为一种审美的理想乌托邦,并不足以支撑与工具理性相抗衡,这种审美超越甚至显露出些许逃避的意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彼此对立,使道德、人性和爱被重新呼唤。在现代社会的精神“荒原”中,宗教信仰的道德意味一再复现,因而在《玉石人像》的最后,霍桑回归了宗教救赎这个美国精神根深蒂固的思想支柱,回归纯粹的精神世界和一切的开端,在宗教中寻找“最后的中心点”。[4](P2)
《玉石人像》中以贝尼山庄园为代表的田园理想和以文明古都罗马为代表的城市意象作为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表征,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隐喻了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的反叛和颠覆。霍桑以怀疑的态度审视理性社会的核心价值和所谓的物质进步的神话,质疑现代性宏大叙事下人性的基础,在现代文明之外寻找一条审美救赎之路,在审美话语中呼唤一个失落的自我和家园。他以自然和宗教为媒介,补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撕裂,向外寻求一个诗意的人类栖居地、向内返归精神上的朝圣,在审美想象中重建道德意义,审美期望和道德理想由此构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世界。
四、结语
现代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上的一统性,以个体的差异为代价,在这个庞大资本机器的统治下,所有事物的发展维持着表象上的井然秩序,所有的生命和时间都被明码标价成待价而沽的商品。现代性的浪潮推动着僵化的个体奔向一个模糊不明的、我们幻想的更优越的未来和文明,那些神圣的信仰、古老的传统、本我的需求被通通抹杀。个体被迫裹挟在现代性的潮流中,这股潮流既是社会的助推器,也是人格的清除键,把我们越来越远的推离最初的圣堂和海岸线。
戈林曾评论道:“霍桑在他的小说中写的是他前面的时代,也是他的时代,而我们今天读来发现他也写了我们的时代。”[6](P2116)霍桑在作品中对美国文化和精神、人类生存状况和人性的探讨,不仅在其所在的时代具有深刻的意义,在若干年后的今天仍显示出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和恒久的活力。霍桑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虽隔着民族和时空的界限,但我们却存在着诸多相似的社会问题: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对家园的吞噬、现代性对人的主体性的抹杀、名利欲望对情感和道德的腐蚀等等。重温霍桑的作品,是对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感性结构的检视,也是对当前时代发展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