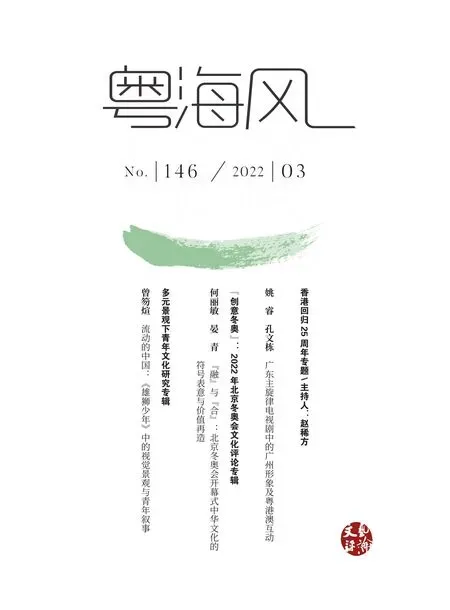《千万与春住》:器物迷恋、日常殿宇与都市社会的价值建构
2022-11-26王怀昭等
文/王怀昭等
引 言
王怀昭(主持人,中山大学在站博士后):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张欣的近作《千万与春住》。在百舸争流、大风大浪的20世纪90年代,张欣、张梅、黄爱东西几位女作家,以小说、散文等文学体裁,将广州这座城市的俗世烟火、喜剧悲情描画得活色生香。于此,以广州为创作背景的城市文学在当代城市文学版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张欣创作于90年代的小说,比如《伴你到黎明》《爱又如何》《掘金时代》等探讨的是市场经济崛起后,都市男女面临的失序的生活迷惘、传统价值裂变后人遭遇的精神迷失。《千万与春住》延续这一小说主题,并进一步深化,对当下中国转型时期商品经济与消费主义形塑市民身份认同,影响市民德行和价值体系的问题作了审美化的反映。从这一点来说,小说为我们理解中国当代都市精神、特别是广州城市精神提供了一个照见的窗口。也促使我们思考市民精神价值体系的建构需要何种日常生活力量。
一、器物迷恋与市民身份认同
刘可(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我觉得这本书相当有价值的部分来自当代都市日常生活的书写。小说以戏剧化、充满张力的故事情节,以及大量的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包括但不限于人物的饮食、衣着、人际关系、职场来往),暗示了社会生活中阶层、教育和医疗问题,涵括了当代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敏锐捕捉到时代观念和人们身心状态的变化,比如对男女关系的讨论(滕纳蜜对薛一峰没有感情后,还能靠着曾经长久相处积累下来的默契,陪伴着度过许多个艰难的日子),当代女性对于身体与欲望的态度(讨论“跳蛋”),女性审美的变化(对待化妆、穿搭、奢侈品、消费的态度),这些都显示出当代小说少有的细腻与烟火气。这种关于当代都市世俗生活细节与情感经验的书写,回到肉身、回到感性、回到生活的温热触感与细腻肌理,无疑是对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的美学价值乃至文化意义的肯定。并且,作者以广州这座城市为主要背景展开故事情节,充分展现了广州文化的世俗性特征,为当代城市文学版图补上了名为广州的一角。
张诗瑶(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对我来说,食物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我觉得刘可提到的“回到肉身,回到感性,回到生活温热触感”,其关键在于“回到食物”。都说“食在广州”,这部带有广州地域特色的作品频频提及食物。食物不仅是人类的群体性行为,还与文化相结合,由于人类群体共同生活,食物的处理、加工上也就逐渐产生共性。作为人类日常生活中最频繁的实践行为,食物以及饮食活动本身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饮食不仅在物质层面上“养育”了“一方人”,也形塑了地方性口味,并以饮食态度、观念、习俗、记忆等形式,将关于“吃”的饮食文化烙印在个体身上。食物常常和家庭、情感、文化绑定在一起,是享受也是慰藉。滕纳蜜、薛一峰二人赶上了财富积累的快车,凭借运气和努力叩响了“上流社会”的大门,名牌、房产、消费能力等等都在显示着二人似乎已经进入了新的阶层,但是这种“进入”并不等于“适应”,此时,来自食物的记忆成为缓解焦虑的“良药”,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关键纽带。
滕纳蜜只在无人处食用中意的红油猪耳,在外人面前喝的是威士忌、贵腐、香槟中的大地之魂,强迫自己接触上流社会常吃的食物以便尽快融入陌生世界,她需要也乐于通过大啖西餐的方式来无言地宣告新的社会身份。滕纳蜜把食物比作自己的三千后宫,通过囤积大量食物来提高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力,从而在陌生的环境中确证自我的身份。她赋予红油猪耳联系过去及现在自我的特殊意义,食物指代性便得以体现。通过饮食习惯与地方产生更紧密的联系,过去的记忆得到激发,这种联系便增强了身份认同。
薛一峰喜爱猪肚、猪肠,但却深觉自己处于鄙视链最终端。可见具体食物与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形成了清晰的对应关系。如果说吃什么是区分阶层的重要依据,那么餐桌礼仪、相近的饮食习惯是确立双方文化身份一致的重要标准,薛一峰尽管在财富积累方面进入了新的阶层,但是“异乡人”的耻感与自卑却无法抹去。他把一部分的缺失转移到了食物上,将其当作“亲密爱人”,由于经常和政府体制打交道,薛一峰打点上下,待人妥帖,做事周全,努力获得这类群体的认可。小说中,他独自享受吃饭的时刻,熟悉的饮食场地给他提供了稳定的就餐环境,维持了稳定的心理预期,虽然意外不知何时降临,但眼前的食物是实实在在可控的。简言之,滕纳蜜、薛一峰运用不同的饮食态度和策略来建构自我的社会身份。
宫铭杉(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张欣借故事人物形象的吃穿用度传达出被现代都市文明浸染的思维方式和诸多生活观念,向我们提出了新问题,即当消费主义不断侵袭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时,我们该如何去面对人性的善恶,认识人与人的关系。
除了诗瑶所说的食物对人的身份和幸福感的塑造作用,代表幸福的“器物”也是纳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她建构自身社会身份,判断他人生存状态的“符号”。即使在家中待客,纳蜜也要穿上最合适的“战袍”,喷上清冷、疏离味道的香水向前夫证实自己过得很好。她惯用挑剔的眼光打量着身边人的着装。在校花妈妈准备前往小桑君上班的富田菊日料店时,纳蜜带着鄙夷的目光评价着校花妈妈的衣着。“闪光提花织锦面料的连衣裙,图案是蜻蜓伫立在百合花上,蓝粉黄为主色用金线编排在一起”[1],她将重点放在校花妈妈的衣着质地和审美品位上,不由得开始怀念当年在文化局工作的校花妈妈以黑白为主端庄典雅的衣着。可以说,前后两段生活时期的不同着装品位区分出了纳蜜对母亲的基本认知,年轻幸福生活时的得体内敛,与遭遇人生变故后的喧腾廉价。
更可悲的是,这些器物也是纳蜜的情感寄托,缓解了她内心的孤寂。纳蜜有一个房间,装满了能够慰藉她的中国胃以及失落灵魂的食物。当她知道自己儿子的下落后,她尝试把一些储藏间的食物送给了打扫卫生的阿姨。丰富的“器物”给纳蜜的生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后遗症”。在小说中,除了“器物”,纳蜜的内心并没有更稳固的情感寄托。同时,“道德”“情感”取代了器物等外在物质层面,成为她难以企及的彼岸。“器物”虽承载着纳蜜的生存价值,却不能让她获得充沛丰盈的精神力量,填补道德良知的缺口,实现心灵救赎。小说中诸如此类的“器物”描写不仅是都市生活的重要表征,同时也体现了中产阶层的审美品位和生活态度,彰显了他们对自身社会身份的认知。经由消费主义改造过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观念,使城市中产阶层逐渐固化了新的审美化的生活方式和心灵体验,并最终建构了独特的文化心理。所以,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纳蜜对器物着迷、盲目堆砌的心理具有难以忽略的典型性。她的存在证实了消费主义对当代社会以及现代城市文明的影响,已经逐渐从物质层面渗透到精神层面。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看见张欣小说的另一重价值——以器物为代表的都市文化内涵,以及器物对于人物形象建构的有力支撑。
总体而言,《千万与春住》通过对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反思,审视都市生活中人性的复杂性,以极具戏剧性的故事深入探究看似坚固的社会道德伦理的松动与转变,并最终指向化解都市中产阶层心灵困境、实现精神救赎的仁善与慈悲。
二、在日常殿宇中汲取生活力量的可能
顾萌萌(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我想接着铭杉关于精神救赎的发言谈谈我的看法。在我看来,这部广州书写的小说有诸多都市的故事元素:职业女性、三角恋、闺蜜反目、调换孩子、拐卖儿童、出轨离婚等等,张欣显然没想打造多么富有故事性的情节,而是侧重挖掘人在命运偶然性中的生存状态。小说写出了人生在世,想做好人却做不成的人最痛苦;写出了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真实人性;写出了人们在规则和潜规则之间行走,在利益、体面和良知的计算中做抉择的行为方式。正如作者所言:“写小说,其中的人物不必那么纯粹。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生活中极少有纯粹的人。”[2]
不同于一般主人公的良好形象,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一反常态,刻画了一位恶毒的主人公滕纳蜜。她因为嫉妒闺蜜夏语冰而调包了孩子,之后还弄丢了孩子,并且始终不认错,连母亲都对她说:“滕纳蜜,你是真坏。”[3]但就是这样一个刻薄的女人,却让读者不能坦然地去厌恶或者憎恨。可能因为在小说中,滕纳蜜最先出场,读者会先入为主地把她当作主角,尽管她恶毒,但读者也会对她产生理解和怜悯,从而减少了厌恶、痛恨之情。如果换作小配角,也许人物形象就会立马萎缩到好人/坏人的评价标准上了。张欣认为,小说里的人物,只要被偏爱,就会成为一个失败的标识。她在自序中所强调的“日常”,也包括了“庸常之人”,她要将人的异化状态从各种理念态度中抽出,在幽暗曲折的人心中给予人物生活的力量。当然,这对于写作是有难度的,张欣成功地给予了滕纳蜜“庸常之人”的力量。滕纳蜜知道自己有罪,但是直到故事的最后她也没有认罪,因为如果她承认了自己的罪,就等于抛弃了自己,叙事便可能会落入“塑造典型”的窠臼。故事的最后,小桑君来到了滕纳蜜家,并对她说出“我从来也没有怪罪过你”。[4]在网友的书评中,一些读者倾向于不原谅滕纳蜜,觉得这个结局对于她过于美好和轻松了。也许这正是作者想要刻画的主题,对人物的悲悯让她写出: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与春住。对于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在一种超脱世俗的悲悯情怀下,是恨不起来的。唯有善念才是救赎。
曾笏煊(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我想就萌萌师姐发言中关于日常生活的观点做一下补充。日常是张欣小说的关键词:“也只有日常才能够流传(不
是传世,远到不了那一步),它是思想情感的肉身。”[5]因此张欣借助书写日常生活中庸常之人的生命状态。另一方面,张欣认为日常不等于平淡,强调故事要有传奇色彩,这样“才能吸引大家,才会让人觉得好看,
否则就和隔壁大爷家发生的故事没什么差别了”,[6]这意味着日常并不等同于生活的“原生态”,也不能是“隔壁大爷家”的生活,而是作家有意识、有选择性的剪裁和建构,并带有较为明确的商业目的。《千万与春住》延续着张爱玲“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的都市小说传统,侧重描写日常生活中常中见奇的面向。借助换子、失子等传奇的故事情节,张欣试图抓住都市中产阶级患得患失的精神症结和对人生变故的惶惑无力。相比男女情爱的复杂纠缠和两代人亲情的扑朔迷离,日常工作和一日三餐自然成了人生安稳的底子,也是现代人似乎能抓住的唯一恒常。而那些无法释怀的忧伤与无奈也只能借助于不可知的未来,“用时间来慢慢消化,慢慢解决”。[7]在张欣看来,日常是通向《红楼梦》等杰作的路径,那些琐碎的人间烟火也正是小说的真实性和深刻性得以依附的殿宇。
潘旭科(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我顺着前面两位同学的观点继续讲。在我看来,《千万与春住》是一部以传奇故事写日常生活的小说,小说情节可谓曲折离奇,是一个现代都市中“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但作者却认为日常才是精神的殿宇,意在写出凡间烟火背后的江河日月烟波浩荡。整体而言,小说写出了生活之常、情感之常、人性之常:书中人物都经历了一些变故,但生活仍旧在继续,并没有因为谁而发生改变;女性之间既有相互扶持又有相互竞争的友情,异性之间不同类型的情爱,代际之间的母爱、父爱在小说中均有呈现;滕纳蜜对于夏语冰的妒忌,周经纬深受现代文明影响却依然无法摆脱传统观念、仍有不敢直面问题的软弱,夏语冰、薛一峰不辞辛苦帮邓小芬治病时的善良等都是真实的人性体现。
小说展现了作者对于当今城市生活与人际关系的精准把握,但小说对于现实的描摹和对于人性的书写仍有一些遗憾之处。书写人性的堕落与救赎离不开对于现实的宏观认知与详细描摹,但小说中的传奇故事尚有一些叙事上的破绽,诸如滕纳蜜认为自己是犯人的女儿,天生有罪的想法缺乏更为详细的描写。
《千万与春住》在写作上的各种症候或许反映了当下的时代真相,比如滕纳蜜为了让自己的儿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偷偷与夏语冰的儿子做了互换;夏语冰和薛一峰通过人际网络帮助邓小芬联系医生的故事已经触及了像邓小芬这样的人看病难的问题;来自农村的邓小芬为自己生病拖累他人而深感愧疚自责,也映衬出时代的罪与罚,等等。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现实变得愈发难以把握也愈发难以改变,文本对于都市文明的探索,其光彩与不足也彰显出了都市文学的新的可能性。
三、怨恨还是救赎?中国转型时期都市社会的价值建构
罗涵诣(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前面几位同门对张欣小说中关于日常生活的书写的解读基本上围绕小说的内容层面,我想就小说的形式说说看法。首先,独特的日常生活描写彰示出《千万与春住》独特的都市感。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张欣说“日常即殿宇”,在小说中也能看出张欣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她的细致体现在她所描绘的这些日常当中——房间的布置、食物的制作过程、音乐的插入等等,可以看出这些细节是有作者的深究在其中的,就像她在自序中说到的那样,如果写错了,就会有一种疏离感。其次,独特的城乡结构模式是小说独特都市感的另一个体现。小说解构了传统都市小说与乡土小说中城市/农村二元的对立。在许多小说文本中,乡村常常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出现,但张欣则更侧重借用城乡这个平台去展现人物性格,作家似乎注意到在新的都市环境下人的自我、人和人之间都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在描绘都市人时,张欣在他们身上赋予了更复杂的意义。滕纳蜜怀有嫉妒、憎恨之心,但她面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依旧有负罪感;薛一峰是官场上的能手,有追慕美女香车的一面,但他对夏语冰的帮助不可忽视。而当代表城市文明的人物介入时,处在乡村当中的人物拥有了自主选择权:比如,面对夏语冰抛来的橄榄枝,王大壮不为所动,依旧留在乡村开拖拉机等。
小说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夏语冰,作者将她置于罪与忏悔的叙述逻辑和城乡互动的空间转换之间。由于父亲的影响,滕纳蜜认为自己是生而有罪、罪无可赦的人,将孩子调包以后,她的负罪感更加强烈。但她的忏悔都停留在了形式层面上——给小桑君买下一家店、在校花妈妈死后为她做法事等,她没有认清罪的成因而将罪归咎于她是贪污犯的女儿,即天生有罪;校花妈妈的负罪感来源于女儿滕纳蜜的所作所为,她也是第一个找到夏语冰并道歉的人;薛一峰的罪来自于交换孩子,但是他通过帮助夏语冰的方式完成了赎罪;被夏语冰照料的邓小芬,其负罪感除了来源于“病人除了病,还多一重犯罪感”的亏欠,还有王大壮因为她的恩情不和夏语冰相认,于是她在手术前交代后事,让王大壮以后要听从夏语冰的安排。可以看到,罪与忏悔的描写不仅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还让始终没有负罪感的夏语冰更加凸出。此外,夏语冰也多次从都市进入乡村,使都市与乡村彼此建立起对话、交流的联系。而就夏语冰出身优渥富足的家庭,经历过私奔,也遭遇了朋友背叛、丈夫出轨等挫折,在生活的磨难中她依然能够保持自我的尊严与教养。作者在她身上所赋予的是理想的人物品格。
杨淑芬(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我非常认同涵诣说的,在纵向的城乡空间架构中,人性的罪与悔表露无遗,而在横向上,小说通过女性、婚姻关系和社会生活呈现了人性的贪念与自私,由此追踪都市人在物欲生活中的自我救赎,这构成了文本的精神内核。在这种自我救赎中,作者首先解构了一种金钱主义的都市生活,与此同时,又建构了另一种具有内在品格的精英生活。作者无处不在地揭穿都市人华丽生活背后的孤独、虚假和脆弱,小到滕纳蜜深夜必喝的二锅头和必吃的红油猪耳,平常到都市大街小巷无处不在的小资格调的各种艺术餐厅、高级场所,细化到主要人物的都市性格——梁少武的市侩和恋物,薛一峰的八面玲珑,滕纳蜜的极致物化和金钱主义。
在小说第十六章,校花妈妈为迎接亲外孙所做的准备其实是非常形式化的——她开始打扮起来,而滕纳蜜则毫不掩饰对母亲低俗穿衣品位的嫌弃。并且,在小说文本里,除了摔倒住院时出现过纳蜜母亲的全名,其他都是用“校花妈妈”来指代。可见,“周文芳”在小说里没有价值和意义,“校花妈妈”才是有意义的。“校花”所代表美丽的外表条件是周文芳最大的资产,作为标准的花瓶,她也呈现了美丽有余但思虑不周的人生历程。这种将外在的装饰看作个人资产和品质的重要标准的价值观念,除了周文芳,还有薛一峰和滕纳蜜。
正是通过类似的描述,作者讽刺并解构了都市人和都市生活,但是同时,她又不可避免地建构了另一种都市生活。小说展现了都市人在繁重的现实生活危机中,一种关于内外的自我救赎。在作者的表述里,男性很轻易地从苦难中抽身,而女性却总是作为善后的一方。面对换子、丢子、认子的人生裂变,周经纬及时抽身;薛一峰卖力赎罪,为的是从愧疚感中抽离,重建家庭。滕纳蜜不断在情感错失和伦理失序上进行自我修复,夏语冰在现实生活变故中依然坚持对内心进行审视、疗救、重构。
作者解构了滕纳蜜和薛一峰等人的世俗的都市精神,那种外在精致而内里肮脏的世俗精神并不足以对抗尘世,甚至在危机面前不堪一击。因而,作者提出了一种她更为欣赏的精神,这种精神性的内在营构具体表现为一些性格特点和人格品质:他们具有内在的精神性力量,是教养、尊严、勇气建构了他们处事待物的方式和力量。所以我们可以在出身条件和生活境遇完全迥异的两个人物(夏语冰和邓小芬)身上,看到了相近的教养和精神——在面对人生的挫折、困难和磨难时,即便难免经受迷乱、痛苦和怅然,但是依然怀有善意,拥有自我救赎和人性慈悲的力量。这种尊严和胸怀显然影响了下一代,在王大壮和小桑君身上都看到慈悲的曙光。这是一种现代人在物欲生活中实现自我救赎和他者救赎的力量,也正是在这种外在的人物塑造和内在的精神建构中,小说闪耀着文学的价值光芒。
王怀昭(中山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理解文本的方法除了深入文本内部加以细读,还可以通过文本之间的对读。联系张欣在20世纪90年代写的小说,也许对《千万与春住》的内在精神,会有更准确的认识。张欣的《伴你到黎明》,表现的看似是男女情感生变导致的女性职业转向,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女性面对不确定的现代社会所产生的生命转变。而同时期的另一篇小说《爱又如何》,则叙述职业女性可馨与丈夫沈伟,婚后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磨难,诸如工作单位派系斗争、孩子生病、长辈病倒,他们的爱与温情在这当中逐渐被消磨殆尽,原本相爱和谐的两个人后来面对彼此,只剩下疲惫和沉默。
在2019年出版的小说《千万与春住》中,张欣延续了她在20世纪90年代所表现的创作主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在书写现代社会中的男女所面临的精神失怙困境时,把笔触指向现代人的内心隐恶,并提出人在犯罪之后是否能自我救赎的问题。不过,张欣并没有继续往前探索,而是表达了她的人性观:承认自己内心的恶,或者不原谅他人的恶,本身就是一种诚实。这种诚实,是人与他人,人与世界和解的基础。滕纳蜜在把自己的孩子换成闺密的孩子并被送到美国,却又把闺密的孩子弄丢之后,她其实是被自己的罪咎感所捆绑的,多年的单身生活,她自我放弃,生活毫无秩序,这些也许是她自我惩罚的方式。因此多年后在找到闺密的孩子之后,她才会崩溃大哭,即使这当中有矫饰的成分。面对自己的过错她没有道歉,也拒绝道歉,乍看之下这个人物实在不可爱,但是却不由得让人产生怜悯。如果把张欣的这三篇小说进行对读,会发现三者之间是有内在的主题联系的,其内在精神互相呼应。三篇小说都表达了:在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原本忠贞、正直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冲击,并逐渐变得不堪一击。它们的价值也受到人们内心的怀疑。
其实,张欣力图表达的小说内在精神,恰恰契合了舍勒对于现代性的判断。舍勒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怨恨心态,与韦伯所提到的资本家的“实干精神”相比,“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中迈步向前的,并不是实干精神,不是资本主义中的英雄成分,不是‘具有王者气度的商人’和组织者,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他们渴求最安稳的生活,渴求能够预测他们那充满惊惧的生活,他们构成了松巴特恰到好处地描绘的新的市民德行和价值体系。”[8]
陈天(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我认为小说对于不同阶层整体形象的建构,包括德行、价值体系等等,背后隐藏着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千万与春住》中的滕纳蜜、薛一峰、夏语冰同属于中产阶级,不同的是,滕纳蜜和薛一峰是从底层一路打拼上来、实现了阶层跃升的富裕的中产阶级。而夏语冰因着家庭出身,多少有天生贵族的意思。因而,三人形象的差异和对比,实际上不仅仅只是制造了一种戏剧张力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所隐藏的道德评价体系。最明显的例子是,当王大壮请律师来广州索要抚养费的时候,这三名当事人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反应。滕纳蜜和薛一峰夫妇觉得这是王大壮一家人见利忘义敲诈勒索,还说“乡下人就是这个鬼样子,又薄情又贪财”,而夏语冰却凭着一位母亲的直觉认为肯定是王大壮遇到了什么难处,然后不遗余力地帮助王大壮。这一点让薛一峰感到非常羞愧,认为夏语冰使得他和滕纳蜜相形见绌,并且还有一种被良心和良知审判的感觉。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不仅是一个嘲笑中产阶级贪婪虚伪的讽刺剧,更重要的是,它背后隐藏着一种复杂的话语行为,这个故事所呈现的道德标准,在叙事中所显露的价值判断,是否真的具有不证自明的普适性?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各自走过不同的历史遭际,而当下又面对不同的发展困境,所以我总是有点怀疑这种过于单一的视角,过于直白的爱恨。
就像《千万与春住》这本书所呈现的,小说中主要形象的生产,本质上都是以这些人物的出生环境、家庭背景以及童年经历为基础展开的一系列想象,因此无论是天生贵族的夏语冰和还是属于进取的富裕中产阶级的滕纳蜜,表面上看都有相似的风采,但是她们的过去却如影随形地附着在她们的内心世界。不过在《千万与春住》中,真正的原罪不是家境的贫穷和出身的低微,而是不安于现状。就像邓小芬一家,虽然相对贫穷,但是在小说中,这一家人所显露的都是善良、无私、热情、淳朴的一面,他们最大的特点在于知足常乐,不贪婪。这就和一直寻求阶层跃升的滕纳蜜和薛一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薛一峰滕纳蜜夫妇非常进取,可以说是从底层一路爬升上来的,并且,当纳蜜下定决心要摆脱贫困境地的那一刻起,也就是当她决定送走自己的儿子,而把夏语冰的儿子留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她似乎就开始了她的堕落之旅。所以,这其实是在暗示,阶层的跃升意味着必然要付出道德的代价,于是,知足成为了这部小说中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在中国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总有一个群体在文化场域中受到压抑,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农民企业家是勤劳致富的代表,但到了90年代,他们就成为庸俗粗野的土大款、暴发户的代名词。充满进取心和奋斗精神的中产阶级曾经也是励志的典型,但是如今他们这种打破阶级壁垒的努力,却被视为一种必然导致道德缺失的贪婪。其实,我们很难说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转变,只能说知识是一种权力,在利用这种权力建构一种道德规范和人性标准的时候,是有一种内在的视角和立场存在的,由此而诞生的规范和标准是否真的像它自身所显示的那样具有普适性,我们应对此保持审慎的怀疑。
郭冰茹(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欣善于处理都市题材,尤其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折射下的都市景观,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张欣的一系列作品,比如《掘金时代》《首席》,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千万与春住》,都细腻地呈现了小人物在欲望都市中的困境、挣扎、奋斗和守候。她的这些作品携带着广州的独特气息,也兼具都市文学的共性特征。我想从广州和城市文学的书写脉络谈谈《千万与春住》。
首先,关于广州的城市表达。熟悉广州历史的同学都知道十三行,这是清代“一口通商”时期唯一官方指定的对外贸易牙行。广州比上海开埠通商早了近一百年的时间,有着丰厚的商贸文化积淀。同时广州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最早进入市场化经济体系的城市之一,直到现在也依然保持着一线城市的位置。不过,在20世纪中国“城市文学”的版图中,我们很难像讨论“京派”或“海派”那样讨论“粤派”文学,也很难像讨论张爱玲、王安忆之于上海,或者方方、池莉之于武汉那样清晰地描绘出张欣之于广州的书写位置。究其原因,我想除了一些客观因素之外,大体与广州这个城市的文化性格有关。黄天骥老师用“及第粥”来形容广府文化,就是驳杂且交融。从包容性和有活力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是优势,但对于写作者要呈现城市个性,要凸显城市品格而言,难度就非常大,他必须得在“及第粥”的各种食材中有所取舍,并且以个人经验去贴近。或许这是文学创作很难形成风格相对统一的“粤派”或者“广州书写”的原因,也是张欣的都市书写很难被清晰指认为“广州制造”的原因。
其次,关于城市文学。说到“城市文学”,我们可以概括出几个关键词,比如:革命,这源于左翼文学的传统,从茅盾的《子夜》到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器物,这与城市物质消费的属性紧密相关,十里洋场的广告牌、百货公司、电影院、咖啡馆和跳舞场里的灯红酒绿,成为“海派”小说中炫目的都市风景线;人情,则是建立在器物上的人际关系,情人间的耳鬓厮磨,亲人间的扶助或反目,朋友间的亲善或算计,对手间的倾轧或同情,从《海上花列传》、张爱玲的“传奇”到《长恨歌》《繁花》,古典世情小说中的声色犬马、世态人情在20世纪的城市文学中有了鲜活的表达。说到这儿,我们不难发现关于上海的书写几乎成为“城市文学”的基本框架,定义了“城市文学”的写作方式。在这些文学表达中,凸显其城市特征的不是地标性建筑、方言词汇、地方性知识,至少不全是。而是浸透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性,这在书写革命的《子夜》《上海的早晨》中也不例外。当我们将上海作为一种方法来考察城市文学的创作时,才有可能更清楚地把握城市文学的整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个案分析。
最后,关于《千万与春住》的写作特色。如果我们将《千万与春住》放置在城市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整体框架中来考察,会发现张欣的城市书写也是基于对日常生活的精细描摹。她在这部作品的自序中说“日常即殿宇”,讲到最不起眼的日常如何写得出彩最考验作家的功力,因此这部作品中张欣是有意识地在日常生活书写上下功夫,主人公吃什么、穿什么、见什么人、去什么地方,笔笔精细,透出都市日常的丰厚质感,进而也呈现出城市文学世俗性的文化内核。但是,如何切入这种世俗性以凸显广州的城市特点,却是张欣的独特之处。我觉得这种独特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各种街头小吃、大排档、茶楼餐馆写出“食在广州”的城市氛围。当然食物并不仅仅是能吃的东西,诗瑶已经做过仔细的分析,我不赘述;二是比起上海书写精于人与人之间的弄堂政治,张欣更关注“物”对人的异化。城市文学总是以欲望作为基本的叙事动力,张欣抓住了广州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侵蚀这一特征,写出人在物欲面前的失魂落魄、挣扎纠结或是诗性坚守。正如张欣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我更关心的还是人,人心和人性”。我想,这是《千万与春住》体现出的文本意义,也是张欣之于城市文学或者广州书写的价值。
注释:
[1]张欣:《千万与春住》,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195页。
[2]张欣:《附体,而非无限靠近(创作谈)》,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0205746/,2022年4月11日。
[3]同[1],第651页。
[4]同[1],第246页。
[5]同[1],第3页。
[6]张欣:《“通俗还是深沉?我内心其实一直挺矛盾的”》,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10-13/1907689.shtml,2022年4月11日。
[7]同[1],第100页。
[8][德]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刘小枫编,罗悌伦等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