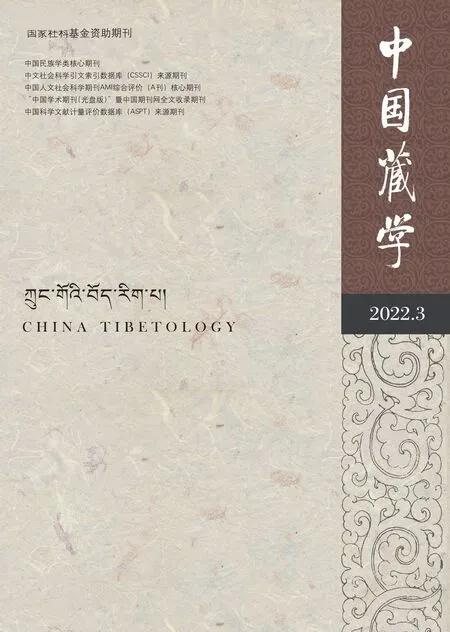“话说”西藏:对叙述主体的传播观想①
2022-11-25泽玉
泽 玉
皮特·夏普在评述西藏时说:“每一代作家均借助他们对西藏的设计(和想象)将无意识化为有意识,表露他们各自最热切关注、未遂的心愿,以及恐惧、希望等等。”②沈卫荣:《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导论”第3页。事实上,借传播表达“观想”中的西藏并不是作家的专属行为。西藏神秘的轮回转世观、复杂多样的婚姻家庭结构、隐秘的丧俗等,嵌刻在社会肌理中的文化、生活形态总被不同的群体读解后化为不同形态的话语被传播。传播技术迭代更是催生了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用文字、用镜头或用声音“话说”着他们感悟而得的西藏,带着个人“观想”印记的西藏议题在传播中被固化或被演绎。假媒介之手传播的“话说”必然会涉及谁来说——怎么说——通过何种渠道来说、话说者有多少“粉丝”等问题,在这样的叙事中,“话语就是权力”得到深刻体现,①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17页。在建构“话语”的过程中,建构者的主体身份、建构的内容、建构的渠道都反映着意识形态、社会权力,也形成了被建构对象的社会形象和生活情态。
从微观层面来说,话语是个体使用语言的表现,但它的力量远超人们的想象,诺曼·费尔克拉夫对此颇有感悟地指出:“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②[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35页。西藏远在雪山之巅,历史上受限于环境和交通,与世界的通联有限,但关于西藏的话语却持续存在。在历史的景深中,究竟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话语描摹了西藏,吸引着探险家不断涉足这一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用他们的话语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怎样的西藏呢?他们的描述是否客观、是否存在自相矛盾呢?下面我们从“他者”的话语切入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西方叙述者的西藏图景与话语偏向
(一)黄金铺叙的想象
从2400多年前开始,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的一个关于黄金的议题在很长时间中成为西方“话说”西藏的焦点,若干个世纪中,这个话题驱动了数位探险家踏足西藏。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③[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徐松岩译:《历史》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54页。第三卷中提到一种像蚂蚁的生物,这种生物“体型比狗小,但比狐狸大,它们从地底翻出的沙土中含有诱人的金子,人们把它称为‘蚂蚁金’”。尽管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并没有明确指出“蚂蚁金”就是在西藏,但文中所说“所有其他印度人以北”的地理指向让世人认定“蚂蚁金”就是西藏的一个物种。《历史》中还说,波斯国王饲养过一些这样的蚂蚁,他们就是由猎人在这里捕获的。印度采金人要在正中午太阳最大的时候,趁“大蚂蚁”休息去采挖金沙,否则,被“大蚂蚁”发现后,一个采挖者也别想逃脱。12世纪的普利斯特·约翰(Prester John)也同样作过类似描述,只是,他笔下的“蚂蚁”有7条腿、4个翅膀,变得更为玄幻。
早期学者、探险家的描述使西方人对西藏的认知中植入了对“黄金”的执念,西藏拥有黄金富矿成为“颠扑不破”的刻板印象。9世纪下半叶,阿里古格和洛党两地发现金矿,加上这一时期先后有153位译师到印度去学法,他们以黄金为盘缠,估计带出近12万两黄金④东噶·洛桑赤列著,唐景福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第35页。,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西藏拥有黄金富矿的佐证。完成于982年的古波斯文舆地书《世界境域志》中指出西藏极为具体的产金地点,成书于16世纪的《拉失德史》中将古格描述为能轻易找到黄金的奇特区域。1253年法国人鲁布鲁克修士提到西藏的黄金时说:“他们的地区如此盛产黄金,以致于需要黄金的人,只要让人掘地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它。”⑤[瑞士]米歇尔·泰勒著,耿昇译:《发现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14页。意大利的耶稣会士伊波利托·德希德里(1715年经拉达克抵达拉萨)在他的游记中以亲见者的立场叙述说,西藏有很大的天然金块,他的西藏“黄金说”提到的地方非常具体,甚至指出在工布有很多人因为黄金而变得富有⑥[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西藏的黄金和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第40页。。1720年,清军官员焦应旂押送粮草从西宁随大军进入西藏,他在《藏程纪略》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一处金矿,书中“漫不经心”的记述被西方人认为是为防外人觊觎的刻意“缄默”。
西藏人对西方探险家觊觎黄金的心思并非一无所知。17世纪下半叶法国医生贝尔尼埃随蒙兀儿人拜访拉达克国王时,国王强调说他的王国并没有蕴藏黄金,只有少量的水晶、麝香、羊毛和甜瓜,国王的表述被视为害怕被征服的谨慎,并没有被西方人的采信。①[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西藏的黄金和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第6页。
对财富的神往使西藏成为西方探险家心中的东方“埃尔多拉多”②传说藏匿于安第斯山脉某处的黄金国。1513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入中美洲占据了巴拿马,将埃尔多拉多的传说散布于世。。1775年,班禅大师赠送给第一任印度总督赫斯定一些金锭和金矿粉末,之前,赫斯定在西藏的寺院中见到过大量镀金佛像和其他金器,这刺激了英国人对西藏黄金的贪欲。1862年,驻扎于印度的英国年轻军官托马斯·乔治·蒙哥马利请示上级后派出了他物色的“探险家”秘密踏足西藏,这些探险家无一不经过伪装,表面上是手持佛珠、转经筒,而怀里却揣着指南针和六分仪。蒙哥马利的努力让英国人拥有了拉达克区域7万平方英里的地图,这让英国人如获至宝,蒙哥马利本人通过这份地图换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1904年英国人用枪炮打开西藏的大门,西方人对西藏财富的想象终于变成了对西藏财富的掠夺。③梁俊艳:《第二次入侵西藏的英军——绅士还是强盗》,《中国藏学》2013年第S2期,第84—98页。此文中可见,当时英军仅运出西藏的藏文文献资料就多达460多驮。在多篇文献中数量有所不同,但事实是,数量不少、文献珍贵,和文献一同运出的还有佛像、唐卡、珠宝等等。也就是说,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方社会对西藏的关注已从黄金等财富上扩展到了领土、政权、宗教等问题上,包括大英帝国、俄罗斯沙皇帝国在内的“每一个列强都怀疑对方对西藏怀有企图,但又对对方的企图一无所知”④[意]图齐等著,向红笳译:《喜马拉雅的人与神》,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287页。,所以各自早早开始了秘密绘制西藏地图、收集科学资料的行动。
(二)西方叙述者话语偏向
从17世纪初开始,陆续有传教士努力学习藏语、了解藏文化,他们带着上帝视角的“关怀”,要为西藏“驱散遮住愚昧无知的黑云”⑤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547页。作者表达的意思应该是“驱散愚昧无知的黑云”。。这些传教士、探险家无论是仅踏足西藏边界,还是顺利抵达拉萨,“闯关”之旅一经结束,大多会著书立说,换取学术、政治上的声望。但经他们“耳闻”或“目睹”传播出去的西藏没有被描绘成“美丽的香巴拉”的,贯穿始终的是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恶劣的气候、猖獗的土匪、阴暗野蛮的居民。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也对西藏进行了“污名化”描述:“西藏地域十分辽阔……当地居民都是佛教徒,并且都是臭名昭著的强盗土匪……他们通过魔鬼般的行为表现出强大的巫术和伟大的奇迹……他们的习俗是招人厌恶的。”⑥[意]马可·波罗著,苏桂梅译:《马可·波罗游记》,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60页。
西方旅行者率先看到并传播出去的是自然环境恶劣、社会条件落后、民众愚昧、思想不开化的西藏图景,最严重的莫过于吐蕃人“吞食亡故父母遗体”……西方社会开始工业化后,在这些探险家眼里的西藏更显得蛮荒、落后,且与现代文明严重割裂。英国人彼得·霍普柯克在《闯入世界屋脊的人》中概述,1950年之前,大部分西藏人“简朴的生活方式自中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普通人根本不知道电灯、电线、钟表之类的东西存在,西藏人与世隔绝,在世界上“忍受痛苦而毫无怨尤”。而在荒蛮、落后的社会图景的另一方面,西藏又是一个“与其他任何地方都截然不同的地区”,是“一生在雪峰间秘密度过的修道者和巫师的世界”①转引自[法]大卫·妮尔著,耿昇译:《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导言”第2页。。在这样语言构述中,一个拥有另一类文明的“神秘”西藏被描绘而出,这一类描述让西藏最终失去了“历史、地理、时间、宗教和现实根基,沦为一个精神的、虚幻的、非人间的香格里拉”②沈卫荣:《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导论”第5页。,成为人们“想象”的西藏。
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社会关于西藏的话语在政治需求与“精神想象”叠加下,“荒野”西藏和其“纯净高地”身份不时杂糅,使其流变为“时间停滞”的香格里拉。在一些西方学者的话语中,这个“香格里拉”不允许被现代文明“玷污”,得保持“原生态”模板,一旦人们的生活变了模样,悖于“原生态”状况,“粗野式”发展即成为西方社会评述西藏的热词。
弗雷德里克·勒努瓦在谈到发展中的西藏社会时曾诘问:“为什么人们要让一个热爱自由并想到带着他的牦牛在山区里过简单生活的牧民搬到城市里面,并成为一名官员,去享受现代生活的舒服惬意呢?”③[卢森堡]阿尔伯特·艾廷格著,周健等译:《“西藏问题”国际纷争的背景、流变及视域》,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8年,第223页。在全球化的智能时代,面对西藏议题,弗雷德里克·勒努瓦这位法国学者不再讲思辨,一味强调西藏“未开化的好处”。对西藏发展持“反现代化”观点的西方人士远不止他一位,在这一类学者、狂热分子的话语中,西藏修铁路、拉萨建购物中心都成为“中国式文化粗野”的表现。
二、“虚无”西藏,另一种“幻象”
工业文明引发人类社会深刻变革后,人们对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制度的依赖蔓延到了整个世界。西藏虽居于世界“第三极”,和平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发展成就,家庭的生活细节中都显见现代文明带来的深刻影响。最为可赞的是,这样的影响以城市为中心,辐射到广大的农牧区,即使在偏远的农牧区,电动牛奶分离器、太阳能电板、智能手机都不再是“神奇”的物件了。普通百姓的认知水平得到极大提升,改变生活品质是社会普遍诉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享受着现代文明福利的西方人,置喙西藏发展的切入点居然是“启动了现代化”。
纵观而论,西方人描述的“西藏——香格里拉”这一话语,实际上表现出了双标和矛盾,从不见他们在哪一个文本叙述中将他们“简朴的中世纪”视为“香格里拉”,而被他们叙述为“沉溺在人祭,同类相食,鬼神及生殖器官的崇拜之中”④[英]彼得·霍普柯克著,向红笳、尹建新译:《闯入世界屋脊的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页。的苯教徒的故乡,在他们需要时就变成了“人间圣地”“香格里拉”。就拿纳粹成员海因里希·哈勒来说,他凭借《西藏七年》一书和改编的电影蜚声世界,且不论电影中的杜撰,单说书中提到的“康巴人”内涵的转变,就显得他颇是“技高人胆大”——最初介绍康巴人时,海因里希·哈勒提到的是“强盗般”的群体,这个群体“抢夺成性”“祸害一方”,但当康区的叛乱分子发起暴动冲击解放军后,这些“强盗”变成了“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民族”中的“一群异常坚强和正直的人”。只要能为己所用,前后话语自相矛盾全然不是问题。学者更敦群培曾在《智游列国漫记》中批评同胞“喜欢随意杜撰一些毫无根据的离奇古怪的故事”,但更敦群培若见识到西方人“应政治之需”的描摹西藏的能力,恐怕会觉得编撰离奇故事调剂枯燥生活的西藏人是那样的单纯、简单。
近几百年来,西方社会各类探索西藏、传播西藏的人士中,虽有图齐那样深层浸于西藏文化研究的学者,也有在98岁高龄之际还渴望“魂葬羌塘”的大卫·妮尔这样为西藏社会变迁而喜悦的痴迷者,但表面上声称是探险或学术研究,实则暗怀着资本与领土扩张的企图,潜含着对财富的觊觎与掠夺之意的人更是多数。从“鬼神的故乡”流变为“香格里拉”,其中也隐现着“高明”的“精神殖民”。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传播者的身份、传播者的话语都有可能对社会认识体系、信仰体系再造产生影响,不可等闲视之。
在历史中“凝滞”,与现代化割裂,田园牧歌依然飘荡,现代物质形不成侵扰,人们保持着精神的纯净、生活的纯粹,尤其还有着强大信仰的支撑,普通民众心性平和、宁静,幸福指数不为物质所影响,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对生死有所参悟,随时可以供“感兴趣”的人研究、欣赏、膜拜并对他们洗净尘世生活负累下的精神虚空发挥效用——这样的西藏,历史上不曾有过,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全然是一种与历史、现实悖逆的虚妄“想象”,是人为构造的另一种幻象。在这样“想象”的支撑下,不时有人拿媒体宣传的不丹王国“幸福指数”作论据来论说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姑且不论人们是否片面地看待了不丹社会,但在今天,撇开自然环境对人生存的影响、知识对社会改进的力量,认为一个自然条件并不得天独厚、存量知识也不足以让大众衣食无忧的区域社会能“超然于物外”地成为“桃花源”,这本身就是反智行为或另有企图的话语引导。
三、“话说”西藏的话语学理视角
即使说西方人深入西藏腹地,描绘他们眼中的西藏社会图景,丰富了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但不容忽视的是,他们对西藏的呈现是有选择、有偏向的,构建的也是局部图景,西藏的社会、民生状况都只是他们的研究客体,他们并不怀有推进西藏社会发展的思想和行动。西藏和平解放后,西方对西藏描述性的话语从有选择的社会情景、宗教文化状况等截面转向了倾向鲜明的态度和意见表达。这一类话语中,负面评价、有争议的话题更大范围地左右着国际舆论,牵引着外界认知西藏的议题,影响着中国的国际形象。
从话语建构者身份的角度来说,大卫·波纳维亚在《西方人在西藏的早期活动》一文中提到想方设法进入西藏的人是“间谍、传教士、学者、地理学家、秘术士、士兵和怪诞之人”。当代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在评判的语言分析中将话语界定为“对主题和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和其他表现方式”。他认为“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①[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序”第1页。在将“话语实践本身分析为霸权斗争的一个形式的方法”上,诺曼·费尔克拉夫洞见到“开辟话题,提出问题”都会有权力的不对称,谁开辟了话题、建构了话题者——其身份必然使话题自带立场与背景、也彰显着目的。由此,西方“间谍、传教士、学者”开辟的西藏话题自然也就服务于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实践。在充满掠夺欲望的“探寻”背景下,也有踏足西藏的西方人提出“祝愿您长时间地享受已使开化的民族失去的这种幸福,当开化民族陷入无止境地追求贪婪和野心的时候,你们却在荒山的保护下继续深化在和平和欢乐之中……”②[瑞士]米歇尔·泰勒著,耿昇译:《发现西藏》,第77页。,然而,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在半封建半农奴制的社会制度中,“荒山保护下的和平欢乐”显得经不起推敲且在话语上毫无现实意义。
从社会事实角度系统研究社会的学科方法肇始于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在这一时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靠工业革命迅速崛起,中国恰处于乾隆末年的衰落期,西藏依然在封闭状态中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从社会发展历程来说,从晚清到民国,抵御外敌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最为艰巨的任务,在没有建立统一、强大的民主共和国的背景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状况全然没有无可能成为社会学科研究的重点对象。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没有形成与西方对等的社科研究成果。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独成一脉后,社会科学研究服务国家的实践探索成为惯常操作,例如《菊与刀》就是此类研究的典范。传教士、探险家、社科研究者们踏足西藏后形成的研究文本,给西方社会带去的远不止是消遣。这些文本为形成西方人“想象”中的西藏社会立下“功劳”,也成为西方社会“话说”中国的论据。
由此可以说,早期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受限于专业发展滞缓、研究素养不足等现实状况,没有生产出足够分量的社科研究成果与西方社科研究进行“对话”。于是,在对外传播话语中,我们被动处于“任人评说”的境地。而今,要传播西藏发展中的真实面貌,需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多维而立体地构建有感染力、有可信度、有共情力的话语体系。
四、叙述主体变化与全新西藏图景的呈现
传播是与人类社会共生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演进与复杂程度的改变,传播扮演的角色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涵盖传播者的身份、传播路径、传播内容、传播发挥的社会功用等方面。因此,区域社会在自我表达方面,可通过传播内容、方式的变化,实现形象迭换。从西藏民主改革到现在,西藏经历了大众传播到泛众传播的传播生态变化,西藏全新的形象变得立体、多维且饱含鲜活的细节,这与传播叙述主体多元化关系密切。叙述主体的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和平解放后,西藏在大众传播上有所发展。现如今,西藏专业传播涉及的大众媒体种类与世界各地无差别,在通联世界的媒介建设方面,西藏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报纸、广播电视、门户网站、电影、期刊无一不以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呈现这片高原向前行进中的诸多故事。专业化传播的主体是媒体,内容的生产者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行各业人民群众,大众媒介是他们确立的传播主场,这一传播主场地的确立是国家力量的体现。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构建起全新的西藏社会图景,形成了中国媒介话说西藏的内容体系,建构出有利于不同社会认识西藏、理解西藏的阐释话语。
随着大众传播深植西藏,它所铺展开的一幅幅变化万千的画卷更是让世人见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所发生的“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沧桑巨变。这些变化所反映的不仅是城市、楼房、道路等社会面貌的变化,更是表现了“西藏人”的变化。专业化媒介的传播内容形成了受众对西藏更为具体而多元的认知,媒介传播的本愿既是为反映社会发展真实状况,也是想通过特定内容的实现观念改变、经验传递、理解共情、文化传承等目标,从而为建设更为美好的大同社会创造条件——这与某些西方人士关注西藏、传播西藏的动机与目的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换言之,西方社会既然记述并认可“旧西藏”的真实面貌,就应该客观看待今日西藏的巨大变化,并理性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
另一方面,新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话说”西藏的讲述者身份结构。西藏和平解放后,社会制度的变化引发了西藏的系列变化,呈现西藏的话语也随之发生改变。显著的一点是,“话说”西藏的队伍中“当地人”的数量明显增加——讲述者身份结构的变化不是单纯的媒介变迁的问题,也不是单纯讲述内容丰富与否、深度加深与否、内容接地气与否的问题,更深层次折射的是社会变迁、社会意识转变和媒介权力扩张等问题。
以往,无论是在西方学者精巧的“田野考察”著作中,还是在记述新闻事件的文本中,西藏当地人话说生活变迁基本上是借他人之手完成的,他们所表达的话语受到各种“把关人”的严格把关,回避不了“把关人”的话语设计和主题建构。而新媒体的出现,作为网民个体的西藏“当地人”具有了在法律框架下实现媒介话语表达的最大自由——这里强调的“媒介”话语表达不仅仅反映着群众政治话语权力的获得,同样也反映了社会进步下与媒介素养相关的媒介权力的表现。和平解放前,一些连戏院为何物都不清楚的普通民众,今天可以随性选择不同的平台观看各种节目,甚至有机会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舞台表演原生态的舞蹈;和平解放前,可能被人当作研究对象来观察的普通人,今天也在媒介中观察审视着世界不同区域人们的生活。从“任人评说”到“自我述说”的变迁中,一种自我呈现、自我解释的力量已经在形成并逐渐壮大,这是对外交流、沟通的基础,好比在报道事实的新闻文本中,总要有当事人的声音,并且基于真实性原则,这个声音还得是原原本本的,不能被修剪枝叶、断章取义。当然作为当事人的述说者本身在使用述说能力的同时,其健全的思考力、认知力是述说全面、深刻、客观、公正的基础。
廓清以上问题后,更进一步需要思考的是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应如何利用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等方面的变化,实现消除刻板印象、纠偏、呈现真实西藏,并进而完成好媒介传播主体宣传新时代、讲好西藏故事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