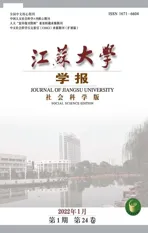文学中的秘鲁华人史:评萧锦荣长篇自传体小说《伊萨卡之旅》和《此生不易》
2022-11-24王凯
王 凯
有关华人移民秘鲁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的1492年,但华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移民秘鲁是从1849年开始的。概括来说,1849年之后的秘鲁华人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49—1879年间的契约劳工(即苦力)时期;1883—1899年为华人移民秘鲁的第二阶段,刚刚获得解放的契约劳工的亲朋好友在1874年签署的《天津条约》保护下数以千计地涌入秘鲁;第三阶段是自1900年至今的自由移民时期。在该时期,众多来自中国的创业者、企业家移居秘鲁。然而,对于华人移民秘鲁的这段历史,主流社会在种族主义的影响下往往采取的是无视和排斥的态度,并将他们长期排除在秘鲁的正史之外。作为秘鲁华人的一分子,在秘鲁生活了近三十年的离散和跨国作家萧锦荣(Siu Kam Wen,1950—)为了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特意在他的两部长篇自传体小说《伊萨卡之旅》(ViajeaItaca,2004)和《此生不易》(Lavidanoesunatómbola,2007)中描述了这三个历史时期的若干重要片段,并聚焦于秘鲁华人史上那些涉及奴役、歧视、屠杀以及自我剥削的苦难时刻,深刻揭示了华人在秘鲁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与残酷暴行,旨在为秘鲁华人发声,还他们以公义。这两篇小说,不仅为我们展现了秘鲁华人独特的移民经历及其特殊的身份观和家园观,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以文学的方式构建起了一种揭示历史真相的秘鲁华人史。
一、 复数的伊萨卡:别样的身份观和家园观
萧锦荣在《伊萨卡之旅》的扉页上引用了卡瓦菲斯(C.P.Cavafy,1863—1933)的诗《伊萨卡岛》(Ithaca),道尽了他本人所经历的“伊萨卡之旅”的别样滋味:“伊萨卡给了你美丽的旅程/没有她,你将永不会上路/然而她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了/假如你发现她一贫如洗,她可并没有欺骗你/收获了无穷的智慧和丰富的经历/到时你必会领悟伊萨卡(Ithaca)的真谛”。
《伊萨卡之旅》是萧锦荣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先以英语创作完成,后由作者本人翻译成西班牙语(1)关于萧锦荣用英语创作的问题,他在《西班牙语文学中的中国声音》中谈道:“我曾尝试过用英语写作。实际上,《伊萨卡之旅》起初就是用英语写的。之后,我又将这部作品从英语翻回西班牙语。我意识到,自己的英语刻意打磨的痕迹过重,不像我预期的那么自然。因而,就小说创作而言,我放弃了用英语写作。”。与《末程》《此生不易》等以秘鲁华人社会为刻画对象的作品不同的是,《伊萨卡之旅》对秘鲁的再现采取的是局外人的视角或者说主人公对秘鲁的审视完全是一种离别后的感悟。故事发生在1990年夏天,距离“我”离开利马已有5年。和在秘鲁的日子相比,如今的“我”生活惬意,拥有稳定的工作和独立的房产。唯一的不足就是过了而立之年的“我”尚未找到合适的人生伴侣。于是,“我”再次踏上秘鲁,希望能够和教父的小女儿罗莎喜结良缘。然而,这场“伊萨卡之旅”却并不如想象中那般顺利、愉快。从一觉醒来睁开眼睛的第一刻起,“我”就感受到了一股沁入心脾的“淡淡的忧伤”:“在利马能赋予游客的诸事中,这是最令我心惊胆寒的。我既逃不掉人行道边的恶臭和混乱,也无法摆脱贫民区的污秽不堪;我尤其深惧这里冬天的鬼天气:阴沉、无雨的天空;阴湿的土地;损人健康的瘴气;还有身边的一切给你带来的浓浓的阴郁”(2)SIU K W. Viaje a taca (a journey to Ithaca) [M]. Morrisville: Lulu, Inc. 2004:25.。显然,秘鲁的环境从一开始就把“我”这个将其视为“伊萨卡”的“外”人拒之千里。而“我”对利马的第一感受同样是颇有隔膜的。吃了这记闭门羹后,“我”和罗莎的交往也没能给予“我”心灵上的安慰。她对“我”的感情始终若即若离。在同罗莎一起游历秘鲁各地的旅途中,本应浪漫的旅程却又被“我”那不服水土的肚子给搅黄了。最终,罗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和“我”提出了分手。于是,“我”仓皇地离开,结束了这段“倒霉之旅”。“我”彻底和秘鲁说了再见,而秘鲁也没有对“我”有任何挽留。
至此,让我们回到这部小说的题目和萧锦荣在卷首引用的诗句上来。众所周知,在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中,伊萨卡岛是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故乡。特洛伊战争获胜后,奥德修斯历尽诱惑和苦难,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实现了伟大的回归。自此,伊萨卡和故乡就成了同义词。但显然,小说中的“我”在秘鲁所经历的“伊萨卡之旅”却并没有奥德修斯那般辉煌和豪迈。迎接“我”的既没有荣耀与崇拜,也没有妻儿与老小,而是利马的臭气熏天和罗莎的冷若冰霜,毫无半点“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成就感。针对这次秘鲁之行,有评论称:“在《伊萨卡之旅》中,这位自传式的主人公在1990年夏天有如一位都市漫游者游走在利马的大街小巷,述说着这座城市的阴郁和破败,回忆着这座城市毫不宜人的天气。而且,他还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有钱有势的利马人……还有这个他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却拒绝给予他工作机会和秘鲁国籍的国家”(3)LOPEZ-CALVO I. Sino-Peruvian identity and community as prison: Siu Kam Wen’s rendering of self-exploitation and other survival strategies [J] . Afro-Hispanic review,2008(27):77.。可见,“我”对秘鲁并不像奥德修斯对伊萨卡那般向往和期盼,而是感到失望,甚至是绝望。那么,伊萨卡之于“我”究竟为何呢?在萧锦荣的笔下,伊萨卡又被赋予了何种崭新的阐释呢?其实,这就是萧锦荣引用卡瓦菲斯诗句的目的所在。萧锦荣在接受笔者的访谈时,曾就他所处的三重流亡经验这么说道:“尽管我在秘鲁生活了25年,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可每每走在这两个国家的街头的时候,我的内心却总是找不到踏实的感觉。2006年,我回了趟香港。当我穿梭在那熙熙攘攘的窄巷中的时候,我留意到周围的人都和我长着同样的面孔,这时,一股释然、放松的感觉突然涌上了心头,那是一种回家的闲适感”(4)王凯.穿行在语言、文化间:美国华裔西语作家萧锦荣访谈录 [J].当代外国文学,2018(1):159-168.。显然,这种流亡的经验给他带来了强烈的疏离感。尽管他一度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这种归属感也只是转瞬即逝的,他不可能永远享受这种闲适。为了生存,他注定还要在三种语言、文化和地理空间中继续出发,继续流亡,在旅途中追寻虚无缥缈的故乡,一如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所言:流亡“是人与故乡之间、自我与家园之间的强制性断裂。这种断裂是无法愈合的”(5)SAID E. Relections on exile [M]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73.。从这层意义上讲,萧锦荣借卡瓦菲斯的诗所呈现的伊萨卡已然不是《奥德赛》所指的一个具体地方,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故乡,而是赋予了人不断出发、不断漂泊的理由,“没有她,你将永不会上路”。另一方面,荷马诗中的奥德修斯在经历了一番苦难和挫折后,最终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回归”故乡伊萨卡。而卡瓦菲斯则不然,他对奥德赛“回归之旅”的现代阐释抹除了“回归”的重要性。他所观照的是收获“无穷的智慧和丰富的经历”后对“伊萨卡的真谛”的领悟,是一种对被模糊化却又理想化了的故乡的“抵达”。显然,这是对伊萨卡的虚化:伊萨卡依然是故乡的代名词,但已失去了具体所指,演变成了可以被认同为故乡的所指。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但它更是一种理想和想象。现如今,秘鲁之于小说中的主人公早已不是那个单数的、唯一的伊萨卡(6)Ithaca萧锦荣所用为单数,经查阅相关期刊文章,黄浩发表在《青年作家》2015年第3期上的《以细读探究卡瓦菲斯的诗中秘》一文所使用的译文为“这些伊萨卡”,故复数形式的“伊萨卡”似更为贴切。,而是诸多伊萨卡中的一个,是他的血脉中、他的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而,他的秘鲁之行,毋宁说是回归,不如说是抵达;既然秘鲁在他的心中从不曾离去,也就无所谓失而复得,他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新的,都是对往日经验的补充和累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与秘鲁的格格不入以及和罗莎失败的恋情使他对家有了新的感悟:“现在我最想要的就是回家。家就是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弟弟、我的姐妹们)生活的地方”(7)SIU K W. Viaje a taca (a journey to Ithaca) [M]. Morrisville: Lulu, Inc. 2004:191.。从对家的理解,“我”又引申出了对家园和故乡的思考,“我对家园也没有十分清晰的界定”。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又将个人“三重流亡”的生存状态自比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我是三重的无家可归”(8)同②:192.。在《西班牙语文学中的中国声音》中,萧锦荣对家园、故乡以及身份的问题也表达了相似看法:“所谓的‘忠诚问题’让我内心极度痛苦:很久以来,我不知道自己的祖国在哪里。但毫无疑问,我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也许,用这种方式解释更恰切一些: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而作为作家,我觉得自己是秘鲁人”(9)王凯.西班牙语文学中的中国声音 [J].博览群书,2012(9):39-43.。不难发现,萧锦荣在此所再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去中心化的身份认同观。浸淫在三种语言、文化以及三个国度间的自我,身份是多重的、杂糅的,内心经历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既有痛苦与焦虑,又有欣悦与希望,鲜明地呈现出一种混合身份认同的特征,这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2014)在《文化身份问题》(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中所言:“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同一自我不再是中心。我们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10)HALL 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277.与此同时,身份的不断变动,必然导致主体对家园概念的重新界定。在新的混合身份认同的影响下,家园不再是单数的、固定的地理空间,而成了复数的、流动的概念,这也就是伊萨卡为何不再是具体的、单数的原因所在。
二、 种族主义:秘鲁华人史中永远的痛
如前文所言,在萧锦荣再现秘鲁社会的小说中,《末程》和《此生不易》可属一类,其特点是局内人对秘鲁华人社会的描述,而《伊萨卡之旅》则自成一类,作品从局外人的角度俯瞰了秘鲁社会及历史上的种种弊病和争端——太平洋战争、种族矛盾、政局紊乱、社会动荡等,并实现了对“伊萨卡”的再认识。萧锦荣刻意安排的、贯穿整篇小说的背景是极其有趣的。1990年,恰逢秘鲁迎来新一轮的总统大选。竞选的一方是秘鲁知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1936—),另一方是秘鲁日裔移民滕森(Alberto Kenyo Fujimori, 1938—)。在进入决选前,略萨得票为27.6%,而滕森以三个百分点的劣势屈居第二。面对这种局面,主人公“我”是这样评价的:“和略萨几近失败相比,更使上流阶层恼火和颇感荒谬的是这个历来由白人当选国家首脑的国家竟然有可能沦落到由一个具有亚洲血统的人来治理的地步了”(11)SIU K W. Viaje a taca (a journey to Ithaca) [M]. Morrisville: Lulu, Inc. 2004:16-17.。可见,从一开始,作者就有意将种族问题推到风口浪尖。身为华人作家,萧锦荣自然更加关心秘鲁历史中的华人以及秘鲁社会对华人的排斥和歧视。在此,滕森不过是一个导火线罢了(12)据苑雨舒《萧锦荣笔下的秘鲁华人:身份认同与价值冲突》,“由于华人是最先到达秘鲁的亚洲人,所以秘鲁人习惯将日本人、韩国人都称呼为‘中国人’。就连滕森在竞选的时候也被媒体冠以‘中国人’之称”。。继续论述之前,让我们再简单地回顾一下秘鲁华人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华人第一次踏上秘鲁的土地是在1849年。随着奴隶制的废除、欧洲移民难以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自1868年以来,源源不断的中国劳工从澳门和广东输入秘鲁,以合同工的形式在种植园做苦力。据统计,仅1849年至1874年间,就有多达10万名来自福建和广东的中国劳工,他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可谓形同奴隶。他们除了要忍受白人的压制外,还要遭受黑人监工——以前为黑奴——的压迫(13)胡其瑜.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M].周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94.。太平洋战争期间,许多华人因不堪忍受艰苦的劳动环境,纷纷站在智利人一边,遭到秘鲁军队的残酷屠杀。进入20世纪以来,秘鲁的中国移民多为私营业主并过着艰苦的生活。其中,大批华人因秘鲁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秘鲁政府对亚裔的歧视,纷纷选择再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
更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华人经验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但这却有可能是较少得到研究的现象之一”(14)PAOLIELLO A. Chinese, Tusan and Kuei: the representation or Chinese peruvian identity in Siu Kam Wen’s short stories [J].Antares: letras e humanidades, 2013(9):51.。自然,地处南美的秘鲁也不例外。正如开篇时所言,在秘鲁,华人经验和华人对当地的贡献“在秘鲁的官方史学中遭到刻意的压制”(15)HU-DEHART E. Latin America in Asia-Pacific perspective [M].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20.。然而,新历史主义指出:“假如整个的文化被视为是一种文本的话,也就是说,假如一个历史时期所有的文本痕迹都可以被同时‘算作’再现和事件的话,那么,将‘历史’作为审查工具的难度必将与日俱增”(16)GALLAGHER C,GREENBLATT S.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16.。再者,“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人类学(或者历史)轶事都属于文本的范畴。从编造的角度而言,两者都是虚构的,都是依靠想象而来的,都是在可获得的叙事与描写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为将它们结合起来加以考量提供了某种可能性”(17)同⑥:31.。显然,具有文本性的历史与文学的边界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重合的,换言之,对文学文本的细读与剖析与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和梳理可以起到相互烛照的作用。按照该逻辑,对萧锦荣小说的研究既是对秘鲁少数族裔文学的挖掘,对秘鲁文学版图的重新定义,又是对秘鲁华人史的另类再现,对被压抑、被掩埋的秘鲁华人史的言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他的数部作品中,“秘鲁的华人经验,尤其是利马的华人经验,都被巧妙地记录了下来”(18)PAOLIELLO A. Chinese, Tusan and Kuei: the representation or Chinese peruvian identity in Siu Kam Wen’s short stories [J].Antares: letras e humanidades, 2013(9):51.,而这其中就包括他的这部长篇自传体小说《伊萨卡之旅》。
具体而言,在《伊萨卡之旅》中,萧锦荣细数了秘鲁华人的血泪史,随着“我”漫游秘鲁的脚步,再现了一部不为人知的秘鲁华人史。在首都利马,“我”所游历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景点是两座墓园。在Presbítero Maestro墓园中,“我”专程去瞻仰了中国苦力的墓地并评述了他们被遗忘的一生:
他们是留着辫子的中国苦力,在甘蔗田、沿海的棉花田和鸟粪岛上辛苦劳作,幸运地从横跨大西洋的海上远洋中死里逃生并挨过了一贫如洗的生活。他们一天都不曾丧失过自己中国人的身份,终其一生都始终保持着他们的传统、价值和生活习惯;然而,中国名字却使他们蒙受了不幸,那些被遗忘的墓碑便是见证。在大多数人的墓碑上,都只歪歪扭扭地刻着有名无姓的名字;还有的人的姓氏被张冠李戴,误把他们雇主的姓氏刻在了上面;更有甚者,墓碑上只有他们为人所熟知的绰号(19)SIU K W.Viaje a taca (a journey to Ithaca) [M]. Morrisville: Lulu, Inc. 2004:34.。
在这段叙述中,萧锦荣掀开了秘鲁华人史的第一章,不仅再现了中国苦力在秘鲁生活的艰辛、所从事的行业,也从姓名这一颇具文化意义的符号上凸显了19世纪中国移民在秘鲁惨遭埋没和遗忘的卑微。在秘鲁人眼中,“讨厌的中国佬是被偷运进这个国家的”(20)同②:149.,因此是不属于这个国家的,是不合法的,是没有资格享受平等权利的。在这篇小说中,萧锦荣还专辟一章来讲述“秘鲁的犯罪史”,详细叙述了秘鲁从1530年至1985年长达四个多世纪以来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其中,他特意提到了1881年的两次对中国人的迫害。第一次是1881年1月16日,在智利军队即将攻陷利马前夕,一群暴民在秘鲁军队的带领下洗劫了首都的市中心并放火焚烧中国商人的店铺,以作为对中国苦力加入智利军队的报复。第二场暴行则发生在同年2月。当时恰逢智利军队占领利马,整个国家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卡涅特的一群黑人和印第安人对中国苦力进行了残暴的屠杀。据保守估计,一天当中就有1 000名中国苦力惨遭杀害,可谓横尸遍野、血流成河。进入20世纪后半叶,尽管暴力流血事件渐渐消亡,但华人仍然遭受着种族歧视,不能与白人享受同等待遇。而这正是“我”选择再次流亡、再次移民到夏威夷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是“我”很难将秘鲁视为家园、视为故乡的重要因素。在一次与罗莎交谈的过程中,“我”无奈地抱怨道:大学毕业不久,“我就发现被政府公职和国有企业拒之门外,它们是不接受外籍人士的申请的。后来,我又到私人公司去碰运气,结果发现它们对外籍员工的招募是有限额的。经过一年各种的临时工作和申请入籍的失败,我最终决定我受够了,我要离开这个国家”。当罗莎追问道“我”入籍失败的原因时,“我”继续答道:“要想得到入籍资格,我必须有一份稳定、全职和收入丰厚的工作”,“而要想得到一份稳定、全职和收入丰厚的工作,除非我成为正式的公民,否则是做梦也别想得到的”(21)SIU K W.Viaje a taca (a journey to Ithaca) [M]. Morrisville: Lulu, Inc. 2004:44-45.。显而易见,秘鲁政府对中国移民的入籍政策就如同移民法中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其目的就是为了排斥移民的同时又不破坏其合法性(22)根据秘鲁1995年修订的《入籍法》第一章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凡是希望通过归化加入秘鲁国籍的外国人,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a. 在秘鲁连续合法居住两年以上(含两年);b. 具有固定的职业、从事一项艺术门类、具有一门手艺或者从事固定的商业活动;c.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无犯罪记录。据萧锦荣于2019年8月6日给笔者的邮件,该法律在修订前更严格,凡希望入籍秘鲁的外国人必须在秘鲁连续合法居住十年以上。。随后,萧锦荣又在另一章节中对秘鲁种族问题的由来已久做了专门评述:“种族偏见在秘鲁那颗不常露面的太阳下是司空见惯的。在这个国家,孩子们从小就被要求去学习区分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黑人和桑博人、印第安人和乔洛人以及穆拉托人和嫁接者的不同(23)克里奥尔人(Creoles)指生于美洲而父母是西班牙人的白种人,梅斯蒂索人(mestizos)指的是出生在美洲的白种人和当地印第安人的混血后裔,桑博人(zambos)指的是西非黑人奴隶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裔,乔洛人(cholos)指的是想同化于西班牙文化的印第安人,穆拉托人(mulattos)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后裔,嫁接者(injertos)指的是华人后代,现在称为土生者(tusán)。……对种族主义的奉行是很微妙的,……有时候很难被注意到,但大多数时候都是赤裸裸的、明目张胆的”(24)同①:59.。从这短短不到200年间华人在秘鲁历史中的地位和境遇而言,“我”对秘鲁这个国家是颇有微词的。对于一个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对待的国家,“我”又怎可能心甘情愿地将其视为我的“家园”、我的“故乡”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伊萨卡之旅”也绝非是回归故土的旅程,不过是一场反思之旅,是对秘鲁的重新发现。
在歧视议题的言说上,小说的结尾极具象征意义。为缓和“我”与罗莎的紧张关系,“我”给她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她可以撇开成见,回心转意,切勿毁了这桩婚事。在此,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寄去这封信的同时,“我”还随信给不懂英语的罗莎寄去了一本英文小说《傲慢与偏见》(PrideandPrejudice),并且还刻意提醒那些渴望一探其中究竟的读者,这本书最初的题目是《第一印象》(FirstImpressions)。笔者以为,此处除情节需要外,更为重要的是萧锦荣希望借这一悬念引起广大西班牙语读者的注意。这本小说看似是送给罗莎的,实则是送给以罗莎为代表的生活在秘鲁的西班牙语读者的。结尾的启示在于,无论是不同的性别,还是不同的种族,都应该抛弃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慢与偏见”。在与他者的相处中,“第一印象”固然重要,但仅凭“第一印象”就对对方的本质加以负面的评论往往会酿成大错,甚至是惨剧。
三、 自我剥削:秘鲁华人史中的又一层阴影
如上所述,《此生不易》与《伊萨卡之旅》的切入视角与主题观照不同,《此生不易》从局内人的视角对秘鲁华人社会的经济生活,尤其是自我剥削予以深刻的检视与思考。众所周知,在秘鲁华人所从事的行当中,经营餐馆、小商店和杂货店是最为普遍的,尤其是杂货店,“从20世纪30年代起……取代了意大利人开的小酒馆(bodegas),遍布利马和秘鲁大多数主要城市的大街小巷。因为大多数杂货店都坐落在街角,所以秘鲁人……将这些杂货店称为‘角落里的中国人’”(25)王凯.穿行在语言、文化间:美国华裔西语作家萧锦荣访谈录 [J].当代外国文学,2018(1):159-168.。有关秘鲁华人杂货店主的生活,伊格纳西奥·洛佩兹-卡沃认为:“秘鲁华人店主的工作伦理遵循的是中国农民自我剥削的老传统”(26)LOPEZ-CALVO I. Sino-Peruvian identity and community as prison: Siu Kam Wen’s rendering of self-exploitation and other survival strategies [J] . Afro-Hispanic review, 2008(1):75.。而自我剥削,按照该学者的分类,又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店主自我强加的贫穷、新客的缺乏安全感以及三合会收取保护费(27)同②:80.。萧锦荣分别借助埃克托、艾利亚斯和炮仔这三个典型人物将华人社区中的自我剥削现象完整地呈现出来,但他最为关注的还是杂货店主唐奥古斯托的自我剥削,尤其是对他儿子埃克托的剥削。和萧锦荣本人一样,埃克托八岁时和他的母亲远渡重洋来到秘鲁,才第一次见到生身父亲唐奥古斯托。到达秘鲁后,他和父亲和谐的父子关系仅仅维持了两年就画上了句号。父亲古板、保守、刻薄,像绝大部分老华人移民一样信守实用主义,推崇读书无用论,希望有一天埃克托也可以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继承他的事业,成为一名合格的杂货店主。可他这个长子却偏偏和他的理想背道而驰,超乎寻常地喜欢读书,12岁不到就读完了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的三部和已经出版问世的所有金庸创作的武侠小说,并且还自学了西班牙语。但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埃克托在父亲的逼迫下,早早辍学回家,为家里挣钱。对埃克托而言,杂货店的工作枯燥乏味,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的生活,辛苦不说,挣的钱还少得可怜:他“每天从早七点到晚九点都在杂货店里工作,他因此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可以领到300索尔的零花钱。这笔钱只够他在他休息的那个下午去看一两场电影,买十来本笑话书或者四本中文书,外加请他的朋友们看一两部电影,此外就什么也干不了了”(28)SIU K W. La vida no es una tombola (this sort of life) [M]. Lima: Ediciones del Vicerrectorado Académico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Mayor de San Marcos,2008:65.。更加过分的是,正因为埃克托是自己的孩子,唐奥古斯托非但没有对他更加慷慨,反倒变本加厉地对他加以盘剥。在一年365天当中,埃克托最痛恨的就是圣诞节前夜。在那天,他不仅要比平时收工更晚,而且还要受到情感上的打击与伤害。子夜时分,在店铺打烊前,店里的帮工黄先生总是能收到唐奥古斯托的一个红包,作为对他加班加点的犒劳。而埃克托却什么都得不到,哪怕是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此外,让埃克托更为伤心欲绝的是,几乎所有的孩子在这一晚都能从自己父母那里收到一份圣诞礼物,但他却什么都没有,只能落寞地欣赏别人在节日里的喜悦和兴奋。显然,在埃克托心里,父亲阴影笼罩下的生活是痛苦的,是晦暗的,这正像萧锦荣在《后记》中所写的那样:“埃克托这个人物基本上是我为我自己制作的一个假面,惟有戴上这个面具我才能够跟那个伤痕累累并且时至今日回忆起来仍然怆然泪下的过去拉开距离”(29)本部分内容未收录至作者提供的英译本中,详情请参见王萌女士译本《后记》部分第250页。。可见,自我剥削对秘鲁华人造成了另一层面的伤害,无疑加重了秘鲁华人在移居国经历的苦难。
自1849年,华人已在秘鲁生活了170多年,为秘鲁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但在官方的秘鲁历史中,华人作为移民的历史却长期被压制、被消音。而华人作为秘鲁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秘鲁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华人作家之一,萧锦荣不仅在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伊萨卡之旅》和《此生不易》中表现出秘鲁华人独特的身份观、家园观,还着意用文字如实记录下秘鲁华人的移民经历和无数不应被忘却的时刻,真实还原了秘鲁华人在海外所经历的艰难时世,这无异于是书写了一部另类的秘鲁华人史,让长期被埋没的秘鲁华人在历史中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从这层意义上讲,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不仅是对秘鲁族裔文学的重新发现,对秘鲁文学版图的重新界定,而且还是对秘鲁历史的颠覆与重构,对秘鲁华人史的发声与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