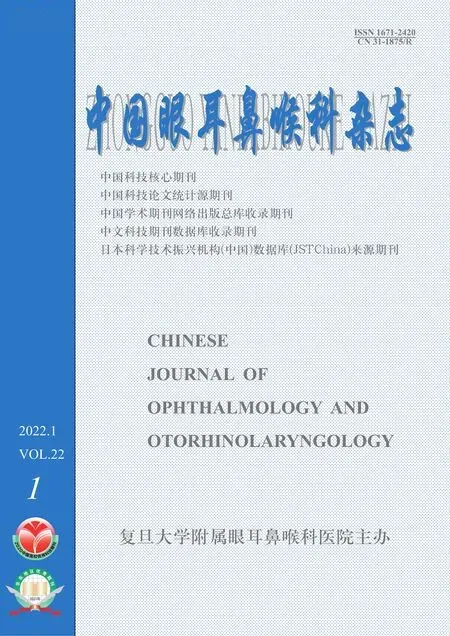嗜酸性粒细胞型慢性鼻窦炎与哮喘的关系
2022-11-24彭敏张丹梅
彭敏 张丹梅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汾阳医院耳鼻喉科 汾阳 032200)
慢性鼻窦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CRS)临床上按形态学分为慢性鼻窦炎不伴鼻息肉(CRS without nasal polyps,CRSsNP)和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CRS with nasal polyps,CRSwNP)[1]。但按照伴或不伴鼻息肉进行分类不能反映手术及药物治疗的效果。近年来,随着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将CRS按内表型分为嗜酸性粒细胞型慢性鼻窦炎(eosinophilic CRS,ECRS)与非嗜酸性粒细胞型慢性鼻窦炎(non-eosinophilic CRS,non-ECRS)[1]。
2020年欧洲鼻窦炎和鼻息肉的意见书将组织中每400倍镜视野中嗜酸性粒细胞(eosinophil,EOS)计数≥10个定义为ECRS[2]。有研究[1]显示,西方国家以ECRS主,亚洲地区以non-ECRS为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疾病谱在发生改变。据报道,ECRS在韩国和泰国的比例较前上升[3-4],在我国北京近11年来,ECRS的比例从59.1%显著增加到73.7%[5]。
CRS患者相比健康人增加了罹患哮喘的风险,其中ECRS比non-ECRS更多伴有哮喘以及哮喘形成前的病变:气道高反应和下呼吸道功能异常[6-7]。有研究[6]显示,ECRS患者伴哮喘、气道高反应及肺功能异常的比例分别为55.3%、47.4%、65.8%。虽然“联合气道”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已被广泛接受,但ECRS与哮喘的共病机制仍不清楚。
1 ECRS与哮喘的共病机制
基于“联合气道”理论,ECRS与哮喘共病可能因素包括:①上、下呼吸道在解剖结构上相延续;②相似的组织及病理学特征;③鼻-肺局部相互作用[8];除此之外,ECRS与哮喘可通过全身途径而放大相互的影响,包括骨髓和白细胞介素-5(interleukin-5,IL-5)[9]。骨髓是产生EOS祖细胞的场所,细胞因子如IL-5、EOS趋化因子(eotaxin)及受激活调节正常T细胞表达和分泌因子(regulated upon activation normal T-cell expressed and secreted factor,RANTES)等协调EOS从骨髓转移到局部,如鼻、肺组织,炎症产生放大效应。IL-5、eotaxin、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还对骨髓EOS祖细胞上的IL-5受体ɑ亚基(receptor ɑ-subunit,Rɑ)表达有上调作用,是ECRS和哮喘共病的重要全身机制[9]。已有小鼠模型证实IL-5和IL-5mRNA存在于嗜酸性气道炎症中[10]。
哮喘分为嗜酸性哮喘(EOS≥3%)和非嗜酸性哮喘。嗜酸性哮喘由Th2细胞亚群释放的一系列促炎细胞因子诱导EOS的聚集和激活,包括IL-4、IL-5和IL-13。淋巴细胞和上皮细胞产生的趋化因子包括RANTES和eotaxin,也对EOS产生聚集作用[11]。暴露于过敏原会导致树突状细胞和上皮细胞产生IL-33、IL-25和胸腺基质淋巴生成素,刺激Th2细胞释放细胞因子IL-4、IL-5及IL-13,进而诱导EOS、肥大细胞以及产生免疫球蛋白E(immunoglobulin E,IgE)的B细胞的生成。IgE反应的免疫记忆通过骨髓中的浆细胞维持,呼吸道黏膜是浆细胞的发育部位,是骨髓中浆细胞的来源,对维持IgE反应的免疫记忆有重要作用[12]。
ECRS与嗜酸性哮喘中的细胞因子模式相似,均由Th2型细胞因子介导上述免疫反应。此外,IL-13可使黏液分泌及纤毛清除相关蛋白(MUC5AC及pendrin)在肺和鼻组织中的mRNA表达增加,促进黏液分泌增加、纤毛清除功能降低而导致哮喘及鼻窦炎的发生[13],最近研究[14]表明ECRS比non-ECRS中MUC5AC及pendrin的表达更高。Ponikau等[15]发现伴有哮喘的CRS患者鼻窦黏膜中存在与哮喘相似的病理变化:上皮损伤和基底膜增厚,鼻窦黏膜组织中伴明显的EOS浸润,证实了CRS 与哮喘病理改变的一致性。同样,张敏等[16]发现ECRS的支气管黏膜以嗜酸性炎症为主,不同炎性亚型的CRSwNP和哮喘为同一气道的不同部位疾病且有着相似的炎性表型。
气道高反应(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AHR)是哮喘的主要特征之一。气道包含许多常驻细胞(气道上皮细胞和内皮细胞等)以及迁移性炎症细胞(EOS、中性粒细胞等),这些细胞能够分泌多种介质,如组胺、半胱氨酰白三烯、前列腺素D2等可以直接收缩支气管平滑肌;而迁移性的炎症细胞产生的炎症介质对气道平滑肌收缩的作用更强,同时可增强毛细血管膜的通透性,导致黏膜水肿[11]。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气道神经重塑是嗜酸性哮喘中增强刺激敏感度和气道反应性的关键机制[17]。
2 ECRS与哮喘的共病关系
“联合气道疾病”假说阐述了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与哮喘的共病机制,但有关AR对肺功能的影响仍存在争议。关于上、下呼吸道疾病之间的关系,有研究[18-19]认为AR对肺功能无影响,而是CRS导致潜在的肺功能异常。即使从不吸烟的CRS患者也存在早期小气道阻塞性改变[20]。部分CRS同时伴AHR[6]。肺功能异常及AHR患者常无肺部症状,但长期可能发展成为哮喘[21]。相比non-ECRS,ECRS的肺功能更差,与哮喘共病率更高[7,22],据统计,在ECRS患者中约50%合并哮喘[23]。此外,哮喘不只是ECRS的合并症,也是ECRS复发的危险因素之一。Rosati等[24]的一项前瞻性研究中,342例ECRS患者术后随访1年,发现合并哮喘患者在复发组和未复发组差异虽无统计学意义,但复发组伴哮喘的比例(66.7%)比未复发组更高(49.5%)。Grayson等[25]的一项长达10年的前瞻性研究中,纳入44例CRSwNP患者,术后随访10年,发现在ECRS亚组中长期复发组比未长期复发组哮喘发生率更高,且复发与组织EOS浸润、IL-5的表达相关。所以哮喘可能对ECRS术后短期和长期复发都有影响。Grayson等的研究虽然样本量大但随访时间短,Rosati等的研究随访时间长但样本量少,所以还需要大样本、长时间随访的研究证实。ECRS与哮喘共病的细胞及细胞因子可能是其长期复发的危险因素。是否合并哮喘的ECRS比单纯ECRS患者有不同炎症因子或哮喘通过全身途径放大ECRS的炎症因子作用,是否我们应该对伴有哮喘的ECRS患者采取更加积极的治疗方式,如扩大手术范围,使用短期全身类固醇激素或靶向治疗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部分哮喘患者症状隐匿,仅表现为咳嗽,易于与其他疾病症状混淆,导致耳鼻喉科医师容易忽视对哮喘的诊断[26],Tanaka等[22]发现在需要手术的ECRS患者中约20%的患者哮喘诊断不足。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局限于哮喘的典型症状,对伴有慢性咳嗽或夜间咳嗽的CRS,特别是ECRS患者应仔细鉴别,必要时行肺功能和支气管激发/舒张试验检查,提高哮喘的检出率。
3 下呼吸道功能及AHR的预测指标
ECRS患者常伴有潜在的下呼吸道功能障碍及AHR,这些无症状的肺部病变可能发展成哮喘[21],所以在哮喘形成前对这些病变进行早期评估尤为重要。而目前我们的早期评估仍然不足,研究者提出了可以预测大、小气道功能的指标,以此指导临床医师进行初步筛查。
1秒用力呼气量(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1 second,FEV1)是反映大气道功能的重要指标,用力呼气量为25%~75%肺活量时的平均流量(mean forced expiratory flow between 25% and 75% of the forced vital capacity,FEF25-75)、25%及50%肺活量时的最大呼气流速(maximal expiratory flow rate at 25% of vital capacity,V25;maximal expiratory flow rate at 50% of vital capacity,V50)是反映小气道功能的主要指标。Zhao等[19]发现CRSwNP外周EOS计数与V25、V50呈负相关,组织EOS计数与FEV1、FEF25-75、V25及V50呈负相关。张露等[27]发现CRSwNP患者中外周EOS计数与FEV1呈负相关,是FEV1变异率的独立预测指标,而与FEF25-75无相关性。尽管以上2个研究中CRSwNP并未按内表型分类,但结果反映了ECRS的相关指标[28](外周血及组织EOS计数)与大、小气道功能的相关性。然而,Uraguchi等[7]将CRSwNP分为ECRS伴哮喘、ECRS不伴哮喘及non-ECRS组,ECRS不伴哮喘组的V50、V25明显低于non-ECRS组;但在ECRS不伴哮喘组中,外周血及组织EOS计数与大、小气道功能均无相关性。所以,外周血及组织EOS计数是否可用于预测ECRS患者的大、小气道功能以及是否还可用其他指标预测还有待研究。
Chen等[29]将CRS患者根据支气管激发试验分为AHR组和非AHR(non-AHR,NAHR)组,发现AHR组双侧嗅裂(olfactory cleft,OC)评分、外周血EOS计数及后组筛窦(posterior ethmoid sinus,PE)评分均显著高于NAHR组;多因素回归分析后发现只有OC评分和外周血EOS计数是AHR的独立危险因素,具有预测价值,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分别为0.800和0.637,而PE评分没有预测价值。Sakuma等[28]发现OC评分、PE评分及外周血EOS计数增高是ECRS的主要特征。所以基于这2项研究,推测OC评分及外周血EOS计数可能是预测ECRS患者AHR的指标,PE评分是否可以用于预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证实。
Chen等[30]发现IL-25在CRSwNP(其中ECRS占85.7%)息肉组织中显著升高,IL-25、息肉组织EOS计数和外周血EOS计数是AHR的独立危险因素,AUC分别为0.845、0.743和0.699。IL-25、组织EOS计数可作为ECRS患者预测AHR的分子指标,其中IL-25的预测效能最高。总之,息肉组织中IL-25和OC评分预测ECRS的AHR效能相当,前者属有创检查,过程繁琐;后者无创、简便,但主观性强,要求医师具有较高的CT阅片水平。
4 治疗和预后
功能性鼻内镜手术(function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FESS)不仅可以缓解ECRS伴哮喘患者的鼻部症状,还可减轻哮喘症状以及改善肺功能[31-32],但术后复发率高[33]。根治性鼻窦手术(radic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RESS)相比FESS术后1年内鼻部症状改善更佳,复发率更低;虽然2种术式在术后3年、5年鼻部症状和复发率并无差异,但RESS修正手术率更低,哮喘控制率更佳[33],2组肺功能均无改善。Alsharif等[34]首次提出了Reboot术式,意为“重启”,“重启”手术较FESS术后2年复发率明显降低,手术风险无差异,但未讨论手术对哮喘患者肺功能以及症状的影响。
ECRS对大环内酯类药物抵抗,对局部糖皮质激素反应良好。短期口服糖皮质激素较局部鼻用激素对ECRS伴哮喘患者的鼻部症状、肺功能及气道敏感度均改善更明显,但药物不良反应更明显[35]。针对信号分子的单克隆抗体治疗,目前生物治疗有效的靶点为IgE、IL-5和IL-4Rɑ,代表药物分别为奥马珠单抗、美泊利单抗及双倍珠单抗。奥马珠单抗、美泊利单抗都可以明显改善ECRS伴哮喘患者的鼻部症状、肺功能,美泊利单抗还使所有口服糖皮质激素依赖的患者都成功地停用了激素[36-37];多中心研究发现双倍珠单抗明显改善了CRSwNP伴哮喘患者的鼻部症状、肺功能以及哮喘加重频率,且安全性良好[38]。所以针对免疫内在型的靶向生物治疗是未来个体化治疗的方向之一。
5 展望
目前我们应提高ECRS患者中哮喘的检出率,还应重视哮喘形成前的AHR、下呼吸道功能的评估,尽早对隐匿性肺部病变进行干预。哮喘增加了ECRS的复发率,是否应采取不同于单纯ECRS的治疗方式,包括手术范围、类固醇激素及靶向药物的应用等还有待研究。ECRS与哮喘的共病机制尚不清楚,还需要深入研究,目前生物治疗靶点还需要多中心、大样本研究来论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