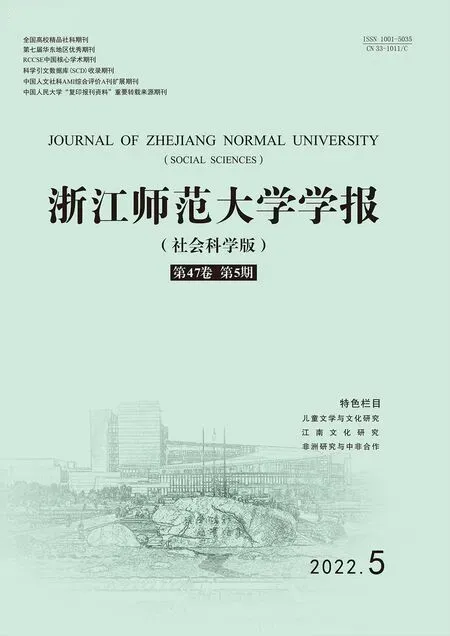域外儿童文学的批判阐释与本土儿童文学的创造性生成
2022-11-24胡丽娜
胡丽娜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百年进程就是不断继承与发现本土传统资源、批判性吸纳域外文学经验,以现代儿童文学的艺术标准进行儿童化与现代化创造的过程。晚清以降,在域外儿童文学译介出版与传播的影响下,本土儿童文学开启了萌蘖与发展之路。儿童文学发展之初即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于: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文学步伐,在西方儿童文学影响的焦虑下建设本土儿童文学,还是探索一条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创造性转化本土与域外资源,进而探索富于中国文学特质的发展之路?在周作人、郑振铎等人的倡导下,发生期儿童文学自觉且有效地以改编为路径,对本国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资源予以收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以现代儿童文学的概念进行儿童化的改造。同时,积极借鉴、批判吸收西方儿童文学经典艺术创作的智慧与经验,开创了中国儿童文学主体建构与审美自觉的发展道路。
一、西风东渐与域外儿童文学的“洋为中用”
晚清以降,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蘖与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之旅密不可分。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中,包括西方儿童文学在内的诸种文学形式成为转型期中国文学寻找建设出路的“路标”。自18世纪中叶以来,域外儿童文学的艺术探索及其沉淀的佳作——如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等经典作品——纷至沓来登陆遥远的东方土地。域外儿童文学的中国译介、传播与接受,一方面是中外儿童文学艺术的交流与对话,是域外儿童文学数百年间发展成就与经验的展现;另一方面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现实境遇,在大河改道的转型时期,中国儿童文学批判吸收域外经验,将其本土化,并积极谋求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
同时,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并非封闭状态的独立存在,而是历史潮流中文学为现实所裹挟的鲜明写照。晚清以降,梁启超等人对儿童群体的重视,对儿童文学的倡导,其初衷在于关注和解决国家和民族的兴亡问题。这种注重文学现实功用价值和意义的历史感始终贯穿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到了“五四”时期,受西方人类学、儿童心理学等思潮的影响,儿童文学界掀起了“儿童本位论”的思潮,其重要标志是对以安徒生童话为代表的域外儿童文学经典的集中译介、评介与推广。反观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即使是在倡导“儿童本位论”最激烈的“五四”时期,儿童文学都不是纯粹的文学建设,而是与儿童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新青年》杂志曾刊发征求“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文章的启事。茅盾认为“五四”时期对儿童文学的关注,是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的。据他回忆,1922年,时任《新青年》主编的陈仲甫在私人谈话中,对当时儿童文学运动重视直译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而忘记了“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的做法表示不赞成。[1]由此,中国儿童文学甫一诞生就深深扎根中国的现实,背负着服务国家民族的重任。在中国儿童文学建设的征程中,以文学来激励、唤醒国人,达成教化鼓动作用的尝试从未停歇。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一直贯穿于中国作家的创作,作家们主动学习西方儿童文学的同时,积极寻求适宜于中国土壤的文学表现形式。亦即,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儿童文学往何处走、儿童文学如何建设一直是核心问题。对西方儿童文学的考察与学习也一直以服从并服务于中国现实与文学发展的需求为目标。随着时代对文学需求的嬗变,原本作为优秀儿童文学的代名词和创作标杆的西方儿童文学,开始经受批判和质疑。作家们也从对域外经典的膜拜、崇敬、赞誉,转向秉持“洋为中用”立场进行批判性吸收。
“洋为中用”的一个重要准则,是依据意识形态、现实政治、文化语境等具体因素对作品进行解读和评判。这种文学接受的态度和立场的流动性,集中体现为批评家对域外经典文本评判标准的变动方面。作为译介最多、传播最广的儿童文学经典,安徒生童话可谓域外儿童文学中国传播与接受中的典型。从《域外小说集》中翻译的《皇帝的新衣》,到《十之九》为例的各种文言译文,再到“五四”之后《新青年》《妇女杂志》《小说月报》的集中刊载,还有各种译本的出版,从清末到“五四”,安徒生童话的中国传播经历了从不被注意到逐渐被认识,再到广受赞誉与推崇的过程。据郑振铎的统计,截至1925年《小说月报·安徒生号》出版之前,全国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作品一共有43种68篇。[2]安徒生童话的译介与广泛接受和周作人、郑振铎、赵景深等文学大师热忱的介绍密不可分。“五四”时期的文学大师们毫不吝啬对安徒生文学成就的肯定与赞誉。周作人高度肯定安徒生童话的崇高地位,认为文学的童话“到了安徒生而达到理想的境地”,他人的创作则是“童话式的一种讽刺或教训罢了”。[3]郑振铎也推崇安徒生童话的丰富性,认为它既“为儿童最好的读物”,又“为成人所深喜”;既是“有趣的故事”,又是“用散文写的最优美的诗”。[4]但是,在“五四”时期短暂实践儿童本位论的创作之后,被周作人所赞许的那些“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受到了批判,许多原本诚挚赞赏安徒生创作的作家纷纷走出“自己的园地”,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
安徒生作品中原先被推崇的“真实”也成为批判的焦点。20世纪20年代,郑振铎曾结合安徒生的童话对“真实”有过精彩分析:
文艺作品之所以能感动读者,完全在他的叙写的真实。但所谓“真实”,并非谓文艺如人间史迹的记述,所述的事迹必须是真实的,乃谓所叙写的事迹,不妨为想象的、幻想的、神奇的,而他的叙写却非真实的不可。如安徒生的童话,虽叙写小绿虫、蝴蝶,以及其他动物世界的事,而他的叙述却极为真实,能使读者身历其境,这就是所谓“叙写的真实”。至于那种写未读过书的农夫的说话,而却用典故与“雅词”,写中国的事,而使人觉得“非中国的”,则即使其所写的事迹完全是真实的,也非所谓文艺上的“真实”,决不能感动读者。[5]
1924年,正是《小说月报》大力推介安徒生作品的时候,也是倡导实践“儿童本位论”的高峰。安徒生“叙写的真实”,令读者身临其境的艺术创造力为大家认可。到了1935年,即安徒生135周年诞辰的时候,儿童文学批评界的态度出现了大逆转,转向对安徒生作品的批评,其矛头就在于其作品的逃避现实和耽于幻想。作为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典范,安徒生童话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儿童文学的艺术标准,本土儿童文学曾一度以其为创作的参照标准。但是在波澜壮阔的现实潮流中,“五四”时期所崇奉的“儿童本位论”,周作人所秉持的儿童文学的相对单纯封闭的“自己的园地”的观念,在此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甚至面临被否定和扬弃。20世纪30年代,中国再次陷入内忧外患,革命战争的持续,以及更大规模的抗日战争的爆发,时代呼唤着文学的现实功用性,儿童文学如何更好地叙写真实、服务现实需求再一次被提上日程。到了1947年,范泉在探讨新儿童文学的起点的时候,提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下,应该如何建立中国风格的新儿童文学,安徒生的童话再一次面临质疑与批评。他认为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是用封建外衣娱乐儿童感情,对于新儿童文学建设来说是不适宜的。当时处在苦难中的中国孩子,不能忘记现实,不能一味飘飘然地沉浸在神仙贵族的世界里。他认为针对儿童的写作,“应当把血淋淋的现实还给孩子们,应当跟政治和社会密切地联系起来”。[6]因此,安徒生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不同接受境遇,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洋为中用”的落实情况。这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用心读周作人对于安徒生的诸种评价,却发现周作人取安徒生童话也并不怀着全面研究安徒生童话的出发点,而只是要为他的儿童文学事业加码,为他的性情倾向做注解。”“‘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和急于为中国新生的儿童文学取样的出发点决定了周作人在推出有‘小儿一样的语言’和‘小野蛮一样的思想’的‘安徒生童话’的同时,却将有多层思想内涵和多重美学风格的‘安徒生童话’忽略了。”[7]即便是自称为“安党”的周作人对安徒生的评价也是选择性吸收。因此,中国儿童文学对安徒生的接受、批评同样是基于“洋为中用”立场、结合不同时代需求和文学建设目标的选择性吸收和扬弃。
同时,不同时期的译者对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一直秉持着“洋为中用”的中国化立场。很多作品再版的时候都会根据特定的语境文化进行调整。如顾均正在《乌拉波拉故事集》1954年再版的时候,特意写了《重版题记》,肯定柏吉尔的创作是把科学和技术知识写成童话形式的成功尝试。但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作家的创作环境是在20世纪30年代孕育着法西斯政权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作者不满意于当时的现实环境,但阶级意识较为模糊,故事中时时流露出一种愤世嫉俗的气氛。重版时,为了消除这种不好的气氛,译者就在译文方面进行修订,将那种超阶级的、对人类的冷酷嘲讽,以及消极悲观的插话都删去,有的篇目因为无法作局部删节,干脆就全部删除,如“火柴和蜡烛”“世界的末日”“金刚石和他的弟兄”等。[8]
在具体译文的传达方面,即使是周作人这样赞同并实践“如实”翻译的学者,也建议结合中国文化特点,充分考虑中国读者接受习惯,在翻译中予以必要的转换和改造,进行创造性解读。他在《卖纱帽的与猴子》的附记指出:《卖纱帽的与猴子》原本是一则民间故事,中国也有类似故事,只是略有不同。在翻译中,“一切悉仍其旧”,包括其中养老泉的故事,篇中歌辞等。但周作人也主张在具体转化时,可以依据接受情况进行一些“酌量变换”。如纱帽的说法有些古旧,可以改用毡帽之类,用中国地方歌谣来代替篇中的日本儿歌,但“须文词轻妙,稍带滑稽便好”。[9]
秉持“洋为中用”的立场对域外儿童文学进行批判性接受与传播是清末以来本土儿童文学建设的重要原则,它倡导在批判吸收,甚至在翻译过程中基于中国国情和读者需求进行改造,更好地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充足的艺术养分。域外儿童文学给予了中国儿童文学文学观念、技巧等多方面的滋养和影响。但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最终考量和评判,并不在于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规模和数量,亦不在于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程度,而在于中国儿童文学本身的发展水平,也就是说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儿童文学本体的建构,即原创中国儿童文学的壮大和发展,这才是中国儿童文学独立的主体性和审美自觉的表现。
洪汛涛在《童话讲稿》中提出了童话的发展道路,应该是儿童的、文学的、幻想的、向上的、中国的、当代的,其中“中国的”这个要求体现为:“我们中国的童话,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它产生于中国,是写给中国的儿童所读,因而必须是中国式的。它具有中国的内容,要使得中国儿童能接受和喜爱。中国的童话,走中国童话的道路。一味模仿外国,那是一条岔道,不能离中国之经,叛中国之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会愈走愈远。”[10]不一味模仿外国儿童文学,而是要批判性吸收,创造性转化,这也是茅盾在研究外国文学时的态度:“取精用宏,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这样才能创造划时代的文学。”[11]由此,安徒生童话这一经典的中国传播境遇,充分展现了本土儿童文学汲取域外儿童文学创作经验和智慧的批判立场。同时,扎根中国现实语境,凸显文学现实功用的价值取向,在作家的自觉创作中也得到落实和体现。这种理论批判和创作选择的“殊途同归”,展现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自觉性的不断加强,及其在不断摸索与迂回曲折中探寻本土儿童文学发展的自我个性。
二、域外启蒙与本土儿童文学的自主探索
域外儿童文学经典的译介,让一度闭关锁国的国人见识了儿童文学经典的魅力。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木偶奇遇记》等不同时段的经典,成为中国儿童的精神食粮,更是启蒙与引导文学新人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的重要“恩物”。许多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作家,最初萌生对儿童文学的热爱都源于童年对西方儿童文学的阅读。陈原说:“如果说我童年因为读了一大堆中华、商务版的各国童话故事,使我知道有大人国,小人国,白雪公主,七个矮人等童话世界,那么到少年时代,开明的这两本书《木偶奇遇记》(徐调孚译)和《吉诃德先生传》(节本)则开始诱导我进入外国文学的现实世界。那时脍炙人口的《爱的教育》(夏丏尊译)和《宝岛》(顾均正译),我也读了,也不如前面两本对我那么有启发。”[12]徐调孚也说:“就由于安徒生童话的嗜读,总引起我们对于儿童文学的兴趣,因而坚定我们从事的决心。”[13]翻译大家任溶溶回忆自己的翻译是源于少年时期对苏联儿童文学作品的热爱,那些作品在他眼前展现了一个新世界,促使他“开始打算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14]在域外经典儿童文学的滋养下,曾经的文学少年成长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翻译的中坚力量。
“中国儿童文学不是纯粹的,它有异邦的血统。”中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文学奖的作家曹文轩,曾以《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安徒生恩重如山》为题,深情论述安徒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深远影响,他以为安徒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源头”,“中国儿童文学的许多特质,都与安徒生童话有着隐形的关系……中国儿童文学的躯体里流淌着安徒生的血液”。[15]正是以安徒生及其童话为代表的域外儿童文学优秀作家和作品的持续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早期儿童文学作品相对鲜明的学习痕迹。
赵景深曾在《妇女杂志》刊载安徒生童话的系列译作,在译介的同时,他还尝试童话创作。1933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小朋友童话》,其例言中直接表明创作是受到安徒生的影响:“斯时赵先生正努力于移译安徒生童话,故行文每多受此丹麦先哲之影响。”[16]作家的创作深受安徒生的影响,赵景深现象并非个例。“五四”前后,在域外儿童文学启迪之下的创作者,其作品不少均有着明显的安徒生之风格。叶圣陶就是有力的例证。叶圣陶坦言他的创作受益于西方儿童文学经典的引领。当时《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童话》等陆续翻译出版。时任小学教员的叶圣陶就注意到了这种适宜于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萌生了尝试创作的念头。[17]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是儿童文学发生期第一部童话集,被鲁迅赞誉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道路。[18]但审视叶圣陶的童话,其前期童话《小白船》《芳儿的梦》《燕子》《梧桐子》等,描摹孩提时代的美丽梦境,书写“美丽的童话的人生”和“儿童的天真的国土”,[19]具有浓郁的安徒生色彩。这或许也是叶圣陶的童话被认为是中国诗意童话的源头,秉持着“美而不真”的唯美原则,着力塑造了一种理想的意境”的原因所在。[20]富有意味的是,叶圣陶又被尊奉为现实主义童话的开山鼻祖,[21]因为他的童话浸润了许多成人的悲哀,有着深切的现实主义情怀。
叶圣陶从诗意的、洋溢着浓郁安徒生色彩的童话转向现实主义童话的自觉意识,正是中国本土儿童文学主体性探求的积极尝试,甚至可以说,叶圣陶在《稻草人》文本创作中实践的分裂、警醒正是本土儿童文学走向审美自觉的努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圣陶是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走向的启示者,叶圣陶在童话创作上的自省、纠结和最后的选择,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儿童文学在西方儿童文学经典影响下的一种审美选择。
《稻草人》童话集中的23篇作品呈现了殊异的风格:有诗意、唯美的表现,有理想的追求;也有冷峻、现实的描绘,更有对苦难的控诉。《稻草人》文本的多元性和艺术转变,预演了此后儿童文学发展的多样可能与多元的丰富和繁荣。叶圣陶创作中的矛盾心态和两难选择,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现实困顿中的犹豫。叶圣陶的典型性还在于他以个人的创作转向表征了整个儿童文学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选择与走向,即不断被加强的现实主义潮流。叶圣陶作为中国儿童文学最初的预示者,他由诗意童话向现实主义童话的转向,典型地反映了儿童文学趋向现实主义这一主潮。这既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在他身上的体现。叶圣陶极其真切地演绎了“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矛盾与选择。
与叶圣陶自觉的艺术转型不同,陈伯吹的自我批判更多代表了沿着域外儿童文学艺术经验探索的作家的心声。陈伯吹曾以“弯路”为题对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进行总结反思。他认为自己在创作上之所以“舍本逐末、弃近求远地走进了狭隘的胡同”,没有写出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儿童文学作品,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过度倾心于西洋的文学与儿童文学。在有意识学习儿童文学的时候,大多以《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水孩子》《金河王》和《杨柳风》《木偶奇遇记》等西洋文学为蓝本。但是,待到系统省思自己儿童文学道路时,却发现,欧洲较早、较著名的童话作家,他们的辉煌硕果,都生发自民间文学的根柢。《格林童话》等作品流传不衰的秘诀却在于对本民族的民间文学遗产的充分吸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加工和推陈出新。在强调创作上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重要性之后,陈伯吹进一步对自己的理论文字开刀,认为在理论论述中引经据典的往往是外国作家的作品,不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犯了“数典忘祖”的错误,同时这也是漠视民间文学,轻视土生土长的现代文学的“崇洋思想”作祟的结果。[22]
陈伯吹先生对自己儿童文学道路的省思道出了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者的共同焦虑。晚清以降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一直受惠于西方儿童文学的滋养,但这种滋养同时也是一种框限和规约。在亦步亦趋的学习模仿过程中,如何挣脱这种模子的束缚,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国气派和作风,形塑中国儿童文学独具的美学特色,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础上开创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自觉,引发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如影随形的焦虑和省思。
三、“古为今用”与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域外儿童文学影响的焦虑与中国传统资源的时代转换是交织在一起的。发生期儿童文学的发展,既要“洋为中用”,借鉴西方儿童文学的经验,又要“古为今用”,立足中国历史语境探求对传统资源的继承与发扬问题。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对“传统”有过独到论述:“历史感不仅感知到了过去的过去性,也感知到了它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感迫使一个人不但用铭刻在心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感觉去写作,而且他还会感到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处于这个整体之中的他自己国家的文学同时存在,组成了一个共存的秩序。这种历史感既是永恒感又是暂存感,还是永恒与暂存交织在一起的感觉,就是这种意识使一位作家成为传统的;与此同时,它使得一位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在同时代诗人中的位置。”[23]不难看出,在艾略特的认识中,“传统”首先“涉及一种历史感”,传统具有一种规约的力量,是一种“共存的秩序”,这种历史感与现代性的共存,规约着作家的创作。
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历史和丰厚积累,对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有着天然的规约作用。儿童文学的发生,是中国文学传统延续中的一种变更,这充分体现在儿童文学建设中对传统和民族资源的改编。传统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根基,潜移默化作家的创作姿态、文化使命等。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既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延续与更新,又行进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即在西学东渐,世界文学汇入的大潮中进行转型和创造。陈思和提出20世纪之后中国文学发展的鲜明特征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这些世界性因素与原有的文学传统形成了冲击、碰撞、对话和交流,并最后融入中国文学的发展。“‘五四’运动以后,外来思潮与本国实际历史境遇相结合的任务提到了历史的日程;‘五四’时期同时涌入中国的各种外来思潮能否在中国生根,关键在于,是否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24]此番言论概括的是五四运动之后外来思潮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命运,但如果将这一言论放置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也同样适用。即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进程中,哪些传统资源能够而且适合进行现代转换,不断对传统资源重新编码,并在这种重现阐释与创造性转化中实现自我主体的持续建构。
传统文学中源远流长的童谣、民间故事、神话等形式,曾给不同历史阶段的童年带去无限快乐。传教士泰勒·何兰德在北京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牛郎织女、吴刚伐桂等故事都深深融入童年文学生活。他曾记录孩子陶醉于保姆叙述故事的情景:
在这位老保姆讲述银河故事的时候,我并没有睡着。小男孩也非常安静地坐在小板凳上,肘顶着膝盖,手捧着腮,嘴张得大大的,眼睛还经常好奇地眨呀眨。这个故事对老保姆来说自然是真的。织女和牛郎都是鲜活的人物,鲜花盛开,万紫千红,我们好像都可以闻到那醉人的香味,清风慢慢地飘来,轻轻地吹拂着我们的面颊。她不知讲过这个故事多少遍了,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其真实性,而且她非常愿意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美丽的故事。[25]
尽管有民间故事丰富童年的阅读,但在中国旧式教育中,儿童往往不被理解和重视,只是矮小的成人。到了现代,即便有学校教育,但传统蒙学读物浸润下的儿童都已浸淫“少年老成”主义。即使是歌谣的吟唱,也要撒上爱国保种的胡椒末。[26]这是周作人对传统中国的儿童生活状态、文学读物供给的批判式写照。
在批判之后,更为任重道远的是直面现实,满足儿童文学需求并建设现代的儿童文学。发生期本土儿童文学睿智地尝试着“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是叶圣陶、黎锦晖、陈衡哲等为代表的原创文学的多元尝试,另一方面则是以改编为路径,对传统文学资源的整理发现与创造性转化。这也是“五四”时期周作人、郑振铎、郭沫若、赵景深等人致力于本土文学建设的重要路径。周作人曾作《儿歌之研究》,指出儿歌、童话契合孩童接受的特点:“幼稚教育,务在顺应自然,助其发达,歌谣游戏,为之主课。儿歌之诘屈,童话之荒唐,皆有取焉。以尔时小儿心思,亦尔诘屈,亦尔荒唐,乃与二者正相适合,若达雅之词,崇正之义,反有所不受也。由是言之,儿歌之用,亦无非应儿童身心发达之度,以满足其喜欢多语之性而已。童话游戏,其旨准此。”[27]既然儿歌、童话是适宜于儿童接受的文学样式,那么对儿歌、童话的收集、整理就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建设儿童文学的必要策略。
收集、整理的路径有两种:一种是面向典籍的整理。周作人较早意识到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可以采用的童话材料。他认为中国虽然无童话之名,但晋唐小说中却有成文之童话,比如唐代的《酉阳杂俎·吴洞》故事中备受后母欺凌的叶限就可与法国贝洛童话的《玻璃鞋》相媲美,而且在时间上,这则故事比《玻璃鞋》要早1 200多年。“中国许多的所谓札记小说”中就有不少“可以采用的童话材料”,“很值得一番整理研究”。[28]如《女雀》《螺女》《蛇郎》《老虎外婆》等民间童话都与儿童极为契合。童话之外,还有童谣的收集。周作人从《古谣谚》中摘录有关古代“童谣”的议论,还根据范寅的《越谚》采集儿歌,加以增补,决意编纂《越中儿歌集》。另一种是面向民间的征集活动。早在1914年,周作人就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刊载《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戏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第兹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29]
周作人对童话、童谣的收集整理有着近乎急切的想法。在《儿童的文学》《儿童的书》等重要文章中,他仍坚持倡导要收集各地的歌谣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加以编订成为“儿童的书”。周作人对歌谣、童话等民间资源的重视,得益于广阔的理论视野。如将绍兴乡间流行的《蛇郎》《老虎外婆》等传说,与欧洲的《美女与野兽》、北美土著人的蛇婚传说及希腊、埃及民间故事进行关联研究。周作人对童话民族意义的重视,对国外安特路郎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建设的方向和儿童文学研究的品格。如童话研究的民俗学取向,“儿童教育与童话之关系,近已少有人论及,顾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鲜有不误者。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乃为得之”。[30]
同样致力于民间童话的征集、翻译和研究的还有郑振铎。郑振铎曾以中山狼的故事为个案,考察了马中锡的《中山狼传》、康海的《中山狼》杂剧、王九思的《中山狼》原本,以及流传于印度、高丽各处的民间传说和法国的《列那狐的历史》、挪威的民间故事等。他发现这些故事情节略异,但故事之间有可惊异的类似,比如施恩的人与忘恩的兽是差不多相同的,为此,他认为把中国各地传说依同样的方法去研究其根源与变异,应该是一件很伟大、很有趣并且很有意义的工作。[31]郑振铎还考察了《伊索寓言》中《榨牛奶的女郎》和《雪涛小说》《青城子·志异续编》等在叙述的层次与结构方面的相同之处。类似这种基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立场,以宏阔的视野对中国儿童文学进行收集整理的工作,正是建构中国化文学的重要路径。
如果说对童谣、童话等民间资源的收集和整理尚是儿童文学建设的一种基础性工作,那么如何将这些传统资源转化为符合新的儿童观念的作品,则是进一步的工作,这势必要通过改编这一环节。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已树立了重视改编作品研究的传统。早期的儿童文学研究曾一度将改编作品纳入儿童文学的来源范畴加以考察,并以之作为儿童文学事业建设的重要基础。1923年魏寿镛、周侯予的《儿童文学研究》,1928年张圣瑜的《儿童文学概论》和20世纪30年代王人路的《儿童读物的研究》、钱畊莘的《儿童文学》、吕伯攸的《儿童文学概论》等专著,以及郭沫若的《儿童文学之管见》、周邦道的《儿童的文学研究》等重要论文都以不同篇幅对收集的途径、改编的标准等问题进行相应的论述。如魏寿镛、周侯予将收集、翻译、创作列为儿童文学三大来源,建议从民间口传、旧有书籍和各书局、学校出版的书籍、报刊等出版物中收集儿童文学材料,用“客观的标准”加一番审查功夫,或者摘取,或者修改。[32]改编的重要性,即其作为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的方法和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在中国儿童文学诞生、发展之初就已明确昭示。更为重要的是,对民间资源的吸收与转化一直是与西方儿童文学译介并行的一种建设路径。比如黎锦晖就在儿童戏剧这种西洋文艺形式中运用了大量的民间资源,《十姐妹》《十兄弟》的雏形就是民间流传很广的《十兄弟修长城》等故事。当下儿童文学发展和研究所要进行的是将这种传统有效地继承并发扬光大。这也是全球化时代,维系儿童文学的本土特色与民族传统,探究儿童文学异质性生存的重要路径。
中外儿童文学发展历程共同表明,对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改编是儿童文学发展和建设极为倚重的创作策略之一。从布尔芬奇的《希腊罗马神话》、兰姆姊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到各种儿童版本的《鲁滨逊漂流记》,从安徒生童话对民间故事的创造性转化到蔚然兴起的《小红帽》《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等后现代图画书创作,从迪斯尼、梦工厂对各国经典童话和民间故事的影视改编到当代中国《大圣归来》《哪吒魔童降世》等传统文化动漫的异军突起,丰富多元而形态各异的改编实践,构成了儿童文学艺术长廊中的别致景观。中外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共同表明,改编不仅是各国儿童文学早期生成与建设的重要策略,更是儿童文学在不断更新的时代语境下葆有创作活力的创新路径。直至今日,对民间故事、童谣的改编和重述,对传统文化的再解读和阐释以及图画书再造,依然是彰显本土儿童文学的民族气质和特色的不可或缺的内容构成。
以叶圣陶、陈伯吹为代表的创作探索与反思,代表了本土作家审美自觉的努力,这也是百年来儿童文学发展的主流;而以周作人、郑振铎为代表开创的对传统资源的整理、再发现与改编,代表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翼,立足本土民间和传统资源的现代编码,逐渐摸索出传统资源现代化转化的建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