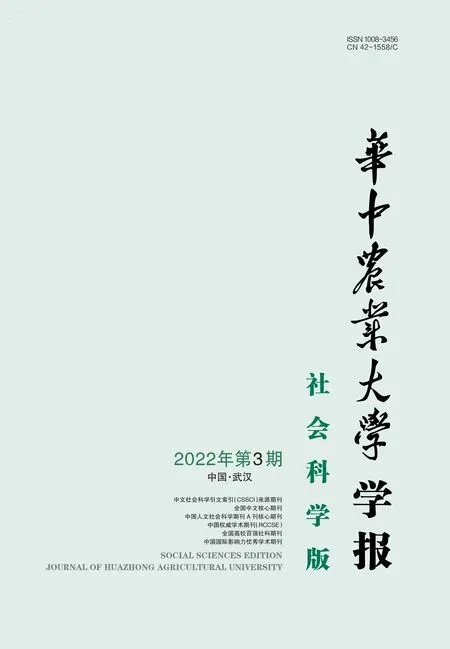种子开源的缘起、现实价值与实践模式
2022-11-24万志前周贤桀
万志前,周贤桀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农业农村法治创新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0)
长期以来,包括植物种子在内的生物遗传资源一直作为人类公共财产[1],免费且不受限制地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民育种,任何国家和群体不得独占[2]。十九世纪末农业科学的出现标志着植物育种与植物生产相分离的历史性转变[3]。现代种子不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种质资源和现代育种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育种需要大量的智力、资金和物质投入,为保障育种者的投入回报,育种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应运而生,且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强度不断提高。知识产权通过赋予育种发明人一定时期的独占排他权,能有效将知识产品的外部性内部化,进而激励育种研发创新[4],但知识产权保护削弱了植物种子作为公共物品的属性[5],其独占排他性也阻碍了植物育种创新所必需的遗传资源的获取,增加了交易成本,阻滞了育种创新。
鉴于知识产权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采用一种既能激励创造又不限制公众使用的机制,而非现在的独占权模式[6]。在源于计算机科学的“开源软件运动”的启示下,将植物育种过程类比软件开发,旨在实现植物遗传资源和育种技术开放获取的种子开源构想被提出并付诸实践[7],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如抗条锈病的开源小麦品种 “Convento ” C在德国和荷兰被广泛种植,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发的开源品种 “Sunviv” a番茄被证明对叶枯病和褐腐病具有良好的抗性,https://opensourceseeds.org/en/Find%20varieties.。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育种创新是“端稳中国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为此,我国在政策层面提出“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2)见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http://www.gov.cn/xinwen/2020-12/18/content_5571002.htm;《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完善开源知识产权和法律体系(3)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lh/2021-03/13/c_1127205564_6.htm.。种子开源作为植物新品种保护和发展的创新模式,是开源知识产权体系的一部分,有利于获取育种资源,降低育种成本,加速育种创新,克服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的弊端,但目前我国尚无种子开源的实践。
现有研究主要涉及从知识产权排他保护的局限性分析种子开源的必要性[8]、开源制度作为知识产权保护替代方法的可能[9]、开源对农民、育种者和育种行业乃至社会的影响[10]以及遗传资源开源保护的困境与出路[11]等。已有研究为开源运动在育种领域乃至生物领域的拓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对种子开源的缘起探究、价值分析和模式归纳有待拓展。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种子开源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模式选择。
一、种子开源的内涵与缘起
开源即计算机软件领域的“开放源代码”运动。最初是Richard Stallman 为反对AT&T 公司对Unix源代码的封闭,以推广自由软件为目的所建立的自由软件联盟计划(GNU 计划),旨在消除或减少获取软件代码的障碍。源于软件领域的开源运动延伸至育种领域所产生的种子开源,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原因。
1.种子开源的内涵
类比软件领域的开源,种子开源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植物种质进行生产、育种、繁殖和分发;同时,任何用户都有义务将相同的权利赋予植物种质的其他使用者[12]。以此实现种质资源的开放共享,实现育种领域的开放式创新。其具体内涵如下:
种子开源是对育种领域知识产权排他性保护的修正。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这一概念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而推行[13]。知识产权通过对创新成果赋权的方式,授予特定主体排除他人运用其创新成果或商业积累的优势利益(商誉)的权利,以保护合法的竞争力量,建立竞争秩序[14]。如通过确定权利归属和授予发明人排他性权益的专利制度,就是使研究与开发的收益内部化,从而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15],但知识产权排他性保护增加了他人获取育种材料与技术的难度。不同于知识产权的独占排他性,开源旨在将成果尽快推向公众,减少其他创新者获取上游创新技术和资源的阻碍,鼓励新技术的高效运用,加快后续创新者的技术研发进程。种子开源可以产生创新的链式反应,即原始创新可带来后续创新,而后续每一个创新又可为创新提供潜在资源或者工具,继而有助于所有参与主体创新能力的突破性提升[16]。就此而言,种子开源在修正知识产权排他性所导致负面效果的同时,也有利于创造更多可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成果。
种子开源旨在提高植物种质和育种技术等创新要素的可获得性,并非否认知识产权。种子开源是在承认育种者知识产权的基础上,采取特定开源模式使一定范围内的植物遗传资源和育种技术的获取更加容易。开源意味着任何参与者都可以使用开放的植物种质资源和育种技术,使用者也有义务保证将其获得的种质资源与育种技术供后续使用者自由使用[12],进而保障种质资源和技术的可获得性。但开源并不意味着免费,也不意味着没有限制或责任[8]。作为将专有权向公众让渡的回报,开源的贡献者不仅可以自由接触和利用其他育种者的开源种子,还可根据开源种子的利用情况收取一定的使用费。
种子开源秉承自由、开放与共享的理念。首先,种子开源体现了自由的理念。在符合开源条件前提下,不论是出于商业目的抑或非商业目的,使用者可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自由地将开源范围内种质和技术用于育种研究和植物生产,对使用者新获得的育种成果,后续使用者亦可自由使用。其次,种子开源体现了开放创新的理念。不同于封闭式创新,开放式创新模式意味着,企业可同时利用内外部创新和商业化资源[17],进而拓宽企业生存和发展空间,使之有更多的机会融合内外部技术以提高突破性创新能力[18]。开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过后续成果的延续开放,将使更多的育种资源和技术纳入开源体系下,实现开源范围的“病毒式传播”[9]。最后,种子开源体现了共享的理念。不同于传统知识产权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以实现激励创新的目的,开源不是通过直接支付的方式激励参与者创新,而是通过间接回报,包括外在的(如提高声誉和发展社交网络)与内在的(如令人满意的心理需求、愉悦感和社会归属感)方式激励用户参与[19]。使用开源种子进行研发的育种者不仅需要与他人共享育种成果,也需要公开实验数据以减少其他育种者的重复投入。共享有利于提高研究者在育种行业的声誉,增强育种者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2.种子开源的缘起
防止种质资源私有化、育种领域的累积性创新特点以及种子和软件的共通性是计算机软件领域的开源运动延伸至育种领域的主要起因。
种子开源缘起于克服种质资源私有化趋势。随着育种技术的进步,育种投入不断增加,育种研发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在种子企业的推动下,美国于1930 年5 月13 日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授权植物专利的法律,即《植物专利法》(PPA),该法仅保护无性繁殖植物(不包含块茎类),1970年通过的《植物品种保护法》(PVPA)则将有性繁殖植物纳入其保护范围(4)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于2018年进行了修改,将其保护范围扩大至无性繁殖品种。。随着20世纪70年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美国通过专利商标局的审查实务以及司法判例(5)在Exparte Hibberd(1985)案中,美国专利商标局首次承认植物发明可以受普通专利的保护;在J.E.M AG Supply v.Pioneer Hi-Bred(2001年)案中,美国联邦法院认为专利法第101条没有排斥植物发明的可专利性。,确立了以发明专利法保护相关植物发明,不论是有性繁殖植物还是无性繁殖植物,只要满足专利授予条件即可。在植物专利法、植物品种保护法和发明专利法的三重保护下,植物的基因序列、组织、品种、育种方法等均受到法律保护,这无疑加剧了植物种质资源的私有化程度。种子企业通过对留种种植农民的起诉,进一步巩固了其对种质资源的控制,种质正从公共资源变为私有产品。为避免植物相关发明知识产权保护所导致的种质资源私有化趋势,旨在保留农民、园丁和育种者自由使用、保存、重新种植种子权利的开源种子理念最先在美国被正式提出并付诸实践[20]。
种子开源起因于育种创新的特殊性。知识本身是进一步产生知识(创新)的最重要投入[21],植物育种往往需要以已有种质和技术为基础,具有累积性和顺序性的特点,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的[22],且现代生物育种会不可避免地使用某些基础性生物技术研究工具[23],这些研究工具通常由许多紧密相关的分散权利构成[24]。受知识产权排他性影响,此种权利结构会阻碍育种技术向下游延伸扩散,因此,需要引入开源模式以减少或消除创新要素获取的障碍,提高育种领域整体研发创新效率。育种的复杂性决定了开源模式的适用空间。育种研发是一个反复试错的庞大工程,仅由少数人员显然难以实施,种子开源建立的开源社区能为育种者提供信息共享渠道,育种者可以在他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避免重复研究。对于开源者来说,借助开源社群可优化自身技术,节约研发投入和诉讼成本,提高市场影响力,其收益亦可弥补放弃的经济利益[25]。
种子和软件的共通性,也是开源模式引入种子领域的重要原因。首先,两者都具有动态创新的特点。任何软件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产品,软件的维护更新是一个不断积累优化的过程。良种的选育也非一蹴而就,需要不断累积选育优化。其次,开源软件所秉承的开放理念与种子创新相契合。软件开源通过源代码开放,实现信息的可访问性,使用者可自由使用、拷贝、分发、修改和优化开源代码,进而产生高质量和可靠性强的代码。种子开源的灵感也来源于开放许可[26]。种子使用也是一个创新过程,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确定为创造者,农业是一种“开放的科学”[27]。种子创新需要自由开放的空间,而非阻碍植物材料获得的知识产权排他性保护。开源引入育种领域可以创建一种“受保护的公地”[28],让农民和育种者自由获取植物材料,避免植物遗传资源因知识产权保护而封闭化。最后,两者都具有自我复制性。软件的使用和复制是相伴的,植物种子的使用也是如此,种植种子就是种子的自我复制。
二、种子开源的现实价值
种子开源作为一种开放创新模式,其具有整合育种资源、促进育种创新以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现实价值。
1.整合育种资源
种子开源能实现育种资源整合,优化育种资源配置。作物种质资源是育种原始创新和现代种业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29]。若育种资源分散,归属于不同的主体,则会影响现代种业的持续发展。从种质资源分布看,大量的种质资源分别归属于不同的育种者和农民,种质资源数量庞大且分散的特点使其取得和利用变得复杂。而种子开源可为育种资源整合和集中提供便利。众多育种者和农民通过开源组织将资源彼此开放并进行整合优化,可极大地便利遗传资源取得,为育种提供创新要素。
种子开源也可打破国家间育种资源交换的障碍。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世界生物资源分布极为不均。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所确立的遗传资源国家主权框架下,跨国植物种质的流动不仅受到品种权或专利权保护的影响,还裹挟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随着CBD 的生效推广,许多国家开始立法限制遗传资源的出口和交换,遗传资源使用国(发达国家居多)与遗传资源丰富国(发展中国家居多)的利益冲突加剧[30],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创新资源流动受阻。尽管国际上一直促进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工作,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机制而困难重重[31]。不仅如此,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代表的部分区域经济联盟试图通过禁止农民保存和交换对传统农业社区至关重要的种子,以增强对农业的跨国控制[32],这进一步阻碍了种质资源的跨国流通。种子开源则可以促进育种领域的国际合作,各国可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参与育种国际分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种质资源和育种技术。种子开源也能为跨国育种资源的交换提供平台,使“资源”换“技术”成为可能,提高育种资源整体利用效率。例如种质资源提供国可以低价或免费使用育种成果或获取育种技术,遗传资源使用国或跨国种子公司则可借助种质资源改良现有品种,培育出更多的优良品种。
2.促进育种创新
种子开源能有效克服育种领域的“反公地悲剧”,进而有利于育种创新。受Hardin“公地悲剧”理论的启发[33],Heller 等提出了与之对应的“反公地悲剧”理论:资源或产权过度分割以致破碎化,导致资源排他性过强,进而造成资源使用不足的悲剧[34]。育种领域相较其他领域更容易出现反公地悲剧。随着育种技术的进步和育种竞争的加剧,某些品种的基因片段和组织分属不同权利人的现象愈发普遍;某一基础研究工具也往往由多个紧密相关的权利所构成。研究者为寻找到改良植物特性的有效方法或种质资源,必须获得权利主体的逐个授权,导致整体交易成本过高[35]。此种因多种权利相互重叠交叉形成的“专利丛林”会束缚创新,甚至造成技术资源完全无法利用[36],进而引发育种领域的“反公地悲剧”。
当前植物育种领域已被证明存在明显的“专利丛林”现象[37],此现象会随着新品种的累积和专利数量的增加而愈演愈烈。为解决权利重叠所导致资源和技术利用的障碍,知识产权制度内部设置了某些权利限制制度,但受制于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框架,这些制度难以实现种子开源的功能。如品种权中的“育种豁免”,能使育种者自由获取受保护的繁殖材料用于新品种开发和培育,但该豁免仅限于品种开发阶段,如果后续育种成果是原始品种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其能否商业化仍取决于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专利制度中设置的“开放许可”与“研究豁免”制度同样难以实现种子开源的功能。专利开放许可虽与开源具有高度的近似性,但开放专利所产生的后续研究成果是否开放取决于后续专利权人的自愿,因而不具有延续性。至于研究豁免,其适用不仅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6)研究豁免的适用条件主要通过判例法和制定法两种方式确定。普通法系国家一般是通过司法判例确定,大陆法系国家倾向于通过制定法明文规定,但这并非绝对。各国关于研究豁免的适用条件,尚无统一标准,但大体存在两种模式:一是商业目的与非商业目的的区分模式;二是研究对象与研究工具的区分模式。,适用范围也不明确,无法解决育种材料或技术自由获取的问题。而在种子开源环境下,只要品种权或专利权人同意将其育种成果开放,他人使用该育种成果或技术便无需征得权利人的许可,使用者也能免遭侵权指控,且使用者需将使用开源种子所取得的成果纳入开源范围,能克服权利主体过于复杂而无法使用的困境。同时,种子开源可以节约授权许可所耗费的谈判成本,提高育种效率,促进育种创新。
种子开源有利于化解品种权与专利权共存所产生的困境,进而促进育种创新。TRIPS协定第27条3(b)项规定成员应当提供专利或专门制度或二者结合保护植物新品种,普遍认为,UPOV 公约规定的品种权即为该条款所要求的专门制度[38]。两种制度保护同一客体有两种模式,即叠加保护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和分立保护模式(欧盟为代表)。叠加保护模式下专利权和品种权会在同一品种上共存,分立保护模式下专利权与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有明显界限,且通常认为对同一品种无需同时申请两种权利叠加保护。但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基因重组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某些植物受品种权保护的同时,构成该植物的某些部分或培育方法也可能受专利保护,由此产生了同一品种上专利权与品种权的共存现象。但由于专利权保护制度与品种权保护制度存在差异,往往导致某些制度功能无法实现。如品种权制度规定了农民留种豁免和育种豁免的例外,而专利制度一般没有这两项例外(7)目前仅有少数国家的专利法中规定了育种豁免制度。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613-5-3条、德国专利法第11.2.b、瑞士专利法第9(e)条规定了育种豁免。。又如根据品种权制度,他人利用受保护的繁殖材料育种或留存少量种子用于种植,不构成品种权侵权,但如果同一客体上专利权和品种权共存时,因专利制度无留种豁免和育种豁免的规定,则会构成专利侵权,进而导致育种豁免落空、农民留种无法实现,并可能导致品种权或专利权的实施困难[39]。种子开源为化解品种权和专利权共存所产生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方案。如将专利权和品种权所保护的客体均作为开源对象,即使专利制度与品种权制度存在差异,使用者也可自由使用开源育种成果而无需担心侵权指控,进而消除获取育种成果进行后续创新的障碍。
3.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现代农业所带来的短期高速增长的生产能力曾令世界惊喜,但其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注定不可持续[40]。现实表明,在人口数量急剧膨胀、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日益加剧、农作物品种多样性日渐减少的当下,世界粮食安全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41]。
种子开源可以激活种业领域创新,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受制于以水土资源为代表的农业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通过种子创新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的作用日益凸显。遗憾的是,在知识产权推动的全球种子市场的整合进程中[42],种业企业经过不断的合并或兼并,种业市场已经演进到寡头垄断阶段[43]。此种情形提高了中小企业参与种业市场竞争的门槛,限制或窒息了育种领域的竞争,影响了育种创新。保障粮食安全需要种业领域的有效竞争,需要优良品种持续供给。种子开源能消除中小育种者获取育种材料和技术的障碍,减少育种投入成本,激活育种者创新潜能,培育更多优质品种,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种源保障。
种子开源有利于保存并丰富农业作物品种多样性,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丰富的作物品种不仅能满足不同生态场所和耕作制度的种植需求,更是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基础。但是,本来是保护育种成果、促进育种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却对物种多样性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生物技术创新所开发的“有益新物种”可能对其他物种产生竞争优势,进而人为地淘汰其他物种,导致生物多样性发生无法挽回的损失[44];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促使少数“精英”高产品种被广泛种植,造成大量传统作物品种消失(8)据世界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由于高产作物对小众谷物品系种植空间的驱逐,在过去100 年间,世界上已有超过90%的农作物品种从农田中消失。我国从1956年到2014年丧失71.8%地方谷物品种数目。,影响了未来种子供应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作为修正知识产权排他性的种子开源,能减弱知识产权对生物多样性的消极影响。首先,种子开源消除了包括农民在内的众多中小育种者获取育种遗传资源的障碍,为育种者改良已有品种、选育更多优质品种和增加作物多样性创造了条件。其次,种子开源为培育适应地方气候的品种提供了便利。在开源体系下,育种者贡献其现代育种技术,农民则贡献农民品种、育种经验及地方知识,基于此方式产生的育种成果具有适应地方气候的优点,对保存区域遗传资源,维护地方生物多样性具有积极作用。最后,种子开源组织出于丰富育种所需种质资源的需要,会收集和保存已有种质资源,这也有利于维护农业作物品种多样性。
三、种子开源的实践模式
种子开源的实践始于美国,此后在德国、印度、荷兰、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均有不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9)如美国OSSI组织、荷兰HIVOS计划、德国种子公地计划(OSS)以及印度APNA BEEJ“开源种子网络”等。。此外,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的开放存取系统已经有效地应用于作物改良[45]。目前种子开源实践大体有如下三种模式。
1.道德承诺模式
美国开源种子倡议组织(open source seed initiative,OSSI)是种子开源道德承诺模式的代表。鉴于知识产权对种质资源取得和育种发展的阻滞作用日益凸显,2012 年,基于创建“受保护的种子公地”(10)该构想最早由CAMBIA 组织的Richard Jefferson 所提出,意在将生物技术和研究与“支持运营自由和合作自由”的 “Copylef” t许可协议相结合,以创建“受保护的植物种质公地”,受保护的种子公地准许公众自由访问和优化资源,且不会对下游使用施加任何限制。的构想,由包括植物育种者、农民、种子公司和可持续发展倡导者在内的主体组建了非盈利性的OSSI 组织。该组织最初以开源软件的 “Copylef” t许可证为蓝本,采取种子开源许可证的模式,但冗长的许可证文本被参与者认为过于复杂而不具有实用性。OSSI 组织者在征询开源参与者的意见后,选择了道德承诺模式,用誓言取代许可证(11)OSSI承诺:您可以选择以任何方式自由使用这些OSSI誓言下的种子。作为回报,您保证不通过专利或其他方式限制他人对这些种子或其衍生物的使用,并将此承诺包括在这些种子或其衍生物的任何转让中。,并专门组建开源社区和网站以推动开源种子不受限制的交换流通[9]。
OSSI 组织所确定的目标是促进植物种质的共享,支持并认可育种者的工作,鼓励多元和分散化的种子产业。实现上述目标的核心策略在于不断扩大组织影响力和增加承诺开源作物的数量和使用范围。对农民、园丁和育种者,OSSI 承诺可以自由使用开源作物进行种植和改良,以此扩大“承诺”种子的使用。对开源品种贡献者,OSSI组织承诺品种贡献者可与有意向以商业方式销售开源品种的种子公司缔结独占销售合同,以确保公平的利益分享和育种回报。但要求此类约定仅对缔约双方有约束力,不得限制其他开源种子使用者(12)见OSSI发布《开源种子计划品种指定协议》,https://osseeds.org/pledge-a-variety-to-ossi/.。对种子销售公司,OSSI 组织以合作者的身份将建立的开源种子网站与销售开源种子公司的网站关联,通过OSSI网站和宣传材料,将农民和园丁引导到与其合作的种子公司,拓展合作公司的业务。OSSI 组织通过建立开源种子贡献者和销售渠道的开源社区,不但为参与者提供了开源种子的释放机制,而且使育种者贡献获得社会认可,以此鼓励育种者和种子公司使用 “OSSI承诺”释放种子,不断扩大开源种子库[5]。
总的来说,OSSI组织成功开创了基于道德承诺的“自由种子”(13)使用OSSI-承诺的种子被称为“自由种子”,而不是“免费”种子,以强调OSSI-承诺种子在使用方面是自由的,但不一定在价格上是免费的。参见:https://osseeds.org/the-open-source-seed-initiative-growing-access-to-a-liberated-domain-of-plant-genetic-diversity/.释放机制,从实践效果看,该组织在成立数年内便拥有相当数量的开源品种和合作的育种者与种子公司(14)截至2021 年7 月29 日,OSSI 组织有415 个质押种子用于开源,38 位育种者和61 家种子合作公司,数据来源:https://osseeds.org/.。但不可忽视的是,道德承诺的种子开源模式能顺利推行原因之一在于美国事实上对种子繁殖和销售没有法律上限制,中小育种者可以自由出售种子,这为种子开源中至关重要的开源种子交换扫清了法律障碍。但受各国法律制度差异影响,OSSI模式很难适用其他国家。
2.许可证模式
德国是种子开源许可证模式的代表。2017 年4 月,德国非政府组织Agrecol 发布了开源种子(open source seeds,OSS)许可证,该组织在成立初期通过联系使用公共资金的育种机构取得了丰富的开源种质。OSS 许可证赋予被许可人自由使用开源种子进行生产、交换和改良的权利,与此同时,被许可人有义务将其获得的种质及其衍生物传递给其他使用者。此方式使开源种子进入“受保护的公地”从而无法再被私人占有(15)见OSS组织开源种子许可证说明:https://opensourceseeds.org/en/open-source-seed-licence.。因此,从运行上看,OSS 许可证会产生开源种子的链式反应,只要有第一个许可就会发生后续许可,即被许可人成为许可人,以相同的许可传递种质资源。
OSS 许可证本质上是植物种子和部分组织的材料转移协议,在法律上属“专门合同”,适用德国民法典所规定的“一般交易条款”(16)《德国民法典》第二编第二章:一般交易条款(General Business Terms and Conditions):305 条:一般交易条款是所有为数量多的合同而预先拟定的由合同当事人一方(使用人)在合同订立时向合同当事人另一方提出的合同条款。。依照法律规定,一般交易条款使用人需负担提示说明的义务,确保相对人知悉或有知悉的可能,且需经相对方同意[46]。只要符合上述规定,任何种质转移的行为均可获得法律承认。为确保接收方悉知OSS许可证有关条款和内容,该组织针对不同规模的开源种质转移分别制定了告知模式:对于零售贸易商,需在小包装上印刷节选版的OSS许可证,并提供的完整电子版本;对于大批量使用者,则需确保育种材料随附许可证的副本一并送达,并明确告知被许可人有关该种质的权利义务会延及所有的衍生物和复制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OSS 许可证将检举违反开源条款的行为纳入该协议的义务,以确保种子开源条款(17)OSS 许可证防范和追查开源侵权的主要工具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之名古屋议定书》规定的用于新品种审查的种质文件:植物遗传资源的使用者必须记录获取的时间和地点,并在适当的情况下,还要检查“与获取和惠益分享有关的权利和义务的存在与否”。获得法律保护并在欧盟范围内得到强制执行。
OSS 许可证作为一种新模式面临法律和资金两个现实问题:一是作为一种法律工具,可能与现有种子法律冲突。根据欧盟法律规定,相关作物的种质只有在品种获得欧盟委员会植物品种数据库中注册后,才能合法流通。《德国种子营销法》所规范的种子和欧洲植物品种保护法所保护的品种均需在欧盟委员会植物品种数据库中注册,其品种释放与OSS许可证没有冲突。但不满足品种授权标准而无法获得品种权保护的种子,因其无法注册而难以流通(只能少量交换),影响了开源种质资源的丰富性,与OSS 许可证的目标冲突。二是非基于知识产权许可费的融资模式,难以满足未来开源植物育种的资金需要[12]。
3.农民合作模式
菲律宾的MASIPAG组织是种子开源农民合作模式的代表。19世纪80年代,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和部分科学家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民进行走访调研,以评估农户损失和稻米生产状况,并同农民协商对策。在众多农民团体的支持下,经过一系列协商,被称为 “BIGA” S的全国性会议最终于1985年召开,并在该会议上宣布组建MASIPAG组织(18)见MASIPAG组织介绍,https://masipag.org/about-masipag/.。
MASIPAG聚焦于水稻种植和培育,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寻求农民的全面发展以及维护农业作物多样性为目标。该组织成立初期便建立了以农民为主导,包括非政府组织、教会组织、科学家在内的种质交换合作网络,利用自有农场进行育种和品种维护,以近乎免费的方式为农民提供水稻种子,形成了与现代主流农业生产不同的模式。尽管稻米种子交换网络已初具开源模式雏形,但该组织直到2019 年才正式提出稻米种子开源(19)MASIPAG 全国办公室2019 年10 月22 日发布《Farmer’s seeds,grains of liberation!》,https://masipag.org/2019/10/farmersseeds-grains-of-liberation/.。该组织通过在农民群体中培养育种者并推广育种技术,借助自有农场和国有后备农场维持传统品种的延续,选育了一批耐洪、耐寒和抗病虫害的品种,以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20)该组织收集和维护了1313 个传统水稻品种(TRV)和105 个传统玉米品种;1288 个MASIPAG 水稻与506 个农民培育的水稻(农民品种)并建立了188个MASIPAG 试验农场中每个试验农场。见https://masipag.org/programs/.。肯尼亚的种子保存网络也是一种农民合作模式的种子开源。该组织在荷兰HIVOS 组织“开源种子系统计划”支持下(21)HIVOS 开源种子系统(OPEN SOURCE SEED SYSTEMS)项目(该项目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及国际生物多样性组织资助),见https://hivos.org/program/open-source-seed-system/.成立,尝试与育种者、农民合作,并通过倡议多方利益相关者开发“受保护的种子公地”取代知识产权的排他性保护,以保存和共享传统种子。农民合作模式的实践证明,种子开源在减少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22)例如HIVOS 组织在包括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运行的该开源种子保存计划吸引了10 家种子企业帮助农民保存种子,为2000 名农民带来了适应地方气候的豆类、高粱和小米的新品种,为40000 名农民、研究人员和种子检查员创建一个无专利种子的数字交流平台。,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该组织重点关注的是保障低收入农民获取种子以维系生计,而非促进育种发展和种质资源流通,并且受制于育种技术水平,现有开源品种大多是基于本土品种选育,并未同域外科研机构或国际组织形成有效协作。
四、结论与讨论
种子开源的理念和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尚属新兴事物,从已有的实践和经验看,种子开源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一种补充和修正,其所秉承的自由、开放、共享的理念符合育种领域的创新特点与需求。我国目前对种子开源尚处在理论探索阶段,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促进育种创新,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可参考域外实践经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种子开源模式。
从域外经验看,种子开源的实践大多停留在育种遗传材料本身的开源,即种质的开源。然而随着育种技术在培育新品种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将其纳入开源体系实有必要,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育种资源整合,促进育种创新。我国拥有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在内的数量庞大的受政府公共财政资金资助的育种机构,农作物新品种选育主要依赖于这类机构[47],并且在获植物新品种授权的主体结构中,这类机构的占比较大(23)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指数报告(2020 年)》:2019 年的品种权授权量中,教学科研单位占国内授权总量的43.12%。。因此,可尝试在高校、科研院所中实行许可证模式的种子开源。同时,鼓励其他育种者和农民加入开源组织,贡献其种质资源和育种经验。
种子开源具有广阔的前景,也会面临法律规则的挑战。根据我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或林木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推广;应当登记的农作物品种未经登记的,不得推广。对于没有审定和登记的品种能否开源,尚需品种管理制度予以回应。种子开源对专利制度的挑战在于,开源会导致未获专利保护的材料或技术过早进入开源体系而丧失新颖性,使其无法取得专利,此种“开放悖论”[48]的潜在风险会阻碍育种研发者的公开其材料或技术。因此,倘若实施种子开源,尚需专利法对此进行回应,如将因开源所导致的公开作为丧失新颖性的例外[49]。种子开源对于品种权制度的挑战在于,种子开源会导致修饰性育种,产生实质性派生品种。为保护原始品种权人的正当利益,阻止修饰性育种,促进育种原始创新,我国新修改的《种子法》(2021年12月24日第三次修正)新增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规定,即实施实质性性派生品种应当征得原始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同意。但现行规定太过简单,无法落地实施。因此,目前亟待相关部门制定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办法,对诸如实质性派生品种的技术规范、判定标准、判定机关等加以明确。此外,我国参照UPOV1978 文本制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未引入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因此,修订该《条例》时应引入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并协调好与《种子法》的关系,共同为种子开源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总之,种子开源是当下和未来育种创新的一个积极且有益的方向,如何化解此种育种创新模式同现有制度的冲突及其潜在风险尚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