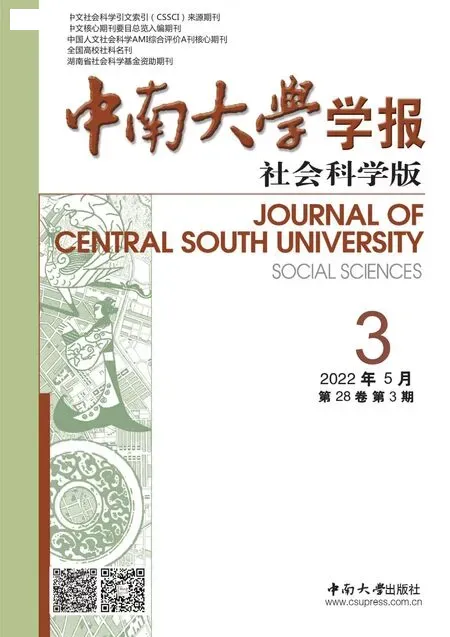康德“促进至善是人之道德义务”命题的义理基础与实践指向
2022-11-23朱毅
朱毅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在康德伦理学中,至善(summum bonum)被界说为纯粹实践理性对象的无条件总体[1](115)。至善是一种“完整的和完满的善”,在内容上确立起德性与幸福先天联结的必然性,同时兼顾人的“自然目的”与“道德目的”,使这两种“善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of the good)[2]得以协调和统一。当然,在康德的理解中,至善中的德性与幸福地位并不对等,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至上的善(作为至善的第一个条件)构成道德,与此相反,幸福虽然构成至善的第二个要求,但却是这样构成的,即幸福只不过是前者的有道德条件的、但毕竟是必然的后果。惟有在这种隶属关系中,至善才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全部客体”[1](126)。因此,至善对人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德性与幸福始终无法获得精确匹配的一致性,我们只能在来世预设“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才可能期望实现至善。至善由此从道德领域延伸到宗教领域,并在后 一个领域中作为人的“希望的对象”。康德至善概念的理论底色,始终兼具道德与宗教两重维度。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对至善问题的讨论始终坚持一个核心观点:我们每个人都负有“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这一说法以各种形式频繁出现在其文本之中。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就提出,“我们应当力求促进至善”,“对我们来说,促进至善本就是义务,因而预设这种至善的可能性就不仅是权限,而且也是与作为需要的义务相结合的必然性”[1](133)。在《判断力批判》中,他也强调:“道德法则作为应用于我们的自由的形式上的理性条件,独自就使我们负有义务,无须依赖某个目的作为质料上的条件;但是,它毕竟也为我们乃至先天地规定了一个终极目的,它使我们有义务追求这一目的,而这一目的就是通过自由而可能的尘世中的至善。”[1](469)然而,对于“促进至善”作为人的道德义务的根本原因,康德的解释看起来非常简单:“把至善设定为我们追求的对象,是道德法则使之成为我们的义务的。”[1](137)“促进至善”之所以是人的道德义务,似乎仅仅源自纯粹理性道德法则的实践要求,“道德法则命令,要使一个尘世中可能的至善成为我的一切行为的最终对象”[1](137)。
而事实上,康德并未以任何形式从道德法则中直接推演出“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和《道德形而上学》中,他根本没有提及至善的内容。即便在涉及至善问题的其他文本中,康德也没有着意论证“促进至善”作为人的道德义务的理论根据。这就不免让人疑惑:既然康德明确提出了“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但为什么这个义务与道德法则的关系却并不明朗?学者Murphy 也注意到,康德似乎更倾向于直接把“促进至善”作为某种对基本道德法则的意识(或另一种道德经验的事实),并未打算从任何既定前提中演绎出这个义务[3]。
或许正是因为缺乏对这个问题的充分阐释,不少研究者直接质疑“促进至善”作为人的道德义务的合理性,并且质疑至善概念在康德伦理学中的重要性。对此,本文将首先展示学界围绕康德至善概念的相关争论及存在的问题,然后另辟新径,通过深入解析至善与道德法则的内在关联,探究康德为何把“促进至善”设定为人的道德义务,以及他设定这一特殊义务的理论特质和实 践意义,从而论证此说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合理性。
一、学界对康德命题的质疑
对康德的“促进至善”之为人的道德义务说,不少研究者在学理上表示质疑。概言之,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促进至善”不可能是人的道德义务,这一设定在逻辑上与康德主张的“应当蕴含能够”(sollen impliziert können)的核心观点不符。纯粹理性颁布的道德命令,规定的必然是可行的道德义务,不能超出人的道德能力的可控范围,而至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理念,其本身内含超越性,无法成为我们道德实践的对象。由于至善的实现不是在现世中,而是在来世中才是可能的,且必须依赖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形而上学悬设。因此,倘若“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那么康德实际上自相矛盾地提出了一个无法完成的义务概念[4]。
其次,即便“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说能够成立,这个义务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实践意义依然是含混和模糊的,因其并未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去“促进至善”。学者Auxter 就认为,如果“促进至善”是一种道德实践的规范,那么它对人们提出的规范性要求是不清晰的,“至善是一个模糊且令人困惑的观念,无法有效地关联任何分辨对错的行动。至善对人的实践判断和行动来说不是一个可能的理想,因为它不符合通过自由而产生可能性结果的条件。它不能帮助我们评价自由和能力,它超出了我们的自由能力”[5]。
再次,“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这种说法本身在概念上就自相矛盾。一方面,义务意指“一个客观法则与一个意志的关系,这个意志就其主观性状来说并不必然为这个法则所规定(一个强制)”[6](420),义务概念就其本义而言蕴含一种行动“非此不可”的道德强制性。另一方面,至善是一个理性存在者在完善意愿中必然指向的对象[1](118)。假如把至善与义务对接起来,那么“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似乎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以“自我强制”的方式促成和实现一个理想性的目的。这种说法听起来非常奇怪,因为倘若“促进至善”对人而言是一件“喜闻乐见”之事,那么我们并不需要为之额外附加某种“强制性”,或者说没有必要以道德的方式强制任何一种理想或希望。正如康德所言,“一个要人们乐意做某事的命令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我们已经自发地知道我们有责任去做什么,如果我们除此之外也意识到自己乐意去做此事。这方面的一个命令就是完全不必要的”[1](89)。
相对于上述质疑,康德哲学的经典诠释者Beck 的质疑更全面也更具代表性。在他看来,康德在道德哲学中引入至善概念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其一,这将损害康德意志自律的核心立场;其二,道德法则“绝对命令”所规定的内容并不涉及至善,至善也不包含在“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概念之中。因此,要么根本不存在“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要么这个义务不过就是道德法则已经规定过的内容:“假如我竭尽全力——这是一切道德诫命所能要求于我的全部东西——促进至善,我将要做些什么呢?只有出自对法则的敬重而行动,对此,我早有认识。”[7](302)不仅如此,Beck 还认为:“至善的概念并非实践概念,而是理性的辩证理想。就它可能具有的实践后果而言,它在康德哲学中并不重要。”[7](302)
针对Beck 的批评,不少研究者曾尝试为康德提供辩护。其中以Silber 的研究最为典型。一方面,他通过论证至善为形式的道德法则增添质料性的内容,以显明至善在康德伦理学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试图将康德的至善进一步区分为两个互为关联的不同层面,即“内在的至善”(immanence of the highest good)和“超越的至善”(transcendence of the highest good)[8]。在他看来,前一种至善隶属于现象世界,是人的道德能力可触及的范围,因而“促进至善”对人而言是道德义务;后一种至善隶属于超越的本体世界,不是人的道德实践的对象,而是评价一切自由实践的理想标准,对至善的促进不能作为人的道德义务。
这种区分方式深刻影响了之后不少诠释者的理解。以Reath 的观点为例,他认为康德的至善概念蕴含“宗教(神学)”和“世俗(政治)”两重维度[9]。其中,作为“宗教(神学)”维度的至善,描述的是一个在彼岸世界中德性与幸福相统一的理想状态;作为“世俗(政治)”维度的至善,描述的则是一个在此岸世界中通过人类伦理共同体的构建可能达成的最终目的。Reath 认为,康德实际上在后期哲学的发展中逐渐放弃了“宗教(神学)”维度的至善,转向“世俗(政治)”维度的至善。与Silber 的观点类似,他也主张应该在至善的“世俗(政治)”维度之中才能有意义地讨论“促进至善”这个道德义务。
本文认为,上述有关“促进至善”能否作为人的道德义务的争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其论点都建立在一个相当可疑的基础上,即“应该蕴含能够”。按照这个标准,“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唯有在至善目的具有实现可能性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因而不少研究者不得不放弃至善内容的完整性,以此为代价来论证“促进至善”作为人的道德义务的合理性。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康德设定“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的出发点与人是否有能力实现至善无关。事实上,他一再强调一切对道德义务基础的论证和阐明都不能依据经验性的原则:“责任的根据在这里不是在人的本性中或者在人被置于其中的世界里面的种种状态中去寻找,而是必须先天地仅仅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去寻找。”[6](396)也就是说,纯粹理性法则对人的意志规定是无条件的,不以人的主观道德能力的实际大小或在世的客观状态为标准:“理性不依赖于任何显像独自地要求什么应当发生,因此,对于世界也许迄今还根本没有提出过实例的那些行为,把一切都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人甚至会怀疑其可行性,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为理性所严厉要求的。”[6](414)正如尽管在现实中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过真诚的朋友,这也丝毫不减弱理性无条件地要求我们在友谊中保持纯粹的真诚。
因此,从康德的至善概念中区分出不同的维度,这对于全面把握这个概念的复杂内涵或许是重要的,却无助于澄清康德设定“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的理论根据。为探明这一学理奥秘,我们必须另辟新径。
二、康德命题的义理基础
如前所述,虽然康德明确主张“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但他并没有直接从道德法则中推演出这个义务。对此,有学者试图完成康德没有完成的工作。例如,在Alonso 看来,至善是一个通过道德法则被构建起来的对象。他依据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至善概念的相关描述,同时对比了《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提出的“目的王国”,认为二者在义理上都是相通的,均指涉一个被道德法则构建起来的道德世界。在这个理知世界中,每个理性的道德存在者在理想状况下都严格遵循道德法则的规定。因此,既然至善被理解为一个理想中的道德世界,那么至善就是道德法则所建构出来的结果。这就能很好地理解为何每个人都负有“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因为在这个理想道德世界中,我们都负有建立和维护好这个世界的责任[10]。
将至善理解为一个理想中的道德世界,这确实能够在康德的相关文本中找到依据。但是将“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简单还原为对道德法则的严格遵守,却并不符合康德的原意。在康德看来,道德法则对人的意志的独立规定直接指向的对象是道德本身,而非任何可能的实践结果。换言之,道德法则直接规定的是人的道德目的,即德性的完善,并不同时确保人的自然目的(幸福)的实现。因为“道德法则独自说来毕竟不应许幸福”[1](136)。然而,至善概念作为德性与幸福相统一的理念,一开始就必然关涉道德目的与自然目的,因而它不可能是道德法则的直接对象。这样,“促进至善”就不能简单还原为人对道德法则的严格遵守。另外,既然在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中,每个人已经能够自觉地遵守道德法则,那么从“应然性”的角度提出“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对个人而言似乎就是不必要的。
虽然Alonso 的观点存在明显的缺陷,但他把康德的至善理解为一个被道德法则构建起来的理想道德世界,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促进至善”作为人的道德义务的缘由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康德始终认为:“至善是在道德上被规定的意志先天被给予的客体。”[1](121)至善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是道德意志的一个先天必然的客体?对此,康德给出过一个很特殊的解释:
尽管至善是一个纯粹实践理性,亦即一个纯粹意志的全部客体,但它并不因此就能被视为纯粹意志的规定根据,而惟有道德法则才必须被视为使至善和至善的造就或者促成成为自己的客体的根据。
但不言而喻的是,如果在至上的概念中道德法则作为至上的条件已经一起包含在内了,那么,至善就不仅仅是客体,而且是就连它的概念以及它通过我们的实践理性而可能的实存的表象,也同时会是纯粹意志的规定根据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在这个概念中已经包含并同时被想到的道德法则,而不是任何别的对象在按照自律的原则规定着意志。[1](116−117)
在上面两段表述中,康德一方面强调道德法则是纯粹意志的规定根据,另一方面又补充说,当道德法则作为“至上条件”已经包含在至善概念之中时,至善也可以成为纯粹意志的规定根据,而这并不损害意志自律的最高原则。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康德实际上已经有条件地承认并肯定了至善作为纯粹意志规定根据的合法权利。根据这个解释,对纯粹意志而言,其实际指向的对象就不止一个,而是两个:一是当道德法则独立地规定意志时,意志直接指向的对象就是行为的道德性;二是当至善以道德法则为条件规定意志时,意志指向的对象还包含至善。显然,以道德法则为前提,至善概念中的幸福要素已经被间接地纳入意志的规定根据之中了。因此,康德意志概念的对象应该指向两个维度:一是以纯粹理性的道德法则来规定自身,促成意志的道德自律;二是以道德法则为根据,将德性与幸福相统一的至善作为意志追求的最终目的。
就此而言,若要对纯粹意志进行一种彻底而完整的规定,道德法则与至善均不可或缺。康德还特别强调了二者彼此密不可分的关联性:
既然对在自己的概念中包含着这种联结的至善的促进是我们的意志的一个先天必然的客体,而且与道德法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前者的不可能性必定也证明后者的谬误。因此,如果至善按照实践规则是不可能的,那么,要求促进至善的道德法则也必定是幻想的,是置于空的想象出来的目的之上的,因而自身就是错误的。[1](121)
在康德看来,虽然道德法则始终是至善存立的关键,至善也必须以道德法则为前提才能合法地规定意志,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预设至善的可能性,才可能真正完成理性对意志的完整规定,否则道德法则自身将陷入谬误。这就说明至善这个理想性的目的,必须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意愿,包含在道德法则对意志规定的过程中。也就是说,至善是人的理性道德意识所映射的一个背景性条件。康德自己的说法也可以很好地佐证这一点:“在实践的原理中,道德意识和对作为道德的后果而与道德成比例的幸福的期待之间,一种自然的和必然的结合至少是可以设想为可能的(但当然还并不因此就是可以认识到和看出的)。”[1](126)这里提到的“道德意识”和“与道德成比例的幸福的期待”广义上均属于理性主体的内在意识。前者作为原因,是对道德法则无条件的遵循;后者作为结果,则是由道德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对至善实现的期待。因此,唯有至善在原初意义上内嵌于理性主体内在的道德意识之中,道德意识的产生才可能伴随着对至善的追求。基于此,康德认定,以道德法则为“至上条件”的至善,能够且应当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至善是纯粹意志的一个先天必然的客体。本文认为,这才是康德设定“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的根本出发点。
至善与道德法则紧密相连的关键在于至善必须在原初意义上已经内嵌于理性主体的道德意识之中,并因此获得规定意志的合法权利。然而,“促进至善”为何自始就内嵌于理性主体的道德意识之中,这还有待进一步解释。
关于这一点,我们发现,康德实际上早在第一批判首次论及至善概念时,就暗示过了。在“纯粹理性的法规”中,康德把至善视为“纯粹理性终极目的之规定根据”。在他看来,纯粹理性(理论的和实践的)运用的全部旨趣最终可归结为三个根本问题:①我能够知道什么?②我应当做什么?③我可以希望什么?其中,第一个问题涉及理性的思辨运用,与认识论相关;第二个问题涉及理性的实践运用,与伦理学相关;第三个问题则是在第二个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果我现在如此行事,使我并非不配享幸福,我如何也可以由此能够享有幸福呢?”[11](516)对此,康德的回答是:唯有当“道德性的体系与幸福的体系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时,“每一个人才有理由依照他在行为中使自己配享幸福的同等程度来希望幸福”。这里必须预设“一个统一的纯粹理性的理念”,这个理念正是“至善的理想”[11](516)。对于这个特殊理想,康德是这样描述的:
如今,在一个理知的世界里,也就是在一个道德的世界里,在一个我们从其概念抽掉了一切道德性的障碍(偏好)的世界里,这样一个与道德性相结合成正比的幸福的体系也可以被设想为必然的,因为部分地为道德法则所推动、部分地为其所限制的自由就会是普遍的幸福的原因,因而有理性的存在者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本身就会是其自己的、同时也是别人的持久福祉的创造者。[11](516−517)
不难看出,在康德对至善原初的构想中,至善一开始就被标识为一个理知的道德世界,其特别之处在于:尽管这是一个由道德法则建构起来的理想世界,排除了所有可能的“道德性的障碍(偏好)”,每个人都自愿遵守道德法则,但这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并不单纯指向道德,而是还指向与道德相关的幸福,它是一个“与道德性相结合成正比的幸福的体系”。因此每个理性的道德存在者既是自我也是他人“持久福祉的创造者”。在这个意义上,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相统一的理想,就构成每个理性的道德存在者普遍意愿的共同目标。
尽管这还只是一个有关至善概念的理论构想,但康德认为,这种纯然的理念设计并非旨在满足某种虚妄的思辨意图,而是有其鲜明的实践指向。他紧接着就说:“一个道德世界的理念具有客观的实在性,不是好像它指向一种理知直观的对象(诸如此类的对象我们根本不能思维),而是指向感官世界,但这个感官世界是作为纯粹理性在其实践应用中的一个对象。”[11](516)这就是说,至善作为一个理想中的道德世界,始终指向的是现实的感官世界,因此它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或意图之中,必须在感官世界中被真正地实现出来。换言之,对每一个理性的道德存在者而言,至善是一个在现实中有待被开辟出来的未来的道德世界。“我们必须以必然的方式通过理性把自己表现为属于这样一个世界的,即使感官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显像的世界,我们也必须假定那个世界就是我们在感官世界中的行为的一个后果,而既然感官世界并未向我们呈现这样一种联结,我们就必须假定那个世界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未来的世界。”[11](517)
在第二批判中,康德以另一种表述形式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道德法则为我们敞开了一个纯粹的知性世界,并积极地规定着这个世界。同时,“这个法则应当使感官世界作为一个感性自然(就有理性的存在者来说)获得一个知性世界,亦即获得一个超感性自然的形式,却并不损害感官世界自身的机械作用……所以,超感性自然就我们对它能够形成一个概念而言,无非就是一个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之下的自然。但是,这种自律法则就是道德法则,因而它就是一个超感性自然和一个纯粹知性世界的基本法则,这个世界的倒影应当实存于感官世界中,但同时并不损害感官世界的法则”[1](46−47)。这里表达的基本意思与之前是一致的:通过道德法则,我们被置入一个理知的世界之中,而这个世界应该以“倒影”的形式实存于感官世界,从而使“感性自然”获得一种“超感性自然的形式”。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唯有通过每个理性存在者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
因此,倘若至善被理解为一个理想中未来的道德世界,而这个世界必须在现实世界之中被实现出来,那么就可以合理地推论,对至善的促进,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至善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愿景,实际上就像指南针一样,在终极意义上为我们一切可能的道德实践提供了不断前进的目标和方向。假如独断地否定至善理想及其可能性,那么势必导致纯粹的实践理性对感官世界的整体运用从根本上失去意义,理性道德意志的行动也将沦为一种相当怪异的实践方式,即“为道德而道德”,“为义务而义务”。因此,康德认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一种需要乃是基于一种义务的,即是使某种东西(至善)成为我的意志的对象,以便尽我的一切力量去促成它;但我在这里必须预设它的可能性……否则的话,竭力追求一个其实空洞和没有客体的概念的客体,就会是实践上不可能的。”[1](151)
三、康德命题的实践指向
我们认为,康德其实并不打算从道德法则的“绝对命令”中直接推演出“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这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是一个未经任何证明的独断设定。但实际上,康德设定这个义务有其更深层次的理由:至善作为一个理想中可能的道德世界,实际上已经作为一种普遍的意愿内嵌于理性主体的道德意识之中了,从而构成我们一切道德实践所必须预设的背景性条件。因此,以道德法则为基础的至善,能够且应当作为意志合法的规定根据。就此而言,现实中我们履行的种种不同类型的道德义务,本质上都共同指向一个统一的目标,即“促进至善”,为的就是要让那个在理想中的道德世界,从观念走向现实,真正实存于现实世界之中。
反观Beck 的观点,他的判断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即“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并未额外添加任何新的实践内容,也没有独立于道德法则的“绝对命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可有可无。接下来,我们将展示“促进至善”这个道德义务的独立特质,进一步显明它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实践意义。
康德在《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指出,为实现道德的本真性,我们在任何时候“无论是为了认识什么是义务,还是为了敦促人们去履行义务,都不需要一个目的”[12](4−5),因为从任何经验性的质料目的中都不可能确立起真正的道德,这将损害意志的自律性。但同时康德补充道:
从道德中毕竟产生出一种目的,因为对于理性而言,回答“从我们的这种正当行为中究竟将产生出什么”这个问题,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以及即使此事并不完全由我们掌握,但我们能够以什么作为一个目的来调整自己的所作所为,以便至少与它协调一致,这些都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虽然这只是一个客体的理念,这个客体既把我们所应有的所有那些目的的形式条件(义务),同时又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目的的所有与此协调一致的有条件的东西(与对义务的那种遵循相适应的幸福),结合在一起并包含在自身之中。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尘世上的至善的理念。[12](5−6)
尽管不同类型的道德义务指向的规范性内容不尽相同,道德行动的实践结果也不一样,但在康德看来,不仅意志就其本性而言不能没有目的,而且我们的一切道德实践不能永远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它们必须依据一个客观的目的理念被系统联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共同朝向一个方向迈进。否则,只是为了追求道德行为的正当性,那么这些自由的道德实践本身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就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道德义务与目的依然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而这个目的就是“一种尘世上的至善的理念”。这个整体性的目的理念之所以必要,康德之后在论及人类伦理共同体的概念时说得很清楚:“因为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每个物种在客观上,在理性的理念中,都注定要趋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促进作为共同的善的一种至善。”[12](98)在他看来,仅凭个人自我的道德完善,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实现道德上的至善,所有人都必须为至善这个统一性的目的被联结成一个整体才有可能。从这个角度看,“促进至善”作为人的道德义务,就“不是对人们的义务,而是人的族类对自己的义务”[12](98)。
在此,“促进至善”作为道德义务的独立特质及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至善”是一个整体性的义务,它并不平行或并列于其他具体义务。至善作为最终目的,总体上统摄和引领了一切可能的道德实践,“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对人的其他义务发挥着一种范导性作用,“虽然并不增加道德义务的数目,但却为它们造就了一个把所有目的结合起来的特殊的关联点”[12](8)。也就是说,以促进至善为根本目的,我们可以将所有被先天规定的道德义务系统化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就此而言,康德依据道德法则的立法方式、约束性对象和约束性程度,具体划分的不同种类的义务,在广义上均隶属于“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因为它们除了自身指向的特殊内容外,还在更高的层面上服务于追求至善这一最终目的。对此,Wood 给出的解释很具有参考意义,在他看来:“至善是一个哲学上的理想,它能统一和制约纯粹实践理性的一切目的,并且自身根本不属于‘普遍的理性道德’所认识到的那些义务,故而,只要一个人确实为道德法则要求他去促进的一切有条件的目的而奋斗,那么,在道德上指责他没有把至善本身当作自己行动的对象,就是十分荒谬的。”[13](76)
第二,“促进至善”作为道德义务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它本有的超越性。这很大程度上是由至善概念本身的根本性质决定的。至善是一个超越性的理性理念,并无经验性的对象与之对应,这就促使“促进至善”作为人的道德义务本质上是一个“超出了尘世上的义务概念”[12](8),它不可能像其他具体义务一样,直观地向我们呈现任何具体的规范内容。但基于这个特殊义务的范导性功能,我们也可以把对不同类型的义务的履行过程,同时看成是对至善的促进。毕竟,作为一个有待在未来实现的理想的道德世界,“促进至善”依赖每个人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对至善的促进“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观念中它是一个理想性的目的,在现实中则外化为对不同义务的无条件遵循。正如康德所言,“在实施(nexu effective[效果的联系])中,目的是最后的东西,但在观念和意图(nexu finali[目的的联系])中,它却是最先的东西”[12](8)。
第三,“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与理性的道德信仰始终存在微妙的关联。对康德而言,至善是道德导向宗教的契机,也是其道德神学论证的逻辑起点。康德一度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中,赋予至善概念以超越性的宗教(神学)维度。一方面,为了确保至善最终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在自由的道德实践之外,还必须假定一种来世的生活,相信“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另一方面,一旦这种基于纯粹理性的道德信仰得以确立,康德认为,我们就可以按照与神明的类比来思维自己,努力使自己的意志与上帝的神圣意志保持一致,独立在现世中开启一种善的生活方式[14](283)。与此相应,“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也可被视为是上帝这个最高的存在者颁布给我们的神圣诫命。“我们惟有从一个道德上完善的(神圣的和仁慈的),同时也是全能的意志那里才能希望至善,从而通过与这个意志的一致才能希望达到至善。”[1](136)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为至善理想的实现所做的种种道德努力,从根本上说不仅是为了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世俗愿望,也是为了荣耀上帝创世的终极意图。“创造者的唯一目的既不是人的道德性自身,也不单是幸福自身,而是在世间可能的至善,它就在二者的统一和协调一致。”[14](282)
四、结语
通过对“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的理论根据的分析,可以看到,康德设定这个特殊义务的方式采用的是一种从“目的”到“义务”的独特路径。也就是说,康德并没有从道德法则中直接推演出“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相反,他首先将至善解释为一个理想中的道德世界,而后将这一理想以观念的形式内嵌于理性主体的道德意识之中,从而确立起至善与道德法则规定意志的一致性。这使得纯粹意志的对象在根本上指向两个维度:一方面指向道德本身,另一方面指向德福相统一的至善。当至善理想被理解为一个有待在现实世界中被开辟出来的未来的道德世界时,我们每个人就负有“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
同时也可以看到,“促进至善”作为人的道德义务,本质上是一个“与义务的后果”相关的实践命题,充分发挥着对其他具体义务的范导性作用。通过至善这个整体性的目的理念,将不同类型的义务系统化为一个统一整体,共同致力于理想的道德世界的创建。而从道德信仰的角度看,这正好符合上帝创世的道德意图。这表明,康德不仅在狭义上密切关注着作为个体的人应当如何履行不同种类的具体义务,同时也积极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类在族类意义上如何履行对自己的义务。然而,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如何才能被协调统一起来?“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是否精确契合于康德讨论过的所有义务?这依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究的理论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