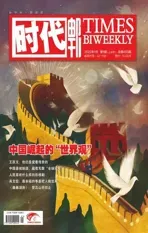“老帮老”平台:让“候鸟老人”此心安处是吾乡
2022-11-23柳昌林刘邓王军锋
● 柳昌林 刘邓 王军锋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2.6亿,老龄化进一步加深,如何养老成为家庭、社会、国家都必须正视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探索一种激活邻里相帮的文化传统,让老人们通过“楼上帮楼下、左邻帮右舍、年轻帮年老、身体好帮身体差”,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海南省定安县夕阳红老年服务中心发起人、负责人付子云、李陈丹通过9年求索实践,给出了一个“答案”。
9年来,两位中年人几乎投入全部身家,搭建起老人之间的互助平台和信任网络,用爱心奉献带动老人志愿服务,通过激发老年人的力量解决养老问题,以极低的成本实现3万老人的居家互助养老。
“所有人都能收获快乐,这就是我的目的”
来自重庆的晏永超2012年就在定安买了房,为他的退休生活做准备。也就是在那一年,黝黑壮实的内蒙古汉子付子云在自家屋顶上和10多位老人开了个会,商量如何激发老年人的力量,免费居家互助养老。
“当时有人劝我加入夕阳红,我就怀疑,为什么不收钱?能有那么多人愿意无偿服务吗?”晏永超说。类似的质疑,付子云和李陈丹早就习以为常。
来自浙江温州的李陈丹,眼神透着坚毅和善良,她是付子云在夕阳红中最重要的伙伴。夕阳红成立之初,即使是她也曾不理解地问付子云:“这么多老人组织起来,对你有什么好处?”付子云说:“所有人都能收获快乐,这就是我的目的。”
每年冬天,晏永超都会从重庆飞到海南住上几个月,他悄悄地以旁观者身份观察着夕阳红。这一观察,就是5年。“5年来,我发现付子云和李陈丹的的确确是在无私奉献,志愿者也是在做无偿服务,他们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2017年,晏永超加入了夕阳红。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定安县夕阳红老年服务中心是一家以坚持“志愿慈善服务、居养结合、互助养老”为宗旨、居家互助养老的非营利民间组织。目前拥有夕阳红社会大学一所,大型艺术团一个,太极、戏曲、民乐、书法、绘画、合唱、模特等50多支小队,骨干成员3000多人。
如果只是让老人们玩得开心,那并不出奇。在发展过程中,针对老人们的突发情况,就医、护理等急难需求,夕阳红成立了一支“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并在33个小区设立“居家康养服务站”,公布志愿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随叫随到。
9年来,在付子云、李陈丹二人感召下,定安县自愿开展居家互助养老的老人,从2012年的10多人,快速增长至近3万人,其中外地候鸟老人占八成,本地县城老人约两成。此外,还辐射带动定安县次滩村、高林村等农村老人的居家养老。
为什么要发起这样的组织?付子云说:“发心起念是想帮助小区里跟我父母一样的老人过更幸福的老年生活,但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是‘被逼的’。”
实际上,逼迫付子云的是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我国城市家庭结构小型化特征明显,“421”结构的家庭增多,2个年轻人既要照顾4个或更多老人,又要抚育下一代,加之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分身乏术,难以兼顾。中国超2.6亿老人、1.8亿独生子女家庭都在关注着敬老养老问题。
“依靠公共资源养老,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想试试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我的私心:我只有一个孩子,我老了以后怎么办?想乘凉,得自己先把树种上,做着做着我自己也就老了,我要老在自己的事业里,老在自己的组织里。”付子云说。
“爱心多了,私心少了”
夕阳红组织里,年纪小的老人不到60岁,年纪大的超过90岁。很多老人每年秋冬都迫不及待地从各地赶来定安,夕阳红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他们“南飞”。
71岁老人胡晓文加入夕阳红后,待在海南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开始只待一个月,现在每年在定安至少要住上5个月。“我是奉献者,也是受益者。声乐、绘画、书法这里都有,这是老有所乐;生病了、水电(设施)坏了,一个电话就有志愿者来帮忙——我深深体会到了老有所依。”
“我是1960年代的兵,我的一生,感触最深的有两件事:学焦裕禄、学雷锋。”77岁老人胡国良说。夕阳红的志愿公益活动,让他感受到了“人人学雷锋”的浓郁氛围。
付子云和李陈丹合作成立了一家小装修公司,9年累计投入260多万用于夕阳红活动场地租赁和老人们集体活动的支出,用老人们的话说,“赔进去几台大奔”。
自愿加入夕阳红的老人越来越多。“我们中很多人都是别人花钱都请不到的人才,为什么投在他俩旗下?他俩无私搭建了这个平台,我们再找他俩要钱,良心上过不去。他俩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晏永超说。
在夕阳红组织“比退休前还要忙”,但大家都乐在其中。夕阳红学雷锋志愿服务队队长王巧玲说:“记得有一个老人摔倒了,生活不能自理。我们就上门帮忙打扫卫生、送饭。虽然互相不认识,但都愿意帮忙。在暮年的路上,我就想着做点善事、实事。他们的品德感染了我,大家相互感染,爱心多了,私心少了。”
面对他们的赞誉,付子云和李陈丹说:“是老人们的无私奉献感动了我俩,给了我俩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
付子云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今年73岁的母亲戴素贞,她也自认是儿子事业的最大受益者。“我浑身都是病,是享了孩子的福,不来定安,没有夕阳红,我活不到这么大岁数。”戴素贞说,“我感觉我儿子做的是好事,大家都喜欢他,别的老人问我‘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教得这么好’时,我就挺高兴。”
“家里要是有一个人反对,不可能坚持那么多年。”付子云的爱人李翠萍说,“我照顾好家里老人和小孩,让他无后顾之忧,让他只要一回头,就能看到我。我和女儿、爸妈、老人们都心疼他。他微信群多,电话也特别多,出去一天,晚上回来嗓子都是哑的。”
为了夕阳红这个“大家”,默默付出的还有李陈丹的“小家”。偶然的机会,李陈丹结识了付子云,双方理念相合,从此为了夕阳红的事业相互扶持,共同努力。
李陈丹有自己的遗憾:“这些年奔波在养老事业中,顾不上陪伴女儿!”她也感觉亏欠了自己的爱人:“他的事业没有做成,我有一半责任。这么多年,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做不成这个事儿。养老事业,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而是一家人在做。”
他们的付出,老人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俩上有老下有小,挣些辛苦钱还都花在我们老人身上,确实感动了我。我儿子女儿每年都跟我说,你就不能不过去吗?我说不行啊,那边有好多朋友等我,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姑娘。”72岁老人闫玉婵说。
付子云和李陈丹最困难的时候,组织活动拿不出500块钱,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老人们说,别借了,这点钱他们出了。付子云说不行,不能收老人一分钱。
“互助这种模式一旦用钱来做,就会变味。一旦变成商业利益关系,这些互助行为怎么定价?这些‘候鸟’人才和志愿者老师,要花多少钱来聘请?一幅字画多少钱,教一首歌多少钱,组织一场活动多少钱,他们的时间值多少钱?这也是拿钱做不好的事情。拿钱买不来真心真情!”付子云认为。
段大成在夕阳红免费教了5年声乐,他认为夕阳红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免费互帮互助的“小气候”。“在夕阳红,我付出没收一分钱,我享受也没花一分钱,我们觉得很自然。”
“很多人看重夕阳红的平台,希望将老人们引流过去,给我俩分红;有商人出地,要与我们合作办收费养老机构;有保健品公司要给我俩钱,希望做这些老年人的生意;还有一些社会捐款。我们都拒绝了,就是要试试,能不能不花钱把养老这件事儿做成!”付子云说。
“养老这个阵地,只能交给党”
2021年4月,付子云和李陈丹各自的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付子云亲弟弟确诊为胰腺癌晚期;李陈丹的丈夫突发中风偏瘫,可能需要长期护理。得知消息后,夕阳红的老师们热心帮付子云联系到北京的专家,给他弟弟做了手术。李陈丹为给丈夫治病,卖掉了在海口的一套房子。经过治疗,她的丈夫能下地走了。“多亏了老师们的帮助,这就是我们做互助养老的‘福报’。”付子云说。
危机虽然过去,但考验仍在继续,最大的考验是经济压力陡增。“现在是最难的时候,但一万个不忍心放弃。我们坚持到今天不容易,相信有一天会好的。”李陈丹说,“我也有这个毅力坚持做下去,实在不行,我想老人们也不会怪我。”
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前路究竟在何方?“作为一名党员,我首先想到的是向党组织求助。”付子云说,“养老这个阵地,只能交给党。如果当地政府能以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予以支持,把我们纳入社区养老的一个环节,作为党群服务的一个实践站,这是上策。”
付子云设想的另一条出路是,从衣食住行等方面为老人们配置养老服务,收取服务费用,如将现有的夕阳红饭店做成“长者食堂”等,以商养“善”,用市场的力量来解决养老问题。
如何找到做公益和做生意的平衡点?如何避免被误解?付子云说要坚持平价、自愿、因需配置的原则,变输血为造血。
展望未来,付子云认为居家互助养老,必须与国家的适老化改造相结合,在小区配置集中互助养老点,解决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通过集中配置护理人员,营造“有暖度的开放式的养老院”,实现“就地就近,在小区里养老”。“这么多条路,根本停不下来。这是利国利民利己的事情,我愿为养老事业贡献绵薄之力,发一点荧光。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方向,我要把它当作一生的事业去做!”付子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