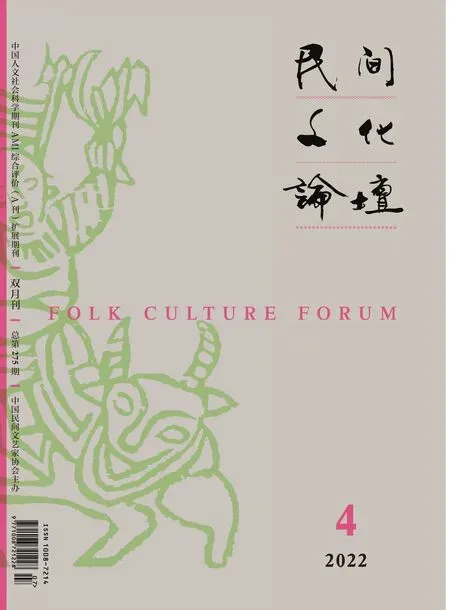替补、主角到配角:地方社会变迁中红薯文化的传播与建构
2022-11-23雷俊霞
雷俊霞
引 言
在中国,红薯又称甘薯、白薯、地瓜、红芋、山芋、番薯、红苕等。①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农林科学院编著:《红薯》,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页。作为百姓的重要粮食之一,曾经是中国南方百姓的淀粉类主食,也被整个中原和华南的百姓食用,历史悠久。但是,它“几乎一开始就是重要的舶来品,似乎在16世纪后半叶传入中国,至1594年已广为人知,当时福建的一位地方官呼吁种植以防饥馑。”②[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5页。作为一种舶来品,它大致通过两条路线来到中国:一是由印度、缅甸传入云南;另一条是由菲律宾引入我国福建沿海。③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农林科学院编著:《红薯》,第1页。在明朝时期,普通大众还不了解这种食物,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时候红薯才广泛种植并大量存在,逐渐成为东部乃至全中国百姓的重要主食。
人类学诞生以来,食物就是人类学家“研究的中心命题或者中心命题的附带存在”④彭兆荣:《品尝:开放的口味与封闭的道德》,《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列维-斯特劳斯关注食物与进食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特纳关注仪式中的食物及其象征意义;古迪开启了食物作为独立表达范式的书写;西敏司认为对糖这种“家用的、日常的物品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世界是怎样从它曾经的样子变为它现在的模样,澄清它在变化的同时又是如何在某些层面上保持内在的一致性的”⑤[美]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朱建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页。。罗安清在松茸所展示的人类与非人类区隔模糊的世界里,探讨人与物之间意想不到的形态。⑥[日]罗安清:《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张晓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54页。这给我们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视域内,认识和把握人们如何以日常物品透视个人、地方社会与国家互动的关系以重要启示。
就红薯文化的研究而言,尤金·N·安德森在《中国食物》里全面梳理了红薯在中国的种植与推广、与中国人的关系、在中国人饮食中的地位。①[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刘东译,第75页。郑南通过对红薯名实辨析和传播途径的考察,勾勒出红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路径,探讨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民众和中国社会的影响。②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57—81页。胡林蔓将红薯作为民族村寨蔬菜品种变迁的重要内容,梳理其在民族村寨与国家互动中的重要作用。③胡林蔓:《民族村寨蔬菜品种变迁的人类学研究——以平善村为例》,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28页。王大宾则将红薯置于农业和景观变化的大背景下,考察红薯种植在人地关系、社会需求等方面的作用,及其对地方农业种植结构的改变。④王大宾:《技术、经济与景观过程——清至民国年间的河南农业》,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14—123页。刘伦文将红薯作为坡脚土家族重要的粮食作物考察土家族的社会与文化变迁。⑤刘伦文:《母语存留区土家族社会与文化——坡脚土家族社区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48页。这些积极的探索与关注,扩展了红薯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红薯在角色演变中如何体现个人、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这是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红薯以备荒救灾的食物、重要的粮食、绿色食品、保健食物等多重角色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替补、主角和配角的角色演变不断通过人们的身体实践和集体记忆建构关于红薯的多重文化符号。基于替补、主角和配角的不断建构、传播与重构,红薯文化作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动态文本,勾连了个人、地方社会与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红薯在人们生活中角色的历次转变,使其既是串联异域与本土的载体,又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动态文本,更是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历史与智慧。这是中国发展的宝贵财富,对当下和未来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替补:“粮食不够红薯来凑”的异域食物传播
红薯文化能够由南向北传播与技术的进步及人们对红薯的逐渐认知有关。红薯能够从南方向北传播,一方面是栽培与储存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是官方的提倡和民众的积极配合。红薯原产美洲,16世纪末经福建巡抚金学曾等人的倡导推广,逐渐在福建、广东等省栽种并推广,并在救灾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后成为南方百姓的主要粮食之一。1608年,江南受灾,经徐光启等人倡导,红薯从福建被引进淞沪,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灾后人民的饥饿问题。红薯适应性强,无论平地与山丘,不管干旱还是潮湿均能正常生长,但是红薯却是在南方普遍传播了一百多年后才传入北方的。其中最主要是技术方面的原因,由于我国北方冬天气候寒冷,留种藏种较为困难,影响了红薯从南向北传播。《农政全书》全面总结了红薯的栽培技术,其中最主要的是留种的两种方法——传卵法和传藤法,并就如何保存种薯和种蔓提出了切实易行的办法——窖藏法,这为红薯文化由南向北传播解决了技术上的瓶颈问题。张光直认为:“它到明朝末年才传到中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水手们把它传到了中国。”⑥张光直:《番薯人的故事》“前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页。尤金·N·安德森认为“白薯在明朝实际上还不为人知,此时(清朝)已大量存在,其传播主要归功于18和19世纪法国传教士的活动”⑦[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刘东译,第89页。。很显然,一种陌生的外来作物忽然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需要一个逐渐认知的过程,传教士的活动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推广认知的作用。
红薯初入中国时,在福建地区曾作为富人茶点类的稀罕物存在。红薯真正被河南民众认可并普遍推广,得益于官方的大力提倡和民间的积极配合。乾隆年间,河南大灾,为救济灾民,“朝廷命闽浙总督雅德将番薯藤种采寄到河南,后又令河南巡抚毕元劝民广为栽种,并令毕元将陆耀的《甘薯录》刊布传抄,广为散发,向民众传播甘薯种植的知识与理念。之后,毕元又聘请陈世元到河南来教种番薯”①胡庭积:《河南农业发展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由于河南灾荒导致饥民无数,在福建备灾救荒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红薯引起了朝廷的关注。陈宏谋于乾隆九年(1744)“明令治下认真引进薯种,教民种植”②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农林科学院编著:《红薯》,第1—2页。。朝廷的重视并责成办理,地方官的积极作为,才有了民众对一种新作物的逐渐认知与接受。19世纪初,红薯种植逐渐向北推广到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地。之后,又向西推广到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最后遍及全国。
回顾河南灾害史,旱、涝、沙、碱等自然灾害频发,其中以水灾和旱灾为主,整个20世纪影响特别大的灾害有五次③管志光主编:《20世纪河南重大灾害纪实》,北京:地震出版社,2002年。:两次大旱灾、三次大水灾。1920年旱灾受灾人口达1500多万,出现“寸草不生,十室九空”的惨状;1942年的旱灾加上蝗灾,导致春秋两季庄稼全部绝收,“辽阔中原,赤地千里”,受灾民众达500多万,其中饿死300多万人。就水灾而言,1933年黄河决口50多处,受灾面积8637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364万,伤亡人数达18293人,出现“流尸千里”的惨状。1938年黄河花园口大决堤,导致89万人死亡,391万人外逃,耕地被淹达177万亩,造成“呼号震天,横尸遍野”的“大浩劫、大灾难”;1958年的黄河大水淹没村庄1708个,灾民74.08万人,淹没耕地304万亩。灾荒时期,人们缺吃少喝,这时对环境适应性强、产量高、营养丰富的红薯成为备灾救荒的一种选择。
20世纪红薯在河南的种植和食用逐渐扩展开来,由民国初年的不足20万亩,1936年达到466.4万亩,总产量达3.33亿公斤;1949年种植面积为897.9万亩,总产量5.25亿公斤。④胡庭积:《河南农业发展史》,第106页。1958年种植面积达2400多万亩,总产量接近60亿斤(折粮);20世纪80年代,红薯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2000万亩左右。⑤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农林科学院编著:《红薯》,第5页。红薯在河南有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由于气候和种植习惯的不同,河南红薯分为春薯和夏薯两种,春薯的生长周期一般在180天,在清明后栽种;夏薯的生长周期约为120天,在芒种前后种植。农民一般会挑选个头大,生长匀称,健康的红薯做红薯母,在惊蛰前后育苗,在温度、湿度合适的情况下,红薯母出苗率很高。打垄、插种、踏实、浇水等环节之后,红薯就开始生长,适时除草,待红薯叶叶相覆、条条相绞时需要翻秧,红薯经过近四个月的生长,待立冬前后,就是杀秧刨红薯的季节。红薯产量极高,干旱贫瘠的山区,亩产可达4000斤左右,土壤肥沃的平原地区亩产可达万斤。立冬之后,红薯大丰收,窖藏法为保存红薯及薯种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办法。“朴素的农民深知,他们无法预测市场的变化,更无力控制市场的活动;他们可以做到的只是以自己的双手生产出足够经受灾难的存粮,这才最安全。”⑥彭兆荣:《饮食人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9页。至此,红薯从“备灾救荒”的替补席逐渐登上生活的舞台,作为主粮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主角”。
二、主角:“没有红薯不能活”的食俗建构
灾荒年代,红薯在中国书写了“红薯汤、红薯馍、没有红薯不能活”的真实生活与集体实践。灾难让人们饱受饥饿的折磨,苦难的生活孕育了人们关于苦难的深刻记忆,灾难记忆里人们有很多关于红薯的美好回忆,苦难书写着红薯曾经救灾救难的辉煌传奇。与红薯文化相伴的日子里,70后、80后成长起来的人们记忆里蕴藏着关于红薯的乡音、乡土与乡愁。
(一)苦难生活与红薯传播
红薯藉由不同路径传入中国。在朝廷、地方官、殖民者、传教士、水手、商人、华侨和中国普通民众等的多方合力之下,红薯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福建和广东为红薯最早传入与推广之地,逐渐从稀罕物成为“贫者赖以充饥”的食物。在因灾歉收和民食艰难的历史时期,清乾隆年间红薯逐渐由福建、广东、云南等地传入广西、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四川;然后继续向北、向西传播,进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和东三省等。红薯的引入,给地瘠、人众、民苦、食艰的中华大地带来了重要的粮食作物。因备灾救荒而在中国全面推广的红薯文化,逐渐成为灾难与饥饿的文化符号深入中国大众的记忆深处。
1958年在老一辈的记忆中印象深刻。在河南,如果某个孩子催饭说自己饿或者吃饭狼吞虎咽,大人常说:“你看这孩子跟58年的饿死鬼托生的一样”。这是个全面受灾和百姓普遍挨饿的年份,也是离现实最近的大灾难之年,大多数七十岁左右的河南老人都刻骨铭心。58年的灾荒和饥饿让全国人民备受饥饿的折磨,红薯为人们提供了能活命的重要口粮。苦难的年代,红薯救命救灾,有了红薯人们不挨饿。
那一年(58年),我差不多有五六岁,天天挨饿,如果能烀一锅红薯,大人小孩就都能吃饱。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清早的馍,洋火盒,晌午的面条捞不着,筷子一掘,捞个红薯叶,筷子一起猛子,捞个红薯梗子。①访谈对象:雷友谊,男,67岁;访谈人:雷俊霞;访谈时间:2019年10月5日;访谈地点:河南淮阳刘大庄。
我们(广东人)管它叫番薯,58年大饥荒,大家都挨饿,那是救命的粮食,番薯、番薯叶都能吃。②访谈对象:何星亮,男,65岁;访谈人:雷俊霞;访谈时间:2021年2月8日;访谈地点:何星亮研究员家中。
红薯好吃啊,那时候饿嘞啥都能吃。我就是不能吃那个苜蓿干,一吃就发晕,恶心,难受。我才十来岁就跟着人家出去干活,吃的饭是胡萝卜段、红薯干搁一起烀嘞。就这能不饿着就已经很好了。58年,那时候粮食一亩地只产百十斤。发大水,红芋窖里红芋都泡烂了,就那都吃完了。大概58年吧,我跟着大男人们去干活,抬泥兜子。换了几个锅饼子。自己舍不得吃,搁裤腰上别着拿回家。俺娘生病了,在俺舅家住着,还病着,没有啥吃,一家人都等着我往家带吃的。锅饼子是红薯干面掺了大蜀黍、小蜀黍糁子捏嘞,就那救活了全家人。③访谈对象:尤凤兰,女,78岁;访谈人:雷俊霞;访谈时间:2017年9月14日、2020年09月16日、2021年1月23日;访谈地点:尤凤兰家中。以上内容是根据三次访谈的内容整理而成。
在最饥饿而又无奈的年份(1958年末),红薯浑身都是宝,红薯块、红薯梗、红薯叶都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救活百姓的重要食物。
饿嘞实在没法子了,大人饿嘞爬不动,小孩饿嘞“喵呜喵呜”嘞。我去生产队场地里扫红薯叶子,好叶子都没有了,都是碎红薯叶子,里面有羊屎蛋子,有坷垃头子。就那拿回家,搁锅里添点水,烀半锅,有稀嘞有稠嘞,大人小孩吃了,就那都能活命。①访谈对象:陈玉亮,男,77岁;访谈人:雷俊霞;访谈时间:2019年8月16日;访谈地点:河南永城陈集镇。
苦难的生活和红薯的甜蜜里蕴藏着百姓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和美好期待。越是苦难,越要力争上游,带着乐观的态度团结一致“撸起袖子加油干”。先进带动和帮助后进,一起克服困难,创造美好生活。
过去的日子哪能跟现在比,(现在)啥吃嘞都有。(那时候嘞)日子不能提,不饿死都不错了。哪想着以后会有现在这样的生活。那时候就盼着红薯能吃饱,能给小孩吃点糁子馍就很满足了。60年大丰收,大家干劲大嘞很,要是看到路上有不干活的人,搁那瞎胡溜,不论是谁,也不论是哪个庄上嘞,逮住就让他去干活。后来真有东西吃了,红薯能吃饱了,馍里捏的红薯面,锅里蒸嘞红薯,调嘞红薯叶菜,锅里馍里都是它,能吃饱真嘞很满足。②访谈对象:尤凤兰,女,78岁;访谈人:雷俊霞;访谈时间:2021年1月23日;访谈地点:尤凤兰家中。
1963年8月上旬,河南境内太行山以东发生解放以来第一次特大暴雨,造成5万个村镇,17个县城被水或围或淹,造成财产、人畜方面的重大损失。③河南省气象局资料室编:《河南省灾害性天气气候概况(1951—1980)》,内部资料,1981年,第17页。这一重大自然灾害带给人们的饥饿记忆历久弥新,外来的救灾物资里红薯依然“唱主角”。
63年河南发大水,到处坑满河平。我的弟弟就是那一年出生,起了名字叫“河平”,他的名字也记录了那场洪灾。天天下雨,啥庄稼都不生长,只有高坡上的红薯还能有一点产量。连续下了几个月,8月份雨大得很,所有庄稼都绝收,连野菜都不生长。没东西吃,都饿着。后来,国家调来了救济物资,才有点吃的。当时各家都发了一小把一小把扎得很整齐的粉条、红薯干、苜蓿干等食品。④访谈对象:张凤兰,女,72岁;访谈人:雷俊霞;访谈时间:2021年2月12日;访谈地点:张凤兰家中。
(二)乡土、乡愁与红薯记忆
红薯的生命力极强,各地流传有打油诗:“红薯没有娘,随意插截秧,土里到土外,根叶都是粮。”60年代开始红薯在河南普遍种植,加上种植技术的推广,农家肥、氮磷钾肥的辅助,红薯产量大增,人们终于从饥饿走向温饱。
关于乡愁的文章随处可见,他们以红薯为视角抒发对乡土的牵挂、乡愁的浓烈、乡音的怀念,以及对熟悉而美好的乡村生活的怀恋。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中国人,大多经历过有红薯陪伴的童年,从闽南乡村的红薯香飘四溢的童年、赣西农村快乐的挖薯仔、湘潭大地被红薯与杂粮挤满的童年、重庆孩子童年足迹里的红苕、山西人儿时的红薯饭、胶东半岛农渔民吃红薯、红薯干就虾酱和咸鱼干的童年,到中原大地挖坑点火烧红薯的鲜美。田间地头一群可爱的孩子捡树枝、挖红薯、搭土灶、烤地瓜,个个灰头土脸,地瓜味道鲜美诱人。烤红薯是对味蕾的奖赏,而红薯秧是孩童游戏的工具,一根根红薯秧跳绳就能刷出孩童的游戏和快乐。红薯梗制作的手镯、项链和耳坠,缀满童年的乐趣,则属于孩童关于红薯的文化创意。
夏天的红薯叶凉拌菜、清炒红薯梗、红薯叶烙饼;寒霜之后的新鲜红薯、秋风吹干的红薯干;冬日暖阳里的红薯粥、红薯干大米粥、红薯面煎饼、红薯叶面条、红薯叶包子、红薯面窝窝头、红薯粉条炖菜、红薯淀粉粥、红薯丸子等等,红薯成了人们餐桌上的主角。红薯与人们相伴的艰难岁月,它的顽强与随意生长,是这几代人集体记忆里的重要内容。
三、配角:“大米白面红薯客串”的多元文化建构与重构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终于迎来能吃上“大米饭、白蒸馍”的“好生活”,但是经历过苦难的人们,永远无法忘记那段有红薯相伴的生活。随着全国粮食大丰收,细米白面成为普通人的主食,红薯逐渐从主角的舞台上慢慢退出,但作为配角它依然调剂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忆苦思甜、地方特色或养生食品等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集体记忆的红薯文化
红薯自传入中国以来,从福建的最初引进,到海南的备灾救荒试点,河南的救灾救难,以及后期逐渐传到全国各地,在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不同民族中传播与传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人们日常饮食中的主角。“感知者的世界以历时经验来规定,是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一套有序的期待。”①[美]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因此,当能吃的食物越来越丰富时,红薯尽管不再主宰人们的一日三餐,但依然因其“好吃”而让人们“好想”,并在对比中建构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好生活”的美好期待。经历过苦难和饥饿的老一辈念念不忘红薯的“好”,并在对比中更加珍惜今日的美好生活。在物资匮乏但尚能吃饱的年轻一代人记忆里,红薯给了他们与同伴相处的快乐与美好,乡土中人与人之间的“熟悉”以及“乡土社会从熟悉到信任”而产生的可靠感。②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7页。在现代化和城镇化带来的极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陌生感,让人们更加怀念乡音、乡土和乡愁。
红薯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成为了解“有意义之世界和赋予有意义之世界以生命的土著观点”③彭兆荣:《饮食人类学》,第114—115页。的最直接的介体,它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角度,体现着群体的价值观。“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人们以红薯的奉献来认知官员的奉献与为民,红薯对环境没有特殊要求,有土壤有温度就可以随意生长,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一切,民众心目中的官员就应该像红薯一样,有担当有奉献精神。民间俗语“热水里的粉条——瓤条了”,以晒干了的红薯粉条进入热水之前的耿直和僵硬,与进入热水之后的柔软与滑润来比拟人的倔强性格以及与人相处的变通哲学。红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标,民众以他们的立场和视域,从日常食物的角度理解和认知世界。
“食物在滋养心灵之前必须先滋养集体的胃”④[美]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4页。,长期以来,红薯为缺乏食物的中国百姓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营养,并在日积月累中成为人们心灵的营养,逐渐成为具有“地方知识”和“民间智慧”的特色饮食。
(二)特色品牌与绿色食品
“直接靠土地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①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页。,以农为生的人们,在富于地方性的乡土生活里,向土地讨生活,在一方水土上与生态共存,与生活经验结合而产生出属于地方性的农产品。借助互联网,输入“红薯”“特产”两个关键词,发现全国有二十多个省的淘宝卖家售卖红薯及其深加工制品。红薯文化在全国广泛传播的同时,与当地的生态相适应、与人们的饮食习惯结合从而形成凝聚“地方性知识”②[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的特产,使食物在传统的意义上出现了全新的功能。
农业的发展,人工和技术的进步使食物在保证民众温饱的基础上出现了剩余,作为商品进入交换领域才有了可能,商业是“人们在食品自足基础上争取生活提高的行为”③彭兆荣:《饮食人类学》,第148页。。市场经济时代,红薯的综合价值逐渐被人们认识,有些地方将红薯作为重要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有的将传统产业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来抓,进行红薯制品的深度加工如制作红薯淀粉、红薯粉条、红薯片、红薯糖、红薯酸奶等,并尝试进行创意开发。遵义市红薯生产及产业化发展借助新品种、新技术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有重要意义。④周开芳:《遵义市红薯生产现状、问题及对策措施浅析》,《贵州农业科学》,2009年第9期。遵义市的紫心苕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⑤周开芳、左明玉等:《不同脱毒红薯品种对产量及其品质的影响》,《种子》,2011年第1期。红薯与酸奶配合开发制作对合理开发利用红薯资源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⑥黄治国、卫春会、殷小茹:《红薯酸奶加工工艺研究》,《中国酿造》,2011年第2期。“唱好加工戏,树好名优牌”等举措也可以带动红薯的产业化发展与流通。⑦钟来福、周明洪:《树红薯品牌,唱红薯大戏》,《农业经济问题》,2000年第7期。很多红薯产地,结合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进行创新创业的引领与开发,聚焦红薯,创意开发,品牌化经营,将红薯纳入世界经济行列。广西东兴河洲村以“仑河”和“红姑娘”两个红薯产业品牌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⑧胡美术:《中越边境的“空心村”治理实践研究:以东兴河洲村为例》,《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6期。在进行产业开发和品牌化经营的商业实践中,红薯的营养保健价值是进行品牌开发的重要着眼点,也是红薯文化深度建构的优势所在。
日常保健和养生实践中,红薯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逐渐为人们所认知。红薯中所含的膳食纤维,能有效刺激肠道,增强肠道蠕动,具有通便排毒,预防痔疮和大肠癌发生的功效。“营养学家将其视为一种药食兼用、营养均衡的保健食品。”⑨黄治国、卫春会、殷小茹:《红薯酸奶加工工艺研究》,《中国酿造》,2011年第2期。《本草纲目》认为甘薯具有“味甘,性平,无毒;具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⑩王维主编:《精编本草纲目》,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第189—190页。的功效。民间有黑豆与白心红薯同煮浓汤治愈便秘的偏方。
红薯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薯块中含有较高的淀粉、蛋白质及各种维生素,有独特的营养价值。同时,它还是一种碱性食物,与其他粮食同食可以起到酸碱中和的效果。红薯叶是备受青睐的绿色食品,有“百变绿叶蔬菜”“蔬菜皇后”之称,它具有止血、降糖、解毒和防止夜盲等功效,且方便易得、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与红薯相关的食品很多,或是乡村百姓日常生活的菜肴,或是城市居民生活的调剂,或是游客关于乡村的猎奇。红薯叶制作的食品也有很多,如凉拌红薯叶、清炒红薯叶、红薯叶面条、红薯叶馅饺子、红薯叶馅饼、蒸红薯叶等几十种,但是关于红薯叶的食用南北方也有差异。
我们老家东北能吃到蒸红薯、烤红薯、红薯粉条,没有吃过跟红薯有关的其他制品,几乎不吃红薯叶。不过在云南生活了这十来年,在菜场经常见到有卖红薯叶的。没买过,不太清楚怎么吃。①访谈对象:原源,女,39岁;访谈人:雷俊霞;访谈时间:2021年1月24日;访谈方式:微信。
灾难年代,有“一年红薯半年粮”之说,红薯的大面积种植及广泛推广,有效解决了粮食不足所带来的饥荒。丰裕之年,人们不再发愁温饱问题,“吃得好,吃得健康”成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红薯被贴上了“养生的佳品”“抗癌食品”“冠军蔬菜”“护眼小卫士”“最亲民的养生食品”“长寿食品”等一系列与健康密切相关的文化标签,成为人们餐桌上“最有魅力的客串”。
红薯养生保健功效还和季节与节气相关联。民间认为,红薯是秋冬季节养生的佳品。北京民间有白露节吃红薯的习俗。
(三)社会变迁的动态文本
康拉德认为变迁是“从一个相对孤立、平等主义和同质的社区,变成一个职业分化、信仰多样、社会阶级与地位存在高下的社会”②[美]康拉德·科塔克:《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第四版),张经纬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页。。近代以来,尤其是近七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动态文本,我们可以由红薯文化来窥见中国社会变迁的诸多方面。
红薯又称番薯,此处“番”字具有与文明中心关系和距离较远的含义,后转用为“未开化的、外族人群的污名化表达”③彭兆荣:《饮食人类学》,第132页。。番仔、芋仔是以日常粗贱的食物而指称“蛮夷”,张光直自称“番薯人”。“台湾岛的确酷似一枚番薯,而且这种草本植物的根块,是旧社会穷苦人常用来果腹的,所以台胞以番薯人自喻,似命苦势弱的哀叹。”④何标:《番薯藤系两岸情》“前言”,北京:台海出版社,2003年,第1页。随着红薯文化的深入传播,这些表述已经成为方言里的地方性知识,由“他指”而变为“他指”与“我指”并用的变动文本。
红薯由境外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引起了各地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无论南方的水稻还是北方的小麦,都是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实现的,红薯的种植方式相对简单,对耕作方式没有精细化的要求。同时改变的还有栽培制度的变化、选种方式、储藏方式、生活方式等的改变。红薯可以蒸着吃、烤着吃、煮着吃,市场经济条件下,红薯还成了人们的重要经济作物。
大约到了65年,有了化肥,红薯的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了,基本上可以吃饱了,各家种的红薯吃饱之后有了结余。老百姓开始琢磨着做红薯淀粉、制作粉条、做红薯丸子。红薯几乎浑身是宝,最困难的时候,红薯秧能养活人,后来稍微富余一些了,红薯秧喂羊、喂猪,或者打碎了做各种饲料。下红薯粉时洗红薯的红薯渣,蒸了吃也是美味。实在多了也可以用来喂牲口,牲口吃了上膘。⑤访谈对象:雷友谊,男,68岁;访谈人:雷俊霞;访谈时间:2020年12月21日;访谈方式:电话。
红薯在中国的传播,改变了中国传统的食物结构,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滋润了人们的心灵。红薯的引进、传播、培育与改良的过程,也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借由红薯这一重要媒介实现交往、交流与交融的过程。
结 语
红薯由境外进入中国,在适应中国生长环境的过程中,与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相伴相生,传承中不断积淀。红薯在中华大地的传播,食俗建构与重构的历史,也反映食物作为一种流动性文化符号不断突破地域界限,在征服人们肠胃的同时,不断征服人们心灵的历史。在中原大地,红薯文化传播借助于居中而面向四方的地域优势,在南引、北传、西拓、东扩的过程中建构了多元而多样的红薯文化。食俗与灾荒勾连,与苦难同行,见证历史,书写集体记忆和乡愁。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红薯文化的多元重构,凸显集体记忆与乡愁,突出地方特色,彰显养生本色,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与成果,是多元文化的现实表征,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民间智慧贡献给时代的一笔财富。红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的彰显。红薯文化的传播及其所建构的一系列文化体现了人们面对灾难时的乐观态度与生存智慧,这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