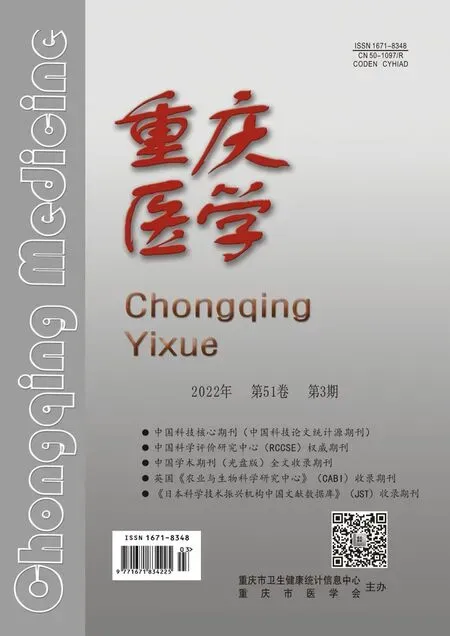基于肠道菌群探讨砷剂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研究进展*
2022-11-23陶雨晨任建业王冬琴胡可心综述陆嘉惠审校
陶雨晨,任建业,王冬琴,胡可心 综述,陆嘉惠 审校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200071)
20世纪70年代,哈尔滨医科大学率先使用三氧化二砷(AS2O3)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并获得成功。此后,国内外学者围绕砷剂(主要是AS2O3和硫化砷)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然而,砷剂对不同患者的个体差异性较大,主要表现在对砷剂耐受性以及诸如消化道反应、肝肾功能损害、皮肤神经反应和慢性砷中毒等不良反应的发生。
肠道是口服药物在体内代谢的重要场所,肠道内寄生的大量细菌对药物的生物转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高通量测序和代谢组学技术的突破,人们逐渐认识到肠道菌群对机体的潜在重要性。肠道菌的代谢转化被认为是影响药效和毒性效应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为对砷剂的临床治疗作用及不良反应给予更多维度的阐释。本文以肠道菌群为切入点,从“菌-病”“菌-药”两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揭示肠道菌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及对中药药效和毒性效应研究提供帮助。
1 肠道菌群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在人类的胃肠道中有一个巨大的微生物生态系统,容纳着数万亿个微生物细胞。肠道的必需菌包括益生菌和共生菌,正常情况下,肠道菌群表层的主要成分是大肠埃希菌、肠球菌,中层主要是以类杆菌为主的厌氧菌,深层则主要是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深层的菌群可以与肠黏膜上皮表面的特异性受体结合,形成可以抵御过路菌侵袭的生物屏障。
一项囊括美国、中国和欧洲1 200例样本的人类粪便微生物宏基因组综合目录确定了这些粪便微生物群中总计990万个微生物基因,超过10亿年的哺乳动物-微生物共同进化导致了相互依赖[1]。正常菌群有许多重要的生理功能:如拮抗作用、免疫作用、排毒作用、抗肿瘤作用、抗衰老作用等。因此,肠道菌群在宿主免疫应答的成熟和持续发育中起着关键作用,提供防止病原体过度生长的保护,影响宿主细胞增殖,调节肠道内分泌功能、神经信号,对特定药物起反应或修饰作用和消除外源性毒物等。鉴于肠道菌群的多种功能,使得它们成为慢性疾病研究的焦点,包括癌症和炎症、代谢、心血管、免疫、神经、精神系统的疾病[2-5]。
1.1 肠道菌群可以促进造血重建
相关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在正常造血和促进造血恢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STAFFAS等[7]认为,肠道菌群耗竭可以削弱骨髓移植后的造血功能,同时会减少能量收集和内脏脂肪组织合成,而补充热量可以弥补由于菌群不足导致的造血功能受损。JOSEFSDOTTIR等[8]在小鼠上证明了抗生素消耗肠道菌群可以损害造血功能,抗生素可以导致肠道共生菌群的平衡和多样性遭到严重的破坏,进而导致小鼠出现贫血和白细胞减少,血小板计数显著增加,淋巴细胞减少,表现为CD4+/CD8+比例降低。但是,造血功能被抑制的表现是短暂的,抗生素对小鼠造血功能的不利影响是可逆的。进一步实验表明,肠道菌群可以通过激活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1(STAT1)信号来维持稳定的造血,从而证明了肠道菌群的耗竭在抗生素相关性骨髓移植的发展中至关重要。
1.2 肠道菌群可以调节T细胞免疫
肠道菌群是一个信号枢纽,它将饮食等环境输入与遗传和免疫信号整合在一起,从而影响宿主的代谢和免疫等反应,免疫系统和肠道菌群之间的交流异常可能导致复杂疾病的发生、发展[9-11]。ZITVOGEL等[12]把肠道菌群组促进致癌的机制总结为:(1)通过微生物及其产物的直接致癌作用;(2)通过改变循环代谢物,进而成为致癌物;(3)通过刺激宿主合成营养因子;(4)通过诱导促炎和免疫抑制途径干扰宿主癌免疫监视。
肠道微生物群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宿主因子,可能被调节以增强免疫疗法的反应[13]。肠道菌群可能通过促进造血作用来指导先天免疫细胞的发育,有助于人们认识到哺乳动物及其微生物群之间的深层进化联系[14-15]。肠道菌群在肠道Th17细胞的发育中起着关键作用。此外,一些共生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如丁酸盐、丙酸盐和乙酸盐,可诱导调节性T细胞(Treg)的分化和增殖[16]。
VIAUD等[17]为了证实“环磷酰胺的治疗效果部分取决于其刺激抗肿瘤免疫反应的能力”观点,通过小鼠模型证明了环磷酰胺可以改变小肠内微生物群的组成,并诱导选定的革兰阳性菌转移到次级淋巴组织中,这些细菌刺激特定亚群的“致病性”辅助Th17(pTh17)和记忆Th1免疫反应的产生;无菌或用抗生素杀死革兰阳性菌的荷瘤小鼠显示出pTh17反应的降低,并且它们的肿瘤对环磷酰胺有耐药性;过继性转移pTh17细胞可部分恢复环磷酰胺的抗肿瘤作用,这些结果表明肠道微生物群有助于形成抗癌免疫应答。
1.3 肠道菌群可以预防感染
研究表明感染是血液恶性肿瘤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而大部分感染是由细菌引起的,肠道菌群失调与细菌感染也是密切相关的。血液恶性肿瘤患者与健康人肠道菌群的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GGE)指纹图谱有明显差异:与健康人相比,血液恶性肿瘤患者肠道菌群结构与多样性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肠道大肠埃希菌呈现过度增长趋势,有益菌柔嫩梭菌减少或缺失,以及粪肠球菌、硫磺肠球菌、约氏不动杆菌等肠道内一些细菌呈现特异性增长[18]。
正常情况下,人类通过厌氧肠道菌群保护免受感染,提供定植抵抗力。在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中,内源性肠道革兰阳性和革兰阴性菌常引起感染性并发症。研究发现,白血病患者在化疗后,粪样中由于厌氧菌减少了1万倍,导致细菌总数比健康人低100倍,同时,潜在致病性肠球菌增加了100倍。厌氧菌和需氧菌之间的平衡失调可以进一步增加患者革兰阳性需氧菌感染的风险[19]。WEN等[20]在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中发现,在抗癌治疗期间,肠道菌群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与胃肠道黏膜炎相吻合——有利于潜在病原体的共生体厌氧菌群减少。
ALQAHTANI等[21]认为降低艰难梭菌感染(CDI)复发风险的最有效策略之一是粪便微生物移植(FMT)。目前,很少有关于免疫功能低下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FMT疗效和安全性的数据。文献报道沙特阿拉伯1例被诊断为高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69岁女性到急诊科就诊,抱怨有臭味、顽固性、水样腹泻和全身腹痛,需要每天输血,并报告了过去多次使用甲硝唑和万古霉素作为单药或联合疗法成功治疗的CDI发作。在这一入院期间,奥拉万古霉素(大剂量)和静脉注射甲硝唑治疗不成功,但是通过FMT治疗,尽管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ANC)<0.25×109/L,但患者恢复良好,并于术后不久开始化疗。FMT治疗成功且安全,随访8周未发现复发和不良事件。
2 肠道菌群与AS2O3
AS2O3+全反式维A酸联合应用的“上海方案”已成为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首选。肠道微生物对降低宿主砷负荷、提高砷的生物利用度及降低砷的肝毒性有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可以保护小鼠免受砷引起的死亡,用抗生素治疗的小鼠和无细菌的小鼠在粪便中排泄的砷更少,在器官中积累的砷也更多[22]。
CHI等[23]在常规饲养的正常小鼠和利用抗生素破坏肠道菌群小鼠中注射亚砷酸后发现,肠道菌群紊乱小鼠尿液总砷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小鼠,一甲基砷酸/二甲基砷酸比值(砷代谢和毒性的生物标志物)显著增加,但粪便中总砷水平却较低。同时,仅肠道菌群紊乱小鼠出现一氧化碳代谢基因[包括FOLR2、BHMT和MTHFR]的表达下调,肝脏S-腺苷甲硫氨酸(SAM)水平显著降低,可能会影响砷甲基化。此外,在肠道菌群紊乱小鼠中,砷干扰了基因表达,包括p53信号通路,上调了许多肝细胞癌(HCC)中高表达的癌基因,下调了一些抑癌基因,表明HCC的发病风险增加。
AS2O3也是中药砒霜的主要成分,为砒石经生化而得的精制品[24],以内服每日量3~6 mg或每日量10~30 mg入丸、散用,或研末外用,或入膏药贴之;成人口服AS2O3的中毒量为5~50 mg(敏感者仅服1 mg即可中毒),其致死量为70~180 mg。然而,由于个体对砷的耐受性不同,因而中毒程度有极大差异,耐受性高者,服至10 000 mg,经治疗仍可恢复健康[25]。
3 肠道菌群与硫化砷
目前,临床上应用硫化砷药物主要以雄黄为主。雄黄,主含二硫化二砷,以内服每日50~100 mg入丸、散用;外用适量,熏涂患处[26]。文献报道,口服雄黄20 mg时可危及生命,但耐受高者可达10 000 mg,一般成人口服雄黄的中毒剂量为10 mg,致死量为100~200 mg[25]。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临床应用含雄黄的复方制剂或单方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取得了显著的治疗效果。由于雄黄不溶于水,临床上常见的含雄黄制剂以丸剂、片剂、胶囊剂等为主,如:复方黄黛片、青黄散、定清片、六神丸、牛黄解毒片、安宫牛黄丸、梅花点舌丸等。
雄黄的毒性已被证明与可溶性或生物可及砷的水平有关,雄黄可溶性砷中的砷形态为As(Ⅲ)、As(Ⅴ),且As(Ⅲ)水平高于As(Ⅴ),雄黄可溶性砷与As单元素在肠道菌群的作用下,通过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合技术(HPLC-ICP-MS)只检测到的砷形态为As(Ⅲ)、As(Ⅴ)[27]。研究表明,雄黄与三价砷等量的AS2O3对肠道菌群影响具有相似性,临床使用雄黄后出现的不良反应可能与菌群紊乱有关:雄黄给药后肠道保护性细菌如乳酸菌属等减少,发生炎症;低剂量时抗炎性细菌如瘤胃球菌属、粘放线菌属等增多,可以抵消菌群失调造成的轻度炎症;高剂量时菌群紊乱,变形菌门增多,肠道炎症加剧,出现水肿等炎性反应[28]。
牛黄解毒片是含雄黄的经典名方,一些研究表明,牛黄解毒片比雄黄更安全。体外研究证实了牛黄解毒片中其他中药对雄黄中砷生物利用度的影响,以及肠道微生物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大黄、黄芩、桔梗、甘草能显著降低雄黄中砷在人工胃肠液中的生物可接受性。肠道菌群在培养基中能吸收雄黄中的可溶性砷,对降低雄黄的生物利用率起着重要作用。大黄、黄芩、桔梗可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群来提高其对砷的吸收活性[29]。
4 小 结
肠道菌群是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及造血功能的一个关键的外在调节因子[30],对维持机体内环境稳态有着重要作用。一旦肠道菌群失调,会增加细菌和病毒感染的风险。肠道菌群将成为人类疾病(砷中毒)渗透率的重要解释因素,并成为砷剂“以毒攻毒”预防和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临床策略的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