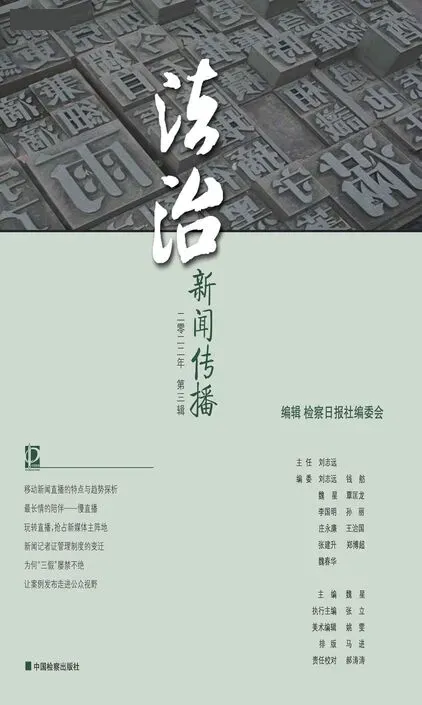法律电影要反映活生生的中国现实
2022-11-23■车浩
■车 浩
改编自1957年美国经典影片《十二怒汉》的华语影片《十二公民》,曾斩获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单元最大奖,成为罗马电影节史上第一部获此殊荣的中国影片。
这是一部与法律有关的电影,法律界对该片的评价参差不齐。有些法律人认为有普法功能,高呼走进中国法律电影新时代。也有不少人认为一些地方很别扭,做作不自然,还有专业方面的硬伤。
法律界操碎了心,但导演徐昂的回应很淡定,大意就是,他不是要拍一部法律电影,而是想拍一部反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偏见问题的电影,法律问题只是个壳儿。
由《十二公民》想到中国的法律电影该怎么拍?接下来说的,纯属一些个人“偏见”。
为什么《十二怒汉》经典:三层结构浑然一体
在谈论对《十二公民》的看法之前,先说一下这个电影的原版,也就是1957年的美国电影《十二怒汉》,这部经典已经没有争议地进入电影殿堂,是怎么做到的?依我之见,《十二怒汉》的奥妙,是三个层次叠合出来的厚度。这个三层次的基本结构,是这部电影的灵魂。
第一个层次的焦点,是先要树立起一个靶子。这个靶子,在《十二怒汉》中表现为法律领域中的一些重要观念,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合理怀疑,等等。第二个层次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案情中巧妙地设计出能够让人通往前一层次的无罪结论的合理怀疑。第三个层次的焦点,是哪些具体的、斑斓复杂的人性表现,妨碍了人们去认识这些疑点,或者即使认识到,却仍然不能就此通往无罪的结论。简单地讲,第一层次是理念问题,第二层次是技术问题,第三层次是人性问题。
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上面三个层次可以拆解开来,分别思考和用功,最后叠合在一起,浑然天成,就铸成了《十二怒汉》。
第一个层次的功能在于对这部电影的方向进行引领。没有它,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第二个层次的老人说谎、匕首用法、戴眼镜的夜睡女等各种疑点。第二个层面的各种疑点,对观影者是最具有刺激性的,能够满足其探索欲、惊奇感、智力猜谜、恍然大悟等种种心理渴求。第三个层面,是要让这12 个人面目鲜活,性格迥异,小到观察案件的切入角度,大到各自的人生阅历和价值观念,都有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剧烈冲撞之处,如此才会让剧情一波三折,充满张力。
《十二公民》的翻拍:电影主题不是法律
跟俄罗斯和日本的版本一样,中国的《十二公民》也是对《十二怒汉》三重结构的完全拷贝。而《十二公民》让人遗憾的一个原因,就是创作人员没有能够理解和把握这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在第三层次上用力过猛,以致与前两个层次严重脱节。
在《十二公民》中,电影的主题被甩到第三个层次上来,但创作者又偏把这种脱节和偏离当作是自认为成功的有意追求。这样一来,就使得前两个层次的结构,对于表现《十二公民》创作者所说的新主题而言,完全是可有可无,甚至是多余繁冗的累赘。
关于第一个层面的法律理念问题,《十二公民》是通过8 号陪审员用两句话,向其他人进行了简单介绍。关于第二个层面的疑点设计问题,《十二公民》完全复制了《十二怒汉》的桥段,没有任何创新。至于第三个层面的人物性格冲突,这是《十二公民》最用力用心的地方,12 个人来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出租车司机、房地产商、医生、河南保安、检察官、北京土著、小卖部老板等,互不相识、阅历性情迥异的人凑在一起讨论这个案件。随着剧情的推进,每个人背后的故事也浮出水面。按照导演徐昂的想法,表现人性和偏见的第三个层次,是《十二怒汉》以及他的《十二公民》的精华所在。
于是乎,《十二公民》把最重要的部分、最用力的地方放在了第三个层面上,即如何展现12 个中国人,由其自身的阶层、出身、阅历、职业背景所共同决定的每个人的性格、价值观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看法,作为一种前见或者说偏见,影响了对这个案件的讨论。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这部电影令人遗憾之处。想一想,如果把这部影片讨论的案件置换成任何一个中国社会的话题,效果不都是一样的吗?比如,找一个工厂职工开会的场景,找一个大爷大妈在胡同里围成一圈侃大山的场景,找一个街头采访的场景,绝对都能够表现出“偏见”和“不好好说话”的主题,又何必翻拍《十二怒汉》,费尽心机地设计出一个中国根本没有的陪审团,来虚拟讨论一个根本不可能影响实际判决的案件呢?
什么是经典电影的“本土化”
其实,《十二公民》更让人遗憾之处在于,错误地回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到底什么叫作经典电影的“本土化”?
导演徐昂显然是有本土化的野心。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它在讲一个中国的问题,但是在西方的框架讲中国的问题,然后得到西方人的认可和关注。”他所说的“中国的问题”,就是为什么“12个中国人不能坐在一起好好说话”,答案就是,镶嵌在中国社会里的这12个人,身上带着不同的中国故事。
显然,如上所说,正是由于导演把《十二怒汉》的重心理解为第三层次的人性和偏见,于是,他的“本土化”努力,其实就是第三层次的本土化。我只是想问,以一个中国人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这个故事中最大的中国特色,最应该本土化的地方,难道是这些东西吗?
首先,它肯定不是第三层次中的人性与偏见,一群不同背景的人讨论问题时的分歧,那是任何国家、任何族群里普遍存在的永恒主题。而且,它也不是第二个层次中的合理怀疑。对疑点的发现与探究,对这些疑点是否“合乎情理”的推演,同样是普遍存在于各色人等中的能力和兴趣,不为美国人独占,也不是中国人的特色。甚至,也不是被很多人诟病的“陪审团”,因为,电影中已经努力表示了,这只是一个用于教学的形式,形式上模拟而已。
不必非得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就从普通人的角度去感受,如果你关注今天的中国社会,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如果出现在中国,最大的障碍是在第一层次的法律观念上。美国人拍的《十二怒汉》,第一个层面上的焦点,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以及合理怀疑等一系列法律理念。任何一个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人都会明白,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一些司法人员,面对这些源自西方的法律理念,整体上还处在水土不服的阶段。
《十二公民》里的司机、商人、医生、保安、小卖部老板,都是中国社会里的普通职业者。在现实生活中找这些人聊一聊,问一问,就会发现:
讲“无罪推定”,他会困惑:“真要是没事,警察为啥不抓别人只抓他呢?”
讲“合理怀疑”,他会不理解:“那么多的有罪证据,就因为这么一点怀疑,就把人放了?”“万一?哪有那么多万一!”
讲“疑罪从无”,他更难接受:“不是他干的,那是谁干的?”“找不到真凶,就能把这么大嫌疑的人给放了?”“人都死了,最后怎么能没有人负责呢?”举美国的辛普森案,他完全洞悉:“有钱人嘛,做工作了呗,肯定有司法腐败。”
这才是今天中国社会中普通人关于犯罪问题的真实看法。法律要惩罚有罪者,也要保护无辜的人,从道理上讲,这种两全其美完全正确。但是,实践中的情形往往是,两者冲突时何者优先?什么是可以被放弃和牺牲的价值?这一问题的答案,目前中国社会中大多数普通人的观念与《十二怒汉》中所展现的美国人的法律观念,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差异和冲突。
想一想近年来被曝光的、影响巨大的一些冤错案,大多是由于真凶落网,或者死者复活,才得以昭雪。这些案件在当时被定罪,当然有多种因素,但疑罪从无的观念没有被当作不可突破的铁则,至少是不能否认的因素之一。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就更是如此了。这些舶来品,从来没有真正地融入到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动选择中。老百姓看到罪犯落网,就开始为司法人员的英勇擒敌、及时破案、为民锄奸而呐喊助威,提供舆论支持。如果事后发现是冤案,则忙着刷屏痛斥司法人员草菅人命、不负责任的行为,提供舆论声讨。至于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值得反思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以及合理怀疑,普通人基本上是不关心也没兴趣的。
不管书本上怎么写,法条上怎么说,政策上怎么宣扬,但是观念的力量常常是历史地长期地形成,根植于普通人的内心深处。虽然经过了这些年学界的呼吁,立法部门的实践,有些渐进的变化,但是整体上仍然是缓慢的。这才是活生生的中国现实,是中国当下普通人的朴素情感和法律观念。
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层次,而不是第三层次。正是那些位于第一层次的法律观念,而不是位于第三层次的人性偏见,才是12 个中国公民与12 个美国公民,在类似案件中认定是否有罪时,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差异。这才是12 个中国人在讨论一个案件时,与讨论其他事情相比,最容易困惑的地方,会真正起冲突的地方,这才是最接地气的东西。这也是这部中国版的《十二公民》本来最值得期待的“本土化”之处。
在同样的案件和法律问题面前,中国人从最开始的、作为思考起点的思维习惯上,与《十二怒汉》中在第一个层次所展现的那些产自于美国社会被美国人自然接受的法律观念,是完全不同,甚至激烈冲突的。可惜的是,这个最有价值进行“本土化”的地方,却被导演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