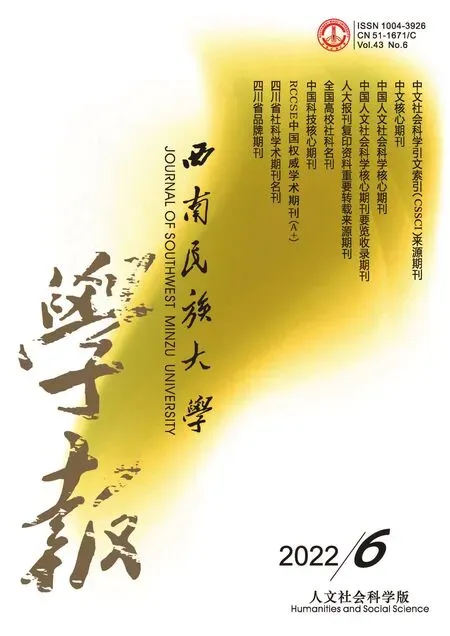中华传统灾难文化的心理创伤应对机制研究
2022-11-23汪晓萍
汪晓萍
[提要]人类进化史也是人类战胜灾难的历史,在与灾难抗争前行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灾难文化体系,蕴藏着丰富的心理创伤疗愈资源,发展出应对灾后心理创伤的预防机制、缓冲机制、复原与创伤后成长机制。以灾难意识、灾难解释、灾难应对为主的中华独特灾难认知体系预防着心理创伤的发生;灾难发生时,受集体主义价值观深刻影响的社会支持体系,从紧急社会救助、情绪调节模式、仪式供给等方面缓解着灾难的冲击;灾难发生后,理性的言语范式、伦理性记忆策略及灾难叙事模式等灾难文化传递体系进一步增强了个体心理弹性,促进着创伤后的复原与成长。
人类历史上各种灾难事件时有发生,“自然与技术灾难数量与严重性的增加,对于目前诸多人类环境适应的韧性和持续性的匮乏构成了最为明显的考量”[1]。以传染病为例,鼠疫、非典、新冠肺炎等等不断发生,“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2](P.119)灾难发生后,人们总会有需要纾解的负性情绪、需要安抚的哀伤与创痛。最新研究显示,在新冠疫情期间,民众普遍存在抑郁、焦虑、恐惧、无助等创伤应激反应[3],这就使心理创伤和心理弹性成为灾难应对的重要主题,也促使灾难文化发展出疗愈心理创伤、增强心理弹性的机制,形成一种独特的“成语”[4](P.80)。对个体而言,这些“成语”能够帮助其应对灾难、度过危机、减轻痛苦,恢复心理平衡,防止正常的应激反应发展为过度的、反复的心理创伤(ASD或PTSD),进而增强人类环境适应的韧性与持续性。重视与研究这些“成语”,挖掘与明晰这些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并形成有效的心理创伤应对机制,不仅能够增强人们面对灾难的信心与能力,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一、预防机制:降低心理创伤发生概率的灾难认知体系
影响心理创伤发生的具体因素很多,包括遗传与生物因素、创伤严重程度(如,是否威胁个体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创伤性质(如,是天灾还是人祸)、个体的反应(如,个体如何进行信息加工)、个体的易感性(如,是智商高低不同还是具有加重焦虑的人格特质、文化要求等)、社会支持(如,有无精神支持、资源的可获得性)等等,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创伤前的变量、与创伤本身有关的变量和创伤后变量等三类。灾难文化对心理创伤的预防主要通过灾难认知体系的建构,作用于创伤前的变量,减轻个体对灾难事件的易感性,增强掌控感、自我效能感等,以降低后期心理创伤发生的可能性。
(一)减轻个体对灾难事件的易感性及增加与灾难相关的知识储备
当“一个经验在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性的。”[5](P.218)灾难之所以带来心理创伤,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具有不确定性、严重性、危险性造成。灾难意识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危机意识、风险意识,是人对灾难发生的主观反应,“风险感知主要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受社会组织和价值观的影响,导引行为并且影响什么是‘危险’的判断”[1]。如果对灾难发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就会在较大程度上减轻灾难带来的冲击力。
中华民族有着深刻的灾难意识,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灾难预警、风险相关理念等内容,如“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6](P.543)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对灾难的认知度,让大家能够接纳和理解生活中不确定性、不可预测事件的存在与发生,提醒人们居安思危,降低了个体对灾难事件的易感性。《易经·乾卦》九三爻辞有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7](P.531)朱熹作注时说:“言能忧惧如是,则虽处危地而无咎也。”[7](P.31)不仅如此,人们还发展出一系列应对灾难事件的知识、经验与能力,如在防灾减灾方面,传统社会通过长期的观察,积累了丰富、朴素的灾难前兆知识以预告、警示灾难的发生,又譬如地震前会有动物的异常活动、天文现象会有变化等等。在传统典籍中还为人们提供了不少具体的行为指导呼吁人们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如对垃圾进行定点堆放、注意饮食卫生等可以防治瘟疫发生,“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8](P.339)“六畜自死,皆疫病,则有毒,不可食之”[8](P.371)“虫坠一器,酒弃不饮;鼠涉一筐,饭捐不食”[9](P.22-23)。政府会编辑印行医书,向老百姓传播预防疫病的知识,如宋太宗淳化三年,“命医官集太平圣惠方一百卷,乙亥,以印本颁天下”[10](P.736);还编纂颁行一些简单易用的方书,录于木版石条在村坊要路晓示,这对疫病防治的作用更为直接有效;建立了地方长官兼河堤使制度,并常态化修河筑堤、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改造农田等,如北宋初年每年春季征调民夫数十万人加固河堤,“自是岁以为常,皆用正月首事,季春而毕”[11](P.186)“禁民伐桑枣为薪。又诏黄、汴河两岸每岁委所在长吏课民多栽榆柳,以防河决”[12](P.72)等等,这些举措不仅有效防患了水灾,也让民众意识到灾难存在的客观性、一定程度上的可预防性,提醒人们保持适度的警觉性,“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6](P.544),以无灾防灾、有灾抗灾、灾后救灾等健康心态面对灾难。
(二)增强心理掌控感的灾难解释体系
文化影响着个体以什么样的理由和方式面对灾难、应对风险。中华传统文化从人、天(含自然或超自然力量)、社会关系及其互动状态对灾难何以发生进行了归因,形成了独特的灾难解释体系,其核心在于:首先,灾难的发生可能与人、天、社会关系不和谐有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13](P.322),若遵循珍爱生命、敬畏自然的基本准则,便能达到天、人、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共荣状态,呈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4](P.137)的境界,在这种状态下灾难发生的概率就会变小,反之,则表示上述几者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其次,灾难发生与人心有关,“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15](P.113),既然人(社会)也可以影响着天(自然),其结果就是可以协调和顺应天(自然)的存在和发展,减少灾难、造福人类。
与之相匹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人们提供了处理人、天、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与基本行为准则,使人们能够既具有能动性,又不会行为失当、为所欲为、无所节制,导致因天、人、社会关系不和谐而带来灾难。在核心价值观方面,儒家强调“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6](P.340),要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爰足以谓仁?”[17](P.118)在行为准则方面,则强调“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13](P.322)还提供了类似“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17](P.117)等通俗易懂的案例供人们效仿。
在民间,还常将灾害解释为上天等自然或超自然力量的结果,或者是恶灵作怪、鬼魅作祟、妖怪作恶等,如羌族地区就将地震解释为天神“木比塔造地”“癞蛤蟆支地”“毒药猫作怪”等。这些归因使灾难发生得以解释,也由于这样的归因,人在自然面前就获得了一定的确定性、能动性,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获得一定的掌控感,缓解焦虑,减轻恐惧:人们可以通过祭祀、民俗、图腾崇拜等来避免灾祸,如在民间便有春节燃放鞭炮、年终或立春时节驱傩逐疫、过节时祈福消灾、饮屠苏酒除疫气等各种习俗;同时形成了一系列与现代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减少地质灾害等理念不谋而合的习俗,如从周开始,长江、黄河、淮水、济水等四条河流被列为国家祭祀的对象,并在汉朝形成定制,一直沿袭至清;在我国藏、彝族地区有把某些山岭视为神山的情况,不能随便动土和随意开凿等等。这些关于灾难成因的解释并非仅仅是科学不够发达的产物,就降低人们面对灾难威胁时的恐惧、平缓灾难冲击、减少心理创伤形成而言,尤其是对于缺少足够能力和资源来应对灾难的个体来说,这样的解释体系正是他们在文化心理上对灾难做出的选择与适应,对此我们应尽量客观认识、理性看待。
(三)赋予个体自我效能感的灾难应对风格
通常,我们可以通过集体无意识来了解一个文化群体的灾难认知模式及应对风格。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普遍现存的、连续的、总体上一致的心灵条件或者基础”[18](P.370),作为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主要通过神话、仪式、传说、语言文字等方式呈现。下面以神话为例进行说明:
面对不断发生的灾难,对天地万物的困惑及自身能力的限制,先民们幻想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以依赖,并创造出一系列形象的、人格化的神,如鳞身的伏羲、蛇躯的女蜗,这是人类主体世界对自然客体一种原初的适应。随着人类探索与实践的进步,神话中的英雄逐渐世俗化,由人格化、形象化的神逐渐演变而为世间英雄。以各民族文化都经历过的洪荒年代为例,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关于洪水滔天的神话,这是关于人与灾难关系的典型范例,它讲述了人类如何面临洪水滔天的境地,以及这一境地蕴含着的灭顶之灾和重焕生机双重意象,考量着人类如何“向死而生”。对此绝境以女娲、大禹、李冰等为代表的治水英雄,从“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到领导人民凿山疏流降伏水患,再到修筑水利工程造福百姓,这一“神—人格化神—世间英雄”的变迁,展示了“从创世纪神话到英雄神话,是一个由神而人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神性退隐、人性逐渐凸现的递进过程”[19],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是有能力奋起抗争及改变受制于大自然的被动局面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主体性、效能感逐渐增强。
在中国神话中不仅有人格化的神,还通过将自然人格化加强理解,以摆脱对大自然的全然依附,消解灾难影响,获得更大的生存可能与面对灾难的精神力量。如认为自然万物是盘古和女娲“垂死化生”而来,盘古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20](P.15-53);“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20](P.45);同时,人们形成了人天合一、万物有灵的思想,“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21](P.335)这样人们在获得万物有灵的情感后,就可以用自己的情感经验、意愿等去体验、共情、解释自然,在潮起潮落、春去春来中感受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进而推及于人事,虽然肉体会消解但生命依然可以延续。正是在把自然人格化及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先民获得了面对灾难、超越恐惧的精神力量。
透过对这些典型中国神话的分析,我们从神话所展现“人与天”关系的宏大叙事母题中,看到个体在灾难面前的主体性存在,展示着作为人的自我效能感,发展出中华民族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应对灾难的文化力量,追日之夸父、补天之女娲、填海之精卫等无不如此。这些集体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面对灾难时的反应度、倾向性及应对模式等。具体来说,人类总会面临无可逃避的、不确定何时会降临的灾难,这让人们产生不安之感,因此追求绝对的安全感、确定感是徒劳和无意义的。如此一来,便唤醒了先民的灾难意识、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也激发了先民对自身力量的识别、自我救赎的自觉与责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在地增强了人们面对灾难的勇气与掌控感,并使之成为生命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灾难来临时,这种潜在的心理准备成为减力阀,减弱了人们对灾难的易感性与冲击力,促使人们在行为上更倾向于选择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这些特质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后期罹患PTSD和其他情绪性障碍的可能性。
二、缓冲机制:集体主义价值体系影响下的社会支持系统
无论是哪一种灾难发生时,最终都会波及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如带来个体与群体的紧张感甚至不同程度的社会解体,致使物质生存、社会秩序、习惯性满足感和价值实现的社会需求等被破坏,冲击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与心理环境。作为一种多维的建构,社会支持主要是指人们通过人际关系所获得的心理上、物质上的有用资源和社会性的关怀。几乎所有对精神健康的研究都指出:社会支持是精神疾病预防和康复的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伦理关系为基础进行形构,大力倡导仁爱、和谐等价值观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集中国传统文化特征、道德标准、政治原则于一体的以集体主义价值体系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一社会支持系统强调成员之间的凝聚力、责任感、牺牲精神以及对群体决策的服从力,提升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互助的意愿、能力与潜力,而集体共享的价值观、道德观、习俗等是理解和处理个人遭遇和问题的依据,构建了一个真正具有共同体性质的人际网络,形成了中华民族扶危济困、同舟共济的社会支持体系,在灾难发生时营造出一种相对稳定而友善的社会物质与心理环境,传达着安全、庇护、希望、守望相助的氛围,缓解了灾难对个体的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心理创伤发生的可能。
(一)恢复联结感的紧急社会救助体系
灾难常常带给人们强烈的无力感、无助感,甚至感受到与外界联结的中断,此刻重建灾难亲历者的安全感,创造有信任感的联系,是减少心理创伤发生的基础。灾难发生后,个体安全感最基本的来源是安全有保障的生活环境、稳定输出的物质条件以及来自他人及社会群体的支持与帮助,因此,是否能够通过人际关系获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物质资源,是否能够了解准确畅通的信息等,是缓和应激带来的负面冲击与影响的关键。这一时期的援助重点在于生命救援、食品与住所提供、卫生与流行病免疫援助等。这些紧急救助措施是这个时间点上最好的心理干预,通过紧急社会救助的获得以及快速动员起来的灾后重建,使来自他者的、集体的、社会的、国家的帮助与行动,让个体充分、安全地回到现实中,并获得基本的安全感、稳定感、联结感。
中国传统社会的紧急社会救助由来自国家和民间两股力量组成,其中国家是抗灾救灾的主要力量,民间部分则是对国家力量的有效补充与辅助,不容小觑,进而形成了国家——民间,自上而下、合作与联合的传统,共同构筑了人们应对灾难的重要社会救助系统。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一般根据灾难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施救措施抗灾救灾,如水灾、旱灾、蝗灾等发生后予以田租、赋税、徭税的减免,发放财物,开仓赈济,安置流民等。据《后汉书》中载:“迁文安令,遇时疾疫,谷贵人饥,尚开仓稟给,营救疾者,百姓蒙其济”[22](P.1284)。北宋仁宗皇祐三年“诏:淄、青等州,自春巳以来,民颇艰食,其军储留及一年,余尽以赈贷之”[23](P.4088);在传染病发生后,会启动一系列应对措施,如遣使颁药“令翰林医官院选名医于散药处参问疾状而给之”[24](P.4622),或“颁简要济众方,敕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23](P.4092);在颁药赐方的时候,还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如“己巳,赐戎泸州、富顺监圣惠方各一部,以其地多障疫也”[25](P.1926),并在疫情发生后设立隔离区,对相关人员采取隔离措施,“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野战病院记录之始”[26](P.13)。在“《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中,还首次出现“疠所”一词。“疠所”就是隔离区[27]。到汉代,隔离措施已趋完善,据《汉书·平帝纪》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28](P.353),到南北朝时期,隔离措施就已形成制度;对密切接触者也会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如《晋书·王彪之传》有载,“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29]。不仅如此,中国古代还有政府常设的隔离机构,如武则天时期的悲田养病坊、宋徽宗时设立的安济坊等。民间力量一方面是来自社会成员间自救互救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另一方面是宗族救济,即由宗族承担的宗族成员间互相帮助、共济困难的职责。“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也,宗人之所尊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为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汇聚之道,故谓之族也”[30](P.5-6)。《后汉书》里谈到:“逆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给宗族姻亲,又殓葬遭疫死亡而不能自收者”[31](P.2720)。
当灾难导致资源丧失或个体无法获得资源时,就会产生强大的心理冲击和压力,这些来自他人、家族、社会、国家的救助,作为一种具体有效的社会支持,缓解了人们的焦虑、恐惧、担忧、无助等情绪,给灾难中的人们带来一定的安全感、力量感、联结感,加强了灾难亲历者的心理韧性。由于心理韧性属于个体内部资源,这样既降低了灾难危险因素对个体的负面影响,也对创伤后成长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增进人际和谐的灾后情绪调节模式
灾难总是会激起人们的情绪反应,这些情绪中有消极的如焦虑、恐惧、愤怒、抑郁、悲伤、沮丧等,也有积极面对的情绪产生。如何表达与应对这些消极情绪反应、在应对灾难过程中“如何去诱发个体积极情绪的产生,主动发挥积极情绪的保护作用,以促进个体的适应能力”[32],是灾难应对需要回应的重要议题,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大多数情绪研究者承认情绪调节模式具有文化差异,认为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对情绪构成、体验、表达和管理的方式有深远的影响。情绪调节历来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受集体主义价值体系的影响,在中华文化里情绪情感不仅是个体心理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生存与适应的重要指标,强调情绪与情感问题的处理要服从于礼仪,服从于个人修养,服从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国家等关系和谐的需要,如养浩然之气、天人合一、致中和等个性修养方法、促进各种关系和谐的方法无不与情绪情感的调节联系在一起。
在灾后情绪调节模式上,中华传统灾难应对系统为个体减轻痛苦、减少心理创伤发生提供了行为与认知层面的策略。首先,行为层面的情绪调节策略,相对于情绪表达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情绪表达抑制作为灾后的情绪表达模式,呈现出克己、中庸、妥协、忍耐、曲折、委婉、内敛等特性,表达抑制是指个体“在情绪唤起时减少或有意识抑制自己的情绪表达行为”[33],因为,并非只有让情绪表达出来才是有益的。“9·11”后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与受难者对谈受难心理反而会加深其心理创伤,在灾难情境下选择情绪表达抑制可能是更具适应性的调节模式。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认为,公开承认自己不愉悦的情绪感受与传统文化强调遵礼的要求是相悖的,因此会“鼓励压抑强烈的情绪表达,从而对他人带来最小的不利影响,以实现社会和谐。”[34]即使是有某些公开的情绪表达,也“主要表示对特定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的认同,而不是自己此时此刻的内心真实感受。”[35]灾难后的情绪表达抑制在关注建立一种关系和谐且更让人满意的外部环境的同时,获得情绪调适、自我满足和成长需要。其次,认知层面的调节策略则以意义为指向激发积极情绪,以缓解消极情绪、拓展新视角、激发潜在活力、增进个人资源(如心理弹性、技能)等。通常,意义指向是以评价为基础,利用目标、信念、信仰、人生观、价值观等为灾难事件灌注意义,激发积极情绪。如经历地震后,人们会更加注重家庭、朋友的关系,重新确定生活目标、更加热爱生活等;疫情之后,人们也更加关照身体健康、更加注重珍惜当下等等。
(三)弱化创伤体验的灾难言语范式
言语作为一种符号,表达世界是如何被感知和解释的,是联结主客观世界的桥梁;言语是主观的、充满判断的,是体验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创伤性经历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尤其是“对客观事件的主观体验,才构成了创伤。……你越是相信你身处险境,你的创伤就越是严重。”[36]大多数心理治疗活动是完全以语言为媒介来完成的,把体验变成言语的过程本身便具有治疗功能。因此,灾难发生后人们怎样描述灾难、描述灾难体验,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一过程,既可以是带着内在疗治功能的过程,也可能成为加深创伤的过程。
跨文化心理学与人类学者的研究也注意到:“在不鼓励公开流露内心悲伤情绪,亦不习惯直白的口头交流的‘高语境’非西方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更注意思想、情感、信念表达的集体倾向的语境氛围与习俗规范,并且更倾向于从自己的文化传统观念、价值观和共同体实际生活来定义、理解、选择自己的观念和行为”[37]。灾难发生后,人们总是容易被焦虑、愤怒、恐惧等情绪所淹没、裹挟,中华传统文化认为沉湎于恐慌与焦虑中是无益的,缓解焦虑、恐慌等情绪首先须学会用多元视角描述灾难事件,接纳外在境遇,帮助人们稳定情绪、从情绪淹没中抽离出来。经典作品提供了诸多极具适应性的观念与视角供人们参考,并经过传统的教育体系不断强化最终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38](P.268)其次,灾难言语范式还体现在人们言说灾难时所呈现出共情——希望——力量的多层次描述。发生灾难之后人们必然备受冲击,如《诗经·大雅·云汉》中对周宣王时期旱灾的描述:“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于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旱既大甚,蕴隆虫虫……旱既大甚,则不可推……旱既大甚,则不可沮。……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熏。”[39](P.766-769)其中,六个“旱既大甚”的反复咏叹,淋漓尽致地描绘着悲情,但是,人们并没有止步于情绪的宣泄,也同时帮助人们看到希望,这在传统典籍中类似的言语范式不胜枚举,如“否极泰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40](P.230)“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等。灾难虽然带来痛苦,但是相信伤痛总会过去,事情总会迎来转机,因为自身就拥有能够带来转机的力量。“瞻昂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无赢。大命近止,无弃尔成。何求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宁?”[39](P.766-769)
在中国传统灾难文化里,描述灾难及灾难相关感受的言语范式,充满了理性色彩,理性是人类在进化中获得的最新且最复杂的降低应激的机制,这是一种更具适应性的言语策略。在多视角、多层次描述灾难、言说灾难的过程中,也促使人们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寻求使人受益的替代性积极经验,提醒人们居安思危,提高防灾减灾、应对灾难的能力,增强对灾难的掌控感,缓释着灾难时的创伤体验。
三、复原与创伤后成长机制:灾难的文化传递模式
经历灾难事件后,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精神、情绪、生理的紧张,出现各种症状,改善症状、疗愈创伤最核心的任务就在于帮助创伤个体恢复自主权与重建新连接。中华传统灾难应对系统所提供的灾难记忆策略、纾解负性情绪的仪式、意义性叙事等文化传递模式在尊重和基于创伤个体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帮助个体建构灾难,恢复自主权,重建新联结,完成心理的复原与重建,并且通过这一系列文化传递模式,促进个体在自我力量、人际关系、价值观等方面的积极变化,实现创伤后成长。
(一)缓解创伤症状的记忆策略:伦理性记忆
心理创伤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过去”或“不会消失的过去”[41](P.123-124),心理创伤本质上可能是人们对创伤性事件痛苦体验与细节的记忆,创伤记忆也不只是对发生了什么的事实的记忆,也是对体验的记忆,“情绪高涨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反应,这些反应决定了记忆如何构建、储存、重建和检索”[42],“也就是说,记忆不只是‘知道’,而且是‘感受’”[43](P.3)。如PTSD的主要症状就包括对创伤事件不由自主的回忆、闪回,为了防御这些记忆带来的痛苦与感受,人们会启动某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机能,采取各种方式如压抑、否认、隔离、选择性遗忘等,但是无论人们使用何种方式防御这些创伤,“我们只能坚持这个事实,即过去被保存在心理生活中,与其说这是个例外,不如说这是规律”[44](P.78)。现代医学对PTSD生理机制的研究也证实:创伤发生后与记忆有关的前额叶、杏仁核、海马等脑区的功能可能发生可塑性变化,同时由于“残存的灾害记忆不仅会决定个人的生活方式,在集体记忆的情况下,也会决定社会整体走向,以致成为文化。”[45]因此“人类到底应该记住什么?”成为一个问题,“记忆系统的生存价值是很显然的,这些记忆的内容帮助个体适应他所居住的特定世界”[46](P.67),为了有利于大脑以缓解创伤、疗愈创伤的方式记忆创伤,也为了趋利避害,保护和促进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文化会对记忆进行建构,帮助个体不仅记住过去发生了什么,也记忆灾难带来的教训与意义,因此也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灾难记忆呈现出明显的伦理倾向。
记忆是被建构的,人们绝不是被动地记录着过去,而是在记忆中积极地重建过去。灾难记忆的伦理性首先体现在关于灾难的主流认知与记忆被赋予了积极崇高的意义。“对悲剧性损失和急剧变化寻求解释和意义是灾难研究关注的问题”[1],虽然创伤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但是它也为人们提供了意义发现的机会。意义发现就是个体从创伤或不幸等消极生活事件中发现个人的、社会的、心理的以及精神上的益处的一种认知和行为应对过程。作为一种应对方式,人们试图弄清楚事件发生的原因、目的,或者试图去理解它对生活的意义。心理动力学和存在主义理论家认为,寻找创伤性事件的意义是一个健康的过程,它可以引导人们对创伤获得某种控制感,并将这一经历与对自身的认识相结合。通常,能够理解灾难事件意义的人,患PTSD或者其他长期情绪问题的可能性较小,神经解剖学的研究也发现,“灾难性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创伤应激源,可能是由于皮层以及杏仁核对灾难信息赋予一定的意义所决定的”[47]。理解和赋予灾难事件意义的人也能够更快走出创伤的阴影,获得创伤后成长。
灾难记忆的伦理性还体现在帮助社会成员承认在创伤之上治愈力量的存在,进而将与灾难有关的记忆进行正面转化。“在文化里,灾难被描绘成净化剂和新生事物的推动力,因此几乎是受欢迎的,而非被阻的。”[48]这一转化不仅是记住灾难,也是为了化解对灾难的恐惧、修复受损的心灵与社会,促使人们在灾难、死亡的话题中反思生存境遇,追问生命意义;黑死病之后的“欧洲人对这场死亡的体验是前所未有的,人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劫后余生者从他人的死亡恐惧之中,唤起了对自我生命存在幸福的追求和对生之权力的百般珍惜。”[49](P.199)当人们带着浓浓的忧患意识发现生命意义、传承灾难记忆的时候,往往会超越灾难给个体带来的心理冲击、生活变化等,直面灾难的客观存在,立足于家园重建与抗灾复兴,将灾难书写、记忆为一部生存和发展的奋斗史,一部心灵救赎史。
(二)纾解负性情绪的文化仪式供给
在灾难应对过程中,文化提供了包括仪式、民俗等在内的一系列工具。其中,仪式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为应对灾难及其影响提供了独到的视野。对仪式作为疾病治疗、情绪调节等的工具和效果的肯定虽然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但是在意义和内容表达上却有着不同的民族背景和地方性知识系统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仪式,并在先秦时期就从单纯的仪式行为,发展出内涵更加丰富的能够表达思想、组织社会的工具“礼”,这些仪式包容、支持着灾难事件的经历者,为他们创造了安全、理解、容纳的环境以让来访者充分表露、领悟其被压抑的情绪。以哀悼仪式为例,所有的经典著作也都确认了哀悼在解决创伤性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完成哀伤的正常过程,哀伤将永远存在,“未解决或不完整的哀悼方式,将造成在创伤过程中的停滞和羁绊”[50](P.64)。就灾难相关仪式而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不少灾后禳除的仪式,如旱灾时举行的雩祭、雨水过多的止雨仪式、灾荒年举行的行荒礼、震后“赦天下”“禳鬼神”“安抚州县”等,不少仪式到今天依然还存在。王田在其文中描述了羌族今天依然会举行的求雨仪式:“一路上,求雨的浩荡队伍敲锣打鼓,沿途十多个村落均会响应并要在海子附近鸣枪放炮,呐喊声震天。当地人讲,每次求雨无不灵验,都会得到甘霖”[51]。
人类历史上因为灾难带来的社会恐慌与心理创伤见诸各个历史阶段,从未停歇,虽然克己、中庸、妥协的情绪表达模式在灾难发生时有积极的功能,但是长期的情绪表达抑制对身心健康的危害也是客观存在的,会引发各种症状。针对这些症状,社会对待疾病的传统仪式也被延续下来,巫医就是其中之一,并成为中国医学的起源,陈邦贤《中国医学史》提及:中国医学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立。《解诂》云“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52](P.270-271),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常常被称为“祝由术”。“祝”者咒也,“由”者病的原由也,祝由术是包括中草药在内的、借符咒禁禳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在庄重的仪式中,受人尊敬拥有权威的巫师通过药、咒、法术、催眠、暗示、激发等手段,让病人相信自己的病是由于特定的鬼神作祟,在巫师象征性地祈求某神的原谅或驱使某鬼遁逃的过程中,病人内在的防御机能被充分诱发,因生病而产生的忧郁、恐惧、焦虑、无助、不安等情绪在不知不觉间得到了纾解。这些做法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其发挥作用的机理是通过特殊的手段和方术,在人的生理、身体、心理之间建立起特殊的联结。在今天看来,虽然在形式上可能有些荒诞,但是在医疗不发达的古代,这些做法能让人在心理上得到安慰,进而增强他们战胜疾疫的信心,诚如医学界广为流传的那句“有时治愈,常常缓解,总是慰藉。”
就应对灾难而言,仪式不仅可以减轻紧张、恐惧、疑惑或痛苦,还可以加强社会联系与整合,增进人们互信维护,强化人际纽带,激发邻里间和社区内相互协作与救助的潜能。借助仪式人们在特定的节日、纪念日等定期开展纪念活动,促进人们的表达、阐释、反思与升华;通过遗迹、遗物、遗址、场馆等铭记灾难,提供载体与机会,给悲情与哀伤以宣泄、给情感以追忆、给丧失以哀悼、给思念以寄托;借助仪式也告诉人们要节制悲伤,并顺应自然法则以应对生活中的重大变故,“节哀”“顺变”,妥善收藏心中的哀情,缓缓恢复心灵的平衡与和谐,重申生活继续下去的主题;借助仪式,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变化和境遇中,传递关爱、表达情绪,沟通过去与未来,改变与重构人的价值观念等,这种借助仪式来缓解焦虑、减轻压力、释放情绪、获取力量的方法延续千年而不灭,即便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代,这些文化痕迹依然或多或少存在并被人们所需要。
(三)增强心理弹性的创伤叙事
创伤性经历通常潜伏在潜意识之中,却又常常以不同的方式重现在创伤影响者生活中,干扰着他们的情绪,隔离着他们与外界的连接;叙事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赋予个人经验以连贯意义的表达、理解、体验、诠释,原创性和象征性的诗歌、艺术、劳动等是实现连接、通向超越性存在的最切近路径。创伤叙事关注创伤性事件对个体、集体及人类心理和身体带来的影响与体验,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与治愈功能被整个社会及民众所需要,它通过写作、讲述、阅读、舞蹈等言语或者非言语的表述对创伤事件、经历、感受加以描述和再加工,提供了一个理解创伤、重塑自我、重构过去、构想未来的渠道与框架,帮助个体保持自我同一性与整体性,获得存在确定性与连贯的意义,成为恢复心理平衡、疗愈精神创伤的特效药。
文化的书写与传递模式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成为人们筛选和应对意外事件的格式,不管它考虑事实与否,但呈现出的灾难图片和故事确实能做到这点。人们用他们提供的模版重视或漠视或重新调整事实。确实,当一个意识模式和现实碰撞的时候,往往是这个模式获胜而非事实”[48]。
在中华传统以文化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文化核心的影响下,中华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灾难叙事文本参照,譬如诗歌、小说、传记、散文、曲艺、美术、民歌、民谣等书写载体,并且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影视、广播、报纸、展览、主题晚会、互联网等也加入到灾难书写的行列。这些不同的书写载体,贯穿着中华文化创伤叙事的文本特征,帮助人们意识到经历灾难或创伤后会产生普遍性的身心反应,进而通过其营造的审视距离与空间感,将人们从遭遇灾难事件所产生的焦虑、痛苦等负面情绪中抽离出来,避免沉溺其中,从而保持适度的理性。“这本小说出版后,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时常想起集中营生活了:它已经变成了我的主人公的经历”[53]。在阅读、观看这些表述的过程中,人们感同身受地加入灾难表述之中,宣泄痛苦、感受灾难,并通过这样的叙事让人们看到困苦艰辛是一种自然规律,在尽可能坦然面对与接纳创伤的同时又不失希望与力量。灾难的中国式书写在整合创伤自我与现实自我,缓解症状、抚慰心灵、疗愈创伤、超越创伤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功能,让个体的经历、情绪、感受等获得尊重、被倾听、被看到,创伤者将潜意识创伤外化,上升到意识层面,将内在记忆转化为外在现实,恢复与外界的联结。诚然,这种叙事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遗忘和放弃独特个人经历和自我体验,就艺术创作而言可能是一种遗憾,然而这样的创伤叙事模式对创伤的抚慰和疗愈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成为增强心理弹性的有效路径。
既然人类与灾难相伴而行,无法逃避,唯有面对与抗争,而人们在记录灾害带来危害与苦难的同时,也发挥着叙事的社会功能:积极引导舆论,疏导公众情绪,传递集体记忆,发展出共享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规则,并经过锤炼、升华形成属于一个民族的精神谱系。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数不胜数,如抗战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洪抢险精神、抗疫精神等无不是在经历各种灾难之后凝练而成,这些“结晶于上下5000年沉淀在人们心灵河床之上,蕴藏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之中”[54]的中华民族精神,正是中华儿女面对各种灾难同心同德、守望相助、坚守梦想、不懈奋斗、团结一致的思想根基,而面对灾难的精神转化,不仅为个体与民族提供了宣泄苦难、疗愈创伤、重建精神家园的理想途径,其在创伤康复过程中体现出的韧性、能动性等也是应对灾难的动力和支撑,更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结语
灾难与人类发展过程紧密相联,在与灾难同行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应对心理创伤的文化机制,强调和重视这一文化资源,“是由文化对于人类生存适应与灾难创伤复原功能的本质所决定的。”[37]将心理创伤与广泛的社会情境、文化环境相联系,提高大众对文化中心理疗愈资源的了解与认知,为人们应对灾难、减轻痛苦提供多元化资源,是促进大众心理健康素养提升的有益选择。将灾难经历者放置在一个真实的文化语境之中,能够看到自己身上蕴含的文化应对资源,在增强文化认同感、归属感与文化自信的同时,维系个体与生活的深度连接,并朝向心理创伤疗愈的终极目标:重归生活及超越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