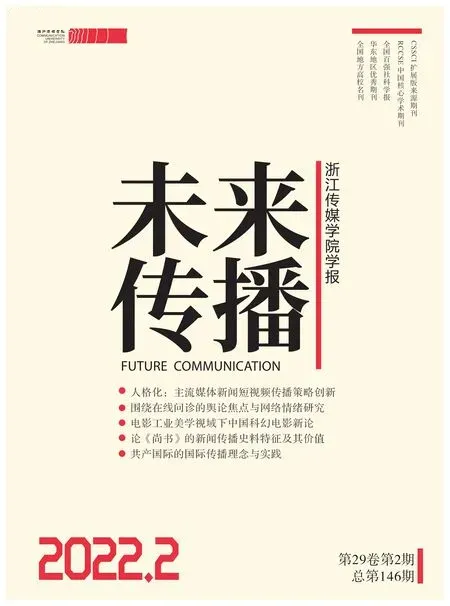想象力消费:电影工业美学的延伸
2022-11-23李玥阳
李玥阳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24)
2019年,在电影《流浪地球》上映之后,陈旭光在《中国电影蓝皮书2019》和《类型拓展、“工业美学”分层与“想象力消费”的广阔空间——论〈流浪地球〉的“电影工业美学”兼与〈疯狂外星人〉比较》等文章中提出,科幻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的软肋,但是以“《流浪地球》为标志,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时间,开始了。”[1]这种新时代不仅在于《流浪地球》开启了电影高度工业化的新前景,并且赋予电影工业一种难得的硬科幻的想象力。与此同时,《疯狂外星人》拒绝复制好莱坞,致力于走一条本土科幻之路。在这里,电影工业美学发生了“分层”,进入到想象力消费的新时代,这种想象力包括科幻、恐怖冒险等多个层面。此后,陈旭光等人又在更多面向展开对“想象力消费”这一概念的理论思考。在《论互联网时代电影的“想象力消费”》一文中,陈旭光梳理了西方文艺理论中关于“想象力”的论述,并提到中国“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思想,以及1949年以后借鉴苏联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想象力的发生。文章特别提到了互联网时代“想象力”的特别之处:“互联网时代的后想象力大多表现为‘拟像’的仿造(counterfeit)、生产(production)之后的仿真(simulation)阶段,成为完全没有现实摹本的超现实拟像。也就是说,同样是‘想象力’这个术语,后人类、后假定性、拟像时代的想象力,其内涵特征与现实主义甚至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均有很大的不同”[2]。而受众对于这种想象力的接受也将具有时代特征,是一种复杂的消费行为:“我们也可以说,‘想象力消费’既是一种艺术审美消费,又是一种经济消费,因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文化经济消费。”[2]
应当说,“想象力消费”提示出中国影视正在浮现的重要现象,即旧有的以现实主义为主要诉求的文艺范式正在发生的转型与巨变,当下在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占据主导地位的并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另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思潮。就电影而言,对于这种新范式进行理论思考与阐释,将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新美学形态的浮现,与媒介技术的变革息息相关,中国电影在多年来提高工业化水平的急切召唤之下,全新的电影形态是媒介变革、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结果。这与“电影工业美学”的发展一脉相承,一如陈旭光的分析,是电影工业美学进一步发展、分层的结果。换言之,“想象力消费”概念的提出,是电影工业美学在新时代的全新延伸,对于这次文艺形态的转型的成败与未来影响,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观望、考察与分析。
一、“想象力”:现实主义的超越
“想象力消费”这一概念在最显在的层面上,是对中国电影现实主义范式之“转型”的回应。这种反思基于一个事实,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电影的“想象力”是以现实主义来加以限定的,即使是无法以现实主义来阐释的现象,也会在现实主义中谋求存在的合理性。例如,1949年以后对“鬼”的接受,曾经历了长时间的论争与重构。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们便展开了对《红梅记》“鬼戏”改编本的探讨,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反映论中展开。支持者大都认为,鬼戏和神话属于同一个性质。鬼魂形象仍然“是人和人世间现实斗争的反映”,[3]对于那些宣扬迷信的,应该批判继承。这是将鬼戏作为现实斗争的反映。80年代《红梅记》的改编戏曲《李慧娘》重新上演,支持者的论述基于同样的逻辑:“鬼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宣扬封建迷信,因果报应,愚弄人民,恐吓人民,这样的鬼戏是糟粕,应该消亡。……还有一种鬼戏,为受压迫者鸣不平,鼓舞人们的斗志,说出人民的愿望,在善与恶的斗争中,站在善的一方面,在美与丑的斗争中,站在美的一方面,这样的鬼戏,在在社会主义舞台上,应该有一席之地。”[3]也就是说,鬼戏可以是现实生活中被压迫者和人民愿望的反映,并因此拥有存在的合法性。
与之类似,既往带有幻想倾向的电影都带有强烈的现实诉求。1958年著名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是20世纪5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幻想类电影。但与其说这是一部“科幻”电影,不如说这是一部乌托邦式的畅想社会主义未来的电影,它基于幻想,却落脚于现实。影片中对于天气的控制,结尾处长满瓜果梨桃的大树,都是对社会主义技术进步前景的良好预期。彼时现实中创造的奇迹,如在雪山上试验种青稞,使雪山有了植物,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注脚。这种现实主义范畴中的幻想来源于“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多重性。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梳理了“现实主义”的不同含义。在通常的意义上,现实主义的题材是“平凡的、当代的、日常的”,与英雄和浪漫传奇相对。而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定义,给现实主义带来了根本性影响,“典型”不能混同于常见的人物,现实主义也不再是对现实的直接复制,而是变成了“有原则、有组织的选择”,这就包含了“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前景的理解”。[4]也就是说,在现实主义这一能指之上,既包含着反对浪漫传奇的“当代的、日常的”的现实主义,又包含着充满浪漫想象的“未来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主义,它们在不同层面构成对立的关系。50年代末期“科学文艺”最活跃的时期,也是现实主义讨论最激烈的时期。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中国不由惊叹,对未来的幻想已经变成了眼前的现实。继而,中国文艺界展开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激烈论争,这一论争以《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为导火线,核心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否能彼此脱离。[5]1958年,毛泽东在讨论新诗时,提出了另一种说法,即“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6]可以看出,在新中国现实主义的探讨中,始终包含着超越现实主义的冲动与可能性。
这种在现实主义范畴中,尝试超越现实主义的倾向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彼时带有幻想元素的电影仍然没有跳出现实主义的限定,如《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以及更晚近的《霹雳贝贝》(1988)等。《珊瑚岛上的死光》在发达现代科技,乃至科幻的外表下,却只是讲述了一个极富现实感的可怕未来——剧中神奇的“激光器”像是核武器的复制品,电影所讲述的正是核武器被坏人利用所引发的恐慌。更晚近的“第一部儿童科幻片”《霹雳贝贝》则讲述了一个有特异功能的带电的孩子,他是外星人与地球人的结晶。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科幻电影的元素,超能力、外星人等。但外星人只在片头序幕一闪而过,贝贝的超能力也与日常生活中的“特异功能”十分相似,整部电影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的轨迹。
以上述事实为前提,“想象力消费”向我们昭示出现实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新世纪的文化艺术发生了不同既往的转变,有了全新的趋向。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媒介变革,VCD机横空出世,一系列电影作品通过全新的媒介进入中国,如《午夜凶铃》《夺宝奇兵》《古墓丽影》。这些电影所携带的盗墓、恐怖题材不同于中国本土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是带有传奇或罗曼司的特征。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中国也掀起了恐怖盗墓影视热潮。此次恐怖盗墓影视剧的叙事方式已经跳出现实主义,与本土神怪武侠传统相结合,形成不同以往的影视潮流。同时,以2019年的《流浪地球》为明确的标识,国产硬科幻电影也被创造出来,接下来的一系列电影《疯狂外星人》《重启地球》《平行森林》等,更是对国产科幻影片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推进。总体而言,无论是科幻题材,还是玄幻、盗墓、恐怖推理题材,新世纪的影视剧都发生了结构性转型。这些作品不仅是传奇式的、幻想的,同时也是带有赛博格倾向的,它们无法再以“发展规律和前景”来阐释,既往的现实主义不能囊括这些作品。在这个意义上,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来赋予其意义,而“想象力消费”则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阐释的维度。
二、“想象力消费”与外来影响:罗曼司、虚构文学与黑色电影
从上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中国的电影来看,无论是《古墓丽影》《夺宝奇兵》还是《闪灵》都在更大的范畴内倾向于幻想、虚构类的电影。一如陈旭光所说,所谓的“幻想”不只包括科幻,还包括更广阔的面向。陈旭光将其概括为“想象力消费”的四种形态,包括“超现实的、假定性美学和寓言性电影”“玄幻、魔幻类电影”“科幻类电影”和“影游融合类电影”。[2]这一判断无疑是敏锐的。在90年代外来电影的影响下,中国电影出现了较早的恐怖片习得之作,如阿甘导演的《凶宅幽灵》(2002)《闪灵凶猛》(2001),文学领域也出现了周德东、蔡骏等模仿痕迹较重的早期恐怖小说,此后涌现的盗墓题材小说和影视剧也受到这一脉络的影响。
这一电影文化可以上溯到中世纪罗曼司传统。董雯婷曾在《西方文论关键词:罗曼司》一文中进行概念的追溯,认为罗曼司作为一个中世纪的文化现象,更倾向于指代一种口头流传的故事,内容包括神话、历史、武功歌、基督教文学、民间故事、童话等作品。这种故事与历史写作相对,董雯婷引用了格伦(D.H.Green)在《中世纪罗曼司的开始:事实与虚构,1150—1220》中的论断:“中世纪早期的七十年“欧洲文学传统呈现出一个转向,从明显倾向于历史写作,到倾向于虚构叙事,最充分的例证就是罗曼司的模式。”[7]这也正是在区分“写真实”的历史写作与虚构故事的不同思路,即一种“有意识的虚构”。董雯婷继而梳理了罗曼司此后的发展和转变过程,指出罗曼司超越现实的特征,在18世纪以后慢慢转化成虚构小说(Fiction),包括此后影响深远的哥特小说等。[7]对于这一问题,著名的“克苏鲁神话体系”创世人,美国哥特(恐怖)小说家H.P.洛夫克拉夫特在其西方哥特小说简史的研究中做了更具体的论述。洛夫克拉夫特认为,这一传统在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时期,是“对神学可怕的颠覆和对魔鬼撒旦的崇拜”,此后恐怖幻想文艺中常见的意象,如“那些要求入土为安的尸骨、将他活着的至爱带走的魔鬼情人、死亡恶魔……紧闭的卧室、不死的巫婆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神秘的中世纪遗产里找到影子。”[8]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传统不断拓展,并催生了“描写恐怖和异想天开的散文——哥特派的诞生”[8](123)。在哥特小说的末期,出现了经济学家威廉·歌德温的恐怖作品,如《圣·里昂》。而歌德温的女儿,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则完成了从哥特小说到科幻小说的重要转变。她在哥特小说的余韵中,写出了那部被命名为文学史首部科幻小说的《弗雷肯斯坦》,成为此后不断被重拍的科幻电影重要题材。应当说,诸多后来在新世纪中国电影中出现的主题,已经在欧美从罗曼司到哥特、科幻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具备了本土的原初形态,如《奥特朗图城堡》《乌尔多夫城堡的秘密》中的哥特式古堡,《鬼船》中永远不会停航的鬼船,霍桑《农牧神的大理石雕像》《七堵山墙的房子》、爱伦·坡《鄂榭府的倒塌》中那些闹鬼的、被阴霾笼罩的古老别墅或宅院,以及玛丽·雪莱《弗雷肯斯坦》中耳熟能详的科学怪人。这些意象在20世纪初期好莱坞类型片形成的过程中被电影化,在20世纪20年代环球影业公司建构的恐怖世界中,僵尸、古墓、吸血鬼、狼人,都是上述文化的电影形态。这一外来影视文化在90年代中后期以院线或碟片等方式进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旧有的现实主义格局,转变为中国电影中的鬼宅、荒村、孤岛,并经过中国科幻电影的艰难酝酿,在2019年催生出《流浪地球》等中国科幻大制作电影。
在哥特文化之外,同样在新世纪影响中国电影文化的是介于“哥特式恐怖片和敌托邦科幻片之间”[9]的另一种电影类型——黑色电影。而黑色电影同样来源于哥特文化,在通常意义上,黑色电影被认为是发生在美国的、“硬派小说和德国表现主义综合的结果”。[9]无论是以钱德勒为代表的硬汉派推理小说,还是深受哥特文化影响的德国表现主义电影,都可以看到以推理、惊悚悬疑为主要特征的黑色电影,与哥特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而当下影视剧中带有“黑色”色彩的不在少数,刁亦男《白日焰火》、爱奇艺“迷雾剧场”《无证之罪》等,都与这一脉络有关。
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已经发生,并在当下中国形成独具特征的影视形态的这种新趋向,确乎是一种“想象力的转型”,这一转型并不能在中国本土的文化中被阐释,而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此轮影视文化中“想象力”的发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极大改写了中国影视文化的旧有形态。陈旭光“想象力消费”的论述,及这一概念所尝试囊括的较广泛的范围,都成为进一步探讨的可能起点。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外来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中国“幻想”影视剧并非亦步亦趋模仿外来电影,而是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渐趋形成基于自身文化的本土特征。这些本土特征还造成中外观众在相同电影文本上的不同接受过程。凡此种种,都使得“想象力消费”的提出更像是一种全新探讨的开端,其包含的不同层面和广阔范畴都需要在进一步探讨中不断细化。
三、“想象力消费”:媒介变革与电影工业美学
陈旭光对于“想象力消费”的思考是建立在电影工业美学的基础之上的。陈旭光对于“电影工业美学”的讨论是在“电影产业化”多年历程之后,对“电影工业”这一命题的再度回归与重申。如果说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电影产业化进程,将电影放置在“第三产业”,以凸显电影娱乐产品的功能,那么“电影工业美学”(也包括饶曙光重工业电影美学)则再度强调了电影作为工业产品的层面,强调了电影作为“重工业”的可能性,以及工业向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向——凡此种种,都涉及“媒介”问题。2018年,陈旭光在阐述电影工业美学概念时,一方面将电影视为拒绝精英主义的“常人的美”,同时又拒绝仅仅以产业和市场等非艺术的观点看待电影。这种美学强调一种调和式的美学建构,“从切实的现实问题出发,在日新月异、风云变幻的中国电影场域内发现问题、联动产研、沟通上下,进行一种‘中间层面的研究’。”[10]彼时的讨论更多在工业和商业化的层面上。而此后的“想象力消费”则囊括了“工业”这一概念所无法覆盖的部分,它更多着眼于后工业时代的数字和虚拟经济及新媒介的涌现。在此,媒介的更替与融合成为想象力消费的重要面向,这也正是陈旭光在影游融合、VR、拟像等问题的探讨中试图传达的。
事实上,上文所探讨的世界范围内的“想象力转型”,尽管以罗曼司与哥特传统的再度勃兴为表象,但其深层驱动力还是要回到媒介变革这里。例如,被誉为“赛博朋克”科幻小说奠基人的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1984年开始创作对电影《黑客帝国》影响深远的赛博格三部曲,第一部便以“新罗曼司”为名(Neuromancer)。[11]这部小说讲述了一群“电脑牛仔”放弃躯体,进入赛博空间的故事。此处的“新罗曼司”强调的不仅仅是罗曼司的复制,而是强调全新媒介的登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新想象方式。在中国发生的转型同样如此。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中国、并引发中国“想象力转型”的电影《古墓丽影》,本身便是游戏改编之作,同样包含着媒介变革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想象力消费”较之于“电影工业美学”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海外学者试图思考新媒体与虚拟技术诞生后的美学,如建构一种新型的“数字美学”,[12]陈旭光之“想象力消费”也正是在中国电影的“后工业时代”,探索新美学方案的尝试。
因此,“想象力消费”势必包含着电影本体论的再思考,需要直面电影本体论重构的问题。应当说,电影的“想象力”与媒介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早在世界电影史发端处,乔治·梅里爱在《月球旅行记》《魔术》等电影的制作中,便不断探索电影制片技术的各种可能性。但梅里爱的技术创造,如叠映、停机再拍,仍然基于胶片摄影机的技术限定。也就是说,无论电影中的想象有多么奇妙,胶片摄影机仍然遵循自身的记录特性,摄影机需要现实参照物,胶片感光后形成的影像是不可修改的。因此,梅里爱的“月球旅行”只能在固定镜头中切换或叠映不同的布景。正是在胶片摄影机这种“机械复制”的基础上,电影发展出了巴赞的现实主义美学以及克拉考尔的“物质世界的复原”理论。但在“想象力消费”的时代,电影已经越来越多地借助数字摄录设备制作,电脑数字技术可以随时加入到电影制作之中,某些电影甚至完全由电脑制作完成。电影的发行也依靠数字技术完成,无论是互联网还是院线的数字放映设备。电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计算机软件可以“将摄像机的设定、状态和摄像机拍摄的相关信息集合成数据库,方便后面的数字非线性编辑”。[13]这也就是说,数字的成像技术已经不同以往,它不再依赖于现实中的参照物,并且数字生成的图像也不再是不可修改的,人为介入可以出现在影片制作的任何阶段。而当电影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电影艺术和电影观念也将随之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尝试在数字电影阶段重新阐释巴赞等人的理论,寻找此前忽视的理论面向。但无论怎样钩沉那些被压抑的层面,都只是将胶片摄影机时代的电影观念搬到数字电影时代。它们能够给非现实的“幻想”提供理论资源,却始终不能回应数字时代的幻想与胶片时代的巨大差异。
陈旭光在不只一篇文章中,强调了“想象力消费”之“拟像”的层面,这无疑是具有洞察力的。鲍德里亚谈到复制品媒介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强调了最感兴趣的第三个阶段,即仿真阶段,将这一阶段描述为:“一个你不再谈论复制的阶段——因为复制仍然提示着存在一种讯息——也是现实的一切参照物都销声匿迹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媒介不再是复制现实的一种工具,而是使现实消失的一种形式。”[12](98)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提示出数字电影时代电影观和世界观层面正在发生的断裂——数字电影的“想象力”不仅仅关乎虚构性,不只是幻想或超现实的问题,而是一种更深远的整体性转变。它所涉及的问题将是“后人类”“后人文主义”或者“后电影”。现实已经消失,人文主义最重要的三维空间已经被赛博格的无限时空所取代。摄影机背后的眼睛可以是任何一种人类或非人类的观看。不仅如此,一种没有现实参照物的电影将可能与任何一种媒介融合,在融合过程中,重要的不是现实参照,而是媒介之间的互文性。例如,游戏改编电影已经是常见的现象,但一如约斯·德·穆尔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中指出的,游戏与电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游戏缺少电影叙事的时间层面,游戏玩家处在“永恒的现在”。“你可以用本·拉登或布什总统的形象来代替太空飞船,但是根本不会对游戏产生任何改变。”因此,游戏常常无关叙事或与叙事相脱离,“在大多数冒险游戏中,叙事通常是与游戏本身相抵牾的。”[12](75-77)就此而言,当游戏改编成电影,重要的问题便不是电影与现实参照物的关系,而是与叙事冲突的游戏与作为叙事的电影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垂直的深度模式被取消了,被代之以横向的指涉关系。(这也正是张明浩、陈旭光在《影游融合的“合”与“不合”——论动画电影〈姜子牙〉中的游戏影响》一文中试图探讨的。[14])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既往的电影现实主义理论需要重新思考,电影的幻想理论乃至本体论都需要进行颠覆性的重构。“想象力消费”所提供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可能的探索。全新的想象力是怎样被生产并被消费的,这种生产和消费与8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时代的生产和消费有何不同?这些都是“想象力消费”涉及的面向。
总体而言,作为当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想象力消费”包含着诸多亟待思考和解答的疑问。这个植根于电影,却又超越电影的概念,以电影为起点,同时指向更宏大的层面。与电影相关的首先是“电影是什么”,继而是“我是谁”,以及如何建构我们的身份等等。这个相互递进的追问,需要在层层剥离和反思中深入思考。